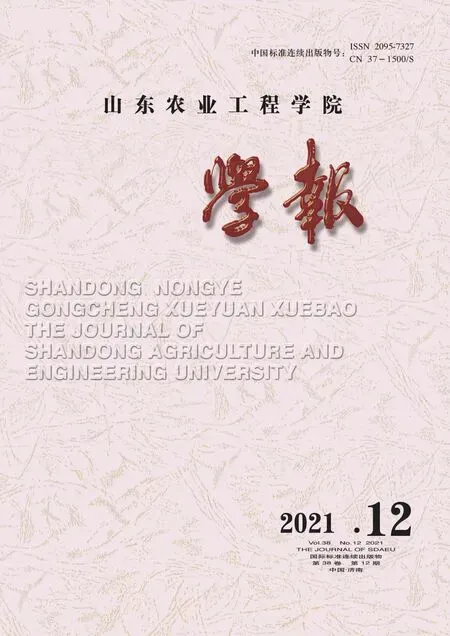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资料翻译策略研究
刘庆连,马 莉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乡村旅游的主要宗旨在于“旅游度假”,是指以郊外村庄作为旅游空间,以“人文无干扰、生态无破坏[1]”为主打宣传内容,希望游客到来后,能够更多地了解本地乡村民情、礼仪风俗,观赏、品尝、购买本地特色农家产品,最终达到增加地方收入,提振地方经济的目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乡村旅游景点必定会逐渐接待更多的外国游客。为做好宣传工作,需基于翻译目的论,做好乡村旅游资料翻译工作。
1 翻译目的论内涵简析
翻译目的论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其一,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翻译理论创始人凯瑟琳娜·莱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提出,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翻译策略互相联系,在传统的原文与译文功能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并发展了翻译批判模式[2]。凯瑟琳娜认为,翻译应该具备综合性和交际性。具体而言,对原文资料进行翻译后得到的译文,在语言形式与交际功能方面都应尽量与原文相同。但在此基础上,译文在实践应用时应该有别于原文,彰显译文的功能特征。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引入外国电影后,均需由专业人员进行二次创作,而大众看到的中文版本实际上都是“译制片”。该类影片的特点为,一群中国专业翻译人员在说中文的过程中,尽量模仿外国人说话的习惯、情感表达方式,使观众看后感到产生十分新奇的感觉——尽管听到的话语都是汉语,但却感觉是在观看外文原声电影。而此种“感觉”便是同时结合了翻译的综合性和实践应用性。
其二,同样是德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的汉斯·弗米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系列讲座中提出了“翻译的普遍理论”,随后整理并出版为《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在该书中,汉斯与凯瑟琳娜共同提出: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过程,更将该将之视为“将一种语言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交集符号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活动,故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而任何一种行为都必须具备一个目的”。至此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翻译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即只有在明确翻译目的的前提下,开展的翻译工作才是有意义的,而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翻译同一篇原文时,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其三,在基于翻译普遍理论的翻译目的性基础上,贾斯塔·霍茨围绕翻译行为理论进行了深度整合,彻底定调“翻译受目的趋势,应具备翻译结果导向”。此理论刚刚提出时,与翻译目的论有诸多相似之处,后来经过汉斯·弗米尔的整理,将两种理论合二为一。
其四,克里斯汀娜·诺德对德国功能学派的所有翻译理论进行综合整理,对翻译过程中围绕“文本分析”应该进行的所有考虑,可能影响翻译结果的所有内外因素、如何在原文功能基础上制定切合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等进行了大量分析,最终得出“翻译者应遵循‘功能加忠诚’的指导原则”,即原文件中希望传达的信息本身在翻译过程中并不应该作大幅度调整,但针对特定的受众,可对翻译模式进行一定的调整。至此阶段,翻译目的论宣告完善。以《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童话故事的翻译过程为例。目前,我国书籍市场中拥有上述两书的多个版本,有完全忠实外文的版本,有适合低龄儿童阅读的版本。必须承认的是,外文原版书籍中,童话故事例夹杂了很多“邪恶”内容,且并不仅仅是恶毒的女巫,更多地体现在主人公的身上。但在儿童版本中,除了女巫等反派角色的少数恶劣行径被简要描述之外,其他角色都没有“恶行”,目的在于帮助儿童建立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支持正义、反对邪恶。
总体而言,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必须具备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忠实性原则、功能性原则。而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必须服从目的原则。
2 乡村旅游资源的内涵和特性分析
2.1 乡村旅游资源的定义
将乡村旅游资料翻译成外文之前,有关人员必须充分了解什么时乡村旅游资源,只有明确此种资源的特性,了解运用方式以及开发此种资源后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能保证翻译后的资料具备实用价值。具体而言,乡村旅游资源是指能够吸引旅游者前来进行旅游活动,被旅游业充分利用,在此过程中产生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的“乡村景观客体”。构成乡村旅游资源的要素分为两部分:其一,基础部分,即自然环境。如果没有自然环境的支撑,则乡村旅游项目几乎无法吸引游客;其二,发展部分,即人文因素。与常规的风景名胜区不同,在乡村景致中,“人类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则乡村便无法形成。基于此,乡村旅游资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下产生的文化景观,可视为大自然、物质、非物质等要素组合而成的和谐乡村地域复合体。
2.2 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分析
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具备如下特性:
(1)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乡村是人类生存的场所,早在城市之前便已出现。一般而言,当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生态学的原理,明确人地协调关系的重要意义之后,大自然便会给予人们恩惠,进而促使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如果相反,人类过度攫取自然资源,使自然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则大自然便会惩罚人类。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下,逐渐认识并掌握了自然规律,故我国现代乡村旅游资源处处彰显“和谐”。
(2)资源类型多种多样。尽管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深度发展时期,但党和国家没有一刻忘记乡村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聚焦三农问题,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最终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广阔的乡村范围内,“农”具备广义性,指代“农”、“林”、“牧”、“副”、“鱼”,因此,乡村旅游资源包含农村、牧村、渔村、林区等多重景观,集中了镇、村落等多种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据罗警官。除此之外,我国幅员辽阔,各族人民的传统文化、民族风情都得到了完整地传承,故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也使得乡村旅游资源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总体而言,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具有时代性、统一性、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璀璨历史的一种现代缩影。因此,将乡村旅游资料翻译成外文时,翻译人员必须明确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角度,在保留资料源文含义大致不变的情况下,使外国读者同时了解历史上的中国乡村和现代中国乡村,激发其“前来中国实地游览”的兴趣,在达到文化宣传的目的之后,促进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3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资料翻译原则
3.1 乡村旅游资料翻译过程中面临的困难简析
3.1.1 不同语言文化背景导致的思维理解差异
将乡村旅游资料翻译成外文的过程中,翻译人员面对的首个困难为不同语言文化背景导致的思维理解差异。比如提及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营造出的璀璨文化盛世令人无限向往;到了汉代之后,尽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其他流派日渐衰微,但传承并未完全中断;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怀着救亡图存的理念,广泛学习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最终成就了如今的中国。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核心精髓可用两个字进行概括“包容”。中国文化是广义的,能够接纳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中的正确支出纳入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摒弃其中不符合中国国情以及与人类生存发展背道而驰的错误观念。导致中国文化最终形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传承从未断档。而外国则不同,同为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的文化传承早已中断;而在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中,充满了零和博弈的思维。受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影响,很多外国读者对一些词汇的理解与中国人是不同的。比如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希望与全球各个国家共同努力,早日使全人类都过上好日子。但令人遗憾的是,美西方国家仅仅从“实力”视角考虑问题,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导致的理解差异之外,中西方对特定事物的理解和叙述也存在差异。比如我国很多乡村地区都留有结构相对完整的古代庙宇(如城隍庙、灶王庙等),将描述此类建筑的语句翻译成英语时, 如 “前殿”、“后殿”、“仪门”、“明堂”、“照壁”等词汇,在外语中没有对应的、可直接进行转换的词汇。而如果将“前殿”、“后殿”等词汇直接以“a house”的形式进行翻译,则无法凸显我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而如果以汉语拼音形式表示上述词汇时,西方国家的人民由于从未接触过“城隍庙”等乡村旅游景点,故面对“Qian Dian”之类的直译词汇时也无法完成有效理解。
3.1.2 地域文化造成的生活习性差异
尽管同处一个地球,但由于生活地带存在经纬度的差异,由此形成的生活习性差异也影响乡村旅游资料的翻译效果。如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吕宜莹等人在研究报告中提到:英伦三道位于大西洋东海岸,常年受西(海岸)风影响,故该地区夏季温度适宜,十分适合度假,而英国人也普遍将“夏季”作为描述美好事物的形容词。比如莎士比亚便将其爱人比作“a summer’s day”。 但在东半球的中国,描述风向时并不习惯使用 “东、西”作为主形容词,而是以“南、北”为主,在此基础上增加“东、西”前缀,形成“东南风”、“西北风”的形式。基于此,受地域影响,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习性差异也体现在对词句的描述上,如果在翻译乡村旅游资料时忽略这些差异,则会令其他国家的读者产生“明明认识某个词语,但却无法理解其含义”的困惑。
3.1.3 风俗习惯导致的信息传达差异
实际上,风俗习惯作为文化的一种具象形式,也经常导致翻译信息的传达过程受影响。比如在东西方餐饮文化方面,西方长期以来实行“分食制”。如两人以上吃西餐时,往往根据人数,点对应份数的牛排、汤品、甜点等,每一个餐具都只能由一个人使用。但中国(特别是乡村地区)的饮食文化非常注重“热闹”,强调“同食分享”,即菜品由大号的盘、碗、盆等盛装,放置于餐桌之上后,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筷子夹取食物。翻译人员在翻译我国乡村旅游景点的 “进食景象”时,如果忽视对中国餐饮文化中“看重热闹”部分的描述,则西方人民会感到不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议”,并认为中国人缺乏卫生意识。一旦因此对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留下了较差的印象,则翻译宣传工作必定受到影响。
3.2 基于解决困难考量的乡村旅游资料翻译原则
3.2.1 适当“增译”或“减译”原则
我国翻译界有一项共识,即翻译的内容必须同时达到“信、达、雅”的要求。通俗而言,翻译而成的译文与源文相比,其中传递的信息必须保证准确,在此基础上,读者经由译文获得的主要信息必须在原文之中能够找到对照之处,此外,针对一些特定的词汇进行翻译时,应以译文受众能够接受的语言词汇进行对照。以我国乡村旅游资料为例,在宣传灶王庙时,为了使外国(以英语系国家为受众)人民更加清晰地了解此种旅游资源,翻译人员需要对“灶王”进行解释,并介绍中国古代老百姓拜灶王的目的——希望辟邪除灾、迎祥纳福。当翻译人员增加对有关信息的介绍之后,目标受众必定能够更好地理解。与“增译”对应的是“减译”,主要针对一些特定语言中的描述词汇。比如某乡村旅游景点的主打资源为民间戏台,中文描述句式为“戏台是单檐歇山顶,藻井呈鸡笼形,雕龙画凤,朱金装饰,远远看去,熠熠生辉[3]”。其中的“雕龙画凤、朱金装饰”等词汇翻译成外文之后,不仅十分拖沓,且汉语原意也会被大幅度曲解,显得不伦不类,因此,翻译时可直接以“精美(exquisite)”一词代替即可。
3.2.2 句式构成方式调整原则
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通病为:按照句式组成顺序机械翻译。比如舟宿夜江的介绍中提到:“此地史称‘周宿渡’,古时是个渡口,曾是古代内河进入宁波城的必经要道[4]。”如果按照汉语思维进行直译,得出的英文句式为 “This place is known as ‘zhou su du’ in history.It was a ferry in ancient times.It was once a necessary route for inland rivers to enter Ningbo City.”对照之下可发现,一句连贯的汉语被“肢解”成了三句看似相互独立的英语,失去了连续性的同时,还显得索然无味,对外宣传推广的作用必定大打折扣。正确的翻译原则为,翻译人员应该明确英语句式构成的习惯,即将时间形容词放在句首或结尾,使形式主语的描述更加顺畅,比如“In ancient times,it was a ferry station called ‘Zhou Su du’and was an important passage to Ningbo city by the waterway system[5].”顺畅性十足。
4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资料翻译方法
4.1 直接音译法
翻译目的论强调,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应该尽量避免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如上文所述的我国20世纪90年代外国译制片的制作过程,配音演员以外国人说外语的习惯说中文,并在称呼姓名时直接沿用外语称呼。此种直接使用的“源文”的音译法呈现在中国观众眼前时,自然会形成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明明是在看外国电影,感受到的是外国的文化,但入耳的语言却是一种既熟悉有略感新鲜的汉语。实际上,此种直接音译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将之应用于乡村旅游资料翻译时,也能产生十分良好的效果。
4.2 忠实资料源文的顺势翻译法
顺势翻译法实际上是直接音译法的一种特殊类型,注重部分特殊的翻译内容应该忠实资料原文。比如上文提到的“舟宿夜江”乡村旅游景点中,其中一个渡口为“周宿渡”,翻译时直接使用汉语拼音代替即可,而不是采用“Zhou su ferry”的形式。此外,如果翻译人员制作音频宣传资料,则在配音“周宿渡”时,不应参照外国人说中文的方式(分不清声调),而是将汉语普通话的“周宿渡”发音清晰吐出,从而使外国人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乡村旅游景点的信息。
综上所述,为提高乡村旅游资源的对外宣传水平,翻译人员首先应该明确翻译的目的——使中国月薪日益且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景致逐渐被外国人熟悉,令其能够正确理解,进而产生“来中国乡村看看”的想法。以此为基础,翻译成的外文语句同样应该遵循“信达雅”的标准,抓住宣传重点,去除外国人不易理解的华丽形容词藻,尽量降低文化差异的影响。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