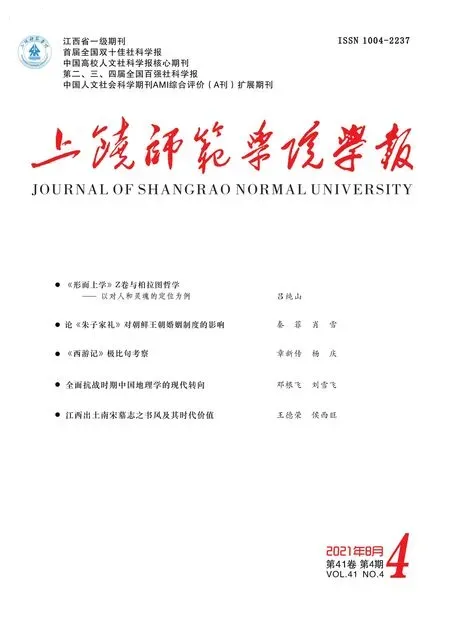《形而上学》Ζ卷与柏拉图哲学
——以对人和灵魂的定位为例
吕纯山
(天津外国语大学 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天津300204)
一、柏拉图论人和灵魂
(一)柏拉图对人的定位
柏拉图在《理想国》③中译本参考: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岳麓书社,2010。参考的希腊文本是:S.R.Slings,Platonis Re mpvblica m(Oxf or d:Oxf or d University Press,2003)。507b中这样描述理念:“我们说存在很多美的东西……而我们又说有一个美自身(αὐτο`καλο`ν),有一个善自身(αὐτο`ἀγαθο'ν),以及同样,关于一切我们在前此把它们当作是众多的东西来看待。现在,反过来,我们都把它们置于和它们每个相应的单一的理念之下(πα'λινακατ̓ ἰδε'ανμι'ανἑκα'στου),因为这理念是单一的,我们说它们每一个就是存在(ὁ`ἐ'στιν)。……而一类东西,我们说是能够被看到,但是它们不能被思考,而反过来,理念能够被思考(τα`ςαἰδε′αςνοεῖσθαι),但是它们不能被看到。”在柏拉图那里,所有的理念都是一个个“自身”(το`αὐτο`),“每一个在自身中都是一(αὐ το`ἑ`νἑ'καστονεναι)”(《理想国》476a)。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的理念(εδος/ἰδε'α,for m)④出于尊重学界传统,也为了区分术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的不同含义,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我们把柏拉图的ε͂̓ιδος翻译为“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翻译为“形式”,二者的英文翻译都为for m;在类的意义上,我们都翻译为“种”(species)。,就其根本而言,是不同于众多可感事物但与其相似的独立而分离的存在物,它根本上是一类可感事物的种概念(εδος/ἰδε'α,species),是他所追求的“是什么”的确切对象,与众多的可感事物相对,是理智的对象、知识的对象。它本身作为类概念,同时又是一个个“X自身”,亚里士多德后来评价理念既普遍又个别,就是在作为类概念却分离存在的意义上而言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柏拉图理念,多是伦理学概念,如善、正义、节制、勇敢、智慧、虔诚、美等,还有如知识、德性、描述,以及相等、相似、静止、运动、大小等。
那么,柏拉图的“人”是不是理念呢?他本人的观点前后并不一致,似乎有一个从把它归入与理念相对的可感世界,到怀疑,并最终肯定是理念的发展过程。在《斐多》①中译本参考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8;希腊文本参考:E.A.Duke,W.F.Hicken,W.S.M.Nicoll,D.B.Robinson,J.C.G.Strachan,ΦΑΙΔΩΝ,in Pl atonis Oper a,To mvs.I(Oxfor d:Oxford Universit y Press,1995)。中,柏拉图在讨论相等本身、美本身等理念时,含糊地把“人”或“马”归入可感事物:
许多美的事物怎么样,比如人、马、衣服或其他东西?(《斐多》78e)
而在《巴门尼德》②中译本参考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8;希腊文本参考:I.Bur net,ΠΑΡΜΕΝΙΔΗΞin Platonis Oper a,Tomvs.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1)。中,他似乎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在130b-d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那么这些东西如何?”巴门尼德问道,“有一个凭自身存在的正义的理念,美的理念,善的理念,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吗?”
“有”,他说。
“有一个‘人’的理念吗,它与我们以及其他所有人分离?有一个‘人’的理念本身吗,或者火的理念,水的理念?”
苏格拉底说:“巴门尼德,对这些东西我经常感到困惑,我不知道该用和其他理念相同的方式还是不同的方式谈论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这段话中,柏拉图对于人是否是理念并不确定,同时也对人是否与美、善、正义这些理念应以相同方式讨论表示出疑议和困惑。对于“火本身”这样的事物是否存在,他在《蒂迈欧》③中译本参考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8。(51c-d)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些事物本身确实存在,这些理念不是我们感性知觉的对象,而只是我们理智的对象。”对于“人”是不是理念这个问题,柏拉图在其知识论的重要代表著作《泰阿泰德》中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明确“人”“石头”这样的概念就是个别事物的集合,就是种或类,就是理念(εδος/ἰδε'α):
我们必须这样来表述个别的东西以及许多东西的集合(περι`πολλῶνἁθροισθε'ντων),所谓集合(̔αθρο'ισματι)就是指人或石头或每一种动物以及种/类/理念(εδος)。(《泰阿泰德》157b-c)
这句话指出,“人”这样的概念是许多个别人的集合,是一种类概念、种概念,当然,也是一个理念。不过,在同一文本中,柏拉图进一步把可知的复合物(συλλαβ)也定位为种概念(εδος/ἰδε′α):“复合物会是某种绝对不可划分的一个种/类(μι′ατιςἰδε′α)。”(《泰阿泰德》205c)这种由元素构成的复合物与可感的元素相对——前者可知,后者可感;前者可描述,后者不可以。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提及由字母构成的音节是“一个种/类”(μι′αἰδε′α/ἑ′νεδος),如203c、203e,甚至还推及其他事物上:“音节是由榫合在一起的若干字母形成的某一个种/类(ἑ′ντιεδος),对与语言文字而言是这样,对于其他各种东西而言也是这样。”(204a)而他提及的复合物还有木制的马车(207a-c)。这样看来,在柏拉图这里,可知的复合物和种是人或石头、马车、音节这样的事物的一个集合,一个类。顺便说一句,虽然柏拉图很多对话都谈及εδος/ἰδε′α,但《泰阿泰德》这一文本讨论的都是后来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核心卷ΖΗΘ所讨论的质形复合物,而非我们所熟悉的善、美、知识等概念——这样看来,区分一般概念和复合物概念,是否从柏拉图就开始而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呢?同时,在同一文本中,他提到三种“描述”(λο′γος)。我们知道,《泰阿泰德》的宗旨是给知识下定义,在否定了前两种定义后,给出的第三个定义是:“知识是带有描述的真信念”(201d),然后具体讨论了三种“描述”,最终的结论因为描述和真信念同义反复而否定了对知识的这一定义方式,但是,结论被否定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理论都不可取,相反,在笔者看来,描述的三种选择都被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其中一种说描述就是名词和动词构成的陈述,对此我们不多赘言,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二和第三种。第二种是对贯通各元素的“路径”的描述,这是与前文的元素与复合物理论相关的理论,虽然柏拉图在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路径”就是与元素构成复合物的另一种成分,但在笔者看来,这几乎是跃然纸上的一个结论;“路径”也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①参考的希腊文本是:W.W.Jaeger,Aristotelis Metaphysica,(London:Oxfor d University Press,1957);英文本是:J.Bar nes,The Complete Wor ks of Aristotle(Princeton Universit y Press,1984);中文文本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下同,个别翻译或有调整。Ζ17用了形式(εἶδος)来表述——二者的功能都在于使元素或质料成为一个统一体,一个事物,甚至二人分别在《泰阿泰德》和《形而上学》Ζ17用的都是音节和字母关系的例子,而且对元素字母和音节的讨论,都在1041b12以下,我们甚至注意到1041b12至本章末尾部分与《泰阿泰德》的文本相似性都很强。第三种是对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差异(διαφορα′)”的描述,也是他在《形而上学》Η卷中的“差异”,被亚里士多德类比于形式,那么,究竟描述或定义所要描述的是“路径”“差异”和形式,还是“可知的复合物”和“种”?这是柏拉图在文本中没有回答的问题,可能也是亚里士多德面对的问题。
(二)柏拉图论灵魂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里不想提及三分学说或不朽学说,只想谈形而上学上的灵魂和人那里与躯体相对应的灵魂。《法义》②参阅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十卷把灵魂定义为“能够自己让自己动起来的运动”(896a)、是万物中最古老的、是万物所有运动和变化的原因(896b)、是先于物体并统治物体的(896b5),“灵魂驱动天上、地上和海里的每一事物,乃通过自身的种种运动,这些运动的名称是:意愿、探察、照管、深思、正确和错误的意见、欢欣、痛心、勇敢、胆怯、憎恨和喜爱——并通过所有与这些类似的或原初的运动;这些运动控制着物体的次级运动,驱动每一事物生长和衰退,分裂和结合,并伴随热、冷、重、轻、硬和软、亮和黑、苦和甜;灵魂使用所有这些,总是将努斯作为帮手——努斯,正确地讲,即诸神眼中的神——教化每一事物朝向正确的和幸福的东西”(896e-897b)。这样的灵魂被后来的普罗提诺解释为宇宙灵魂和人类灵魂两个层次,虽然柏拉图本人没有这么区分。
而就人类灵魂而言,是否有一个单一的人类灵魂被所有的人分有?这是柏拉图没有回答的问题。他在多个文本如《理想国》《斐德罗》中似乎把人的理性灵魂或灵魂定位为认识理念的能力,脱离躯体后进入理念世界,观照理念,与理念一样永恒不朽,但是,既没有肯定宇宙灵魂是理念,也没有说人类灵魂或每个人的灵魂是理念。不过,灵魂和躯体构成人却是其基本思想,而且柏拉图把躯体看作禁锢灵魂的存在,死亡是灵魂对躯体的摆脱。同时,柏拉图对灵魂与理念关系的看法是很复杂的,虽然《斐多》中也基本把人的理性灵魂定位到对美、善这类理念的观照上,却一直强调灵魂与理念的相似性:“灵魂单独由自身察知的时候,就进入那纯粹、永恒、不朽、不变的领域,以自身的不易灵性为本,于独立不受阻碍之时,就永远与那些不变性质同在,永远如一,常住不变,因为它与永恒是相通的。”(《斐多》79d)“灵魂最像那神圣的、不朽的、灵明的、齐一定、不可分解的,永恒不变的。”(《斐多》80b)偶尔他也有一种含糊的说法,隐约中提到了灵魂是一种实体,但似乎以一种提到别人观点的口吻,而没有进一步讨论:
辛弥亚:“因为我们同意我们的灵魂早在进入身体之前就存在着,就像它本身是实体。现在我深信自己接受这种实体是有充分、正确的根据的。”
苏格拉底:“辛弥亚啊,这是对灵魂的另外一种看法。”(《斐多》92d-e)
二、亚里士多德对人和灵魂理论的发展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引入质料克服了理念的分离,而这种克服是在两种意义上进行的。首先,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更强调现实世界里存在的东西,作为第一实体的εἶδος并不必然是理智的对象,也是可感的对象。在人这里,存在的是如苏格拉底或卡里亚斯这样的个别的人,他们都由他们各自的灵魂和各自的躯体复合而成,换言之,存在的不是“人本身”,第一实体也并不是“人本身”,而是个别人,如苏格拉底或卡里亚斯。对“人”这一概念,亚里士多德有两种不同的定位,最著名的一次定位就是在《范畴篇》,与 柏 拉 图 的 理 念 一 样 是 一 种 种 概 念(εἶδος,species)与“动物”这样的属概念(γε′νος)概念一起被称为“第二实体”,是与苏格拉底这个人相对的,认为它们比其他性质更是实体,但是与个别事物相比,则是一种性质。在《形而上学》Ζ13-16中,他肯定种属是普遍的,不是实体,不能脱离个别的人或个别的马等个别事物而存在。不只如此,让人惊喜的是,他在《形而上学》Ζ10-11中更明确地认为人、马、动物这样的概念是普遍看待个别灵魂和个别躯体之后所产生的概念,即普遍的质形复合物,同时明确了人和灵魂的关系:
人和马以及这样被应用到个别事物之上的东西,是普遍的,不是实体,而是由这一个别的描述和这一个别的质料组成被当作普遍事物的某物;但是当我们说到个别事物时,苏格拉底是由终极的个别质料组成的;在所有其他实例中也是相似的。(《形而上学》Ζ10,1035b27-31)
也很清楚灵魂是第一实体而躯体是质料,人和动物是由被看作普遍的这两者构成的。苏格拉底或克里斯科斯,如果灵魂也是苏格拉底,那就有两重意义了(一方面是作为灵魂的苏格拉底,一方面是作为复合物的苏格拉底)。简单说来,假如他就是这个灵魂和这个身体,作为个体就和普遍相类似。(《形而上学》Ζ11,1037a5-10)
这两段著名的话不仅回应了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的“集合”“种/类”“可知的复合物”等概念,还把作为定义对象的这些概念准确地定位到“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上,就人而言,它不再是柏拉图那里单纯的εδος,而是灵魂和躯体的复合物,是个别灵魂和个别躯体被普遍看待后产生的概念。亦即,亚里士多德的个别的εδος是把柏拉图的单一理念εδος如人具体到如苏格拉底这样的个别人身上,且进一步被分析为个别灵魂和个别躯体之后的个别灵魂,即苏格拉底的灵魂;而作为柏拉图种概念的人,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也包含了质料,但并非可感的质料,而是普遍地看待个别人的质料之后得到的概念。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用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填补了柏拉图《泰阿泰德》可知的复合物与可感的元素之间的罅隙:前者是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是知识论上的概念,后者是个别的可感质料,是存在论上的概念。当然,存在论和知识论、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区分,是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哲学关注的重点。
总之,就人而言,柏拉图明确“人”是理念,有“人本身”存在,他的确说过人是灵魂和躯体构成的,并肯定有宇宙灵魂和人类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因为与理念本性相似,对理念有观照,却从未说灵魂是理念;而且柏拉图因为更关注理念世界,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被分有的人在个别的人身上可有不同、如何不同,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灵魂是他多个对话都提到的。而亚里士多德却肯定灵魂是人的第一实体,或者说,Ζ卷所强调的个别的第一实体,是如苏格拉底的灵魂这样的存在物,这一灵魂和他的躯体复合而成的苏格拉底这个人,就是形式、质料和个别事物。
因此,就灵魂而言,亚里士多德突破了柏拉图的理念永恒不动的限制,更从功能的角度肯定了灵魂和躯体的统一性,认为灵魂是躯体的功能,躯体是灵魂的工具。就人的灵魂而言,不仅有植物的营养、消化、吸收功能,还有动物的感觉功能,更有人独特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功能。或者说,真正的存在不再是柏拉图那里静止不动、永恒不朽的理念,而是运动的、有的还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比如动植物。在他看来,首先,“灵魂是活的躯体的原因和本原”(《论灵魂》①参阅英译本:W.D.Ross,Aristotelis De ani 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中译本: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下同。415b8)。而原因我们知道是多种的——有四种原因,那么灵魂可以说是三种原因:它是能使自身运动的原因,是目的因,而且是具有灵魂的躯体的就像实体一样的原因,即,灵魂是活的躯体的动力因、目的因和形式因。其次,“很明显,这就像是实体,因为实体就是所有事物存在的原因”(《论灵魂》415b12)。因为,对于所有活着的事物来说活着就是存在,而活着的原因和本原就是灵魂。进一步说,现实就是这样潜在事物的描述。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肯定的是灵魂是活的躯体的实体,是潜在躯体的现实。再次,“很明显,灵魂是就像目的的原因”(《论灵魂》415b15)。因为就像理性行动都有一定的目的一样,自然本性也同样具有一定的目的,动物的灵魂或者说活的躯体的灵魂也根据自然本性而行动,对这样的灵魂而言,活着的躯体就是它的工具,因此动物或植物活着其实都是为了灵魂的目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对灵魂和躯体关系的阐述,与他对形式和质料关系的阐述是完全一致的,灵魂和躯体可以说是他的形式和质料的典型。灵魂如《形而上学》中的形式一样,是第一实体,是本质,是原因、本原、目的,是现实。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灵魂是第一实体,是不与躯体分离存在的,但人的本质依存于灵魂,对人的定义就是对灵魂的描述:“动物的灵魂(即有生命东西的实体),就是理性实体,是形式,是特定身体的本质。”(《形而上学》Ζ10,1035b14-16)“复合物某种意义上有描述,某种意义上又没有描述。因为就质料而言没有(因为它是不可定义的),就第一实体而言又有描述,例如,对人来说就有对灵魂的描述。实体就是内在的形式,复合物由于由它和质料构成而称为实体。”(《形而上学》Ζ11,1037a26-30)当然,如何构成对灵魂的描述,对灵魂的描述如何就是对人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在Ζ卷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直到Η3亚里士多德才明确,因为对灵魂的描述离不开躯体,对动物的描述也是对灵魂和躯体的描述,所以究竟是对灵魂下定义还是对动物下定义是一样的。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Ζ卷因为没有得出质形复合定义方式,因此也无法给出有关定义的结论。
总之,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了可感事物中形式的个别性,肯定了每个人的个别灵魂的实体性,另一方面,却把柏拉图那里单纯的类概念理念“人”,改造为普遍地看待个别形式和个别质料之后产生的概念,即普遍的质形复合物人,也可以说明确了柏拉图提到却没有进一步阐释的“可知的复合物”概念。然而,如果说形式的个别性问题我们可以清楚领悟的话,作为类概念的人究竟是柏拉图那里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普遍的质形复合物,《形而上学》Z卷的文本中却并非如我们上文所揭示的那般泾渭分明,Ζ7-8甚至提出一种个别的人由理念“人”和可感的个别躯体构成的复合物概念,而且Ζ10-11的文本展示的更多是与上述引文相反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部分内容展开讨论,以清楚地看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如何逐步发展的。
三、《形而上学》Ζ7-8的形式因、种与柏拉图的理念
Ζ7-8是插入的,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也正因为它是后来插入的,什么时候被创作的就是一个谜。笔者曾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肯定了这里是从描述的角度提及形式,并给出了与前文相反的定语,即是普遍的种,而且同一种下个别事物的形式是相同的这样的结论,同时认为这样的观点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最终结论①可参阅吕纯山《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Ζ卷第7-8章中的形式概念》,《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本文在第81页“我们就会否认形式是普遍的观点”的看法,是在把Ζ卷的形式概念和实体概念完全等同的前提下说的,这句话中如果把“形式”改为“实体”,或许更少歧义,因为7-8章中的形式,是从定义对象的角度考察的,是普遍的,与柏拉图的理念或种概念一致。“最终给出了个别形式的定义”一句也跳跃太大,定义针对的不是个别的形式,而是普遍的种,但普遍的定义也适用于个别形式。。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中,笔者进一步认为Ζ卷的形式与实体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形式承担着存在论上个别的第一实体和知识论上普遍的定义对象的双重角色,后一种角色尤其体现在Ζ7-8,这两章多处文本提到的普遍的形式不是作为第一实体,而是作为普遍定义的对象,因此Ζ卷的形式既个别又普遍②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吕纯山《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形而上学〉ΖΗΛ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00-113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吕纯山《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形而上学〉ΖΗΛ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00-113页。。而笔者在这里要从与柏拉图哲学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柏拉图的理念根本上就是种概念,Ζ7-8的形式实际上等同于理念和种,比如人,而不是作为质形复合物——躯体与灵魂的复合物——的人的灵魂。
Ζ7有两段话值得讨论。第一段话提到事物的自然/本性(φυ′σις),用了“合乎形式的自然/本性(ἡ κατα`το'εἶδοςφυ′σις,for mal nat ure,③罗斯英译文,见:J.Bar nes,The Co mplete Wor ks of Aristotl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罗斯英译文,见:J.Barnes,The Co mplete Wor ks of Aristotl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die Nat ur i m Sinne der For m④Szlezák德译文,见:T.A.Szlezák,Aristoteles Metaphysik,Berlin:Akade mie Verlag Gmb H.,2003.)”等字眼,并举了“人生人”的例子:“凡是生成的东西,每一个都可能存在或不存在,这是由于个体中的质料(ἡἐνἑκα′στωτλη)造成的——一般说来,由之而生的是自然/本性(φυ′σις),依其生长的是自然/本性(因为凡生成的东西都具有自然,例如,植物和动物)——被生成的所谓合乎形式的自然/本性是相同的(虽然这本性在另一个体中:因为人生人)。”(《形而上学》Ζ7,1032a20-25)“合乎形式的自然/本性”就是人吗?这是既怪异,又无法从上下文推导出来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用的语言这么模糊,是否预示着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另一段话更为重要,确立了这几章谈论形式的角度——描述的角度,同时也把形式的复杂性推向极致:
我们从两方面来说铜球是什么,就质料说是铜,就形式说是这样的形状(το'εδοςο′̔τισχματοιο′νδε),而形状就是它所隶属的最初的属(τοῦτο′ἐστιτο'γε′νοςεἰςπρῶτοντι′θεται),那么,这个铜球在它的描述中就有质料。(《形而上学》Ζ7,1033a1-3)
我们曾经详细讨论过这段话的复杂性,认为这段话改变了前文特别清晰的实体个别性的论证线索,从描述的角度讨论,在正式论证开始的Ζ4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形式,却用与το′δετι(这一个)相反的τοιο′νδε(这 样 的/这 类)作 定 语,并 与 种 属 概 念(εδος/γε′νος)等 同 起 来,深 刻 地 烙 上 了 普 遍 性 特征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吕纯山《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形而上学〉ZHA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00-113页。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这段话中不区分种和属概念的做法,应该与柏拉图是一致的,而且把类概念与质料对照表述,或许是他克服理念分离问题的第一步——把理念放入质料之中克服其分离,个别的人都是“人”这一理念与各自不同的质料相结合而成。我们知道,后世注释史上极有代表性的一种解释传统就是,形式是普遍的种,而质料是个别的,我们所熟悉的陈康先生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坚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εἶδος的一致性,它们都是相,亚里士多德那里的个别事物就是相和质料的复合物⑥参见:Chen Chung-Hwan,Sophia,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New Yor k:Geor g Ol ms Verlag Hildeshe m,1976),p.217、p.220、p.222-228,及其他等各处。;与此同时,他认为我们在上文所强调的普遍的质形复合物反而是一个不适合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入侵者⑦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陈康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个为人忽视了的重要概念》以及《普遍的复合体——一种典型亚里士多德的实在二重化》,这两篇文章收在: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第326-332页、333-345页。第一篇文章原载于《张君劢先生七十寿辰纪念论文集》1956年;第二篇文章是英文译文,译自Phronesis,Vol.9(1964)。。在笔者看来,在写作Ζ7-8的这个时间段,亚里士多德或许还只是相对简单地把柏拉图的理念放入质料之中,在这一点上陈康先生所代表的这一传统看法是对的,但必须指出,这仅仅是一个发展阶段,并不意味着个别事物的个别性是由质料决定的。同时,陈先生把质形复合物认为是一个入侵者的思想也值得商榷,我们上文已经给出自己的解释。或许,在克服分离的第一阶段,亚里士多德还没有深思理念与可感质料之间的关系,只强调了柏拉图的作为类概念的分离的理念并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样的思想也体现在Ζ8:
那么,在个别的球体之外有一个球吗?或者在砖之外有一所房子吗?(1033b21)
很显然,形式因(η̒τῶνεἰδῶναἰτι′α),或者像某些人习惯地称之为理念(τινεςλε′γειντα`εδη),如果是些在个体之外的东西(παρα`τα`καθ̓καστα),对于生成和实体就毫无用处。并以同样理由,也并不是就自身而言的实体。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看得清楚,生成者和被生成者是相似的,虽然决非相同,不是数目上的一,而是在种上的(ε'̔ντεδει,der Art nach①M.Fr ede和G.Pat zig的译法,参见:M.Fr ede&G.Pat zig,Ar ist ot el es,Met aphysikZ‘:Text,Über set zungundKomment ar,2vol s,(München:Ver l agC.H.BeckMünchen,1988),s.87。,der Art〔der For m〕nach②T.A.Szlezák的译法,参见:T.A.Szlezák,Aristoteles Metaphysik(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 H.,2003)。,in for m③罗斯英译文,见:J.Bar nes,The Co mplete Wor ks of Aristotl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一,例如,在自然物中(因为人生人)。(1033b26-32)
四、Ζ10-11的形式与复合物
如果说Ζ7-8是由于后来插入的缘故而造成了文本的复杂性的话,那么,Ζ10-11的文本则以相互矛盾的论述和对形式作为定义对象的强调而著名。只是,仅仅因为“第一哲学”的宗旨或Ζ卷最终的目的是要讨论没有质料的形式——即努斯或神,最终在《形而上学》Λ6-7、Λ9-10得到了阐释——就要否定定义的对象和构成中不能包括质料的部分吗?毕竟,无论按照《形而上学》Δ8对实体的罗列,还是Λ1对三类实体——月下世界中的质形复合物如动植物,天体(《形而上学》Λ8),努斯或神——的表述和实际的论述,还有他实际上在文本中展开的是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阐释,讨论存在首要的就是讨论实体,其他范畴都是在与实体类比的意义上得到阐释,而作为质形复合物的动植物是实体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也正是ΖΗΘ卷讨论的可感事物。况且,结合他在Η卷给出的质形复合定义和在《论灵魂》Β卷给出的有关灵魂的定义(“灵魂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一个自然躯体的第一种现实。”《论灵魂》Β2,412a28)来看,一方面他最终的对质形复合物下的定义不能不涉及质料,另一方面,Ζ卷即使涉及质料,也并不一定破坏整卷的宗旨。因此,除了“第一哲学”宗旨的限制,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
Ζ10-11中除了前文提及的对种属概念很明确的定位——普遍的质形复合物——之外,这两卷的主要思想强调的是,虽然我们面对质形复合物进行定义,但定义只能针对其中的形式,构成定义的部分也只能是对形式的描述。他提到的复合物有由弧形构成的圆形、由字母构成的音节、由锐角构成的直角、由骨肉肌腱等构成的人、扁鼻、铜球以及泥像等,但是他却强调定义扁鼻或铜球时只能对“扁”或“球形(σφαῖρα)”或“圆形(κυ′κλος)”①罗斯在对此的阐释中区分了动物和圆的质料,认为前者是可感质料,后者是理智质料,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动物的定义中必须提及可感质料,而圆的定义中却千万不能提及铜这样的可感质料,而要提及图形这样的理智质料[参见:W.D.Ross,Aristotle’s Metaphys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p.203-204]。然而在笔者看来,亚里士多德是把动物和铜球对等看待的,亚里士多德的确把躯体或铜看作可感质料,因此极力要排除出定义之外,区分动物和圆反而模糊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且属是否理智质料,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认为数学对象是理智质料(Ζ10,1036a4-11)。。然而我们的疑问是,扁鼻和铜球与扁和球形是同一类定义对象吗?毕竟,如果说前一类是本卷一直肯定的实体,而后一类则是数学对象,在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划分中,前者是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后者是数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其他文本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这个问题,不仅在《论天》②参考的中译本是:亚里士多德《论天》,徐开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译文或有修订。(Α9,277b31-278a5③“在一切由于自然和处于技术的构造和产物中,我们都能区分出依据自身的形状与质料相结合的形状。例如,球体的形式与金质的和铜质的球体不同,圆环和形状与铜制的和木制的圆环相异。在说明球体或圆环的本质时,我们不包括金的或铜的定理,因为它们不属于我们所定义的东西的实体。但是,如果说明的是铜质和金质的球体,我们就包括它们。”)这样的自然哲学著作中,甚至《形而上学》(Ε1,1025b32-1026a6④“那些被定义的东西,如本质,一些像扁鼻,一些像扁平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扁鼻是与质料结合在一起的(扁鼻即是扁平的鼻子),而扁平则独立于可感的质料。那么,如果所有的自然物在本性上都可以类比于扁鼻,例如鼻子、眼睛、面孔、肌肉、骨骼,以及一般而言的动物;又如叶、根、皮以及一般而言的植物(它们的定义都离不开运动且永远具有质料),很显然我们必须寻求并定义这些自然对象的本质,以及为何在一定范围内——就它并不脱离质料而言——它属于研究灵魂的自然哲学家。”)也进一步肯定了二者的不同,更有《物理学》B卷中对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研究对象的区分。在他看来,数学家把它们分离出来考察,当然只是思想中的分离,因为数学对象都不能运动。尤其如经常提及的扁鼻,数学家关注的是扁平或凹陷这样的形状,而自然哲学家不仅关注形状,还要关注鼻子。而且,亚里士多德给出数学对象如圆的定义是从中心到圆周均等的图形(《形而上学》Ζ8,1033b14),但对于究竟定义动物还是定义灵魂进行了统一化处理——都要提及灵魂和躯体,都是普遍的,如在《形而上学》Η3。因此:
没有质料的形式的描述区别于在质料中的形状的描述,这个说明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把它假定为一条真理。(《论天》Α9,278a24)
事实上,他所提到的作为形式的对象,是圆形、直线、球形、扁形、各种形状、灵魂、一般的天,其中,数学对象和一般的概念,与柏拉图所讨论的对象并无二致,所给出的定义方式也一致,而对灵魂的描述,柏拉图给出的定义是:“能够自己让自己动起来的运动”(《法义》896a)①参阅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却强调灵魂不脱离躯体,最后在《论灵魂》这一自然哲学著作中给出了结合躯体的定义。但是,在《形而上学》Ζ卷,亚里士多德固然在存在论上强调柏拉图理念的分离是最大的问题,认为形式要放在质料之中作为复合物而存在,但笔者认为在知识论问题上,他的思想尚且停留在定义对象只能是单纯的εδος的立场上,强调只有形式才是定义的对象,不能包含质料。
然而,具体到人的形式或实体上,亚里士多德在整个Ζ卷中第一次肯定了人的实体是灵魂,但同时表明,即使人的形式总是在肌肉骨骼之中,也只能描述形式,即使所有的圆形都是青铜的,青铜也非形式的部分,定义不针对它也不对它进行描述:
直线不能分解为半线而消灭,正如把人分解为骨骼、肌腱、肌肉,而不能以它们为实体的部分。这些东西只能作为质料,是复合物的(συνο′λου)部分,决 不 是 描 述所指的 形 式 的 部分,所以不包含在描述之中。有时候上述部分中也有描述,有时则不然,除非是复合物的描述(τοῦσυνειλημμε′νου)。(Ζ10,1035a18-24)
就是那些看来是不相分离的东西,也难免有类似情况,如果所见的圆形都是青铜的,青铜依旧不是形式部分,不过难于用思想把它移开罢了。例如人的形式(το'τοῦἀνθρω′πουεδος)总是显现在肌肉、骨骼,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那么这些东西是形式和描述的部分吗?或者不是,而是质料。是否由于它只能从这类质料生成,我们就无法把它分开呢?即使事情可能如此,也不知何时出现。(Ζ11,1036a35-b10)
因为像这样作为质料的部分,不能内在于实体的描述中,它们甚至不是实体的部分,而是复合物的(τςσυνο′λης)部分。它在某种意义上有描述,某种意义上又没有描述。因为就质料而言没有(因为不可定义),就第一实体而言又有描述,例如,于人而言就是对灵魂的描述(ἀνθρω′που ὁτςψυχςλο′γος)(Ζ11,1037a24-29)。
传统注释上,当我们解释这些话时,一般都从亚里士多德的宗旨出发考虑,但笔者在这里想要质疑的是,亚里士多德把复合物和形式对照的做法,是否还与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所表达的思想的模糊性相关?柏拉图在对第三个知识定义的讨论中提出第二种描述,即“贯通各元素而达整体的路径”(208c)时,柏拉图一方面肯定了由元素构成的复合物可知、有描述,而且认为复合物是种概念(εδος),一方面又肯定描述的对象是“路径”,他没有明确的是,究竟我们要描述的是包括元素在内的复合物?还是贯通各元素的路径?如果我们把柏拉图举的音节与字母、马车与木料的关系的例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Ζ17同样列举的音节与字母、房屋与砖瓦、人和躯体的关系的例子相对照——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做法并非毫无道理,甚至就是一种直接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阶段更倾向于把对种的描述等同于对形式的描述,把对人的描述等同于对灵魂的描述,亦即,在柏拉图所谓贯通各元素的“路径”和“差异”,还是“可知的复合物”这两个选项之间,选择了前者,也就选择了保守,肯定描述的对象是形式概念,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种,这一概念显然与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不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或许,就像柏拉图直接把可感的质料与可知的复合物直接对照一样,亚里士多德在写作这些内容时也没有意识到作为描述的部分的质料不应该是可感的东西,而要意识到这一点,可能需要长期的思考过程。
但这两卷文本的描述是如此错综复杂。除了以上的否定性思想,也有我们在上文提到的种属是普遍质形复合物概念的创造性思想,同时,也有更为明晰的说法,即对复合物中质料的肯定:
既然动物的灵魂(因为这就是生物的实体)就是就描述而言的实体,以及在这样的肉体中的形式和本质(因此,如果每一个〔部分〕要被很好地定义,就不能离开了功能〔οὐκνευτοῦργου〕来被定义,而没有感觉功能就不存在)。(Ζ10,1035b14-18)
我们看这段话,似乎与我们所引的前几段话并不一致,突然强调了定义中质料的重要性,以及生物的“功能”。他指出,下定义时忽视质料是费力不讨好的,因为人总有部分,铜球总是在青铜中,我们定义人这样的生物时,不能不提及其部分,不能不提及部分的运动或功能。这里,明确提及了后来他在《论灵魂》中所论述的“功能(ἐ′ργον)”,虽然还没有像在《论灵魂》中对灵魂的定位那么明确,但也提示我们对人下定义时不要只是对其灵魂进行描述,恐怕也不能忽视其躯体。但同时我们也能意识到,与《论灵魂》中对灵魂的实体地位和功能的论述相比,这里的描述太单薄了,甚至无法与Η卷相提并论。而Ζ10-11相互矛盾的论述,似乎也提示我们文本可能有被错误编辑的嫌疑①上文所引用的对种属概念进行重新解释的Ζ10的1035b27-31和Ζ11的1037a5-10这两段话,以及强调定义中包含质料并对功能进行描述的Ζ10的1035b14-18和Ζ11的1036b21-32这两段话,其主题更与Η卷而非Ζ卷一致。这些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却与Ζ卷的思想相矛盾,因此这些思想或许是亚里士多德后来修改的,或许被编辑者放错了位置。。
最后,我们还想提及一点,Ζ12所讨论的“人是两足动物”也是柏拉图的著名定义,不仅被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学著作中广泛讨论,而且,他在这里从这个分类法定义入手思考实体定义方式,说明此时的他还是在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之下。我们已经论证过,Ζ12的论证是无果的,人既不可能被以单一的种差序列分类所包含,因此得不到最后的种差;也不可能通过种差找到实体,因为找到表述本质的种差的基础在于知道实体是什么,是循环论证,这是他在《论动物的部分》Α2-3明确论证的,当然Η6对此的呼应也说明其未完成性②参阅:吕纯山:《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形而上学〉ΖΗΛ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39-148页。。这些都说明Ζ卷不是他最成熟的思想,至少它在Η卷、《论灵魂》《论动物的部分》等之前。
五、结束语
《形而上学》Ζ卷的复杂晦涩有多种原因,对于从质形复合物入手讨论形式,却一直强调定义的对象只能是形式、不能包括质料的做法,多从第一哲学的宗旨思考问题,仿佛给出质形复合物的定义反而会耽搁对形式的定义。然而,亚里士多德终究在Η卷给出了质形复合物的定义,整个核心卷也都没有对第一哲学的对象展开研究。因此,Ζ卷强调只能定义形式而非复合物,可能正是他的种概念从柏拉图的理念到自己的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的发展,把实体与其他如伦理学的一般概念相区分,以及定义方式从分类法定义到质料形式定义的转变过程。从他典型的人的例子入手,指出他在文本中对人和灵魂的复杂而矛盾的论述,一方面说明了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也证明Ζ卷的思想并非其最成熟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在最应该讨论作为人的第一实体灵魂的Ζ7-8,没有讨论灵魂,却大谈特谈人,从而,把作为个别的人如苏格拉底这一灵魂和躯体复合物的第一实体个别的灵魂,和柏拉图的理念和种概念人,以及普遍地看待个别灵魂和个别躯体之后形成的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人,混乱地纠缠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