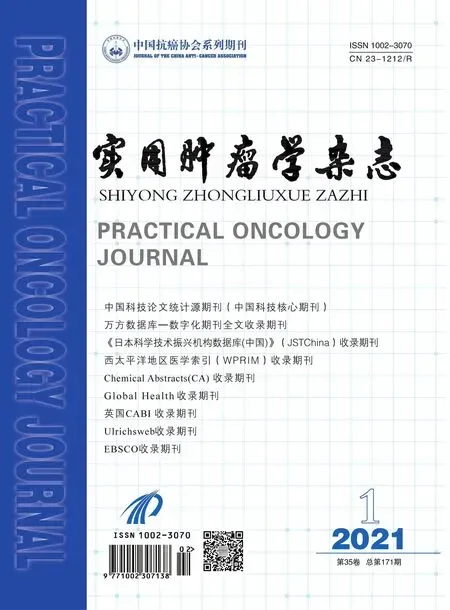CAR-T疗法在卵巢癌中的应用前景
张文文 姜亮亮 综述 王晶 审校
卵巢癌是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五大常见原因,其死亡率超过任何其他妇科肿瘤。2018年,全球诊断出超过295 000例卵巢癌新病例,同年死亡人数约184 000例[1]。由于卵巢癌的隐蔽性及有限的筛查手段导致多数患者初治时已是晚期。尽管治疗方法得以发展,但由于其预后差和易复发,其五年生存率仍不理想[2]。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颖有效的治疗方法来改善预后。
近年来,随着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作为检查点抑制剂以及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细胞(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中的显著突破[3],利用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的细胞免疫疗法在实体瘤的研究中越发流行。CAR-T疗法代表了癌症免疫疗法的里程碑式转变,其利用表达嵌合抗原受体(CAR)的基因工程T细胞通过基因转移技术重定向及重新编程后过继转移回自身,识别并附着于肿瘤表面,选择性靶向并杀死表达相关抗原的肿瘤细胞[4]。许多研究表明,CAR-T疗法在卵巢癌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本综述中,我们概述了卵巢癌中CAR-T疗法的生物学基础、临床应用、所面对的挑战及可能改善治疗效果的策略(图1)。

图1 CAR-T在卵巢癌中的研究进展示意图
1 CAR的结构
CAR是一种工程化的合成受体,它对肿瘤细胞的影响主要是由基本结构决定的。CAR主要由细胞外抗原识别区(ScFvs)、间隔区、跨膜结构域及细胞内信号转导区组成。ScFvs主要由重链和轻链的可变区组成,理论上可识别在靶细胞上表达的任何类型的表面抗原,而不受主要组织相容复合物(MHC)分子的限制[5-6];间隔区又称铰链结构域,为重轻链提供足够的折叠空间,与ScFvs共同构成细胞外结构域;跨膜结构域则将细胞外部分与细胞内信号转导结构域相连接,通常来源于CD8、CD3-ζ、CD4、OX40和H2-Kb[7];信号转导区包括T细胞受体(TCR)的信号转导组分和/或共刺激受体,其主要功能为激活T细胞[8]。
目前已有四代CAR在临床实践中应用。1989年以色列一个研究小组首次将ScFv和CD3-ζ链基因连接刺激T细胞活化,创造出第一代CAR-T细胞[9];由于这种CAR-T细胞的低效性及低持久性,研究者在原始基础上加入共刺激分子(如CD28)[10];为了进一步增强体内持久性及效应性,研究者们开发出包含两个共刺激结构域的第三代CAR[11];第四代CAR称作“TRUCK T细胞”,它可以产生细胞因子(特别是IL12)用于促进肿瘤微环境中CAR-T细胞的进一步活化[12]。此外,最近研究者又开发出了各种新型CAR-T,如使用截短形式的CD19蛋白的自体T细胞、双抗原靶向CAR、抑制性CAR等[13-15]。
2 CARs的转导
CAR-T细胞的转导是用遗传学方法将特定基因转移到小鼠和人T细胞中,主要包括传统的载体系统及新兴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常见的载体系统包括病毒类及非病毒类载体,由于病毒能够在体内和细胞外传播到全身,并且可以穿透细胞核且效率高,大多数的CAR-T研究都利用病毒载体进行转导[16],卵巢癌中常用的病毒方法包括逆转录病毒[17]、慢病毒[18]、腺病毒及腺相关病毒[19],但其也有制造过程相对复杂,成本较高等缺点;与之相对的非病毒载体如脂质体介导的基因转移[20]、mRNA介导的基因转导[21]、转座子系统[22]则易于操作,可转移大规模的基因,且炎症感染率低,但同时也需要克服转染率低和转基因表达差等问题。因此,在操作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的载体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载体系统,新兴的基因组编辑技术也是CAR-T疗法必需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包括最初的大范围核酸酶、转录激活子样效应核酸酶(TALEN)和锌指核酸酶(ZFN)的分子技术,以及近几年使用最广泛的CRISPR/Cas9平台。CRISPR/Cas9是在细菌和古细菌中发现的Ⅱ型获得性免疫防御系统,CRISPR序列由散布在高度保守的重复DNA序列中的“间隔”序列组成。间隔序列与外来核酸互补,并允许Cas9降解外来物质并保护其免受入侵病毒(即噬菌体)、质粒和其他类型的外来核酸的侵害[23]。CRISPR/Cas9利用可定制的单链向导RNA(sgRNA)形式的核酸靶向基因组中的特定基因座,并利用核酸内切酶Cas9(一种双链RNA特异性核糖核酸酶)靶向任何DNA操作[24]。与其他可编程核酸酶相比,CRISPR/Cas9系统更简便、灵活和多重基因编辑潜力等[25]。据最新研究显示,CRISPR/Cas9系统与病毒或非病毒转基因传递方法相结合,可用于将CAR-T细胞调节剂导入特定的基因组位点[26-27],并改善激活诱导细胞死亡(AICD)现象。这项新兴技术有可能彻底改变以CAR-T细胞为基础的癌症治疗方法。尽管该技术可用于克服常规CAR-T疗法中存在的若干障碍,但是想真正投入临床仍须解决临床翻译中的诸多挑战,如用大规模转染系统生产CRISPR/Cas9编辑的CAR-T细胞时电穿孔后淋巴细胞活力降低,在细胞收获时不能达到目标输注剂量[28],Cas9-sgRNA结合和切割与靶DNA序列高度相似的序列导致基因组中不需要的位点发生突变等[29]。尽管面对很多挑战,未来几年,CRISPR/Cas9仍可能成为基于基因编辑的许多疗法的引擎。目前,Salas-Mckee所在的中心正在进行CRISPR/Cas9技术的首次人体试验,该技术使用多重sgRNA提高工程化T细胞在癌症中的疗效[30]。
3 卵巢癌中CAR-T细胞治疗的合理性及优势
CAR-T细胞在单个融合分子中结合了抗原特异性和T淋巴细胞活化特性[31]。尽管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体瘤中的尝试却不尽人意。和血液系统疾病相比,实体瘤很难找到针对性的特异性抗原;而且CAR-T细胞必须克服实体瘤特殊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异常的血管系统、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分子和免疫调节剂等对其抗肿瘤活性的限制[4]。虽然将CAR-T应用于实体瘤存在挑战,但其仍为治疗卵巢癌提供了新的视角[32-33]。第一项关于卵巢癌的CAR-T研究是由Hwu等[33]在1993年进行的,他们在卵巢癌组织的肿瘤浸润细胞(TILs)上遗传表达针对叶酸结合蛋白(MOV18)的scFV。这种修饰的TILs成功裂解卵巢癌细胞,为探索针对卵巢癌的CAR-T疗法打开了新的机会之窗。
就卵巢癌而言,CAR-T治疗有两个优势。其一,卵巢癌细胞表面表达很多肿瘤相关抗原,据报道除CA125外,癌细胞还表达超过60种肿瘤相关抗原[34]。这为CAR-T设计提供了更多的目标;目前,许多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以明确其治疗卵巢癌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在一项针对间皮素(CART-meso)的CAR-T细胞试验(NCT02159716)中,初步结果显示在没有肿瘤外效应或细胞释放综合征的情况下,输注的CAR-T细胞具有良好的耐受性[31]。目前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还有NCT03799913和NCT03916679等。最近,Rodriguez-Garcia等[35]还开发并评估了靶向苗勒氏抑制物质2型受体(MISIIR)的CAR,他们发现这种CAR-T细胞在体外可表现出抗原特异性反应,并溶解了一组患者来源的卵巢癌肿瘤标本,在体内消除了MISIIR过表达的肿瘤。除此之外,在卵巢癌中还测试了包括MUC16[36]、PSMA[37]和5T4[32]等多种肿瘤抗原用于CAR-T疗法;其二,卵巢癌的主要转移区为腹膜腔,所以可以仿照腹腔注射化疗药物,直接向有腹腔转移的卵巢癌患者腹腔内注射(IP)CAR-T细胞使得其与卵巢癌细胞直接接触,很大程度避免了通过静脉(Ⅳ)注射造成的T细胞浸润及归巢问题[8]。最近,John团队利用体内卵巢癌模型发现局部腹腔注射TAG72-BBζCAR-T细胞可以消除抗原阳性疾病并且延长小鼠总生存期,而静脉注射则对疾病的控制无效[38]。这也充分说明CAR-T疗法在卵巢癌中区别于其他实体瘤的优势。
4 卵巢癌中CAR-T细胞治疗的挑战
第一个不得不提的挑战是其副作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效应),其是由T细胞活化和增殖引起的过继性T细胞疗法后可见的严重全身毒性,与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IL)以及干扰素的循环水平升高有关。2017年Tanyi等[39]在一名患有复发性卵巢癌的患者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区室性CRS,她在用自体CART-meso治疗过程中产生大量胸水,其中IL-6明显增加,且胸膜腔内CART-meso细胞水平明显多于外周血液。可以看出卵巢癌生长和扩散的独特性质可导致对CAR-T疗法的意外反应。针对这一挑战,研究者也在不断做新的尝试,最近一个研究团队利用共表达与肿瘤微环境中存在的趋化因子环境相匹配的受体可能使CAR-T疗法更有效的原理设计了一个可增强IL-8反应能力的CAR-T细胞,观察发现,其可增强对肿瘤的控制,但并未发现明显的CRS效应,体重也无减轻[40]。
第二个挑战是靶向非肿瘤毒性,主要是由于所选抗原在肿瘤细胞及少数正常细胞表面均表达,导致CAR-T细胞攻击肿瘤细胞同时殃及正常细胞以致其损伤。目前已开发出可行的策略以使CAR-T细胞通过调节scFvs亲和力区分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41],降低scFvs亲和力但保持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靶向CAR-T细胞的强大抗肿瘤功效可以消除或强烈抑制对正常组织的反应性[42]。如基于组合分裂信号受体和顺序作用受体概念设计的CAR-T细胞[43-44]。
同时,研究者们正在尝试用CAR-T疗法联合其他治疗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北京一个研究小组利用血管破坏剂(VDA)和CAR-T细胞联合,破坏或抑制肿瘤部位异常血管系统,增加血管通透性并进一步促进CAR-T细胞向肿瘤部位的浸润[45]。此外,还有研究者把薄膜镍钛合金(TFN)作为CAR-T细胞的传递和支持设备向患有卵巢癌的小鼠中植入,并发现植入后T细胞快速扩增,与传统T细胞注射相比,CAR-T细胞的密度峰值增加了232倍,并可将高密度的T细胞直接递送至肿瘤部位,最大程度发挥疗效[46]。此外例如联合化疗、PD1阻断、嵌合受体疫苗等方法也在尝试中[47-48]。
5 小结与展望
CAR-T疗法已成为一种潜在的癌症治疗方法,在卵巢癌中也显示出了它独有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以验证其在卵巢癌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外,CAR-T疗法与其他方法联合也是一种有前景的治疗策略,如化学疗法、免疫检查点阻断、细胞因子治疗等。然而,这种新颖有效的方法还没有广泛应用于卵巢癌患者是因为还存在许多挑战和不足。因此,应用CAR-T细胞疗法治疗包括卵巢癌在内的实体瘤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