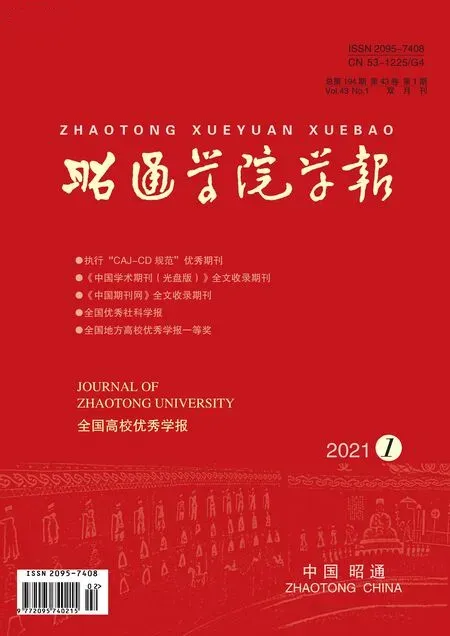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
——对《恩惠》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张 晶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出现在20 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蓬勃发展。被认为是第三次女权运动的重要流派,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弗朗索瓦·德·艾奥博尼于1974年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标志着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开端。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加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是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来看待生态问题,指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父权压迫女性同出一辙,都是在根植于以父权制为逻辑的认识之上,对世界进行简单粗暴、一分为二的统治,从而对此进行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女性和自然,认为“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1]它倡导建构多元生态文化,旨在建立一个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三个系统之间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获得了美国图书奖,普利策小说奖,诺贝尔文学奖等诸多奖项,被誉为美国黑人文学领域的代言人之一。她的小说以意味深长的主题、生动的对话和不同类型的人物而闻名。作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深切关注黑人女性的生存和自我身份的建构,她的作品真实地刻画了黑人女性遭受来自社会以及黑人男性的歧视的痛苦,展现了她们为追求自我认同、平等和幸福而奋斗的过程。
莫里森的第九部长篇小说《恩惠》一出版就备受关注,获得评论家们的赞誉,并被《纽约时报书评》编辑遴选为“2008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小说篇幅不长,仅仅167 页。在小说中,佛罗伦斯的母亲为了改变女儿的命运,自小将她卖给“心里没有野兽”的小农场主雅各布,这个16 岁的黑人女孩却最终没有摆脱命运的摧残,她渴望得到母爱和爱情,最终都失败了。莫里森通过对小说中的人和自然事物的描写,揭示了人类将自然边缘化、男权中心主义将女性边缘化的社会现实,传达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男人和女人平等相处的新型社会的愿望,彰显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二、父权制社会中的二元对立
(一)人类对自然的主宰
在西方传统思维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就是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尼尔·史密斯说:“自然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人类的设计,既是荒野,也是耕作的田园。”[2]这一对自然的定义表现了在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能统治自然,自然为我所用。在十七世纪的殖民时期,殖民统治者的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疯狂地追求财富、掠夺自然资源。西方殖民者将自己与自然割裂开来,把自然视为他者、被统治者和剥削的对象。在《恩惠》中,莫里森通过对美洲殖民地的描写说明了早期的欧洲移民者肆意地破坏大自然、剥削原住民。殖民者无休止地圈地,砍伐整棵整棵的大树,把森林变成无法生长任何植物的沙丘,并且随意占有女人,企图毁掉一切土著居民。“他们从大地的灵魂中挣脱出来……像所有婴儿一样不足。”[3]59“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普鲁姆伍德认为,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形态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通过强加的殖民者土地模式和理想风景意识来对非人类自然进行殖民化。”[4]当时殖民者主要从事皮毛、烟草、木材、朗姆酒等生意,掠夺和占有自然资源。他们认为自然资源永远不会枯竭,“就像木柴,很快烧成灰又很快会得到补充”,[3]32“土壤永不会衰竭”。[3]33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对自然的占有欲,莉娜告诉弗洛伦斯一个关于旅人和鹰的故事:当旅人站在峰巅,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他开怀大笑说:“这是我的。”[3]68故事中的旅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世上的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精神,心中充满了征服的快感。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
农场主雅各布·伐尔克早年是个孤儿。他心酸的经历使他不同于其他白人奴隶主。起初,他心怀仁慈,富有同情心,厌恶作把奴隶当做商品进行买卖,他认为“血肉之躯不是他的商品”。[3]22然而,在目睹了他去收债的奴隶主恢弘、华丽的大房子以后,他无法抑制对财富的欲望,他开始梦想要在不远的将来,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一栋这么大的住宅。在回家的路上,雅各布的想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对自然环境的描写暗示了雅各布物质欲望的膨胀和掠夺自然资源的计划,“当他返回小旅馆时……没有雾——无论是金色或灰色的 ——阻碍他。”“远处闪耀的银光根本并非遥不可及……等着他去品尝。”[3]37回到农场后,雅各布变得“迟缓且不易讨好”。[3]39他逐渐开始投资种植园,并通过剥削和控制奴隶以满足他的扩张欲望。贪婪的种子他在心中疯狂地成长,他开始破坏自然,建立自己的梦想豪宅,“一栋既不适合农场主,甚至不适合商人,而是与一名乡绅相匹配的宅子。”[3]97他未经树木的同意,砍伐了五十棵,最后招来了厄运。雅各布建造的未完工的豪宅正是人类破坏自然、剥削自然的罪证。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和自然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当人类因贪婪无视自然界和人类存在的规律,无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离灾难就不远了。
(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根据墨菲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最开始就把自然和文化、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和对女性的压迫紧密相连”。[4]在西方传统的价值论中,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是相互对立的,女性和自然同样受到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女性是莫里森关注的焦点,她在作品中忠实地展现了她们无法言说的惨痛经历和心理创伤。农场女主人丽贝卡来自中下层,尽管她是个白人女人,在父权文化中仍然遭受着很多歧视,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她父亲得知雅各布正在寻找一个身强力壮的妻子,便抓住机会卖掉了自己的女儿。“她可以指望的只能是做佣仆、娼妓和妻子。”[3]85她选择了最后一个,对她来说似乎是最安全的。所以她横渡大海来到了她从未踏足过的新大陆,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雅各布。两人名义上是夫妻关系而实质上他们处于从属关系。当雅各布洗澡时她用肥皂和短刷清洗他的身体,然后用布擦干,而丽贝卡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对待。当雅各布建造一所根本不需要的大房子时,她高兴得就像她在收获季节一样,因为这可以让她丈夫在农场呆得更久。雅各布因病去世后,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无心照顾农场。显然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完全依附于男性,始终无法摆脱男性的奴役。
在小说中,佛罗伦斯是最后一个来到农场的女奴,她是小说中最悲剧的人物。雅各布到奴隶主家里讨债时,奴隶主想利用他的女奴作为补偿。令雅各布惊讶的是,女奴恳求让她和儿子留下,而带走佛罗伦斯——她八岁的女儿。因为被母亲抛弃,佛洛伦斯从此失去了身份和归属感,给她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雅各布的农场,她的生活比以前好一点。她得到了莉娜的关心和爱护,但这一切都没有使她摆脱精神的奴役,她总是想取悦别人,渴望获得别人的认可。遇见铁匠后,她成了爱的奴隶。她在墙上写道:“在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存在之前,我就已经被你杀死了……最终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没有死。我第一次活着。”[3]41深深的爱慕使她历尽艰难险阻找到了铁匠,但铁匠误以为她故意伤害一个小男孩,揍了她一顿,把她无情地赶走,不给她任何解释的机会。在父权制社会,男性统治、压迫和奴役女性,女性没有话语权。男性的压迫和奴役根植于女性的内心,使女性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奴隶。
小说中描述的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样受到父权制社会的歧视和压迫。土著女奴莉娜原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印第安部落。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使她成了孤儿。在白人奴役和文化的影响下,她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一天晚上,主人喝醉了爬上她的床,此后经常毒打她,最后把她卖给了新主人雅各布。到了农场,莉娜教会雅各布如何晒鱼干,如何为家畜繁殖做准备、如何保护庄稼,帮助他打理农场。但是她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只要天气不是太恶劣,她就住在鸡舍里”。[3]54佛罗伦斯的母亲在小说的最后叙述了自己身为黑人和女性所遭受的摧残和压迫,还有她不得不抛弃女儿的苦衷:母亲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迫害。“我不知道谁是你的爸爸。四下太黑,我看不清他们任何人……在这种地方做女人,就是做一个永远长不上的裸露伤口。”[3]180佛罗伦斯正在发育的胸脯引起了主人的注意,母亲对此忧心忡忡。她在前来讨债的雅各布身上看到了希望,认为他“心中没有野兽”,恳请他把女儿带走,希望女儿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辙。
三、多元和谐关系的建构
(一)女性的自我建构
“艾琳·戴梦得和欧蓝斯坦曾经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不能停滞于摧毁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还应该注重构建新故事,新故事是尊重确保生命延续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4]莫里森在《恩惠》中也体现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特点,不仅呈现了“互为联系的压迫”,[5]解构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且勾画了一个新型的多元和谐的世界。小说中的主要女性角色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通过不同的方式自我建构。
莉娜通过回归自然和找回记忆中的印第安文化实现自我建构。在印第安文化中,地球是万物之母,人类的栖息地,也是他们精神的源泉力量。在他们眼中,人和自然融为一体,他们的生命旅程源于自然,并以回归到自然结束生命的旅程。大火烧毁了莉娜的家园,使她不得不抹掉记忆、远离自然。到了农场,她在村子里没有一点舒适感和安逸感。最后,带着极大的孤独、气恼和伤痛,莉娜决定依靠自己的记忆和才智,把母亲教给她的东西和印第安的习俗拼凑起来,使自己变得强大。回归印第安文化使莉娜找到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同时,莉娜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成为自然界又一活跃的事物,她和动物唧唧喳喳地交谈,与植物聊天,在阳光和细雨中嬉戏。融入大自然使她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在太太到来时,她的自我创造已臻于完美。”[3]55显然,莉娜已成功地完成了自我建构。
雅各布死后,女主人丽贝卡也染上了重病,佛罗伦斯为了拯救她的生命,孤身一人踏上路途遥远、艰辛重重的寻找铁匠之旅,这象征着佛罗伦斯开始自我认同的建构。在佛罗伦斯寻找铁匠的路途中,大量的自然景象的描写,象征着大自然给予她的指引,并暗示了她对铁匠的爱的悲惨结局。“我梦到樱桃树朝我走来……我不知道它们想要什么。看一看?摸一摸?一棵树弯下腰来”。[3]113这里的樱桃树是母亲的象征,母亲想说点什么向女儿表达她的爱,但是佛罗伦斯不能理解。在铁匠的房子里,她梦见自己在一片湛蓝的湖边,当她靠近水面时,她看不到自己的脸,连个影子也没有。“藏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藏呢?”[3]152她仍然不能理解大自然给她的暗示。直到铁匠因为误会让她离开,佛罗伦斯终于明白她的脸不在蓝色的湖里暗示了在铁匠眼里她没有自我,只是一个粗野的奴隶。历经磨难后,佛罗伦斯开始自我反思,逐渐意识到没有精神独立连爱情都得不到,精神自由对女性极其重要。由此可以发现她的主体意识被唤醒,开始自我认同的建构。回到农场后,佛罗伦斯不再温顺,而是变得野性。她在墙上刻下了告白:“我还是佛罗伦斯。从头到脚。不被原谅。不肯原谅……奴隶。自由。我延续着。”[3]177通过最后的告白佛罗伦斯向铁匠所代表的父权制男性发出了反抗的怒吼,自我认同之旅得到了升华。小说的最后一章,母亲叙述了自己“卖女为奴”的苦心、无奈和深深的母爱,佛罗伦斯在告白结束时把对母亲称呼从最初的悯哈妹改成了妈妈,并对妈妈说:“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因为我的脚底板和坚柏树一样坚硬了。”[3]177至此母亲和女儿在心中达成了和解,弗洛伦斯找到了遗失多年的母爱,最终实现了自我建构。
如果说弗洛伦斯通过寻找失去的母爱找回自我,“悲哀”则是通过成为母亲完成了自我建构。“悲哀”是一位船长的混血女儿,经历了一次沉船事故成了孤儿。后来被好心的雅各布带回农场,唤作Sorrow, 意为悲哀。因为心里障碍,她性格孤僻,只和她自己幻想出来的“双胞”交流。“双胞”是她的”安全保障,是她的快乐所在,是她的向导”。[3]133“双胞”成了她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她的灵魂,表现了”悲哀”深切渴望追寻自我。“悲哀”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在两名白人承包工人的帮助下,凭借勇敢和冷静,她最终在水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水象征着自然,表明自然在女性寻求自我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悲哀”的生产过程就像万物在自然界的生长的过程一样,水中的婴儿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说明了大自然在人类延续过程中的重要性。“悲哀”成为母亲后,她从一个没有自我的个体蜕变成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她自信她这次独自完成了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她当即就知道了该给她起什么名字。该给自己起什么名字。”[3]148她把自己重新命名为“完整”“双胞”也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悲哀”最终实现了自我独立,成为莫里森描写的女性角色中自我建构最成功的。由此可见,融入自然与女性的自我建构紧密相连。
(二)建构和谐的两性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和女性是相互依存的,“女人承担和男人一样重要的任务,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而男人并不感到威胁,因为他需要她”。[6]只有男女平等协作,互补互助,才能构建多元和谐的世界。在小说中,莫里森不仅描写了被压迫妇女的悲惨遭遇,也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在她看来,男性和女性只有互相尊重和依赖,才能建构一个和谐的世界。雅各布意外地继承了一个120 英亩的小农场,但是“土地似乎拒绝遵从他的意志”[3]54,他遇到了各种困难,是莉娜教他如何种植和看管家畜。女主人丽贝卡来到农场后,他丝毫不必操心农场的营生,因为“丽贝卡和她的两个助手像日出一样可靠,像柱桩一样牢固”。[3]22雅各布坚信女人天生比男人可靠。起初,农场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和共生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仁爱,非中央集权的社区”。[7]雅各布的农场犹如“伊甸园”,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观念、不同身份和利益的人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互相帮助,亲如一家。在承包工人威拉德和斯卡利眼里,在农场里有父母(雅各布和丽贝卡),姐妹(莉娜,弗洛伦斯,和“悲哀”)和儿子(他们俩)。在小说中,莫里森把雅各布的农场描绘成“伊甸园”,表达她对一个新型和谐社会的渴望,在这个社会里,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和不同阶层的人可以克服种族和性别歧视,彼此和谐相处。
四、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的“终极关怀是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8]《恩惠》通过解构父权制统治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建构了一个多元的新型和谐世界,表达了莫里森希望解放女性和自然,实现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同时,也为我们缓解生态危机,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多元的社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