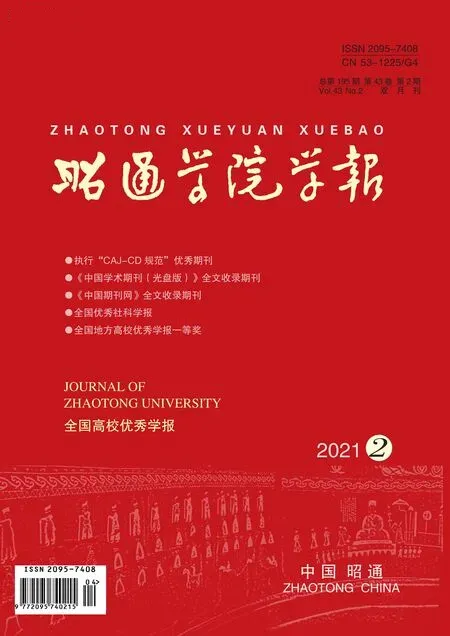电影《玻璃城堡》的空间叙事结构和符号影像
马丽君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部,广西 南宁 530007)
一、前言
电影《玻璃城堡》改编自200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出版后持续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250多周,其被改编为电影并于2017年在北美上映,由奥斯卡影后布丽·拉尔森和实力派巨星伍迪·哈里森领衔主演。影片通过美国著名记者珍妮特·沃尔斯离奇曲折的家庭生活和成长经历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后期嬉皮士登场,世界都疯狂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本土特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种族等问题。
影片名为“玻璃城堡”,但影片从始至终都没出现过“玻璃城堡”。父亲雷克斯许诺为孩子们建造一座拥有太阳能电池和水净化系统的“玻璃城堡”,孩子们盼望憧憬着,然而这个耀眼的建筑最终只停留在了父亲“宏伟壮观”的图纸上,地基只是填满了废物和垃圾。虚无的城堡贯穿整部影片,如影随形,它是孩子们艰难颠沛童年生活中唯一的光明和信念,同时也如一个符号印记深深打入孩子心头,映照和讽刺着他们扭曲痛苦的成长历程。
导演德斯汀·克里顿善用空间语言,如《少年收容所》中的收容所、贾登父亲的车。作为其又一力作,《玻璃城堡》也隐伏着大量的空间叙事符号,如美丽虚无的城堡,承载一家人四处漂泊、破败陈旧的汽车,堆满杂物密不透风的汽车后尾箱,犹他州古老矿业城镇孱弱无生气的小白屋,腐朽昏暗的韦尔奇老家,东倒西歪、无水无电的霍巴特街93号,纽约下东区废弃大楼中老鼠洞般杂乱黑暗的贫民窟等等。这些符号影像交织于银屏,呈现出独特的空间叙事结构。
二、空间影像建构的宏大叙事
建筑与电影两个“空间艺术”可交叉共存。库伯联盟建筑学院院长安东尼·维德勒说过:“建筑在电影布景的营造中起着显著的作用,而电影同样有能力通过光与影、尺度与运动“建构”自己的建筑。”[1]《玻璃城堡》中顺叙与插叙并行,现实和回忆交错推进,平实又荒诞的美国家庭生活与“城堡”、饭店、木屋、小酒馆等建筑影像共同交织在三层空间叙事中,激活和突破了呆板而平直的叙事线。
(一)社会体制层面
电影故事开始于纽约一个灯火明亮、服务员环伺的豪华餐厅。二女儿珍娜盛装打扮,陪同金融精英未婚夫与他的大客户一起用餐。珍娜优雅风趣,谈笑风生,魅力四射。接着珍娜坐出租车回家,这时镜头一转,空间色彩变暗,窗外街道旁出现了在肮脏凌乱的垃圾堆里翻捡破烂的母亲以及衣衫破旧、脾气暴躁的父亲,两人与成熟干练的华尔街都市丽人珍娜顿时形成巨大反差,更与前面高贵优雅的豪华餐厅格格不入。珍娜表面平静无波,但是身体却不由自主的滑落下去,害怕父亲认出自己,更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样饥寒交迫的父母。如此的空间视觉反差在影片中时常出现,如高档时尚的婚房与摇摇欲坠、残旧破败的小木屋的反差;璀璨辉煌的纽约大城市与僻静荒凉的韦尔奇小镇的反差;干净卫生、服务周到、饮食充足的医院和无水无电、了无生气、食物缺乏的儿时之家的反差。
强烈而频繁的空间影像对比,让我们不禁思考导演的真实用意,难道只是为了展现珍娜自强自立、脱离贫困的励志人生?其实不然,联系影片名称“玻璃城堡”,答案跃然而出,因为“城堡”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符号性的概念。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历史长河里,城堡承载着西方的建筑文明和社会文化,深植于西方人的文化和精神理念之中,对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影响深远。城堡伴随权利而生,高墙铁壁,沧桑、沉重而禁锢。“禁锢”是城堡本身固有的一个符号意义,《美女与野兽》《对垒风暴》《黑林城堡之犬》等电影中都有表现。《玻璃城堡》也同样延续这一主题,冷静深刻、鲜明残酷地述说着文明对原始的禁锢;工业化大都市对自然的禁锢;上流社会对底层社会的禁锢;秩序对于反抗的禁锢;还有白人对黑人禁锢。
“繁华都市,富豪比肩,高楼耸立,但空气污染太严重了,连星星都看不见。”父亲福克斯精通天文地理,亲近自然喜欢冒险。他教授孩子们关于沙漠植被、熔岩地质和宇宙星空等知识,但也空想冒进,反对学校教育,不喜城市文明,抗拒政府救济。他鼓励孩子们从生活中学习,不让孩子们接受正规教育,认为学校都是“骗人的”,医生说的也是“鬼话”。他拒绝与珍娜的主治医师握手,因为“全家人三个月不吃饭,才够医生购买一辆豪车”。雷克斯对“有钱人的代表”——珍娜的未婚夫戴维也颇为不满,曾一拳将其鼻子打开花,同时他还在珍娜的订婚仪式上大肆戏谑讥讽所谓的上流成功人士。
雷克斯是个退伍空军,接受过正统国家意识形态的熏陶,可是面对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摧毁和虚假伪善的社会制度,他心生愤慨,进而酗酒麻醉,远离社会,排斥文明,与喜爱艺术的妻子带着4个孩子常年开着破车游荡在美国各地,正如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中的人物一样,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唯有漂泊和流浪。雷克斯目光敏锐,能清晰指出“这是一场土地抢夺,政府官员用纳税人的钱拆楼,然后把产权分给开发商,再与开发商秘密分红”,然而作为“制度之外”的平民百姓,他又空想而没有执行力,只能被禁锢在沉重压抑的“城堡”中,横冲直而找不到出路,正如临死前对珍娜所说:“我耗尽一生,在旷野中搜寻那些恶魔,却没发现它们一直藏在我的身体里。”
自然与文明体制的冲撞和矛盾,在影片中是通过空间色彩和影像的对比来突显的。如前期流浪时自然风光明亮,一家人欢声笑语,轻松愉悦。可是当珍娜不幸被火灼伤住院,医生和社工追问雷克斯孩子们的教育和医护问题时,在面临着自然与社会重新接轨、医疗费用和社会体制等现实问题时,无助的雷克斯只能叫小儿子布莱恩装病搅局,趁慌乱抱走珍娜,仓皇而逃。从此,光明快乐不再,剩下的只有底层百姓的苦难和脱离社会进程的悲哀,晕黄和昏暗的空间色彩开始浮现,明显不同于前期,珍娜三姐弟连同出生不久的小莫莉都被关进密不透风汽车后尾箱,四处逃窜,所到之处皆为上帝所遗忘,所居的屋子一个比一个破烂,承载着一家人温情欢快的汽车空间气氛也变得沉重,在奶奶厄玛意图猥亵布莱克后,父亲雷克斯终于爆发,将珍娜从汽车中强拉下车,再次逃离酗酒,珍娜与父亲的信任之弦骤然断裂。
“禁锢”意识还表现于种族。美国黑人于1863年被宣布解放,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不得不依附受制于白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种族歧视和隔离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如影片中,公共游泳池只有早上一个小时对黑人开放,其余时间不得进入。白人限制禁锢黑人,黑人仇视憎恨白人,泳池白人管理员被父亲雷克斯暴揍时,黑人远远围观,无一人出手帮助,管理员逃脱后,黑人还心有不甘,齐声唏嘘雷克斯:“为什么放了他?”
导演德斯汀·克里顿通过空间禁锢符号冷静客观地向观众展现了文明进程、社会发展和体制完善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评判倾向。片中珍娜豪华的屋子、时尚的工作环境和高雅的生活都是通过挣脱父亲,远离自然重新融入社会和文明所获得的,但是当父亲问她是否开心时她又犹豫了。餐厅中几番挣扎之后,珍娜终于反驳了丈夫的谎言,告诉上流人士她的父亲贫穷低微但也聪明伟大,最终奔向父亲,辞去工作,重返自然。珍娜从对社会文明体制的认可到迷惘抗拒是通过两次离开餐厅大门的不同影像来展现的。前一次的珍娜享受美好高雅的生活,与未婚夫轻松惬意离开;而后一次则深刻厌恶自己对于物质的屈服,压抑喘不过气,最终猛然推开了餐厅大门,逃离华丽的金色牢笼。当然,在表现珍娜从最初对父母价值观人生观极大的不赞同甚至憎恨再到片尾的突然谅解上,导演处理得有些生硬和不自然,但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黑暗是路途,光明是去处,那从来也永远不会降临的天国才是真谛”。[2]也许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文明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秩序与冲突、反抗与服从永远都不可能协调。
(二)家庭伦理层面
“欢迎回家,儿子。”珍娜的奶奶厄玛,一个有着三层下巴、脸色青灰的妇人将雷克斯一家迎入屋内,也将孩子们带入了雷克斯的原生家庭,近距离“窥视”父亲那散发恶臭,如“布满煤灰毯子”的童年。“她关节的响动,她龟裂结茧的双手……我根本无法呼吸。”父亲儿时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阴暗狭窄的空间里,一个身体遭受母亲侵害而无力抗争,唯有紧抱双臂蜷缩在自己“城堡”中的男孩。
沉闷的家乡,变态的母亲,痛苦的回忆,一切切迫使父亲远走他乡,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韦尔奇”对于雷克斯来说就是一道难以磨灭的创伤。游泳池内,妻子因为拮据提议齐家回韦尔奇时,雷克斯马上变得阴郁不安,并将内心的恐惧与愤怒发泄在了珍娜身上,几次将不会游泳的女儿用力拋入水中,差点让其溺毙,接着还跟游泳池管理员大打出手。
冷淡的家庭氛围和畸形的人伦关系是潜伏在父亲雷克斯内心深处的“原始伤痛”。原始伤痛一旦产生就很难改变,它可以被抑制、转换和改变,但不会被清除和消灭,它始终保持着初发之时最原始的纯粹性,深深潜藏人类意识深处,形成“本我”。影片通过两个空间景象展现了父亲对于“原始伤痛”潜意识的逃离和抗拒。一个空间是移动的汽车。在回韦尔奇的路上,父亲嘴唇紧抿,下颚紧绷,神态挣扎而痛苦,整张脸隐在黑暗中,模糊而闪烁,不同于妻儿脸上的明亮。第二个空间是自己的故居,一栋偌大却破败的房子。屋内的影像是颠倒而错乱。肥胖、苍白、性格古怪、行为变态的奶奶,孱弱乏味、没有存在感的爷爷,胡子拉碴、沉闷呆愣的叔叔以及平日开朗欢脱、嗓门粗大而进屋后却僵硬沉默的父亲。
韦尔奇故居的“浓墨重彩”,是导演试图借助这一空间抒写着人类对于家庭伦理的敬畏与反抗。奶奶厄玛无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生硬冷酷,监视和掌控着屋内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她喜欢一问一答且生硬无趣的电视节目;要求孩子们“不准在房间乱跑,不准大喊大叫,不准叽歪”;弟弟布莱克将难以下咽的青豆吐出,立马遭到她的重击。空间色彩与主人一致,禁锢而阴暗,窗帘时刻拉合,密不透风,只留一丝缝隙。这样的空间抑制人心,扼杀人欲,里面的人躁动着、挣扎着,急切破窗而出呼吸外面的空气。
对于原生家庭,父亲逃离又回归,内心挣扎和恐惧可想而知,他坐立不安,神情闪烁,害怕和抗拒着家庭伦理的再次捆缚。可是挣扎越用力绳子勒得越紧,父亲雷克斯始终无法逃脱社会体制和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对家庭伦理道德有着潜意识的遵从和敬畏。因此,当母亲不顾儿子威望在孙子孙女面前奚落他时,他沉默不吭声;当珍娜维护弟弟骂厄玛老巫婆时,他拍案而起,他大声要求女儿尊重他的母亲;当获知厄玛去世时,他悲愤的用椅子砸碎了窗子的玻璃;在厄玛的葬礼上,他穿着前所未有的正式,神情哀伤而肃穆。
(三)自我本体层面
影片中父亲雷克斯清醒与昏沉交替出现。清醒时博学多才,擅长工程机械,会带着孩子们装修房子,在荒野中追逐恶魔,并手绘可以看见星星的玻璃城堡;昏沉时酗酒无度,沉迷赌博,对孩子不管不顾,甚至偷窃孩子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你从未想过建一所玻璃城堡。”伤心失望的珍娜将手中罐身已被划破、分毫不剩的储钱罐愤怒扔向父亲,拒绝父亲再用美丽的城堡谎言欺骗自己,毅然脱离家庭前往纽约。
一只笼子去寻找一只鸟。[3]“城堡”既是救赎也是牢笼。雷克斯梦想建立心灵家园,渴望寻找强大保护,疗愈儿时创伤,将自己从现代文明带来的迷惘与困惑中解救出来。因此当儿子遭遇与自己同样来自厄玛的侵害时,无意识中隐蔽的原始伤痛突然冒头给予了雷克斯重重一击,他如迷失的孩童般手足无措地将内心愤怒伤心和憎恨全部付诸在了尚未成型的玻璃城堡上。“城堡”是“母慈子孝”,温情家庭和正常伦理的符号,是雷克斯即将溺水时能抓住的唯一稻草,他要喘气和呼吸,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再次提起笔准备继续建造玻璃城堡。可城堡最终没有建成,因为雷克斯本身是“秩序与混沌的交界。”[4]他知道城堡是家园的篱笆,疗伤的圣地,但更是力量的符号,秩序的堡垒,所以自始至终雷克斯都没想过真正踏入城堡。
昏暗阴冷的厄玛家,突然出现一束明亮的灯光,灯光笼罩下,洁白美妙的图纸与紧张颤抖、双脚不受控制不停抖动的男子形成强烈对比,接受或抗拒,前进或后退,影片巧妙而细腻地通过这一空间影像展现出了雷克斯内心的痛苦。“城堡”与雷克斯另外两次配套出场也运用了这一手法。第一次是父亲酗酒斗殴回到家中,酩酊大醉、憔悴不堪的父亲与晕黄灯光下的浸润暖意的城堡图纸的对比。在这缺水断电的破屋种为数不多的光明里,神思恍惚的醉汉没有买回孩子们急缺的食物,反而让女儿强忍巨大恐惧,拿起针线帮自己缝合因为斗殴而留下的狰狞的伤口;一次是父亲意图挽留即将离家的女儿,意志坚决、冷静隐忍的女儿与图纸旁眼神闪烁、顾左右而言它的父亲的对比,父亲明显紧张而逃避,拒绝相信女儿的背叛。
父亲力主打造城堡,可他与城堡却并不和谐。出现在图纸前的父亲永远都是疲惫沧桑和茫然,紧张纠结如困顿之兽,在逃离或建造间不断拉锯。作为心理治疗的箱庭沙具,城堡给人以封闭、防御之感,会让人心生强大的自我防御意识,力图逃避寻求保护。如《美女与野兽》中“丑陋”的野兽王子和《惊情四百年》中狰狞的吸血鬼德古拉,因为异于常人只能躲在荒凉寂寞的城堡中,等待爱人的归来。同样,城堡美丽华盖遮蔽出的安全之域将雷克斯与陌生恐怖的现实世界隔离,让他自由徜徉于自然世界,遗忘原始伤痛。可是城堡毕竟只是窒息中幻化出的乌托邦,这个理想之国是玻璃材质,通透而易碎,美丽而不真实,里面楼梯、天花板、电能系统等一切还井然有序,宣告着雷克斯本我对秩序伦理的依从,而这都是他努力逃脱和极力抗拒的,因此城堡虽美,却不是雷克斯的终极之所。
三、空间叙事符号化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将空间与社会相连,用“全景敞视”说明空间基础与权力运作紧密不可分割。城市社会学理论奠基人列斐伏尔又将空间分为物质、精神、社会三种,最重要为社会性空间。他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关系重组和秩序构造的过程。[5]空间具有社会性,是权力和制度运作的基础,规劝和训导着空间中的个体。同样,《玻璃城堡》通过社会、家庭、个体这三层空间叙事展现了传统公开野蛮的统治已转为隐蔽的心理上的禁锢,没有人能脱离社会脱离体制而活。
影片的空间影像充斥愤怒与抗拒,同时也贯穿着秩序,具有符号化的概念。父亲雷克斯能力超群,富有创造力,只要他愿意随便都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是他愤世嫉俗,酗酒赌博骗钱,与人不和,每次工作都做不长久,孩子们跟着他四处流浪,挨饿受冻,不能接受正规教育。而且他拒绝政府救济,逃税逃医药费,一家人居无定所,家徒四壁,孩子缺乏基本的物质和安全保障。二女儿珍娜做饭被火灼伤,还没治愈就被带出医院;弟弟布莱克头破血流没钱去医院,只能缠上几层纱布了事;最小的妹妹莫莉饿得头昏眼花,被迫用黄油拌糖充饥,面对此景,大姐洛里愤然向父母大声喊出:“我们饿了!”孩子们唯一温馨的记忆来自于父亲戒酒后的圣诞节,因工作获得薪酬后的雷克斯终于让妻子和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和吃上了美味的食物,而这些都来自于对秩序的服从。
权力通过话语权表现,空间、知识、权利三位一体,教育生来具有社会性。和《死亡诗社》《神奇队长》《蒙娜丽莎的微笑》等影片一样,《玻璃城堡》也展现了美国的教育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风潮下,教育倡导自由,要求解放,如雷克斯讨厌学校,拒绝正规教育,他与妻子自己教授孩子们知识和文化,鼓励孩子们探索自然和宇宙。在他们的教导下,孩子们喜爱看书和学习,一个个快速立足于纽约,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雷克斯又过于极端偏执,他极力贬低教育,认为学校迂腐伪善,不值一提。孩子们主要成长空间是东倒西歪、破旧寒酸、与社会现实完全隔离的小屋。而且为了躲避追债,一家人行经之地多是偏僻荒野的城镇。韦尔奇光线昏暗、烟雾缭绕的小酒吧中,父亲赌友罗比一语道破:“我们都是热锅上的虾蟹,不知何时就会被烹熟。”在这种为社会经济发展所抛弃的破败城镇中,孩子们学不到正常的交往和社交方式,他们潜意识畏惧社会,因此最终洛里选择做自由画家,风格奇幻;珍娜的衣物放在箱子中,时刻准备离开;莫莉成为“巨婴”,住在父母家中靠父母养活,根本无法融入社会。
四、结语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人际关系的组合,空间中有着既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系。如雷克斯不满当局,嘲讽政治,但是他自由冒险和刺激的生活方式脱离社会,最终只能给孩子们带来不幸,永远无法建造玻璃城堡,因为要想看到城堡内的美丽风景,必须先进入城堡,接受城堡的秩序与统治。《玻璃城堡》充斥建筑空间群像,每一个空间符号都独具隐喻和象征意义。影片的空间色彩由前期的明亮清新变为后期的暗淡沉静;空间中的人从自由欢快转向束缚悲伤;空间气氛也由轻松愉悦逐渐压抑苦闷,深刻展现着反传统反理性思潮下,深处精神危机和悲观情绪的现代人的挣扎与困惑,并且正如雷克斯与妻子之间的抽象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虚幻与现实、抗拒与遵从、颠覆与重建的争斗将会一直存在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