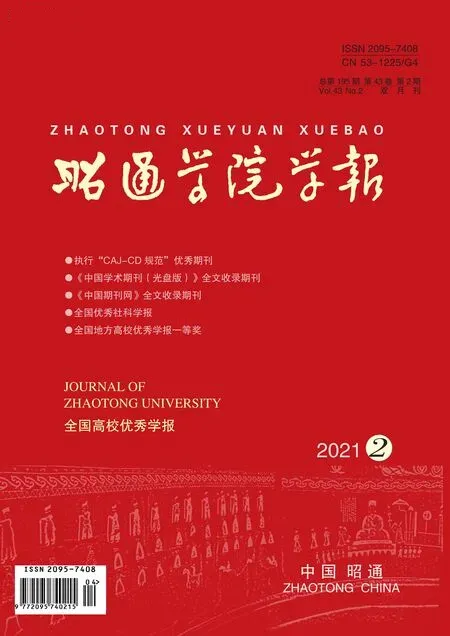梁宗岱与中西诗学精神的汇通
孟亚杰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关键字:梁宗岱;中西诗学;比较诗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方思想与意识,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碰撞,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和意识的觉醒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应该看到,在五四初期存在的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而片面否定传统的情形。李长之就曾反省说,五四运动是移植的,是从西方折来的花,不是根植于本土的营养。[1]到了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重新认识,不一味地追求西方,而是同时吸收借鉴两者中合理的元素。而在这些学者中,梁宗岱是十分突出的。他的诗论融合中西,以其开放性和独特性实现着中西诗学的对话。
一、梁宗岱与象征主义
提到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人们自然而然的便会想起瓦莱里,这源于其在法国留学时与瓦莱里的深入交往,以及他对瓦莱里诗论和象征主义的推崇。梁宗岱终生也对瓦莱里和象征主义保持了极高的热爱与评价,他曾评价瓦莱里说:“梵乐希底诗,我们可以说,已达到音乐,那最纯粹,也许是最高的艺术底境界了。”[2]20这是因为在梁宗岱看来,象征主义能够超越现实人生,使作家作品摆脱功利性,创作纯粹,也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与作品的精神世界契合。因此他推崇的西方作家多多少少也都与象征主义有联系,比如波德莱尔、布莱克,他们一些作品也被梁宗岱视作艺术的典范,视作可效仿的对象。除了在作家作品层面的推崇,象征主义的精神也几乎渗透到他每一篇批评文章中。在他这里象征主义不是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运动,而是作为艺术理想和创作原则存在。他认为最上层的作品都是有一定的象征高度的。此外,立足于彼时中国浪漫主义与自由诗的发展情况,梁宗岱认为虽然它们还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相比之下,象征主义更能赋予文艺无限的未来,所以只有与象征主义对接,中国文学才能实现质的转变。当然,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推崇和介绍绝不是盲目的,他十分清楚了解象征主义的精神本质,所以并不是像五四初期大多学者生搬西方思想一般照搬象征主义的模式,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将其作为一种参照系,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新诗的发展。
由于社会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民族在哲学意识和审美意识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思维习惯上,中国人衡量关注现实人生的标尺是伦理道德,因此常为现实世界束缚;而西方则更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考。这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中国文学重视作品的教化功能,关注作品的实用性。虽然增强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但也使得作品成为载道的工具,功利性过胜而内在审美深度不足,影响文学艺术的生机。这样的局限,梁宗岱曾感叹说,中国人由于思想狭隘被现实生活禁锢而普遍的缺少宇宙意识,而他又认为是否具有宇宙意识直接影响作品的高下,宇宙意识是伟大作品的必备元素。他认为歌德、瓦莱里等人的诗作之所以能够长久的感动人心,便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的追问和反思,他们的作品拥有永久的哲理:“我是谁?世界是什么……”[2]22他也赞赏陈子昂诗中具有的宇宙意识,“古今中外底诗里有几首能令我们这么真切地感到宇宙底精神?”所以他把宇宙意识精神引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纠正中国文学过于功利化的追求,希望中国文学具有审美深度和跨越时空的穿透力,也要求作家创作的深度和对文学的虔诚。
二、梁宗岱与中国传统诗学
梁宗岱曾在海外学习多年,对象征主义也是极尽推崇和热爱,因此有些学者说他是个象征主义者,但梁宗岱并非全盘西化的学者,在他的批评理论中也随处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与承继。他把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形容为一次回乡的心灵历程,如发现桃园一般新鲜、惊喜甚至销魂。[2]30在梁宗岱的艺术原则与世界里,中西方诗学都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中国诗学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同样具有西方诗学所不具备的特征,比如中国诗学中的自然、和谐、顿悟、直觉等古典审美范畴。梁宗岱也经常用带有明显中国的美学范畴来品评瓦莱里的著作:“它并不是间接叩我们底理解之门,而是直接地,虽然不一定清晰地,诉诸我们底感受和想象之堂奥”,这里便是用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感觉、重感受来解释介绍瓦莱里的诗作,即其诗作直面我们的感受情感,理解其意义反而处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这样用中国传统诗学来阐述西方现代的作品,也可以看作是梁宗岱为中国传统诗学现代化转向做出的尝试与努力。从他与朱光潜关于象征的不同看法,也可看到他的这种努力,朱光潜认为文艺上的“象征”与修辞学上的“比”极为相似,梁宗岱则认为《诗经》中的“兴”更能道出象征的微妙之处,还做了十分精微的分析。此外,梁宗岱还用王国维的情景关系理论来说明象征。总而言之,中国古典诗学的相关范畴在梁宗岱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与激活了它们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前述提到,梁宗岱引入宇宙意识是为了纠正中国文学过于功利化的追求。梁宗岱是一个对中西方诗学精神都十分了解,且具有民族自豪感的学者。所以在接受西方,引入西方的时候,他也同样注重为这些西方范畴找寻中国本土基础。关于艺术功用性的问题,我国的庄子主张取消文艺的功利性,追求超然的心态、忘我的境界及精神的超越。正是基于此,梁宗岱的诗学也承继了庄子的艺术精神。他曾说:“《庄子》对中国人的艺术感受性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深远”[3]。在《象征主义》一文中梁宗岱曾说瓦莱里是“一往凝神默想,像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宇宙万象,只足以助他参悟生之秘奥”,这就是说他认为瓦莱里是我国古代的先知一样,通过保持虚静状态而慢慢达到了物我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即”心斋”与”坐忘”。他用这一中国道家用语来关联瓦莱里与中国古代先知的阐释,便是其进行西方范畴本土化、民族化很好的例证。此外,在论述庄子艺术精神与象征的关系时,他认为“物我一体、形神两忘”是象征的最高境界。[2]73这便是把西方诗学的象征与中国传统审美心理贯通起来。除却在接受与阐释西方诗学过程中自觉或有意承继中国传统诗学精神,梁宗岱许多理论文章也都体现了他对中国诗学精神的完整把握,比如对“比”“兴”的细致辨析,对“意”和“象”的区分,对陶渊明谢灵运诗境界高低的比较,甚至对佛家“禅机”的理解,都彰显着他诗学体系中的传统文化情怀。
除了在内在精神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承继,在形式上,梁宗岱也表现出对中国诗学的热忱。中西方民族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异,同样也体现在诗学用语上。西方批评话语追求体系逻辑的缜密、结构的严谨与语言的知识性分析,而中国诗学不太重视内在的逻辑,也不依照固定的程序,较为讲究语言的华美诗意与整齐对仗,大都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且隐喻极多,因而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与阐释空间。作为较早接受西方思想与教育影响的学者,梁宗岱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且他在海外学习多年,当然清楚中国诗学存在的缺陷,但他并未像当时多数学者那样忙于移植西方的批评话语而丢弃中国传统诗学。而是合理运用中国诗学中的元素,将诗与批评结合起来,使得他的文学批评他避免了过于学院化的倾向,文情并茂又逻辑严明。诗人彭燕郊曾评价梁宗岱的诗学文章说:“写说理文字的笔端常带感情”“一般认为,诗人之论往往敏感有余而冷静不足。诗人之论重文采而轻逻辑,理论家之论则刚好相反梁先生则往往能兼具两者之长”。也就是说梁宗岱的文学批评能够做到抒情与批评风格兼具。
除了在诗学文章中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继承,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梁宗岱也有着强烈的热忱。梁宗岱由新诗创作进入诗坛,综观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几年的诗歌创作,梁宗岱的诗歌在美学和诗艺上都很突出的。从欧洲留学回来之后,更为追求强调诗歌的形式,称自己不可救药的爱上了形式,认为诗歌的意义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那“芳馥的外形的”。比如面对被新文化运动者抛弃的词,他认为小令和长调正式词的特长,正是因为它们有长短才能配合我们的情感。对他的这种认识与进行的创作,卞之琳认为是倒退和复旧,但也可以看作是梁宗岱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留恋。梁宗岱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着极高的艺术追求,他曾经说一个作家应以创造有生命的且美丽的东西为戒条。当然,理想与实际创作是两回事。就实际情况来说,梁宗岱的理论高度是远超他的诗歌创作的,所以我们熟知的也是他作为理论家、批评家的身份。但是他内在的诗人气质和灵性及在创作时获得体验、总结的经验肯定会影响他的理论批评与建构。李振声在评价梁宗岱《象征主义》一文时曾提到:“梁是诗人,他是以诗的笔触去探涉理论问题的”。如此种种也使得他的诗学体系呈现出一种十分难得的灵性与诗意。在梁宗岱的诗学文章中很难见到深奥的学术用语,随处可见的是诗情画意。梁宗岱的批评话语范式接近散文体,在论述一些问题时也常用评点式、片段式的语言,且语言优美,潇洒自如,十分具有中国传统诗学点到为止、顿悟的意味,虽如此,且丝毫不影响说明阐释的效果,如他的《谈诗》。梁宗岱的文字还十分富有想象,这是因为他在行文中喜用比喻,评价瓦莱里时:“像群蜂把远方的音信带给芳馥的午昼一把,在他的心灵深处嗡嗡飞鸣,要求永久的不朽的衣裳。”评价《九歌》时:“它们本身就是一座幽林,或骤然降临在这幽林的春天。”[2]218如此的例子在《诗与真》中俯拾皆是,他这样善用奇特比喻来说明抽象道理的实践,与我国古代的孟子颇为相似,另外受传统文化的而影响,梁宗岱还曾从事过一阵子医药研究为着造福乡里,可以说既有诗心又有侠义心肠,如此说来,梁宗岱不独在理论与创作层面与中国传统诗学一脉相承,在个人精神与行为上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连。也正是这些文化与精神,为他的诗学体系提供了广阔强大的思想支撑与表现方式。
三、梁宗岱的比较诗学
叶维廉认为五四本身就包含着比较文学的课题。诚然,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的碰撞下产生。早在20世纪初,便有学者有意识将中国文化、文学与西方进行比较,以及进行中西学术交融的尝试,如刘师培、王国维、鲁迅、矛盾等人。综观梁宗岱的诗学体系,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对中西诗学比较的实践与实现。
中西诗学的比较是宏观的文化与思想层面的对比,也是微观的理论、范畴、观念、风格文体等层面的比较,对研究者的素质和眼光都有很高的要求,研究必须能够透过大量的文化现象与繁杂事实把握住两者在精神上存在的共通与异同。梁宗岱曾说:“正当东西文化之冲,要把二者尽量吸取,贯通,融化而开辟一个新局面——并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非明目张胆去模仿西洋。”[2]43这就是说在他的意识里,中西文化是平等的,两者的碰撞并不是极端的“存此消彼”,而是相互交融、共通,如此才能开拓新局面。这样开阔的视野与文化态度便决定了梁宗岱是用一种极为理性的思维去看待中西诗学,站在两者的共通之处去审视和实践,从而极大地避免了只照搬一种文化模式的各种问题与局限。比如我们熟知的他对象征主义、宇宙意识、纯诗理论等范畴的阐发,便是从精神本质上证明中西诗学的渊源与交汇,实现了两者的汇通。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象征主义是纯粹的西方舶来品。中国新文学早期的作家诗人如李金发、穆木天等人对象征主义也是这么介绍的——来自西方语境。他们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也是生搬硬套,难免水土不服与本土排斥,所以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小。与前人把象征主义作为完全的西方舶来品不同,梁宗岱认为在美学原则上,中国文学中也存在大量的“象征主义”。
梁宗岱通过大量例证对比证明并阐释了象征的特性即“融洽或无间”与“含蓄或无限”,在中西诗学中均存在,西方的歌德、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等的作品,中国的屈原、陶渊明等的诗作,乃至日本诗人芭蕉的作品都存在这样的特性,所以在最高的美学原则上中西方诗学是相通的。如果中国传统诗学中也本存在象征的足迹,而由瓦莱里系统阐释的“纯诗”理论,则完全初期西方的文化语境。瓦莱里认为纯诗就是不掺杂任何非诗歌杂质的纯粹诗作,就如纯水一般。这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他也认为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并且认为这样的纯诗在西方都很难找到,东方更不会存在。此番言论,显然是带有文化偏见的。但梁宗岱不这么认为,他依旧将纯诗理论置于中西比较的框架中,来挖掘其中中国和西方诗学共有的元素,以此证明纯诗在中西方都存在,西方的瓦莱里、马拉美等象征主义作家,中国不同朝代的诗人,如屈原、李白、姜白石等人的作品中都有纯诗的范例,并且中国的纯诗作品丝毫不亚于西方作家。他说,中国古诗词中有很多纯诗作品,姜白石的《暗香》《疏影》等作品营造出的世界就十分美妙,纯净,“度给我们一种无名的美底颤栗么”[2]88
中西比较中较常见及常用的方法当属平行比较。因为文学艺术就最高的哲学和美学原则来说,古今中西均有想通的地方,如此便为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行比较提供了条件。梁宗岱在实践中西诗学比较时,最常用及出色的也是平行比较,关注作家作品本身,根植于实证,通过自身开阔的视野,包容的文化态度,理性的艺术思维实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文学的对话交融,印证了跨文化诗学汇通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中国传统诗学精神与西方诗学精神本是产生于不同、在某些层面上甚至对立的文化语境中。五四运动使得两条本来平行的线发生碰撞,也带来对两种不同模式的比较和反思,在对西方学习接受的过程中,难免弯路。梁宗岱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西方诗学之长来纠正中国诗学的局限,但不厚此薄彼,在接受西方诗学精神过程中重视找寻本土精神之基,在接受西方的同时,也承继中国传统诗学精神,融合两者之长,从中也可看到梁宗岱对中国传统诗学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与实践。此外,其诗学体系也以独特性和开放性实现了中西诗学精神的汇通对话,虽然对这些“汇通点”的搭建有些单薄,但作为跨文化交叉视野的一种尝试,其本身就十分具有价值,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