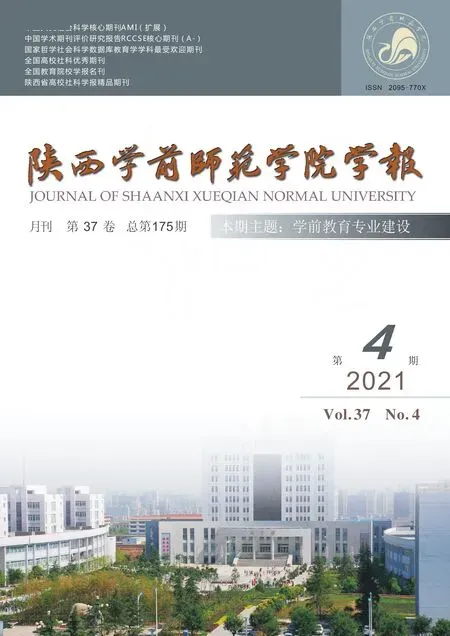从甲骨河卜辞看殷商人的神灵建构
崔 凤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我国神话产生甚早,涉及内容广泛,但由于后世出于“雅驯”的目的,对神话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对神话研究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所幸的是,甲骨卜辞中保留了大量未经篡改的殷商先民的“神”以及神话思维。甲骨文中涉及“河”的卜辞较多,根据“河”所指之不同及各卜辞内容的差异,大致可以看出殷商先民的神灵建构。
一、由实物而物神——万物有灵
“河”字在甲骨文中最早是作为其本义——即实物而出现的。这也符合造字规律与用字规则:为具体之实物先造字,而抽象之物后造字或借字来表示。作为实物的河例证如下:
(1)壬辰王其涉河……易日?(《合集》5225)
(2)贞:往于河有雨?(《合集》8329)
(3)有虹自北饮于河。(《合集》10405 反、13442正)
(4)至河,毕其戎飨方。(《屯南》1009)
(5)王令毕供众伐,在河西北。(《屯南》4489)
上述(1)—(5)五例中的“河”均是名词,是地名,是处所,是可以抵达、可以饮用、可以跨渡、可以看到的实实在在的实物。其所指究竟是哪一条实物河?朱彦民在《论殷卜辞中“河”的自然神属性》通过黄河名称的变化、商代黄河故道的方位、传世文献记载等方面肯定了这样的结论,“在甲骨文中,作为地名的河,不是河流的泛称,而是专指流经商代晚期王都之东而向北去的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就是指商代之时流经殷墟都城东边不远处的大水系——今天被称之为‘黄河’的商时河道而言。作为一条重要的河流之专用名词的“河”,不仅甲骨文中的如此,在古代文献中就是指今天的‘黄河’。”[1]
并非甲骨文中所有的“河”所指均为实物,如:
(6)卯河。(《合集》1166)
(7)贞凡河于上甲。(《合集》1204)
(8)癸巳卜,又于河?不用。(《合集》34240)
(9)癸丑卜,何,贞祀河。(《合集补编》10356)
(10)癸巳贞:既燎于河……于岳……(《合集》34225)
上述(6)—(10)五例中“河”是作为祭祀对象(即河神)而存在的,不仅有明显“祀河”的表述,描述了其有赐“又(福佑)”“雨”的神力,并与商人逝去的祖先神“上甲”同时出现,且涉及到了“凡”“燎”“卯”等具体的祭法。
“河”由普通实物跃而为物神,是由于殷商时期人们秉承“万物有灵”的观念,即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说的“把自然物看作是本身具有灵性的实物”[2]715。“万物有灵观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它们构成一个完整学说的各部分。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2]414其实两个信条之间的联系正是“河神”的建构过程。这个连结的纽带就在于以人为视角的观照中“河”与人类的同异。第一个信条里,包括“河”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灵魂、思维、感觉,与人类的灵魂、思维、感觉性质相同,这来源于殷商时人“物我不分”的认识论。如果说第一个信条里人类认识到的是“我”与“河”的同,那第二个信条里认识到的是“河”与人的不同,或者说是河之所以成神的灵性所在。其灵性表现在其本身所具有的与人完全不同的水的形态、河水的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可以切实感受到的福利和灾祸。殷商时人仍保持“灵魂不死”的观念,认为灵魂均是肉体死亡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存在的,然河的“肉体”似乎是永远相对不变的,经历数代人死亡之后河的形态依然不变。再加上河水的起伏涨落运动,似乎出于某种力量的结果,这种无法解释的力量,被归结为神秘的力量。殷商先民生活在黄河流域,黄河是其生活的重要物资,是人类与家畜饮用水的重要来源,是灌溉得以实现的必备条件,可黄河又会因各种因素给人类带来灾害。如:
无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必然会引起黄河的泛滥与干涸,也必然会影响居住在黄河附近殷商先民的生产与生活。
所有的这些“灵性”都与人类以及其他动植物是不同的,正是因为“不同”以及对“不同”的无法解释,才产生了对“河”别样的感情,即“怕”与“敬”,这也是对所有神灵的感情,也是神灵建构中必然的过程。
二、神职混沌——综合之神
殷商为文明发展的初期,甲骨文中对于这一时期神话发展也有记载,其特点在于这一时期其实属于神话体系的混沌期,即诸神职能的交叉与重叠。仍以河神为例,河神的神力表现在人类祈求恩赐或饶恕的甲骨河卜辞之中,虽然有些研究论文认为河神有自己相对独立神职,如“‘令雨’是自然神的职能,卜辞中除帝之外,只有河有此本领……”[3],然而殷商人向河神所求甚多,包括求雨,又不仅仅是求雨。如:
(16)又于河?(《合集》9577)
(18)甲申卜,宾,贞告秋于河?(《合集》9627)
(19)戊午卜,宾贞:酒,求年于岳、河、夒?(《合集》10076)
(20)辛未贞:求禾于髙眔河?(《屯南》916)
向河神所求之物为“雨”“年”“秋”“禾”“佑”等,既有实在的庄稼,又有虚幻的福佑。虽说,丰收本就是多种因素综合才能形成的结果,通过向河神求适当的雨水进而求作物的丰收似乎也并无道理,可既然有这样多种因素综合思维的话,也就没有向河神求“年”的必要,向河神求雨,向风神求风,向太阳神求阳光就一定会丰收。且有“祈于河年又雨”的存在,表明“雨”与“年”是两回事。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向雨神求庄稼是通过雨神“令雨”的职能而完成的,只是符合现代的逻辑,并不符合殷商的实际。
况且也并非只有河神可以掌管雨水,如:
(21)丙寅卜,其燎于岳,雨?(《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0)
以上所举(21)—(25)之例,祖先神上甲、示壬、伊奭,自然神岳神,土地神社神都是求雨的对象。可见,河神的职能与其他自然诸神如“岳”“雨”“云”以及祖先神均有重复或者交叉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神其实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其职能还未有完全明显的划分或者区别。不能做到对于神职能之间大体的区分,如将自然现象只分管于某一个神或哪几种神。甲骨卜辞中的神从职能上说都是综合神。
这不仅是甲骨卜辞表现出来的事实,而且符合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当时神话所应该处于的一种混沌的初始状态。殷人向诸神求雨,其实是反映出当时对雨的认识,还是比较具象的,或者说是针对“雨从哪里来”这一问题的回答,其答案只是根据当时所观察出来的现象或思想的联系所做出的回答,雨水与河水形态相似,有云才有雨,高山处容易形成地形雨……所以,这种求雨于诸神的卜辞的存在,是其无法解释雨水形成过程的一种反映。诸神神力的交叉与重叠,功能的综合都是必然的。有人曾致力于构建甲骨文中神话体系,将自然之神进行了详细的划分,然这种分法只能说是依据现存甲骨神名的分法,若按照职能划分是是永远也无法分清的。故其在雨神之后又不得不客观地说“岳神和河神具有降雨的神力……[4]33,即便是陈梦家归纳为拥有令雨、令风、令蛴、降艰、降食、降祸等十六个方面的‘帝’”,本身也是综合神。或者说它的综合性并不是由于他在甲骨神话中的地位,而只是当时诸神特质的一个代表。这与事物的产生发展状态是有关系的,万事万物处于产生之初,本就是一片混沌。
三、河神形象——人神同性
甲骨文中虽未出现具体河神形象的描写,然其拟人化的形态极为明显,这其实是对神话研究中中国神“神性格”定论最有力的反驳。对于中西神话进行比较的文章历来不在少数,然有一点是被普遍认同的,即中西方神话中神性格不同,西方将神人化,而中国将人神化,如《中西方神话异同性探析》中谈到的“中西方神话中各种神的性格有着很大差异。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除了少数几位大多数都具有人性……像人类一样喜怒哀乐、欲望好恶,在血缘、思想、性情、行为方面跟凡人没多大区别。西方人将神人化。西方神话里的神不仅有美丽的外形,还有人类的性格情感、意志、欲望。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有着相同的外形,性格鲜明,同样有喜怒哀乐……古希腊人以自己的形象创作了神……中国人将人神化……在性格方面,中国的神多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神通广大,充满博爱之心,悲天悯人,为人类创造福祉,几乎没有西方神的负面性格。”[5]而甲骨文中保存最初最完整未经过加工和阐释的神话形态中的“神”与后期庄严肃穆、绝情绝欲及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神的形态不同,而是类似西方(如希腊)神话中的神。
(26)丁巳卜,其燎于河牢沉。(《合集》32161)
(27)辛已卜,贞:来辛卯酒河十牛,卯十牢?(《屯南》1116)
(29)己亥卜,贞:王至于今水,燎于河,三小牢,沉三牛?有雨,王步。(《合集》14380)
(30)贞:嬖珏酒河?(《合集》14588)
(32)贞:勿舞河,亡其雨?(《合集》14197)
(33)……雨,庸……舞……(《合集》12839)
(34)奏河?(《合集》14606正)
(35)癸亥卜,勿奏河?(《合集》14605)
在对河神的祭祀方式中,有舞祭、乐祭。在“乐舞起源说”中有一种观点就是“巫术说”,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就说到“歌舞之兴,其起于古之巫术乎?”[7]6。虽未必为确论,然以歌舞娱神,确是乐舞的重要功能之一。比甲骨稍晚些的《诗经》,有“风雅颂”之分,“颂”为宗庙祭祀之乐舞,祭祀娱神之乐“颂”与人世之乐舞“风雅”分明不杂,不相混用,足见商周时对以乐舞娱神的重视。娱神现象的存在,反过来也证明在商人的心目中神是有情绪的,有感情,所以才会欣喜。这种现象在《尚书·金縢》中也有体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6]495-496,也是以才艺来侍奉鬼神,以求鬼神的欢愉。会欣喜,当然也会愤怒,其愤怒表现在河神为祟作怪。
(37)河祟我……不我祟?(《合集》2415正)
(38)丁卯卜,惟河祟。(《合集》14619)
(39)壬午卜,宾,贞河祟我。(《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98)
(40)壬寅卜,宾,贞河祟我?(《英藏》1167)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说的“人在能给他带来丰足或不幸的物体中看到了影响他的生活的神……”[2]660,而且是有着和人一样情绪且能被引发情绪的神,“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高兴或不悦……”[2]414。
四、神系世界——殷商社会写照
甲骨河卜辞中展现出来的河神神系世界,说到底就是殷商社会的写照。申小龙在《汉字人文精神论》中论“汉字的主体思维”时说,“(主体思维方式)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8]96。当时殷商人即以自己生活的环境、社会制度来构建神系世界。
甲骨河卜辞中河神的“定性”为男性,证据为对河神家庭成员“河妻”等的称呼,与“妻”相对的是“夫”,是男性,如:
(41)辛丑卜,于河妾。(《合集》658)
(42)御方于河妻。(《合集》686)
(45)又于河女。(《合集》1403)
将河神定性为男性,这其实是殷商处于父系社会在神话世界中的折射,以男子为尊,男子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宰。父系社会相比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下降,甚至成为男人的附庸,河神系统中的“河女”“河母王”“河妻”“河妾”等均是依附于河神的称呼,连自己独立的名字都没有,其对男性依附性的凸显,更甚于甲骨卜辞中商王有名字的女性配偶,如“妣癸”“妣辛”等。殷商是宗法制的发展期,在河神的世界里,“河神似乎进一步形成了家族势力……”[9]。卜辞中河神的家族势力,尚未有子孙支派势力,只在河神及其妻室之间,如上文提到的“河妻”“河妾”“河母王”“河女”。河神的家族成员并不独立于河神之外,她们是随着河神的势力而拥有神力,从而成为殷商人祭祀和祷告对象的。这些女子在殷商卜辞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河妾”“河女”只用来占卜是否用其祭祀,而对于“妻”,则采用的是“御”“祈”等祭祀方式。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商王婚姻制度的认识争执不下,即是赞同以胡厚宣为代表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还是以陈梦家为代表的多配偶制。因为“妻、妾在甲骨文时期无贵贱之分,只有用法上的差别。‘妻’一般只指先王的配偶,‘妾’既可用指先王配偶,也可指‘子’等的配偶,即‘妾’使用范围更广。”[10]221。如果说称呼不能别贵贱,那祭法又该做何解释?且称呼之中,尚有另一点不同,即是否称“王”,如上述提到的“癸卯卜,史,贞来辛……于河母王”,称“河母”为“王”,而未见以“王”称呼其他女子。若以“神系世界——殷商社会写照”来反推的话,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更倾向于相信以胡厚宣为代表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商王婚姻制度。
商代实行内外服与王位世袭制度,无论领域大小,均有“王”的存在。故,在神的世界里,河神手握大权,类似于人类世界中“王”的存在。
(46)贞:翌甲戌河其令〔雨〕?贞:翌甲戌河不令雨?(《合集》14638)
(47)求于河年。(《合集》28259)
(48)庚申卜,其又于河。(《合集》30432)
(49)酒河五十牛?酒河三十牛,氏我女?贞:酒于河报?……有于河我女?(《合集补编》100)
河神手握大权,是卜辞中除了“帝”外唯一一个有“令雨”能力的神灵。“卜辞中以河为首的水神系统和以岳为首的山神系统也已经形成……”[9]。河神作为水神系统之首,并不是说甲骨卜辞中各系水神都在他的直接管辖之下,而是说他是水神世界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存在。甲骨卜辞中,也有他系水神,如“淮河”“洹”,然其在卜辞中出现次数及所占比例是远远不能与“河”(黄河)相提并论的。且“河岳神在赐福下世、保佑年成方面则又为帝神所不及。”[9]49中的女性虽与河神有关,然是以女子为贡品向河神祭祀。在殷商时人类王的世界中,身为统治者的男性,常有作为贡品而被献上的美女。故,作为与王类似的河神也被赋予了这种权力。出现以美女而不以男子向河神的献祭,是由于对河神的“定性”以及王晖在《商代卜辞中祈雨巫术的文化意蕴》中提到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阴阳交感巫术”。[11]50中殷商人还赋以河神人的世界王所用的仪仗,江世龙《甲骨文释读》释“戈”,“祭祀时仪仗队所用……”[10]54。总之,殷商人是以现实社会为参照来构建河神神系世界的。
五、小结
甲骨卜辞中保存的大量河卜辞,对于了解殷商先民的“神”以及神话思维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比卜辞中“河”之所指及卜辞内容的差异,阐释了河神被建构的过程、原因及其建构过程中殷商先民的思维。在“万物有灵观”下将河与人类对比,由“同与不同”而产生“怕”与“敬”的情绪,诠释了神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及过程;其神的形象,与传统印象中“将人神化”的中国神格不同,而是接近西方神话中的“将神人化”,即神具有人的情感、欲望、需求;甲骨河卜辞中展现出来的神系世界,是以殷商时期实实在在的社会为参照建立的,包括将神“定性”为男性以及祭祀所用的仪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