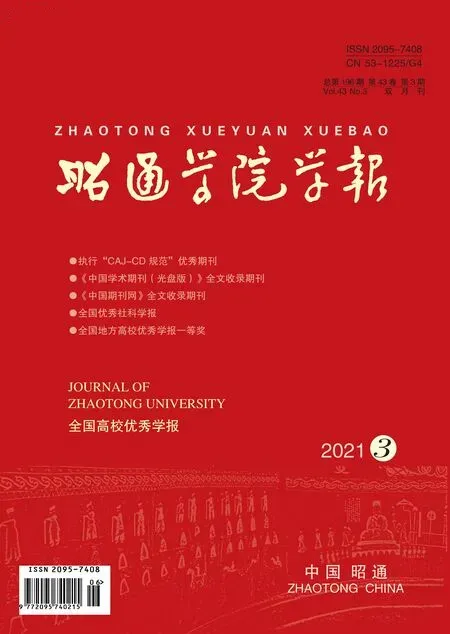如何理解“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
谢 姣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从柏拉图《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发端,艺术、诗与真理成为了西方哲学家的关注点。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论证艺术的合理性,不仅是一个现实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艺术)仍然要求拥有真理的权利。”[1]1艺术能不能体现真理?诗是真理的“创造者”或者“背弃者”?诗在艺术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话题关涉到哲学家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关系到艺术的地位。海德格尔关于 “艺术”“诗”“真理”关系问题的梳理,渗透了他的艺术观,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就这一问题的一次总结,对包括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内的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问题的思维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德格尔在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开篇指出:“本源一词在此指的是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的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某个东西的本源就是它的本质之源。”[2]1在第三节“真理与艺术”中,他提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2]59。按照前后文本的理解,海德格尔认为,一切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音乐、诗歌等,都“如期所是地”是诗。为什么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呢? 海德格尔好似听到了读者对于这一结论的疑问,在后面的文本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那么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就都势必归结为诗歌了。这纯粹是独断嘛!当然,只要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各类艺术都是语言艺术的变种——如果我们可以用语言艺术这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名称来规定诗歌的话,那就是独断了!”[2]60从这一段中,海德格尔认为,在承认各类艺术都是语言艺术的变种的基础上,就能得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的结论。同时,海德格尔还指出:“艺术的本质本身就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2]59由此可见,“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本质的本质。这里不止要看到“艺术”和“诗”的勾连,还应该看到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走向对“真理”的通达。由此,我们就不难从中剖析出海德格尔对于艺术、诗与真理关系的两重思考:
一、诗意的创造完成真理的生发
柏拉图在《理想国》讨论了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比如床,神创造了唯一的一张自然的床,也就是理念的床;木匠创造的床,是对自然的床或者说理念的床的模仿,它是不真实的,而且转瞬即逝;而画家创作的床,是对工匠创造的床的模仿,因此是模仿的模仿,和真实之间隔着两层。这样,柏拉图所说的作为模仿的艺术,自然不可能体现真理。柏拉图认为,“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它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3]396“模仿者对于自己所模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模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3]399艺术不但不表现真理,艺术创造的作品是远离真理的,它打交道的是心灵中远离理性的那个部分,并且向它学习。
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艺术的本性就是摹仿,但是他对于艺术之摹仿的理解却与柏拉图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念”是不存在的,木匠创造的那个特殊的床就是实际存在的。艺术不是一种模仿的技术,而是一种对生活、事件、行动的再现和创造。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是真实的,它能够带给人们知识,满足人们求知的需求。他认为写诗之所以富有哲学的意味,甚至超过了历史,是因为诗歌与历史描叙个别不同的是,它描写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事。这里所说的普遍性,“是指某一种人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4]28艺术能反映现实世界所具有的现实性和普遍性,也就是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而亚里士多德同时认为“探索真理必以保持常态而不受变改之事物为始”[5]219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能够体现真理。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的这种体现,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把握的,是从艺术对于现实的再现和创造上来理解的。
海德格尔指出“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2]22。但他同时发问,“艺术即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这一命题会使那个已经过时的观点,即那个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的观点,卷土重来么?[2]22海德格尔认为艺术能够体现真理,但显然他并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是对现实的再现。海德格尔认为,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常常把跟存在者相符看成是真理,但梵高的画并不是因为把农鞋描绘得惟妙惟肖才成为了艺术作品,也不是因为它把现实事物移置到画里就成为了艺术家所生产的一个产品。海德格尔对于艺术对真理的呈现,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理解的。他认为真理的自行设置,是由于存在者的敞开性,也即是存在者的“无蔽状态”,为真理的“自行设置”提供了场所和可能。
“生产过程把这种存在者如此这般地置入敞开领域之中,从而被生产的东西才照亮了它出现于其中的敞开领域的敞开性”[2]50,这一生产过程就是“创作”。对于创作过程的诠释,作品照亮了“它出现于其中的敞开领域的敞开性”,侧面揭示了真理是如何通过“诗意创造而发生”。 存在者的无蔽“不是一种纯然现存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发”[2]41。在澄明和遮蔽的斗争中,发生着真理;在真理的本质中,作品成为作品自身。艺术就在真理所开启的敞开领域中。在这种敞开性中,不同姿态的行动者显示为多样的形态,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显示而且使真理在于存在者的整体关系中生发出来。凡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到:“今天早上,我在教堂里看到一个小个子的老婆婆,大概是一个卖足炉的小贩;她使我深深地想起伦勃朗的铜版画,在那幅画中,有一个阅读圣经的妇女,她的头靠在手上睡着了。勃兰克写得很美,对这幅画的感触很深,我想朱理·米歇列在她的《女人是永远不会老的》这本书里所写的,也是这样。德·盖奈斯戴的诗《她的生命之路的尽头是孤独的》,也使我想起伦勃朗的铜版画。”[6]37教堂里小个子的老婆婆,朱理·米歇列在《女人是永远不会老的》中的描写,德·盖奈斯戴的诗《她的生命之路的尽头是孤独的》,都让凡高想起了伦勃朗的铜版画。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和时代,只要能和观者实现心灵的契合,真理就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实现了真理化。在此,各种艺术形式,诗、书、画,不过是一种具化的表达,它们都在“诗意的创造”中生发真理,显示出一种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各类艺术成为了“语言艺术的变种”。“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这里的“诗”不是“诗歌”,而是“一切艺术”都遵循的真理澄明着的筹划方法,是一种“诗意的创建”。
二、诗的本质蕴含着真理的创建
在对于诗的理解中,柏拉图认为,理性是善的,感情是无益而懦弱的;而最容易模仿的,恰恰是人不冷静的部分。诗人擅长的就是对人的心灵暴躁和多变的部分进行模仿,“(诗人)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3]404。不止如此,诗歌还有一个最大的罪状,就是它使让人纵情于“爱情与愤怒、以及心灵的其它各种欲望和苦乐”,让人心生怜悯,从而能够腐蚀最优秀的人物。柏拉图认为 “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3]401但比起绘画等其它艺术,柏拉图显然认为诗歌的危险更大。诗歌不仅本身是真理的背弃者,而且还能蛊惑人们背弃理性和真理。因此,他提出要把诗歌驱逐出治理良好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悲剧)能让我们感到快感,“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我们看到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是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4]11,他也认为颜色、音乐、文字等的美可以带来快感。在诗歌的创作中,诗人应该用言词把情节描写得惟妙惟肖,让人身临其境,就好像诗歌里面的情景都摆在观众面前一样。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语言在诗歌创作中重要性,也看到了诗歌的重要社会功能。他认为诗歌能够引起怜悯和恐惧而使情感得到陶冶,使情感处于适当的强度,将有利于心理的健康和社会道德。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诗,因为诗的本质中蕴含着真理的创建。他指出“所有作品都具有这样一种物因素”[2]4,而对于诗歌来说,它的“物因素”体现为“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语言是诗,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诗歌;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2]62。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不是人类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工具,不是有了人类然后有了语言,而是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类的存在。海德格尔还对语言进行了区分,分为技术语言和诗性语言,技术化的语言变得形式化、数学化和符号化,已经成为了形而上学化的语言,不能显现存在;而真正的语言就是这种诗性的语言,它是与存在相连的。语言首先“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使得存在者被带入敞开之域,而被显现出来。“在没有语言的地方,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为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2]61。正是因为有了语言的命名,物才能作为存在显现出来;如果没有语言,石头、植物和动物等物的存在就会被遮蔽,就不会被显现出来。语言本身就是诗,也就是原诗。同时,“命名”还意味着“道说”,“道说”是“澄明之筹划”。“道”是一种“不可说”,“道说”也就是不可说的说。人并不是先有了言说的能力,然后才有了语言;而是在应和语言的过程中完成了道说。在“说”之前,是倾听沉默的、孤寂的“道说”,然后才使它发声。对“不可说”进行一种“可说”的表达,把神秘的奥妙展现出来,达到无弊的真理敞开。“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诗就成为了本真的语言,成为了“存在者的词语性创建”[7]45。“创建” 包含着“作为赠予的创建 、作为建基的创建、作为开端的创建”[2]65。海德格尔指出,“建筑和绘画总是已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领域中”“它们是存在者之澄明范围内的各有特色的诗意创作,而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中发生了”[2]62。相比于建筑和绘画等其他艺术,诗是开创者,是意义的生发者;诗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其他如建筑、音乐、绘画等只有当它们具备有诗的含意的时候才是艺术的。
综上,“艺术的本质是诗”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因为“诗意的创造完成真理的生发”,正是诗意的生产过程将存在者置入了敞开的领域,从而照亮了存在者之无蔽的真理;在这种敞开之中,存在表现出各种迥然各异的形态,也就产生了各种艺术形式。二是因为“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诗意的本真的语言在本质上来说就是原诗,语言的命名,把物带到了敞开的领域,让它作为存在者被显现出来,从而让狭义上的诗歌得以在语言中生发;诗还是一种“道说”,把“不可说”以“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达成一种对生存真理的创建,为艺术提供了一个最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