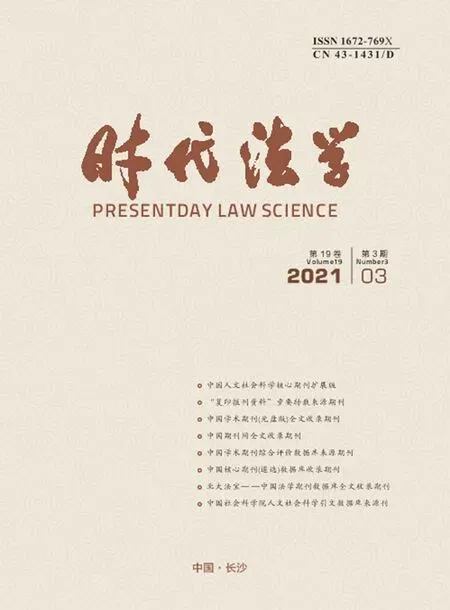数字贸易时代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
朱雅妮
(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引言
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共识。这种共识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某些领域倒退的情境下特别难能可贵。也有人认为这是全球化以另一种不似传统的方式进行,即通过互联网和数据的流动,让包括小企业、个体经营者等更多主体参与到全球市场当中。虽然数字经济初现端倪,定论为时尚早,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至少见证了这样一些经济发展的脉络:其一,世界货物贸易的增长在近二十年中遭遇了重大瓶颈。战后全球市场复兴给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然而,技术飞速发展缩短了全球价值链,商品需求率变低成为货物贸易增长乏力的结构性原因,数据流动加速了生产去中心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投资需求减少、货物交易及服务贸易供应成本降低。其二,金融危机后,投资、金融等资本流动尽管有所恢复甚至达到了金融危机前水平,但对全球GDP的贡献依然没有突出改变。当贸易和资本的全球流动步入低谷时,包括信息、搜索、通讯、交易、视听和公司内部通讯等的数据跨境流动量则快速增长。据麦肯锡公司的报告,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流动将全球GDP总量提升了10%,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远远大于传统的全球货物贸易。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跨境数据流动是数字交易的重心,国际贸易规则是如何调整和规范跨境数据流动?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数字贸易发展本身,也关系到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乃至整个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与创新。
一、多边贸易规则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调整与局限
所谓跨境数据流动是个人数据跨越国界的流动(1)该概念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80年在《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南》中第一次提出。。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认为跨境数据流动指跨越国界对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机器可读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和检索(2)UNCTC.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nsborder Data Flows.New York:United National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982:8.。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据的外延不断扩大,跨境数据流动中的数据不再局限于个人数据。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就规定只要数据形式为“电子形式”,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数据(3)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rticle 14.2.2.。而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以下简称USMCA)中更是将政府数据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视线里(4)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Article 19.1.。
(一)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
WTO 是调整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多边规则平台,但WTO体系中没有直接针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WTO规则也不例外。WTO成立之初,各成员国无法预见信息和科学技术对国际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也不可能制定出能够满足现代数据跨境流动需求的多边规则。尽管如此,WTO已有的部分协定可能对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贸易具有调整作用。WTO中的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存在重合的特征决定了WTO规则对数据流动的一定适用性。
WTO将电子商务定义为:以电子方式生产、分销、营销、销售或交付的货物和服务(5)WTO Work Programme on E-Commerce (WTO 1998)WT/L/274,para.1.3.。具体而言,电子商务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通过互联网进行选择和购买,但通过传统线下方式完成货物或者服务的传递和交付,例如在淘宝上购物;第二种,通过互联网完成全部的选择、购买和传递,例如电子书的网上购买和交付、在线提供法律咨询等;第三种,涉及到电子传输功能的交易,包括网络服务功能的交易。这三种交易模式下涉及的信息都涵盖在数据范畴当中。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不能完全代表未来数字化经济发展方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的概念取代电子商务,认为数字贸易是通过互联网传输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明确排除了商业活动中的有形物理产品,哪怕是有相应数字对应形式的物理产品,如电子书等(6)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1, USICT pub.4415,Investigation No.332-531(2013).但该数字贸易定义提出以后,公共评论认为定义的范围因为排除了有形物理产品而过窄,也有些评论认为定义没有充分反映互联网活动的特征。所以美国贸易委员会考虑知识产权密集型货物和服务中对数字贸易的影响。见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 USICT pub.4485,Investigation No.332-540(2014)。美国将数字贸易基本分为四类:数字内容、社会媒介、搜索引擎和其他服务产品。其中,数字内容包括数字音乐、数字游戏、数字视频和数字书;社会媒介包括社交网站、用户评论网站;搜索引擎包括通用和专业的搜索引擎;其他产品和服务则包括软件服务、通过云计算提供的数据服务(包括处理和数据贮存)、通过互联网提供的通信服务(如电子邮件)以及通过云计算的计算平台服务。。当然,至今还未形成公认的关于数字贸易的标准或定义(7)李忠民,周维颖,田仲他.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2014,(6):132.,但一般认为数字贸易具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互联网传输为媒介;第二,以数字化数据(digitaldata)信息为贸易标的;第三,是与传统贸易方式不同的创新商业模式,内容包括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可见WTO电子商务概念下涉及的数据范围大小与数字贸易概念下涉及的数据范围大小存在高度重叠,但并不完全一致。
(二)WTO规则适用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可行性分析
WTO既有规则能否适用于跨境数据流动,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分析。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适用法律时将考虑跨境数据流动所涉及的贸易类型,然后决定是适用WTO的货物贸易规则,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还是服务贸易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前者的调整对象为有形货物,调整方式主要是边境海关征税;而后者的主要标的是无形服务,更多通过准入及给予服务的待遇去调整服务贸易本身,难以对其征收关税。不同协议的调整方式、自由化程度、贸易待遇规定不同,因此适用GATT还是GATS将对跨境数据流动产生显著不同的调整效果。
第一,适用GATT的情形。通过互联网进行的选择和购买,但通过传统线下方式完成的产品交付时涉及的数据(例如在线订立关于软件的销售合同,通过海运将该批次软件从一国运输到另一国)多数情况与GATT的义务相关。但如果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选择、购买和交付时所涉及的数据,则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更多有形产品摆脱了实物限制,转化成数字产品和服务并直接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当有形产品具有了服务内容时,会呈现出货物和服务的双重属性,数据流动到底是适用GATT还是GATS将引起一定争论,WTO本身并没有界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具体标准。
第二,适用GATS的情形。跨境服务贸易中涉及或产生的数据受GATS调整的可能性增大。例如携程网为用户提供的预定机票和住宿酒店过程中涉及或产生的个人身份信息和出行数据,这些数据无需借助有形载体形式,直接通过互联网流动。由于GATS调整的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特征,而数字贸易中的数据也不具有形载体的形式,因而跨境数据流动所涉及GATS规则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第三,WTO规则难以涵盖的情形。倘若是大数据计算中产生的以电子数据本身为标的的交易,则难以适用货物贸易规则或服务贸易规则。例如美国交通数据供应商Inrix将搜集到的交通状况数据卖给一家投资基金,该投资基金利用购买的交通数据推算某商场货物销售量,继而根据分析结果决定对该商场进行股权投资。此贸易过程中的标的物是数据本身,既没有实物载体形式,也不是附随服务产生,故无法适用GATT或GATS,换言之,WTO很难对此类跨境数据流动进行规范。
(三)GATS规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数据及其交易的特征决定了相较于WTO其他规则,GATS与跨境数据流动的关联度更高,本文将重点讨论GATS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调整情况。GATS规则的适用逻辑为:第一步,分析跨境数据流动所涉措施是否属于服务贸易,若非服务贸易则不能适用GATS;第二步,对所涉措施进行服务贸易分类,考察成员国所做的具体承诺;第三步,分析跨境数据流动的相关措施是否违反了成员国在GATS下的具体承诺。其中第二步是判断的关键点和难点。因为WTO成员国在GATS下的具体承诺针对不同部门并以不同服务模式为基础做出,不同服务模式下对相同部门的具体承诺可能不同,相同服务模式下对不同部门的具体承诺也可能不同。服务模式和服务部门分类两个核心要素共同影响了具体承诺,关系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水平。例如,一国在计算机服务类别下所做的具体承诺可能有别于它在通信服务类别下的所做的具体承诺,一国在计算机服务类别中对跨境交付做出的承诺也可能不同于该类别中对境外消费做出的具体承诺。
1.服务模式的边界问题
根据GATS第1条第2款,服务贸易分为跨境交付(模式1)、境外消费(模式2)、商业存在(模式3)和自然人流动(模式4)四种模式。跨境交付与跨境数据流动最为密切,因为服务的跨境流动往往伴随着消费个人数据和商业数据的交流。当WTO成员国通过模式1对某一服务做出具体承诺时,意味着做出了允许相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承诺(8)Daniel Crosby, Analysis of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Under WTO Service Trade Rules and Commitment,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2016:3.。反过来说成员国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也可能影响该国在某一服务部门下就模式1做出的承诺。
在GATS缔约之初,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两种服务模式之间的界分相对清晰,“跨境交付”指“自一成员领土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提供服务”,而“境外消费”指“在一成员领土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二者的区别在于:模式2的消费者跨越了国境,模式1中消费者并未出境,而是服务由本国生产并跨境送达国外消费者。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据的流动以及数据密集型产品的跨境交易都不再需要消费者或者出售者实际跨越边境,使得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模式的边界在数字贸易时代变得日益模糊,很多时候无法清晰界定数据的跨境流动到底是跨境交付还是境外消费。数据流动可以使得消费者看起来跨越边境到外国消费了某些特殊的服务。在云计算时代,在线服务并不一定通过消费者设备所在地的服务器提供,而是由服务提供者所用设备驻地的服务器提供,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获取服务相当于“出境”了一趟。例如,一个瑞士的消费者访问了英国的亚马逊网站阅读一本电子书,数据存储在英国的服务器当中,消费者访问了这些数据,该过程既可视为是瑞士消费者到英国进行了消费,也可以视为英国图书供应商向他国消费者跨境提供了服务。质言之,该项数据跨境流动行为既能解读为模式1又能被理解为模式2。可以说,GATS服务模式的分类不能完全解决数字贸易中数据跨境流动行为的定性问题。而服务模式又是确认成员国具体承诺的必要前提,服务模式在数字化时代模糊的边界暴露了GATS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适用性的不足。
2.服务分类问题
GATS各成员国在服务部门下的承诺大多是根据《服务部门分类表》(9)The 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MTN.GNS/W/120,1991.(简称W/120)作出,W/120将160种服务分为12个大部门,依次往下分为部门及次部门。W/120对服务部门的划分是建立在1991年《联合国中央产品分类表》(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简称CPC)服务门类的基础上,当今许多与电子或数据有关的服务门类未能涵盖其中,或者涵盖在内的服务因为技术的发展出现归类模糊的情况。简言之,GATS的服务部门分类陈旧,难以涵盖新兴服务。
乌拉圭回合谈判之时,电脑及其相关服务行业为新兴部门,各成员国对电脑及其相关服务”(computer and related service)(10)电脑及其相关服务是W/120划分的12种服务部门之一的“businessservices”下设的一个部门“computer and related services”,在此之下又分为“data base”和“data processing”等次部门,而该两次部门与数据的跨境流动有密切关系。给予的自由度较大,并未在GATS中对“电脑及其服务门类”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做更多限制。以欧盟为例,欧盟对“电脑及其相关服务”下包括与电脑硬件安装相关的咨询服务、软件实现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库服务、维护及修理以及其他电脑服务等(11)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WTO Doc.GATS/SC/31(1994).在内的所有次部门都作出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并且对跨境交付、境外消费以及商业存在中的数据流动的具体承诺几乎不加限制。时至今日,欧盟想要轻易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也面临GATS的制度阻碍。假设欧盟想通过域内规范限制外国公司和它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进入内部市场,就会发现搜索引擎属于“数据处理服务”,而欧盟自身对“数据处理服务”所属的“电脑及其相关服务”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进行任何限制。
欧盟的情形表明未能预见某一服务部门的发展趋势,轻易放开该服务部门的市场门槛或给予不设限制的国民待遇具有一定的风险,同时给国内规则的设立、改变或创新留下较为不利的政策空间。为了避免陷入被动,WTO成员国会采取法律解释的方法去化解尬局。具体而言,一些成员国会通过将某一新兴部门解释成为具体承诺较为严格的服务部门,而不是具体承诺较为宽松的服务部门来应对考虑不周带来的不便。例如,一些WTO成员国基于相似性将“数字服务”(digital service)解释成为属于“视听服务”(audiovisual services)。作“视听服务”类别解释的目的在于,几乎很少成员国在该类别中做出过具体承诺,也无需承担义务。多数国家都未在“视听服务”中进行具体承诺,因为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之时以“视听服务”与文化利益和传统的紧密联系性为由,不愿放开对该领域的调控空间。
上诉机构曾经认为“一个服务只会属于某一类,而不会同时隶属于两类不同的服务,因此服务分类和次分类彼此排斥(mutually exclusive)”(12)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Appellate Body WT/DS285/AB/R, WTO, para.180.的观点与跨境数据流动的现实不符合。当一种服务形态可以归于不同的服务部门和类别时,反过来足以说明W/120的服务部门分类存在着无法对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进行科学归类的瑕疵,尤其是技术、信息进一步变化发展时,服务分类滞后引起的服务部门归属不清将严重影响对成员国具体承诺的判断,甚至虚化GATS对数据形成的规制效力。
二、国际贸易裁判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调控及其困境——美国赌博案的启示
以GATS为代表的WTO法律在调整跨境数据流动的过程中暴露出与电子和网络技术发展不相适应的滞后性,不能很好规范未来数字贸易。那么,WTO的判例法能不能弥补制定法的不足?美国赌博案(13)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ing and Betting Services,WT/DS285/R.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美国赌博案是一起涉及到利用电子方式,如互联网、电讯、邮递等方式提供赌博和投注服务的案件。美国政府限制安提瓜的服务提供者向美国跨境提供赌博和投注服务,安提瓜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了其在GATS下做出的具体承诺,遂请求WTO成立专家组。后来美国和安提瓜分别就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14)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Appellate Body WT/DS285/AB/R.。安提瓜认为,既然美国就“其他娱乐服务(运动除外)”(10.D)下跨境提供服务作出不对相关服务的提供施加任何限制的全面承诺(15)GATS下各成员国服务部门的开放及开放程度都取决于该成员所做的具体承诺。具体承诺可以限定在某些部门,并且在已经承诺开放市场的服务部门,成员还可以进一步限制境外服务提供者的数目和服务提供方式。此处的全面承诺,指的是美国在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限制两项中均为“没有”,也即在允许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之后,未对两者加以限制。,那么美国不允许安提瓜跨境提供赌博和投注服务的行为违反了其在GATS下的具体承诺。
该案件的第一步,专家组应该明确:通过互联网、电讯等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是否也属于GATS中的服务贸易?在美国赌博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没有异议,也就打开了GATS调整跨境数据流动的大门。既然美国赌博案所涉措施是服务行为,第二步需要确定赌博案所涉及的服务归于何种服务模式?如前所述,不同的服务模式下各成员国对于同一部门的具体承诺可能有所不同。专家组认为,跨境提供赌博和投注服务当然属于GATS第1条规定的“(a)自一成员领域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提供服务”,也即跨境交付(模式1),但未进一步说明归类理由。如前所述,根据数据流动和存储的特点,由数据流动而产生的跨境交易,可以是数据从服务提供者向消费者一端流动,产生了数据“跨境”;也可能是消费者访问了服务提供者所在国的数据库,形成了“境外消费”。美国赌博案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判案时未加解释地认定该案所涉为模式1,使得人们不能清楚地了解WTO 裁判机构对模式1和模式2的界分标准和裁判逻辑,跨境数据流动的服务模式归类问题依然没有清晰指针。
既然专家组对所涉措施的服务模式加以确认,第三步需要分析该模式下美国的具体承诺究竟为何?美国具体承诺的内容成为赌博案的核心问题之一。表面上看,美国的具体承诺表中没有提及赌博和投注服务,但美国在“其他娱乐服务(运动除外)”中不加限制的全面承诺,这就需要澄清赌博和投注服务是否属于“其他娱乐服务(运动除外)”。该问题既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释的重点。专家组认为,要确定美国的具体承诺是否包括赌博和投注服务应该参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对具体承诺表进行解释。1993年《减让表指引》规定,为了使具体承诺表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关于服务承诺的分类应该参照W/120并使相关服务的大类和分类的编号与《联合国中央产品分类表》(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简称CPC)编号相对应(16)W/120的分类标准则参考了1991年《联合国中央产品分类表》(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拟定。为了更加准确地指导成员国编写各服务部门下的具体承诺,WTO秘书处还应乌拉圭回合谈判各方的要求编写了《减让表指引》(Scheduling Guidelines1993),以便各成员能对有关的理解形成共识。。那么W/120中第10.D(运动及其他娱乐服务)分类与CPC的第964项相对应,第964项再细分为“964运动及其他娱乐服务:9649其他娱乐服务:96492赌博及投注服务”(17)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ing and Betting Services,WT/DS285/R,Para.6.89.。根据上述推理可得,美国既然在“运动及其他娱乐服务(运动除外)”中做出了具体承诺,且这个分类下包括了赌博及投注服务,专家组裁定:美国的具体承诺包括“赌博和投注服务”。美国认为,在美国的理解当中“运动”类别中才包括了赌博及投注,而美国特意将“运动”排除在外,就是等同于将赌博及投注排除在外。美国还认为,专家组对美国具体承诺表的解释存在疑问,不能轻易将W/120、CPC和1993年《减让表指引》作为解释具体承诺的相关文件,这会增加具体承诺本身的不确定性。上诉机构不认同专家组解释具体承诺的逻辑,认为专家组将W/120和1993年《减让表指引》作为解释美国具体承诺表“背景资料”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上诉机构认为,由于每个成员的具体承诺表是GATS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代表所有成员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应该根据相同的标准予以解释。与大部分成员国的具体承诺表相同,美国的承诺表也基本参照W/120的结构和用语完成。在没有相反论据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假设该行业的适用范围与W/120的分类相同(18)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Appellate Body WT/DS285/AB/R, WTO, para.180.。所以,上诉机构认为,美国的具体承诺表中也应该包括赌博和投注服务。但上诉机构得出此结论的理由与专家组的理由不同。专家组较为主观地将三个不同文件作为解释美国具体承诺的资料,从而得出了赌博和投注服务归于“其他娱乐服务”门类的结论。上诉机构首先明确具体承诺是共同的意思表示,接下来确定共同意思表示的标准是什么,最后得出了与专家组相同的结论。从美国赌博案也可知,服务贸易的分类并非易事,关乎到具体承诺表的解释及解释的依据,尤其是在新网络技术情形下,GATS的服务分类将会面临着更多的解释问题。
三、贸易协定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创新
WTO准司法实践的演变对数据流动的法律调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似乎进入一个“司法能动主义”境地。然而司法移植不能取代在实体问题上的政治共识,特别是在数字贸易这样的高技术复杂领域。尽管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发挥了作用,但期待通过“法官造法”来解决数据跨境流动所产生的所有法律问题显然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WTO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首先,WTO数据法律规定不完整,不能提供足够水平的法律确定性。前述服务分类困境、服务模式的边界模糊等问题暴露了贸易规则与贸易实践的脱节。2011年美国便质疑WTO在商品或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是否应该调整数字贸易,这些规则是否可以涵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19)WTO.General Exceptions: Article XIV of the GATS,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repertory_e/g4_e.htm. 访问于2020年9月16日。。其次,世贸组织的议事方式有失效率,很难跟上数字贸易的发展步伐。WTO框架下主要讨论和解决与贸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如贸易和文化,贸易和隐私,贸易和人权等。但各种议题彼此牵制,国家间不同的政策、利益和文化的考量和较量会消解合意产生的基础并进而影响其他议题进程,阻碍着数字贸易谈判及解决方案的出台。加上多哈回合谈判长期踌躇不前,种种因素都动摇着人们对多边法律规则体系的信心,转而希望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为数据跨境流动及其他数字贸易议题提供法律供给。
(一)双边协定中的数据条款
在跨境数据流动多边规范不足的情形下,当今的数字贸易的监管环境受到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受美国思维的影响。2002年起,美国开始在双边贸易协定中创设具体的数字条款(20)自2002年以来,美国与澳大利亚、巴林、智利、摩洛哥、阿曼、秘鲁、新加坡、巴拿马、哥伦比亚及韩国的双边协定中所有包含WTO-plus条款以扩大数字贸易领域的范围。,以落实其一直在寻求实施的“数字议程”(21)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 of 2002.https://uscode.house.gov/view.xhtml?edition=prelim&num=0&req=granuleid:USC-prelim-title19-section3801.访问于2020年8月27日。,达到扩大数字贸易领域的目标。被视为先进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规定了自由的跨境信息流动,要求各方“避免对跨境电子信息流动设置或维持不必要的障碍”(22)United State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t Article 15.8.,另一方面订入“有关在电子商务中使用及使用互联网的原则”,详细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接入他们所选择的服务及数码产品、自行选择应用程序和服务、将所选择的装置连上互联网等权利(23)United State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t Article 15.7.。美国的数据治理理念及规则在美国同他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逐渐确立,并随他国的借鉴而扩散。新加坡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和韩国间、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多少都能看到美国数据条款的影子。
(二)区域贸易协定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
除了双边贸易协定,美国还极力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塑造数据流动的总体法律环境并创建了具体规则。USMCA及TPP集中反映了美国关于跨境数据治理的态度与立法实践。作为“21世纪”的贸易协定,TPP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据规则推向了更高和更严的标准,实现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追求的对被称为“黄金标准”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大幅超越(24)Mira Burri, The Governance of Data and Data Flows in Trade Agreements:The Pitfalls of Legal Adaptation, 51 U.C.D.L.Rev.65(2017).p.110.。2018年11月30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签署的USMCA是目前覆盖面最广的贸易协定,其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以TPP规则作为基础。除直接承袭TPP中的部分条款外,USMCA对TPP中的数字贸易规则进行了一系列升级和深化,纳入了一些未被 TPP 覆盖的新规则。体现如下:
第一,在信息跨境转移方面。TPP第14.11条允许涵盖的主体为商业活动的目的,以电子方式进行跨境信息(包括个人信息)的传输,容忍各缔约方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不同措施,并认可各缔约方自行制定电子数据传输法律规则的必要性。简而言之,TPP鼓励跨境数据传输,但允许各国自主数据立法及采取不同措施。然而USMCA第19.11条删除了“各缔约方就电子方式进行的信息传输进行法律规范”一条,也即不明确支持成员方对电子方式信息传输各自的立法需求。另外,规定也从“各成员应当(shall)允许信息跨境流动”转变为“任何一方均不得禁止信息跨境流动”这样更为严厉的措辞,规则的刚性大为增强。
第二,关于限制数据本地化措施。第14.13(2)条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以要求在一方领土范围内使用或设置计算设施作为允许在该领土内开展业务的条件。但第14.13(1)条允许缔约方基于通信安全和保密对各自的计算设施予以法律规制,第14.13(3)条也不禁止缔约方为了实现合理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或维持与第2款不符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只有在不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或构成对贸易的变相限制”,以及不“对信息转移施加超过实现目标所需的限制”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不过USMCA则更为强硬,只在第19.12条中保留了“任何缔约方不得以要求在一方领土范围内使用或设置计算设施作为允许在该领土内开展业务的条件”的规定,删除了诸如TPP14.13(1)和(3)的例外性规定。也即根本不考虑缔约国基于通信安全和保密的例外,也不允许缔约国为了所谓的公共政策目标而偏离该条的规定。
第三,关于源代码的规定。根据TPP第14.17条,各成员国不得以要求转让或获得另一方个人所有的软件源代码,作为在其领土内进口、分销、销售或使用该软件或包含该软件的产品的条件。该条的目的在于保护软件公司,解决他们对知识产权损失或专有代码安全漏洞的担忧。该禁令仅适用于“大众市场软件或含有此类软件的产品”,那些定做的产品、用于关键基础设施的软件以及商业合同中的软件都被排除在外。在USMCA中,关于源代码的规定同样变得更为严格。首先,在USMCA的第19.16条当中,除了源代码,还将源代码中体现的算法也纳入进来。其次,不再区分“大众市场软件”“基础设施软件”或“商业合同中的软件”,换言之,几乎所有类型的软件源代码及其源代码所代表的算法都不能被成员要求转让,以作为在其领土内进口、分销、销售或使用的条件。
第四,在USMCA中增加了“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以及“公开政府数据”两条,以填补TPP在该两个问题上的空缺。USMCA是全球首个明确要推动政府电子数据公开的贸易协定,尽管该协定并未对政府公开电子数据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但提到了“公众方便取得政府信息的重要性”。
四、结语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新的经济样态,在旧有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变革,国际贸易法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人们曾寄希望于WTO这样一个制度化的多边场所去减少数字贸易中的法律障碍并形成较为统一的规则,WTO自身也试图为适应数据流动作出改变。截至2018年,WTO已有多项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协议包括《信息技术协定》,该协定取消了计算和信息技术设备的贸易关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护了如计算机程序这样的与信息技术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GATS及其附件中关于金融服务、电脑服务和电讯方面的协定。然而,这些协议都没有明确地解决数据跨边界流动问题,也没能涵盖基于互联网出现的多类新服务。面对无法回避的信息技术及其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冲击,WTO 并没有能够作出足够深思熟虑的法律回应,他们希望通过审判弥补漏缺的做法也未能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效果(25)Susan Ariel Aaranson and Patrick Leblond, Another Digital Divide: The Rise of Data Realm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TO, 2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8), p.250.。WTO显示出的调控乏力也许与其自身逻辑基础有关。国际贸易法的目的是管制货物贸易,其做法是通过降低关税达到产品间的公平竞争。这种贸易管理体系基于物理性或物质性特征,采用以国家为中心、自上而下的规则范式,与具有虚拟性、不分国界流动的数据所需要的治理模式有相当的不匹配。WTO机制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本身面临极大的挑战。
数据跨境流动多边规则的供给不足为区域贸易协定提供了契机,后者解决了某些“非贸易”或WTO附加问题,比如消费者保护、隐私和数据自由流动的保障。以USMCA和TPP为代表的美国数据法律模板之所以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它的高标准,也因为它所涵盖的问题的广度,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USMCA在金融服务章节首次引入禁止本地数据存储要求的条款,直接引入“数字贸易”一词作为章节标题,要求限制政府披露专有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的能力,确保数据的跨境自由传输,最大限度减少数据存储与处理地点的限制,确保应用于数字市场的消费者保护措施。应该说这些规则试图在自由数据流动和数据保护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朝着协调经济和非经济利益迈出了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