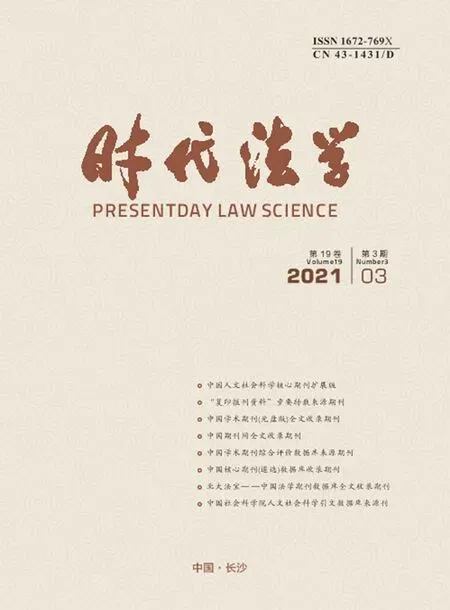专属经济区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活动的国际法分析*
余敏友,周昱圻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引言
海洋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人类生存和发展日益依赖海洋,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都与海洋科学研究密切相关(1)Alfred H. A. Soons,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Law of the Sea, Kluwer Law Press, 1982, pp.11-15.。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一方面,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远远不够,海洋科学研究是人类认知海洋、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海洋科学研究是人类进一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基础实践,有助于人类解决陆上问题(2)ZOU Keyuan, Govern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34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 1(2003).。国家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与海洋科技水平密不可分,海洋科技水平也一度对于其所主张的大陆架(3)《大陆架公约》第1条规定:“本条款称‘大陆架’者谓:(a)邻接海岸但在领海以外之海底区域之海床及底土,其上海水深度不逾二百公尺,或虽逾此限度而其上海水深度仍使该区域天然资源有开发之可能性者;(b)邻接岛屿海岸之类似海底区域之海床及底土。”第5条第8款规定:“对大陆架从事实地研究必须征得沿海国同意。倘有适当机构提出请求而目的系在对大陆架之物理或生物特征作纯科学研究者,沿海国通常不得拒予同意,但沿海国有意时,有权加入或参与研究,研究之结果不论在何情形下均应发表。”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
现代意义的海洋科学研究始于1872年至1876年英国海军“挑战者号”(the H.M.S Challenger)科学家在航行中对海底与水体进行取样研究(4)Satya N. Nandan, Introduction to Office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1991), at vii.。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启了国际条约规范海洋科学研究行为的征程(5)U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Law of the Sea: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A Revised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2010), para.1。1958年《大陆架公约》确定了沿海国对大陆架上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享有管辖权(6)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并未形成专属经济区制度,彼时“领海之外即公海”,沿海国依据1958年《大陆架公约》可以对领海之外的海床底土主张权利。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创设出了专属经济区制度,将领海之外的一定范围内水域作为沿海国可以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一般情况下,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关系是海床底土和上覆水域的关系。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存在高度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测量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第十三部分专门规定了海洋科学研究制度。《公约》由于没有明确界定“海洋科学研究”,易于引发如何具体规范科研/测量活动的争议。
实践中,各国由于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活动、情报收集活动而产生的争议屡见不鲜。从EP-3型侦察机撞击事件,到鲍迪奇号事件、斯科特号事件、无暇号事件,美国一直在挑战所谓的他国“过度海洋主张”(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受挑战的沿海国主张测量活动和情报收集活动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7)See ZHANG Haiwen, Is It Safeguard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Maritim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 Comments on Raul (Pete) Pedrozo’s Article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1, 36, 38 (2010); Sam Bateman, A Response to Pedrozo: The Wider Utility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10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77, 179 (2011); XUE Guifa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ydrographic Survey in the EEZs: Closing up the Legal Loopholes?, in: Myron H. Nordquist, Tommy T. B. Koh& John Norton Moore (eds.),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2009), 205-225; S. Kopela, The ‘territorialisation’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mplications for maritime jurisdiction, 6,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ac.uk/resources/ibru/conferences/sos/s_kopela_paper.pdf.,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进行此类活动须征得该沿海国同意。美国认为,从《公约》第19条、第40条等条款看来,测量活动是明显与海洋科学研究并列的活动,属于《公约》第58条“其他国际合法用途”的范围。美国自1979年推行“航行自由计划”以来,派遣军舰、军机进入其他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活动,挑战沿海国的海洋主张(8)余敏友,冯洁菡.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国际法批判[J].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4):6-31.。因此,厘清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确定其内涵对于明确海洋权利及义务非常重要。
一、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及内涵
虽然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讨论过海洋科学研究的界定问题,也曾有过几个版本定义条款(9)UNDOALOS, above n.5, pp.4-6.,但是《公约》最终没有对海洋科学研究一个明确的界定。许多国际法学者试图从学理上对这一概念予以定义,并分析其内涵,但分歧较大。实践中,水文测量(hydrographic survey)、军事测量(military survey)和军事信息收集(military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等与海洋科学研究紧密相关的活动,是否应该属于《公约》第十三部分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从而接受沿海国的管理与规范,也存在争议。
首先,对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主要分歧聚焦于海洋科学研究的目的,即是否须以增进人类对于海洋环境的知识为目的,海洋科学研究是否包括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与应用性海洋科学研究。部分国际法学者认为(10)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Martinus Nijhoff Press, 2012, p.414; Raul (Pete) Pedrozo, Preserving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Right to Conduc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hin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 21 (2010).,海洋科学研究须以增进人类的科学知识为目的,从而将海洋科学研究限缩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来自美国海军军官学院的Roach和Smith(11)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13-414.,他们认为海洋科学研究是隶属于海洋数据收集(marine data collection)的下位概念。他们通过对于海洋数据收集体系的构建,将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活动(包括水文测量与军事测量)并列。由此一来,测量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因而通过主张《公约》第58条第一款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将专属经济区内的测量活动认定为不受沿海国规范的海洋自由。也有部分国际法学者认为(12)R. R. Churchill & A. 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00; P. K. Mukherjee, The consent regime of oceanic research i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5 Marine Policy 98, 99-100 (1981); 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p.6-7;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433-434.,海洋科学研究应该是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与应用性海洋科学研究。宋斯(Soons)将海洋科学研究定义为:“以海洋环境为对象的任何调查,不论其以何种方式在何地进行”(13)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24.。他认为海洋科学研究分为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与应用性海洋科学研究,前者专指为增进知识而进行的研究活动。持此类观点的人中,又可以是否将水文测量和军事测量并入海洋科学研究作区分。
以Mukherjee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将测量活动并入海洋科学研究。他认为海洋科学研究包括三大类: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应用性海洋科学研究、军事研究。他将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细分为五类:海洋物理学研究、海洋化学研究、海洋生物学研究、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以及水文测量(14)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9-100.。与之相对应的,以宋斯为代表的学者不主张测量活动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理由主要是基于《公约》上下文(context)的考虑,认为海洋科学研究应与测量活动(水文测量)并列(15)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p.124-125.。他还认为水文测量符合《公约》第58条第一款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因而不受沿海国的规范(16)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57.。
同时,部分学者认为测量活动的产出(主要指其收集到的数据信息)有经济价值(17)Sam Bateman, Hydrographic surveying in the EEZ: differences and overlaps with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29 Marine Policy 163, 169(2005); Moritaka Hayashi,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 in the EEZ: definition of key terms, 29 Marine Policy 123, 131(2005).。水文测量对于沿海国管理其专属经济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接影响沿海国对于专属经济区的勘探与开发,以及沿海国对于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的保护(18)Sam Bateman, above n.7, 180-181.。因此,Bateman提出沿海国可以规范专属经济区内的测量活动,其理由不是基于测量活动可以归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而是因测量活动伴随的经济价值(19)Sam Bateman, above n.7, 180-181; Sam Bateman, above n.17, 172.。尽管美国学者也承认水文测量对于沿海国的经济价值与环境保护重要性(20)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6.,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测量活动应属海洋自由,而非沿海国的管辖范围。
尽管《公约》未直接将海洋科学研究分为基础性与应用性,但结合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历史,基础性/应用性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从1958年《大陆架公约》开设就得到了体现(21)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Article 5, 499 UNTS 312; 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8-100, 102.,在第二、三次海洋法会议中也得到了充分讨论。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中,加拿大提出“海洋科学研究应定义为:旨在增加海洋环境知识,包括海洋资源和生物,并包括所有相关科学活动的任何基础或应用研究。”(22)UN Doc A/AC.138/SC.III/L.18 (Canada), Preamble, para. 2, and principle 2.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定义的提案从1973至1976年一直不断。英美学者所广泛援引的定义就出自1975年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ISNT)中的“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means any study or related experimental work designed to increase man’s knowledge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23)UNCLOS III, Informal Single Negotiating Text (ISNT), Part III, MSR Part, Article 1.。1977年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ICNT)与《公约》,没有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在此需要探讨《公约》是否已经将海洋科学研究限定在基础性海洋科学的范围之内。
《公约》第246条第三款明确了“在正常情形下,沿海国应对其他国家或各主管国际组织按照本公约专为和平目的和为了增进海洋环境的科学知识以谋全人类利益,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给予同意。为此目的,沿海国应制定规则和程序,确保不致不合理推迟或拒绝给予同意。”这一条款被普遍认为是对于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24)P. K. Mukherjee, above n.12, 102.。根据《公约》第246条,对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沿海国应该采取有限同意制度(qualified consent regime)(25)P. K. Mukherjee, above n.12, 104.,同意合格的研究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进行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依据《公约》的上下文解释:首先,根据《公约》第246条第一款、第二款,沿海国有权管辖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应该得到沿海国同意,且沿海国应同意研究国家进行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其次,根据《公约》第246条第五款,沿海国有权拒绝同意对涉及该款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该条款便包含了与资源勘探开发相关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可见,《公约》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不仅包括纯粹基础性科学研究活动,也包括与资源勘探开发有关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活动(《公约》第246条第五款)。
因此,《公约》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应该是有广泛内涵的活动,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张的纯知识性研究活动。Soons、Churchill、Tanaka等人认为海洋科学研究应被定义为“以海洋环境为对象的任何调查,不论其以何种方式、在何地进行”,更符合《公约》的目的与宗旨。 Mukherjee认为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本质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目的、动机,因此他在广义的“海洋科学研究”之下进一步区分,其中,水文测量和军事研究都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26)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8-100.。但在实践中,测量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关系一直是争议的热点。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海洋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清晰的界定。
二、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活动辨析
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活动之间是否实质一致、逐渐趋同(27)ZHANG Haiwen, above n.7, 36; Sam Bateman, above n.7, 179-180.,还是存在明显差异以致互斥排他(28)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14, 21-22;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14-416.,抑或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29)Sam Bateman, above n.17, 172.。下文先分析水文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的关系,而后分析军事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的关系。
(一)海洋科学研究与水文测量的关系
水文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的关系,无外乎两种观点:第一,对立互斥,持这种观点以英美国家学者居多,他们认为水文测量活动应是“为航行安全及制作航海图而进行的信息获取活动”(30)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1-22;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6.,而海洋科学研究以增进海洋科学知识为目的,两者目的不同,因此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行为。第二,实质一致且逐渐趋同。Bateman在2005年主张,虽然两者使用的方式方法存在重叠,但水文测量和海洋科学研究是可以做区分的不同行为(31)Sam Bateman, above n.17, 168.,2011年他却认为这两类活动不断趋同难以区分(32)Sam Bateman, above n.7, 180-181.。部分国际组织如国际海道测量局(IHB)也支持其观点。下文进一步分析这两种观点。
能否进行以航行安全为目的海洋科学研究?正如美国学者所述,海洋科学研究目的不同于水文测量活动。后者以航行安全为目的,而前者并非如此,能否进行以航行安全为目的海洋科学研究是关键。Churchill与Lowe认为,海洋科学研究有各种各样的目的(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serves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33)R. R. Churchill & A. V. Lowe, above n.12, p.400.,其中包括对波浪、洋流、海床和天气的研究,以便使航行更加安全(34)R. R. Churchill & A. V. Lowe, above n.12, p.400.。联合国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司制定的《海洋科学研究指南》(2010)认为,海洋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35)UNDOALOS, above n.5, para. 9.。认为海洋科学研究不包括以航行安全为目的研究活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目的可以包括为航行安全利益,与水文测量的区别也不在于目的的不同。
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是否与水文测量活动实质一致且逐渐趋同?Bateman教授的主张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他认为严格区分(水文)测量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是对《公约》的过度解读(36)Sam Bateman, above n.7, 179.。《公约》区别列举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活动,只是为了将此类活动一并作为被禁止活动或者需要获得沿海国授权之活动。而且,这种区分只涉及通行制度而不涉及专属经济区制度(37)Sam Bateman, above n.7, 179.。然而,这只是可能性,毕竟《公约》谈判过程没有特别聚焦水文测量活动(38)Sam Bateman, above n.17, 165.,从而体现其与海洋科学研究之不同。因此,很难说Bateman教授的主张有足够的理据。第二,Bateman列举了相关国际组织专家意见,认为区分海洋科学研究与水文测量非常困难(39)Sam Bateman, above n.7, 181.,2005年他主张虽然可能存在手段重叠,但这两种活动仍是可分而非不可区分的(40)Sam Bateman, above n.17, 168.。他的主张自相矛盾,水文测量活动是否区分于海洋科学研究,难以定论。因此,水文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
首先,需要从溯源的角度对水文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进行分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认定第一次水文测量是在1843年(41)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NOAA), History of Hydrographic Surveying, available at https://nauticalcharts.noaa.gov/learn/history-of-hydrographic-surveying.html.。这个时间早于英国“挑战者号”进行的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海洋科学研究的时间(1872年),水文测量明显早于海洋科学研究,从源头上来说,两者并不是同一个行为。其次,需要从采取的方式方法分析海洋科学研究与水文测量。水文测量的发展,经历了沿线测量、线拖测量、回声测量与多波束声呐技术四个阶段(42)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NOAA), History of Hydrographic Surveying, available at https://nauticalcharts.noaa.gov/learn/history-of-hydrographic-surveying.html.。目前水文测量主要采用的声学探测方式与海洋科学研究是一致的(43)Sam Bateman, above n.17, 166.,国外学者也普遍承认海洋科学研究与水文测量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44)Sam Bateman, above n.17, 166;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50; 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2.。最后,《公约》第19条、第21条及第54条等,将(水文)测量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并列。这也是英美学者大多主张水文测量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之一(45)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11.,这点不容忽视,也难以推翻。即使Bateman主张这是对于《公约》的过度解读,也不能直接认定这两类行为完全一致,从而轻易地将水文测量纳入《公约》第十三部分的管辖范围。
综上,水文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是不同的两类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手段、方式,也可以有相同的目的——均以航行安全利益为目的。如前所述,海洋科学研究是一个广义概念,即“以海洋环境为对象的任何调查,不论其以何种方式、在何地进行”。由此,很可能存在既符合海洋科学研究又符合水文测量的活动。《公约》第19条、第21条等以通行权为依据,从而对无害通过及过境通行予以认定,而不是以船舶类型为依据。在这样的上下文(context)中,《公约》调整的是具体的行为活动,如果仅以概念不同进行区别,将水文测量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之交集排除在《公约》第十三部分之外,从而主张专属经济区内的测量自由,是不符合《公约》的,甚至会导致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瓦解(46)See XUE Guifang, above n.7, p.222.。因此,如果相关的活动既符合海洋科学研究,又符合水文测量,那么理应属于《公约》第十三部分的范围,从而受到沿海国的规范。
(二)海洋科学研究与军事测量的关系
《公约》没有明确提及军事测量活动(47)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37.,且其概念非常模糊(48)Sam Bateman, above n.17, 172-173.。根据《公约》第19条与第21条关于无害通过的规定,第19条所指的“测量活动”直接指向了第21条的“水文测量”。水文测量是《公约》缔约过程中讨论较少的议题,军事测量这一概念都不在《公约》商议范围之中。军事测量是“在领海、群岛水域、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专属经济区、公海以及大陆架,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海洋数据收集活动”(49)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7.。
军事测量包括海洋学、水文、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化学、生物、声学等相关数据(50)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7.。从军事测量范围可以看出,与公认的海洋科学研究范围(51)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6; 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9-100;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14-415.具有高度一致性。后者同样包括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因此,在中美关于军事测量的争端中,美方主张军事测量是伴随军事目的的测量行为,因此不同于海洋科学研究(52)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2.。国内学者(53)ZHANG Haiwen, above n.7, 36;郑雷.论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他国军事活动的法律立场——以“无瑕号”事件为视[J].法学家,2011,(1):143;管建强.美国无权擅自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测量” ——评“中美南海摩擦事件”[J].法学,2009,(4):55;杨瑛.专属经济区制度与军事活动的法律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7,(5):123-124;万彬华.论专属经济区“海洋科学研究”和“军事测量” 的法律问题[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5):59;宋云霞.海洋科学研究法律制度解析[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1,(2):75-76;邹立刚,王崇敏.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科研活动的管辖权[J].社会科学家,2012,(11):14-15.则普遍认为军事测量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军事测量活动应该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通过分析军事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所采取的手段与技术,这些学者主张,两者并无本质不同,而差异仅在于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军事测量的目的,存在区分不能的情况,应该将军事测量活动纳入海洋科学研究之中。
首先,军事测量活动概念极其模糊,不易识别(54)Sam Bateman, above n.17, 173.。英美学者的军事测量活动/军事数据收集活动(Military Data Gathering)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即一切以军事为目的的海洋数据收集活动。在此基础上,军事测量活动不仅区别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也区别于水文测量活动。然而,水文测量活动本身就可以包括两类,一类是国家主导的,可以用于军事的水文测量;另一类则是国防之外的民间机构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主导的水文测量。前者正是军事测量所覆盖的范围,属于两种测量活动的交集。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必然不能以军事为其目的,军事研究也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与基础性/应用性海洋科学研究相并列(55)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8-100.。因此,美国所主张的分类,人为地割裂了概念,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几类活动的本质特点。
其次,对于军事测量来说,军事活动应是其合适的上位概念。这也是争议双方共同承认的(56)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36-437; Zhang Haiwen, above n.7, 31-32.。需要考虑争议相关的军事测量是否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判断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活动是否应该受沿海国的规范。对于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内,同时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军事测量活动,沿海国享有管辖权。对于一些未必以海洋环境作为研究、数据收集对象的军事活动,例如情报收集活动(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必须着重考虑其合法性问题。
三、专属经济区内测量活动的合法性
专属经济区内的测量活动,包括水文测量与军事测量(作为军事活动的一种),其合法性是有争议的(57)Proelss ed., United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C. H. Beck Press, 2017, p.453.。2002年至2009年先后发生了鲍迪奇号与无暇号事件,中美学界纷纷讨论沿海国是否有权规范专属经济区的测量活动(以军事测量为主)。下文先分析两类测量活动是否是符合《公约》第58条第一款之“其他合法用途”,再从《公约》第59条的角度探究两类测量活动是否属于剩余权利(residual right)的范畴。
(一)《公约》第58条第一款
《公约》第58条是英美等海洋大国主张测量活动自由的主要依据。英美等国主张《公约》提供了专属经济区内测量活动的法律基础,其主要依据是《公约》第58条第一款,即“在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在本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享有第87条所指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诸如同船舶和飞机的操作及海底电缆和管道的使用有关的并符合公约其他规定的那些用途”。测量活动正属于此种用途,是《公约》专属经济区制度赋予非沿海国的权利。为分析这一问题,下文先探讨《公约》第58条第一款的解释,再分析该规定对水文测量、军事测量的适用。
首先,什么是《公约》第58条第一款中的“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如何认定测量活动是否与“航行和飞越的自由”有关。“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指的是“航行和飞越自由”所依赖的一些海上活动。《公约》列举“诸如同船舶和飞机的操作以及…有关的并符合公约其他规定的那些用途”。正如宋斯指出的那样,“一艘船(无论是否是研究船)在通行中为船舶航行安全而收集数据的行为 (如测深和风速和风向的观察),不能被视为研究”(58)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49.,而应当被视为与船舶操作相关的正常活动(normal activities)(59)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49.。Bateman在此基础上提出,这类行为既不能被认定为海洋科学研究,也不能被认定为测量活动(60)Sam Bateman, above n.17, p.165.。这两位学者所指的正常活动正是《公约》第58条第一款的“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一方面,这类活动与航行、飞越自由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可以认定其中的相关性联系;另一方面,这类活动不构成海洋科学研究或测量活动,也就是说不存在沿海国可以规范这类正常活动的可能性,这类活动属于沿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之自由。与之相反,如果这类活动被认定为海洋科学研究或是测量活动,那么极有可能受到沿海国的规范,从而不能被《公约》第58条第一款所适用。尽管公约并没有予以解释,但这类“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应是一个小范围的概念,不能扩大解释。尤其是与沿海国主权性权利、管辖权相关的活动(61)See The M/V ‘Virginia G’ (Panama v. Guinea-Bissau), Merits, Judgment, ITLOS Case No. 19(2014), p.69, para. 217.,不宜认为是他国之自由。
其次,水文测量活动是否属于《公约》第58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据前所述,如果水文测量作为一种数据收集活动,被视为宋斯所主张的在通行中为船舶航行安全所进行的那种数据收集行为,那么这类活动应被视为合法用途下的正常活动,水文测量却是为航行安全及制作航海图而进行的信息获取活动。这类活动与船舶本身为航行所做的数据收集活动有明显区别。因此,水文测量活动与“航行、飞越的自由”没有足够充分的相关性。他国难以直接依据《公约》第58条,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主张水文测量自由。另外,从国家实践来说,目前15个以上国家要求进行水文测量活动之前须通知沿海国并获得同意(62)Kopela, above n.7, 5.。中国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8条规定:“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绘活动,应当经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测绘部门批准,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国家实践中,都难以认定水文测量就是符合《公约》第58条第一款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水文测量是对海洋的合理、合法利用,然而这种合法用途并非《公约》赋予的不受沿海国规范的自由。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水文测量是否属于《公约》第59条所规定的剩余权利的范畴。
最后,分析《公约》第58条第一款对军事测量活动的适用。军事测量活动被认为是军事活动的一种,必须从军事活动的角度考虑军事测量是否属于“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海洋军事活动违反了和平原则,这项原则贯穿于《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宪章》第2条以及《公约》第88条、第301条都阐释了这一原则。而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海洋军事测量,以军事用途为目的,旨在支持军队登陆及对沿海国作战,构成了对沿海国的威胁,不能视为和平利用海洋的合法用途(63)宿涛.试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和平规定对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限制和影响[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6):83;郑雷.论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他国军事活动的法律立场——以“无瑕号”事件为视[J].法学家,2011,(1):144; 杨瑛.专属经济区制度与军事活动的法律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7,(5):122;万彬华.论专属经济区“海洋科学研究”和“军事测量” 的法律问题[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5):60-61;丁成耀.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测量船闯入中国专属经济区事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2):81.。美国学者Pedrozo则主张,《公约》并未禁止军事活动,而只是禁止了“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活动。与中国学者的主张相反,《公约》第19条第二款明确列举了一系列军事活动。这意味着《公约》在区分军事活动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64)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5.。因此,非侵略性军事活动符合《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5)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5.。
军事活动(包括军事测量)是否违反了“和平目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仅仅因为军事活动伴随着军事战略目的,而将其定性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而认定其违反了一般国际法。“一些可能发生在公海的海军演习和常规武器试验是可以被接受的”(66)Alexander Proelss, Peaceful Purposes, MPEPIL, para. 15.。《公约》第88条也适用于专属经济区,不能一概禁止军事活动。否则,如果采取严格解释,无论是沿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无法在专属经济区或公海上进行军事活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处于国际局势紧张,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武力使用的区域,这类军事活动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和平目的的行为。
综上,军事活动并不必然就是《公约》第88条与第301条所禁止的活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排除其合法性,即便“合法用途”的军事活动,也不能认定是与航行、飞越等活动有关的“其他合法国际用途”,从而通过《公约》第58条合法化,需进一步分析军事测量活动是否属于《公约》第59条的“剩余权利”范畴。
(二)《公约》第59条
《公约》第59条“解决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的归属的冲突的基础”规定:“在本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任何其他一国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根据前文分析,在不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竞合的情况下,测量活动不属于《公约》第56条与第58条的调整范围。下文拟分析测量活动与《公约》第59条之关系,进一步探究测量活动的权利归属问题。
《公约》第59条作为一个候补条款(backup clause)(67)Proelss, above n.57, p.460.,针对的是《公约》没有分配权利或管辖权的活动。尽管前文论述了测量活动并不是《公约》第58条第一款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之范围,但是对于军事活动(军事测量)是否属于“剩余权利”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下文先分析“合法用途”的测量活动,尤其是军事(测量)活动,是否属于《公约》第59条的“剩余权利”。
从国家实践而言,包括巴西、印度、中国、伊朗、孟加拉国在内的十个国家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提出主张(68)Kopela, above n.7, 4.。其中,大部分国家要求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活动前须获得同意。伊朗1993年《海域法》禁止一切不符合其权利和利益的军事活动与演习、信息收集及其他一切活动。但是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则反对这类主张(69)D. R. Rothwell & T.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2016, Hart Press, p.280.。海洋强国认为,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应属于海洋自由的范畴;即使属于“剩余权利”,也必须考虑到沿海国以外国家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沿海国安全利益(70)See Proelss, above n.57, p.462.。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沿海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理由,有权管辖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
就目前研究而言,主张军事活动属于“剩余权利”范畴者,没有很好的理据(71)Guilfoyle认为主张剩余权利更加公平,See Douglas Guilfoyle, The High Seas, in Donald R. Rothwell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14; 易显河认为《公约》第59条是为资源以外的权利所创设,而军事活动正是属于这类权利,See Sienho Yee, Sketching the Debate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An Editorial Comment,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3 (2010).。认定剩余权利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因为其证明的标准是公约并没有对这类权利决定归属。但是《公约》第56条与第58条,前者规定沿海国的主权性权利与管辖权,后者赋予沿海国以外的他国许多公海自由。要证明军事活动不在以上两个条款之中,方能证明它属于《公约》第59条之下。
Pedrozo主张中国和美国可以签订协定专门针对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的双边协定,其模板是美苏《美苏预防公海事故协定》(72)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7.。这类协定需承认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的合法性,并加以规范。Pedrozo这类主张实际上是在承认军事活动就是《公约》并未分配权利的活动。理由如下:
1.如果《公约》将军事活动的权利分配给了沿海国,则完全不需要由军事活动国与沿海国以协定方式对相关活动予以规范。依据《公约》第56条第三款,沿海国可以制定国内法,且其他国家必须遵守。
2.如果《公约》已将军事活动的权利分配给沿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认定这类活动为专属经济区内的自由。那么,其他国家也无必要再和沿海国缔结协定处理此事项。其他国家完全可以主张军事活动自由,不受沿海国的规范。
Pedrozo、Roach等人均带有美国军方背景,他们对于海洋权利的主张与美国国家立场一致。因此,军事活动作为专属经济区上的“剩余权利”是可以通过争议各国的法律立场主张加以推断的。
综上,军事活动(包括军事测量)是属于《公约》第59条的范围之内的活动,但具体如何主张、如何使其受到规范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依据《公约》第59条,“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加以解决”。因此,实际如何处理关于这类活动的矛盾,取决于各方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利益的平衡,这个平衡是以公平为其判断基础的,所以不得不进行个案考虑(73)See Proelss, above n.57, p.459; Tommy T.B. Koh, Remark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Myroon H. Nordquist, Tommy T.B. Koh& John Norton Moore (eds.),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Martinus Nijhoff Press, 2009, p.55.。沿海国的安全利益与外国军事活动的利益(74)See Proelss, above n.57, p.459; Tommy T.B. Koh, Remark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Myroon H. Nordquist, Tommy T.B. Koh& John Norton Moore (eds.),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Martinus Nijhoff Press, 2009, p.55.甚至领袖型国家确保国际秩序安全的利益(75)Sienho Yee, above n.71, 5.,其间必须有基于全面考虑的平衡。
从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路径看,随着人类科技水平进步,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因此,沿海国必然会对于其邻近海域提出越来越多的权利声索与主张(76)XUE Guifang, above n.7, p.223。这种权利主张也在逐步固化,原有的海洋区域法律地位属性也会随之而转变。1945年9月,美国发布两份《杜鲁门公告》主张了国家对于大陆架、公海自然资源享有权利。这一行为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对于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
《公约》确立领海的宽度,确认国家可以主张12海里的领海,解决了前两次海洋法会议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公约》第五部分创设性地规定了自成一体(sui generis)的专属经济区,赋予了沿海国两类主权性权利及三类管辖权。专属经济区制度创设以来,许多沿海国开始通过国内立法或者提交声明等方式,主张对于专属经济区上的事项享有权利,目前甚至有专属经济区“领土化”之势(77)Kopela, above n.7, 1-15.。许多沿海国主张对其专属经济区的系列活动享有权利,这些活动包括军事活动、水文测量、建造使用设施结构、海关管理、水下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等等(78)除前文对于水文测量和军事活动之规制以外,中国、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在内的十三个国家已经主张了对专属经济区内的一切设施结构享有管辖权;古巴、海地、纳米比亚等七国主张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公约》未明确授予的海关管辖权;中国、澳大利亚、冰岛、葡萄牙、西班牙等十三国主张对于专属经济区内水下文化遗产的管辖权。。“领土化”趋势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国际法的发展,沿海国对于权利的固化,很有可能产生习惯国际法,使得其对测量活动的权利进一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结语
综上所述,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与测量活动,概念非常模糊,但应用非常广泛。本文认为,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是以海洋环境为对象的调查、研究活动。测量活动(包括水文测量与军事测量)都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有交集,对于同时属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测量活动,应该受《公约》第十三部分的约束。因此,专属经济区内的测量活动受沿海国的管辖。专属经济区内那些确实有别于海洋科学研究的测量活动,不符合《公约》第58条规定的“与航行、飞越自由相关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沿海国之外的测量国,不得主张海洋科学研究自由。那些符合“和平目的”的测量活动,属于《公约》第59条“剩余权利”的范畴,因此沿海国与其他国家均可以主张权利,但是在专属经济区“领土化”趋势下,沿海国更有意愿且有能力去规范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测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