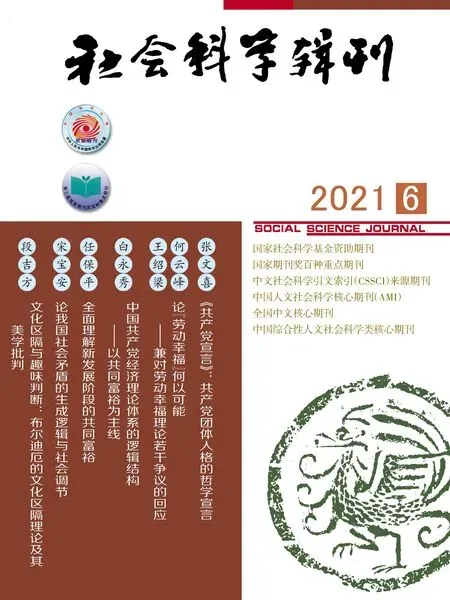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接受
曾 军 汪一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中国文论70年来一以贯之的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西马文论”)则是其中不断激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各种思想论争、应对现实挑战的重要思想资源。长期以来,学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认为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和研究始于1978年,标志性事件是徐崇温发表《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该文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流变以及代表人物和主要学派。〔1〕至于西马文论方面,虽然1980年出版的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2〕打开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叙述体系,但是中国学者真正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为名展开研究则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其中,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该年陆梅林编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和冯宪光的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国第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3〕因此,在当下的学术史叙述中,西马文论多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伴随着20世纪西方文论译介特别是1985年“方法论”热潮而进入中国的西学新潮。①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冯宪光的《“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马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与启迪》、董学文的《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模式的反思》等。但事实上,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胡风(包括“七月派”)对卢卡奇文论的接受,以及布莱希特、萨特的中国译介,等等。②关于卢卡奇的接受研究,可以参考艾晓明的专著《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第七章《中外两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辨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关于布莱希特的接受研究,可以参考俞仪方的论文《布莱希特研究在中国:1929—1998》(《德国研究》1998年第4期);关于萨特的接受研究,可以参考赵守成的论文《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刘大涛的专著《萨特在中国的影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因此,本文所欲展开的是重返新中国初期中国对西方学术资源引进和接受的历史现场,重新梳理那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接受模式进行理论提炼。
从现有资料来看,新中国初期译介进入中国且现在我们将之归属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已有不少。③从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到金元浦《借鉴与融汇中国当代文艺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的研究与接受》(群言出版社,2015年),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西马文论的认知在不断“扩容”,为便于论述,这里暂时以当下学界普遍认可的西马文论家为中心确定西马文论的大致框架:(1)聚焦创作方法的西马文论(“现实—现代”主义):卢卡奇、布莱希特、布洛赫、加洛蒂、费歇尔;(2)聚焦文本的结构主义西马文论:阿尔都塞、马舍雷、戈德曼;(3)人本主义倾向的西马文论:萨特、梅洛-庞蒂、列斐伏尔、沙夫;(4)文化批评的西马文论:葛兰西、考德威尔、威廉斯、伊格尔顿、詹明信;(5)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弗洛姆、哈贝马斯;此外,还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人物如卢森堡。根据当时中国学者接受内容的侧重点,下文按现实主义视域和美学视域两个方面展开论述。④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经初步绘制了新中国初期“西马东渐”的学术地图,可以参考曾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旅行及其引发的理论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
一、现实主义视域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实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创作方法和艺术观念上最为重要的理论主张。因此,从现实主义视域关注西马文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理论界非常自然的选择,同时这一视域选择也相应地遮蔽了其所译介的西马文论家的其他丰富的理论面向。卢卡奇(George Lukács)、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加洛蒂(Goger Garaudy)、费歇尔(Ernest Fischer)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西马理论家,尽管他们最终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但中国学者在具体接受过程中对其态度则不尽相同:卢卡奇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论始终是处于被批判状态,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戏剧观则成为黄佐临试图改造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斯坦尼体系”)时所征用的理论资源,加洛蒂和费歇尔收编现代主义为现实主义扩容的文艺观在当时也遭到了批判。
卢卡奇是新中国文论最为熟悉的西马文论家之一。⑤从这一时期教材中对卢卡奇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中,西马理论家只引用了卢卡奇2次,分别在107、241页,均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反面教材加以批判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的《文艺学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五章第一节《批判修正主义在世界观与创作问题上的反动谬误》也引用卢卡奇的原文作为驳斥对象。卢卡奇的观点能体现在文艺学教材中,由此可见卢卡奇的“知名度”。在卢卡奇的中国接受历程中,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是一个重要节点。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卢卡奇摆脱了“卢卡奇与胡风”“卢卡奇与苏联潮流派”的关系,开始以文学的“修正主义”身份进入中国。1958年,《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在中国出版,集中苏联、民主德国学者对卢卡奇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考赫的两篇文章,考赫不仅以批判的方式回顾了卢卡奇重要的理论时刻,而且点出了卢卡奇的“修正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这是卢卡奇中国接受历程中的一个突破。⑥考赫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卢卡契的政治、文艺学和地位》《卢卡契的理论和政治》。参考译文社编:《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2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27-179页。1960年是卢卡奇中国译介的一个高峰。这一年,《世界文学》编辑部选编的《卢卡奇修正主义文艺论文选译》、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卢卡奇修正主义资料选辑》以及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料室编译的《有关修正主义者卢卡奇修正主义资料索引》三本“内部资料”出版;同年,《山东大学学报》以一组专题对卢卡奇展开批判。①这组文章共3篇,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Z1期上,即孙昌熙的《G.卢卡契为什么宣扬批判现实主义》、刘光裕的《卢卡契修正主义文艺观批判》和狄其骢的《批判卢卡契在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上的谬论》。《山东大学学报》对卢卡奇的批判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于卢卡奇文艺观的认识。孙昌熙论述道:“卢卡契的文艺思想主要就是否定文艺的阶级性、党性而代之以‘人性’、‘人道主义’;宣扬世界观与创作无关,从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指导创作的重大作用;夸大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从而毒化和破坏社会主义文艺,达到它攻击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一总结是较为到位的。质言之,对于卢卡奇的批判实质是两种现实主义诗学的博弈,不论在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正统文学观念的时期还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确立,卢卡奇推崇的“批判现实主义”始终是被作为异端对待的,其核心在于在“写真实/写典型”观念上的分歧。②这一时期一些期刊也刊登了关于卢卡奇的论文,如《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刊出的《作家与世界观》(1960年第7期)一文,就是卢卡奇原文的直接翻译,但是文前的“编者按”予以说明:“这是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还有一些英语世界对卢卡奇文艺思想评论的翻译,如美国学者斯泰因勒(George Steiner)的《卢卡契的文艺思想》(1960年第7期)、英国学者戴维(Donald Davie)的《现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63年第4期)和叶封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翻译的《乔治·卢卡契:美学的特点》(1964年第12期)。然而,因为现实主义的立场前见,致使其他诸种阅读卢卡奇的可能性被遮蔽。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学者已接触到“作为美学家的卢卡奇”“作为文化理论家的卢卡奇”“作为哲学家的卢卡奇”三副面孔。例如,《卢卡契修正主义文艺论文选译(八)》(《世界文学》编辑部印,1960年)中的《民主与文化》(冯植生译)一文(活页样式,第一页右上角有“内部资料·请勿外传”字样),就是一篇极为精彩的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可能是新中国早期具有文化研究性质的理论文章。
另一位对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家是布莱希特。1959年“布莱希特热”的主要促成机遇是中德(民主德国)建交10周年纪念活动③黄佐临提道:“根据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协定,我们决定在建国十周年时演出布莱希特的名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对加强中德文化交流,增进中德人民友谊,有着重大意义。”参见黄佐临:《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江流编:《我与写意戏剧观佐临从艺六十年文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55页。以及日本导演、剧作家千田是也和德国作家冈特·威森堡的推动。〔4〕这次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冯至等学者编译的《布莱希特选集》出版,冯至在该书“后记”表达的对布莱希特的认识集中在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剧作家的“战斗性”以及戏剧所营造的“间离效果”〔5〕。这一时期对布莱希特研究贡献较大的是黄佐临。1959年,他撰写的《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已经显示出征用布莱希特理论的意图。〔6〕1962年的《漫谈戏剧观》可以视作黄佐临对上述思考的深入〔7〕,该文发表后,学界围绕“戏剧观”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也引起了1962—1963年又一次“布莱希特热”。《漫谈戏剧观》的核心思想在于借助布莱希特理论打破斯坦尼体系的束缚、激活中国“写意”戏剧观,在理论互鉴、互融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戏剧革命化、日常化、辩证化和历史化改造。同时,将布莱希特作为前沿窗口,中国戏剧界也可以观察到其他西方现代戏剧的诸种样式。黄佐临将其作为斯坦尼体系的对立面而译介,以其抗衡斯坦尼体系的教条化影响;同时,布莱希特在斯坦尼体系、中国传统戏曲以及西方现代戏剧间扮演着突破者和沟通者双重角色。周宪将这种极为特殊的接受现象概括为“黄佐临现象”〔8〕。总体而言,1962年的热潮已经具有明显的研究性质,并且两次热潮的发生从“政治推动”到“艺术争鸣”的转变,体现了当时学界的艺术自觉。④1962—1963年“布莱希特热”中研究水准较高的文本有:卞之琳:《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系列,《世界文学》1962年第5、6、Z2(7、8月合刊)期;丁扬忠:《布莱希特与他的教育剧》,《剧本》1962年第9期;黄佐临:《从一个戏谈布莱希特的编剧特征》,《中国戏剧》1963年第1期;焦菊隐:《豹头·熊腰·凤尾——在中国剧协举办的第一期话剧作者学习创作研究会上的讲话》,《中国戏剧》1963年第3期。翻译理论文本主要有中国戏剧协会研究室编的《戏剧理论译文集》第9辑中的6篇论文,分别为《娱乐戏剧还是教育戏剧》(丁扬忠译,张黎校对)、《街景》(君余译)、《表演艺术的新技巧》(张黎译)、《戏剧小工具篇》(张黎译)、《〈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导演说明》(孙凤城译,叶逢植校)、《论布莱希特戏剧》(颜天译)。1964年后,“布莱希特热”退潮。①这次退潮可能与姚文元的文章《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有关,该文第一部分就1962—1963年戏剧观讨论认为,“脱离社会主义戏剧艺术实践的客观实际,从外国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艺术家那里规定的定义,来规定社会主义的戏剧观,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从中可以发现,布莱希特已被悄然冠以“资产阶级艺术家”的帽子。原文刊于《收获》1964年第2期。参见江苏省文联资料室、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印:《革命现代戏资料汇编》第2辑,1965年,第96-142页。其实,布莱希特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一直是作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文艺形式”而被批判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苏联学者纠结于布莱希特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而将其命名为“左翼表现主义”〔9〕时,中国学者却避开了这一问题,进而发现了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理论之间的联系。这种“接受的分歧”显示了在中—苏的理论张力中古典理论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建设的一个重要资源。
这一时期“卢布之争”已经译介进入中国②参考加洛蒂的论文《费歇尔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辩论——为艾伦斯特·费歇尔六十五周年诞辰而作》,张英佑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5年第3期。文章称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卢卡奇路线,另一条是布莱希特路线,“这两派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对立,是由于对艺术的本质和职能的观点不同、对艺术性的评论和标准的观点不同、对艺术和群众的关系的观点不同”。,但没有受到中国学者关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边界认识是通过对加洛蒂③加洛蒂是这一时期颇受中国学界关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除了关于“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译介,这一时期“内部发行”加洛蒂的著作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费歇尔的批判完成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1963年,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出版。该书借鉴现代主义(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的艺术手法,“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突破“过分狭隘的现实主义标准”〔10〕。此书发表后旋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引发激烈反应,以苏联为首的“正统”阵营对其“修正”姿态展开大批判。中国学界于1964年开始关注共产主义阵营中这场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共翻译了7篇《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章节和有关书评④具体译介的论文和这一事件的历史经过,可以参考洪子诚:《可爱的燕子,或蝙蝠——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5期。,并在《〈无边的现实主义〉代后记》译文后以“译者按”的形式将该书定义为“反现实主义逆流”〔11〕。1964年底,罗大冈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关于该书的书评,彻底地批判了加洛蒂的文艺观,论证文艺应当为阶级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我们提倡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加罗迪表面上反对固定不变的旧现实主义,实质上他所反对首先是、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12〕费歇尔的文艺观与加洛蒂相似,他大力论证现代主义艺术的合法性,在《艺术与思想的上层建筑》一文中他论述道:“谁在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结构主义等主义中看不到反抗的因素,谁简单地把它们说成是一种‘时髦’,颓废和由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畸形,说成没落的上层建筑,谁就不可能掌握现代文艺中的问题。”⑤这一时期《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翻译了关于费歇尔的4篇论文,分别是费歇尔的《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1963年第1期)、《艺术与思想的上层建筑》(1964年第3期)、《上升与没落之间》(1964年第6期),加洛蒂的论文《费歇尔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辩论——为艾伦斯特·费歇尔六十五周年诞辰而作》(1965年第3期)。“译者按”认为此文“全盘否定了阶级斗争对文艺观的作用”,是“修正主义观点”〔13〕。
二、美学视域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初期的“美学大讨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学大讨论”中关于美的本质问题,是新的美学话语体系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重要阵地。正如童庆炳论述的:“1956年开始的美学问题大讨论,最初仍然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是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进行的,并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讨论。”〔14〕在此大背景下,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同路人”身份与存在主义“唯心哲学”之间出现了接受的分歧;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考德威尔(Cristopher Caudwell)作为“美学大讨论”的补充资源进入中国;在对“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中,弗洛姆(Erich Fromm)的人本主义美学观作为“内部材料”“供批判用”。
存在主义美学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进入中国,有学者考证钱钟书、汪曾祺、张爱玲等人的文学创作就受到存在主义思潮影响,并且“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欢乐喜庆的新生活的阳光便迅速驱散了文坛上的存在主义‘阴云’”〔15〕。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萨特、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的相关理论文本以及与存在主义美学思潮相关的文学作品译介进入中国,但存在主义美学作为唯心主义哲学总体处于边缘态势。1954年,作为共产主义“同路人”的萨特与其伴侣波伏娃受到苏联政府邀请访苏,次年便受中国政府邀请并开启中国之行。正如柳鸣九指出的,萨特是当时“国际统战的对象”,因此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还“保持怀疑、警惕”〔16〕。中国之行对萨特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中,萨特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新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17〕,并在此后的文艺工作中表现出浓烈的“中国情结”①这里的“中国情结”指萨特在“五月风暴”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原样》(The Quel)杂志为主要阵地积极宣扬“毛泽东美学”。参见曾军:《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对“双百”时期的“文学是人学”争鸣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钱谷融在文章中以萨特为例,指出萨特“最终脱离了他们原来的流派,而被融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阵营里来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毕竟是热爱人,热爱生活的”〔18〕。而王道乾则专门撰文《关于让-保罗·萨特——驳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一个问题》,认为钱谷融与萨特的共同之处在于理解“人性”时“抽掉了历史内容与资产阶级内容”,进而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唯我主义”〔19〕。从钱谷融和王道乾的对话中不难看出,萨特在新中国初期文论中更多是作为一种案例存在,中国学者关心更多的是文学的人道主义问题而非存在主义哲学问题。这一时期中国读者对萨特存在想象性误读,例如当时在国内流传的萨特的剧本《涅克拉索夫》和《丽瑟》〔20〕,前者是一部讽刺反共的政治闹剧,后者则表明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二者在萨特的文学创作中均不是代表作。相对于萨特,梅洛-庞蒂之于中国学者较为陌生,这一时期只翻译了他的几篇论文和评述。②参见〔法〕梅劳-庞蒂:《眼和心》,戴修人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1期;〔法〕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梅洛·庞蒂哲学中的存在和辩证法》,《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1期;〔法〕巴里安德(J.-C.Pariente):《梅劳-庞蒂:〈符号〉和〈眼和心〉》,《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2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魏克(David Thoreau Wieck)的《一种存在主义美学:沙特和梅劳-庞蒂的学说》(仲清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期),是一篇学理性较强的关于存在主义美学的综述,其中已经提及萨特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什么是文学》,同时概括了梅洛-庞蒂美学思想的九个主要特征。此外,1963年出版的“内部读物”《存在主义哲学》一书摘选了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雅斯栢斯”)、萨特、梅洛-庞蒂的相关文章,该书“前言”中称:“‘存在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参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此外,《局外人》(孟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等待戈多》(施咸荣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厌恶》(收录于萨特作品集《厌恶及其他》,郑永慧译,作家出版社,1965年)等反映存在主义思潮的文学作品以“黄皮书”方式译介进入中国,这为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列斐伏尔是在“美学大讨论”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知识补充进入中国的。有当代学者回忆道:“‘美学大讨论’以后,中国美学界不仅翻译出版了……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1957)……。”〔21〕1957年俄译本《美学概论》①从材料搜集情况而言,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译介进入中国后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除了笔者在正文中已经论述了部分,还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例如,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就读过这本书,参见李圣传、黄大地:《黄药眠与“美学大讨论”的潮起潮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此外,当时一篇涉及建筑美学的论文也引用了该书的一些内容,由此可见《美学概论》当时传播是具备一定社会性的,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美学研究领域。参见吴景祥:《建筑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成长》,《建筑学报》1961年第8期。(杨成寅、姚岳山译,朝花美术出版社)译成中文;也是在这一年,《美学概论》(俄译本)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编入《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高叔眉译、曹葆华校)。〔22〕《美学概论》俄译本序言中就称:“列斐伏尔的著作贯穿了两个基本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理解和说明艺术、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史。”〔23〕不难发现,俄苏学者对《美学概论》的评价仍是以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准,但是细读此书,不难发现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美学概论》中引用了《手稿》中的名言:“……在社会中,对于人来说,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都是人的实现,也就是说,都是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所以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24〕尽管1956年《手稿》的中译本已经出版〔25〕,但是列斐伏尔对《手稿》的美学化阐释很有可能是在中国学界第一次出现。较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列斐伏尔的理论参与了现实主义诗学的相关争论,如“革命的浪漫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等,但均是作为“修正主义”理论加以批判,这与美学领域的译介形成鲜明对比,列斐伏尔在新中国初期的接受情况还有待深入考察。〔26〕
美学大讨论期间,朱光潜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考德威尔《论美——对资产阶级的美学的研究》一文,并撰写《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一文。②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于《译文》1958年第5期。参见《朱光潜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74-223页。之所以译介这篇文章,朱光潜的解释是:“尽管他的见解和我的有些分歧,而在美为主客观统一这个基本论点上则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篇论文颇有启发性,所以把它放在附录里。”〔27〕朱光潜显然采取了一种资源化的态度,试图借用考德威尔的“英国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文艺理论家”〔28〕身份来论证自己的“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的美学观。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美学在新中国初期译介中也遭到批判。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弗洛姆的认知还较为零散,有学者将其视为心理学专家〔29〕,但是在美学方面则是侧重于其对《手稿》人本化阐释。1964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五辑)中摘录弗洛姆著作《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第四章《人的本性》和第五章《异化》,两篇文章集中论述了劳动、异化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30〕很显然,在批判人道主义的视角下弗洛姆理论的丰富性并没有完全打开,它再一次“复活”是在1980年代。
三、批判性接受:西马文论译介的经验总结
除了上文所述现实主义和美学两个视域之外,还有一些西马文论家通过其他途径译介进入中国,如对卢森堡(Rosa Luxemburg)、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以杰出革命者的身份进行传记宣传,其中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及其理论价值在译介过程中已经提及。③《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10辑在“葛兰西”词条中对其作了大致的概括:“葛兰西的主要著作收在《狱中札记》中。在哲学方面,葛兰西主要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还研究过美学、社会学和哲学史等。葛兰西对意大利文化的研究、对天主教的反动作用的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葛兰西研究了基础和上层建筑、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还研究了文化革命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参见《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1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11页。虽然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部分美学、文论著作也译介进入中国,如沙夫(Adam Schaff)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①〔波〕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林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此外,沙夫的其他哲学文本这一时期也有引进,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并没有将东欧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的、具有创新性的思潮流派来看待②除了上述重要著作译介,一些论文集的汇编也促进了学界对于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的认识。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两辑《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译文集,其“前言”中说:“为了帮助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这次斗争的情况,我们从两年来外国报刊上选择一部分最主要的有关这次斗争的批评文章。”其中第二辑中有匈牙利论文4篇、波兰论文7篇、捷克斯洛伐克论文10篇、保加利亚论文5篇。,东欧学者的相关著作被视为俄苏文论的子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代中国学界译介的两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专著。1963年2月,南斯拉夫学者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供内部参考)③〔南斯拉夫〕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上、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有学者总结道:“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的出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发展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理论工作者是通过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外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名字及其著作和观点的。”参见衣俊卿:《中译者序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页。在中国出版,该书第五编《第三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涵盖了卢卡奇,还介绍了科尔什、葛兰西,第六编《现今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外的马克思主义”。同年9月,英国学者利·拉贝兹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供内部参考)〔31〕在国内出版,其中第二部分《人格、真理和历史》第十章题为《相对主义和阶级意识:格奥尔格·卢卡契》,这一部分还介绍了“德波林”“布洛赫”“青年马克思”等内容;第四部分《新左翼》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情况,这都是在1980年代让中国学者非常兴奋的一些关键词。由此可见,在1960年代的中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体系已初具形态,尽管这一知识体系最初是通过译介方式建构的,但是不论是英国学者(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南斯拉夫学者(社会主义阵营)的专著,它们的出版都说明在1960年代中国学者已经有了一种更大的学术视野,开始有意识地绕开苏联去寻找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
总体而言,“批判性接受”成为新中国初期西马文论译介的主要方式。这不仅仅表现在译介方式上的“灰皮书”“黄皮书”“内部资料”“供内部参考”“供批判用”“编者按”等,还深刻地体现在对西马文论的理论态度上:西马文论一方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又身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学术语境,这导致新中国初期学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过程中采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新发展”的双重视域。然而,“批判性接受”不是不接受——区别于“闭关锁国”式的彻底封闭,它是批判与接受的交织:接受的目的是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完成对西马文论的接受。尽管这一过程中强大的立场前见会遮蔽放送者本身的多元性,但是批判性接受从本质而言还是开放的,纵观文学史与文化史,它具有发展成为接受理论中“元模式”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初期西马文论的批判性接受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
第一,批判视域的“俄苏化”影响。“俄苏化”影响直接体现在诸多理论文本都是参照“俄译本”译介进入中国的;另一方面,对于卢卡奇的批判现实主义、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批判,也都是承袭苏联文艺界的观点;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独创性被遮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将其视为俄苏文论的一个子系统。对布莱希特的译介尽管是试图突破斯坦尼体系,但这恰恰是俄苏化影响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学界没有形成对西马文论家的总体性认识,但是对于西马文论总体上持批判态度,主要是基于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推崇的立场,因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共识就是“反对苏联已经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据目前搜集到的材料看,1963年,通过梅洛·庞蒂著作《辩证法的历险》①就目前的材料搜集来看,《辩证法的历险》在1960年代有两个选译本: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存在主义哲学》选译的是全书的“序”和第二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辑选译的是第二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章《真理报》。译者均为杨一之。的部分内容,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初步接触到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这里的“西方”已经具有一种区别于地理空间意义的文化意义,指的是有别于苏联“正统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收录《辩证法的历险》一文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一书的“编者说明”写道:“本书是《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选录了一些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从中可以看出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将西马思潮定义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奠定了最初“西马非马”的论调。因此,从对梅洛-庞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认知到1978年徐崇温“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译介,可以明显发现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变迁。因此,通过西马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建构过程中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纠结”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学者是选择“以俄为师”,但是当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后,“反思俄苏化”又成为问题的另一面,但其中俄苏话语强大的前见又潜在地发挥着影响,“以俄为师—反思俄苏化”成为新中国文论建设过程中内在的张力。
第二,两种不同形式的批判性接受初步显现。在对待卢卡奇、加洛蒂时,是完全的“独白式批判性接受”,接受者以话语霸权的姿态彻底地控制了接受声部,放送者沦为不能发声、必须沉默的存在,接受者的前见不再仅仅成为一种影响,而成为接受过程中的全部支配力量;在对待布莱希特、列斐伏尔、考德威尔时,特别是黄佐临、焦菊隐对于布莱希特的理论态度,体现出一种“对话式批判性接受”,接受者与放送者在理性对话过程中既积极地改造放送者,同时也改造接受主体本身。赛义德曾以卢卡奇在法语世界的接受(以戈德曼为代表)和英语世界的接受(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提出了“理论旅行”〔32〕的基本框架。但是,理论在跨文化旅行中遭遇抵抗却是较为常见的一个现象,这是赛义德没有具体论述的内容。这里通过对两种批判性接受的辨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模型。
第三,批判性接受的内部话语成分存在时间性转变的可能。归纳比较这一时期西马文论的译介文本,可以发现批判性接受内部的话语成分大致有三类:“放送者直接的话语”即翻译的理论文本、“由接受者转述的放送者话语”即中国学者客观转述的西马文论以及“接受者的话语”——一般由“编者按”“前言”以及文本内部的批判性言语组成。这三种不同性质的话语因社会语境的变迁促成接受行为的时间性转变,影响着特定时代接受者的认识,生成了批判性接受本质上的开放性。正如有学者回忆到:“灰皮书”“黄皮书”的出版在“20世纪60年代为配合‘反修’斗争……后来,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流入社会,成为有关研究人员的重要资料和某些年轻人的启蒙读物,最后被纳入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行列,其作用和影响是始料所不及的”〔33〕。这当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从一九五六年起……曾陆续选译印出卢卡契的论文三十余篇,有关评论资料十余篇……一九六五年,译稿已基本集齐”〔34〕。这一批关于卢卡奇的文稿,之所以在1980年代后能成为卢卡奇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主要原因之一是省略了新中国初期较为激进的、具有批判性质的接受者的话语,保留了放送者直接的话语。
正如巴赫金所言:“不存在任何绝对死去的东西:每一涵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35〕当下对新中国初期西马文论接受的研究构成了重返新中国文论的一个契机。新中国初期对西马文论的译介是基于文论发展的需要而面向外部的资源探寻,借助西马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突破传统新中国文论研究中“中—苏”二元立场,由此探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建设历程中的世界性因素。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思想的批判性接受与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学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世界性影响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全球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