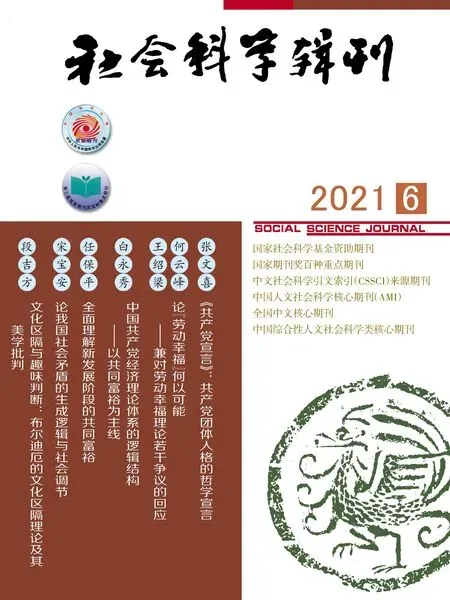重拾生活:社会工作的本质回归与理论重构
童 敏
一、问题的提出
来自“科学慈善”运动的西方社会工作一直被视为一种提供关怀的助人服务,它始终秉持着“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1〕在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由于受到专业化的挑战以及制度安排等众多现实因素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总是过多地关注“助人”服务的落实,而忽视了服务中“自助”的人文关怀,为此人们不断质疑其是否承担起了社会工作的初心,这导致西方社会工作在其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人们对其本质的质疑声〔2〕,特别是在专业服务取得快速发展后需要进行实务经验理论总结时,就更加迫切需要回归初心,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本质,以便在繁杂纷乱的实务经验面前找到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进而建构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工作理论。〔3〕
对社会工作本质的审视和讨论是人们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社会工作也不例外。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不仅专业服务领域得到迅速拓展,而且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建成了颇具规模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社会工作督导队伍。就中国的社会工作而言,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总结本土的实务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社会工作理论。鉴于此,中国社会工作者需要承担起历史责任,重新回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本质上来,审视社会工作理论逻辑与社会工作本质上的内在关联以及中西方之间的差别,从而找到能够承载社会工作本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使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既具有本土实践经验的内涵,又具有社会工作本质的人文关怀。
二、源于实际生活的社会工作
作为西方社会工作创始人之一的美国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领袖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在“科学慈善”服务基础上提出深入贫困家庭的“友好访问者”的家庭入户服务,她带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热心人士来到贫困家庭中开展个案帮扶,将实际生活中的物质帮助与心理辅导工作结合起来。〔4〕里士满在1901年的一次全美工作会议上将这样的个案帮扶服务的原理总结为“在环境中帮助他人”(to help the person in his situation)〔5〕。里士满认为,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生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要么是个人无法适应生活环境的要求,要么是生活环境妨碍个人的适应,二者都表现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与生活环境关系的失调。〔6〕因此,里士满相信,有效的社会工作服务既需要针对个人开展直接服务,也需要针对个人的生活环境开展间接服务,将个人的改变与生活环境的改变结合起来,相互促进。〔7〕
西方社会工作的另一位重要创始人是简·亚当斯(Jane Addams)。作为美国睦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她倡导在贫困人群居住的社区建立综合服务中心,针对社区居民的现实生活需要开展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居民在生活中需要什么服务,就开展什么服务。〔8〕因此,亚当斯所在组织的服务范围很广,包括社区居民常规需要的多项内容,如孩子课业辅导、闲暇娱乐、职业培训和技能学习以及特殊需要的艺术沙龙等。〔9〕此外,亚当斯还通过社区居民的互助以及培育骨干志愿者等方式让社区居民了解社区的需求,并且通过社区居民参与和社会倡导等手段推动整个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她甚至反对里士满提出的个案工作的专业化服务策略,主张只有通过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10〕
高登·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是里士满的学生,她深受里士满“在环境中帮助他人”这一服务理念的影响,认为在帮助人们摆脱生活困境过程中,针对个人的心理和针对环境的社会这两方面的服务需要同时开展,二者根本无法拆分开来,因为心理和社会就是人们发生改变的两面,它们一起构成生活改变的整体,是人们寻求成长过程中的两个最核心元素。〔11〕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的成长规律,汉密尔顿称这种人与环境无法拆分开来的现象为“人在情境中”(the person-in-his-situation)〔12〕,即人的任何改变都离不开他所在的环境的影响,环境是人成长改变的现实条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密尔顿用了“his situation”来描述人们所处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是能够被人们直接感知到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直接与之互动的环境。简而言之,这种环境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绝不是人们预先设想的某种概念意义上环境。在这种现实中,人的任何改变都是发生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的,不仅影响自己,而且也影响环境,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的整个生活状况也将因此发生改变。〔13〕
三、抽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取向
尽管里士满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在环境中帮助他人”,但在是否专业的质疑声中里士满还是为社会工作选择了医学诊断的服务框架,把社会工作等同于医学,强调就服务对象的问题开展全面研究和科学诊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针对服务对象做了全面的研究和诊断之后,才有可能制定科学的服务计划,开展有效的专业服务。〔14〕这样,服务对象就成为需要社会工作者给予诊断的对象,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由此,里士满创建的个案工作也就成为置身于服务对象生活之外的标准化规范指导。从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开始踏上一条抽离日常生活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下,人的心理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从人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变成心理治疗师研究、诊断和治疗的焦点。社会工作也是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这一诊断治疗的理论逻辑一直占据社会工作理论的主流,有学者甚至直接把社会工作等同于对个人心理困扰的治疗。〔15〕
为了促进人与环境的联结,也有很多社会工作学者没有直接引入注重个人心理纵向深度分析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而是采用了关注横向环境适应的黑恩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的自我心理学和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kson)的人生八阶段理论。〔16〕正是在这种注重自我的环境适应功能的理论基础上,社会工作建构起了强调问题评估和问题解决的心理治疗路径,以便加强心理与环境的联结,如问题解决模式、任务中心模式以及危机介入模式等,认为社会工作需要处理的是人们在环境适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弗洛伊德所关注的个人心理结构的困扰。〔17〕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民权运动和服务使用者运动的影响下,社会工作理论开始关注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质疑之前只关注个人心理治疗的社会工作理论的正当性,认为这种心理治疗取向的社会工作只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变种,把人们的失败归结为个人的原因,看不到社会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具有明显的社会污名化倾向。〔18〕因此,有学者要求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这种社会环境的改变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甚至有学者直接把社会结构作为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因素来考察,强调社会结构的局限才是导致人们产生问题的关键。〔19〕这样,社会工作理论开始出现与心理治疗取向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取向的发展趋势,不再注重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而是把个人放回到环境中,关注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从“人在情境中”个人的一端转变成环境的另一端。但实际上,二者的服务逻辑却是极其相似的,都采取了抽离日常生活的实证主义逻辑,只是传统的心理治疗取向关注个人,而社会结构取向仅仅关注环境而已。
四、抽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反抗
当社会工作为了专业认同选择了抽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发展取向之后,社会工作者便不自觉地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实务中需要深入实践场景,从实际生活出发遵循个别化的服务原则;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却需要抽离实践场景,依据普遍化的科学原则总结实务经验。这样,对于实务社会工作者来说,理论就成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鸡肋”。甚至一些社会工作者直接反对以理论作为指导来开展专业服务,认为人们之所以把是否运用理论作为是否专业的标准之一,是因为相信理论能够揭示现象的本质,呈现事物的普遍规律,则又陷入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知识观。正是在这种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就会面临两个突出的难题:一是如何将人与环境联系起来,避免因相互割裂导致的要么偏向心理、要么偏向环境的理论发展困境,解决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实际专业服务提出的要求;二是如何将人的改变能力发挥出来,避免因只关注问题而导致的社会污名化和改变动力不足等难题,以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真正走向“助人自助”的发展目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生态系统视角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因素也像心理因素一样是不断变化的,不仅人影响环境,而且环境也在影响人,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20〕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凯罗尔·梅厄(Carol Meyer)发现,由于受传统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不自觉地把人与环境割裂开来,要么只关注个人心理的调适、要么只注重环境的改善,并没有把人与环境看作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21〕因此,梅厄认为,社会工作需要一种崭新的服务逻辑,注重人与环境的转换过程,把两者联系起来。〔22〕由此,社会工作考察的焦点就不再是个人或者环境的不足,而是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过程,分析人们如何行动才能带来环境的改变或者环境的改变如何影响人们的应对行动。〔2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另外两名教师凯罗·吉门恩(Carel Germain)和艾利克斯·基特曼恩(Alex Gitterman)指出,社会工作是在人们的生活场景中开展的助人服务,它不是针对人们的不足,而是针对人们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遭遇的困难,需要将人与环境结合起来,找到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平衡点。〔24〕这样的生态系统视角的服务逻辑就具有了将人与环境联结起来的功能,它不再把个人与环境割裂开来。〔25〕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发现,这种抽离日常生活以问题修补为目标的服务逻辑不仅无法推动服务对象发生真正改变,而且还会导致压迫关系的产生,迫使服务对象按照社会工作者的意图加以改变,使服务对象出现“越帮越弱”的情况。优势视角就是这样一种视角,它直接挑战这种以问题修补为目标的服务逻辑,认为人们一旦把服务对象视为是有问题的人,就会不自觉地关注环境中的不足,人的问题与环境的不足就会相互制约,形成恶性循环。〔26〕为此,优势视角强调,人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想法,需要假设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每种环境都是有资源的。〔27〕只有这样,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才会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实际上,优势视角代表着一种与问题修补视角完全不同的理论发展取向,这种取向不再关注人的问题,而是注重人的优势。类似的还包括增能理论。增能理论尽管也强调人的能力,但是与优势视角不同,它假设人们具有一种自觉(self-awareness)的能力,通过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人们就能够自觉地发现自身拥有的生活改变力量,并且通过集体行动学习掌握这种能力。〔28〕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掘人的优势、从优势入手推动人的改变,这几乎成为社会工作的基本服务原则。〔29〕
五、回归实际生活的理论探索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工作开始放弃抽离日常生活的宏大描述,转向对宏大叙事背后人们日常生活的考察。人们发现,表面普遍一致的“客观”规律掩盖了背后的多元故事,这样,主流之外的在地日常化的生活经验重新回到社会工作者的视野中。〔30〕特别是在国际化的文化交流中,在地知识的生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31〕与传统的、以问题修补为目的、抽离日常生活的标准化服务逻辑不同,这种注重在地生活经验的服务逻辑相信生活是多元的、变化的,生活自身就拥有发展变化的逻辑,绝不是人对环境的简单适应,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需要与问题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帮助利益相关方厘清各自的要求,以便能够有效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多元化发展诉求。〔32〕此外,不确定性也常常被视为现实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与抽离现实生活所追求的普遍化、一致化的传统社会工作理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社会工作者把“建构”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逻辑框架。〔3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建构”的服务逻辑框架关注的是与主流不同的日常生活,并且还把权力关系的考察引入到人们现实的日常人际交往中,但是这样的分析借助了一个很重要的工具——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后现代社会建构主义相信,人们与环境之间的交流是需要借助语言这个媒介的。〔34〕由此,社会建构主义所提到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现象,只是这种现象不同于实证主义所推崇的普遍一致的宏大社会事实。正是因为如此,这种服务逻辑框架仅仅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意义的建构过程,仍旧注重对人们生活的社会维度考察,并没有就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讨论生活,导致其不自觉地忽视了人们与环境以及与身体之间的交流,很容易夸大人际交往的作用和意义,低估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要求,进而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
直接提出从人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是澳大利亚国际知名社会工作学者简·福克(Jan Fook)。她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与生活经验直接相关联的小场景对人们成长改变的作用更为突出。〔35〕为此,福克提出了场景服务的概念,认为生活中的小场景才是理解人们的自我和把握自我成长改变规律的关键。〔36〕在这种生活的小场景中,人们通过审视自己的应对能力就能够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可改变之处,承担起生活改变的责任。〔37〕这样,人们就不会站在生活之外寻找生活困境的解决方法,而是能够融入现实生活中探索改变困境的途径。〔38〕这是一种在生活场景中寻求成长改变的方式,它始终以现实生活为起点,与传统的以原则为导向(rule-bound)抽离日常生活的服务逻辑不同。〔39〕福克强调,只有把人们的改变放回到他们的生活场景中,人们自身拥有的改变力量才能被激发出来;因此人的成长改变是脱离不开环境的,也无法完全由环境来决定。〔40〕
不过,福克倡导的批判社会工作在讨论人们的反思学习能力时,却用了批判反思的概念,强调对社会处境进行行动反思,审视社会处境的现实要求。〔41〕显然,批判社会工作是从社会维度来审视生活中的小环境的,其目的是促进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的结合,实现所谓的社会情境中的“个人解放”〔42〕。
六、作为一种知识观的生活
尽管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来自生活—抽离生活—回归生活”的发展轨迹,但是始终都把生活作为人们一种日常的经验,认为生活经验背后呈现的是人们的心理特征或者社会结构。就生活经验本身而言,它是松散、零碎、变动的,是无规律可循的。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尝试对生活进行界定和分析时,不可避免地将其延伸到心理分析或者社会结构分析的层面——要么把人视为对环境的适应,要么把环境作为决定人的行为的根本原因。即使引入了社会建构主义逻辑来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也依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建构,展现的是人们社会层面的生活,并没有就生活本身开展讨论。因此,在科学理性的实证知识观指导下,生活这一概念始终被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置于科学理性探索的边缘,作为心理分析和社会分析的原材料和附属品,并没有获得学者们的足够关注。
一旦人们把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焦点放在了心理分析或者社会分析上,就会不自觉地采取一种单向因果分析的实证逻辑,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站在生活之外审视生活的问题,只关注人们生活中的不足——不是遭遇问题的心理层面或者社会层面,就是心理与社会两者关系的失衡——根本忽视了生活的一项重要特征:人与环境的联结。人始终处在环境中,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在推动环境的变化。人与环境之间的循环影响是生活的核心特征,它不适用于单向的因果分析逻辑,而是需要运用一种双向的闭环思维将人对环境影响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连接起来。在这种双向的闭环思维下,人们对环境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人们直接影响环境的能力,而且取决于人们对环境影响自身的预见能力。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具备在环境变化中推动环境改变的能力,不再是抽离生活的“评判官”,而是融入生活并且促进生活改变的“推动者”。因此,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指人们分析现象的一种维度,也不是指不同于心理和社会的一种领域,而是人们理解现实的一种视角,即一种把生活视为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现实,不是非“科学”的代名词。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知识观指导下,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不仅需要放弃抽离日常生活的实证主义逻辑,让人们能够真正融入现实生活,而且需要放弃容易跌入相对主义陷阱的建构主义逻辑,促使人们能够接纳现实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成长之路。显然,这种循环影响的生活知识观恰恰信奉一种有条件的建构主义逻辑,在推动人们接纳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激发人们的成长动力,而在激发人们成长动力的过程中又能够进一步推动人们扎根现实生活、了解现实生活的需求。由此,社会工作的助人服务就不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那么简单,而转变成了对人们成长规律的探寻,包括如何接纳现实生活环境的要求和如何在特定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找到成长之路。一旦引入了这种生活知识观,社会工作助人服务的客观性就不是遭到削弱,而是得到了增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现实要求,既不夸大它的客观性,也不忽视它的可变性,使社会工作的助人服务有了激发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能动性的作用。
七、建构以生活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社会工作是在抽离日常生活的机构服务中完成了自己的专业化发展要求的,而中国社会工作则是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开始专业化探索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条件,任何中国本土的专业化服务都脱离不开对生活场景的考察,都需要回答如何促使人们在生活场景中找到成长的路径,从而带动整个生活场景改变的提问。正是在满足这样的专业化服务要求基础上,中国社会工作才能走出自己的专业化发展道路。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建立在这样的生活改变的服务逻辑之上。生活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它需要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边缘位置走出来,成为人们考察的中心,使自身不同于机构服务的、独特的改变逻辑呈现出来,确保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拥有现实的基础和蕴含自身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不再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附属。
这种以生活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让中国社会工作有了本土化的实践路径,它既不是以问题的界定和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问题实践策略,也不是以优势的确定以及能力和资源的发挥为中心的优势实践策略,而是融入特定生活场景中寻找可改变之处的空间实践策略。在这种空间实践策略中,人们不仅具有了扎根现实生活的能力,而且具有了改变现实生活的能力。由此,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也就拥有了清晰的专业定位,尽管它需要关注人们的心理,但是它不同于心理咨询,不是为了帮助人们消除内心的困扰,而是为了提升人们身处生活困境中的应对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力避免因过分关注心理而忽视人们自身的生活应对能力的问题。同样,尽管也需要考察社会因素对人们的影响,但是它不同于社会支持,因为它不是为了让人们避免问题的困扰,而是为了提升人们身处生活困境时的社会资源运用能力。我们需要尽力避免因过分注重社会支持建设而导致人们自身生活应对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只有在以生活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指导下,才能真正在生活场景的实践中找到自己的专业位置,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就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服务目标而言,一旦社会工作者采用西方这种抽离日常生活的问题视角或者优势视角开展专业服务,就会不自觉地陷入两难境地。“助人”服务开展得越多,人们要么成为有问题的人,自主的能力变得越弱;要么强调自身能力的发挥,忽视现实的需求,加剧了与现实的对抗,最终都无法达到“自助”的目的。显然,要将“助人”转变成“自助”需要将社会工作者的“助人”服务与人们自身的成长要求结合起来,提升人们自身在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应对能力,发挥人们在现实生活场景中带动生活场景改变的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学会运用以生活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逻辑,不再成为站在人们生活之外指导人们生活改变的“专家”,而是担任深入人们生活场景中陪伴人们成长改变的“同行者”。
八、总结
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脱离不开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追问,它是对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社会工作本质的回答,是人们运用理论逻辑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工作本质的过程。特别是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亟须总结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建构能够呈现本土实践经验并且可以与西方社会工作对话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建构更需要回归社会工作的初心,以便能够真正为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提供积极的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虽然源自生活实践,但是在机构服务专业化的推动下,逐渐采取了抽离日常生活的理论建构策略,这样的理论建构策略必然使西方社会工作面临人与环境脱节以及过度关注问题的困境。尤其是,随着多元社会的发展,普遍、一致的宏大故事受到人们的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也需要重新回到生活实践。不过,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是从社会角度理解生活实践内涵的,依旧采取传统的科学理性角度审视生活,并把它作为理性的对立面,置于人们关注的边缘,没有将其视为理论建构的核心。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则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在社区这种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始专业化探索的。生活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因此建立一种以生活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不仅能够协助人们在生活场景实践中找到成长改变的路径,推动现实生活的改变,而且能够真正促使社会工作实现“助人自助”的目标,坚守社会工作的专业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