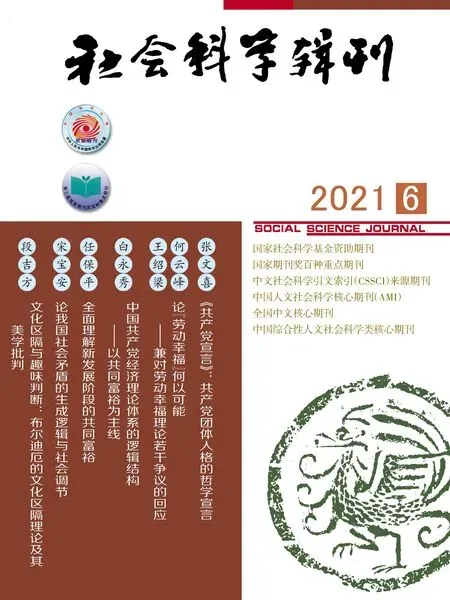“诗意”消失的空间批判
——从列斐伏尔的“诗创实践”与“诗学革命”视角
车玉玲
在高度现代化的当代世界中,如何“诗意”地栖居在繁华的都市中以及诗意的存在何以可能等问题,进入了20世纪哲学家们思考的视野。“诗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它常常与神秘、神性、超越、自由、感性、美等相关联,或者说是一种理性与技术规定之外的样态。正因为如此,在消费主义至上的当代社会中,最无力与没用的“诗意”被哲学家们赋予了新的内涵。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用“诗意的栖居”描述了人的理想的筑居状态。而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诗意”以新的意义和价值,甚至把抵抗物化与消费社会、变革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希望寄于此。学界却并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原因也许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直接使用“诗意”一词,比如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精神、葛兰西的新文化、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等等,这些范畴都倡导一种不同于被技术所操控与规训的新的文化样态。笔者尝试以“诗意”来诠释该思潮中的这一特点,并从空间批判的视角探讨“诗意”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消失的原因。
20世纪中叶以后,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直接提出了“诗创化的实践”概念,以此作为他所理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而且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批判》的第2卷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瞬间”(moment),在这里蕴含着“诗学革命”的思想,诗性的瞬间成为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途径。列斐伏尔直接提出了“诗意”在改变当代人的存在状态和空间问题的重要位置,“诗意”不仅跃升为他哲学中的一个范畴,而且成为实现变革与救赎的可能途径。
一、被遮蔽的“诗意”存在
“诗意”是人的本性之一,人除了具有动物的本性与生物特性之外,还具有超越性、精神性、创造性、神性等等,这些可以统称为形而上学的本性,这就是“诗意”存在的根源。同时,人还具有情绪与感性,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他的内在不可抗拒的各种情绪。具体而言,“诗意”存在的本质在于人是能够意识到无限的有限者,人能够超越自身生物有限性的限制而与无限相连,这里的无限既包括人能意识到自身的短暂与宇宙的恒久,也包括人能以神圣为尺度来不断完善自身,与无限相连并接近,“诗意”就存在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然而,永恒永不可得,无限永难达到,必死的生命中有着无法消除的恐惧与绝望,同时也有狂喜、爱、希望、激情等等强烈的情绪,诗常常是最好的表达。然而,在当代的商品社会中,却已经没有了诗歌、诗人存在的条件与土壤,真正的诗与诸神一起成为回忆和背影。很多哲学家都思考与回答了作为人的本质的“诗意”是如何被消解与遮蔽的问题,他们分别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语言、技术、商品等方面深刻地剖析了这一根源。
一般我们在谈到“诗意”的时候,总是和田园牧歌联系在一起,“诗意”与农耕社会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因此,随着农耕社会的渐行渐远,“诗意”也随之丧失了。换言之,“诗意”的消失与现代性的进程是相伴生的。大地时代结束,而技术时代来临了,技术成为了支配现代社会的“架座”,这意味着技术在各个方面实现了对于现代社会的控制及其对于现代人的支配。技术不再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持存”而“架座”了人的生活、社会、自然,同时技术不断地扩张并成为一种功利性的活动。技术所造就的社会与自然是明晰的、可计算的、功利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诗意”存在土壤的理性化的世界。当海德格尔看到美国的宇宙飞船登月发回地球的照片时,他更加惊慌而忧虑了,他在《明镜周刊》的访谈中说:“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总是一个进步推动下一个进步运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1〕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来的现代人,筑居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诗意”何来呢?
可以说,海德格尔主要是从技术重塑了人及人的生活世界这一视域深刻地剖析了“诗意”消失的原因,他表达了天、地、人、神共在的“诗意栖居”的理想,可是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却缺少对于造成现代人空间问题的政治与经济方面原因的分析。作为海德格尔最优秀的学生,马尔库塞与他的老师在思想上分道扬镳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海德格尔关注的是缺少具体的社会条件的、孤独的此在个体。列斐伏尔也认为,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思想是一种“右倾的”“怀旧的”都市社会批判立场。〔2〕正是在这一方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比海德格尔更前进一步,他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具体阐释了现代社会“诗意”丧失的现实因素以及恢复空间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方法。
“诗意”作为人之本性的存在,一方面来源于人性之中对于无限性与超越性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来自大自然带给人类的惊诧,更具体来说,来自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然而,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筑居于其中的空间却已经千篇一律了。同质化的都市空间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场所,高架路桥、商圈、社区、摩天大楼、休闲场所、修剪整齐的绿地等等,我们难以从建筑风格和民俗文化上区分出各地的差别,只能在刻意保留的古镇和供游客欣赏的民俗表演中感受到这个地方曾经独有的特色。自20世纪中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用“空间生产”解释了产生这一后果的原因。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明确阐释了空间的资本化,空间本身成为资本与商品是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当代的城镇化进程和超大都市的不断涌现,都是资本逻辑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空间不再仅仅是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场所”,而是以资本的形式进入了流通领域,他们被买卖、炒作,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宠”,使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方式,缓解了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和延续。”〔3〕
空间资本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当代都市空间的千篇一律,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后果是: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多样而丰富的大自然不断被蚕食、吞并乃至消失。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面对技术对于人的控制曾说:“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则是人死了。”〔4〕空间生产的直接后果是在全球不断涌现的当代社会,是大自然的渐行渐远与不断被吞噬。被空间生产改造后的自然空间,以资本的原则被塑造为一个个“产品”,这些产品可重复与批量生产,是一个被组织与规划出来的空间。随着这样空间的不断扩张,原生态的自然空间逐渐萎缩。我们知道,除了城市之外,乡村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主要聚居地,并且人们通常把乡村当作一个休憩地与避难所,尤其是在战乱、瘟疫等盛行之际。但是,在当代社会,乡村成为城市的附庸,它不再代表另一种文化与生存方式,更多地成为大都市劳动力的补给站与生活资料的供应地。超大都市的出现,把更多的空间组织成一种可利用和控制的资本空间。这意味着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无差别的人造空间,奥妙无穷的自然界渐行渐远,人们的“诗意”得以被激发的外在条件丧失了。
可以说,“诗意”的缺失与城市化的进程直接相关,在越是喧嚣与繁华的都市,越缺少“诗意”存在的土壤。“诗意”与都市真是互相矛盾而不能共存的吗?这个问题的提出促使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理想的筑居状态。实际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蕴藏在中国当代的城市设计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新概念,把生态系统的维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当然也是当代城镇化建设的原则与方向。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增长速度很快,因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如何解决与规避已经出现的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美丽中国”与“美好生活”的提出就是对于同质化资本空间的纠偏,为“诗意”栖居的实现提供现实的可能。
二、“诗创实践”与诗创实践本体论
同质化的都市空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实践,这不仅是恢复人之“诗意”存在的前提,更是回归到真正的人之存在方式的必要条件。当代学界对于实践进行了片面化的诠释,几乎把实践等同于物质生产本身,而忽略了实践中所具有的终极关怀的含义。在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范畴中,人的解放与理想社会的生成是实践的终极目标。但在资本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这一维度被一些“追随者们”遗忘与舍弃了。列斐伏尔重新阐释了实践的含义,并提出了“诗创化实践”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元哲学明显地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5〕,“诗创化实践”成为列斐伏尔所诠释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概言之,列斐伏尔对于实践的理解是要突破仅仅从生产与劳动的角度理解实践的局限性,回到语言的人、游戏的人、日常生活的人这些更全面而本真的人的存在中,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实践就是所谓的“诗创”(poiesis)。也就是说,实践中也包含着生产之外的人的广阔的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体验,“爱、激情、身体、感受——充沛过剩的创造力、冲动激动与想象实践……诗创活动”〔6〕。
列斐伏尔的“诗创实践”概念兼具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色彩。“诗创实践”就是存在本身在大地的展开与创造过程,就是人的身体对于周围自然物适应与再造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这里,这种适应不仅表现为对于时间、空间等自然物的改造,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由生产过程而造就的人化自然,更主要的是包含着这种适应过程的“剩余物”,如节日、休闲、体育活动、都市化等等。也就是说,除了适应与改造自然之外,还包含着人对于自身的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适应。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观在其本来意义上是从对象化活动的角度来阐释的,这种对象化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当然不只局限于物质生产的领域,创造性、超越性、革命性乃至最终实现的人的自由与解放,都包含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但是,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完全将其遗弃了。发达资本主义“制作”出了一个强制的由工业生产组织起来的日常生活与同质化的都市空间,在这里,实践已经被片面化为一种单纯的生产活动本身,这直接导致了现代人存在的物化状态。因此,“诗创实践”的提出是对这种被操控的日常生活的反叛。
列斐伏尔的“诗创实践”作为人之存在的基本方式具有本体论的性质,他用诗创实践本体论代替了物质生产实践本体论。在他看来,这是对于马克思实践观念本意的恢复。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虽然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但是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是从古希腊的实践概念中来的,甚至应该回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实践概念。实践是一种非功利性质的道德活动。实践和制作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前者属于智慧领域,善是贯穿实践的目标,而制作则是一种科技理性的现实操作领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把二者统一起来,但是在这里隐含一个前提:实践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的完整性的实现,制作应该与这一终极目标直接相关联,才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来含义。这样,就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目标具有了共同性。问题在于,随着技术原则的泛化,实践的技术化倾向完全阉割掉了它对智慧与善的追求,这一重要因素的遗忘,直接造成了当代的种种问题。
同质化都市空间的出现,正是这种实证化实践观念的结果。在这种实践观念中贯穿着两个主线:技术原则与资本逻辑,二者互相勾连造成了当代的这种空间形态。城市学家芒福德用“机械式的思维方式”来描述现代城市建设中遵循的技术原则。在城市空间的建设中,机械论中的规则、手段、目标等成为准则,城市是按照效率与实用的原则被筑造出来,精神与人文的内涵则被边缘化了。有机城市被机械城市所替代,于是,城市不再是一个“有机整体”,“城市从作为联合的工具,文化的避风港,变为了分崩离析的工具并日益对真正的文化构成威胁”〔7〕。另外,按照资本逻辑生产出来的当代都市空间,具有资本的属性,空间成为商品与资本增殖的新载体,效益最大与效率最高成为内在目标。货币成为城市中所有空间可以通约的衡量标准,资本拜物教成为现代人的新宗教。由于缺少具有统摄作用的文化内涵,文化变成各种杂糅的拼盘。在这样一个被规约与生产出的空间中,“诗意”不仅是多余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三、“诗学革命”与差异化空间
空间批判的最终指向之一是实现人的理想的筑居之所,或者说“诗意”栖居。在这里,体现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理论的最终目标是指向现实生活本身,“诗意”能够走出文学的表达范围而演变为“诗学革命”,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就在于其理论自身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列斐伏尔提出,只有通过“诗创实践”造就一个差异性的空间,才能为人的“诗意”存在提供条件。为此,应该回到日常生活本身,而不是被资本所宰制的异化了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提出了“日常生活艺术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8〕日常生活本身应该是不断地创造与“奇遇”,这是一个自我发现与自我生产的过程,而且是所有生产中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一种形式,因为一切的生产最终都应该服务于人的生活与自身的完整,这是人的最本真的生活。
“诗创实践”这一范畴的提出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是直接相关的,“诗创实践”是与被异化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理想的存在方式,“诗学革命”就是走出异化的日常生活的主要途径。在列斐伏尔看来,单调而重复的日常生活同时又是丰富而鲜活的,是一切意义、创造性、差异性、艺术性等等的来源。日常生活是一种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平台,是一种未分化的人类实践总体。日常生活具有“平庸与神奇”的二重性,富有“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9〕。不过,在工业社会,日常生活本身的自然节奏被打断与改变了,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重复是按照技术的规则与生产的节奏进行的,而不是原始的、自然的节奏。不仅如此,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商品观念已经浸染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被组织到消费社会的总体环节之中,只剩下单调的同质化重复,而原有的差异与“诗意”则消失殆尽了。日常生活本身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质,并成为异化的基础与中心。被异化的不再仅仅是人的活动的产品,而是日常生活本身被技术与消费的“殖民”。“在现代世界里,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有着潜在主体性的丰富‘主体’;它已经成为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客体’。”〔10〕这意味着风格的消失与同质性的生成。在前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具有个性的痕迹,如传统、习俗、工具、建筑、语言、服饰、节日等等,但是随着商品与消费在一切领域中的扩张与入侵,一切都按照商品的形式被重新塑造了,商品以它的形象造就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一个同质化的世界拔地而起。与风格一起消失的还有“诗意”,主体成为一种幻象。
面对如何从被异化了的日常生活的单调重复中脱颖而出,恢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重新让日常生活具有艺术的想象的问题,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2卷中提出了一个“瞬间”的概念,“他将瞬间解释为‘短促而决定性’的感觉(如狂欢、愉快、投降、反感、惊讶、恐惧、暴虐),它们在某些程度上似乎是对日常生活生存中潜伏着的总体性可能性的一种揭露与启示”〔11〕。“瞬间”意味着一种断裂与新生,在这里蕴含着各种的可能,突破了日常生活的重复,因此列斐伏尔认为,“瞬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拯救”〔12〕。“诗意”与“诗学革命”正是“瞬间”的形而上学的表达,它是一种对连续性的打断,是对异化的日常的逃离,是对麻木而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反叛。但是,“瞬间”并不是脱离日常而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日常生活。理想的日常生活的典型是节日,节日集游戏、集体性、自发性等于一体,它摆脱了日常的刻板与重复,打破了阶层的界限与空间的禁忌,而带有一种狂欢的快感。虽然节日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它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瞬间”,蕴含着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具有前工业社会中狄奥尼修斯式的酒神精神,反理性与反公式化,使人获得一种释放。在节日中,被遮蔽的“诗意”焕发出光彩,人才能超越异化的生活而恢复本真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本真的日常生活本身应该是创造,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才是“诗创实践”的根本。
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于“文化革命”,列斐伏尔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从阶级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去理解革命,而是从生活方式本身出发,力图恢复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性,去改变生活的方式与风格,这是对于异化了的生活方式本身的抵抗,而不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应该说,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变革,是对当代消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全面抵抗。这一革命的内在动力不是阶级利益,而是人性中的“诗意”,这种“诗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瞬间”、节日等等偶然出现的特殊时刻,这些恰恰是同质性日常生活中的突破口。诗学革命的目标是走向日常生活本身,而不是具有小资情调的文学活动。列斐伏尔的这一思想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具有一定的共性,实际上,在这里蕴含着一种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唤醒和人性中的精神属性的坚定的信任。作为具有超验的神性特质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彻底被物化的生活所淹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改变现实的力量从何而来的问题时,除了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的分析,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处都蕴含着对于人性之中的善与形而上学本性的深深期待与信仰。“诗意”和“诗学革命”能够得以产生与爆发的根源并不完全来源于外部的世界,同时来自人本身。这也不仅仅指人性之中对于至善与完整性的追求。另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的理论家们那里,更多地把反抗的起点寄予“身体”,在他们看来,与自然节奏相协调、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人的身体是不能被完全规训的,身体还保留着人类本真属性的特征,因而成为反抗同质性空间与异化生活方式的真正起点。
归根结底,一切的批判与革命最终都是为了人,恢复人的日常生活本真状态,使技术服务于生活而不是生活被技术所“座驾”。空间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所,把空间还给生活,而不是用于资本的增殖。换言之,以本真的日常生活为中心重建差异化的空间,才是改变的必要条件。“如果未曾生产一个适合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13〕以“诗意”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诗创化实践”的最终落脚点是“差异性空间”的建构。“差异”(difference)是对于现代性思想中所倡导的同质性与单一化的反抗与解构,代表着多元、个性、“诗意”与审美。差异化空间建构的动力来自人的诗创化实践而引起的需要,以使用价值与文化表征相结合而进行的空间实践才能构建“诗意”的差异化空间。肯定差异就是肯定个性与艺术,只有差异化空间“才能消除抽象空间同质化的危害,重构被抽象空间击碎的空间有机体,终结抽象空间将个体与社会肌体有机整体性割裂的局限”〔14〕。差异化空间是理想的空间形态,它与抽象空间有着本质区别。同样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抽象空间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空间,是以牺牲日常生活为前提的压迫性空间,它以资本逻辑为原则,以维护统治为目标,把空间抽象化为权力的工具。抽象空间是一个支配性、控制性与权威性的空间,同质化成为具有普世性的统一标准,个体被视为工具,生命的意义沦落为对物质的追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形象地把这样的景象称为“单向度的社会”与“单向度的人”。因此,差异化空间建构不仅具有文化上的内涵,也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途径。
应该指出的是,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空间批判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天真地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诗学革命与“诗意”的瞬间上,对此他们并没有像福柯那样认为现代人已经无可反抗。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诗意”在人的存在中所具有的革命可能,另一方面,他们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分析了空间生产自身中所蕴含的反抗力量,这是更直接、现实的物质力量。在空间压迫最严重的地方,恰恰也蕴含着最强烈的反抗力量,因为未来的革命应该是空间革命,是对于空间控制权也就是哈维所说的城市权利的争夺。但是,不论现实的状况如何,对于人之存在中诗意本性的期待以及以这种本性为根基的“诗创实践”的阐释,不仅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于“诗意”的认识,而且对于深陷物化中的现代人来说,也是一条可能的拯救途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诗意”“诗创化实践”“诗学革命”,不再只是文学范围内的风花雪月,而是具有了现实的物质力量与政治色彩,直接指向人之存在的根本——变革日常生活本身与建构差异化的空间,实现社会的变革。同时,诗创化实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以往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范围,代表了不同于以资本为核心的新的文明类型,直接指向塑造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生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我们的时代病症的诊断是敏锐而深入的,“诗创化实践”与“诗意革命”的提出,直接为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和资本逻辑下的空间生产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思想依旧停留在理论之中,而没有成为现实的力量。比较而言,我国的社会实践却是先于理论而践行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国际的现实情况,中国政府不断调整发展观,从“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到“可持续性发展观”到全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观念不断调整,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其中,在对于空间改造的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绿色、生态、共享、生命共同体成为当代中国空间实践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以往空间资本化的程度,而且使城市与“诗意”的共存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