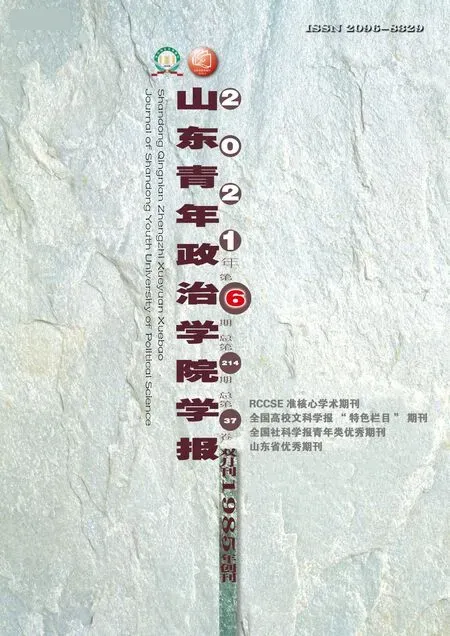朱自清日记释勘
韩佳童
(山东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100)
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据其幼子朱乔森的说法,朱自清的日记本有二十册,分别是1924年7月28日至1925年3月底的一册和1931年8月22日至1948年8月2日的十九册。不幸的是,后十九册中,“1940年2月23日至1941年1月31日的一册,和1941年6月14日至11月8日的一册遗失了”[1]。留存下来的朱自清日记,少部分用中文写作,大部分用英文、日文写作,还有极少一部分用当时的国语拼音符号书写。如何妥善翻译这些外文、拼音符号,是整理朱自清日记首先面临的问题。为此,在编辑《朱自清全集》的过程中,朱乔森聘请了李钢钟、王国华二人分别翻译其中的英文、日文,并请杨张基校正。而对那些极少的用拼音符号写就的部分,则考虑其中“大量人名与另外一些名称”,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译得准,“暂时删去”[2]。实际上,朱自清生前就曾对夫人陈竹隐说过,“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3]。为了尊重他的遗言,朱自清逝世后,陈竹隐也只是妥善保存着它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朱自清日记仅偶有零星片段公诸于世。正是因为不准备发表,日记“更直率地记录了他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更多地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4],具有独特的“真”的意义。再加上日记主人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且长期执教国立清华大学,交游多是当时文教名流;日记所记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涉及抗战、清华大学西迁、组建西南联大等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其具有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笔者在查阅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朱自清全集》九、十两卷所收朱自清日记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别扭之处”,常常使人不知所云。这些“别扭之处”,有的是由于作家本人误记,有的是由于整理过程中字迹错识,更多的则是因为转译造成的舛差。好在全集问世时,编者便以谦虚的态度承认其中难免存在差错并热情希冀读者帮助指出,全集问世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正误的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2004年,周栩发表文章《朱自清日记整理错误举正》,指出朱自清日记对徐中舒、钱钟书的混译。2015年,王晓东发表《从文人到学者:学术视野下的<朱自清全集>重修刍议与校补》,指出朱自清日记中的十处疏漏,并建议将删去的拼音字母日记补全。此后,袁洪权又在《朱自清1934年、1935年日记误记举证二则》中指出朱自清对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举办时间及初晤赵家璧时间的误记,徐强则发表了《<朱自清全集>日记卷中的若干篇名人名辨正》《<朱自清全集>日记卷翻译疏误考校》《朱自清日记之王瑶译本与全集本比勘举例》三篇文章,勘订日记中错误多达几十处。
尽管如此,笔者发现日记中仍存在大量问题未被辨识改正。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研究者查阅使用,同时也使这件珍贵史料的可信度打了些折扣。鉴于此,特整理平时积累考订的问题如下。整理主要集中在1931至1938年间的日记,并以日记记载时间为线,对于相仿之问题则尽量集中说明。需要提出的是,199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曾出版姜建、吴为公编纂的《朱自清年谱》,2010年,《年谱》经姜建修订后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年谱》虽非专门考订朱自清日记错误的著作,但却在事实上对日记形成一种修正。如,1935年1月20日日记记载,“下午赴朱M.S.家,参加读诗与文学讨论会”(本条日记引自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339页,后文凡涉及朱自清日记原文,均引自该版《朱自清全集》第九、十两卷的日记编,不再一一注释,而只在文中标明日记的具体日期)。《年谱》在涉及这一天时,称谱主“下午,赴朱光潜宅,参加朱光潜所组织的读诗与文学讨论会”[5]。对这类年谱中已经存在“正确答案”的问题,本文不再涉及。
一、1931年日记
勘释一:R先生
1931年11月4日,朱自清记:
罗斯小姐告诉我明天是R夫人的生日,问我是否同意给R夫人买些礼物,我同意。
……
十点半钟回来时遇见了萨科威茨(sakowitz)先生。我问他明天应怎样向R先生表示祝贺,他让我在生日卡上签名,还告诉我R夫人对我的中文署名比英文签名更喜欢,我按她喜欢的去签。
次日又记:
王先生和罗斯小姐轮流去请R夫人。他们回来说“R夫人要在浴室里过生日”,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日记记载明确,11月5日是R夫人的生日。既然是R夫人的生日,就应当向R夫人祝贺,而不是“向R先生表示祝贺”。第一则日记中,当“我”询问萨科威茨(sakowitz)先生应当如何祝贺时,他建议“我”在生日卡上签中文名字,原因是R夫人对“我”的中文署名比英文署名更感兴趣。如果是向R先生表示祝贺,为何要格外考虑R夫人对哪种署名方式更喜欢?显然,第一则日记中的R先生应当是R夫人。
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休假一年,赴欧访学。R夫人即罗宾森夫人,是朱自清在英国的第一个房东。朱自清从1931年9月21日起搬入罗宾森夫人寓所租住,直至1932年1月4日搬出。
勘释二:看到女皇
1931年11月10日,朱自清记:“在白厅看到庄严的议会开幕典礼。由于站在卫队和警察后面,只能远远地隔窗看到女皇。仪式比较简朴。”
当时的英国国家元首为温莎王朝的创建者乔治五世,乔治五世为男性君主,日记中的女皇记载明显有误,但不知是朱自清本人误记还是翻译误翻。
二、1933年日记
勘释三:尤金·奥尼尔
1933年1月14日,朱自清“为夏君阅译稿,系尤金·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Eugene O’Neil:The Strange),不恶”。
尤金·奥尼尔英文名有误,应为Eugene O’Neill。其为美国著名剧作家,曾获193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日记中提到的他的剧作《奇异的插曲》英文名也不准确,应为《Strange Interlude》,该剧较著名的译本是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11月出版的王实味译本。
勘释四:《高尔斯华绥之罪》
1933年4月24日记:“晚看孙毓棠、万家宝两君排《高尔斯华绥之罪》,颇佳。”
应为高尔斯华绥之《罪》。
据《曹禺年谱长编》,1933年春天,曹禺翻译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又名《最先与最后》《罪》)。[6]紧接着,曹禺排演此剧,自任导演并饰演弟弟拉里,孙毓棠饰演哥哥吉斯,郑秀饰演女主角汪达。此剧在清华大学“演了七八场,反映很好,不但清华人来看,燕京的人也来看”[7]。1933年4月29日的《清华副刊》就曾报道,“清华剧社于本月二十五日晚八时,假九一八纪念堂,公演《隧道》,《骨皮》,《罪》三剧,是晚观众,颇形拥挤,售得票资,共八十余元,除开支外,余欵尽数捐与本校抗日会云”[8]。
勘释五:《评<杂拌儿>之二》
1933年5月16日记:“《晨报》上有李长之《评<杂拌儿>之二》一文,颇扼要。”
俞平伯著有《杂拌儿》和《杂拌儿之二》。李长之发表在《晨报》上的文章是评后者《杂拌儿之二》的,而不是第二次评《杂拌儿》。
据于天池、李书编《李长之先生学术年表》,1933年5月5日“写《杂拌儿之二》(书评),《北平晨报·北晨学园》506号”[9]。且在书评中,李长之引了俞平伯的一句话:“在爬山,一条路在崖上走,一条路在山坳里走,我自然取其后者。(页一七三,一七四)”[10]这句话,恰好是《杂拌儿之二》所收文章《阳台山大觉寺》里的。就连括号内标注的页码,都与开明书店1933年2月初版的《杂拌儿之二》相吻合。
勘释六:两场论文考试
1933年6月4日记载,“读萧涤非论文”。6月12日记:“下午考萧涤非,余问汉武立乐府事,为所驳,甚惭,萧得超等。”
据清华大学档案,萧涤非论文考试时间是“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也即1933年6月13日,而非朱自清所记1933年6月12日。考试委员有黄晦闻、朱佩弦、陈寅恪、杨遇夫、刘叔雅、俞平伯、闻一多、吴雨僧、钱稻孙,论文题目是“乐府之变迁史”,评定成绩时得超等,1.20分。[11]
早在1933年3月2日,朱自清就曾记,“张教务长上午来,商量萧涤非毕业考试事”。有必要指出,这里的毕业考试与论文考试并非一事。萧涤非的毕业考试已于“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举行,担任萧涤非毕业考试委员的是朱佩弦、陈寅恪、杨遇夫、刘叔雅、俞平伯、闻一多、吴雨僧、叶石荪、叶公超、黄晦闻。考试学科有:“一、中古史(音乐、政治、民俗、文化);二、中古文学史;三、《诗经》、《楚辞》;四、文字学;五、目录学。”这次考试,萧得中等,成绩是1.0。[12]
到了1935年2月19日,朱自清的日记中又出现与另一位学生的论文考试有关的内容:“唐Y.T.先生不任霍士休的考试委员会委员。我们决定请胡适博士代替他。”十天以后,1935年2月28日记:“对霍士休进行考试的口试委员会今天下午开会。进展颇顺利。冯友兰先生指出唐代以后大量传奇故事的渊源。唐代的传奇故事是霍的研究题目,而这正是他论文中的大弱点,但我们却没有发现。”
这两处霍士休均为霍世休,为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此前王晓东已经在文章中指出。唐Y.T.则为汤用彤,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霍世休的论文涉及传奇中的佛教故事,而汤用彤正是此领域的专家。
勘释七:铛吟杂录
1933年6月9日记,“决定暑中拟作之事。……16.铛吟杂录”。
应为《钝吟杂录》。《钝吟杂录》,清冯班著。冯班,字定远,号钝吟,江苏常熟人。其著《钝吟杂录》十卷,《正俗》《读古浅说》《严氏纠谬》,多论诗之语;《家戒》《日记》《诫子贴》《遗言》《通鉴纲目纠谬》《将死之鸣》则涉及书法、小学等领域。此外,还有一版由丁福保辑入《清诗话》的《钝吟杂录》,与原著书题相同,但仅四题六则,专辑原著论乐府之语。
勘释八:蔡荃
1933年9月11日,朱自清记:“文副有蔡荃《蝶恋花》二首,其一极佳。”
朱自清日记中多次提到文副,但含义不同,有时是指沈从文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有时是指吴宓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这里是后者。1933年9月11日的天津《大公报》第297期文学副刊确实刊登了两首《蝶恋花》,但作者署名荪荃,而非蔡荃。
勘释九:孙晓梦
1933年9月15日,朱自清“饭后与孙晓梦及公超谈性事”。
除了孙晓梦,在朱自清的日记中,还多次出现小孟、孙小孟。如1933年10月9日,朱自清“下午入城,为孙小孟婚礼,客到不多,礼亦简,较公超结婚日相去悬远矣”。1936年3月8日,“晚间小孟来访。谈及石荪事”。
其实,无论孙晓梦还是孙小孟,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孙国华。小孟也是指他,而不是某位年轻的孟姓人士。据《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词典》,孙国华“字晓孟。山东潍县人。1914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同年留学美国,入俄亥俄州立大学。1925年入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系,次年获硕士学位。1928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底回国,任国立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1930年兼系主任”[13]。有时,孙国华的字也作筱孟,如梁实秋就曾在《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清华八年》两文中分别以孙小孟、孙筱孟来称呼他这位“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14]的老同学。
勘释十:黄耑木
1933年10月31日记:“至中山公园观溥心畲画,仿宋山水确佳。又有黄耑木《寻亲图》,绘西南栈道,颇苍老奇险,皴法用小横线甚佳。”
黄耑木应为黄端木,即黄向坚,字端木。据《苏州通史》,黄向坚乃吴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其父黄孔昭,曾任云南大姚知县。其父赴任时,黄向坚为诸生,“以应试未随父宦游。擅画山水,早有文誉,思亲备至。顺治八年,局势稍定,即自苏州徒步赴云南大姚寻亲,辗转万余里,几历生死,艰难备尝。十年,侍奉双亲归,居苏州阊门外,事迹感人至深。黄向坚手绘《寻亲图》纪实,并著《寻亲纪程》《滇还纪程》等。戏曲家李玉为作《万里圆》传奇,刊刻《旌孝编》,归庄为撰《黄孝子传》。”[15]康熙十二年,黄向坚去世。
勘释十一:《凤吉公主》
1933年12月31日晚,朱自清“观戏曲学校戏,觉武打尚佳,《取金陵》、《风吉公主》尤胜,然是技非戏。《琼林宴》、《宇宙锋》唱工尚佳,但演者年太稚,情味不出耳。”
日记中所谓《取金陵》与《凤吉公主》,实为同一出戏之不同称谓。《取金陵》,一名《凤吉公主》,前辈艺人阎岚秋之代表作。故事梗概是元末明初,朱元璋率红巾军反元,兵围金陵。元驸马赤福寿与元将曹良臣守城,两军交战,徐达诱使曹良臣入重围,迫其投降。赤福寿阵前遇旧交伍福,伍福劝其投降,言辞恳切。赤福寿两难之下,自刎而死。赤福寿妻凤吉公主得知,点动人马,为夫报仇,阵前厮杀力尽,自杀殉节。朱元璋得金陵剧终。
凤吉公主是剧中主角之一,由武旦演员扮演。在十四、十五两场中,有大段凤吉公主迎战朱元璋手下将领的武戏,是这出戏的一大看点。当时,某一出戏因受观众欢迎,连演若干天是常事,但同一出戏在同一晚的同一场重复演出,几无可能。再结合语境,朱自清关于1933年最后一天观戏的记载原貌应是这样的:观戏曲学校戏,觉武打尚佳,《取金陵》风吉公主尤胜,然是技非戏。《琼林宴》《宇宙锋》唱工尚佳,但演者年太稚,情味不出耳。
朱自清对这晚戏校演出的武戏部分较为满意,并认为《取金陵》里凤吉公主的武戏表演尤其值得称赞。也就是说,“尤胜”的评语针对的是凤吉公主这一角色和这一角色的扮演者,是一个人,而不是所谓《取金陵》或《凤吉公主》这出戏。一般来说,戏校演出多为坐科学生登台,所以朱自清才会认为《琼林宴》《宇宙锋》两出戏“演者年太稚,情味不出”。凤吉公主的表演“是技非戏”,过于炫技,恐怕也与演员年纪尚小,对戏的领会不足有关。
三、1934年日记
勘释十二:妇女与文艺
1934年1月13日,朱自清“晚应冰心女士伉俪之招,冰心女士嘱为妇女与文艺作文,共作桥戏”。
这里的妇女与文艺并不是某个刊物的名字,而是指《女青年月刊》第13卷第3期“妇女与文艺专号(特大号)”。该专号1934年3月出版,特请冰心任编辑顾问。应冰心之约,朱自清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择偶记》一文,主要记述自己几次说亲经历及与发妻武钟谦结亲之经过,署名佩弦。
有关这期专号的组稿细节,刊尾的《编后记》有着详细记述,“这期的妇女与文艺专号,是以特大的姿态而出现。……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顾问谢冰心女士,她很负责任的四处征稿,从老远的北平把稿子一批批的寄来”[16]。值得注意的是,这期妇女与文艺专号上还发表了郑振铎的研究文章《元明以来女曲家考略》。无怪1934年4月1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载,“铎交来《女青年月刊》,用楷体印,并惠稿费三元”。
勘释十三:余姗
1934年2月2日日记记载:“下午至欧美同学会看唐画……今日来名人甚多,余姗亦在,其笑如吴三妹也。”
日记中所说看唐画,是指唐亮的画展。两天之前,朱自清就曾在日记中记载“闻一多等发起为唐亮请参观画展,列名者十人,除公超、林徽音外皆清华人也”。
唐亮,字仲明,清华大学毕业生。先留美,后又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1933年回国。1934年,闻一多等人为其发起画展。画展以欧美同学会和清华同学会名义主办,会场设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的读书室里,自2月3日至10日连展八天。为配合展览,还编印了题为《唐亮西洋画展览》的小册子,里面收录了参展画作名目及闻一多评论唐亮作品的文章《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值得注意的是,画展自3日开始,而日记却记载2日看展。这是因为顾一樵、余上沅、叶公超、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闻一多、李唐晏等十位发起人预先于2日下午招待新闻界人士,这天被“被约到会参观的约有一百十人、大部分都是北平各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和新闻记者”[17]。
日记中所记余姗姓名不确,查当时名人,并无余姗其人。余姗应为俞珊,著名戏剧演员,曾在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所排《莎乐美》一剧中饰女主角,大放异彩。与闻一多、徐志摩、沈从文、田汉等均有绯闻传出,曾嫁与赵太侔,后离婚。蒋光慈的妻子吴似鸿称其“会弹钢琴,会唱京戏,又会讲英语,性格开朗,身材丰满,脸相美丽”[18]。关于余姗是俞珊,在天津《大公报》的报道中也得到证实,“二日的招待会中、有一个华北(不是全国)鼎鼎大名的名人、在此不能不提提、那就是色艺俱全艺术界之后的俞珊女士”[19]。
勘释十四:戏曲音乐展览会
1934年2月18日,朱自清“至北平图书馆,看戏曲音乐展览会,以嘉道间徐白斋画《纱灯》(鲍仲严藏,有秦宽说明)最佳”。
日记中的戏曲音乐展览会,当时报刊多有关注,如1934年2月19日天津《益世报》报道“筹备三月始告就绪之大规模戏曲音乐展览会、已于今晨九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幕、门票每人售洋二角、先期预售者、闻已有千人左右、今晨随时售票入门者且不计焉”[20]。
日记中提到的“徐白斋画《纱灯》”中的“纱灯”不应加书名号。徐白斋,乾隆四十二年生,咸丰二年卒,著名民间画师,擅画纱灯画。展览会上展出的这组徐白斋纱灯画,在当时便引起不少注意,如《时报》报道称,“其次便是所谓昆弋画灯、亦算名贵已极了。即所谓四朝名士(生于乾隆没于咸丰)之徐白斋所绘、而鲍仲严所藏、称为海内绝品者也”[21]。又如天津《大公报》报道,“此外并陈列鲍仲严所藏清嘉道间徐白斋所画纱灯、皆为戏目……甚为精美”[22]。
至于日记中提到的“秦宽说明”,其实不确,秦宽应为奉宽。《时报》便载,“另有一位奉宽先生(当是旗人)者、代为说明、铺张得神奇名贵无比”[23]。奉宽何人?他为何会为鲍仲严的藏品代作说明,铺陈造势?二者是何关系?其实,奉宽就是鲍仲严本人。据著名美术史家王树村著《中国民间美术史》,“最先收集徐白斋灯画的是蒙族人奉宽(字仲严,号远鹤,蒙古人,后改名鲍仲严。通满、蒙文字。抗日战争前任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24]。奉宽对灯画很感兴趣,1919年,经人介绍,奉宽买来徐白斋昆弋灯画104幅。他视为至宝,将画从灯上取下,装裱收藏,也就是这次展览会上亮相的纱灯画。可惜后来日军侵华,奉宽所藏徐白斋灯画半为日本人桥川时雄掳去。
勘释十五:《杨胖赐福》
1934年6月10日记:“晚谷音社首次曲集,俞太太《思凡》为最佳。《杨胖赐福》道白乃如皮黄。”
谷音社是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俞平伯发起,集合校内一众昆曲爱好者的曲社。其主要成员除俞平伯外,还有其夫人许宝驯,以及浦江清、唐兰、陈竹隐、陶光、华粹深等人。日记中所载首次曲集,俞平伯在回忆中也曾提及:“至次年甲戌新正(廿三年)陈遂二次北来,住清校附近,浦唐汪陈及杨文辉兄均从之游。于春夏之交,发议结社,于某日夏晚在工字厅首次公开曲集。”[25]
日记中提及俞太太演唱《思凡》,俞太太是指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思凡》则是昆曲中著名的折子戏,讲述小尼姑色空突破清规戒律,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而紧接着提到的《杨胖赐福》,昆曲中却无此剧名。不过昆曲中有一出著名的《天官赐福》,是演出时经常上演的吉祥开场戏,而且这出戏常被简称为《赐福》。姜德明在《俞平伯与谷音社》一文中提到他曾在琉璃厂书肆购得五册合而为一集的线装书一套,分别是《谷音社首次曲集》《谷音社二次曲集》直至《谷音社五次曲集》。据姜文转述,这套书记载首次曲集时演出的剧目有“《琵琶记》、《长生殿》诸剧中之一折,还有《思凡下山》,以及开场的《天官赐福》等”。[26]据此,《杨胖赐福》其实是杨胖《赐福》,即杨胖演唱的《天官赐福》。而杨胖,其实就是当时参加曲集的某位身材较胖的杨姓昆曲同好。
勘释十六:松堂游赏见闻
1934年,朱自清曾两赴北京西山松堂等地游玩,并著散文《松堂游记》记述游玩见闻。这两次松堂之旅也均在日记中留下了记载,其中1934年6月30日记:
此屋系大理石亭,改为居室,甚高敞明亮,中一碑,记乾隆庚午皇帝赐衾事。有一诗,序言:“驾临健锐云梯营,此营乃去岁征金川成功之旅,又有降虏及临阵俘虏数人习工筑于此,亦得赐食。”诗云:“犹忆前冬月,云梯始习诸。功成事师古,戈止众宁居,实胜昭提侧,华筵快霁初。馂余何必惜,可以逮豚鱼。”此乾隆御笔。室中额云:“策勋缵武”……
晚背诵诗词,余得熟诵静安先生《蝶恋花》及吴兆骞《颀贞观词》,又武穆《满江红》词。
乾隆御诗序言不确。应为:朕于实胜寺傍造室廛,以居云梯军士,命之曰健锐云梯营。室成居定,兹临香山之便因赐以食。是营皆去岁金川成功之旅。适金川降虏及临阵俘番习工筑者数人,令附居营侧。是日并列众末,俾预惠焉。
御诗正文个别字有误。“实胜昭提侧,华筵快霁初”中的“昭”应为“招”。招提,民间私造之寺院也。
乾隆所题匾额“策勋缵武”应为“策勋绩武”。
此外,关于晚诵之诗词,“吴兆骞《颀贞观词》”应为“吴兆骞、顾贞观词”。吴氏、顾氏均为清代词家,且友谊甚笃。顺治十五年,吴兆骞因卷入科场舞弊案被发配宁古塔,顾贞观四处奔走,竭力营救,并留下两首著名的《金缕曲》。
勘释十七:《感觉与诗》
1934年7月4日,朱自清“早办公,下午读约翰·斯皮罗《感觉与诗》(John Sparrow: Sense and Poetry)”。此后,本月8日、9日朱自清一直在读这本书,9日读毕“作提要”,认为“此书虽简单而极清晰也”。
日记所记书名中的“感觉”一词是对“sense”的直译,这本书应译为《意义与诗》。《自由评论》1936年3月27日第17期就曾发表过叶维之的同名书评《意义与诗》。叶维之在文中提到有关这本书的信息,Sense and Petry.Essays on the Place of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Verse.By John Sparrow.London.Constable and Co.1934。[27]从书评来看,这本书主要讨论的也是现代诗中的意义问题,而非感觉。“现代派诗的难懂,大概是人人晓得的罢。斯帕娄先生这部书,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所谓‘意义’在现代诗中的位置如何呢?现代诗与从前的诗有何不同之处呢?斯帕娄先生就在他这部书中,设法解答这种问题。”[28]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书评后面还缀有梁实秋的附识,提到这篇文章刊用的幕后故事,且梁氏借题发挥,提到自己对于诗歌意义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诗之所以有时候近乎“无意义”,实在是因为写作者的思路不清楚的原故。思路清楚,则用任何手法去表现,都可以令人明白。“香稻啄馀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实在不成为一句话,但不能以其辞句颠倒逐斥其为“无意义”,因为细加思索之后,就可以明白这两句话除了表现两个印象之外还是有其字面上的意义的。言倒而理顺,则仍可以令人领悟;惟根本没有清楚的思路,而又强要用一些漂亮的字眼堆砌饾饤,其结果必至不可通。[29]
勘释十八:森茨伯里
1934年7月15日记:“检书似失去森茨伯里《批评初史》(Saintsbrory: A Short History of Criticism)。”
森茨伯里的英文名应为Saintsbury,即George Saintsbury,英国著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梁遇春、朱湘、朱光潜等均曾提及此人,郁达夫还曾在发表于《青年界》1933年第3卷第4期的《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一文中专门推介他的著作《History of Criticism》。
不过梁实秋对此有不同看法,梁氏认为,“圣次保来教授的批评史,意见很偏(偏向于浪漫派),文章极劣(简直不堪入目,他著作极富,关于Prosody一类的亦不少,但其文笔晦涩之极)”[30]。
勘释十九:社会教育院会议
1934年8月26日记:“社会教育院在开封召开会议,庄志祥先生宣读论文《中国谚语的含义》,此文一定会使我感兴趣。”
这则日记中提到的社会教育院,实际是指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1931年12月成立,是一个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31]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主要成员有俞庆棠、梁漱溟、李蒸、雷沛鸿等人。抗战爆发前,该社分别于杭州、济南、开封、广州召开了四次年会。日记所记“社会教育院在开封召开会议”,指的就是在开封召开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第三届年会议程自8月17日至19日,共计三天,会场位于“开封省政府街路北省立初级中学”[32],出席社员147人,中心议题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33]。
在中国社会教育社1935年编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中,并没有庄志祥的名字,在《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中,也没有《中国谚语的含义》这篇论文。但在《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所列“论文与报告”下的“宣读论文”一栏中,有一篇题为《从谚语格言中观察中国民族性》的论文纲要,作者庄泽宣。日记所记“庄志祥先生宣读论文《中国谚语的含义》”其实指的就是庄泽宣的这篇论文。
庄泽宣,浙江嘉兴人,著名教育学家。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同年出洋,先后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先后于国立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任教,从事民众教育研究,著有《教育概论》、《各国教育比较论》等。庄泽宣与中国社会教育社渊源颇深。早在1932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上,庄泽宣便被补选为理事,同时,他又是这次在开封召开的第三届年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理事每届任期三年,至第三届年会召开时,庄泽宣正好任期已满。“本社照章通知各社员改选,于第二次大会时当众开票。结果、钮、孟、雷、庄、甘等五人皆获继任。庄先生虽再三谦辞,而以众望所归一致挽留。”[34]至于庄泽宣在会上宣读之论文,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对搜集到的三千多条谚语和近两千条格言进行分析,将其划分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正心修身、爱重生命、迷信、自私自利等类别,并借此来认识“一般的民众精神生活或中国民族性”[35]。该论文纲要还曾刊载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刊行的《社友通讯》1934年8月15日第3卷第2期“本社第三届年会特大号”上。
勘释二十:叶林
1934年9月4日记:
浦江清来访,见到他很高兴。他谈了很多自己的恋爱故事,使人感到有点乏味。叶林亦来访,对浦的唠叨几乎厌烦得耐不住了。叶给我看他写的一篇论文《从心理学观点看小说写作》。
1935年8月16日又记:“在叶林家晚餐。”
这两处叶林,说的都是朱自清的同事叶麐。
叶麐,原名祥麐,四川古宋人。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赴法国里昂大学进修,1929年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在国立清华大学任教,与同为北大校友的朱自清成为同事。事实上,朱自清与叶麐交往频繁,在朱自清的日记中,叶麐的身影出现频率极高。只不过,朱自清记载时多使用叶麐的字——石荪。仅1934年6月下旬,石荪就曾三次出现在朱自清日记中。1934年6月20日:“晚入城参与石荪婚礼,济济一堂有二百馀人,晚归。”6月25日:“访石荪,并送《蕙风词话》,约去松堂住三日。”28日:“下午不能做事,至平伯处打桥,二局未终,因须至石荪处便饭即归。”
叶麐拿给朱自清看的论文,发表在1934年9月15日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02期上,题为《由心理学的观点试论小说中景物底写法》,署名叶麐。
勘释二十一:于秉奇的婚礼
1934年9月10日,朱自清记:“昨日下午参加岳的婚礼。”
而前一天的朱自清日记是这样的:
下午进城。
参加于秉奇的婚礼。
往观苏州社画展,其中有很多画是出于张氏兄弟手笔。张善孖,张爰(大千)。
朱自清在同一天下午不可能既参观画展又出席两场婚礼,显然“岳的婚礼”和“于秉奇的婚礼”是同一场婚礼,应当统一。
勘释二十二:《现代中国哲学》
1934年10月9日:“冯友兰给我看他在国际哲学会议上的演讲稿,题目是《现代中国哲学》。”
日记中所记国际哲学会议是指1934年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冯友兰演讲的准确题目为《哲学在当代中国》。据冯友兰自述,“我离开苏联,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哲学会议第八次会议。我在国内的时候,先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哲学在当代中国》),在这个会上念了一遍”[36]。这篇英文文章经涂又光翻译后,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松堂全集》。
勘释二十三:N.P.L.书画展览
1934年11月4日,朱自清进城观展:
参观N.P.L.书画展览,大部分是照片。我只对下述展品感兴趣:
1. 中世纪手稿的复制品。
2. 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壁画复制品。
3. 具有现代派建筑风格的瑞士国家图书馆照片。
从这个所谓的“书画展览”展品多为手稿、图书馆艺术品复制件及图书馆照片,再结合这一时间点前后当时报刊所载北平展览信息,可以断定,日记中的“N.P.L.书画展览”,其实是世界图书馆展览会。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由中国国际图书馆“日内瓦总馆胡天石馆长发启,向欧美各国征集展览物品”,旨在以图书馆为“推行文化之枢纽”,“达世界文化之合作”,并“鼓励中国图书馆事业之进展”。[37]中国国际图书馆,始筹备于1932年。1933年,中国国际图书馆欧洲分部在日内瓦成立,这是中国国际图书馆的主要部分,馆址位于“瑞士日内瓦莫达雷特宫,馆长为胡天石”,目的是“传播弘扬中国文化”。[38]“中国国际图书馆在此之后又在世界各地设立分部,中国之部设在上海,正式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39]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发起以后,原定1934年5月在上海举办,但“各处寄品,到达迟早不一”,因此延至双十节方才开幕。据《民报》1934年10月12日报道,“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所举办之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于双十节下午三时在法界福开森路三九三号该馆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40]。展览会反响热烈,不光在上海受到关注,甚至引起华北各方请求,因此主办方决定在上海展览结束后将展品北运,“由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在北平图书馆展览一周”[41]。关于北平展览情形,《民报》也有报道,“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一日在北平图书馆开幕以来、连日观众踊跃、统计不下二万馀人、定七日闭幕、八日装箱南下、并拟将展览情形、编印专刊、以资纪念”[42]。报道所说专刊笔者并未找到,但笔者找到了主办方在上海展览开幕时编印的《世界图书馆展览会目录》,北京展览会上的参会单位及展品与上海展览会当保持一致。
据《目录》,共有国立柏林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十六个国家的六十六个单位参会,展品主要包括图书馆照片和馆藏出版品。其中奥国(AUTRICHE)参展单位有两家,分别是国立维也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Vienne)和印司不鲁克大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I’Université d’Insbruck)。瑞士(SUISSE)参展单位有四家,分别是国立柏尔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Berne)、日内瓦公共图书馆(Bibliothèque Publique de Genève)、巴塞大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I’Université de Ble)和徐利赫中央图书馆(Bibliothèque Centrale de Zurich)。
勘释二十四:《大一中文》
1934年11月27日:“《大一中文》副刊上有篇文章,投稿者自称是我系学生。他的论点并不太严肃,但指出余先生授课中讲‘松柏后凋’之类的题材甚为多馀。”
并不是“《大一中文》副刊上有篇文章”,而是副刊上有篇《大一中文》文章。准确说,是1934年第42卷第6期《清华副刊》上有篇《大一国文》的文章。余先生也不是余先生,而是俞先生,即俞平伯。文章中批评俞平伯“讲‘松柏后凋’之类的题材甚为多馀”的部分如下:
为了培养学生发表思想的能力,于是乎有作文。作文,我不反对,但限题作文,我就不敢赞同……
我们做作文是必须白话文言轮流着做,例如上一会俞平伯先生的文言题是“松柏后凋”,我敢推测,十人中至少有八个人是拿松柏来譬喻君子的。在教师方面,批改这千篇一律,缠了小脚,言不由衷的“今夫天下”“人生于世”的卷子,谅来颇觉气闷;在同学方面呢,作文似乎是义务,原非得已的事情,潦草塞责,只求不过期交卷。
因为时世使然,呌我们这辈人用文言文流畅地发挥自己的意见是困难的事,而况再必得在一个老套题目里打圈子!不信,你可请出题的俞先生亲自来一篇文言的《松柏后凋》,看他一定做得出好文章不?[43]
又,1936年4月13日记:“《清华周报》副刊上有一篇文章《致老师们和高年级同学》,文字很挖苦。”
这篇文章同样发表在《清华副刊》上,具体是1936年4月12日第44卷第1期《清华副刊》上的《写给我们的师长和前辈》一文,署名落生。
四、1935年日记
勘释二十五:《她屈从于妥协》
开头已经提到,朱自清1935年1月20日日记记载,“下午赴朱M.S.家,参加读诗与文学讨论会”。接着,朱自清详细记述了这次讨论会的情形,其中提到:
李健吾与马小姐先朗读王芹溪改编的剧本《她屈从于妥协》。这个中国剧本太欧化了。李先生扮演一个迂腐气十足的旧官吏,可是他讲的却是满嘴最时髦的幽默话,真是矛盾得可笑。马小姐表演摩登女郎真是驾轻就熟,因其本人就是个摩登女郎。
发生在朱光潜家的讨论会,是当时京派文人的著名聚会。沈从文就曾回忆:“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书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44]而1935年1月20日,是这个读书会的首次聚会。从朱自清的日记中可以得知,李健吾也参加了此次聚会,并且和一位马姓女士朗读了“王芹溪改编的剧本《她屈从于妥协》”。那么,王芹溪何许人也?《她屈从于妥协》又是什么剧本?
在当时的文化名流或朱自清友好中,并没有查到有谁姓王,名或者字是芹溪的。但在朱自清日记中,却不止一处提到此人。如1937年11月21日日记记载:“访王芹溪夫妇。”《朱自清年谱》中,有关朱自清这一天的活动是“访汪敬熙夫妇”[45]。也就是说,《年谱》认为,1937年11月21日记中的所谓“王芹溪”是对当时著名心理学家汪敬熙的名字进行转译造成的错讹。但笔者没有查到任何有关汪敬熙业余从事话剧创作、改编的资料,1935年1月20日日记中的王芹溪与汪敬熙显然并非同一人。将目光转回《她屈从于妥协》这部剧本,三个月以后,1935年4月19日,朱自清看了一场话剧,当日日记记载:
观《她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演出技巧颇佳,李导演得很成功。但剧本本身范围狭窄,人物不真实。多是纯血统之中国人,而言行乃欧洲风度。
这场话剧名为《她屈身求爱》,后附英文名《She Stoops to Conquer》直译过来却非常接近三个月前读书会上朗诵过的剧本《她屈从于妥协》。“人物不真实。多是纯血统之中国人,而言行乃欧洲风度”的评价与“这个中国剧本太欧化了”简直如出一辙。两剧情形描述如此接近,那么,后一处日记中的李导演,有没有可能就是当时朱光潜家读书会上朗诵剧本的青年戏剧家、导演李健吾?很快,笔者查到李健吾曾翻译、执导一部三幕剧《委曲求全》,该剧原剧本用英文书写,英文名为《She Stoops to Compromise》,作者是李健吾的老师、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王文显。其内容主要讲述一所高等学府内部文化人的勾心斗角,情节与两处日记记述基本吻合。此外,笔者还在1935年2月7日的《北洋画报》上读到一篇有关朱光潜读书会的报道,报道中提到:
其第一次会已于日前举行。是日到会者计有梁任公之子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音,戏剧作家李健吾,小剧院女演员马静蕴,小说家废名,沈从文及其夫人,散文家朱佩弦,青年诗人林庚等。……开会时间为下午三时,最初为李健吾与马静蕴对读剧本《委曲求全》。剧本为清华教授王文显以英文著,由李译成中文。因李等最近将上演此剧,藉此机会作一练习。[46]
至此了然,两处日记中提到的《她屈从于妥协》《她屈身求爱》实际上指的都是剧本《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mpromise),而所谓“王芹溪改编”其实就是“王文显创作”。
勘释二十六:陈广瑶
1935年1月21日:“教育部请李秋实与王毅去南京商讨中文音标与陈广瑶的汉字简化意见。我对此颇感兴趣。”
陈广瑶应为陈光尧。陈光尧,1906年生,陕西城固人,193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曾为北平研究院助理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致力民间文学,编著有《谜语研究》《歇后语选录》等,同时倡导汉字简化。曾在《语丝》1927年7月16日第140期上发表《简字举例》一文,以简化汉字书写《大学》经文。鲁迅1928年3月21日给陈光尧的回信,即与此文有关。
古兑先生:来稿对于陈光尧先生《简字举例》的唯一的响应《关于简字举例所改大学经文中文字的讨论》,本来极想登载,但因为文中许多字体,为铅字所无,现刻又刻不好,所以只得割爱了。抱歉之至。[47]
该信发表在1928年4月2日第4卷第14期《语丝》“本刊小信”栏目,落署“旅沪一记者”。据《鲁迅全集》文后注释,古兑是陈光尧的化名。也就是说,陈在发表《简字举例》之后,又托名古兑,再次撰文,自导自演,自答自文,以宣传主张,引发影响。此后,鲁迅与陈光尧有多次书信往来,内容仍涉简字。1933年10月l7日日记:“得陈光尧片并书四本。” 1936年2月19日:“得陈光尧信并诗,即复。” 1936年2月26日:“得陈光尧信。” 1936年3月20日:“得陈光尧信并《简字谱》稿,午后复。” 1936年8月8日:“上午得陈光尧信。”[48]
复信二封内容如下:
光尧先生:
两蒙惠书,谨悉一切。先生辛勤之业,闻之已久,夙所钦佩。惟于简字一道,未尝留心,故虽惊于浩汗,而莫赞一辞,非不愿,实不能也。敢布下怀,诸希
谅察为幸。
专此奉复,顺请
撰安。
鲁迅上 二月十九日
光尧先生:
蒙惠书并眎大著,浩如河汉,拜服之至。倘有刊行者,则名利兼获,当诚如大札所云。但际此时会,具此卓见之书店,殊不可得,况以仆之寡陋,终年杜门,更不能有绍介之幸也。其实气魄较大,今固无逾于商务印书馆者耳。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顿首 三月二十日[49]
勘释二十七:张星琅
1935年4月6日记:“郝昺衡与张星琅来访。”
郝昺衡,江苏建湖人,1915年入北大,1924年毕业,师从黄节。1926年起,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建国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星琅应为张星烺,江苏泗阳人。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19年任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后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特别纂辑员,1927年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课程,1928年清华大学成立边疆研究会,张星烺就列名发起人之一。
勘释二十八:朱启黔
1935年7月20日:
《大公报》艺术副刊载文论挑耳图、周尺等,外有宋画院论道圆与行滤者。前者系立体云烟风景。二人之描写方法甚中人意。后者为椭圆,底有线状孔,殆沙漠中所用滤器欤?此朱启黔之意见也。
朱启黔应为朱启钤,民国政治人物,工艺美术家。
勘释二十九:《载酒园诗话评》
1935年9月8日记:“读贺黄公《载酒园诗话评》,贺喜宋诗,却在此点上对批评者黄生加以攻击。”
贺黄公即贺裳,字黄公,明末清初人。著有《载酒园诗话》五卷,卷一泛论古今作诗理法,卷二论初盛唐之诗,卷三论中唐诗,卷四论晚唐诗,卷五论宋诗。与贺裳同时代的安徽歙县人黄生,读贺裳写的《载酒园诗话》,于卷端批注点评。不过黄生的批语长期以来未获流传,民国十七年,“诸宗元始出所藏批本《载酒园诗话》,由黄氏后人黄宾虹录出”[50]。民国二十年,神州国光社刊行影印本《黄白山先生载酒园诗话评》。
贺裳和黄生两人论诗有相同之处,二人均推崇唐人。但黄生之恶宋诗又超过贺裳,因此黄生常在评语中批评贺裳诋宋不能尽意,甚至认为评宋诗本来就是多余之举:“宋人诗总不在话下,取而雌黄之,则识趣其已先陋矣。”[51]
这样再回头看这则日记,问题就十分明显了。首先,贺裳从未写过《载酒园诗话评》,贺裳所著为《载酒园诗话》,《载酒园诗话评》是贺裳的读者黄生的评语辑录。其次,“贺喜宋诗,却在此点上对批评者黄生加以攻击”这一句的主语是贺裳,事件是贺裳攻击黄生。而事实是,不是贺裳读了黄生的诗评攻击黄生,而是黄生读了贺裳的诗评攻击贺裳。翻译之后的日记将主宾颠倒了。
据此,这则日记的本来面目大概可还原为:读黄生《载酒园诗话评》,黄恶宋诗,却在此点上对批评者贺裳加以攻击(以其恶宋不足也)。或者:读贺黄公《载酒园诗话》,贺喜宋诗,黄生在此点上对批评者贺裳加以攻击。不过所谓“贺喜宋诗”,也只是相对黄生而言。
勘释三十:《论<左传>的可靠性》
1935年9月28日,朱自清“读卡尔格伦《论<左传>的可靠性》(Kalgren:On the Authenticity of Tso-Chuan)的中译本”。
这则日记中提到的卡尔格伦(Kalgren),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高本汉。关于高本汉,无需多作介绍。朱自清提到的他著作的英文名称并不准确,应该是《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载《哥德堡大学学报》1926年第32期。文章发表以后,由陆侃如翻译为中文。“我(陆侃如——笔者按,下同)一面口译,卫先生一方面便笔录下来。……后来冯沅君先生知道了,要求拿去给北大研究所的《月刊》充篇幅,故我再以卫先生所记的稿子,和原书细校一遍,又请赵先生复校一遍,以期不致自误误人。”[52]该译文刊登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7 年第1 卷第6、7、8 号上,题为《论左传的真伪及其性质》。同年,陆侃如“到上海来,胡适之先生们正新办个新月书店”,找陆侃如约稿,“问我可有稿件给他们印。我即以此译稿请胡先生再校一遍,拿去印单行本”[53]。单行本出版时,题目改为《左传真伪考》。
两年以后,1937年11月18日,朱自清又记:“读《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中有中国古书真伪之文章,意见甚正确。附录中有冯沅君《左传与国语之异点》一文。”
《左传真伪考及其他》是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4月发行的陆侃如翻译的高本汉论文的小集。除了收入上文提到的《左传真伪考》,还有另外两篇陆译高本汉文章:《中国古书的真伪》(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和《书经中的代名词“厥”字》(The Pronun KUE in the Shu King)。日记所记“中国古书真伪之文章”即指前者。除此之外,还附录了四篇文章,分别是胡适的《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冯沅君的《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卫聚贤的《跋左传真伪考》和《读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以后》。
勘释三十一:《新机轴》
1935年10月3日,朱自清“读《中国的兵》和《周代的封建社会》,前者载于《新机轴》杂志”。
当时并没有名为《新机轴》的杂志。《中国的兵》,作者雷海宗,载《社会科学》1935年第1卷第1期。《社会科学》,“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编辑部”编。编辑部主任吴景超,成员有浦薛凤、蒋廷黻、萧公权等。1935年第1卷第1期第一篇论文就是雷海宗的《中国的兵》,同期还有潘光旦、陈岱孙等人的论文及吴景超、萧公权、王化成等人的书评。这期《社会科学》的出版时间是“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全国报刊索引”平台上所收这期《社会科学》是国立北平艺专的馆藏品扫描件,封皮盖有国立北平艺专图书馆的圆章,并标明“中华民国廿四年拾月五日收到”。因此,这期《社会科学》的出版时间可以缩短到10月5日之前。而朱自清是10月3日读到的《中国的兵》这篇文章,时间是吻合的,去除运抵国立北平艺专图书馆所需的传送时间,这期《社会科学》出刊时间应该就在10月1日至3日之间,甚至很可能就是月头1日。如此短的时间,这篇文章不可能被转载,因此可以断定,朱自清就是从《社会科学》上读到了雷海宗的《中国的兵》,而不是什么《新机轴》。
五、1936年日记
勘释三十二:几部电影名字
1936年1月28日:“下午琏髣等人来访。在城内看《十字军东征》。买票和进入中天影院时发火。”
电影《十字军东征》,即《The Crusades》,一般译《十字军英雄记》。
1936年3月29日,朱自清“进城。在平安影院看《船长之血》,这部影片很好”。
《船长之血》,是对《Captain Blood》的直译,通译《铁血船长》。
1937年2月28日,朱自清“到平安看《真主的花园》”。
《真主的花园》,即《The Garden of Allah》,通译《乐园思凡》。
1937年5月15日,朱自清“看电影《凯瑟琳二世》,场面壮丽,但光线太弱”。
《凯瑟琳二世》,即《Scarlet Empress》,当时多译为《凯塞琳女皇》。该影片由“联美影片公司出产,主角为小飞来伯”[54],主要讲述“母仪天下面首三十君临危邦功罪一人”[55]的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彼得三世之情事及她政变登基的故事。
勘释三十三:两个清华学生姓名
1936年3月6日记:“晚开系会。会后刘钟明、张英超等要求我免去他们西方文学史的必修课程,拒绝之。”
刘钟明,男,云南昆明人,1909年生,1934年本科三年级时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其毕业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获陈寅恪“收集之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近年清华国文系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56]的评语。
张英超则应为张彦超,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1932年入学,1936年毕业。
又,1938年9月1日记:“高年级学生今天出发。任夫山向我道歉。”
任夫山应为任福善,清华大学社会系学生,抗战爆发后随校西迁,1938年8月毕业。也许任福善与朱自清曾有过矛盾,毕业之际,任福善向朱道歉,让曾经的不愉快瓦解冰消。
勘释三十四:抄寄日记
1936年4月5日,朱自清“抄一段一九三三年的日记,将寄给《力报》。”
抗战前后,湖南、广西、贵州先后出现过多家《力报》。但究其始源,则不得不谈与著名报人严怪愚关系密切的长沙《力报》。1936年9月15日,长沙《力报》创刊,社长雷锡龄,严怪愚为记者兼副刊编辑。1938年11月,《力报》遭大火,迁邵阳,称为邵阳《力报》。办报人马多为原来班底,总经理由张治中秘书张稚琴担任。邵阳《力报》敢言敢报,“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在国内第一个披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震动全国。1940年5月13日,多次受到警告的邵阳《力报》终为薛岳下令查封”[57]。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力报》编辑人马发生分裂,张稚琴带走报社部分人手在桂林创办桂林《力报》。雷锡龄出走衡阳并于1940年7月1日创办衡阳《力报》。衡阳陷落,迁贵阳,战后回衡阳复刊,一直发行至1949年11月。朱德龄、严怪愚等人则于1943年6月10日创办沅陵《力报》,继承长沙、邵阳《力报》的敢言传统。“1945年8月底,该报一部分工作人员奉准回到长沙,10月8日恢复出报,至少出版至1948年11月19日。”[58]此外,1947年7月1日至9月6日,贵阳还曾短暂发行过一版《力报》,属抗战时迁贵阳的《力报》之余脉。
从时间就能看出,朱自清要抄的这段“一九三三年的日记”,不可能是寄给上述任何一家《力报》。朱自清真正寄往的是和《力报》同音不同名的《立报》。就在十几天前,1936年3月21日,朱自清还曾在日记本上剪贴了一首名为《兆丰公园晚坐》的旧体诗。这首诗就是刊载在《立报》上的。[59]
《立报》,现代著名小型报,由成舍我联合友人创办。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正式创刊,先为4开1张,后改4开1张半,旗帜鲜明致力报纸大众化。“像成舍我一样,《立报》的编辑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对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以后的新闻工作中又与他们多有接触,加深了这种情感(萨空了因之称他们为‘苦人’或‘苦朋友’)。这正是“报纸大众化”得以实施的思想基础。”[60]正因为《立报》文稿通俗,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定价低廉,在当时广受欢迎。再加上该报立场进步,宣传抗战,“在上海‘八一三’抗战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创当时国内报纸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小型报中最有影响的报纸”[61]。1937年11月25日,因日军侵占上海,《立报》被迫停刊。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恢复出版,后因日军袭港,于1941年12月14日停刊。1945年10月,《立报》在上海重出,至1949年4月30日上海解放前夕停刊。
朱自清所说“一段一九三三年的日记”,其实是指他1933年2月22日日记的节选。这段日记以《<近代史诗>——读书笔记》为题发表在1936年4月11日《立报》言林副刊上,署名朱自清。其文如下:
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第四十卷(一九二九年)见示,中有Harold King作《想象中的近代史诗》(The Modern Epic-A Speculation)一文,颇多新义。略谓史诗一体久已死去,Milton与Speneser欲恢复之。Milton勉有所就Speneser则竟无成。史诗死去之故,或谓系文明不同;今世已非英雄时代,一般人对神话制造亦已无趣味。诚然,吾人已渐不重个人英雄而重群体。如前者大战,得名者往往为某队士卒而非其将领。然林肯,俾士麦等固为出群之才;并世犹有列宁亦其侪辈。此等人吾人许为天才而非英雄;(即拿翁亦然。此等人亦未尝无人为制造神话)今日之英雄,乃制度(Institution)也,非人也。
或又谓英雄须代表文明,非破坏者革命者之谓。而近代人复杂多变,势难约为一类(Type),史诗贵在约,不能约,失其用矣。然而不然,真英雄乃群体(Concourse)。但如火车站者,虽为群体,而已成就,无生长,不足为史诗材料;足为史诗材料者,其惟工厂与银行乎?
近代生活复杂,韵文殆不足用。“近代史诗”,体将近于散文。盖散文应用已久,变化甚多也。虽然,史诗当有太羹玄酒之味,宜简不宜繁,宜举大端(Large unities)而遗细节(Minor confusions)。——准此而论,小说之表现近代生活,或竟不如电影之直截爽快,不事铺张也。
文末乃举纽约第五街中夜之景,为所谓“近代史诗”示例焉。[62]
文章末尾标记“四月六日寄自清华大学”,也就是朱自清抄日记的第二天。
《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收录的这一天日记相关部分如下:
晚读《重读诗》(Poet Lone)第四十卷(一九二九年)中哈罗德·金的《现代史诗探索》(Harold King:The Modern Epic-A Speculation)一文,颇多新意,略谓史诗一体久已死去,弥尔顿(Milton)与斯宾塞(Speneser)欲恢复之,弥尔顿勉有所就,斯宾塞无所成。史诗死去之故,人之文明不同之故。今世已非英雄时代,一般人对神话制造亦无趣味。诚然,吾人已渐不重个人英雄而重群体,如前次大战,得名者往往为某队士卒而非其将领,然林肯、俾士麦等因为出群之才,并世犹有列宁亦其侪辈,此等人吾人许为天才而非英雄(即拿翁亦然,此等亦未尝无人为制神话),今日之英雄乃制度,非人也(Institution)。
或又谓英雄须代表文明而非破坏者、革命者之谓,然近代人复杂多变,势难约为一类(Type)。史诗贵在约;不能约,失其旨矣。然而不然,真英雄乃群体(Cencourse)也,但如火车站虽群体而已成就生长,不足为史诗材料,为史诗材料者,其惟工厂与银行乎?
近代生活非常复杂,韵文殆不足用,现代史诗体(Modern Epic)将近于散文,盖散文应用已久,变化甚多。虽然,史诗当有太羹玄酒之味,宜简不宜繁,宜举大端而遗其细节,以此论之,小说之表现近代生活,或竟不如电影之直截爽快,不事铺张耳。
文末举中夜纽约第五街之景,为所谓现代史诗(Modern Epic)之示例焉。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差别处不少。其中有些是朱自清“抄出正式发表时已有多处不同程度的修改,值得注意的一处是开头增添的说明:‘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诗歌》——笔者注)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见示’”[63]。有些无关紧要,如 “文末举中夜纽约第五街之景”与“文末乃举纽约第五街中夜之景”。且这类差别,有可能也是朱自清投寄时通览润色所致。还有一些是翻译的不同,如“《想象中的近代史诗》”与“《现代史诗探索》”,“为所谓‘近代史诗’示例焉”与“为所谓现代史诗(Modern Epic)之示例焉”。
据《编后记》,朱自清这一天的日记是用中文写的。朱自清读的Harold King的文章是英文文章,如果朱自清日记原文是以“《现代史诗探索》(Harold King:The Modern Epic-A Speculation)”这样英汉双文的形式来记载这些书名、人名等名词,那他在投寄发表时便没有必要将这些名词重新翻译一遍,尤其没有必要将现代一律改译近代。现代与近代,明显是不同译者对同一个名词Modern的不同翻译。朱自清日记原文中的部分名词,很有可能是照录英文,没有翻译。而两种不同的汉语表述,分别是朱自清本人1936年4月5日给《立报》投稿时翻译的,编者整理出版朱自清日记时请译者翻译的。如倒数第二段中的“Modern Epic”,便是朱自清日记原文,朱自清在投稿时将其翻译为“近代史诗”,整句话为:“‘近代史诗’,体将近于散文。”而译者将其翻译为“现代史诗”,且错断句读,这句话变成:“现代史诗体(Modern Epic)将近于散文。”又如“Milton与Speneser欲恢复之”,也是朱自清日记原文,朱自清在投稿时没有翻译这两个人名,但到了整理日记时,译者将其翻译,同时以括号标注原名,这才成为“弥尔顿(Milton)与斯宾塞(Speneser)欲恢复之”。
还有一种导致差别的情况,则是《全集》中的日记存在错误(有可能是日记手稿本身有错,有可能是对手稿的误识误抄),而朱自清发表在《立报》上的日记,经过本人梳理、修订,更为准确,恰好给了我们勘对纠正的机会。“Poet Lone”系误识“Poet Lore”。“Cencourse”应为“Concourse”。“然林肯、俾士麦等因为出群之才”应为“然林肯,俾士麦等固为出群之才”。“即拿翁亦然,此等亦未尝无人为制神话”漏一“造”字。“但如火车站虽群体而已成就生长,不足为史诗材料,为史诗材料者,其惟工厂与银行乎”漏字,句读错误,文意不通;“但如火车站者,虽为群体,而已成就,无生长,不足为史诗材料;足为史诗材料者,其惟工厂与银行乎”则为正解。
开头已经说过,即便是朱自清用中文写的日记,读来也觉得有不少“别扭之处”,这便是一例。好在这段日记曾经发表过,我们得以《立报》版勘对重订。然短短五百字,订出几多问题。更多的日记无他版可对可勘,要解决那些日记里存在的问题,恐怕只有对朱自清的日记手稿重新识读才行。
勘释三十五:P.W.与P.K.
1936年7月6日日记:
……
乘火车南去,陈先生、文藻与隐送行。文藻谓P.W.闻干娘之棺木巳备而大愠怒。他写信给P.K.,责其未告此讯,只催其汇寄丧葬费。后悔使闻知此消息。我原意要他们放心:庶母去世时花费可较预计者少,讵料他们对此事竟大动肝火。
1936年5月28日,朱自清的母亲周绮桐去世,5月31日,朱自清接到父亲发来的信,7月6日,回扬奔丧。这则日记里记的,正是正是朱自清离京赴扬时的情景。从中不难得知,在离别送别之际,朱自清从文藻那里听到一些有关P.W.与P.K.产生矛盾的消息,并为此心伤。文藻,是朱自清二弟朱物华之妻。
从朱自清转述文藻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关键消息:P.K.曾向P.W.催要丧葬费。
此时,朱自清的母亲逝世不久,文藻的话又说在送朱自清回扬奔丧之际。弟媳送大哥回家奔丧,难免要聊到母亲的丧事。有理由相信,这里提到的丧葬费,就是刚刚去世不久的朱自清母亲的丧葬费。P.K.曾向P.W.催要丧葬费,显然P.K.认为P.W.有义务支付这笔丧葬费。那何人才有义务为一个逝者支付丧葬费?一般来说,肩负生养死葬义务的逝者子女是最应该为逝者支付丧葬费的。结合话是从朱自清的二弟媳文藻口中说出,再加上日记中所使用的字母代称,可以断定,P.W.是指朱自清的二弟朱物华。朱物华,字佩玮,1902年生。而P.K.,则是指朱自清的三弟朱国华。朱国华,字佩珂,1907年生。
1936年5月30日,在朱自清接到父亲发来的母亲去世消息的前一天,朱自清曾接到“三弟信,谓母病日益严重,急需款”。1936年7月11日,朱自清返家后的日记也记载他见到了三弟朱国华:“三弟为述母梦。”再结合这则日记中提到的催要丧葬费,置办棺木,基本可以确定,在母亲周绮桐逝世前后,三弟朱国华一直在扬州老家。在大哥、二哥远游的情况下,守护着病重的母亲,料理着家事。母亲去世以后,他曾向二哥朱物华去信催要丧葬费,并且帮助父亲为母亲置办好棺木,但不知何故,他没有把这件事同二哥商量。而当朱物华得知棺木已备,大动肝火。在朱自清动身回扬奔丧时,前来送行的朱物华妻子文藻将这件事告诉了朱自清。
那么,三弟国华没有把为母亲置办棺木的这件事同二哥朱物华商量,朱物华又是怎么知道棺木已备的呢?答案是朱自清告诉他的。这正与日记中“后悔使闻知此消息。我原意要他们放心:庶母去世时花费可较预计者少,讵料他们对此事竟大动肝火”相符。置办棺木的事情扬州方面虽然未同老二物华商量,但父亲或朱国华却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大朱自清,并且是连带具体花费一起告知。朱自清知道以后又告诉了二弟物华夫妇:为母亲置办棺木的花费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多。朱自清告诉二弟夫妇,本意是让二弟夫妇放心,没想到反而触发了二弟三弟之间的矛盾。“讵料他们对此事竟大动肝火”,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物华、文藻夫妇。至于日记中所谓“干娘”“庶母”,是翻译之问题,其实指的都是朱自清兄弟三人的生母周绮桐。
勘释三十六:汪裕奉
1936年7月17日记:“独游西湖。汪庄(汪裕奉)甚佳,地狭有亭八座,且式样各异。”
上条提到,1936年5月28日,朱自清母亲周绮桐去世。7月6日,朱自清回扬州奔丧。为母出殡后,12日赴上海,16日抵杭州,19日离杭北返。在杭期间,朱自清和四妹朱玉华夫妇游览了西湖、理安寺等名胜。汪庄是西湖景区内著名景点,位于南屏山雷峰北麓。建造者汪惕予,著名徽商,汪裕泰茶庄第二代掌门人。汪庄是他的别业。据此,“汪裕奉”应作“汪裕泰”。
勘释三十七:阙特勒碑及唐苾伽可汗碑
1936年9月13日记:“参观北平研究院及北平图书馆的拓片展览会。……看阙特勒碑及唐苾伽可汗碑。”
据天津《大公报》1936年9月10日报道,“国立北平研究院、昨日上午九时在中海怀仁堂西四所该院总办事处举行七周年纪念大会”,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今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开放各研究所、并自今日起至十三日止在怀仁堂博物馆举行拓片展览会”。[64]朱自清就是于展览最后一日前去参观的。
所谓“阙特勒碑”“唐苾伽可汗碑”,前者名称不确,应为“阙特勤碑”,后者一般作“毗伽可汗碑”。
阙特勤碑,1889年被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理学会探险队队长、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在今蒙古境内和硕柴达木地区的科克辛一鄂尔浑河河畔发现。此碑建于公元732年,是当时的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为纪念其前一年去世的弟弟阙特勤而立。“石碑的四面均刻有文字,碑之阳刻汉文铭文,上题‘故阙特勤之碑’的汉文楷书碑额,碑文字体为隶书,十四行,行卅六字,其他各面均为古突厥文。”[65]阙特勤去世后,唐玄宗曾派人吊祭,上述汉文碑额正是玄宗亲笔所书。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同时发现于鄂尔浑河河畔。毗伽可汗,本名默棘连,即上文阙特勤之兄。公元716年在弟弟阙特勤帮助下登上汗位,公元734年被人毒死。唐玄宗派人吊祭,“建立碑庙,并使史官书写碑文(汉文部分)。此碑的突厥文由其侄药利特勒撰写”[66],碑文主要记述了毗伽可汗一生的光辉伟迹。
此外,两碑均立于唐代,只于后一碑名前加标朝代亦有所不妥。
勘释三十八:《T.S.艾略特》
1936年12月10日,朱自清“稍有闲暇,读米尔斯基(P.Mirsky) 的诗《T.S.艾略特》”。
T.S.艾略特,英国诗人,以《荒原》广为人知。米尔斯基,全名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著有《俄国文学史》。
从二人身份便可以得知,朱自清读的不可能是米尔斯基写的诗《T.S.艾略特》。朱自清读的应是米尔斯基写的评论T.S.艾略特的诗歌的文章。1936年8月1日出版的《文季月刊》第1卷第3期就有一篇名为《T.S.艾略忒与布尔乔亚诗歌之终局》的评论文章,作者D·S·Mirsky,即米尔斯基,译者署名罗莫辰。
六、1937年日记
勘释三十九:《归窗一元图》
1937年3月17日记:“最近在沈君处见萧云从的《归窗一元图》手卷。此画活泼而不琐碎。”
按:萧云从有《归寓一元图》传世,无《归窗一元图》。
勘释四十:《风格问题》
1937年4月22日:“朱孟实作《诗与散文》讲演。……第三项中朱曾引用米德尔顿·默里(Midleton Murry)的《风格问题》里的话。默里认为在任何形式中都没有内在的价值。” 1937年8月19日记:“读完米德尔顿·默里的《风格问题》(Midleton Murry:The Problem of Style),是部名著,有许多正确的论据。”1938年9月24日又记:“开始作默里的《风格问题》笔记。”
日记中提到的米德尔顿·默里的英文名有误,应为Middleton Murry,即John Middleton Murry,英国二十世纪早期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新浪漫派代表人物,曾任《雅典娜神庙》(Athenaeum)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主编。早在1921年,沈雁冰就曾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上发表文章《梅莱(Murry)的文学批评》介绍他的新作《文学之面面》(Aspects of Literature)。书名《风格问题》是对《The Problem of Style》的直译,此书一般译作《语体问题》。
勘释四十一:顾炎武的《阎百诗》
1937年4月25日记:“胡博士作‘关于现代中国历史与校勘研究之起源’的讲演。他不同意说利玛窦带来了研究的方法。认为顾炎武的《阎百诗》是受焦竑的《笔乘》之影响。”
末一句应为:认为顾炎武和阎百诗是受焦竑《笔乘》之影响。
阎百诗,即阎若璩,字百诗,是与顾炎武齐名的考据学家。早在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就曾提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顾炎武,阎若璩规定了中国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葛利略,解白勒,波耳,牛敦规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67]
勘释四十二:《白云江树图》
1937年5月8日记:“应张玮邀午餐。张系收藏家,以董其昌之丈馀大幅草书及蓝瑛《白云江树图》为最稀有。”
蓝瑛有《白云红树图》传世,无《白云江树图》。
七、1938年日记
勘释四十三:《陈三立的诗》
1938年3月22日,“读一九三八年二月《天下月刊》上H.H.胡所写《陈三立的诗》”。
《天下月刊》指的是英文刊物《T'IEN HSIA MONTHLY》,《陈三立的诗》指的是发表在该刊1938年2月第6卷第2期上的《Chen San-li,the Poet》,H.H.胡是胡先骕。
勘释四十四:毛玉坤
1938年5月19日:“福田、公超归。常委会决议:国文系和西语系各留一位教授在昆明。陈福田再去昆明,以毛玉坤代之。”
毛玉坤应为毛玉昆,时为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师。在1937年的《长沙临时大学教职员名录》中,查到其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员。[68]1938年度《西南联大各院系第一年级共同科目一览表》则显示其负责文学院外文系“英文一(读本)”“英文一(作文)”的部分课程。[69]据吴宓日记,毛玉昆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授课时还曾遭遇学生罢课风波,“Mlle黄伟惠在沪与毛玉昆结婚,至昆明,欲在联大授课而未得也。毛君在蒙自授二年英文,又遭学生罢课,久乃解决”[70]。
勘释四十五:S.K.陈及其他
1938年5月23日:“下午开校委会。S.K.陈提出课程协作问题,但樊批评他有意摆教务长架子。”
S.K.陈何人?S.K.陈乃陈岱孙,时任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教务分处主任,即日记中的“教务长”。樊为樊际昌,时任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校务委员会主席、总务分处主任。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因校舍不够,文法学院暂设蒙自,上文中提到的校委会,即是蒙自分校校委会。据北京大学档案,1938年4月19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58次会议通过关于陈总等人任职的决定,决定“请陈总先生为本校蒙自分校教务分处主任。请樊际昌先生为本校蒙自分校总务分处主任”[71]。陈总,即是陈岱孙。此时,朱自清也在蒙自,并参加分校校委会会议。据《朱自清年谱》,1938年4月5日,朱自清抵达蒙自,5月2日,当选为分校校务委员会教授代表,5月13日,朱自清“出席蒙自分校校务委员会会议,当选为书记。樊际昌任主席”[72]。
此外,朱自清日记中还存在几处未能完全翻译过来的人名。如1938年2月15日:“陈与冯昨自长沙来,上午来访,他们带来一份Y.R.赵叙述从长沙到昆明旅途详情的抄本。” Y.R.赵为赵元任。1937年7月14日:“今晚开教授会。F.T.陈与沈弗斋口角。”此后数月,F.T.陈或F.T.在日记中多次出现,皆指陈福田。
勘释四十六:柳先生
1938年12月12日记:“赴沈的晚餐会。遇蔡元培先生的女婿柳先生。”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王昭,为蔡元培生下蔡阿根、蔡无忌两子。王昭去世后,蔡元培续娶黄仲玉,黄仲玉生一女威廉,一子柏龄。黄仲玉去世,蔡元培再娶周峻,二人育有二子蔡怀新、蔡英多,一女蔡睟盎。
蔡元培共有二女,但幼女蔡睟盎生于1927年,1938年时才11岁,尚不到婚恋年龄。因此,日记中所说蔡元培先生的女婿,一定是大女蔡威廉的爱人。那蔡威廉的爱人是不是姓柳呢?不是,蔡威廉的爱人姓林,是林文铮。
林文铮,广东梅州人,著名美术理论家。他中学毕业以后赴法留学,1924年,正在法国考察的蔡元培参观在巴黎举办的国际工艺美术学展览会,便由林文铮担任“中国馆的法文秘书,蔡元培在‘展品目录’上写的序言,由林文铮翻译成法文”[73]。1928年春,杭州国立艺术院(即国立杭州艺专)成立,林文铮任教务处长。正是在杭州国立艺术学院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蔡威廉。同年,由蒋梦麟证婚,林文铮与蔡威廉在上海完婚。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林文铮、蔡威廉随艺专内迁湖南沅陵。不久,“杭校奉教育部令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合并,在沅陵改组,威廉因而去职。文铮任杭校教务长十余年,亦于是时去职”[74]。离职后,林文铮携妻儿及老母奔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也正是朱自清会在1938年冬天的昆明遇到他的原因。
在1938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中,林文铮即列外文系讲师之列。[75]到了1939年7月1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13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始决议“聘林文铮先生为本校外国语文系法文讲师。每周六小时,其薪金暂由北京大学方面支付”[76]。
昆明时期,蔡威廉失业,全家老小仅凭林文铮一人微薄的工资养活,生活窘迫。同住北门街的邻居沈从文就曾记下这个家庭的艰难境况:
最忙的自然还是主妇。并且腹中孩子已显然日益长大,到四五月间必将生产。……常常看到这个作母亲的,着了件宽博印花布袍子,背身向外,在那小锅小桌边忙来忙去听我和孩子招呼时,就转身对我笑笑,我心中总觉得很痛苦。生活压在这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微笑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意思想用微笑挪开朋友和自己那点痛苦,却办不到。[77]
然而,屋漏偏风连阴雨,来到昆明一年以后,蔡威廉竟产后病逝。“死的直接原因是产后发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恐费用多担负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蔡威廉死了,给林文铮“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78]
日记中朱自清提到是在“沈的晚餐会”上与之相遇,应当就是在沈从文组织的宴会上遇到沈从文的邻居、蔡元培的女婿林文铮。至于柳先生,则显然是林先生之错讹了。
八、结语
日记作为研究作家生平活动的第一手史料正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将日记纳入研究视野首先便要对其进行甄别考订,以确保可靠。如若不然,则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亦将随着地基不牢而面临倒塌的危险。以上仅考证《朱自清全集》收录的1931至1938年部分日记中存在的错讹。遗憾的是,因为转译、错识等种种原因,《朱自清全集》收录的日记中还存在着一些明知有误却又没有任何头绪可寻的“死疙瘩”,要解决这些问题,尚有待于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有待于对朱自清日记手稿的重新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