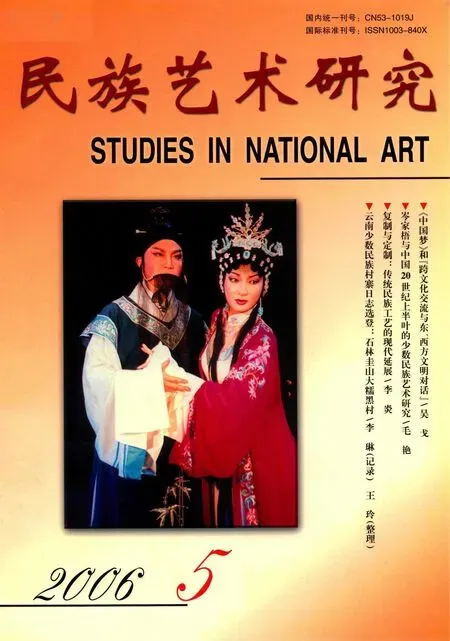电影工业美学视野下华语歌舞片类型建构的困境与策略
刘祎祎
随着市场化态势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华语电影整体自21世纪以来发展速度十分迅猛,无论武侠片、喜剧片这样的传统类型,还是公路片、青春片、科幻片这样的新生力量,均取得过不同程度的亮眼成绩,2019年中国电影更是以超过600亿元的票房成绩力克坊间 “电影寒冬” 唱衰论。但在华语电影多元类型协同共进的格局之下,近年来歌舞片的发展却令人难称满意。除 《如果·爱》《天台爱情》《华丽上班族》等少数几部影片给观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之外,华语歌舞片整体口碑与票房表现欠佳,始终没有自己足够亮眼的代表作。与其他电影类型的蓬勃发展相比较,华语歌舞片反常呈现出失语的态势。
然而,歌舞片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美国、印度等歌舞片传统悠久的国家中,发展势头依旧良好。21世纪以来,好莱坞歌舞片从叙事方式、主题内涵、类型融合、歌舞呈现等多个层面对这一传统类型进行创新,《红磨坊》 《芝加哥》 《歌舞青春》 《妈妈咪呀》《爱乐之城》《马戏之王》等多部影片凭借乐舞与叙事的完美融合与跨类型的多元文化注入而博得了市场和观众的欢迎,这证明歌舞片仍能够在类型电影之林中雄踞一席之地。
尽管歌舞片在国内距离形成成熟稳定的美学风格、较高的工业水准与产业格局相差甚远,但因其巨大的类型潜力,仍值得我们突破现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就是在电影类型美学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电影整体文化与市场格局建构的理论回应,而在某种程度上说,类型片的生产和消费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电影市场的核心景观。本文主要从电影工业美学视域入手,以好莱坞歌舞片做适当参照,并与之进行对比,尝试对华语歌舞片在美学叙事、类型格局、工业制作与产业运作上的缺陷加以分析——希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策略的提出,为华语歌舞片继续探寻类型发展的破题之路;并希冀歌舞片在华语电影的整体格局建构之中,能够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与作用。
一、华语歌舞片类型的“美学困境” 分析
进入21世纪的20年间,华语歌舞片开始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类型之姿登上大银幕。然而,总体而言,仍旧数量寥寥。如果说票房高低某种程度上能佐证影片的大众影响力强弱的话,21世纪以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华语歌舞片可谓屈指可数:2005年陈可辛导演的 《如果·爱》 (票房3007万元),开启了中国歌舞片的新纪元。随后十余年间,《精舞门》 (2008年,票房1510万元)、 《天台爱情》 (2013年,票房1.3亿元)、 《华丽上班族》 (2015年,票房4749万元)等在国产歌舞片票房榜上尚居前列。而其他歌舞片诸如 《斗爱》(2009年)、《乐火男孩》(2009年)、《爱我就给我跳支舞》 (2009年)、《歌舞青春》 中国版 (2010年)、 《精舞门2》(2010年)、《一夜成名》 (2012年)、《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 (2013年)、《你美丽了我的人生》 (2018年)等,却未能如期停留在大众视野的关注中,不仅口碑泛泛,票房更以无一超过400万元而惨淡收场。
论及原因,有文章提到这是 “歌舞叙事母体文化缺乏的问题”, “作为歌舞片的叙事母体文化形式的舞台剧和歌剧在中国观众中的认知度一直不高。”①李盛、方小菊:《中国歌舞片困境的叙事分析》,《电影文学》2011年第14期。还有观点认为国人性格相对内敛含蓄,歌舞片偏外向开放的影像美学与表达风格与观众传统接受度之间存在隔阂。更有人指出,歌舞片在华市场不景气,甚至被称为 “票房毒药”,因而投资人不敢盲目投入,导致没有高话题度的歌舞片出现。如此种种,类似观点即便不被全盘否认,也很大程度上存在片面归因,甚至本末倒置的认知误区。若论文化母体缺乏,我们看到华语歌舞片虽然难掩落寞之势,但近年来 《爱乐之城》 《马戏之王》 等好莱坞歌舞片的内地票房均成功过亿,更不消说 《雨中曲》《音乐之声》《芝加哥》等众多传统及当代歌舞片早已在观众自发追捧与传播中获得了优良口碑。若论市场风险,则正是因为没有集文本叙事、专业歌舞、工业制作、商业运作几方面共同作用良好结合的作品出现,才使得内地歌舞片市场愈加低迷。
华语歌舞片在类型叙事层面始终存在较大的问题,未能摆脱剧作薄弱带来的美学缺陷。内地观众提及华语歌舞片,时常会用“尴尬” 一词作为其形容词的首选,这种不适之感产生的原因无非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剧作自身的情节内容令人难以融入,无法信服;其二,歌舞与叙事融合的方式、时机与程度过于生硬刻意,不够巧妙。有学者曾提出,类型电影依旧存在强、弱两种内在类型分别,强类型的类型假定性明显,不同文本之间在类型词典和语法上都具有更大的相似性②梁君健、尹鸿:《怀旧的青春:中国特色青春片类型分析》,《电影艺术》2017年第3期。。诚然,歌舞片作为类型电影中的强类型,须同时承担歌舞与叙事的相应篇幅,其文本自由度不像弱类型那般开阔,在叙事层面也倾向选择清晰明确的情节结构与角色职能发挥。但就其文本的基本剧作架构而言,起码也应做到逻辑严密、段落清晰、张弛有度。然而,许多国产歌舞片仍无法脱离因其剧作薄弱、叙事混乱带给观众的莫名其妙与游离之感。
从剧作结构上看,陈可辛导演的 《如果·爱》几乎是巴兹·鲁赫曼 《红磨坊》 的国内翻版。然而,相比 《红磨坊》 大制作下的商业类型化表达,《如果·爱》将前者女主角 “夜总会头牌歌妓” 的身份置换成了 “北漂女生”,不仅降低了其后续 ‘变身大明星’的情节说服力,其舞台上下的内容更为游离,其整体氛围也更多沉浸在北漂爱情的文艺片基调之中。另外,《红磨坊》原本描绘女主角与两位男主角的情感纠葛,《如果·爱》却始终在剧情中穿插一个旁观者Monty,身兼表演人员、公车司机、面馆老板等真实或想象性身份,对戏里戏外发生的一切加以评述。这种在三角恋的主角之外另设一个类似观众的旁白角色与观察视角的做法,非但没有令其叙事表达更清晰,反倒弄巧成拙地令原来的双线叙事结构更加混乱,从而暴露出剧作的短板。
杜琪峰导演的 《华丽上班族》 中,许多剧情的设置更经不起推敲,段落内容之间的衔接也十分勉强。例如李想天天把梦想挂在嘴边,却不见以除了跑腿、打杂以外的其他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其职员的职场面貌几乎没有通过具体工作内容来展现,会场中出现了问题竟靠实习员工救场。另外,其角色的设置也缺乏层次感。除青年男女主演之外,张艾嘉-周润发、陈奕迅-汤唯的戏份交杂,这使得主线与副线的情节线索更加模糊,打乱了本应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该片试图通过主角们的 “情感与欲望的矛盾”“来路与去处的选择” 来刻画别样的职场生态,却由于剧作的凌乱削弱了主题应有的张力。
本片改编自2008年由林奕华导演、张艾嘉主演的舞台剧 《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其电影改编中的一大噱头便是花费4000万元搭建职场场景。在这一形式感极强的虚构空间中,只剩高度抽象化的视觉符号——玻璃的墙体、能清晰看到齿轮运转的巨型钟表。该片想以这样的舞台美术布置来表现压抑的职场生活:在全体被监视的环境中,员工只能像钟表一样日夜劳作,隐私和灵魂都变得透明而空洞。因这样的形式表现,职场人真实的工作与情感状态、职业与心理困境的细腻描绘都被抽离在文本之外,电影本身和去掉了 “生活与生存” 的片名一样,只剩空洞的华丽。
类型研究学者托马斯·沙茨认为: “电影制作者运用类型已经建立起来的视觉符码来创造复杂的叙事和主题的情境……视觉编码在叙事的和社会的价值,也延伸到了类型电影制作的非视觉层面。”①[美] 托马斯·沙茨:Hollywood Genres:Formulas,Filmmaking,and the Studio System,载 《电影理论读本》,北京: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323页。华语歌舞片的视觉编码更多地停留在华丽的服装与布景上,却没有在非视觉的主题层面得以延伸与深化。比如 《如果·爱》中的马戏舞台与人物服装,或者 《华丽上班族》 中的职场空间,都只是在进行外在视觉符号的浮夸展示,却没有以之对原本单薄的叙事剧情加以补充,更无法起到对剧作主题与人物情感进行升华的作用。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始终强调剧作的重要性,而上述影片则无论其工业化程度再高,也无力弥补剧作叙事的缺陷,陈可辛和杜琪峰导演的这两部歌舞片都流露出了剧作逻辑的明显短板。另外,两位名导演过多地流露出自己的创作特性—— 《如果·爱》 绵密的情节结构中浓厚的文艺片气质; 《华丽上班族》却又过分依赖视觉符号,从而变为舞台风格化明显的实验片。两部歌舞片自身的定位混乱,让本应平衡的 “作者性” 与 “类型性” 的天平过多倒向前者。工业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即是,在电影的创作中作者需“秉承电影产业观念与类型生产原则,在电影生产中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体验,代之以理性、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方式,游走于电影工业生产的体制之内,服膺于 ‘制片人中心制’ 但又兼顾电影创作的艺术追求,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②陈旭光:《论 “电影工业美学” 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在华语歌舞片的类型创作过程中,更需格外注意类型性和作者性的调和,既不能在影片中缺失类型商业元素,同样要重视剧作叙事的扎实性与逻辑性,让歌舞与叙事不再游离,而是相互融合。
二、华语歌舞片类型的“工业缺陷” 观察
华语歌舞片在工业与产业维度上表现出了产业意识薄弱的问题。其中问题之一是过于夸大导演的作用,缺乏对制片人中心制与整体工业思维的重视与把控。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即为:“对 ‘制片人中心制’的服膺、 ‘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以及电影生产环节秉承并实践标准化生产的类型电影追求。”①陈旭光、张立娜:《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实现》,《电影艺术》2018年第1期。华语歌舞片的创作者作为类型电影的创作者,应对以上原则足够重视,结合当前电影在全媒介文化背景之下应具有的工业制作规范与产业运作理念,使自己的思维理念不断由 “旧作者” 时期向 “新作者” 时期的转变。
以往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 “第四代”“第五代” 的划分方法便基于不同导演群体所呈现的不同代际美学风格与文化思考,导演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亦是其不同代际电影宣传的头号标签,对电影项目拥有着甚高的掌控力。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整体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无论是专业歌舞编导的掌握,还是预算与成本的合理把控,或是电影商业市场全产业链的后续运作,都已超出导演们以往文本创作的经验范畴。综观21世纪以来华语歌舞片的导演,只有 《天台爱情》的导演周杰伦有音乐领域的专业经验;而无论是著名导演陈可辛、杜琪峰,或是 《精舞门》导演傅华阳、 《斗爱》 导演张挺,都从未有过真正参与歌舞片创作的经历,甚至 《精舞门》的导演傅华阳此前仅有一部电影的执导经历②陈春霞:《失语:歌舞片在中国类型化影片中的走向》,《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中国版 《歌舞青春》 的美籍华裔导演陈士铮则更需要面对好莱坞歌舞片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无法避免的类型改写,进而通过专业团队的通力合作,才能基于本土文化背景将其电影的商业类型化与审美接受良好结合。这无疑表明,歌舞片的成功制作,需要更加专业的团队进行配合,而导演需要做好 “体制内的作者”。
所谓 “体制内作者” 是指电影的生产者,首先要认可电影生产是集体合作的产物,电影生产不仅止于导演、编剧,其所涉任何环节都是电影生产系统或产业链条上的有机一环,必须互相制约、配合,才能保证系统功能发挥的最大化③陈旭光:《论 “电影工业美学” 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正是因为导演本人无法把控好电影全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所以歌舞类型片创作中更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协助共同完成。华语歌舞片票房冠军《天台爱情》 的商业成功离不开其国际级制作班底的成功合作。比如,该片在日籍美术大师赤佳仁设计的复古风中医馆舞台上华丽开场,身着中式服装的男女舞者表演了一段颇具强劲节奏感的现代嘻哈歌舞④陈春霞:《失语:歌舞片在中国类型化影片中的走向》,《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口碑较好的 《如果·爱》也请来了印度电影导演兼舞蹈演员法拉· 可汗 (Farah Khan) 担任影片的舞蹈设计,原创歌曲由金培达、高世章作曲,姚谦作词。最终, 《天台爱情》 收获了1.3亿元票房;《如果·爱》也以3000万元票房位列当年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第14位,并入围多个国内外专业奖项评比⑤宋维才:《中国歌舞片的类型探索及可能》,《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采用这种 “体制内作者” 的创作理念制作和运营的类型电影,比较容易契合大众的审美接受度,这也成为这类电影商业收益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华语歌舞片在21世纪仍在经历着由 “导演中心制” 向 “制片人中心制”转型期间的种种阵痛,其项目成本把控上的失当成为影片后续制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比如 《华丽上班族》一片,单是美术指导张叔平在场景搭建上的花费便有4000万元,杜琪峰导演在采访时坦言 “投资上亿,很可能收不回成本”①陆欣:《〈华丽上班族〉:不一样的杜琪峰电影,投资最大的杜琪峰电影》,微信公众号:南都全娱乐 (ID:nd_ent), 2015-08-29。,这表明他对其过高的投资与市场不确定性的担忧,最终其4749万元的票房的确不够理想。如果能有资深监制或制片人与影片导演形成良好的相互制约关系,合理规划资金流向,或许会为华语歌舞片的类型化、规范化进程书写新的一笔。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框架设置中极为重视的一点便是 “制片人中心制” 的设立,所谓“制片人中心制”,即是指让制片人居于电影生产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发挥以其为核心的制片管理功能。这就需要制片人以专业的视角来对整部影片的市场定位、投资把握,演员选择、拍摄流程等方面给予整体把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导演,对投资人与市场、受众共同负责②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 “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唯有如此,制片人得以在影片创作和制作上既坚持商业性,也同时兼顾艺术性和创新性,从而实现电影美学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华语歌舞片亦应践行商业、媒介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产业观念,如此方能助力歌舞类型电影实践,进行其美学与工业的同步升级。
三、类型创新:好莱坞歌舞片与华语歌舞片的对比
21世纪的好莱坞歌舞片为满足电影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类型变化需求,呈现出两种明显的变化趋势:其一,歌舞与叙事的结合更加紧密,创造出了更有感染力的新型叙事方式;其二,好莱坞歌舞片的呈现视野迎来了由传统的梦幻题材向社会现实题材关注的转向,跨类型、亚类型的设置开始更多出现在当代美国歌舞片中。
首先,在歌舞与叙事的融合层面,舞蹈史学者约翰·米勒认为观众应把歌舞与故事的整合水平作为评价歌舞片的重要标准,他将歌舞与剧情的整合方式由完全无关到彼此交融的过程分成几个阶段,华语歌舞片中出现的歌舞大多位于米勒分段方法的中段,即歌舞本身和剧情相关,而内容无涉剧情发展;或丰富情节但不能使之推进歌舞③沙丹:《歌舞乌托邦:〈天台爱情〉的突破与失当》,《电影艺术》2013年第5期。。在华语歌舞片中,我们很难看到叙事与歌舞的完美结合,其歌舞在叙事中并不承担主要功能,更像是类型元素的漂亮点缀,而非承上启下的主要脉络,和剧情起伏并没有必然关联,亦不影响影片的叙事逻辑。
好莱坞歌舞片在21世纪的发展中,已将“故事情节的发展、细节的展现及人物性格的刻画,依靠非电影语言的歌唱和舞蹈来完成,从而使歌唱和舞蹈具有了电影语言的新功能。”④蓝凡:《影像的歌舞叙事:歌舞片论》,《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1期。其角色将自身的背景交代与内心活动都通过歌舞动作来展现,用歌词来代替对白,让歌舞与叙事融合得更加紧密。比如2001年的歌舞片 《芝加哥》 中, “女子监狱探戈”段落便是歌舞融入叙事的优秀典型。六位犯人剪影般闪现在血红色的背景下,用舞蹈与歌词诉说着自己的罪行,而这 “罪行” 之中却又无处不透露出女性作为弱者遭遇背叛时的哀怨与反抗,极大地增强了其戏剧张力。2017年的好莱坞歌舞片 《马戏之王》中,男女主角同样在开篇的歌舞段落中就完成了彼此相识、成长到结婚的全过程,用浓缩而优美的歌舞段落有效推进了情节叙事。21世纪的好莱坞歌舞片中,歌舞段落从此前与叙事并行的另一条平行线,逐渐变为与叙事开始重合甚至交叉,而在这形成交集的过程中,带给观众的是格外有感染力的影像表达。
相比之下,华语歌舞片在歌舞与叙事的融合上,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比如 《华丽上班族》影片前段的团队精英介绍——人物的表情、语言与动作千篇一律;其蹩脚的身体语言非但不能表情达意,甚至生硬麻木、令人尴尬。歌舞段落在其中不仅没有推进叙事,而是退为职场攻心计的类型注脚。在《如果·爱》中,女明星与男导演的爱情多以舞台歌舞表演形式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无数后台歌舞片的翻版,其歌舞片段不参与实质性的叙事,还因和舞台线与日常生活线的内容差距过大,令观众产生割裂感。
其次,较之好莱坞传统歌舞片 “乌托邦式的现实庇护所” 功能的发挥——21世纪以来的美国歌舞片更深入触及现实,运用跨类型的方法融入更多类型的娱乐元素以吸引观众,内容丰富,常变常新;而华语歌舞片则相对单一。
2001年 《芝加哥》的横空出世,让观众感受到了歌舞片中融入犯罪元素带来的强烈震撼。其在叙事过程中多次通过监狱女管教、知名律师等角色,以反讽的手段来揭示人性的虚伪与社会现实的黑暗,用更为立体多面的故事开辟了黑色犯罪元素与歌舞片融合的新路径,如期收获不俗的观众影响力。而华语歌舞片不但缺乏立体细致的角色性格刻画,且其主题更多停留在对人物情感与命运进行描述的阶段,很少从人物入手去展现真实社会现实中人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与烦恼。 《如果·爱》中虽隐约出现了让一个女演员在两个男性导演之间做出自主选择这样的女性意识,但没有就此延续或深入探讨,也没有着墨刻画女星在名利纠结与质疑爱情以外的生活目标或性格特质。
2003年好莱坞的 《甜心辣舞》,通过女主角用歌舞来帮助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实现梦想,完成救赎,同样在 “歌舞” 与 “青春” 的维度之外,增添了更为深广的现实意义。跨类型的犯罪/暴力等黑色元素的加入,让单一类型影片凸显出多元丰富性。比如其《街舞少年》《舞出我人生》中带有挑衅与反抗意味的斗舞段落,不仅是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符号呈现的,更以其舞蹈语汇呈现出自由精神与这种个体话语中的文化内涵,又借歌舞片最终的美好结局传递了社会对青少年的规训与情感感召,使影片不再停留在爱情和梦想共同编织的彩色泡沫之中。相较之下,国产版的 《歌舞青春》 虽然同样聚焦于大学生、青年人生活,但却依旧停留在单薄的造梦模式营构上,缺乏真正依附于中国当下流行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现实思考。
对比好莱坞歌舞片不断创新的开放格局,华语歌舞片的类型仍旧较为单一。其典型样貌仍多聚焦波折爱情的梦幻实现或失意离场,其叙事内容也基本围绕浪漫情怀展开表达,除爱情之外,并未就相伴而生出的其他现实问题伸出触角,也无心进行含有多维文化或美学意味的类型创新。华语歌舞片的票房冠军、由周杰伦导演并主演的 《天台爱情》中,爱情的甜蜜与幻妙成为歌舞与叙事的主线,然而其中男女主人公身份不对等的现实情况并未被着重刻画,更没有关注解决其戏剧冲突的合理性问题,只是采用 “新反派直接解决旧反派” 这种生硬的方式来推进剧情,并未在 “小混混和女明星” 的故事这种老套剧情设定中讲出新意与深意。 《天台爱情》1.3亿元的票房让人不由得感慨明星巨大票房号召力的同时,也很难忽视其在某著名网站刚过及格线的观众评分,影片总体来看更像是明星周杰伦本人的个人秀,观众大多也在为自己的青春情怀买单。21世纪以来华语歌舞片如郭富城与张柏芝主演的 《浪漫樱花》(2001年)、陈小春与范冰冰主演的 《精舞门》 (2008年)、钟汉良与爱戴主演的 《斗爱》(2009年) 等作品也都在取材和主题上聚焦爱情,只崇尚舞蹈对爱情的浪漫表达,题材选取相对单一。
总之,华语歌舞片类型发展单一,浪漫主义倾向过于明显,没有发挥出其更为丰富职能的作用;其以叙事视角、时空与结构构成的叙事策略也相对简单,没有歌舞叙事与现实生活的互文。好莱坞歌舞片21世纪开始了自身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转变,以往将叙述重心放在以爱情为主的种种故事编排上,而近年来则变得贴近现实,题材内容更为广泛。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文化冲突、种族歧视、阶级矛盾等社会痼疾不再被当作需要被歌舞遮盖的对象,而是被当作表达目标,从而拓宽了其叙事内容与关照视野。
四、华语歌舞片类型发展的“工业美学” 思考
托马斯·沙茨曾在其著作 《好莱坞类型电影》中多次谈及类型演变的问题,认为类型电影制作者处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困境之中:即为了保持类型自身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必须不断地变化并且重新创作类型的程式,以跟上观众对于这些议题变化着的构想,以及跟上观众对于类型的不断增长的熟悉度①[美]托马斯·沙茨:Hollywood Genres:Formulas,Filmmaking,and the Studio System,载 《电影理论读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331页。。歌舞片的创作者们同样面临如此局面——无论是呈现形式还是文化主题,以及类型自身的演变,都需要被纳入创作考量之中。在这里,我们以歌舞片类型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好莱坞歌舞片作为对比与参照物,在工业美学的视域下,进行对当代华语歌舞片发展的种种思考。
(一)美学之维:时代感、本土化、大众化共塑的开放格局
首先,应该重视剧本创作的扎实程度,逐步提升叙事水平。电影工业美学始终强调剧本为王,而21世纪华语歌舞片或是剧作自身极为薄弱,没有将其进行符合本土文化背景与审美接受的类型改写;或是沉湎于丰富的视觉符号而疏于歌舞与叙事的结合。尽管由于歌舞元素的融入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影片叙事不像其他类型一般流畅,但这显然不是其一味追求繁复绮丽的歌舞场面的理由,鲜明的时代感与丰富的人性刻画是歌舞片完整叙事框架中同等重要的部分。华语歌舞片应该将自身的叙事视野拓宽,形成开放的类型格局,不再局限于好莱坞业已成熟的情节结构与剧情设置,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以歌舞片的形式对现实世界加以关照。在表现现实与梦幻的乌托邦精神交织复现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类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共存,讲好 “中国故事”,创作出优秀的本土歌舞片。
其次,探索华语歌舞片的本土化特点,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美学转化。中国早期歌唱片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经历了 “不断模仿和力图超越欧美歌舞片主要是好莱坞歌舞片,刻苦寻求自身基本形态及民族风格的艰难历程”②李道新:《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歌唱片——以三四十年代周璇主演的影片为例兼与同期好莱坞歌舞片相比较》, 《当代电影》2000年第6期。,从而使那一时期的歌唱片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与美学风格。当下部分歌舞片让人实觉尴尬,因为其一味追求借鉴西方流行文化体现某种时尚感,而西方流行文化与东方土壤能否良好衔接是问题之一,之二便是流行文化终会面临被替代的局面。有学者指出:“在研究类型电影、推进类型化电影产品的过程中,必须在对电影观众的深入调研和细分的基础上,在追求类型化的同时兼顾现实主义传统,在历史传统的审视中寻找当代意识,在中西的比较中体现民族特色,使电影类型更明确,更多样,更丰富。”③饶曙光:《类型经验 (策略)与中国电影发展战略》,《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而歌舞片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体现丰富的民族特色与传统文化内涵,应在自身的类型发展中重视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化,发展出不同于好莱坞华丽梦幻的美学风格的歌舞片。
再次,在情节设置层面应重视 “大众化”,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 《如果·爱》中,女主角 “女明星” 与 “马戏演员”两个身份都离观众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难以引起共鸣。《华丽上班族》的影片本意是通过职场中利益、情感、人际、欲望的种种纠葛与争夺来展现复杂的人性,但其高度符号化的空间设置虽然华丽,却浮夸得远不似真实工作场景。最终无法收回成本的票房也许是因为影片从形式到内容都与真实职场相差太远,无法对真正的上班族产生信服力。
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式,中国电影正是以 “常人” 和 “大众” 作为消费主体的,而电影工业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资源即是把电影主要定位为一种大众文化。该体系之中,电影工业美学不再属于小众精英化的美学与文化范畴,而是大众化、 “平均的”、不鼓励过度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其承认电影是艺术和工业的矛盾体,并要求电影工作者以综合的、宽容的、多元的心态来进行求真务实、接地气的电影工作①陈旭光、刘祎祎:《中国电影观念流变70年》,《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托马斯·沙茨也曾指出:“电影类型传达的不仅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的,还有大众观众的社会和美学感受。”②[美]托马斯·沙茨:Hollywood Genres:Formulas,Filmmaking,and the Studio System,载 《电影理论读本》,北京: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316页。因此,新时期的歌舞电影主创们应该不断与观众展开对话,影片内容不仅符合大众的审美偏好与精神需求,更要 “赋予中国特有的美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内容”③陈旭光、李卉:《争鸣与发言:当下电影研究场域里的 “电影工业美学”》,《电影新作》2018年第4期。。
(二)工业之维:专业化、产业化、规范化的协同共建
邵牧君先生于1995年在 《电影万岁》中提出 “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④邵牧君:《电影万岁》,《世界电影》1995年第1期。的电影理念言犹在耳,在新时代的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愈发感受到需要在工业与产业的视野之下对电影艺术进行进一步的观察与阐释。随着受众与市场的日新月异,更应重新审视歌舞片的类型发展,希冀从更为专业、整体的层面实现自身类型的工业美学升级。
在整体原则上,结合当前电影在全媒介文化背景之下应具有的工业制作规范与产业运作理念,歌舞片主创应秉承对 “制片人中心制” 的服膺、 “体制内作者” 身份意识的明确以及电影标准化生产的类型电影追求。其导演应做新时代的 “新作者”;从生产者层面认可电影生产是集体合作的产物;通过团队的制约与配合,尽力保证系统运作的最优化。制片人在整体把控影片项目时,应尊重受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需要在创作和制作上既坚持商业性,也同时兼顾艺术性和创新性,从而处理好其类型性与作者性的平衡,实现其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在对歌舞片类型意识的强化与美学品格的坚守中,实现该类型的创新发展。
在工业制作规模上,有学者曾对 “电影工业美学” 进行 “轻度”“中度”“重度” 的形态区分⑤李立、彭静宜:《再历史:对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考古及其理论反思》,《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歌舞片类型的特征之一是由于投资相对较大,属于 “中度” 与 “重度” 的工业美学范畴。在其未来发展中,可以凭借资金投入、团队实力、明星加盟、工业制作水准等方面来细化定位其自身的市场诉求与目标受众。对于部分相对投入低的作品,比如青春歌舞片,可以按照轻度或中度工业美学的标准来进行其剧本选择及后续宣传发行工作。而对于著名导演与主创参与、大投资与大制作的电影,更应选择 “重度” 工业美学的产业运作方法来与之适配,以专业化、流程化的团队运作,打造视听盛宴,形成具有浓厚本土风格的大制作歌舞片,并搞好其全产业链运作。投资甚大的 《华丽上班族》,当时其发行方包括乐视影业、爱奇艺影业等线上与线下的放映终端企业。其更应以此为契机,发挥协同优势,加大宣传、发行力度,有效延伸作品的产业链。
最后,利用全媒介的优势,适当引导消费者的观影趣味,从多种渠道培养歌舞片受众。比如近年来音乐与舞蹈类综艺节目大热,除原有纯歌舞类或舞蹈类电视栏目以外,湖南卫视推出的 《幻乐之城》便是结合了音乐剧、歌舞片的特点来开创新的节目形态的。歌舞片创作亦可以反向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多元内容中汲取资源,全媒介共同创设良好的歌舞片产生的文化环境与发展土壤。另外,歌舞片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培养和储备相关专业人才,提高华语歌舞片创作的软实力。北京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也都设立了音乐剧专业,其间学生数年的专业学习与剧目创作演出实践,都是对后期可能成为歌舞片专业后备人才的良好锻炼。
在中国电影向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型的进程中,华语歌舞片要不断进行自身的类型拓展与创新,要适应和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大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始终追求美学与工业这对二元对立的理论与实践科目的折中与共赢发展,为电影的美学风格与工业品质的提升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歌舞片的主创们需要秉承工业美学的重要类型原则,是 “常人之美” 与 “个性之美” 共存, “类型化” 与 “作者化” 的共建, “制片人中心制” 与 “体制内的作者”共谋。于美学层面,从时代感、本土化、大众化的维度共塑开放的歌舞片类型;于工业层面,从专业化、产业化、规范化的视角协同歌舞片类型的多元构建。由此,电影制作者得以从电影产业升级与话语转变的角度去对当前华语歌舞片类型失语的种种问题重新展开思考,在类型电影的发展进程中建立新时代华语歌舞片的新形态与新机制,就可以发掘出歌舞片类型自身潜在的特有的美学魅力、人文关怀和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