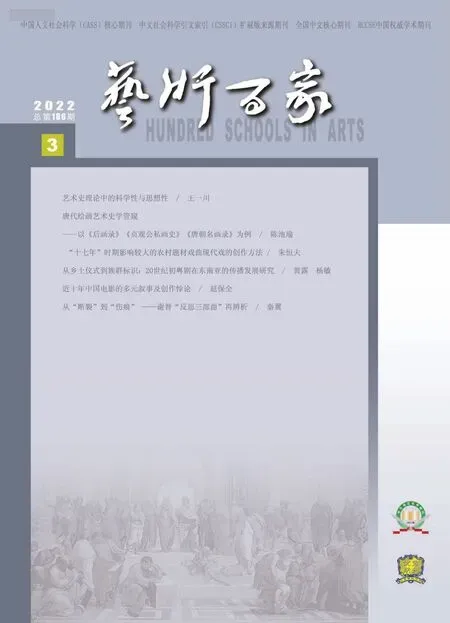乐与政通:音乐与周代政治的治乱兴衰*
刘佳媛
(哈尔滨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乐与政通,作为中国艺术上一个古老的话题,不仅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了乐由祭祀的神坛走向民间,并最终成为对民众传播政治思想的有效工具。乐与政通,这里的“政”并不限于政治,而是社会功能,甚至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乐与政通的目的在于以乐治礼、为维护社会秩序。乐与政通的发展,使其可以观风俗知得失防止腐败,可以移风易俗、寓教于乐改善国民性。由此,乐不仅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成为和“礼”同样重要的治国手段;同时,也进一步加速了乐基于礼制的发展。如,乐的和声、调式、旋律、节拍等,只有在礼制规则的基础上运作,才会和而不乱,达到最佳效果,否则乐不为乐、国不为国……虽然礼制指导了乐的发展及其表现形式,但乐与政通不仅是一个复杂的融合过程,同时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变和漫长的发展历程。单从乐基于礼制的形式表现,不仅难以有效的阐释乐与政的关系,同时也难以深刻认知附着着道德政治内容的乐的本质论。这就需要解答乐与政通的本质关系:道德政治内容是如何被附着在乐之内的;权力者为何要选择乐这一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政治思想;权力者如何通过乐来治国安民邦交。
音乐作为一种“表现性符码”,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特定的声音再现来表达人类的情感,其符号意义过程建立在现象学范畴之上。单纯的缘情使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必然的联系,它之所以成为言志,完全是由于某种规则或约定俗成的惯例。由此,就需要人们通过深入而系统的阐释,才能可观的解析其所存在的文化意蕴和所具有的作用。这使得乐符号本身的象征性及其符码在传达信息时的非逻辑性,使它在表达政治、伦理等清晰、准确的理性观念上存在着难度(附着于其中的政治思想是否能被受众辨认、理解)。同时,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情境,而“政通”作为社会情境发展的重要体现,必然也从多方面影响着乐的产生与发展,进而对受众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一方面表明人们对音乐的理解都是感受和思考的综合体验;另一方面也说明,只有具备了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阐释能力,作为阐释者自己的音乐知识能力,还有音乐文本本身自携的语义能力,才真正进入音乐的欣赏和理解阶段。由此,解析乐与政通所涉及的文化、礼制、社会情境、隐喻、意境等问题,不仅对于认知乐与政通的本质关系和时代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当代音乐的发展也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从乐与政通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基于此,本文以周代政治为对象,基于乐与政通视角,对音乐与周代政治的治乱兴衰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探究。
一、“乐与政通”的精神建构
(一)“乐与政通”的精神建构的源起
中国的诗歌或是言志,或是缘情,中国的音乐可如是观。前者所谓的言志,具有政教性的诉求;而所谓的缘情,则出自天然本真,不过展一己之襟抱,具有自发性。缘情的音乐出于天然,很难说得上和政治有什么关系。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 36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然的歌吟,可能仅仅出于感官而已。又《汉书·艺文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2]1756所歌吟者,不过是在生活中所积累的情绪,钟嵘《诗品·序》用优美的笔触总结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3]2
音乐是人的天性,早在语言混沌未明之时,先民就已经开始自由地吟唱。虽然它植根于人类原始情感的冲动,本只是一种自然情绪的流露,无关于任何出于理性的谋划与安排。但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都具有有目的、有意识、有选择的特定目标。这种情感冲动,一方面标志着音乐艺术的纯粹性、自目的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是有目的地、有意识地赋予音乐精神活动的属性,其“字中有音,声中有字”的音韵表达,从而使其超越了理性的范畴,使之难以成为思维的对象,彻底地进入不可知的领域。英国剑桥学派人类学家简·哈里森在其著作《古代艺术与仪式》中说:“艺术源于一种为艺术和仪式所共有的冲动……艺术和仪式,植根于同一种人所共有的强烈愿望。”[4]13这种强烈的愿望,虽然在原始的音乐中表现为“赫胥氏”怡然自得,以肚子为乐器,打着率性的节拍,歌唱自己天真自足的生活;但却彰显了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想象。因为,在古人的音乐中深刻彰显着对自然的崇拜和神灵的敬畏,其古代朴素哲学的宇宙观和天人观所赋予的文化精蕴,不仅为音乐奠定了社会文化地位,也为言志提供了依据。同时,纯粹的原始音乐虽然是粗糙的,不可知的。但音乐离不开人的发展,原始音乐一旦融入以人为基础结构的社会发展制度之中,不仅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情景文化,也蕴含了社会发展的制度要素。这使得,中国音乐自社会化的发展起始就高度成熟,在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由缘情向“言志”转变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其政教化发展道路。这种政教化发展的音乐,不再是单纯是人对自然的认知,而是融入了更多的社会法则与文化认知。不仅彰显其所蕴含的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更使其乐的传播与表现中浸透着理性的光辉。《周礼·春官·大司乐》有言: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等。[5]573-584由此,礼制下的音乐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天性与情感共鸣,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宣扬与表达。它将社会制度、人的行为规范、等级差异、意识形态等融入到音乐之中,形成了具有一种文化代表、权力象征、“言志”说教的音乐文化和体系,并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引导人们遵守、崇拜、尊重基于礼制下的音乐及其文化体系。应该说,礼制音乐的“言志”初始并非在于“政通”,而是神明崇拜、文化认知、社会统治、阶层分化和规范行为等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但礼制音乐在文化传播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引发的文化道德秩序,不仅推动了社会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更让统治阶层认识到其所具有的制度规范作用与民众服从效果。因为,在礼制音乐的文化场域中,民众不仅更能够遵守阶级的差异分化,也能够认同王权的统治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管理。这使得本与“政”无“通”的音乐,就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以乐德教国子为契机、以礼乐为起点,逐步向“通政”发展。也正因如此,古乐才有了宫、商、角、徵、羽的符号运作(代表君王将相的政治表现以及平民百姓对政局的反应),才有了“正声—德音—和乐”的发展演变和“奸声—溺音—淫乐”的负值评价。将“赏乐”的过程转化成改造思想的过程,在通过乐的价值规范来引导人民对德的信仰与崇尚的同时,将“赏乐”活动变成受众自觉地向官方意识形态标准学习、靠拢的活动。
(二)“乐与政通”精神的建构
在政教性的视阈中,音乐其实更应该被视作“礼乐之乐”,包含着诗、乐、舞,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周礼》的这段文字,不仅可以看作是周代音乐的总结,还可以被看作是上古音乐艺术的总结。这段重要的文字透露出如下重要信息:一、音乐已被纳入到“国子”的贵族化教育体系之中,音乐的教育行为不仅关乎到“兴、道、讽、诵、言、语”等技术性内容,同时也涉及“中、和、祗、庸、孝、友”等思想性因素;二、音乐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宗教和政治,发挥着“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的作用;三、文中记载的《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为六代之乐,按照传统的说法,分为黄帝、尧、舜、禹、汤、武王时的乐舞。[5]575-576而六代乐舞一以贯之,全部关乎政治教化,也就是说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源远流长,而不仅开始于周代;四、文中所记乐舞为“大合乐”,皆场面盛大,是一种人数繁多的群体性音乐活动。包含了由“六律、六同、五声、八音”等音阶与乐器构成的多声部形式,以及自“一变”至于“六变”的多幕剧组成复杂音乐结构;五、乐舞是有主题的,在“中、和、祗、庸、孝、友”的基本主题之外,各幕剧分别有“致羽物及川泽之示”“致祼物及山林之示”“致鳞物及丘陵之示”“致毛物及墳衍之示”“致介物及土示”“致象物及天神”的主题。
所谓的“乐与政通”之乐,所说的正是《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记载这一类型之乐,而从不是单纯的缘情之乐。事实上,中国的音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高度成熟了。所谓的六代之乐今人固无缘得见,然而从考古资料上来看,早期音乐所达到的成就远超想象。如果只是单纯的娱乐而已,大可如《庄子·马蹄》所言那样“鼓腹而游”。事实上,对于先民而言,音乐既是艺术,也是生存。艺术的生命自然得以升华,然而只有在生存的实用之上,才能有艺术。钱钟书先生有言:“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6]226生存先于艺术,今所见上古乐器中,自有用于物质生产者,如河姆渡遗址所出土之骨哨,就是用于引诱猎物者。[7]89-95然而,狩猎只不过是小用,只是音乐表现于民的一部分,音乐真正在社会文化中的大用则体现于“法理”,并首推政治。
音乐从何起源就如同历史从何源起一样,不得而知。然而在文化的追问中,音乐的起源总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传说中的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一直到著名的五帝、商汤、武王的音乐,其篇首开宗明义:“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8]118这表明,虽然音乐的起源不得而知,而对音乐的追忆,却总是同创造文明的英雄,以及政治上的圣人息息相关。因为,音乐的本质是真、善、美,人们创造音乐不仅是欢愉,更在于赞扬美的事物。原始音乐中所蕴含的对自然、神明崇拜的文化精神,当步入社会发展之中时,就逐步的转变为对圣人、大儒、大夫的政教颂德。人们创造音乐、利用音乐颂扬圣人、大儒、大夫的行为,不仅要赞美其德行,更在于引导人们对其尊重和崇拜。这使得,音乐不再单纯是天然而为,而是有目的而为。这种目的,以符号的文化传播转化成改造思想的过程,将赏乐活动变成受众自觉地向官方意识形态标准学习、靠拢的活动。因此,音乐也就和政治的兴衰联系到一起,故而“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
对圣贤的颂扬使得乐成为衡量德有无的核心标准。但如何才能通过乐衡量德、评价德?《乐记》声有“正声”“奸声”,音有“德音”“溺音”,乐有“和乐”“淫乐”。正值向上升华,形成乐的最高正值,方式为正声—德音—和乐。《尚书·尧典》中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9]79古乐对“音”的要求,不仅使得价值判断本身暗含一定的观念指向,同时由此构建了乐与政通的文化精神。既,“正乐”“德音之谓乐”,“乐者,德之华也。”这种通过对乐的价值规范来引导人民对德的信仰与崇尚,乐的表“德”本质使得乐的政治功能取代了它的审美功能而成为权力者制乐的首要动机。由此,原始的音乐无论其原来的面目或精神实质是如何的,在融入社会发展的制度之中后,就已经朝向政教化,及政教理性的方向发展了,并影响着后世的发展。《论语·八佾》载:“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邢昺疏:“于时鲁国礼乐崩坏,故孔子以正乐之法语之。”[10]44与那些根植难以名状之个体精神冲动的音乐相反,和政治有关的“正乐”,从一开始就浸润着理性主义的底色,故而可知也。而这种理性主义,就来自于音乐的公共性,或曰群体性。由此,礼乐完全脱离了纯粹的自然天性,进入到基于社会变革、文化制度与王权统治的发展与演变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文化代言和重要的治国手段。礼乐通过德音、雅颂,不仅规范了音乐创作的和声、调式、旋律、节拍等,还由此构建了一种“天地君亲师”等级差异的音乐文化表达。所有的正统音乐必须按此旋律进行文化意蕴的表达才能称之为“雅乐”,才能守礼制、才能登大雅之堂,否则就不为“正乐”。礼乐“政通”所构建“乐”之文化场域,不仅树立了“正乐”的规则与标准,同时也塑造了社会的规制、道德体系和不同阶层的行为准则、意识形态,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至此,奏乐先要正音、德音须要雅颂、演奏规制有序、乐曲意蕴和谐,不仅成为礼乐的政治标准,也成为礼乐社会文化场域的政治共识。“乐”与“政”的彻底通合,不仅让礼乐成为代表国家最高文化制度的典范,同时也成为改善国民性情、观风俗知得失、防止腐败的重要统治工具。
二、周代音乐的政教性精神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文学有如下的表述:“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simultaneous order)。”[11]32所谓的秩序,意味着整体的文化结构,这一普遍性的论断不止对文学,对艺术也一样恰当。在周代之前的音乐,由于年代久远,其详难征。不过,与周代音乐统治出现的文化结构从一开始,就很清晰。
周代兴起,是以一场征伐开始的;也是由一场乐舞开始的。据说在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的一个早上,周武王率领着“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浩浩荡荡地开赴殷都朝歌,于城外的牧野上展开了激烈的战争。[12]121而《尚书·牧誓》则记载了在这场战争之前,周武王所作的战争动员。其文有如下的记载: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13]284-286有关于《牧誓》,历代注疏家都将之看作是战争的誓词。然而其中有蹊跷之处,刘起釪《古史续辨》质疑道:“既然是‘临战誓众’,作为临战前淬励士气的誓词,为什么叫战士们只进攻六步七步就中止,只刺杀六伐七伐就停下来呢?这岂不是不叫打胜仗吗?”[14]291这一怀疑合情合理。因此,刘先生通过考察文中所记载的黄钺、干戈等器物,又结合了其他载籍与人类学的相关资料,认定《牧誓》远不止战争动员誓词那么简单,而是一篇战争舞蹈誓词。而关于所谓的“步”与“伐”,刘先生又在其《尚书校释译论》中继续加以阐明:“六步七步、六伐七伐等等,都是舞蹈动作,这次举行的是一次军事舞蹈。”[15]1108《牧誓》的战前舞蹈誓词的作用即在于通过演练,进行群体之间的协调。而这一场战争的具体过程,被改编成为周初的《大武》乐章,不断的被后世所追忆。《礼记·乐记》记载了夫子对《大武》的看法: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16]1129-1134无论是所谓的“病不得其众”,还是“以待诸侯之至也”,宾牟贾与夫子所言者,都意在指出,《大武》乐章的核心精神在于团结群体,而这一点,也可以从楚庄王对《大武》乐章的描述中看到,《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17]652-654
政和在人和,《大武》乐章虽有七德,然其主旨却在于禁暴、安民,其基本目的是“和众”。“和众”是丰财、保大、定功之基础,因此,才有后世夫子所谓的“诗可以群”(《论语·阳货》)的理论总结。《礼记·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又曰:“乐统同,礼辨异。”周人之乐的精神核心就在于“和同”,这一点迥别于商代。商周礼乐存在着差异,《礼记·乐记》有言:“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代异世,不相袭礼。”又《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周人的宗法制度,实际上已初步行于商代[18]121;而西周金文中所见的二十种祭祖礼,有十七种和殷礼是同名的[19]45,故而夫子曰:“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然而,就总体上来说,殷周之间的文化变革,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20]451
与周代之“和同”迥异,商代的文化中,充满了暴戾与杀伐的气息。且不说今天所见各种商代墓葬中的累累白骨,以及甲骨文中所记的人殉数量,单就乐舞而言,《左传·襄公十年》有言:“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17]885-886晋悼公所观《桑林》之舞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一定是恐怖异常的,故而使晋悼公惊吓而得疾。李泽厚先生以饕餮纹总结包括音乐在内的商代艺术,将之概括为“狞厉的美”:“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和狞厉的美。它们之所有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诗·商颂》)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那个血与火的野蛮年代。”[21]37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下,所反映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理。据卜辞记录显示,商王朝在其强盛时,与周边数十个方国都存在着紧张的对抗关系。[22]374-390
周人赢得天下,靠的正是能够团结如《尚书·牧誓》所记载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使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史记·周本纪》)。而在取得天下后,面对着殷商民族及其同盟者,周人想到的也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反复的强调“和恒四方民”(《尚书·洛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尚书·召诰》),“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尚书·康诰》)。至于再,至于三的强调对四方百姓的安抚之意与怀柔之心。这也正合于夫子对《大武》乐章历史的描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礼记·乐记》)
包括音乐在内的制礼作乐,同周人分封天下的过程是同步的。分封的主要目的自是统治天下,但其最终结果却是打破各族姓群体之间的界限,促进了族群之间的融合。[23]140正应了《乐记》对音乐的论断“乐者为同”“乐统同”。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所谓的制礼作乐,并不是周初完成的。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礼记·明堂位》亦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流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然而,制礼作乐决然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过程。事实上,就我们所论证的礼乐的和同精神上来看,西周早期和商代都很接近。张光直先生指出,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商代艺术品:“常是庙堂之器,不一定是下层众人能轻易看到的。”[24]104而与之相应的,则是商人的乐舞艺术,也未必是能够吸纳更多人群参与的,这一点,西周早期的音乐与之类似。英国学者罗森指出:“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相对较小而且复杂,要充分欣赏他们,至少有时候它们应该在近距离内被观察。有理由认为宗教仪式可能是一种相对来私人的事情,由与青铜器相关的少数人参加。西周后期的青铜器通过纯粹的数量和组合,来达到它远距离的影响。它们的表面不再装饰极小的细节,弦纹成波浪条饰的流行主题不再有利于近距离的观察,它们相对粗糙的纹饰不妨从更远处来看。而且,编钟引进了一个新的因素——使用青铜器来演奏音乐,成排的大型青铜器奇观和编钟音乐的影响,暗示了当时有比从前更多数量的人群亲眼目睹了宗教仪式,很可能有礼貌地远远站着。”[25]143正是沿着“和同”的轨迹进行制礼作乐的历史进程,才有了孟子与梁惠王及齐宣王谈及“独乐”和“众乐”的观点:“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周代的发展历程表明,周人确立一个重要的社会行动理念、文化准则,那就是“和”。这种“和”所表达的文化意蕴在于“以他平他”,即让相互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相结合,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由此,不仅形成了一种以“天”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原则、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的完整而协调的文化体系,但周人的文化中并非没有“同”,且周文化中的“同”却非商文化中的“同”。商文化中的“同”是“以同裨同”,即排斥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的相互结合,只求同质事物的绝对同一;周文化中的“同”是“存异求同”,既事物之间可以存在差异、矛盾、对立,但通过相互的融合实现共同存在。由此不仅形成了“和同”的文化思想,还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套使差异、矛持、对立达到和谐的国家礼乐制度。基于这种文化所构建的国家礼乐制度和由此不断创新发展的音乐内容、形式等,不仅彰显了周人之乐的精神核心,也让音乐通过符号化的音律传播成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工具,让上至帝王、大夫,下至士兵、贫民等社会不同阶层都能够接受教化,并以“和同”的社会行动理念、文化准则,体现至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乐舞征伐的战士和同”“政和七德的民众和同”“和恒四方民的邦交和同”“分封天下的群族和同”“独乐与众乐的欣赏和同”,不仅是“和同”文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教化的结果,此外还是周代音乐政教性精神的社会表达。为此,孔子称赞周人的礼乐制度“郁郁乎!文哉!”
三、观乐——观诗:治乱兴衰的艺术呈现
诗必以礼,礼必以乐,音乐的呈现,也是政治的呈现。《诗大序》为三百篇开宗明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6]6-18诗三百是教化的产物,也是教化的体现。周人认为,音乐生于政治,并展现了政治的治乱兴衰。因此,可由诗乐来观察政治,故夫子曰:“诗可以观。”(《论语·阳货》)
诗可以观既是理论的,也是历史的。《淮南子·主术训》有载:“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27]296古人认为,音乐产生于天地自然之风,将音乐与风广泛的联系起来。“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礼记·乐记》)“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左传·隐公五年》)“五声和,八风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吕氏春秋·察传》)所谓的八风,《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27]92《淮南子·坠形训》又言:“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27]132对于八风之记载,虽名称有异,但简而言之,所谓八风即是在空间上不同方位之风,与时间上不同季节之风。
古人对音乐的观察,是从听风开始的。而听风,所听者又不仅是音律的高低急徐,而是自然的时序。中国民族是农耕民族,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古代农耕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万年以上[28]1-10,对时间的测量关乎物用与生存。《礼记·乐记》所谓“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即源于此。因此,古人十分重视对风的观测,而对风的观测,则由盲人乐官来掌握,《国语·周语上》记载天子举行祭田礼时:“先时五日,瞽告协风至”,“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昭注:“风土,以音律省风土,风气和则土气养也。”[29]8-9《国语·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韦昭注:“协,和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29]243所谓的协风,即合于时序之风。而“协风”早就记载与甲骨卜辞中:“東方曰析,凤(风)曰协”(《合集·14294》),“禘于东方曰析,风曰协。”(《合集·14295》)
盲人乐官由于目盲而产生了代偿效应,获得了高于常人的听力。通过对风的听观,周人将音乐与时节建立起联系。《周礼·春官·籥章》载:“中春昼击土鼓,龡《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5]631-632在周人的世界里时间不仅是物理的、农业的,也是艺术的。与一年四季春种、秋收、夏长、冬藏相伴随的,是不同的乐章;这些乐章反映着也催促着人们按照时节的规则从事劳作。
而在艺术化之后的,则是政治化。《礼记·月令》以时间为坐标,将自然的物象、音乐艺术和政治行为联系起来。在《月令》的记载中,每一个月份,都有专属的声律,也有应当的政令。这些有司之命令,也就《月令》所谓的“布德和令”:“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月令》之所以称为“令”,即在于此。这些《月令》中所记之“月令”,可以看作是周人政治的传统。周人通过“告朔”来确定时间与物候,再将之施为于政治。《周礼·春官》载“大史”之职守有“颁告朔于国”之事。“告朔”之内容即是“月令”,《左传·僖公五年》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史官于月朔所备之物需要颁布,用以为生活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蔡邕《明堂月令论》说:“古者诸侯朝正天子,受月令以归,而藏诸庙中,天子藏之于明堂也,每月告朔朝庙,出而行之。”[30]58由此,音乐通过时间彻底地与政治建立起了联系。
正因为同时间相联系,听风观乐的政治考察,也具有了历史性。《诗大序》所谓“治世之音”“乱世之音”的区分,以及“变风变雅”说的提出,都是一种“观乐而知政”的理论体现。而这一种理论在周人那里,又是切切实实地落实到艺术观赏之上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适鲁观乐的事件:请观于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如同刘勰之所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季札对所观之周乐,从《小雅》《大雅》《颂》,一直到传说中的舜帝的《韶箾》之乐舞进行了评价。其评价方法既是“美哉”“广哉”等艺术上的评价,更是“盛德”“周德之衰”等政治上的评价,同时也是对乐舞时代背景的历史性评价。因此,历史也成为了音乐政治品格高下的评判标准,即历史悠久的古乐比资历尚浅的新乐而言,具有更高的政治品格。《礼记·乐记》子夏与魏文侯对“古乐”与“新乐”的褒贬已经是老生常谈;而一向非毁礼乐的韩非子也在其《十过》篇中,通过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表明了新乐政治品格更为低下的态度。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31]62-65
与音乐的时间性标准相并列,“观乐—观诗”以观政的文化方式也是空间性的。前文已述,“听风”所听之八风,不只是季节之风,同时也是地理方位之风。因此听风观政,既可以转化为音乐在时间上和政治的联系,也可以转化为音乐在空间上与政治的联系。
国人好说“风土”一词,风总是和土相应。如前文所引《周语上》“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以及韦昭注:“风土,以音律省风土,风气和则土气养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调,《左传·成公九年》曰:“乐操土风,不忘旧也。”一方的风调,产生于一方的风土;故而观其风调,亦可观其风俗。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风调和政治的关系,《周礼·地官·诵训氏》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5]414-415又《夏官·训方氏》:“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5]883观四方之志于四方之俗的方式是“诵”,其所诵者,自当是四方之风调,表明了古人注重以诗歌的方式观察政治。《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16]363《汉书·食货志》又言:“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2]1121-1123观音乐之风,其本在观民之风,“民之风”体现为民生好恶与民生疾苦。诚如《诗大序》所言,观风之义在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将每个个体的喜怒哀乐,汇总成政治的消息。因此才有了十五国风,才有了《孔子诗论》:“《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32]20
而为政者知民风的目的,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1708知民生之疾苦,自当善政以救弊。而通过观风而知民风之不善,亦可以通过诗歌的方式加以疏导改正,《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天子省风以作乐。”杜注:“省风俗作乐以移之。”[17]1411又《孝经·广要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3]42有了通过音乐以疏导风俗的实践,才有了《诗大序》所谓“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经典理论总结。
从周的统治来看,正是吸取了商纣灭亡的历史经验,摒弃了强权政治与暴力统治,通过礼乐制度治理国家。它以风为音律意在确立“天”之精神信仰,以月令意在确立“地”之行为准则,由此构建的秉承“天地”之意的礼乐制度体系不仅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同时也成为国家管理的方式与手段。既“乐与政通”一方面,通过乐的艺术表征和文化表达,树立统治阶级的权威性,不仅教化民众以恭敬服从的精神取代自由散漫的精神以便于统治,同时,也提醒执政者注意自身形象,不要耽于享乐而丧失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对乐的社会考察,在检验国家治理成效的同时,将乐的传播转化成改造民众思想的过程,由此使赏乐活动变成受众自觉地向官方意识形态标准学习、靠拢的活动。周人社会礼乐制度所彰显的“乐与政通”,不仅是音乐政教化发展的重要文化表达,同时也是音乐艺术社会阶层化表达的重要体现,对后世社会发展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深远的。这也就使得当《新乐》出现后,其“节奏明快,弦律多变,情感丰富,男女混杂,尊卑不分……”彰显散漫、随意、傲慢、个体价值的乐之文化,凌驾于恭敬、有序、崇拜、群体价值的《古乐》文化,对其形成严重的挑战或威胁时,也就必然受到统治阶层的批判与抑制。古乐与新乐的斗争表面上看是两个文化的对抗,其实质则是两个阶级的冲突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与周代政治的治乱兴衰是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文化命题,“乐与政通”视阈下的音乐与周代政治的治乱兴衰研究,阐释了音乐的发展之所以不是纯粹的文学或单纯的艺术,而总是依违于政治之间的文学和艺术,是因为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音乐最为抽象,但也最具文化张力;这种文化张力使得音乐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具有与政治同构的特点,同时在文化表征上也具有与政治近似的文化内涵。由此,音乐不仅必然为政治所利用,也使其很容易就成为政治的象征物。因为,在古代不发达的科技和教育使得权力者在向民众传播其政治思想时阻碍重重。虽然国家机器能够通过强权维持其统治,但任何政治权力都无法完全依仗暴力而行。由此,使得权力者必须同时依靠用某些文化形式来辩护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音乐,从增强意识形态控制的角度来看,不仅具有大众性、艺术完美性的文化形式,同时,其多样的传唱方式也容易在社会大众中产生共鸣,并代表着受众心理状态得以迅速传播,引导社会大众的行为方式,也就必然成为政治工具言志、秩序与观政。
“乐与政通”的精神构建,权力者通过乐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对现实世界理应持有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由此,不仅让乐成了人们反省自己德行的形象尺度,也要求民众以恭敬服从的精神以便于统治,祭祀音乐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以“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同创造文明的英雄,以及政治上的圣人息息相关。从而使乐超越了理性的范畴,彻底成为礼的精神表达。“乐与政通”政教性精神,权力者要求个体为在群体中的“同”而放弃“真”,取消个体价值,向群体价值标准看齐。由此,不仅形成乐在文化结构上的“和同”,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基于“和众”的文化秩序,并通过“化”来实现,战争音乐是这种精神的重要体现。但这种“化”并非暴戾与杀伐,而是禁暴、安民。它以“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打破各族姓群体之间的界限,促进了族群之间的融合。从而使乐至于宗法制度之中,流年朝诸侯于明堂,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乐与政通”治乱兴衰的艺术呈现,政治首先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同样,奏乐首先要正音,依据礼制而制定的各种音律、乐理,不仅能代表礼制“有序的和谐”精神,本身的结构形式也暗含着象征政治的意味。权力者由此通过音乐向民众彰显政治呈现,并用以为生活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诗乐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体现。它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来观察政治,知民生之疾苦,自善政以救弊。从而使乐成为人民对德的信仰与崇尚,寓教于乐改善国风的道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