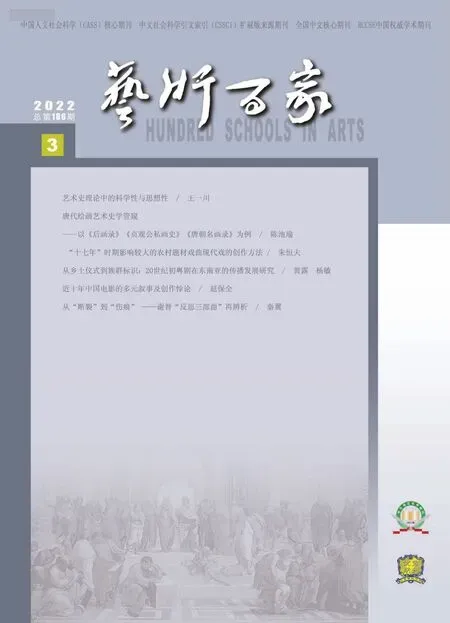中国禅宗美学的审美意境与生态精神*
彭修银,姚羿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开始普遍注重禅宗美学的哲学本体论和范畴本体论等研究。众多学者认为,意境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一种审美意象,包括其理论的形成,不仅受到道玄思想的影响,更是受了到唐代禅宗的影响。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禅宗对具体的艺术门类诸如诗歌、绘画等形式的影响上。近年来,随着生态美学的崛起,逐渐出现了对禅宗审美的文化综合性研究。但无论是作为范畴论的审美意境还是作为生态美学关照的禅宗智慧,其研究似乎都过分局限于某一学术领域。因此笔者尝试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将中国禅宗美学中的审美意境和生态精神相提相论,总结提炼挖掘其内在的相关性和共生性。因为中国禅宗美学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审美意境的营造上,更凸显的是一种东方特有的关注个体生命和感性、强调“心本体”、注重“道在当下”的美学生态精神。显然社会思潮普遍倾向于希望借艺术之力,能够弥合人与自然间日益明显的断裂关系。这在强调创建生态文明,加快生态建设的今天,其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应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生态”概念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但人类工业生产恣意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已不仅囿于自然界,更深入波及到了人类的精神危机。正如欧文·佩基所讲:“物质进步很快地补偿了过去,国家一个个消退、灭亡,信仰与哲学盛行后又失去魅力。”[1]34基于此,余谋昌和鲁枢元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相关的阐述,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是地球这个活物的有机组成,“精神在自然之中,是化生万物的‘母’,是万物运行的‘道’”[2]22显然,“生态精神”指的是地球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共生、和谐与互动。而它既是“人心”之变量,亦是走出生态困境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3]36
既然提到“人心”,不能不联系到由玄到禅的中国禅宗美学。其强调的“心本体”蕴含着对于个体生命与感性的尊重、探索以及开悟的途径等。正如宏智正觉所言:“诸禅德,来来去去山中人,舍得青山便是身。青山是身身是我,更于何处著根尘?”[4]89在此,人与自然及社会间性的和谐共存关系,从始至终均是禅宗开悟观照的对象,这也恰是其生态精神的具体体现。三国时期著名玄学家何晏和王弼的“性情之辨,体用之争”,其用意所在便是引出禅宗与自然和谐共生、以自然作为禅悟载体的生态哲学观。禅宗作为中国特色的佛教,推崇以“得意忘言,不立文字”作为开悟明理的方式去体味自然,此处的“不立文字”应是基于禅宗追求“空”之境界所生发,实指不拘泥于万物表征、不拘囿于表层即“离色离相”的感悟方式,正所谓“五色令人目盲”。由此可见,禅宗在某种意义上承继了老庄精神,同样强调了“色”与“空”二者间的辩证关系,追求还原众生之本来面目的“心道”。
禅宗对待自然所秉持的“道在当下”的生态精神使其在哲学观上十分重视个体在立时对于客观事物的唯心体悟,正所谓“境随心转”,《坛经》中那段著名的“风吹幡动”禅学公案就充分地表达了此种自然观。禅宗世界中的自然心相化使得其对真如法身之追求的兴趣远远高过对自然客观事物本身规律性的探讨[4]101,这种超脱凡俗论域只关注于个体直观世界单对自然“顿如显现”进行观照的行为,既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诸多领域,也在历史的沉淀中形成了其独有的审美意境与生态精神。
一、境生象外,禅意无极:禅宗美学之审美意境与生态精神追求在诗歌艺术中的表现
胡家祥先生曾讲:“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甚或是佛教庄(子)学化的产物。”[5]3作为中国佛学成功“嫁接”印度佛学的典型代表,禅学在唐代以降,其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充分的丰富与拓展,而“以禅入诗”“以诗喻禅”则成为了当时禅意与诗境超越个体自相、进入和合共相的原初发端。
(一)缘起“性空”:禅意与诗境超越个体自相、进入和合共相的原初发端
1.“自性”修为:禅意与诗境均蕴含着自得解悟、悲悯苍生的人文关怀
其实,在禅与诗二者交合圆融的过程中,实已自证了万物“同生共体”的佛学本质。因为禅性之于诗性同为心之所化,为心之所识。作诗者由心生法,并在禅性的空灵隽永中观照自己,直至妙悟出万法唯心,三界虚妄,从而脱离色欲的纠缠,拥有分辨真妄的心志和才智,真正领悟到禅宗世界的“众妙之门”。
事实上,禅与诗的交融并非偶合,因为禅学所向往的悠然心境与诗学所追求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实为异构同质的关系。禅境与诗境所求契合的精神理念均蕴含着纯朴至善的人文关怀。禅宗作为中国大乘佛教之代表,其色空的修佛理想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兼备着出世与入世、悲智双运的利济精神。体现在禅诗的创作上,这种悲悯苍生、利他济世的性空审美意境就愈加明显。譬如唐代李世民有诗云:“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5]18太宗假托殿前经幡这一喻象来象征俗世万法以种种色相在世间流转浮沉的规律。自表象看,它们似梦如电,艳丽如虹。但作者似乎一眼看出了其不可一世、招摇弄空的轻薄,殿前经幡因此成为尘世万法的象征,所体现的不过是世俗智慧之“惑智”。而在无知而无所不知的佛家智慧“圣智”看来,这熙熙攘攘的众生法相不过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7]47的虚妄罢了。由此联想到那些由因缘遇合而生的人和事由于在生灭无常的因果轮回中因执着于事物炫目表相而难得超脱。太宗在此偈中即以慈悲心哀怜叹息陷入“我执”中不得法门的芸芸众生,字里行间中皆流露出其对禅宗所主张凡事皆因缘和合、暂生还灭、无实在自体的“性空”思想的修为与体悟。
与此偈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上官仪的诗作《从驾闾山咏马》:“桂香尘处减,练影月前空。定惑由关吏,徒嗟塞上翁。”[6]18作者在诗中借马的命运悲叹世人不能自主摆脱追求功名利禄的烦扰。《金刚经》有云:“贪嗔痴爱,为四恶业。贪则为己私计,是有我相。嗔则分别尔汝,是有人相。痴则顽傲不逊,是众生相。爱则希觊长年,是寿者相。”[7]58诗中的马,其坐卧行走之所以可以为外力(即关吏)所驾驭,是因为它缺乏自得解悟的慧根;而人虽顶天立地,鼻直眼横,却不见那堂堂大道,赫赫分明,偏因种种念,现出万般形,困顿于贪嗔痴的惛昧无智之中。正所谓:“何期自性,本自具足。”[8]22众生若以妄心揣度外在世界,不去向内诉求“个个本具,个个圆成”[8]58,即人人内在都原本具备的佛性与自性本体,终归会陷入同马一般迷失于黑暗而不自知的“无明”境地,更会失去顿悟“性空”之境的契机。
2.“空”之般若:禅诗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皆为“空”,须丢弃妄念和烦恼
禅诗创作者好以自然物象作为“引禅入诗”的中保或载体,所谓“诗禅一致,等无差别”。如从生态精神的角度来分析,不单单是体现了“禅”与“诗”二者在交融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方面的不二关系,更揭示出禅宗哲学及美学对于人与自然万象之关系的独到见解。
《宛陵录》有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4]133禅宗认为“心”是万物的本源,是自然生态的核心构造,由“心”所生发而出的万物之本性皆为空。而人作为自然之物的一部分,在自然这个巨大的“现象界”中,其顿悟的最高目标即是将假象与实相区分开来,使这构成现象界的二者不再蒙蔽人的内心,进而达到无法无相且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述之“心”其实并非实在本体,它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是世间万物的生命之源,由其所生发而出的自然与人类并不具备任何实体存在的特征。正因如此,这世间万物的生灭往来,缘聚缘散,本就是空空色色,色色空空,幻灭一场罢了。“色”在此意指自然景物,如若在自然的冥想中仅仅只是流连于事物在意识当中所生的法相,而不去追寻其背后的“空”之意境,那么这样流于表面的体悟则终究是虚妄的。而由色法(物质)与名法(精神现象)相构而成的世界,瞬息间便可完成机变无数,那我们对己对物的执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就此放下,同宇宙间的“大自在”和融为一,以一位禅者的无分别心去看待自然与生命的流转腾回。
禅诗中的“空”之般若教引世人以平易之心观照万物,以“自性本空”的经世智慧作为个体的立身之本。但承认万物自性皆空并非意在将人劝离红尘,消极避世。正所谓“似空非无,默而有声”,在这“性空”之中,空的是妄念,空的是烦恼,内在的真如自性依然保持着“如如不动”的本真意志,亘古不变。
(二)“圆照”之境:作为禅宗美学对于生态系统全面深入、浑然圆融的整体观照方式
1.无言之美:禅宗“不立文字”,在平常事物中参悟玄理幽微
现代生态哲学通常将人与社会、自然三者看作是构成世界的复合生态系统。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议题上,强调应从系统化的角度分析二者间的关系。[9]42这种生态整体理论所凸显的生态精神与禅宗哲学及美学所推崇的“缘起说”在核心观点上可谓不谋而合,即慧能所称的“不二法门”或“圆照”。
中国禅宗美学思想中的“圆照”之境,意指境生象外,禅意无极,是一种宇宙间最高级的充满智慧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境界。这显然与长期在“二元对立观”浸润下的西方古典哲学有着质的不同。因此,在此等“禅悦为食,法喜充满”[10]87的光照下,一种“意生言外”的无言之美作为全新的审美意境便出现在了禅师所作的颂偈里:“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9]133此偈大意是劝诫世人了却凡心,面对世事要心存坦然,不必太过计较成败得失;凡事遇缓则圆,做人要像水牛般顺遂自然,手中的“锄头”(我执)要在心中先放下,最后才能真正得以解脱;不执著于身外之物,人活一世,来时双手空空荡荡,去时亦然,是故要顺应自然本性,淡泊名利,志向高远。禅宗讲“不立文字”,并不意在玄妙化“禅”所表达的境味,而是若在言意不可辨处强加言语的阐释,会引听者因此产生分别心,距悟道愈加遥远。
实际上,凡颂偈者,其作者皆擅以平常物什作为参透禅机的喻体,刘恰是禅宗在悟道修炼中所推举的“俯仰观察,见微知著”之精髓所在。所谓见微知著,即以小参大,在看似平常的事物中见出微妙玄通的义理。那么,既然说这玄理幽微,岂非千言万语方得穷理尽妙?其实不然,慧能有云:“此须心行,不在口念。”[8]102真如自性是无法经由理性思维的言语进行表达的,它只能通过一些艺术手段来使“不在口念”的禅理以类似于中国古典艺术中的“留白”形式出现,予人以启发。而在这首个中意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禅诗中,无论是“空手把锄头”还是“桥流水不流”皆与常理相悖,无一不使观者疑窦丛生。实际上,前文中对这寥寥数语所作释义并非确解,实属为领会偈中禅意而设之方便法门。傅大士在《法身颂》中写下此偈,用意无疑是为开示禅法,点化众生,而与禅宗公案相类似,内在涵义的不可确解性在赋予颂偈巨大艺术张力的同时,也使受众无法领略其语义的全貌。不过,这种宗教语义的缺失恰恰使审美意境的解读成为了可能,宗白华先生曾说“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11]137颂偈抑或禅诗的字句上存在着丰富的意象,而这些意象作为意境的载体恰恰是“意生言外”无言之美的想象力源泉。
2.圆融合一:人道、禅道与天道间的整体观照与把握
以超乎寻常之言,说玄妙艰深之理,似乎已成禅宗惯用的参道之法。于是,禅僧常常作偈悟道,诗人亦可触目菩提。譬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中吟诵道:“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使知如幻身。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12]215此诗借用“芍药花”这一意象来譬喻人生如幻如梦,韶华易流逝,劝勉世人不可为事物之一时色相所迷惑。虽是通过写花、写景来悟禅,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自我。自然与人圆融合一,诗性的智慧与生命内涵的整体关照和把握又一次营造了禅宗审美的“圆照”之境。只是与禅僧之颂偈相比,文人以诗当禅,在参悟的过程中那些平易的语言更增添了几分烟火的气息。
无论颂偈还是禅诗,经常使用到的大量田园意象,诸如青秧、涧水、云岩、草树、野老、牧童,均能用作传递禅意的介质,并因之构造出一幅幅自然生态的和谐美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与自然原本便是审美与被审美的关系,而这些自然物象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颂偈和禅诗本身所蕴含的宗教色彩,同时也模糊了禅与自然间的界限感,从而强化了人道、禅道与天道间的生态联系,为读者在体悟“自性”的过程中提供了无尽的审美想象空间。
当然,“圆照”作为禅宗美学针对生态系统全面深入、浑然圆融的整体观照方式,更能使人深入思悟:首先,人与自然同处一个生态场,能量置换结果的损益互为影响。二者皆非衡量万物之尺度,且其关系的非功利性才是彼此和谐共存之本。人类如过分统筹和量化自然,其结果最终会反制自身。因此,须用整体观的视角来重新审度世界。凡此种种,应是禅宗美学所蕴含的生态精神给予今人的最大启迪。
佛家常讲“不可思议”,禅宗亦有“拈花微笑”,要而言之,皆指佛理幽深,体现的是“不立文字”的无言之美和“即心即佛”的审美智慧。若想体察入微,窥破天机,了然这偈中门路,必得使心之昭昭,浊浪不侵,用生命直观的方式,抛弃语言逻辑的阻碍,方能认清这此时、此地、此景的此岸与彼岸的现实,才能领悟到境生象外、圆融合一、禅意无极的妙意。
二、画中阡陌,纸上须弥:禅宗美学之审美意境与生态精神追求在绘画艺术中的表现
禅宗不仅影响了诗歌,亦逐渐波及到了诸种艺术形式,绘画便是在“引禅入诗”之后又一个为禅宗思想所占领的艺术高地。唐之前,中国画通常要着色称之为“丹青”。初唐后,前朝所流行的青绿山水逐渐向金碧山水、浅绛山水等过渡。直到中晚唐时期,黑白设色的水墨山水已基本替代了着色山水而成为文人墨客的首选绘画语言。
(一)水墨“色空”:选择黑、白、灰的水墨语言是为了追求自由、卓然的精神世界,充满着禅意氛围的笔情墨趣营造出“色空”的审美意境
1.色相全眠:水墨之“色”暗合禅者之心的清净、智慧与空寂
水墨黑白,大道至简,看似泾渭分明,两不相容,却在墨纸上如太极两仪般幻化出超脱五色的斑斓世界。唐代著名画家张彦远有云:“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夫画,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细而外露巧密。”[13]193意即描摹对象不能刻意去追求其形色,如若将对于五色的摹画作为绘者心中最终目的,那么整幅作品都将变成匠工手艺的堆砌,毫无意境可言。“五色令人目盲”,对于修心悟道的禅宗而言,以黑白为底色的水墨画无疑为修禅者“明心见性”提供了上佳的修炼门径:心于黑白渐变之中遨游在虚实两界,没有五色的侵扰和凡尘色相的迷惑,得以在心无旁骛的幽游之境中体悟“空”的奥义。
那么,就水墨画而言,何谓“色”?何谓“空”?又何谓“色空”?
首先,基于“存形莫善于画”的功能,中国传统绘画中“色”的第一层含义应指固有色,即“随类赋彩”或“以色貌色”的自然之色相。但古代文人对物象的描摹不仅仅止于“外师造化”,更追求“中得心源”。于是,便有了“墨分五色”“高墨犹绿,下墨如赭”“观色立象”以及心随笔转等诸多用墨、用笔、用色等的随“意”概括和表达,从而呈现出画面之色相,这应是“色”的第二层含义。但于法性而言,无论是物象的固有色还是画面的水墨色相,均属“殊相劣形皆幻色”[14]569,亦即虚无、空泛,这应是禅宗之“色”的内涵所在。
其次,“空”在佛教中虽然有多种释义,但多指任何事物皆因缘而生,无独立存在的实体,谓之“法空”。同时,亦指“心空”,即本心澄澈空寂且广大无际,含容万象。而水墨画的素朴、单纯之色既是文人追求淡泊、宁静的精神介质,更是“诸法空相”的重要载体,它以视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让观者可以体悟“虚无”,直指“空性”。至此,禅宗之“色空”可以理解为禅者以清净、智慧、空寂之心在观照物象时,不被色相所惑,从而顿悟,此心空明。
2.空灵本性:超脱色相、“洞见自性”方能进入恬静的顿悟之境
如果说文人选择了黑、白、灰的水墨语言是为了追求自由、卓然的精神世界,那么在充满着禅意氛围的笔情墨趣中则营造出了一种“色空”的审美意境。
作为禅画的典型例证,五代画家石恪的作品《二祖调心图》描绘的是丰干、慧可二位祖师参禅养心之故事。画面中,慧可单手托腮,双足盘坐,身体微倾,面目似睡非睡,凝神静思;而丰干则面露睡态伏于老虎脊背上,体态形神甚是放松,身下老虎仿佛也为伏虎之人情志所染,尽显温顺平和之境。两幅画面颇具禅意,人物形象温和雅致,寥寥数笔勾勒出两位祖师恬淡闲逸的入禅情态。该画禅意鲜明,两位祖师放浪形骸、自由不羁的形象充分反映了禅宗色空思想对于画家石恪的影响。这种超脱色相,凸显事物“空灵本性”的意境追求恰是禅宗“色空”思想的主旨所在。而此处,寓庄于谐的“墨戏”显然不是佛教教理的沉思辨析,而是面对人生困惑后的顿悟平易。画中两位高人逸士全然没有身为名士的威严,更无佛像的正襟危坐。其双眼迷蒙、似有醉意且不修边幅的傲然洒脱之态与身下老虎憨态可掬的面貌相得益彰,带上了一股人间烟火之气。这正印证了禅宗超脱色相、非宗教化、倾向生活化和世俗化的特点。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言:“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9]258可见,为适应中国国情,禅宗正是以生活化的修行方式吸引了封建时代大批不满时政的文人墨客,正所谓“俯仰皆禅”。
禅宗修行讲求知行结合,使其思想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到修行者的日常生活中去。这一点体现在绘画创作上,即绘者借着艺术的外壳,来深入探讨禅学精神。道家讲求回归自然,而禅宗所求则是看空自然,《二祖调心图》中虎与人违反常态的亲密关系正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这也正是禅宗美学追求全然超脱、“无法无天”生态精神[9]203的具体体现。如此,绘者能通过内在观照把握“此在”,把握最真实的自我,即能自识本心,自见本性,从而达到“色空”的艺境。换言之,虽然凶猛如老虎,也能在人“洞见自性”拥有智慧的抚慰下安然入睡,为禅心所感化,这抑或就是人与物顿悟时均该有的恬静之态。
(二)“止观”禅境:作为禅宗美学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所体现的两大审美意境的“色空”与“止观”,突出对“心”的关注即是对人的自性精神生态基因的审美观照,它可以使之与所描摹的外部世界如山水、植物、动物等具体物象同形同构,更能在追求自然、自在的精神生态的过程中去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禅宗画家既可以通过“遗貌取神”的“减笔”方式给观者带来“色空”的审美意境,又极擅长用艺术形象来展示禅宗思想对“止观”审美意境的追求,“南宋四家”之一的马远代表作《寒江独钓图》便是典型例证。笔者试以管窥豹,探寻其个中禅意。
1.静观默照:息虑宁心有助画意与禅心的“反观自性”
该画虽着意描写“寒江独钓”,却只见微波寥寥,扁舟一叶,渔夫一人耳。一人,一舟,片缕波纹,却依然为观者带来凌冽寒意,孤独满怀,能在方寸画纸间行如此大胆之构图唯“马一角”之当仁不让。此处,在笔者看来,“寒江独钓”的表现重点落在一个“寒”和一个“独”字上,而“寒”又实为“独”的衬托物。画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着笔墨便能画出尘世悲凉,写尽人间沧桑。而造成这寒意与孤独之感的来源就隐匿在画面大量虚空的留白之中。此处之“虚”并非有待填充的空间,而是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亦是身体之“寒”及至内心之“独”的直观呈现。这种心理上的由外内转与禅宗思想中的“止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所谓“止观”是禅定(止)和智慧(观)的合称。意指抑制妄想,息虑凝心以达到佛教的智慧境地。南岳慧思禅师在《大乘止观法门》中说:“能令妄念不流,故名为止。”[15]35《成实论》亦有云:“止能遮结,观能断灭;止如捉草,观如镰刈;止如扫地,观如除粪;止如揩垢,观如水洗。”[16]52由此可见,“止”能使诸妄念止息于刹那之间,而“观”则是达到“止”之后的境界,可以“断灭”事物表象,以达到静观默照、“反观自性”的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禅宗画或有禅意的画作从其创作动机开始就摒弃了礼制社会“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思想,而是把作画的过程视为作者身心与大自然的契合统一以及追求“自在美”的门径。画意与禅心在此得到了体验、相容和共鸣,大自然的生态精神不仅因此化成了作品中的气韵和神韵,还逐渐成为了精神生态、文化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基础和来源。如此,禅门妙法在绘画世界的辅佐下亦如春雨般润泽了这些失意于尘世的桃源之士,使他们得以借禅宗“顿悟”之力修葺自己的精神园地,徜徉在花语与禅意交织的悠然之境中。
2.定“境”生“慧”:天地长空为“心性合一”的参悟提供了生态环境
马远《寒江独钓图》可谓定“境”生“慧”,那么这种“止观”之“境”具体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不妨把小船四周那大片的留白看作是画家的心境,将独坐船头垂钓的渔夫看成是画家自己,一切便都了然。因为在这独特的视角下,你会发现马远所画正是本我在“反观自性”的过程。他乘坐一叶扁舟,以禅定的方式来到自己内心的意识之海。此处渺无边际,除去扁舟激惹起的些许波纹,宁心若镜。在这大海之上,本我反观自性,虽寒风瑟索,却能一心垂钓,呈现专一宁静的止观之态。在此,一切都皆圆满清净,各色烦恼与欲念都沉寂在识海的深渊里。本我以禅定作为饵食,将埋藏在意识之海中的这些不洁之物一一钓起,还给大海一片清净,完成禅宗“佛向性中作,莫作身外求”的自力美学追求,并无限接近《解深密经》中所云之“胜义谛”,亦即世界最真实的本来面目的“离言自性”之境。此处,“性”指自然,亦即人的本来面目。“心”是世界的本体,“性”是“心”的本质,“心性合一”成为了禅宗美学生态智慧的核心。[9]161因此,就如画面所展示,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空境无人的天地之界为其营造了一种能够找回“自心自性”的清净且立体的参悟环境。
“色空”与“止观”作为禅宗美学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所体现的两大审美意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文人士大夫“以画喻禅”的精神图卷,更以“禅虎”和“独钓”等造型构图形象地展示了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以及平常心的顺世生态思想。日常起居,无心是道,注重的是内在的超越,心注一境,追求“无念”“无相”“无住”的解脱之道,从而自悟佛性。这种对“心”的关注即是对人的自性精神生态基因的审美观照[9]3,它可以使之与所描摹的外部世界如山水、植物、动物等具体物象同形同构,更能在追求自然、自在的精神生态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三、空寂无我,自在之音:禅宗美学之审美意境与生态精神追求在音乐艺术中的表现
相较于文学与绘画,音乐于听者而言更具有某种“临即感”,这种善于在审美主体内心中创造“意象流”的艺术形式非常适合成为禅宗意境之传播载体,亦可成为其生态精神的完美代言。
(一)声色皆空:禅宗“以音声为佛事”,与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心心相印,拈花微笑”的境界相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以音乐作品抒禅隐之意、写逸士之心,暗合了离色离相的禅门意境,声色皆空也成为音乐艺术在禅门意境之中的典型表现
1.“琴心”即佛:琴与禅道艺相通,追求一种寂灭无我的审美意境
在“以音声为佛事”的禅宗看来,“若心常清净离诸取着,于有差别境中而常入无差别定,则淫坊酒肆偏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17]66所谓“正声”“淫声”的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欣赏者的心性安宁且没有丝毫杂念,那么无论是何种风格的音乐,其中都皆有禅意可寻。音乐无拘无束,个中含义无法为任何特定的语义所解。禅宗的不立文字也使它具有了音声的特性,使其能与自性相融,如投石生涟漪,涤荡入人心。衢州乌石山杰峰世愚禅师曾有妙解:“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何谓直指人心?曰:开口不在舌头上。曰:见性成佛。性在甚么处?太湖三万六千顷,夜夜波心月色明。”[17]66由此可知,打动人心不必非需口舌之劳,但凭音声、棒喝抑或机锋即可洞察禅理,领略禅悟。体现在中国传统音乐上,这种追求“心心相印,拈花微笑”之境界的特点就愈加明显。
宋代以降,借由抚琴来参禅修行之风气日趋盛行,北宋时甚至发展出影响深远的琴僧系统。一时间,古琴艺术已成为是时文人僧侣修禅悟道的必由载体。古人讲学琴即是悟禅,琴与禅的道艺相通,皆讲求修习时应以破除我执、法执乃至空执作为最终达到无诤三昧之证境的微妙法门。具体表现在琴曲作品中,即是追求离色离相,寂灭无我的审美意境。
宋代刘志方所作琴曲《鸥鹭忘机》可认为是表现此种禅门意趣的上等佳作。此曲取意于《列子·黄帝篇》[18]205中的一则寓言,其内容大意是:古时有一位非常喜好海鸥的人,每日清晨他都要来到海边与海鸥游玩,海鸥一见到他便成群飞来。一日,其父要求他将海鸥捉来两只玩耍,结果等到他怀揣着这种心意再次来到海边的时候,海鸥们却一只都不肯飞下来。该寓言告诫人们要常怀良善之心,不可心怀巧诈。
《鸥鹭忘机》全曲仅有两个乐段,节奏不徐不缓,旋律鲜有大跳,透露着禅独有的虚静之美,从始至终都给人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清谈之感。乐曲开头以连续的滑音作为引子,闻之若见海鸥翩然而起,随风浪于海边的晨空下错落飞行。全曲调性统一(F宫调),第一段的主题乐句在后续旋律不断地换头合尾中得到强调和升华,其中不时出现的双弦剔和拨刺等演奏技法使乐曲整体的情绪逐渐高昂。《醒心琴谱》有云:“人能忘机,鸟即不疑;人机一动,鸟即远离;形可欺,而神不可欺。我神微动,彼神即知,是以圣人与万物同尘,常无心而相随。此即《鸥鹭忘机》之意味。”[4]150故此,圣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合德,是因为“人能忘机”。所谓忘机,即是忘却机巧之心,淡泊明净,不以世事为怀,要以纯真无垢的本心去与自然相互沟通。
但若要达到“忘机”之境界,首先需要认清并远离世间一切幻化之相,正如《金刚经》所云:“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7]77由人五感所生的相终究是不牢靠的。以《鸥鹭忘机》来说,当抚琴人在二度创作的过程中超越五感、心无杂念且外尘不入之时,他也就已进入到了寂灭无我的审美意境之中了,真可谓“琴心”即佛。
2.离色离相:文人逸士借琴音托物言志,追求禅境
如果说《鸥鹭忘机》着意在“寂灭无我”,那么《平沙落雁》则更倾向于表现“离色离相”之意境。
《平沙落雁》最早出现在明末编印的《古音正宗》中,迄今已有四百年历史,其曲作者不详。全曲现存乐章五至八段,可粗略分为三大部分,即呈示部分,展开部分及尾声。《古音正宗》说它“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19]。据不完全统计,《平沙落雁》共有122个版本,每个版本都对该曲进行了不同角度地诠释,足可见其在民间的受众面之广,以及受欢迎程度之深。
《平沙落雁》(本文以《古音正宗》版本为例)开篇就运用了八度大跳进入主题,空灵隽永的音响暗合着空寂静谧的禅境;在短暂的引子之后,乐曲正式入拍(进入第二段),主旋律在三度之内平稳进行,模拟雁阵在高空缓缓飞行;倏然,旋律出现大幅跳进,仿佛雁群在急速扑扇着翅膀,此时吟猱技巧的运用使得乐句充满了戏剧性;第三段乐句采用换头合尾的手法继续回应第二段的主题,雁群高飞的画面感由远及近,其嬉叫声不绝于耳;在经过短暂的连接部分之后(第四段),乐曲进入展开部分,这里新材料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雁群的意象;尔后,雁群渐次歇落在沙洲之上,鸣叫声稀稀落落,乐曲进入尾声。
古琴曲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亦具有和淡、恬淡、静淡、古淡的单音性特质,它常常能在不经意间以跳动的旋律甚或音符撩拨人的心弦,使之怦然心动或豁然开朗,与禅宗顿悟之态极为相似。于是纵观全曲,虽然《平沙落雁》的标题性似乎限制了其表现力,但作者的本意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如泣如诉、不绝如缕的琴声中,抚琴者和听琴者均已沉浸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足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况且又因演奏者对曲谱的理解以及彼时彼刻心情等的差异,该琴曲亦产生了或丰满华彩或恬静跌宕或委婉流畅等多种风格的解读和表现。琴法便是心法,心手具合,指意通达。由此可见,之于曲意无论大雁还是作者的心境均为虚相。按《古音正宗》的题解,此曲编纂之时虽恰逢朱明王朝大厦将倾,但曲中却无半分愤懑之情,反而多出了几许悠然旷达之感。曲作者借大雁之形抒禅隐之意,借琴音之相写逸士之心。此处,作者体味到的是天地之间的至理真情,发出的是世事险恶的感慨,参透的是了无挂碍的生死大事。琴声可悟道,琴心即佛心,因此,从宗教的角度上讲,实际上已经处处暗合了离色离相的禅门意境。
(二)自性无我:禅宗美学不仅着意于生命属性的生态精神,而且也看重从整体论角度出发观照事物存在并兼顾其内在的相通性。从音乐本体的内在精神出发,将审美欣赏活动中所悟得的生命体悟,大而化之为某种以与自然和融为一为目标的生态精神,内外俱澄,可修复人与自然间的间性关系
1.空诸所有:不被语义束缚,注重感性体验才能进入禅宗的审美意境
作为有禅意的音乐代表作,上述作品与有“世界上最慢的音乐”之称的南音相比,在表现手段和审美意境展开的层次上仅可说达到了“小乘之境”。
南音与我们所能听到的绝大部分所谓“民族音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它的音乐特质中既没有“丝竹乱耳”般的喧嚣,亦无拖沓冗长的沉闷,有的只是千回百转,超然物外的灵动之美。南音中有不少与佛禅审美意趣相通的器乐及声乐作品,譬如在清咸丰年间编印的《文焕堂指谱》中,有曲名曰《舞霓裳》和《后庭花》,二曲之乐名与唐代《教坊记》中所载唐曲名相仿;亦有佛乐《你因势》《南海观音赞》等使用法器演奏的作品。
在这些足以见证华夏中古音乐的艺术瑰宝中,拍板、尺八、轧筝、横抱琵琶等是为最常用的南音乐器,搭配南音独有的节拍系统“撩拍”,乐曲的曲调通常婉转绵长,甚至有一句唱词长达九分钟的现象。特殊的音乐结构及乐器使用造就了南音独特的审美意境,人们很难从南音音乐中得到具体的情感指向,即便乐曲本身是标题音乐也同样如此。而正是这一点使它彻底挣脱了语义的束缚,具备了这独一份的悠然恬静。没有了恼人的文字障,南音音乐得以更加自由地借助乐音的跳动与万物同频。它既可以是潺潺流水,巍峨青山,也可以是才子伴佳人,明月配彩云。与自然物象间的无碍互通造就了南音音乐本体自身与禅境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建立在超越生命理性基础之上的,不为人之理性所能掌握。换言之,唯有感性的体验才能把握乐音在时间与空间双重流动条件下所呈现出的审美意境。
诚然,这种纯精神的体悟过程带给主体的是一种似驴非驴、似马非马的审美经验,但感官上的不确定感却恰恰为解除显意识的压抑而大开方便之门。主体因此得以在审美接受活动中获得顿悟禅境之机,真正领悟到离色离相、寂灭无我的审美意境。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远离色相、空诸所有的审美意境与音乐作品创作及演奏过程中的艺术沉思状态十分相近,这种深层次体悟的获得当归功于在禅宗影响下中国传统音乐中所独有的“线性思维”。与西方音乐追求乐音间竞争关系的理念不同,中国传统音乐更加重视不同乐器和不同乐音间的相互配伍,力求“同中存异”。不同音声在“禅”的感召下和融为一,超脱其自有的个体特质,摒除小我,成就大我。同时,使参与其中的乐者将艺术之思同禅修之道两相结合,神貌分离,徜徉在“离色离相,寂灭无我”的艺术境界里。
2.内外俱澄:音乐注重内外互通,有助于人与自然建立完整的通感联系
禅宗美学不仅着意于生命属性的生态精神,与此同时也看重从整体论角度出发去观照事物的存在并兼顾其内在的相通性。音乐对外沟通着万物之灵性,对内其精髓则深深植根于人的志性之中。一个超理性的音乐世界就萌生于这内外互通的灵肉交流之间。于禅宗而言,最广义的音乐或许便是这通达宇内的空灵之响。
“离色离相,寂灭无我”的审美意境所透露出的不仅是禅宗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更代表着一种建构于审美直觉之上超越万物的无上智慧。即不执着于事物表象,能以纯真无垢的内心领悟禅机,心斋坐忘,摒除一切杂念,借音声而明了禅理之精微。禅宗独有的审美意境与般若智慧亦使它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生态精神,是一种由“禅”“定”“慧”中生发而出的自然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能帮助人们在徜徉于音乐浩瀚之海的同时,进入到反观自性的最真实状态,天道、禅道与人道在如此状态下弥合为一,自成一体。人的志性生命亦可在这样的虚静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进而突破一切法障,达到本心清净、再无任何烦恼的澄明境地。
这种本我对自性的悉心观照,在《鬼谷子》中有着十分贴切的叙述:“乃能内视,反听、定志,思之太虚,待神往来。”[20]313曲作者及演奏者在反观自性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内视法来增强内在世界与外在自然间的联系,以寻求一种以纯自我意识体验为主且与禅宗“入定态”相辅相成的超感官体验。在心识与自然的不断交互中,本我意识逐渐与肉身剥离,达到澄明无我之境,从而与自然建立完整的通感联系。
如今,本我与他者的割裂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产生不可调和矛盾的主要动力因,人类在内部志性层面的失衡直接导致了其在处理与外部自然间关系时的混沌状态。这种内外部的失衡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已然深切影响到了人类社会日常运作的方方面面,而如何修复这种割裂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正在面对的重大课题。在笔者看来,禅宗美学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和方案。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有言:“禅的最终目标是使我们免于疯狂或畸形。”[21]137禅学的终极奥义之一即是发掘人类自性中最本真的那一面,而艺术无疑可以成为发掘自性过程中最有力的武器和工具。就音乐而言,通过欣赏那些充满禅意哲思的旋律和音符,我们可以完善自我、以达到澄明之境,并以此作为通达本我的方便法门。当然,亦可从音乐本体的内在精神出发,将审美欣赏活动中所悟得的生命体悟大而化之,即化为某种以与自然和融为一为目标的生态精神,努力内外俱澄,从而以此为契机,修复人与自然间的间性关系。
四、结语:中国禅宗美学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诸多领域,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审美意境表现与生态精神的价值追求
自李泽厚与刘纲纪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为“禅宗美学”正名以来,学术界对禅宗美学正式展开研究至今也不过近四十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围绕禅宗美学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本体论方面,与其它学科间开展纵横比较的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较少。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对禅宗美学之审美意境进行全方位、跨门类地综合研究,努力打破以往倾向单一性研究的学术现状,并以期通过这种方式,为禅宗美学在未来的学科建设及相关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中开启新的思路,提供出相关的研究模式。
中国禅宗美学以东方的智慧,借艺术之力,对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断裂予以“间性弥合”。这样的艺术智慧以审美意境的形式呈现在诸种艺术领域中,即是“性空”“意生言外”“色空”“止观”“离色离相”与“寂灭无我”。同诸等审美意境相伴而生的,是以整体观“圆照”为特征的禅宗美学生态精神,而作为生命之母的大自然既是禅宗美学审美意境传达的特殊媒介,更是使其生态精神得以表现的重要载体。中国禅宗美学对待自然所秉持的“道在当下”的生态精神使其在哲学观上十分重视个体在立时对于客观事物的唯心体悟。中国禅宗在某种意义上承继了老庄精神,强调了“色”与“空”二者间的辩证关系,追求还原众生之本来面目的“心道”。由玄到禅的中国禅宗美学,其强调的“心本体”蕴含着对于个体生命与感性的尊重、探索以及开悟的途径等。禅宗世界中的自然心相化使得其对真如法身之追求的兴趣远远高过对自然客观事物本身规律性的探讨,这种超脱凡俗论域只关注于个体直观世界单对自然“顿如显现”进行观照的行为,既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诸多领域,也在历史的沉淀中形成了其独有的审美意境与生态精神。
对于当今人类社会而言,运用禅宗美学“圆照”方式对世界进行“圆融合一”的整体生态观照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人类方能通过与自然和谐共享同一个生态场从而找寻到“无念”“无相”“无住”的解脱之道,进而修复本我与他者间原本割裂的关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透过现代城市的高楼林立关照与重温人类孩童时期的单纯与美好;唯有如此,禅宗美学“悲智双运”“利他济世”的生态精神才能够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纵观文学、绘画、音乐,无论是“性空”“色空”“止观”“意生言外”亦或是“离色离相,寂灭无我”,凡此种种,无外乎一个“悟”字。唯有审美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立志在这诸种审美意境的徜徉中悟得正果,才可在“兴象天然”的诗境中体验到“软草承跌坐,长松响梵声”之意;在“天机自张”的画境中领会到“轻风摇杂花,细雨乱丛枝”的禅语;在“随物婉转”“妙契自然”的乐境中更进一步会意到禅宗贯穿始终的生态精神,并能突破唯工具论的桎梏,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关系,彻底了悟现实和艺术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只是建立在审美主体知觉及想象活动基础之上所聚合的形相而已。如此,中国禅宗美学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诸多领域,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审美意境表现与生态精神的价值追求。在当下面临人与自然困顿之时,我们能借此更好地领悟“关注当下”“道在平常”于自身修为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研究禅宗美学审美意境及其生态精神的意义所在。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