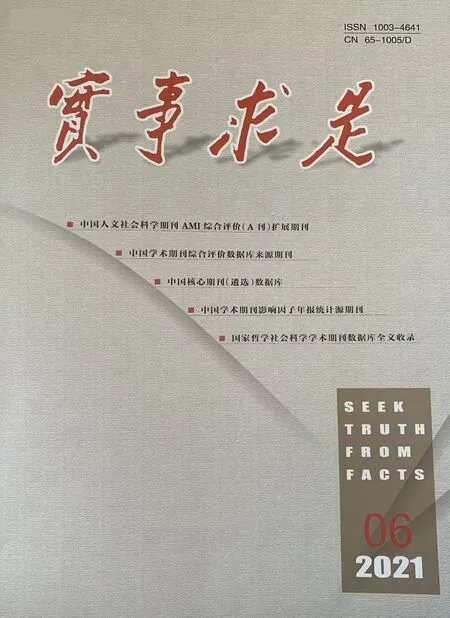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海洋法既有核心原则的继承与革新
黄钰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正朝着成为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方向发展。[1]与此同时,国际海洋治理正处在艰难的转型期,各类矛盾纠纷层出不穷,新的议题不断涌现。习近平主席2019年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2]侧面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海洋规则革新之间的密切关系。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什么”“怎么办”两个层面,即“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阐释,[3]以及如何将“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到国际海洋规则的革新当中。[4]对于“为什么”问题的研究尚存不足,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何以适合指导国际海洋规则革新?尽管在部分研究中有所提及,但多集中在“现实需求”层面。[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海洋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规则革新需求之间的内在契合有待深入剖析。同时,对于同样作为理念性质的海洋法既有核心原则——公海自由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二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也缺乏系统的梳理。为此,本文试从海洋法的两大原则入手,分析“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海洋治理新需求的内在契合性,以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拓展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一、海洋法两大核心原则的缘起与内涵
公海自由原则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已经在长期的国际实践中被广泛接受,成为了海洋法的核心原则,后者还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势。
(一)公海自由原则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缘起
公海自由原则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都起源于国际社会对主权外海洋资源利用的现实需求,在内涵上高度相似,在价值追求上则大相径庭。1605年,格劳秀斯在《捕获法》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海洋自由”问题。为了论证荷兰乃至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在海上航行并进行贸易活动,他阐述了三个层层递进的理由:(1)“先占”不适用于海洋,因此任何国家不能根据对海洋的“发现”而享有主权;(2)海洋及海上航线权不得为任何国家所独占,应为全人类所共有;(3)所有国家均有权自由地利用海洋资源。[6](PP16~46)从上述三项理由可以提炼出三个关键词:“非主权”“共有”和“自由”,而这三个关键词正好对应了公海自由原则的法理基础、法律属性和价值取向。公海自由脱胎于海洋自由,而依上述,公海自由源于对海上贸易的现实需求,在排除主权的基础上,意在建立共有物的观念,最终达致各国自由使用的目的。
与公海一样,国际海底区域也在国家主权范围以外,且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矿物资源,而与公海自由中的航行、捕鱼等不同的是,矿物资源具有稀有性和非再生性,各国在资源开发能力与水平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因此“公平”问题向海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1967年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阿维德帕多(Avid Pardo)在第22届联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对“国际海底区域”提出四个方面的原则:(1)不得据为己有;(2)以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与目的的方式进行探索;(3)开发与利用应以保障全人类利益的目的进行;(4)用于和平目的。[7]显然,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在内容上高度相似。
(二)公海自由原则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内涵的对比
其次,在自然属性以及制度设计上,“国际海底区域”的确有别于“公海”,而基于自然属性上的稀缺性以及权利使用上的限制,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同于“共有物”,是一个新的概念。[10]但笔者认为,尽管是一个新的概念,“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并没有突破“共有物”的基本范畴,其根基与重要特征仍然是“共同共有”,[11]仍然没有突破权属界定的定义方式。因此,对于“国际海底区域”而言,概念之争是次要的,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其应当有利于“全人类利益”这一实质目标。
适用对象的相同性质决定了两大原则在基本内涵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对于“公海自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列出了两项原则性的内容,即“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和“对公海主权主张的无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成立的基础则体现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上,主要包括非主权和全人类共有两个基本属性。同时,还特别规定了缔约国遵守条约的义务及损害赔偿责任,随后也阐述了两项原则性规定——为全人类利益及专为和平目的。显然,非主权属性与和平目的是两大原则共有的且是基础性的内容。非主权属性是构筑起后续自由、共有、和平等内容的基础。和平原则则是二战后国际法的核心内容,由于资源的争夺是诱发国际冲突的重大因素,因此规定对主权外领域的权利行使必须以和平为目的,以避免冲突和维护权利的正常行使。同时,非主权与和平两项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掣肘的,非主权的属性给予了各国竞相利用的空间,而和平的目的则为这一空间标定了界限。
二、两大原则无法适应国际海洋治理的新形势
海洋问题的频发与严重后果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国际海洋治理的必要性,国际海洋秩序维护亟需海洋治理的新范式。公海自由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支撑下的现有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存在先天不足,面对海洋治理的新需求、新议题与新矛盾难以为继。
(一)新的需求:利益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两大原则均始于对主权外海洋区域的利用需求,然而随着对海洋利用与开发的深入,日益凸显的问题就是各国利用海洋获得利益的不均衡。公海自由原则忽视了各国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的差距导致不同国家在对海洋的利用能力方面呈现的巨大差异。以典型的海洋强国——美国为例,其一直主张所谓“海洋自由”,并自1979年推出“自由航行计划”,明显是对公海自由的滥用。[12]与此同时,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良好实施的关键就在于平衡开发实力不足的国家和经济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13]尽管该原则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考虑到了不同国家在利用海洋能力上的差异,但既有的“平衡性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导致相关国家的权利没能得到实现以及海洋利益被发达国家进一步蚕食,无法实现海洋开发利用的持续稳定发展。其一,体现在沿海国与非沿海国之间在海洋开发主导权上的矛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非沿海国在公海的利用和专属经济区生物资源开发等问题上的权益,有赖于沿海国的积极配合,而从实践来看这是很难得到落实的。以“利用”为现实需求、以“自由”为导向的“公海自由”原则显然无法解决各国在利用海洋上的实质不平等状况。其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方面,随着开采的实际进行,新资源勘探规章进一步削弱了平行开发制。金属硫化物等勘探规章对“保留区”制度进行了变革,提出了替代性的“联合企业安排(Joint venture arrangement)”①参见《“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ISBA/16/C/L.5)第16条第2款,以及《“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ISBA/18/A/11)第16条第2款。,可以借此免除向管理局提供“保留区”的义务。此外,“保留区”在实践中有被发达国家侵占的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是鹦鹉螺矿业公司,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注册子公司,获得了开发“保留区”的权限。于是,制度构建本身就存在不足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在实践中就更难以实现其“利益均衡”的目标。
(二)新的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性海洋问题
两大原则的并立,部分根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区而治”的制度框架,而将海洋划分为诸多不同的区域带来了国际海洋法规则客观上的碎片化问题。[5]然而从自然属性上说,海洋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划区而治”的制度框架忽略了海洋这一自然属性,[14]给海洋的整体治理带来了阻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海洋的“整体性”认识不足,竞相制定有关海洋的各类规则,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施以后的国际海洋规则构建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15]这一冲突的存在导致新形势下出现的海洋环境治理、共同打击海盗、海洋生物资源维护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海洋问题都得不到系统化、根本性的解决。根源于“划区而治”制度框架的两大原则,在各自的领域依旧有积极作用,然而基于海洋一体化的自然属性,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海洋问题需要更高层面的、统一的制度安排和各国的通力协作,两大原则对此效力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大原则“非主权”和“共有物”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属性的“消极特性”。确立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非主权”基础,是为了阻止各国的主权要求,避免对公海利用和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无序争夺,而“共有物”的法律属性进一步明确了各国不得对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进行私占和独享。显然,无论是公海自由原则,还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都是对既有或可能阻止“自由或公平”需求之状况的否定性或防御性的制度设计,对于需要主动作为以共同应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海洋问题缺乏积极性的制度激励和理念引导。
(三)新的矛盾:自由与边界、公平与落实
公海自由原则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分别初步解决了“自由利用需求”与“海洋私占”以及“利益共享”与“国家实力不均”两对原始矛盾,各占“自由”与“公平”之两端。如前所述,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从具体制度构建到后续实践都受到了削弱。事实上,另一端的“公海自由”从确立至今,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新的国际制度,如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公海污染防治及资源养护制度,以及更复杂的国际事务,如安理会决议以及其他国家的立法和行动,都在不同程度上限缩了公海上的自由。[16]2017年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公海保护区”,更是进一步限缩了公海自由原则的行使范围。而且,在公海自由原则以自由为主要导向时,在法理上对自由内容的明确,反而未见得是对自由的扩展,[17]而是实质上的限缩,更不用说其中几项内容本身已有明确的限制。
之所以两大原则都面临被削弱的态势,本质上是因为,随着海洋利用与探索的深入,二者均面临着新的矛盾。一方面,部分国家有滥用公海自由的趋势,以及利用“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漏洞获取不当利益的做法。另一方面,各国竞相利用海洋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不管是公海还是国际海底区域,目前都存在制度“真空”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目前海洋治理遇到的新矛盾,在两大原则支撑下的国际海洋法面临两项任务:一是防范“自由”的滑坡侵蚀“自由”本身,二是主动作为以落实“公平”的要求。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海洋法规则的革新不是要推翻以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法体系,[18]“公海自由”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依然是国际海洋法的基础,也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海洋法规则的革新:一是要防范对既有理念和原则的不合理利用,二是要以更好的理念来应对既有原则无法妥善处理的问题。因此,新的理念一方面要契合海洋属性和顺应时代要求对既有规则进行突破,另一方面也要与两大原则在基础内涵上相承接。
进入五月,日军狂轰滥炸浙赣铁路,当时有列载着千余枚地雷的火车被疏散兰溪。六十三师得到消息岂可放过这些宝贝?几番交涉,千余枚地雷悉数收入囊中,也巧,六十三师各连排中有不少是军校十五期工兵科毕业的。得了宝贝的工兵将这批雷沿防御纵深配置,阵地前,马路上,树丛上,房屋里外处处布下了地雷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两大核心原则的继承与革新
(一)从分而治之到整体海洋观
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是通过界定九大海域并分而治之的路径来建构的。从结果来看,这一体系对海洋的分割产生了各国利用不同海域的不同权利内容,事实上,仍然是一种基于传统“海权”思维的制度体系,甚至仍然带有“马汉海权理论”的色彩,即以国家之间的斗争为主旋律,通过对海洋的控制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19](PP1~2)从这个角度出发,现行海洋法规则“分而治之”框架的依据其实是国家对不同海域的控制意愿、控制能力以及不同需求,而并非海洋的自然属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观”,[20]“海洋命运共同体”坚持“人类被海洋连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海洋观”。在“分而治之”的传统框架下,海洋是各国发展的重要资源,不同海域具有不同特性,各个国家和地区被海洋划分为不同地域,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整体海洋观”下,更应该认识到:(1)海洋是各国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交流的载体与纽带;[2](2)海洋具有一体化的自然属性;(3)各国依靠海洋连结成整体,人类与海洋也是一个整体。因此,各国不能只将海洋视为“资源”,还应将其视为连结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渠道,而渠道是不能“独占”的。首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更加强调各国对海洋的“权利”而适度弱化“权力”。其次,“分而治之”的现有体系对于明晰权利和加强海洋管理仍有重要作用,但必须认识到,海洋不同区域的划分是制度构建的结果,而海洋是一个天然的整体,各国对海洋的利用要充分考虑到海洋的这一自然属性,对于整体性和全球性海洋问题应主动担负起责任。最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海洋的连结下成为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应共同努力推动海洋维持长久的稳定和平。同时,人类与海洋也是一个整体,人类对海洋的利用应当是科学友好的,应当“关爱海洋,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20]
(二)从“非主权”的“共有物”到“平等”的“共商共建共享”
如前所述,“非主权”是两大原则的法理基础与制度起点,“共有物”是二者各自区域的法律属性与权利来源。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秉持“人类共有一个家园”,[20]倡导将深海、极地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20]可见,两大原则的基本理念仍然是“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遵循,两大原则当中“公共利益”的重要内涵也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深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非主权”还是“共有物”,都是对部分海域的概括性的、静态的认定,对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行动缺乏明确的、积极的指引,尤其当涉及需要各国通力协作以及自我克制的状况时,现有原则往往很难发挥积极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非主权”的“消极认定”转向更具实际意义的“平等”,从“共有”的静态属性,转向“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行动指引。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非主权”仅仅阻止了各国对海洋的无序争夺,无法防范各国对“自由”的滥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相互尊重,“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20]在尊重的基础上平等地开发和利用海洋,而非罔顾他国利益,滥用所谓“海洋自由”。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奉行“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的相处态度。[2]“共商”不仅是应对具有“整体性”与“共有性”的广阔海域公共问题的基本要求,也是处理争议、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友好态度。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根本路径。[20]海洋不能被独占,而海洋的治理也不是单个或部分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人类长久地利用和开发海洋以促进人类发展的前提是共同建立“可持续”的体制机制,共同建设“污染有效防治、生物多样性合理维护、资源有序开发”的海洋生态,[2]在完善的体制机制与和谐的生态之下,全人类平等地共享海洋的利益。
(三)从单一价值观到“共同命运观”
两大原则价值取向上的相反相成,既反映了海洋法本身的复杂情况,也揭示了海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现实困境。因此,要确保“公平”的实现,必须促进各国主动作为,明确国际社会在海洋治理中的新定位,通过新的价值目标引领海洋的综合治理。
1.新的定位: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的有机统一,[21]超越了两大原则狭隘的现实利用需求,认识到了权利与责任的并存。各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是海洋的权利主体,也是海洋的责任主体,这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对国际社会的新定位,也是以国家利益为起点、开展零和博弈的传统地缘政治向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地缘政治转变过程下的新趋势。[22]“责任共同体”首先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享有权利的同时要承担各自应尽的职责,包括既有国际海洋规则下的明确职责,也包括道义上的责任或政治上的责任。[23](P200)其次,基于对海洋共有性和整体性的认识,国际社会对海洋的责任是“共同的”,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应“加强海上对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2]同时,“共同”还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应互帮互助,“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20]各国应重新认识和调整各自在海洋利用与治理中的角色,意识到海洋的风险防范与问题应对是更好地、可持续地利用海洋的必然要求,面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全球性海洋问题,不能被动地等待责任分配,而要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合理利用、污染防治、资源养护、打击海盗、海平面上升应对等共同责任。
2.新的目标:安全、繁荣、可持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要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要摒弃以往“权力争夺、追逐私益、重利用轻治理”的狭隘观念,在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中心的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下,追求在维持海洋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共同繁荣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和平”的目的已然包含在了两大原则之中,但对于海洋而言,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的必要条件,但却不足以构成安全的充分条件。在新形势下,海洋安全的实现需要各国在面对诸如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时共同合作、积极应对。海洋的长久安全是海洋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新形势下的海洋治理不能仅仅追求和平,各个国家和地区还要在意识到责任主体身份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行动来共同保障海洋安全。
“共同繁荣”的目标有别于传统的“追逐私益”,其首先强调的是“共同”,“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20]作为“共有物”的海洋不能只服务于部分国家,而是要服务于全体人类,中国也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20]进一步来说,共同“繁荣”不仅包含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也蕴含着海洋利用与开发蓬勃进行、海洋文化交相辉映的美好愿景。[2]
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目标,《二十一世纪议程》也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落实该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可持续发展内容是我国落实上述要求的实质理论贡献,其理论基础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的“整体自然(海洋)观”,[20]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又进一步发展出“关爱海洋”的海洋生态观,[5]以及“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的时代担当。[2]
3.新的作为:问题应对、海军职责、争端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观念上的革新,更是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切实的行动路径,这是其区别于现有原则的根本之处。从最初对海洋自由航行和海上自由贸易的现实需求,到现今“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捉襟见肘”,[24]海洋问题层出不穷的现实困境表明,单一的价值取向永远无法应对国际海洋治理的复杂情况,新形势下必须有新的作为,要从“自由”走向“治理”,[16]从“公平”走向“落实”。
在问题应对方面,“海洋的很多问题跨越了国家和地区,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25]因此合作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合作的基础仍然是对海洋整体性以及自身责任主体身份的认知,通过增进互信、加强交流,从相互竞争转变为相互依存,从独立追求利益发展到合作追求利益,[26]进而追求超越单个国家利益的人类共同利益。[27]目前海洋问题频发的一大原因是海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以及使用不合理,其中以供给不足为甚。[28]“海洋命运共同体”号召国际社会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增加海上公共产品的供给,[2]“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9]
在海军职责方面,海军活动是长期以来引起海洋争端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以所谓“海洋自由”为借口,长期利用军舰干扰他国正常海洋管理,破坏地区安全。而“海洋命运共同体”对海军进行了新的角色定位:维护海洋和平安宁的“坚强盾牌”、加强交流合作的“和平方舟”和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生命之船”,[30]由此,海军从制造冲突的因素变成了解决问题、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
在争端解决方面,要秉持“海洋是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的基本理念,[20]尽量避免和减少冲突的发生。“海洋命运共同体”号召各国协商、沟通、合作以推动涉海分歧的妥善解决。[2]以上内容与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一脉相承,尤其是其中“和谐海洋”的理念以及“搁置争议”的开放型海洋政策,对于海洋争端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海洋争端往往涉及国家的主权、资源等核心利益,从现实来看,争端的彻底解决并非易事。因此,在面对重大和敏感问题时,各方应以海洋的稳定与整体和谐为底线,保持冷静、坚守和平,避免采取使局势升级的行动,[32]从而使国际社会能够在和平安全的环境下利用海洋来促进自身发展和共同繁荣。
总之,目前以公海自由以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为中心,从现实需求与规制要求出发的国际海洋规则体系,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都很难适应现今国际海洋治理的新需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包括海洋法在内的现行国际法基本原则,既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又将我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明了国际社会发展的终极问题——人类的命运,[33]既顺应了20世纪以来国际法人本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基本精神的发扬。在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海洋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大有可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与国际海洋的繁荣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下更是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