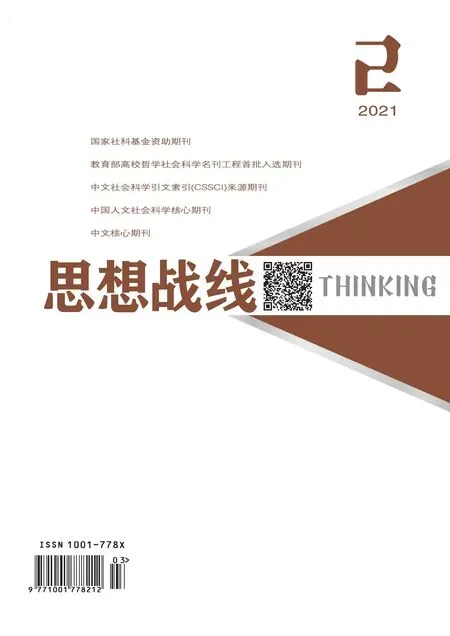神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
——以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为例
李世武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多民族神话、史诗的交流、互鉴。扬·阿斯曼说:“在希腊,荷马史诗传承的过程就是希腊民族形成的过程,正如《托拉》的传承与以色列民族的诞生同时,因为文本的确立与民族同属感的增强相辅相成。”(1)[德]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3页。可以说,中华史诗艺术传统的发生、发展,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华史诗艺术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史诗艺术之林中的一座丰碑。中国史诗艺术研究界拥有足够的本土资源,应该形成跨族际比较诗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推动中华史诗艺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彝族史诗绝不是一座封闭的文化孤岛,而是彝族先民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见证。彝语中部方言区的口传史诗“梅葛”、《教路经·南华彝族口碑文献:彝、汉》和南部方言区的彝文史诗《查姆》《降始史书》《乃古造天地》《尼苏史诗》等史诗歌本中,出现了多篇关于“月中有树”的神话叙事。(2)据笔者的调查研究,史诗“梅葛”是彝语中部方言区部分彝族罗罗颇和里颇民众共享的口头诗歌传统“梅葛”中的唱史类传统,而不是一部固定的史诗。这是一种典型的活态口传史诗,形成了多种异文。《查姆》《降始史书》《乃古造天地》《尼苏史诗》为彝语南部方言区毕摩在口传史诗基础上以彝文写成的史诗文本。彝语口头史诗文本与彝文史诗文本不可一概而论。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可分为“月中不死药”与“月中世界树”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指向令逝者死而复生的范畴,由祭司在为亡灵教路的口传经典中吟唱,发挥以不死药获取与遗失的神话慰藉亲属的功能。此语境中,不死树即不死药。第二种类型指向月中之树为宇宙万物之源或确保宇宙生生不息的神树。
第一种类型,牵涉到不死药神话的研究。古巴比伦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叙述了古老的不死药神话。英雄吉尔伽美什历经磨难后获取不死之仙草,不料在冷泉水中净身洗澡时,水中的一条蛇闻到仙草的香气,游出来叼走了仙草。“他回来一看,这里只有蛇蜕的皮,于是,吉尔伽美什坐下来悲恸号啕,满脸泪水滔滔。”(3)《吉尔伽美什:巴比伦史诗与神话》,赵乐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87页。弗雷泽对死亡神话的研究,以援引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材料并进行分类见长。他对《圣经·创世纪》中的生命树和死亡树,以及广见于世界各地的错传消息和蜕皮的神话皆有论及。他指出,原始人中的哲学家用这些神话来解释人类丧失永生之恩惠的缘由。(4)[英]詹姆斯·G.弗雷泽:《人类的堕落》,载[美]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118页。我国昆仑神话与海上神话,均涉及不死药神话。对此,袁珂先生已进行过详细的考证。他指出,《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诸巫操不死药救活窫窳的文本,是汉文古籍中记载不死药的较早文本。(5)袁 珂:《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第21页。袁珂先生还贯通《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等古籍,梳理出不死药得而复失的神话:英雄羿历尽艰辛,登上昆仑山顶,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遗憾的是羿之妻嫦娥受巫师有黄的蛊惑,独自偷吃不死药,奔入月宫。(6)袁 珂:《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第219~221页。海上神山不死药的神话,亦由袁珂先生系统考证过。如东海祖洲上的不死草、东海扶桑岛扶桑树上结出的不死桑葚,徐福为秦始皇出海求不死药的神话等,均得到详细梳理。(7)袁 珂:《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第479~481页。有学者归纳出羿神话和吉尔伽美什史诗所共有的原型母题,即都包括“主人公探求不死药的旅行”这一母题,并指出这是一个重现频率极高的世界性文学母题。(8)叶舒宪:《日出扶桑:中国上古英雄史诗发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彝语中部方言区史诗传统中吟唱的古代毕圣探求不死药的神话,显然为此母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第二种类型,牵涉世界树(world tree)的研究。伊利亚德分析了中亚和北亚世界树主题在萨满教意识形态和体验中的作用。世界树象征着处于不断再生状态中的宇宙、永不枯竭的宇宙生命的源泉以及天空或现世的天堂。(9)[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段满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9~271页。据《世界创世神话百科全书》的记载,世界树神话广泛分布于多种民族中。在印尼北部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人神话中,创世神变化出上界、中界和下界三位一体的世界,而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由一棵被称为世界中心的世界树所代表,这棵树连接了三界。世界树上一只鸟下的蛋中出现了分别统治三界的三位一体的三位神灵。(10)David A.Leeming,Creation Myths of the World:An Encyclopedia,California:ABC-CLIO,LLC,2010,p.66.吉尔伯特岛民神话叙述道:神灵纳罗杀死父亲,从其眼睛中挖出太阳和月亮,并将其脊椎骨竖立在萨摩亚岛上,创造了世界树。(11)David A.Leeming,Creation Myths of the World:An Encyclopedia,California:ABC-CLIO,LLC,2010,pp.112~113.内兹佩尔塞人相信,天地与世界树相连,世界树是世界之轴。(12)David A.Leeming,Creation Myths of the World:An Encyclopedia,California:ABC-CLIO,LLC,2010,p.206.奥尔梅克创世神话中涉及一棵世界树。(13)David A.Leeming,Creation Myths of the World:An Encyclopedia,California:ABC-CLIO,LLC,2010,p.215.世界树在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通常具有世界之轴(axis mundi)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树或其他垂直的物体,是关于世界中心的一种普遍存在的象征符号,它们作为宇宙之轴或世界之轴而存在。正是这个轴,把受造之物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可以说,它代表着创世者的力量,或者是受造之物或宇宙本身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与混沌截然相反。”(14)David A.Leeming,Creation Myths of the World:An Encyclopedia,California:ABC-CLIO,LLC,2010,p.307.彝族史诗中“月中世界树”神话的研究,为全球世界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通过对不死药神话与世界树神话研究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可归纳出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研究的问题意识。第一,此项研究旨在揭示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独特性。以罗列世界各地神话材料为特征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对具体神话传统的深入阐释。弗雷泽、伊利亚德等进行跨文化神话比较研究的学者,对这些神话的共性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此种研究往往脱离文化环境,因此产生了相应的弊端,即忽视了具体的区域性。有学者指出:“从弗雷泽所处时代以来,对于死亡神话的起源的多方面研究已初具规模。结果没有一种类型是人类共同的,相反,每个文化/地理区域都有具有自身特点的类型。”(15)[美]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页。第二,此项研究旨在揭示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复杂成因。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形成,并不是单向传播的结果,它与地方文化生态环境,与我国昆仑神话、海上神话等神话体系提供的语境,与佛经传入和彝族毕圣的创造皆有关联。第三,此项研究旨在深度阐释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功能。我国多民族神话、史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独特作用的研究、原住民传统深层生态智慧的研究、民族艺术心理治疗功能的研究,均是时代的前沿课题,亦与本文的研究直接相关。经梳理学术史,笔者发现,从这三个角度系统地展开论述的研究成果尚未可见。本文以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为例,分析此神话的类型,对其母题进行考源,论述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以期推动神话等艺术事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作用的研究向前发展。
一、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类型
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可分为“月中不死药”和“月中世界树”两种类型。
(一)“月中不死药”型
此种类型,主要见于中部方言区罗罗颇、里颇祭司在丧葬仪式中为亡灵吟唱的“教路经”(即“赤梅葛”或“阿毕梅葛”)中。(16)学术界一般将彝族祭司统称为毕摩。实际上,不同彝族支系中对祭司的称谓不尽相同。李申呼颇讲述本提供的一则不死药叙事,叙述了祭司奇遇不死药与遗失不死药的失落神话。此神话文本的情节单元是:1.朵觋与儿子、儿媳讨饭为生;2.儿子患麻风病,遭儿媳嫌弃后离婚;3.儿子捕食母巨蟒;4.公巨蟒乞求他食蛇肉但留下蛇骨;5.儿子食用蛇肉后痊愈并与儿媳复婚;6.朵觋受天王邀请上天祭送鬼神;7.儿子目睹公巨蟒以不死药救活母巨蟒的过程并获得不死药的秘密;8.朵觋采集不死药装在柜中;9.儿子死亡;10.不死药为日月所窃取;11.朵觋将残余的药水倒入火塘中,幻化出小娃娃;12.朵觋诅咒天狗向日月复仇,天空中产生了天狗吃日月的现象。(17)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59年,第125~128页。
至今,中部方言区的祭司仍然在丧葬仪式中吟唱这一神话。云南省姚安县左门乡祭司鲁德金现场演述本中,呈现了不死药神话的另一种异文。对鲁德金演述本中不死药神话的母题进行梳理,可得以下条目:1.阿细呗蒻(古代大祭司)罹患麻风病;2.妻子与阿细呗蒻分家;3.阿细呗蒻离群索居,离家入森林,以捕猎为生;4.阿细呗蒻捕食巨蟒,在观察公巨蟒复活母巨蟒的过程中获知不死药的奥秘,并因食用蛇肉而痊愈;5.阿细呗蒻重返世俗界,救治生命,令生命起死回生,并与妻子复婚;6.妻子因好奇打开柜子,不死药由日月所窃,阿细呗蒻失去不死药;7.阿细呗蒻再寻不死药,未果,死亡无可避免。(18)史诗演述者:鲁德金,罗罗颇,1954年生,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左门乡左门村委会干海一组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查者:笔者。访谈时间:2016年12月。访谈地点:官屯乡自家村。
流传在与姚安县毗邻的南华县罗罗颇社区中的“教路经”之“不逝药”一章,叙述了另一异文。此异文的情节单元是:1.阿哥在田房中躲避麻风病;2.妻子捕母巨蟒,用蛇肉治愈了麻风病人;3.阿哥在观察公巨蟒救治母巨蟒的过程中获得不死药的奥秘,并采集了不死药;4.月亮悄悄偷走了一棵不死药;5.不死药为三棵:阿哥一棵、苍山一棵、月亮一棵;6.阿哥的独儿子死亡;7.阿妹为独儿子举行火葬;8.阿哥为儿子烧不死药;9.因儿子的尸骨已经被火烧掉一半,所以阿哥所烧的不死药无法救活儿子。更为遗憾的是,为了救活儿子,不死药已经被烧毁,世间再无不死药,死亡不可避免。(19)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路经·南华彝族口碑文献:彝、汉》,罗有俊,自文清翻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29~130页。
祭司在罗罗颇社区中传唱的不死药神话异文,皆指向“神职人员从巨蟒处获知不死药的奥秘,后来月亮偷走不死药”的母题。也就说,“月中不死药”已经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神话叙事。尽管鲁德金将不死药解释为牡丹树,但据笔者在当地彝区的调查,这棵不死树的树名,更为流行的解释是娑罗树。史诗歌手们普遍讲述,羊死后之所以不闭眼,其原因在于世间之草均已吃过,但永远无法吃到月亮中的娑罗树叶。
(二)“月中世界树”型
此类型在中部方言区和南部方言区均有传唱。在李申呼颇本中,月中梭罗树是创世之树,亦即世界树。其一,梭罗树的树叶化为大地;其二,梭罗树根部出现的野猪和大象是缩地的神兽;其三,梭罗树的果实是花草树木的种源;其四,梭罗树根是鸟兽、昆虫和农作物之源;其五,梭罗树是永生不死之树。(20)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59年,22~27页。
《查姆》叙述的人类进化史中,儒黄炸大帝欲以旱灾毁灭伦理堕落的独眼人,用葫芦收回水源,天上多珠树、地上怒嫩树、海中于乃树缺水而死。儒黄炸大帝同时收回人间不死药的药种。灭绝人种、更换人种的旱灾降临。据译者注释,多珠树是天上令日月发光的光源之树;怒嫩树是大地上令万物生长、人类生育繁衍的生长之树;于乃树是海中水源之树。(21)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87~92页。《查姆》中有天宫玉兔之说。《查姆》云,大洪水泛滥之时,众神派出一只天宫白玉兔,打开东、南、西、北四方的水门,以泄洪水。(22)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查姆》明确叙述的月中之树,是一棵千年不死、万年不亡的垛槠树。(23)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697页。关于日月不死源于不死药的情节是:古帝王孟诺的下属罗洪爷爷制成药方后入天宫,传授给更兹天神,再由更兹天神传授给日月。(24)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757页。月中树为垛槠树,仅是一种类型,《查姆》还记载了太阳之树仵和月亮之树侏。“太阳叫做仵,月亮叫做侏。仵侏亮堂堂,天地晴朗朗。”(25)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759页。在神话诗人的宇宙观中,宇宙光源就是树本身。从古代天文学来看,日中有树,应类推自月中有树。月亮发出冷光,且月中树影为肉眼可见。《查姆》比较完整地叙述了世界树的知识谱系。“天空垛槠树,海中水莲花,地上红绿树,仵树和侏树,不栽此四树,世人会绝种。”(26)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025页。按照文本中的叙述,各种神树之间形成了树名相异而功能一致的关系。
《查姆》诸神话所记之神树,论及在宇宙中的地位,仍以垛槠树为上。垛槠树是创世之初天神共工管辖的大山中生长的世界树。此树为日、月所生之地,为万物生命之源。垛槠树上,生出了整个宇宙。凡举天地、日月、粮种、树种、人种,均为垛槠树所生。垛槠树之大,无有能及。树之白为蓝天,树之黑为大地。它生长出日月花、星云果,生出时间,即年、月、日、时。垛槠树在千层天空中伸出的四只手,手中的四片叶,开出四朵花,这四朵花,是金太阳和明月亮。“那四朵天花,日看像金阳,夜看像明月。百年花不落,千年花鲜艳,万年花灿烂。”(27)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045页。史诗云,此树是山茶木种,表明史诗歌手构想的树种现实原型是山茶花树。垛槠树与山茶花树同种,在根、茎、叶、花等方面外形类似,又是在生命力上超越于现实中的山茶花树的世界树。龙庭金阿玛的时代,金儿郎撒下九千种,种出这棵树。垛槠树之后,诗人还提到仵侏树,仵侏树是阿普笃慕时代粮食和水的来源。(28)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044~1046页。
彝文史诗《降始史书》记载,天地分开之后,龙王珑阿玛分封的龙君王掌管日月,住在月宫中,并在月宫中植下了柏树和檞树。此二树的枝叶伸向四方,树影明朗朗,可知诗人有月亮发光、显现出树影的观念。月中树一枝四片页,四叶四朵花,与《查姆》对垛槠树的叶与花之描述同源。柏树和檞树根生月宫,枝条却伸至地面,绿叶中开出红花,供彝族先祖笃慕乘凉。这两棵神树,是永不枯萎的宇宙生命之树,是世间红花遍地、山川秀丽、生机勃勃的源泉。另一处可与彝族其他史诗传统相比较的情节是,柏檞之树,名为两棵树,其实是同一棵树的一体两面。这与《查姆》中的仵侏一致。“天空柏檞树,白天开金花,夜晚开银花,金花化作日,银花变作月,金阳照大地,皓月洒人间,千千万生命,万万千生灵,阳光普照下,人声传天上,遍地声嘈嘈。”(29)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柏檞之树,为一体两面的树,它在昼夜之间分别开出的金花和银花,成为太阳和月亮之光芒的显现,滋养了宇宙中的生命。太阳和月亮的光芒,就是月宫之树在昼夜之间分别开出的金花和银花。出于对柏檞之树的崇拜,出于对生命之源的崇拜,彝族人形成了冬月十五日采集果树,祭祀树神的习俗。这一习俗发展成为木神节。诗人劝诫世人严禁砍伐古木,严禁放火烧山,以免招致生灵涂炭、自身遭殃的惩罚。“不为别的事,石是山筋脉,树是山血脉,树叶是山衣。山中积霜雪,冰雪化龙泉,木秀显山威,林茂村庄秀。”(30)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诗人还表达了他从自然中体悟到的生态美学思想。柏檞之树,是世间树种、粮种的来源。龙王珑阿玛在月中九重高山上的柏树、檞树之下,取来树种和粮种,令大地树木遍野,山花遍地,谷物丰收。(31)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珑阿玛与天君更兹的对话,也表明月宫之柏檞树,是赤色大地上草木、花卉之源。(32)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降始史书》已有月中柏檞树之说,却又出现了娑罗树的神话。史诗云:“笃慕六只手,伸手可触天,能浇娑罗树。”(33)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译者注释称:“娑罗树:常绿乔木。相传月宫中有棵娑罗树,据说人在地上看月亮时,月亮正中的阴影斑点就是此树。”(34)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可见“月中娑罗树”的神话,应是《降始史书》之“月中有树”神话的原生母题。
彝文史诗《乃古造天地》所叙述的“月宫有树”神话,神树之名为十二属相树。神话云,姐姐俄玛与弟弟俄龙为躲避洪水,骑鱼游月宫,见到皓月清宫之中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大树共分十二杈,依次生长着鼠头、牛头、虎头、兔头、龙头、蛇头、马头、羊头、猴头、鸡头、狗头和猪头。这是记月之始。每杈树枝上,生长三十叶,计算为一月三十天之数。一年十二月,合计三百六十天,是为一周年。此为纪年之始。(35)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这一神话类型,由树杈、树枝和树叶,类推到十二属相记月法和日、月、年历法的发明,叙事生动,表达了树与生命周期的内在联系。《尼苏史诗》记载了避洪水的姐姐俄玛与弟弟俄倮骑鱼游月宫,见到月宫树的奇景,其树也在十二杈上依次长着十二属相的头。姐弟俩约定,若大难不死,将以十二树杈记年,以一杈十二支记月,以一枝三十叶记日。年、月、日的计算之法,始于此。(36)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尼苏史诗:彝、汉》,龙倮贵,潘林宏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7~48页。十二属相指向时间,也在世界树的范畴之内。
上文考察了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两种类型,即“月中不死药”与“月中世界树”。那么,彝族“月中有树”神话之母题成因为何?
二、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成因
彝族“月中有树”神话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现实经验与本土知识提供的文化生态环境
彝语中部方言区和南部方言区的彝族世居之地,植被丰富,古树名木众多,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彝族“月中有树”神话的创编提供了现实基础。“赤梅葛”中,歌手由“蛇蜕皮→不死→麻风病人蜕皮→不死→蛇掌管不死药的奥秘→人类获知不死药→人类遗失不死药”的叙述逻辑展开的神圣叙事,以对蛇蜕皮现象和麻风病的认知为基础。歌手和受众对“月中有树”神话母题的接受,也离不开人们仰望月空时在月中阴影与树影之间进行类推的经验。月中之树的树名,可以是垛槠树(山茶花树种)、仵侏树、柏檞树,但都离不开神话诗人对现实中树木属性,比如根、茎、叶、花的体认和理解。据笔者调查,活形态史诗“梅葛”的最后流传区域之一的云南省姚安县左门乡的罗罗颇民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在呗玛的带领下,聚在神树下举行祭天仪式。呗玛在仪式中,插象征创世神灵的神枝,诵唱创世史诗。祭天神树是典型的世界树。呗玛通过世界树与诸神沟通,祈求诸神庇护宇宙众生。左门乡至今保存着一片原始森林,其中幸存了不少高耸入云的古树名木。古树的存在,为世界树崇拜提供生态基础,激发了呗玛创编世界树神话的灵感。
(二)在外来文本的基础上创造或融合本民族固有文本与外来文本
第一,我国昆仑神话、海上神话中的不死药母题与彝族史诗中“月中不死药”母题间的渊源关系。不死药、不死树的记载,广见于《山海经》《列子》《淮南子》《博物志》《十洲记》等汉文古籍中。无论是陆地上的昆仑神话、还是海上蓬莱、瀛洲、扶桑等诸岛的神话,都广泛涉及不死药神话。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不死药神话与传说,为“月中不死药”神话的产生提供了传统语境。
彝族史诗中的不死药神话叙事表现出几种内在观念。一是蛇掌握不死药的奥秘。在目前可识的两种异文中,均是公蛇以不死药令母蛇死而复生。《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记诸巫之所以“皆操不死药以距之”,实际上是在举行巫、医结合的治疗仪式。治疗的对象——窫窳为二负臣所杀,仅剩尸体,而窫窳的体貌是“蛇身人面”。(37)袁 珂:《〈山海经〉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206页。此则医疗神话叙事的原型,与蛇类冬眠、蜕皮的不死信仰有关。将不死与蛇联系在一起,是远古人类普遍的观念。(38)叶舒宪:《日出扶桑:中国上古英雄史诗发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二是日月取走(偷窃或收回)不死药。在彝族史诗中,为朵觋的儿媳或阿细呗蒻的妻子无意中打开储藏不死药的器物,日月抢走或偷走了不死药。史诗中主人公失去不死药的神圣叙事,与羿失去不死药的神圣叙事非常相似。(3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 逸,乔 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7页。姚安县官屯乡磨盘箐村罗罗颇呗玛骆相福,至今仍在丧葬仪式中诵唱的创世史诗“赤梅葛”,即包含后纪射日的神话。“后纪”,应是中华上古射日英雄“羿”在彝族支系罗罗颇语言中的表达方式。(40)讲述人:骆象福,罗罗颇,1962年生,姚安县官屯镇黄泥塘村委会磨盘箐村人,呗玛,师承骆有品、骆庭才。访谈人:笔者。访谈时间:2020年3月7日。访谈地点:磨盘箐。
据学者对中国上古英雄史诗的重构,在羿神话的原始面貌中,有羿探求不死、经历仪式性的死亡与复活、得到不死药、失去不死药的母题。(41)叶舒宪:《日出扶桑:中国上古英雄史诗发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彝族史诗中的朵觋之子或阿细呗蒻,都经历了类似的旅程。彝族史诗中无意中打开珍藏不死药器物的人乃是祭司的妻子。彝族史诗中取走不死药的不仅有月亮,还有太阳。罗罗颇信众坚信不死药为月亮所取走,这一观念表现在婚礼仪式中。婚礼中,仪式专家在宰杀山羊祭祀众神后,为了以行动实践史诗观念,他们将羊头和羊蹄子堆放在祭坛上,并在羊口中塞入青松针,以象征羊并未死亡。(42)史诗演述者:鲁德金,罗罗颇,1954年生,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左门乡左门村委会干海一组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查者:笔者。访谈时间:2016年12月。访谈地点:官屯乡自家村。
李申呼颇本中,天狗追讨不死药导致日食和月食的母题,则源于天狗食月的传说。据学者考证,天狗食日、月的传说,在明代开始广泛流传,并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引起了社会恐慌。(43)刘泰廷:《御凶、飞天与吞月:中国古代的天狗异兽》,《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李申呼颇本中天狗食日、月的母题,进入“赤梅葛”中不死药神话叙事的时间可能比较晚,甚至有可能在明代以后才进入。
世世代代的史诗歌手往往主动吸收外来的观念和文本,以丰富所属民族的史诗传统。彝族史诗绝不是一座文化孤岛,而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后形成的古典艺术。彝语中部方言区的“月中不死药”神话,尽管有不死药为牡丹树的异文存在,但更普遍的观点是:月中不死药即娑罗树。娑罗树在一些歌本中,还被视为世界树。李申呼颇本明确将娑罗树作为月中世界树。南部方言区的《降始史书》中记载:笃慕能浇娑罗树。(44)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彝族创世史诗:彝、汉》,普璋开,普梅笑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查姆》中虽然未见娑罗树的记载,却出现了天宫白玉兔开天门泄洪水的叙述,这是受汉语文献所记月宫神话之月中玉兔情节影响的印迹。(45)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
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彝族史诗歌手在“月中桂树”“月中娑罗树”等神话文本传入相关方言区之前,早已在原创意义上创编出属于本民族的“月中有树”神话文本。比如,垛槠树(山茶花树种)、仵侏树、柏檞树等树名,以及相关情节与汉文献所见文本的差异,都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支持。也就是说,目前彝族史诗中所见的“月中有树”神话,可能是文化交流后产生的一种融合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综合文本。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于是,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文本的形成就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是在直接借取的基础上创造;第二是在融合固有文本和外来文本的基础上创造。
第二,佛经的传入与汉族、彝族“月中有树”神话的演变。梭罗树在彝族史诗“赤梅葛”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此树叶可化土成地,果可繁衍出花草树木和粮食,树根则是飞鸟、动物和爬虫的母体,梭罗树还是不死树。梭罗树集世界树、生命树和不死树为一体。
梭罗树崇拜,绝非彝族史诗中独有。梭罗树,又名娑罗树,本是印度佛教中的圣树,随佛教传入我国。原始佛教典籍《长阿含经》记载的婆罗树,又译为娑罗树。(46)《长阿含经》,恒 强校注,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6页。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教典籍中,多次提到此树。例如,《阿弥陀经》记载有“娑罗树王佛”。(47)大 祐等:《阿弥陀经注疏》,张景岗点校,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第271页。《妙法莲华经》载:“此王于我法中作比丘,精勤修习,助佛道法,当得作佛,号娑罗树王,国名大光,劫名大高王。其娑罗树王佛有无量菩萨众及无量声闻,其国平正,功德如是。”(48)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李海波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2页。《大般涅槃经》中亦多次提及娑罗树。(49)参见姜子夫《大般涅槃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
“月中娑罗树”代替“月中桂树”并产生新的信仰形态的时间,大致在唐宋时期。《太平御览》引《淮南子》中记载“月中有桂树”,(50)李 昉:《太平御览》第八卷,夏剑钦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75页。西汉后期壁画墓卜千秋墓,(51)贺西林:《洛阳卜千秋墓墓室壁画的再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四川成都简阳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石,(52)俞伟超:《中国画像石全集》第7卷,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79页。四川成都彭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砖等,(53)杨絮飞:《中国汉画图像经典赏析》,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均对“月中桂树”神话有图像表现。
北周庾信在《周大将军赵公墓志铭》中写道:“岁在琱车,年方竹马。月中桂树,切问能训;石上木生,悬思即悟。”(54)庾 信:《〈庾子山集〉注》,倪 璠注,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13页。清代学者倪璠引《酉阳杂俎》辑录的月中有桂、蟾蜍,以及石上生木的神话来注解此句中的月亮神话。东晋著名天文学家虞喜撰写的《安天论》中,引用了俗传月中有仙人和桂树的神话。(55)徐 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页。实际上,桂树在道教中乃长生不死之树。葛洪在《抱朴子》中写道:“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沥合饵之,亦可以先知君脑,或云龟,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也。”(56)王 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淮南子·览冥训》中所记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而高诱所注羿之妻窃不死药而奔月的神话,并未言明不死药为何物。在神话思维中,月中桂树早已成为不死之树。
唐代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中,涉及月亮的神树有桂树、阎扶树和娑罗树。据《酉阳杂俎·天咫》所记,至迟在唐代,佛教中须弥山南阎扶树之影投入行过的月亮中,造成月中有影的神话,已经在我国流传。(57)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页。段成式所引的释书,不知为何名。阎扶树,又名阎浮提树、阎浮树或阎浮提。据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阎浮树之影入月为月影的神话,在《因本经》和《长阿含经》《楼炭经》中均有记载。(58)俞正燮:《癸巳存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长阿含经》曰:“复以何缘月有黑影?以阎浮树影在于月中,故月有影。”(59)《长阿含经》,恒 强校注,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462页。月中有桂树、蟾蜍,从汉代墓室画像可知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神话。佛经称月中阴影为阎浮树之影所入,而中国本土产生的“月中有桂树”神话,则是树在月中。两则神话文本既表现了中国、印度文明中神话思维的类似性,同时也表现出具体情节的差异性。
唐代李邕所作《娑罗树碑记》称娑罗树“恶禽不集,凡草不庇,东瘁则青郊苦而岁不稔,西茂则白藏泰而秋有成”。(60)郎 瑛:《七修类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酉阳杂俎》记载的关于娑罗树的神话叙事,提供了“月中娑罗树”神话产生的线索。(61)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页。此则神话叙事有两点值得留意。第一,巴陵佛寺中的神树娑罗树与月中桂树均是不死之树。月中桂树“树创随合”,寺中娑罗树“随伐随长”;第二,娑罗树之繁盛,可与月中桂树相媲美,即能“邻月中之丹桂”。(62)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页。唐代,是佛道争鸣最为激烈的时期。佛道论争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创新。娑罗树为域外佛教神树,中国则有扶桑、桂树、建木等神树,两国神话叙事拥有深层相通的神树崇拜传统。印度佛教界的阎浮树影入月成月中阴影的月宫神话,与中国本土既有的桂树生月中神话母题相近,具有可以彼此交流的潜在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佛教神树娑罗树“进入”月宫,成为与月中桂树并存的神话叙事,也就在情理之中。
月中娑罗树的神话,在宋代已经广为流传。欧阳修曾写道:“伊洛多奇木,娑罗旧得名。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生。”(63)郎 瑛:《七修类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洪迈在《夷坚志》之“娑罗树子”条中写道:“吴中人每于秋夜得虚空所坠木实,以为娑罗树子,曰是月中桂子也。天竺山尤多,然莫能明为何品树。”(64)洪 迈:《夷坚志》,何 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48页。洪迈还转述林子长在树子坠落时搜集娑罗树的果实,并令园吏种植,春天发芽,却为皂荚树的趣事。足见宋代吴中已经有将娑罗树等同于月桂树,并加以膜拜的传统。宋代诗人毛珝所作诗歌《邀月》,亦是宋代娑罗树代替月中桂树为月宫神树之名的表现。(65)曹庭栋:《宋百家诗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39页。
经过神话诗人的创编,月宫已经成为寄托不死之愿的圣地。而在神话交流过程中逐步代替桂树之名而入月宫的娑罗树,亦成为不死树,成为信众祈愿不病不死的神树。从古至今,有多少受病痛折磨和眷恋生命的信众,如元代诗人袁桷那样仰望月空,恨不能有天梯相助,入月宫采集不死药。(66)袁 桷:《清容居士集》,王 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6页。元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杂剧》唱词说:“驾青牛后走到东海边。灵芝草、长生草二三万岁;娑罗树、扶桑树八九千年。”(67)臧懋循:《元曲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明代学者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卷二十三中记载东乡县:“西北四十里崖壁间悬二石,左类日,右类月。月中空隙有娑罗树一株。”(68)曹学佺:《蜀中广记》(外六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7页。当地人对月中娑罗树的崇拜,已经投射到对乡土自然景观的神话想象中。此外,著名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均将月中娑罗树的神话加以借取,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进一步发挥。吴承恩在《西游记》第八十一回中描写妖怪现身前妖风的强劲时写道,嫦娥承受不住妖风,难以站稳,只能抱住梭罗树来稳定仙体;药盆被吹得失去踪影,玉兔只能慌张去寻找。(69)吴承恩:《西游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927页。吴承恩将月宫受妖风狂吹后一片混乱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许仲琳在《封神演义》第六十六回中,描写心存怨恨的殷郊赶往鹿台时所起的大风之强劲的诗歌云:“只刮得嫦娥抱定梭罗树,空中仙子怎腾云。”(70)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635页。康熙皇帝曾经作诗称赞北京潭柘寺中的娑罗树:“娑罗珍木不易得,此树惟应月中植。”(71)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95页。
第三,彝族诗人以诗歌追溯本源,在借取或融合的基础上,积极创编出丰富的情节,促进了彝族“月中有树”神话特质的形成。彝族自古具有追本溯源,并以诗歌的形式传唱历史的传统。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彝族诗人并未纹丝不动地接受外来的神话,而是积极创编,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死而复生的生命,上天追讨不死药的祭司,生长出天地万物的世界树,树杈上长着十二属相之头的世界树等神话意象,都离不开诗人的艺术创造。彝族“月中有树”神话尽管受到中华文化中“月中桂树”及“月中娑罗树”神话的影响,却在神话叙事方面别出心裁,创造出了独具特质的意象,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月中有树”神话。在“月中不死药”神话中,产生了祭司——即史诗歌手从巨蟒处获知不死药奥秘得以救世,却又失去不死药的母题,形成与嫦娥窃不死药而奔月交相辉映的神话叙事。在“月中世界树”神话中,娑罗树成为宇宙之源、生命之本,赋予了月中神树至高无上的地位,创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树状”宇宙结构和瑰丽多姿的神话意象。从树名、树的形状到树的功能,歌手在神话创编艺术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月中之树为世界树、日月之光为两树一体的月中之树在昼夜中开出的花朵,以及月中属相树等,都是彝族诗人在艺术上的创新表现。
一个社会的成员向另一个社会借用文化元素的过程,叫做传播(diffusion),而贡献那个文化元素的社会,实际上就是那种元素的“发明者”。借用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已故北美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说,任何一种文化的90%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借用得到说明。然而,人们对他们所借用的东西是有所创造的,他们从多种可能性和来源当中进行挑选,他们的选择限于那些与他们目前的文化相互兼容的元素。(72)[美]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翟铁鹏,张 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61页。
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形成,离不开外来“月中有树”神话的传播。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彝族间的友好交往,为“月中有树”神话母题向彝语中部、南部方言区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彝族史诗歌手们对外来神话并未直接借用,而是进行了二次创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月中有树”神话传统。
三、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
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从三个方面发挥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一)强化中华文化认同
在多民族神话、史诗与中华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比如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理论,已经广为援引。实际上,除了追溯祖源的神圣叙事之外,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还区域性或整体性地共享其他神话母题。彝族“月中有树”神话与中华文化中“月中有树”神话的关联性,正是其中一例。史密斯将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的公共文化作为定义民族的必要条件。他说:“从定义上看,民族与族群一样,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神话和记忆之上的共同体。”(73)[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 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52页。在神话跨族际传播、跨文本传播和神话诗人再创造的语境中,史密斯的理论必须进行矫正,即共同的神话可以表达为共享的神话母题。共享神话的真义在于共享某一历史阶段形成的母题,而不是原封不动地共享叙事情节。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与汉文献所记载的“月中有树”神话之间,具有“不死树”“生命树”和“世界树”的共同神话母题。娑罗树代替月桂树之名,进入月宫神话之中,成为月中不死之神树、神药的神话,经过口头传统、文人诗歌、元曲和小说等传播,在中华神话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娑罗树神话是何时传到彝族先民的口头传统中,并由史诗歌手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对此神话母题进行再创编的,难以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彝语中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的彝族史诗传统共享了中华文明中的“月中有树”神话母题,并且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母题,形成了内含文化认同密码的记忆文本,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因库中注入了活力。
从历史上看,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不仅是某一文化上强势的单一民族通过虚构神话文本来凝聚人心策略促成的结果,我们更应该看到,许多神话文本本身具有的魅力。许多神话母题本身的深层价值,在艺术化地满足人类某些普遍渴求的理想方面具有的强大力量,是其得以跨族际传播的重要原因。跨族际共享的神话母题作用于多民族成员意识的深层,强化了多元一体的认同感。
神话母题可视为广义艺术母题的类型之一。围绕共同母题,不同的民族又发展出不同的异文。母题同而文本异,整体观之,即形成了异中有同(母题同)、同中有异(异文)的稳定结构。异文的出现,符合民族神话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异文体现了各民族神话艺术家卓越的创造力,丰富和发展了中华神话艺术的内涵和外延。各民族拥有的共有神话艺术母题越多,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越强烈。因此,深入研究各民族共同的艺术母题及其凝聚力、辐射力,不仅是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之历史过程的重要维度,也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需要。应当将这一原理作为开展“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的核心学理基础之一。
(二)弘扬中华深层生态智慧
科学家们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发出了严重警告。人类正处在一个物种大规模、快速灭绝的时代。(74)Bryan L.Moore,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Anthropocentrism,Switzerland:Springer Nature,2017,p.25.深层生态学的创立者阿伦·奈斯,力主以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从改变人类的生态观念入手,恢复生态平衡与生态和谐。奈斯深刻地认识到,生态智慧是许多古老的、前现代精神的核心。(75)Edited by Dale Jamieson,Malden,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ss.:Blackwell Publishers,2001,p.220.向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学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知识,成为近年来国际生态伦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神话作为原住民的知识经典,其蕴含的生态知识受到高度重视。(76)Melissa K.Nelson,Dan Shilling,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Learning from Indigenous Practices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月中不死药”神话与“月中世界树”神话,都有生命源于神树的共同观念基础。人类很早以前就知晓从植物中汲取药物成分来治疗疾病,并形成了多样化的植物医药学。树木,特别是常绿乔木,为人类保持水土。绿叶和花朵滋养人类的审美情感。树木的果实令诗人推出万物源于树种的观念。树木的种种优越性,激发了彝族诗人的神圣崇拜和亲密情感。在“月中有树”神话的指引下,彝族人形成了神树与生命在生态意义上休戚相关、难舍难分的一体化观念。彝族神话中蕴含深刻的生态伦理,是彝族先人在与大自然相处过程中体悟出的诗性智慧。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尚未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对自然、生命仍存有整体性的敬畏;对万物同源、生命一体的世界观、生命观尚高度认同。正如伊利亚德所言:“铭记如下这个事实对我们很重要:在许多古老传统中,体现世界的神圣性、富饶和永恒性的世界树与创造、繁殖力、领神的观念有一定的联系。这样,世界树就成为生命树和永生树。”(77)[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段满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1页。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蕴含的生态智慧,对于振兴乡村,保护生态环境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本土资源,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结出的智慧之果。彝族先民在这样的智慧指引下,形成一种人与森林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我们应当挖掘、阐释、利用包括彝族史诗在内的各民族艺术传统中的生态智慧,以保护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三)传承中华艺术治疗传统
彝族史诗中的“月中不死药”神话,是作为灵魂医者的仪式专家在死亡悲剧的伤痛中淬炼出来的疗愈心灵之诗。不死药神话在“赤梅葛”诗章中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单元,由唱诵教路经的歌手从心理治疗的层面与死神进行最后一次叙事化的博弈,其间蕴含的是人类竭力挽留即将逝去的生命时表现出的不甘,表达了对生命、对亲情的无比眷恋。诗人提供了一种留住生命、留住爱的可能性,让不死药曾经“存在”,让毕圣在教路仪式中使用不死药从而令人死而复生的黄金时代得到再现,为史诗受众建构心灵皈依的神话家园。只有在活态史诗的演述场域中,也就是在丧葬仪式中正在承受丧亲之痛的史诗受众,才能深刻体会到“月中不死药”神话是作为灵魂医者的仪式专家在死亡悲剧的伤痛中淬炼出来的疗心灵之诗,而不是娱乐众人的纯粹指向“审美”的史诗“艺术”。在神话逻辑中,不死药神话是对死亡悲剧的文化疗愈。它建构了一种神话历史中曾经存在的神药,令在死亡的恐惧和虚无中挣扎的众生,与一个美丽的谎言建立意识深处的联系。
以李申呼颇本为例。此则神话是对史诗歌手朵觋的圣化,是朵觋的英雄传。尽管不能在口头传统的历史中考据“赤梅葛”的确切作者,但可以确定的是:“赤梅葛”主要由历代祭司创编并传唱。不死药神话中的朵觋及其子,具有和巴比伦史诗中的吉尔伽美什和中国古代汉文献记录的史诗英雄羿相近的历程,特别是在不死药的获得和遗失上,几近一致。其次,此则神话涉及不死药与蛇、日、月的关系,源于人类古老的永生信仰。朵觋以为,麻风病人可通过食用蛇肉的方式获得蛇蜕皮的神奇功能,从而获得新生,令肌肤光鲜亮丽。同理,在相似律的作用下,朵觋认为,冬眠、蜕皮的蛇类掌握了不死药的奥秘,而不死药的奥秘则由永恒的日月掌管,巨蛇不过是暂时窃取了日月的神药。
从表层看,此则神话叙事表现的母题是不死药的得而复失;而从现实的深层原因看,此则神话应是两种力量,即对疾病、死亡的绝望与对痊愈和永生的渴望相互博弈后淬炼而成的失落神话。它的活态诵唱传统,至今依然遗存在姚安、大姚、南华等县的彝族丧葬仪式中。它是以诗歌的形式吟唱,因此,准确而言,彝族史诗中的不死药神话,是一种诗学治疗传统。神话中讨饭、住石头房、分家时对仅有的衣裳和裤子进行分配,以及麻风病的罹患和死亡的发生等情节,都是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现实的境遇是一位朵觋和儿子、儿媳生活在只能以乞讨为食,以天然石洞为屋,且衣不蔽体的苦难境遇中。祸不单行,儿子罹患麻风病并不治而亡。处于绝望中的朵觋想象出能治愈麻风病的蛇肉和能起死回生的神药。不死药遗失的神话,解释了世间再无不死药的缘由。丧子之痛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歌手即使失去不死药,仍然要创编出洗坛圣水在火塘中变化出娃娃的神话,以补偿永失所爱的缺憾。朵觋甚至为死亡情感中恨的一面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那就是以充满魔力的语言命令天狗吞食日月以复仇。疾病和死亡引发的复杂情感,在神话的家园中得到疗愈。人类越是处于绝境之中,越是需要创造安慰剂,创造导人乐观的口头传统。不死药神话正是以口头吟唱形式表达的安慰剂。
结 语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的类型、成因及其价值进行了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可分成“月中不死药”和“月中世界树”两种类型。2.现实经验与本土知识为此神话的形成提供了文化生态环境;神话文本的形成存在传播和交融两种可能性,即中华神话传统和印度原始佛教典籍神话中的“月中有树”神话在彝语中部、南部方言区的传播或外来神话文本与本土神话文本的交融;彝族诗人以诗歌唱史,在借取或融合的基础上,积极创编出丰富的情节,促进了彝族“月中有树”神话特质的形成。3.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强化彝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弘扬中华深层生态智慧,有益于社区生态的保护并对当代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月中不死药”神话在丧葬仪式中的活形态演述,具有传承中华艺术治疗传统的作用。
本论题的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神话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首先,宏观层面的比较研究必须以丰富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其次,对于多民族神话、史诗艺术中的相似性,不能仅用单向传播论与被动接受论来解释。自然环境、地方知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本民族歌手进行再创造的才华等构成了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动力。再次,应当超越艺术本位来研究艺术,艺术与文化记忆、文化认同,艺术与生态智慧,艺术与心理治疗等,均是民族艺术研究中亟待深入开拓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