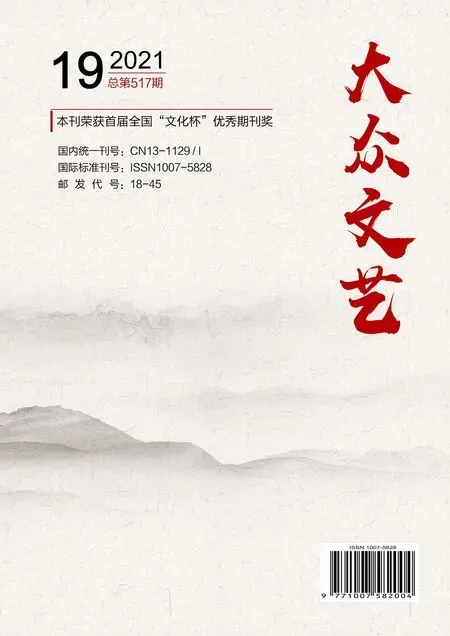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玉簪记》的心学视野
刘丹玉 陆 群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76)
世俗文学粉墨登场的晚明时期,受“王门后学”滋养的、以“心即理”为理论基础的心学在时代的洪流之中绽放出自己的光彩。文人们寄希望于戏剧创作,冲破程朱理学长久以来的束缚——“理”与“欲”之间的冲突。明朝晚期(嘉靖后期至崇祯时期),戏剧文艺作品多以表现市井人情、文化风气为主。解放思潮的演变,离不开哲学与文学的水乳交融,互相滋养。《玉簪记》作者高濂,生活于万历年间,自此剧问世以来,便成为明末讽刺封建枷锁和清规束缚的文艺作品的代表,小说除了讲述“尼姑思凡”这样使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也刻画了晚明僧尼世俗化、众教合流的现象,以《玉簪记》为基点,为我们研究晚明时期心学思想的渐化拓宽了新的研究空间。
一、阶层的流动——从阶级固化到贵贱更替
明中叶之后,政治格局日趋迟滞,工商业日渐繁荣,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级逐渐形成,活跃的市民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社会架构和文化风尚,对长久以来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正统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产生多维度的冲击。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租佃制度促使国家、地主对于佃农的人身控制和财产控制逐渐减弱,佃农的经济独立性大大增强,农民对于个人财产的诉求日益显著,“性情”“理欲”问题日渐焦灼。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带来的机遇使得更多的下层人民可以通过经商、科举等途径改变命运,跻身上层社会。唐朝萧项有诗云:“却对芸窗勤苦处,举头全是锦为衣。”第四出《遇难》中,女主角陈娇莲母亲言道:“一望处,田园荒废,门庭萧瑟。堤拥当年车马隘,如今谁问闲消息?想吾生、富贵等浮云,今方识。”战乱、生意、贬谪也使显贵人家随时都有失去财富和地位的风险。传统的阶级固化不再是命运不可逾越的鸿沟,贵贱福祸,不再“存乎天”,“性情三品”之说也付诸空谈。
面对现实生活多元、剧烈的转变,程朱义理之学的清谈修心机械地把义理套入现实规范人的身心,越发明显地暴露其固守传统、不随势而变的弊端。人们在“修、齐、治、平”之外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但王守仁并没有完全抛弃官方正统的道德观念,依然对程朱理学精神保持着虔诚的尊敬,即便如此,由此而萌生出的思想解放的幼芽,于不经意间对程朱理学的权威构成了潜在威胁[1]。
世界在要求易变,社会在呼唤解放,文艺总能开时代风气之先,而“哲学是时代的灵魂”[2]。晚明的戏剧作品里充斥着自愿平等的男女热情,有一梦倾心至死不渝的杜丽娘、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霍小玉、南柯一梦立地成佛的淳于棼、黄粱一梦了悟出家的卢生,还有冲破世俗枷锁的陈妙常与潘必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逐渐脱离传统固定的模式,追求个人意义上的完满存在。
二、现世的追求——从理想彼岸到男女饮食
如果没有隋唐时期佛学对于哲学问题的探讨,是不会出现宋明理学“研心”“研性”的探究的。安史之乱之后,杨国忠“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开鬻牒之始,唐肃宗时,裴冕“乃令卖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储积为务”[3]。宋英宗时,曾有过这样“赐陕西转运使度牒千籴谷赈济”[4]的举措,至神宗年间,市场钱币流通量不够,官府大量出售度牒以充政府开支,持有度牒的僧尼可借此免去徭役和地税,尤其是宋室南迁之后,军费大增,度牒收入成为官府众多收入中的一大来源,之后度牒始终与国家财政密不可分。至元丰七年,朝廷有文规定“每道为钱百三十千”[5],度牒有了价值尺度便可充当货币的职能,如此一来,僧尼人数骤增,公然买卖度牒从中取利、伪造度牒的现象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出卖亡僧的度牒。自宋儒始,逐渐出现批判佛道二教自然无为、超脱逍遥的观点,精神本体由“无”转“有”,加之生产力的进步,重商逐利的风气盛行,逾越礼制的现象屡见不鲜。
借着心学的破竹之势,人们从封建人伦教化中脱胎,不再将个体命运交予神佛和来生,勇于在现世大胆追求心之所欲。于是晚明的中国呈现出一种文化转型和精神裂变的时代倾向。王守仁去世后,王门诸弟子对其“心学”体悟不同,各自取舍迅速分化,其中泰州学派高扬人的“性”与“情”,李贽认为“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王艮坚持“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罗汝芳主张“吾之此身无异于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亦无异于吾之此身”,都在肯定人的欲望是天然的。当认识世界的本体观念由外界转向内心,人们对于彼岸的依赖随之消解。第八出《谈经》一折中,众尼姑听师父讲经,暗自叹道:“我把芳年虚度,老大蹉跎,衣食浑无措。空门来托钵,做尼姑,也只是当年没奈何。”且剧中人物的言行大量表现出佛道彼此穿插不分的特点:第八出《谈经》中,众道姑请观主出来讲经,观主讲的却是大乘佛教的《法华经》,众道姑皆“齐合掌、念弥陀。”上到统治者,下至底层民众,对于宗教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但实际上反映一种实用和世俗的倾向。
僧尼世俗化的倾向使晚明的戏剧作品中浓厚的利欲、情欲色彩大大湮没其宗教色彩,他们否认一切外在权威,执着于尘世的金钱美色、百姓生活,折射出中晚明鼓荡人心的时代精神和市民阶层全新的处世态度,[6]宗教不再是决定家国生死、人生际遇的存在。毕竟,不管其营造出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如何,终究是为了“解决”现实世界里人的需求和关切。
三、伦理的变迁——从“三纲五常”到“六经皆以情教也”
心学的传播构成了明朝末期一股巨大的启蒙思潮,它“与当时的文学艺术是在同一块土壤基础上开出的花朵”[7],而在文艺领域内一个流行且突出的题材就是男女之间的性爱,折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就是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
如同正统文学已不能代表文艺新声,正统的哲学思想也已经不能代表时代的走向。二程所坚守的“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故要“穷理”,则需“格物”,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并不是要人认识客观物理,实为践行封建伦理纲常。再说“欲”,“欲”与“人欲”不同,“欲”是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好比饥则食,渴则饮,“人欲”则是过分的要求,好比要食美味,饮美酒。但理学家们忽略了一点——他们要人摆脱的“欲”是人的本能,作为社会性的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是受到社会制度制约的,是具有“人性”的,是不会让所个体拥有的本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关系的。
在理学家们看来,超越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便是与天理对立的,但陈妙常作为适龄女子,与俊秀儒雅的潘必正暗生情愫之后,也暗叹自己 “苦守清规。已经数载。无奈尘心未尽。俗念顿生。”道姑的身份与热烈的自我情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程朱理学虽贵为官方正统哲学,却脱离了孔孟最初积极的精神导向,走向意识形态的异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影响深至近现代中国的观念,便是这种禁欲主义在妇女的贞节观上的典型体现,要求女性以牺牲个体生存来践行封建道德。孟秋有云:“心体本自澄澈,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这便是在批评宋代以来理学将先圣的“克己”理解为“克去己私”的传统观念——为了“道德的完美”,贞洁把人类残酷自戕的残酷形式神圣化了[8]。孔子尚且主张“因情而见性”,尊重人自然朴素的情感,不尚遮掩,崇尚率真,女子恋爱婚姻自主如何不能得到肯定和鼓励?从这个角度去看,理学其实是对传统儒学的背叛。《玉簪记》中,女性在择偶方面出现变被动为主动的诉求,虽与朱子的观念相去甚远,但由此可窥得明晚期市民阶层的进步意识促进了社会伦理道德原则的转变。如果说王守仁同时将道德理性和自然感性糅合到心学的体系中,并且无意识地将自然感性至于潜在地位的话,那么王门后学,尤其是“王学左派”,便使心学溢出了内圣之学,呈现出一种“道德理性”的弱化甚至消退,使阳明心学的精神本质中,自然感性的部分从潜在走向显在,进而走向主导地位,而自然感性中最为直观的部分,即“身”,被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可以说心学架构起了个体的内在超越与自适,还有在反叛中坚持自我与独立的人格精神。
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审美与文艺都是时代精神的脉搏,后世之人可以透过文艺作品对时代的思想进行“望、闻、问、切”。透过《玉簪记》中的社会缩影可以看到,晚明,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传统道德伦理开始被重新审视,一切喧哗与躁动的背后,是纲常礼教的松动,以及以人为主体的个体诉求的觉醒。心学变迁中所反映出的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哲学开始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与人的价值,“理”与“欲”,本性与时务,如何取舍,我们的落脚点应回归到“人”本身,倘若要将其具体化,那就是每一个个体的道德意识和真情实感,甚至是细密琐碎的真实生活。我们不能确定宋朝的理学家们在明朝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否还会坚守自己的义理之学,但可以确定的是,心学的出现和发展,是明朝这个传统与创新交融、保守与开放共存的时代所必然产生的意识形态的裂变,也是这个时代留给后世的璀璨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