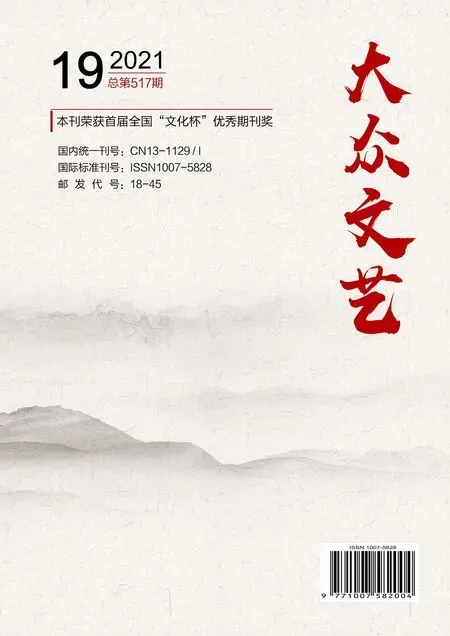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别是一家”
——从否定到肯定的审美流变
司 欣
(济南大学,山东济南 250000)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1]最早刊录了李清照的《词论》并对其进行简短评述,认为《词论》在评述诸位词人的歌词时都旨在揭露其短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胡仔指出这样的论断是不公平的,甚至还用了韩愈的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暗指李清照自不量力,因此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李清照评点先贤、大家做法之不满,并表达了对李清照自大态度之讥讽。这是目前可考的针对李清照《词论》进行专门学术批评的最初文献记载[2]。
20世纪以前,李清照的《词论》尚未受到词学家和批评家们的重视,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学术批评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外,即要数清代裴畅的《词苑萃编》[3]。20世纪始,围绕李清照《词论》研究中最突出的研究论题即为“别是一家”。20世纪中期以来,其内容主要论述“别是一家”说的著作约15部,专门论文67篇,其中第一阶段为划分为五六十年代,约有7篇,第二阶段是七八十年代,约19篇,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约41篇。总共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2篇。(注:论文数量统计主要依据CNKI数据库)。由此可见,20世纪对《词论》“别是一家”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8年以后,其在研究时间上具有极其鲜明的阶段性。
一、否定性意见居多的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夏承焘为代表的学者们多数对词“别是一家”持否定态度,将其定位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主张。夏承焘在《评李清照的〈词论〉——词史札丛之一》[4]中指出从宋词总体的发展角度来判断的话,《词论》这篇文字是起反作用的。他认为在当时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必须担当起时代的号角的重任,与诗合流,表达一些更宏阔的主题,此事迫在眉睫。
此外,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5]也认同这种观点,其一方面赞同词本就是伴随音律出现,因此“别是一家”中说对词协音律等方面的艺术要求无可厚非,但同时也认为李清照拒绝接受苏轼、欧阳修等人在词学上的创新,这种观点过于故步自封,甚至影响到李清照个人创作的格局。当时的大多数学者推崇苏轼“自是一家”的词学观,认为其主张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拓展词的词境、将其风格复杂化,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从而对词体进行全面改革,是值得肯定和接受的;但某种程度而言,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与苏轼等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相悖,反而是有其内在传承联系。正如学者何旭所言,“东坡、易安的词学主张在追求词的高雅上是很相似的。”[6]因此片面地将“别是一家”定义为保守落后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面,黄墨谷先生在《谈“词合流于诗”的问题——与夏承焘先生商榷》[7]中则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不仅是与词的发展规律相一致的,而且全面表现出了当时慢词发展的繁荣盛况。黄墨谷认为,词本就又名曲子词,是一种配合音乐用以歌唱的诗体的专称,因此“协音律”本就是词区别于诗的最大特点,也就理应作为“别是一家”说的合理部分被认可和传承,这是符合当时时代发展主流的。
在《关于李清照〈词论〉中的“别是一家”说的一点不同的看法》[8]一文中,刘遗贤同样认为“别是一家”说与诗学本身发展的趋势以及历史的要求都是相悖而行的。这篇文章是对夏承焘与黄墨谷为何基于同样事实却得出相反结论的一个总结。刘遗贤基本上认同夏承焘等人的观点,认为在李清照的时代该一改萎靡柔媚之声为悲壮激昂的曲子,对于李清照仅醉心于词的形式,而且不适时的过分强调音律,把形式绝对化的做法感到不满。
综上而言,以夏承焘为主的学者们大多推崇苏轼、欧阳修等人的“自是一家”主张,对“别是一家”说基本持否定意见。而黄墨谷等研究者却认为其与当时词的发展规律是相一致的。归根结底是两者选取的比较角度是不同的,前者是从反映论角度总结得出,而后者则是从文学本体论出发进行阐述。游国恩先生等人所持的观点是在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的词理应担负起时代号角的重任,更多地为时代发声。但事实上李清照后期的词一改往日多写闺房婉转之情的风格,词的内容开始更多地开始关注家国兴亡和民生疾苦。由此可见,李清照的“别是一家”并未完全反对苏轼等人扩大词的题材、拓展词的词境的主张,而只是重点突出词的协音律属性,这并不能算作落后过时。
二、从否定到肯定的第二阶段
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对《词论》的研究短暂搁浅,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第二个研究小热潮,此时学界对其的评价与意见开始发生转变。
在《谈谈李清照的〈词论〉》[9]一文中,徐永端认为客观而言《词论》理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篇文章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词论》“别是一家”这一中心论点。指出一些批评家把《词论》强调的协音律说成所谓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形式主义和过分要求协音律的格律派,这是很不客观的。徐永端这一观点是对游国恩等人“李清照的创作并不能实践自己的文学理论”观点的反驳,也是在黄墨谷等观点之后对肯定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的又一创新。缪钺在《灵溪词说·评李清照词》[10]中则认为《词论》只是针对各个词人作品的缺点而阐发的,并未要提出一个完整的关于填词艺术的理论。以此反驳了游国恩等人提出的“别是一家”说过于保守落后的观点。缪钺赞同黄墨谷等人“别是一家”说符合词当时发展主流的观点,也赞同李清照所提出的词应该高雅、典重、协乐等主张,只有如此才能一直保持词的独特性,从而推动词的发展,而并非违背词的发展规律。
费秉勋在《李清照<词论>新探》[11]中对此前学界认为《词论》与李清照词创作实际不相一致的观点提出了新思路。他强调《词论》中提出的铺叙等文学概念,都是以强调协乐为大背景,以此区别惯常所见的同名概念。费秉勋在这篇文章中以《声声慢》等词的铺叙解析来论证李清照的铺叙,并非传统意义上同类景物的陈列,而是十分注重主观与客观、情与景、哀与乐、虚与实的相互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特的铺叙法。
三、充分肯定并多角度深入研究《词论》的第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始,学者对于“别是一家”说充分肯定并开始多角度深入研究。
沈家庄在《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说刍论》[12]中试图从儒学的角度分析“别是一家”说,他认为李清照在《词论》中彻底将“词”与儒学道统和文统进行了切割,全然舍弃了儒家所提倡的文统规范。事实上,李清照中未明确表明词拒绝儒家和文统所主张的文统规范,而只是极力主张词的音乐性,要求根据词本该遵守的音律来判断词的优劣。据此,她应该还只是停留在对词的规范之要求,尚属文学审美阶段,并未达到摒弃儒学正统思想之高度。同时,李清照也在《词论》中批评柳永词在音律方面虽十分出色,但内容方面不够文雅,属“语词尘下”之流。这说明李清照不单单注重词是否并协乐,同样十分重视词之雅正及社会意义。
张惠民在《李清照<词论>的达诂与确评》[13]一文中持相反观点,他指出对儒学思想的遵从仍是李清照词学观的基本准则,易安词有其大前提,即词的思想内容要“尚文雅”,其次才论“协音律”。比如李清照不仅不满柳永的词“语词尘下”,同样不满温庭筠、李煜等的靡靡之音之作。
实际上,沈家庄认为词本身具有天然的婉转清丽,更适宜于表现个人情感,从本质论出发强调词本身的独立性。他主张词本是协音律的可歌之乐,本就不该承担教化之功能。而张惠民则是从《词论》文本出发,认为《词论》有个大前提是词要表现的是雅正、健康及具有社会意义的合于儒家规范的思想情感内容从而得出乐教论的结论。
张静《解开李清照<词论>之谜》[14]则从“女性特有的感悟”这一角度来解析“别是一家”。论者认为李清照不苟同当时的女性处境,因此她要重新审视自我,关照自我和女性的社会地位。词一直被认为是“小道”和诗余,所以词这“诗之附庸”属性与女性在社会中惯常被冠以的附属地位有相通之处,正是基于女性的独特感悟触动了李清照,从而使其提出“别是一家”的命题。
纵观二十世纪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研究的各个层面,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审美流变后,“别是一家”说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但也应该看到,《词论》在文本细读及审美意蕴等方面的挖掘还存在诸多不足。比如对“别是一家”与苏轼“自是一家”的究竟是承继关系抑或是相悖关系的深入研究以及目前从女性角度来研究“别是一家”说,其本人主观要求及最强调的是否是其女性意识这个问题仍值得讨论等等。因此,对其“别是一家”以及《词论》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仍需要付出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