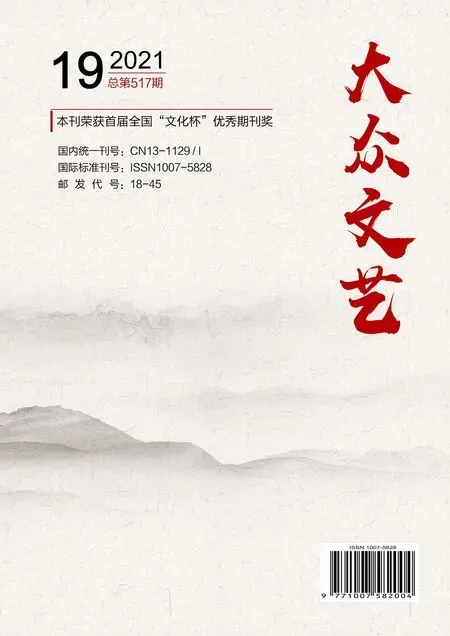论《秀才与刽子手》中的“偶人”艺术
李姝杭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秀才与刽子手》是21世纪之初中国话剧界的一匹黑马,该剧用独树一帜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就是“偶人”艺术,他们戴着面具,以傀儡的身份出现,讲述剧情、抒发感情、发表评论,其形式和作用与西方戏剧中的“歌队”相类似,但更具有“民族化”的特征。郭晓男导演曾自述该剧是一次对黄佐临“写意戏剧观”的实践,而“偶人”艺术便是此次实践完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一、作为“歌队”
“歌队”形式最早运用于古希腊戏剧,其形式通常是一致的群体性行动,主要起到叙述剧情、发表评论、烘托氛围、控制节奏的作用。但自古希腊戏剧之后,“歌队”一直未被赋予实际性的价值,直到20世纪,在布莱希特的努力下,“歌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功能与价值,而现代戏剧中的“歌队”也多接近于这种“布氏歌队”,著名学者布罗凯特曾总结其作用如下:
(1)歌队可以作为剧中的角色来参与剧情。
(2)歌队可以作为剧情外的叙述者来交代剧情信息,如人物身份、地点、时间等。
(3)歌队可以代表作者的观点来对情节和人物发表评论。
(4)歌队也可以以歌舞队的形式抒情。
(5)歌队让观众和剧情产生“间离”,留给观众思考的余地。①
试看其作用在《秀才与刽子手》中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在该剧中,戴着面具的“歌队”一出场,就表明了自己的“偶人”身份和目的,并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背景:“说的是光绪乙巳年,天下纷纷乱如烟......”②,这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他们的“叙述者”身份,但是在该剧中,这种身份并没有贯穿全剧,主要出现在开头和结尾部分。这样的“戏中戏”的设置形成了一种叙述性的叙事结构,提醒观众整部剧的主体部分是一个正在“讲述”中的故事,并且,“偶人”在承担“叙述者”身份的同时往往还兼有“评论者”的身份,例如,在不戴面具的徐秀才第一次登场又下场之后,有“偶人”说:“我们不是要演傀儡戏吗?他又不是傀儡!”③剧中的“老偶人”回答说:“问世间谁人不是傀儡?任你活得有声有色,那也是阎王爷手中的傀儡!他这号么,叫作肉傀儡!”④这一句的回答就是“偶人”对剧中人物做出的评论,也是剧作的主题思想。“偶人”所充当的这种“叙述者”和“评论者”的身份一方面对全剧起到了整体性的“间离”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对主题的深化,在这里,“偶人”是剧作者的化身,作者借这些木偶来看这些小人物被历史大潮裹挟的命运。
其次,虽然“偶人”在剧中作为“叙述者”和“评论者”为全戏制造了一个“戏中戏”的情境,刺激观众对作者所表达的主题进行了反思和思考,达到了“间离”的意义。但在主体剧情中“偶人”是以人物的身份直接参与剧情的,例如,他们可以扮演乡亲、考生这样的群体,也可以扮演王保正、丁朝奉、李爷、小寡妇这样的个体人物。这样的设置使“偶人”们完整地参与了叙事,扮演角色的表演和内容是连贯的,观众的情绪也是连贯的,并没有被完全“陌生化”掉。
另外,“偶人”在剧中的角色扮演从另一个层面也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了芸芸众生的代表,这使得剧中的人物具备了普遍意义,这对戏剧的整体情境形成限制,即便是像徐秀才和马快刀这样的固定角色的意义也在大的情境里被抽象化,他们性格中所展现出来的夸张性和极端性成为现代“单面人”⑤的代表。
最后一点,“歌队”的抒情功能在《秀才与刽子手》中体现的也很明显。例如,在秀才与小寡妇的那场戏中,小寡妇夸赞秀才身材好,在这里实际出现的人物只有小寡妇和徐秀才两人,但此时却有一支女性“歌队”走出,将光膀子的徐秀才团团围绕,用舞姿和歌声来瓦解徐秀才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尊严。在这里,“歌队”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抒情和烘托氛围,以更形象的方式表现了徐秀才的精神困境和心理状态。而“歌队”的这种抒情方式从手法上来讲可以看作是写意与写实的结合,尤其是对于写意手法的运用,使剧中的“歌队”具备了本土性,完成了民族化的转变。
二、剧场性
(一)写意的空间
郭晓男在导演这出戏时,虽然在话剧中融入了许多戏曲元素,如要求人物的“实物性道具少而精”⑥,要求“从昆曲中找元素”⑦等,但是笔者认为真正成就这出“写意戏剧”风格的仍然是“偶人”艺术。
首先,“偶人”的存在“诗化”了舞台。如笔者在前文中所述,“偶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写意性”。例如,在马快刀准备劝说徐秀才为自己代写家信时,“偶人”出场,唱出了马快刀的请求,但这里“偶人”并不是对马快刀心理的外化和明确的代指,因为之后徐秀才准备答应马快刀时,徐秀才身边的“偶人”说:“那就请他进屋吧!”⑧可见,此时“偶人”并不只是马快刀情绪的外化,而是更多地展现了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功能,这样的展现将叙事更加的“舞台化”和“诗意化”。而在扮演人物角色时,“偶人”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如在马爷“斩首”犯人这场戏中,“偶人”扮演犯人,他们表现被杀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舞蹈化的动作以及将脸上的面具摘下挂在铁钩上,这样的处理,既完美地展现了马快刀的心理世界又使其充满艺术性和写意性。如果说,作为“人”存在的“偶人”多少还具备一些写实性,那么作为“景物”存在的“偶人”则完全将舞台写意化了。在马快刀和徐秀才借酒消愁的一场戏中,为了表现时间的转换以及渲染人物的情绪,剧中在音乐响起的同时,让一个女“偶人”手举纸弯月,以舞蹈化的身姿缓缓走过舞台。这种虚拟化的手法让观众产生对戏剧的“间离感”,但从情绪上来讲,这种“间离”让月亮更诗意化地展现了主人公们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与惆怅。
其次,“偶人”的存在使场景的转换更为灵活。例如,在徐秀才准备将马快刀请进自己家里时,场景需由街道转为室内,准备下场的“偶人”分为两拨,一拨下场时将街道的布景推离舞台中央,另一拨则将桌子搬上舞台,并说道:“徐秀才?请!”⑨舞台场景的转换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这样的场景转换使得整个舞台的演出更加流畅和简洁,一定程度上帮助塑造了一个写意的舞台空间。
最后,“偶人”外化了人物的情绪。在该剧中,情绪和梦境通过“偶人”呈现在舞台上,使舞台摆脱了“写实”的束缚。例如,徐秀才醉酒后背对观众,一个靠着他的“偶人”说道:“马快刀,要说这杀人是我不如你,可要说这考试,就是你不如我了。”⑩显然,这里的“偶人”就是徐秀才的自白。还有上文提道过的徐秀才和小寡妇的一场戏,众“偶人”包围着徐秀才,在这里,“偶人”并没有明确的代指,也不是实际性的存在,只是小寡妇内心世界的外化,她对徐秀才的钟情首先来自身体,这种外化的表现方式既让观众看到了小寡妇的思想情绪,也让人看到了徐秀才的心理斗争。
《秀才与刽子手》在“偶人”的表现形式里是写意的,而这种对舞台写意化的塑造方式又是极剧场性的。
(二)夸张的身体
从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到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在20世纪中后期的戏剧潮流中,作为剧场性因素之一的“身体”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在《秀才与刽子手》中,夸张的身体语言扩大了戏剧的表现力,完善了剧作的主题。
在原先的剧本里,“偶人”都是由傀儡师操纵的真实木偶,但在实际演出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木偶改由戴着面具的人直接扮演,这就要求演员行动要区别于普通人,从语音到肢体都表现出极大的夸张性和整一性。这种表演形式与内容上所设置的“戏中戏”的“间离”效果相呼应,将情节抽象化,带给观众“陌生化”的观剧体验。但同时,“偶人”作为剧作者和旁观者的代言人,却也将背后的戏剧精神具象化了。
而剧中许多歌舞化的表演段落所制造的一场场“狂欢”也起到了调节氛围和增强喜剧性与荒诞性的作用,如许秀才做梦高中时,整个夸官游街的过程都在喜气洋洋的歌舞中进行,人物动作极为夸张,但正是这种夸张才让整个过程在与现实的对照下显得更加荒诞和可笑,徐秀才人物精神的缺失和悲剧性被凸显,而观众却在欢笑声中感受着其中的悲凉与无奈。
三、结语
总而言之,“偶人”艺术在《秀才与刽子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在借鉴西方“歌队”表现形式的同时,又将它民族化和本土化,用傀儡式的夸张身体和写意化的戏剧空间体现出了强烈的剧场性,服务于剧作的主旨,是一次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注释:
①[美]布罗凯特,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一一世界戏剧史[M].胡耀恒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②黄维若著.秀才与刽子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8,第1—2页.
③黄维若著.秀才与刽子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8,第4页.
④黄维若著.秀才与刽子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8,第4页.
⑤“单面人”是马尔库塞在分析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现实状况时使用的概念。在他看来, 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批判性、超越性因素, 使社会意识形态趋向单一, 而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人也日益丧失对自由和创新力的渴望, 不再去追求脱离原有轨道的新的生活, 成为“单面人”。
⑥郭晓男.崩溃中的嬉戏——《秀才与刽子手》导演阐述[J].话剧,2006,(03).
⑦郭晓男.崩溃中的嬉戏——《秀才与刽子手》导演阐述[J].话剧,2006,(03).
⑧黄维若著.秀才与刽子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8,第7页.
⑨黄维若著.秀才与刽子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8,第7页.
⑩黄维若著.秀才与刽子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8,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