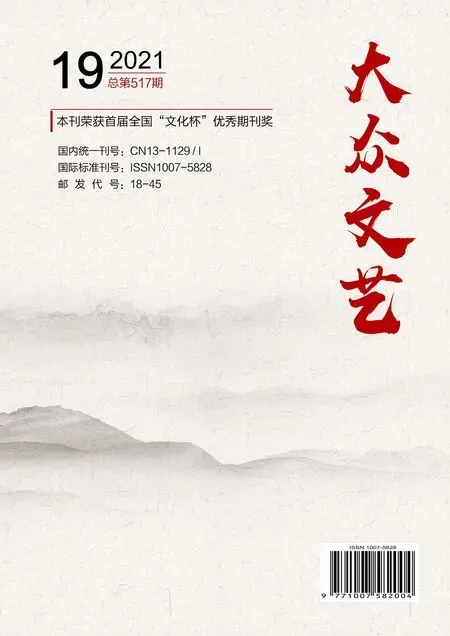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江行初雪图》与中国文人的隐逸文化
王 严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辽宁沈阳 110000)
《江行初雪图》
盛唐以后,文人们的审美从昂扬的沙场慢慢转到精致的案头,山水画也从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发展出淡淡着色的水墨山水,逐渐形成了“微茫惨淡”“荒寒”的审美。最惨淡荒寒无过于冬日景象,江上、风雪、渔人,从静到动,构成了一幅绝佳冬景图的要素。“雪上江行”成了画家很爱发挥的母题,画史中记载王维就曾画过很多这个题材的作品,可惜如今已不见真迹。现存最早的雪上江行题材作品是五代南唐画家赵幹的《江行初雪图》。
这是一张三米多的长卷,描绘了江南地区一场初雪下渔人的生活。寒风乍起,江上泛起烟波,地面与芦苇丛上已有积雪,雪花还在飘落,岸上的行人瑟缩不前,江里的渔人们还在照常辛苦的劳作。
画中描绘近五十个人物,分为行人与渔人两种身份。
起首一段是一片长满芦苇的堤岸,两个纤夫拉着一条小船,小船上的渔人也用力撑篙,渔人和纤夫都在寒冷的天气里打着赤脚。惹人注目的是第二个纤夫,他正回过头来,什么吸引了他的视线?
顺着他目光的方向,我们看到树丛下的小路上正走来两人,骑马的人笼袖瑟缩,幅巾被风吹起,巾脚烈烈的飘。后面跟着的步行的小童,挑着包袱弓起背来抵御寒风的侵袭。二人的目光也都正看向拉纤的场面。
骑马人身后不远处有一座小桥,小桥后面,两个骑驴人行进过来,身后跟着挑担的童仆。前面的骑驴者正回头说着什么。看他们手臂和目光的方向,似乎是在谈论河对岸的一伙渔人。
此时,三个渔人正在压杆起网,中间的那位显然是被对岸的骑驴者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脸上流露出奇异欣喜的神色,忘了压杆,前面的渔人回头提醒他注意。左侧,一个小孩正躲藏在竹林中,羞涩地伸出头来好奇地打量对岸的骑驴人。
骑驴人和小童身后,小路延展到画外,有行人的画面部分到此处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是占画幅一半的渔人生活图卷。我们可以从被风卷起的芦苇叶子看到寒风的凛冽,树干和岸边的枯草上也已经有了积雪,撑篙的渔人紧抱着篙的身体姿态表示他们感受到的寒冷。然而,分明有的工作需要他们把寒冷抛到脑后,比如画面下方的两个抬网的渔夫,他们的下半身几乎赤裸着,却并没有看到有怕冷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十分习惯的。
再后一段,浩渺的江波上随处可见起网和撑篙的渔人,水面上除了小船,木排,还有渔家为了等待起网而搭建的窝棚。
末尾一段,江中一处避风的地方,一户渔人在船上升起了炊烟,一家人分坐在两条小船上,蜷缩着身子,望着正在炊煮的食物。画面下方的又看到了小路,一个小孩跑在前面,一个推小车的老者随后出现,画面到此处戛然而止。天地茫茫,江波无尽,向无穷的画外延伸。
看完整卷的《江行初雪图》,就仿佛跟随着画家饱游一番归来,江声犹然在耳。画家对江南渔家生活一定十分熟悉,才能描绘出这样具有盎然生活气息的画面,令人不禁揣测这幅图的缘起。
此时需要回到画卷开首处,这里有“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幹状”几个字,传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关于赵幹的资料非常少,目前也只知道他供职于南唐画院,善画江浦渔父。这张画是进献给后主李煜的。
李煜作为偏安一隅的一国之君,为何会喜欢如此荒寒清冷的渔家景象呢?这还要从中国文人的隐逸情怀说起。
中国文人的隐逸文化
西方文化中,归隐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归隐的人并没有被提高或者被降低身份。中国文化中的归隐与之不同,隐士成了拥有济世的本领又偏偏遗世独立的象征。中国历史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知识分子(文人)几乎全部有政治欲望,自由知识分子只是在战国时期短暂的繁荣过一段时间,但其主流也是规划和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董仲舒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的单一价值观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宋人辛弃疾词中所说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成了是传统文人人生的唯一价值。
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文人,却并不想被绝对正确的价值观裹挟,特立独行选择不从政而去隐居,这几乎是个人自由的最高境界了,这高尚的人格自然令人肃然起敬,且令所有不得不在宦海中沉浮的普通文人心向往之。隐士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
隐逸文化有确切证据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孔子曾经说过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来申明人生理想[1],传说中的隐士更早,众所周知的许由洗耳的故事发生在帝尧时期,晋代皇甫谧《高士传》这样写道:“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於颍水滨……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这里用巢父来说出许由使自己名噪天下,并非真隐士,真正的隐士要隐得寂寂无闻。
“许由洗耳”究竟是否发生过,无可验证,但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上古时期,中国文化中对隐士也是极推崇。隐士在最初就分为了两种,一种是许由式的,通过隐居令自己名声大振,另一种则是巢父式的真隐士,对以隐居沽名钓誉的行为嗤之以鼻。我们在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巢父式的真隐士才是真正的高人。
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真正的隐士是无名的,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知晓谁是真正的隐士,这就令以隐博名者大行其道,如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姜尚、诸葛亮,甚至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都是靠隐居这条“终南捷径”以退为进,博得大名。
那些无法知晓名字的真隐士,就以符号的形式隐进了诗词和绘画中,其中以“渔人”意象最为典型。
渔人意象与隐逸文化
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典型的渔隐形象参见屈原的《渔父》,文中渔父奉劝被放逐的屈原,屈原不接受,于是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里的渔父是一个典型的隐士的形象。
其后,渔隐的意象一直延续着,在唐诗中得到更多的描述。如柳宗元的《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看到渔翁,就想起泛舟江湖,自由自在的生活。又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雪中渔人所呈现出来的天地清寒,渔翁自得的境界在诗词和绘画中多有表现。在这里,渔人自身是否是隐者并不重要,渔家的生活自然能够抒发出作者的隐逸之心。
大多数古代文人,厌弃眼前的尘嚣缰锁,又无法决然遁世,就是借着诗词绘画中隐士的形象来寄托自己清高的理想和喧嚣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所以文人会挂山水画,在家中“卧游”,典型的古代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山水画中怎么能少得了渔人呢?泛舟也好,垂钓也好,渔人意象因此成了文人隐居理想的投射。
回到《江行初雪图》,画院学生进献给皇帝的绘画作品,必然是投其所好。如我们翻看北宋徽宗时期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到基本是富贵艳丽的气象,像《江行初雪图》这种江湖荒寒清冷的景象,是不可能出现在徽宗的时期的。李煜为何偏爱这个题材的作品呢?
李煜的困境
南唐三代国主都喜爱诗文书画,到后主李煜时更加耽于此道,作为文人的李煜是成功的,他的诗词绝妙,流传千年,无人能出其右;他的绘画据记载也颇有建树,书法独创“金错刀”体,但不幸的是,他还成了一个小国的国君。
南唐从建国到后主被俘共39年,只有烈主时期国势尚可,到了中主时就已经每况愈下,后主李煜登基后,南唐国已经只剩半壁江山,国内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北方强宋的威胁与日俱增。李煜本身性格善良懦弱又不通晓政事,这个国主做得无限烦恼,只好终日躲避于诗文书画与谈佛说道。
他时常写下这样的词句:“事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宴罢又成空,迷梦春雨中”,透露了他的内心多少苦闷无处排遣,想逃离却又无法脱身。文人性格的李煜,在现实中不得意,自然拾起了千古文人一脉相承的归隐之心,他曾有《渔父词》二首,流露出对江湖隐逸的向往:“阆苑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鱗,快活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词句间洋溢着对渔家生活的欣羡。渔人的自由自在必然好过自己日日欢宴的迷梦,但身不由己的李煜只能躲在诗文书画中找寻心灵的自由。
画史中记载赵幹进献给李煜的画作,都是田园牧人,江浦渔父的题材。与赵幹同时的江南名手卫贤和中主时期的名画家董源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大多为山林隐逸的题材,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唐中后期朝堂之中自上而下弥漫着逃避现实的气氛。赵幹进献的渔家生活的画卷,也是以此抚慰后主李煜不能远遁江湖的遗憾。
南唐灭国以后,赵幹此画中的天地荒寒之气,被解读为国势衰落,来日必不久长的象征。此后,寒江渔父的题材作品就被视为不祥图景,很长时间没有画家涉猎。直到北宋中后期,太平日久,人心不再思危,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一干文人推王维为鼻祖,倡导绘画应该融入诗意,以表现“江湖趣远之心”,尘封已久的这个题材才又被重新画起。
渔隐母题
渔人——隐士,江湖——隐居理想,同一个母题,还被后来的画家们反复的画着。中国画有一个框架,那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大背景不变,中国画从题材到面貌都不可能发生巨变,这也是我们看到仿佛中国画千年来变化不大的原因。如果在古代做一个文人画家,写诗词有现成的“典”,绘画有现成的母题,在框架内靠个人文艺修养的深厚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下。除此之外,画家自己独特的诠释,则隐藏着画家和他们背后的时代气氛。同西方绘画的大变革相比,这几乎只是微妙的差异了。
正是这种单一价值观的文化背景派生出的隐逸文化,贯穿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时间,我们看到的诗词和绘画中的渔人,不过是隐逸文化的一部分呈现。解读中国画,笔墨的高妙,画面布局的合适或者精巧,是一种角度,看到画面背后隐藏着的东西,是另外一个角度,结合这两种解读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体会一幅画的内涵。画幅之上,画幅之后,一切总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