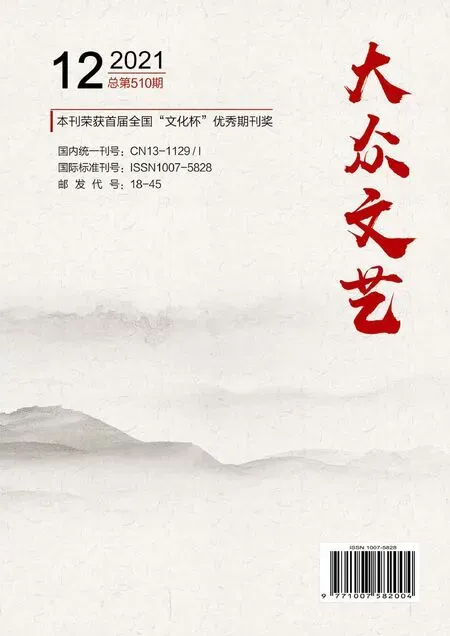法国自传体文学中“自我意识”的演变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一、引言
自传文学在法国由来已久,18至20世纪,从作者自我意识在文本中彰显出的地位来看,大致经历了大致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踊跃的表达高潮(18世纪):卢梭的《忏悔录》发表,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自传就此诞生,这本书是作者自我意识表达的高度富集;接着是逐步解体(19世纪):以波德莱尔的《我心赤裸》为例,浪漫主义兴起,主体危机也随之而来,“我”逐渐从作品中解体、分散。最后是隐退幕后(20世纪):自传文学呈井喷之势,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如纪德的《如果种子不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自传极其相近文类已然成为现当代作家所必须要进行的创作实践,可是作家真正的自我意识却已经从台前转到了幕后,隐而不见,难以触摸。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法国自传体文学从中世纪至20世纪所完成的演变,实质上是文本中作者本人自我意识从发展至离散最后隐匿的一个嬗变过程。
二、卢梭:表达的极致
卢梭一生漂泊不定,著名的《忏悔录》创作于1767至1771年间,于卢梭去世以后发表,是自传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与先驱之作。从《忏悔录》(纳沙泰尔手稿)的初版序言可以看出,卢梭将该书的文体明确为回忆录,但同时他也清楚而自豪地声明了与该文类的传统特征相比,自己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1]。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卢梭强调自己的写作方法古往今来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正如菲利普·勒热讷在《卢梭与自传的革命》中所提到的那样:
“有学识的人都知道卢梭这本书历史渊源颇深,能看出多种传统文类的影子:源自奥古斯丁的宗教性自传,源于蒙田的自画像,护教回忆录,流浪汉小说或教育小说等等。所有这些文类在被卢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被他粗暴地扭曲,是文学向现代化转变的一种奠基性的政变。……”卢梭也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但他重置了一切。《忏悔录》的写作是一种极度大胆的行为,它确实是历史意义上的一个“决裂”,并迅速被同时代的人察觉。”[2]
就这一点来说,《忏悔录》源于传统,但也改变了传统。现代化在这里表现为自传的大众化,自此,自我意识的集中书写如燎原之火蔓延,自传作品也随之大量产出。作为现代自传第一人,卢梭不仅在《忏悔录》中记叙了自己的生平,还阐述了对自传的独特见解,其主观意识的表达主要涉及两方面:肯定自己书写自传的权利,笃信并宣扬自传的真实性。
首先,关于书写自传的权利。一个终其一生都只是平民的人,是否有权利书写自己的自传呢?他又能给读者展示什么呢?以及,说到底,谁又会对这样一个平民的生活琐事感兴趣呢?下面是卢梭的答复:
“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说。我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我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们写出来……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锐丰富而定……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但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3]
卢梭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属于平民的回忆录,它讲述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出身卑微的人,从未有任何建功立业的机会与能力,但取而代之的是高尚的思想情操,灵魂远比所谓的功业要更充实有内涵。个性化的人生观意味着,原则上每个人都有权尝试,这与人们渴望传播自己人生经历的心态相符。尼古拉·邦霍特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忏悔录》与其他回忆录做了比较:“相较于后者所宣扬的贵族主义、建立功勋、经营社会地位、尊严,《忏悔录》强烈而明确地肯定底层工匠的价值,简朴、默默无闻的生活的幸福,奋斗,日常琐事甚至是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实。”[4]
其次,关于自传的真实性。卢梭对自己笃定无疑,对他而言,认识自我不难,难的是让别人也认识他的内心。卢梭撰写自传就是为了改变人们心中自己被扭曲的个人想象,还之以真实与客观。正如蒙田在《随笔集》里所写的那样:“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自己胆小还是残酷,忠心还是虔诚;别人看不透你;他们只是用不确定的假设来对你猜测;他们看得多的是你的表现,不是你的本性”[5]。在这场与蒙田的跨时空对话中,卢梭也同意只有本人才能还原其生活与精神的真实面貌,不过他也随即就与蒙田划清了界线:“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别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像他本人的实际情况”[6]。总的来说,卢梭并不否认其作品中含有自辩的成分,他自诩是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个依照本来面目给自己作画像的人,只有他卢梭做到了极致的自我表达,与蒙田为美化自身形象而创作不同,他仅仅是为了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书写。
卢梭自我意识的高度凝聚还表现为对自己心性的笃定认知。当面对世人的诽谤攻击时,他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姿态,把自己一生中的所有事件原样铺陈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从中提炼出一个真实的卢梭的形象,这样做无异于一种自我挑战,“把一切都说出来”难免会将自己不那么光鲜乃至不可见人的一面暴露出来,而人的自尊天性注定了人都容易被虚荣支配,因此帕斯卡才说“自我是可恨的”,一切自画像都是骗人的。不过卢梭在这一点上不再认同帕斯卡了,他说道:“最胆怯的女信徒也从没有做过一次比我更为深刻的反省,也从不会像我向公众披露的那样,向她的忏悔师更深刻地披露心中的一切”[7]。卢梭只想将本性暴露出来,使读者一览无余。所以他记叙了自己的一桩桩难以启齿的不光彩行为,尽可能地做到真实。而这种“真实”,根据勒热讷的理论,就是《忏悔录》这部作品中“自传契约”①的体现,它以感情的真挚动人取代了事实的真实。让读者的注意力从关注卢梭说的事情真实与否,转移到关注他的表达真诚与否上来了。
卢梭的《忏悔录》是当代法国自传文学的一个新开始。作为一部自传书写者自我意识表达的巅峰之作,它改变了法国自传体叙事的发展方向,为后继的研究者与创作者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波德莱尔:高潮后的解体
波德莱尔的遗作《我心赤裸》出版于1887年,内容包含了私人日记,散文与信件,能够充分反映这位诗人和艺术论家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正如普鲁斯特在评价《恶之花》时所说的那样:“……其中的每一首诗都仅仅是个片段,每读一首,它都会立即与前面读过的片段融为一体。”[8],阅读《我心赤裸》也会为我们呈现波德莱尔思想与感情的全貌,书中包含的散文作品也会与他的诗歌融为一体,使我们对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成就产生更完整、清晰的印象。我们应该像尊重他的诗歌一样尊重这本书,不仅因为他的散文在数量上超过了他的诗,更因为这些文章清晰地揭示了他的道德、艺术观念,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情感。他的一部分私人信件也收录其中,尤其是那些写给他母亲欧匹克夫人的饱含痛苦的信,人们能从中发现他一生多灾多难的根源,而后者反过来成了他创意与才华的不竭源泉。
“自我的蒸发和凝聚,一切尽在其中”[9]。《我心赤裸》的首句同时提到了主观的“我”(凝聚)和非人格化的“我”(蒸发)。第一种“我”往往带有鲜明的自传特征,极尽自我表达之能事;而第二种“我”是一个虚构的、解体的“我”,并不特指某个人。那么,从百年前卢梭高调表达自我以来,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起主语的分离?所谓的主观性到底是什么?又从何而来?我们从个人主观性的源头——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对峙的神话故事说起:
俄狄浦斯来了,斯芬克斯问他:“什么动物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
俄狄浦斯回答道:“谜底是人。因为当他还是个孩童的时候,他用四肢在地上爬动 ;当他成年后,他用双腿行走;而当他老年时,他的拐杖就是第三条腿。”[10]
这个谜语被认为是人类第一次认识自我的象征。关于这个问题,“认识你自己”不仅作为苏格拉底的知名格言被镌刻在德尔菲神庙入口,更为西方传统哲学把主体本身提升到研究的首要位置提供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个体逐步占据了中心地位:16六世纪,蒙田在《随笔集》的序言中写道“我自己是这部书的素材”[11];17世纪,笛卡尔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18世纪,卢梭的《忏悔录》标志着现代自传的开端,另一部作品《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也说明了十八世纪是一个感性时代,而到了十九世纪,主观主义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巩固。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伴随着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争论,文学主体危机初见端倪。在诗歌方面,从波德莱尔开始直至马拉美都对主观主义产生了质疑。争论、质疑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我”的解体。
以上是《我心赤裸》创作的历史背景,“我”不再是传统的书写主题,自传作家面临着新的困境。而波德莱尔一生都希望能给世人带来一本“卢梭的《忏悔录》与之相比都会黯然失色” 的作品。“好吧!没错,这将会是一本复仇之书……我想让人们持续地感知到,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它的宗教狂热,我如同一个陌生人,游离在外。我将以放浪的姿态与整个法兰西抗衡。我渴望复仇正如一个疲惫的人渴望一个浴缸。”[12]1863年6月5日,波德莱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如是诠释了《我心赤裸》一书的写作设想。书名则借鉴了爱伦·坡的想法,后者在《书边批识》中曾这样写道:“假如某些有想法的人,想要凭借其思想、观点与情感,一举惊动全世界,那么他的机会来了。通向成功的大道在他面前已然铺开,笔直而坦阔。实际上,他只需要撰写并出版一部小书就行了,标题也很简单——简洁明了的几个词语——《我心赤裸》……”[13]事实上,波德莱尔所袒露的“心”既没有激动地吐露心声,也没有向读者揭开任何自己的秘密,却是一颗充满愤恨怒火的心:“一部我构想了两年的大作:《我心赤裸》,我将在其中尽情发泄我的怒火。啊!一旦此书得以发表,让雅克的《忏悔录》都将黯然失色。”[14]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书的第一部分:日记,在这一部分当中,自我意识的解体表现为自传结构的缺失,书写形式的碎片化。《我心赤裸》仅留下了一部分未完全展开的笔记,以精粹的形式汇集成波德莱尔的思想轨迹,既恨世挑衅又荒诞不经。波德莱尔坚决拒绝对此书进行构思,绝不是因为放弃了这部作品:“我不打算从任何特定的地方、以任何特定的式样来开始《我心赤裸》,而是要遵循每天产生的灵感及环境,把它续写下去;只要那灵感富于生命,就把它写下来”[15]。这就很符合私人日记的定义:并非连续不断的叙述,而是一种碎片化的写作;随时可以开始,也随时可以中断,也正是由于私人日记的私密性质,它比自传似更具有可信度。《我心赤裸》的写作计划并不是波德莱尔为了摆脱挫败感而想出的法子,而是出于纯粹的写作欲望而想要完成的作品。“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意味着:并非随意疏忽或者漠不关心,恰恰相反:是为了展现作者那股不加掩饰的创作冲动。
我们接着讨论此书的第二部分:信件,在这一部分当中,自我意识的解体表现为破除常规的自我书写主题,一反普通自传对作者生平的记叙,转为具像化忧郁情绪、表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危机。波德莱尔写给其母的书信被认为十九世纪最美、最感人的书信,说是一部作品也不为过。欧匹克夫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波德莱尔的心,他对她完全忠诚,毫无隐瞒,将自己全部的苦恼、失望与未能实现的抱负都倾诉给了她。母亲对于波德莱尔而言既是包含着崇拜的爱慕对象,也是点燃一切极端情绪的暴力的根源:
“我害怕我会不会因此而致命地伤害了你,会不会因此而摧毁你孱弱的身体。……然而,在我当前所处的可怕环境下,我的确深信我们之间有一个人会置另外一个人于死地,而且最后我们将会无一例外地把自己都送上死亡之路。在我死后,你肯定不愿意继续活下去。我是能够维持你的生命力的唯一事物。”[16]
可以说,忧郁与痛苦是波德莱尔作品的主旋律。在发表于《文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艾格尼丝·维莱特解释了“忧郁”(le spleen)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的定义和重要性:
“然而,忧郁(le spleen)涵盖了许多波德莱尔的专属字眼,如焦虑、伤感、厄运、烦恼……它是一种灵魂的疼痛、一种存在主义的不安、一种形而上学的焦虑,还是一种对自身和对世界的不适感……如果忧郁比死亡更痛苦,那是因为它是时间的考验,唯有审美的享受、痴狂的情爱、人造天堂与烂醉如泥才能排解这种忧郁。“贪婪的玩家”“骂骂咧咧的老头”“生命和艺术的黑暗杀手”都是时间在波德莱尔作品中的化身,同时,作为敌手,时间与人类的竞赛却从来不公平……”[17]
时间是波德莱尔作品中的“敌人”。对时间的仇恨也许是其双相情感障碍的表现,因为波德莱尔必须继续生活,也就是继续受苦。不堪忍受苦楚的忧郁情绪不仅见于他写给母亲的信,其实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充斥在他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了,产生自杀的想法是这种痛苦的另一个表征,也是波德莱尔向外界发出的求救信号:
“……我将自杀,没有一点点悲伤。我丝毫感受不到人们称之为悲伤的情绪。我的债务从来不不构成忧虑。没有什么比管理这些东西更容易了。我要自杀是因为我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欲望了,每天入睡和再次醒来的疲惫令人不堪忍受;我要自杀是因为我对他人毫无用处,又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要自杀是因为我相信自己是不朽的……”[18]
尽管我们对波德莱尔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但从分散在他成年后写的文章中的回忆和《我心赤裸》的信件与笔记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再没有哪个孩子的灵魂比小波德莱尔更柔软,更恋慕温情,更充满渴望与幻想:这样的灵魂对于把“为艺术而艺术”②的一代人耗尽的“烦恼”(l’ennui)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目标。在他最有名的一篇写给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假若有什么人年纪轻轻就饱尝忧郁滋味,当然,那就是我。”[19]
波德莱尔的自传作品中的烦恼与忧郁就像冲垮大堤的洪流一样汹涌,这也是我们热切关注该作品的理由所在。主观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它的顶峰后,走向了解体,自传作品也从竭力刻画一个坦诚的真我转向无法排解的忧郁情绪、主体危机等主题。
四、纪德:虚构与隐匿
《如果种子不死》作为我们研究的蓝本之一,是纪德的第一部自传作品,通过叙写自己童年、少年的生活经历,纪德试图寻找自己个性形成的根源,为自己的同性恋辩白。我们将分析这部作品中自传契约的构建以及虚构成分的渗透,解读法国自传作家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所完成的蜕变,即隐退与淡出。
书名《如果种子不死》出自《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死而复生后对众人说过的一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③这个标题意在表明,纪德的同性恋自白是一种为了同类的牺牲。《如果种子不死》的主线是纪德对自己道德观、情感观等不同心理层面嬗变过程的回顾与建构。这一叙述主线的确立与纪德当时面临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密切相关。借助这部自传的写作,借助在自传中建构一个叙述之“我”,纪德希望能从危机中解脱,并对世人的责难进行自辩[20]。
关于作品真实性的誓言是自传家的专属行为,也是自传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几个例子:“我自己是这部书的素材”[21];“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22];“我希望自己不撒谎、真诚地,像给朋友写信一样愉悦地侃侃而谈自己的人生。”[23]这种契约是自传所固有也是特有的,没有它的自传不能称作是自传,而只不过是一本小说罢了。然而,纪德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的第一部分却是这样结尾的:“回忆录永远只能做到半真诚,不管你多么关心真实,因为一切总是比你说出来的更复杂。也许在小说里更加接近真实”[24]。这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一句话,如果考虑到所有自传理论都提到过的一点:通过表现极端的诚意来接近自身的真实。显然,纪德也不例外,他并没有违背自传文体约定俗成的要求,即作者与读者建立契约,承诺讲出关于自己的真实情况:“我追求的不是逼真,而是真实”[25]。
《如果种子不死》中的自传契约是以分散在文中的形式呈现的,与卢梭、夏多布里昂等人的作品中围绕序言展开的情形不同。一些古典自传家在创作时,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表明其作品从属于什么文类,有时这种谨慎关注会因多种类型的序言的撰写(卢梭等)而达到极致,毕竟作者的写作意图宣言是人们对个人文学接受的根基。所以,《如果种子不死》里自传契约的碎片化与模糊性为我们揭露了纪德与其文本惯常的虚伪性。但同时,这部作品也包含了许多自省的片段,为读者呈现了自传契约的基本要素,即动机的真实性,后者在此似乎能起到赎罪的作用:“……我的叙述只有真实才能站得住脚,权当我写这些是一种忏悔吧”[26]。一个毫无戒心的读者或许只能读出字面上的忏悔之意,而不能破解作者的伪装,理解其奥古斯丁式的写作手法。
纪德的确是为了向他人公开自己的同性取向而创作自传,但他的忏悔并非出于内心需求,反倒是有自己的谋划,希望能借此引发一场风波。为符合自传的法则,他深知自己的书需要这样一份可耻的供词,一个诚意的担保。但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不论是纪德的自由,还是他的忏悔,其尺度都是变化的,根据当时的社会道德惯例,或是根据自传家的性格,视其对于戒规是遵从还是反抗。不少令人尴尬的证词都成了著名的忏悔文学作品,这也是读者们有时候会被这类写作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圣奥古斯丁关于自己偷梨的忏悔,卢梭对自己性行为、偷窃丝带、遗弃婴儿的细节披露等。这些事实往往隐藏着自传家的暴露癖倾向,满足了公众窥探他人隐私的欲望,并最终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快慰,因为他们终于能有机会揭开这些大人物的神秘面纱,一睹其荣光覆盖下的真实面貌。
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指出,纪德狡猾地采用自传体形式撰写《如果种子不死》,就是为了将自传契约的有效范围扩大到他的所有作品,这样当人们阅读他的小说时,就如同在浏览“一个人表露心迹的幻想”[27]。纪德自认为是“一个爱自言自语的人”,并且不愿局限于只能展现其人格一面的特定文体。只写自传并不能全面地呈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与斗争:“并非我硬要搞得这么复杂;复杂存在于我心里”[28]。为什么说自传无法还原人的真实形象呢?纪德说,这是因为“描述不能不有所选择”,而选择都是我们主观意识的产物。他在写作时,根据涌上心头的一些混杂的记忆重塑了自己的童年与青年时期:“我写自己的回忆录,信笔所至,并不着意安排”[29]。
作家所想要表达的和文本最终所呈现出来的,二者中间尚且横亘着许多能将事实扭曲的因素。作家从“过去”一路走来,却被“现在”禁锢,无论进行怎样的写作,都会使过去的面目失真。同样地,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始终存在于叙述者与其重塑的人物之间,使作者无法保持客观。勒热讷在《法国的自传》中罗列了一些在自传中难以做到真诚的因素,例如人从心理上正确认识自己是不可能的,作者极有可能编排、伪造事实以树立虚假形象,对于这个写作目标尚缺乏叙事技巧(写不出一个人生)。
《如果种子不死》既涵盖了严格意义上的事实要素,也具备一些显著的虚构性的标志。比如,纪德以这种方式写下了开头:“我生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为一种回顾性的叙述文体,自传记叙了一个真实人物的生平,如同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过一样。那么,考虑到自传家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对契约的破坏与滥用,作者怎么能说“我生于……”?只有他人才能说“他生于……”,而作者“我”可以按照我的方式来解读。这里的“我”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他”。
所以说,自传本身就建立在一个悖论上:真实只能通过虚构的写作来实现。这种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的模糊性是所有忏悔文学的内嵌特征。在纪德的作品中,这种特质往往伴随着他对自我的解构与重新建构。《如果种子不死》中自省的片段只不过是作者为了超越当前着手的文本、孕育下一个作品的一些尝试罢了。
五、结语
从演变史的角度看法国自传体文学,以卢梭《忏悔录》为首的十八世纪传统自传作品中,书写者以序言等为自传契约,笔触大胆、事无巨细地表现自我意识,这一阶段是极致而热情的表达高潮;以波德莱尔《我心赤裸》为例的十九世纪自我书写中,主观主义走向解体,自我意识逐渐碎片化,作品更多体现了主体的危机;到了二十世纪,以纪德《如果种子不死》为范本的自传,则更像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虚构的成分增多,作家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叙写在文本中已经难觅踪影。本文通过对上述三部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自传文学作品的解读,能够得出以下结论:法国自传体文学从18至20世纪的演变,表面上是文类形式的成熟与作品数量的累积,而实质上,书写者的自我意识却完成了从蓬勃发展,转入高潮后的解体,继而隐退的一个过程。
注释:
①法国自传理论家菲利普·勒热讷提出的著名概念“自传契约”(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意指自传者同读者之间存在一个无形“契约”,指作者要在文本中力证书写的真实性,读者才能相信其自传为真.契约的体现形式多样,常见的有以作者真实姓名贯穿全书,或通过序言、题记等声明其真实性.
②"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是1835年由Théophile Gautier提出的口号,基于对美的追求,指出艺术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道德、功利和教义目的.
③《约翰福音》第12章第24节,第25节,摘自《圣经》吕振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