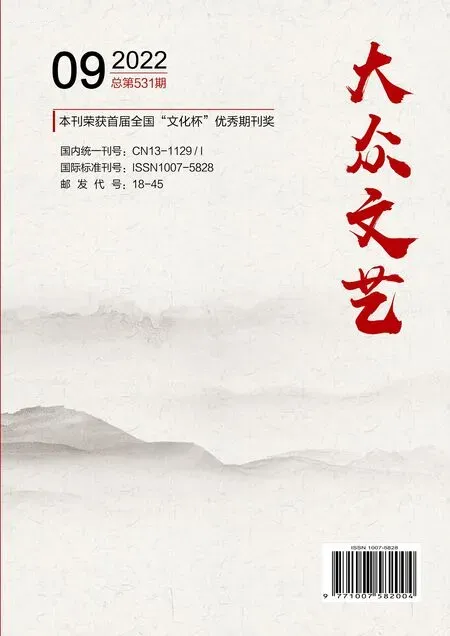离愁渐远渐无穷:夏目漱石《行人》中“行人”意象探析
王晓雪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750000)
夏目漱石后期创作的被称为“后爱情三部曲”的是:《春分之后》(1912)《行人》(1913)和《心》(1914)。这三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虽迥然不同,但也存在紧密联系,都是以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塑造了空虚痛苦的主人公形象。夏目漱石在《行人》中用平和舒缓的讲述方式塑造了在现代社会不断求索并叩问自己灵魂的男性主人公一郎形象,通过描述他在旅行中与周围人的关系,在动态的行走过程中展露其思想变化线索。根据对小说的梳理,可以看到贯穿小说的旅行主线。“行人”在字面意义上指远行走路的人,而在夏目漱石的此篇小说中,“行人”一词却包含了肉体和精神上的行走、探索的两重含义。可以说,“行人”一词微妙地贯穿了夏目漱石《行人》的全篇。
一、“行人”的个人寓意
一郎作为明治末年封建大家族长野家的长子,被定义为家庭的最高权力者。但他作为矛盾重重的明治社会中的个人,却逡巡在探索个人价值与精神准则的路上。一郎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他看不惯旁人伪善的自白,认为自己是道德的捍卫者,他的性格古怪多疑。汲汲追求绝对境界的一郎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连一时的胜利者也做不成,永远只是个失败者”。一郎在与好友H出游的旅途中坦白“我坚决承认绝对的境界,但是,我的世界观越是清楚,绝对就离我越远。”敏感多疑的一郎用自己的生活哲学同社会做着隐忍的对抗,但在生活面前却又不得不卑躬屈膝,将自己伪装成一个风度翩翩的君子。
一郎明明对社会有着更高的绝对追求,但却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妥协得以在社会中立足。这种看似合理的适应社会的理性做法却在一郎的内心激起了更加波澜壮阔的矛盾。他认为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不仅达不到目的,也没有意义。一郎将自己的自我怀疑与内心体验逐渐放大,“我把全人类的不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然后体会着这种不安中生出的每分每秒中累积起来的恐惧。”这种近似于宗教家的思考方式将一郎置身于不被社会理解、独自品尝孤独的蛰居者状态。日益加剧的对自我、家庭、社会的质疑压迫着一郎紧张的神经,他对社会“纯粹真诚”的向往与追求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一郎的头顶,这既是自我对社会的伪装,也是一种缄默的反抗。
情感作为创作的动力,又支配着作者对自然的描绘。夏目漱石将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相结合,把人物的心理态度与小说的情节发展融入到所描绘的环境当中,具有非凡的效果。小说中对雷雨天气有六次描写,例如,一郎要求二郎与阿直单独外宿时,黑压压的天空与暴雨来临前的闷热天气代表着主人公紧张、激动的心情,同时暴雨将要来临也预示着在长野一家中将要掀起一场犹如暴风骤雨般的纷争,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完美地烘托出了人物跌宕起伏的情绪变化。另外,我们发现,当一郎被扰人的思绪纠缠时,暴雨天气总会不期而至。当二郎无法忍受一郎对其猜疑和斥责,毅然决然地搬出家庭独居时、嫂子阿直独自来探访他时、一郎下定决心和H去旅行时恰逢都是阴雨天气。阴雨天气像一个屏障,隔绝了一郎与家庭中其他人的交流,他拥有暴风雨般凌厉、孤寂的性格,成为了囿于书斋的孤独学者。矛盾的思绪与宁静的雨夜融为一体,风雨之夜掩盖的是长野一家躁动的、几近喷涌而出的不幸。
夏目漱石的“则天去私”思想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他晚年提出了“则天去私”的信条,即依据最高法则“天”而舍弃自我。他把西方文明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带来的社会问题寄希望于“无我之境”与寄身于大自然来解决。统而观之,夏目漱石笔下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种种人物与其求索的过程都与他的这两种文学创作观念息息相关。
集中展现一郎心理状态的是《烦恼》一章,一郎对社会和自我的期待是“绝对纯粹”,他在旅行中试探着他人,但社会的虚伪却令他失望。对于自身,一郎希望自己由研究型转向实践型,他对自己有更高的心理期待。而在社会中伪装成谦谦君子的一郎对自己的内心都无法真诚,更是达不到对自我高期待的要求。在整部小说中,作者以“行人”为题,十五次描写了哥哥一郎的旅行经历与感受,其中多次表达出了对水的厌恶,对山的喜爱,而这一喜恶态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郎在大阪主张让弟弟二郎与妻子单独外宿借以测试妻子的忠贞,他对家人的猜忌也逐渐使其在家中处于孤立状态,一郎对外界的不满与不信任逐渐使之在自然中寻求解脱。
在《行人》中,一郎憎恨身边人的伪善与不真诚,他宁愿顶着暴风雨被自然征服并且不断地说着“痛快”,也不愿意对妻子阿直坦诚,心平气和地谈论、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在自然中求索的方式也印证着他内心的想法。他讨厌波涛汹涌、瞬息万变的水,喜爱静止不动的山,这种静态事物能够使他获得内心的平静,也是他决绝追求“纯粹真诚”的一种满足。夏目漱石“则天去私”的思想在创作上体现了追求自然平淡的侘寂之美,不讲求技巧,而在塑造一郎形象时,也体现出了“则天去私”思想影响下的用自然、禅、悟的方式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痛苦。
二、“行人”的家庭寓意
《行人》是1912年至次年发表的小说。在二战之前,日本家族形式受到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夏目漱石创作的《行人》和作品中主人公一郎所处的时期,正是受传统家族观念影响的年代。家庭本应该是一个家庭成员紧密联系的存在,但现实生活中却不尽如此。夏目漱石通过“叙述者”二郎来讲述一郎与阿直的不幸婚姻,进而叙述了一个在世事纷繁中不堪烦忧的大家庭。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长野这个大家族中,一郎夫妻二人与家中其他成员格格不入,这种苦闷状态与疏离的关系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
长野家是明治时期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一家,本该和谐的家庭却因一郎孤傲猜忌的性格和一郎夫妻之间的不和扰得不得清净。一郎是囿于书斋当中高尚、迂腐、又难以坦露自己心迹的家庭一员。他被父母偏爱和骄纵长大,却又偏偏得不到最亲近之人的理解,这难免加重了他心灵的负担。家人无法理解一郎的精神状态。一郎在大阪的旅店中曾经回顾过去,谈起自己认为最有趣的挥棒人和大力士的故事时,母亲和妻子却听不懂,难以参透其中的趣味。长此以往,家里人对敏感的一郎都客客气气、敬而远之了。原本一郎与弟弟最为知心,但一郎却怀疑妻子与弟弟有染,这种猜疑的心态加深了他与家人之间的隔膜,也让他几近崩溃。
在小说当中,一郎与妻子阿直鲜有直接的沟通,两人扮演着“相敬如冰的夫妻”角色。一郎性格暴躁,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阿直虽随和却又十分冷淡,在家庭当中仿佛一个身外人。他们这种缺少有效沟通的相处方式造就了夫妻之间的矛盾隔阂。在长野一家从和歌山回家的火车上,二郎一直挂念着哥嫂之间的关系。嫂子随心所欲、收放自如的冷漠态度使二郎对哥嫂的关系摸不着头脑,而此时,二郎将嫂子想象成一条柔软的大青蛇,紧紧缠绕在正在睡眠的哥哥身体上。蛇是阴柔的女性象征,是二郎对嫂子阿直的直接假想。化身为“大青蛇”的嫂子具有掌控哥哥“脸色”,即其心理状态的绝对权力。阿直内敛的性格不仅不能缓和冷漠的夫妻关系,反而在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生活上雪上加霜,正如缠绕的大青蛇一般,是错综迷离的危险信号,这也加剧了夫妻间的隔阂。
夏目漱石曾经概括自己的有“余裕”的小说是从容不迫的小说,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是普通平凡的小说。在《行人》中,夏目漱石践行着自己的“余裕”论。他用舒缓平淡的口吻叙述事件,将日常生活讲述得饶有趣味。《行人》多次借二郎与阿直的对话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一郎与阿直冰冷矛盾的关系。一郎与阿直像《秃头歌女》中的那对夫妻一般,关系冷淡,对彼此的喜恶完全不熟悉,而一郎却妄图探求阿直的内心并把控她的精神。
夏目漱石用一种闲适趋缓的讲述方式娓娓道来,他站在二郎的视角,从容地将叙述人拉到读者面前,将一个家庭的破裂用自然舒缓的语气讲述出来。这种缓缓叙述现实冲突的方法也成为了夏目漱石“余裕”观的实践。在《行人》中,夏目漱石站在“余裕”的立场上,让主人公采取不断旅行的方式,在旅途中寻找现实之外的艺术与美的世界。他采取旁观的态度审视主人公的命运,以一种平淡、超越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出家庭悲剧,体现出其“余裕”小说观在作品中的实践。
三、“行人”的社会寓意
日本明治维新主张开化,向西方学习,但是西方几百年的开化过程被日本短时间内吸收,难免会造成学习结果的“水土不服”,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促使每个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选择,处在社会当中的个人也变得焦躁、迷失,找寻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意义。夏目漱石面对社会和精神的压力,站在时代的高度,塑造了鲜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揭露了社会存在的弊病。
社会与家庭的压抑一如既往地限制着个人的发展。陷入精神危机当中的一郎在好友H的带领下开始在旅行中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试图寻找出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仅仅是中国民众的痛苦选择,也是日本知识青年在社会危机的压迫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行人》当中一郎表白自己也想像香严和尚那样卸下所有的重担,变得轻松,但是受制于社会与家庭中的一郎却无法摆脱自我的束缚,得到绝对意义上的解脱。
一郎的婚姻家庭是包含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西方文明开化的思想逐渐影响着日本社会,最具敏感性的日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缩影强有力地表达着自己的彷徨与忧虑。在《烦恼》部分中,夏目漱石着重叙述了一郎与H君的旅游过程,在其中,一郎的精神迷失与寻找过程随着旅游的线索一步步发展起来。一郎表白自己想追求最纯粹的真诚,然而他将全人类的不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然后体味着从不安当中累积起来的恐惧,这又让他精神疲惫、痛苦不堪。“要么死、要么发疯、再或者就是入教。”这是绝望的一郎在痛苦当中给自己的三种选择,同时也是夏目漱石面对自己不能左右的现代化社会生活开给自己的一剂药方。
夏目漱石是受西方近代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自由民主的思潮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面对近代社会生活的剧变,夏目漱石直面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将时代的缩影聚焦在痛苦迷茫的知识分子身上。一郎自称自己是一个“研究型的学者”而不是一个“实践型”的学者,并因此十分苦恼,一郎面对家庭矛盾无作为的态度也使他逐渐走向痛苦孤寂的边缘。但一郎的生存困境并不是作者想要描绘的社会个例,他孤立无援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是整个日本现代社会青年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我是猫》中的苦沙弥还是《三四郎》中的三四郎都无一例外的表现出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心灵的苦闷和在社会当中的孤立无援。夏目漱石全面地反映了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之下的知识分子苦闷迷茫的将身状态,在文本中实践了他的文艺创作理论。
总之,一直痛苦探索并且认为“无论怎样努力,幸福依然在彼岸”的不仅仅是迷茫无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郎一人,夏目漱石在文学与社会的探索中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儿。夏目漱石借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表现自己对整个社会的担忧,这不仅仅是一部描写婚姻生活的爱情小说,围绕着核心事件,作者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性、宗教的诸多思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亘古萦绕在文学家的心中,因而不得不说,夏目漱石也是逡巡在精神探索上的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