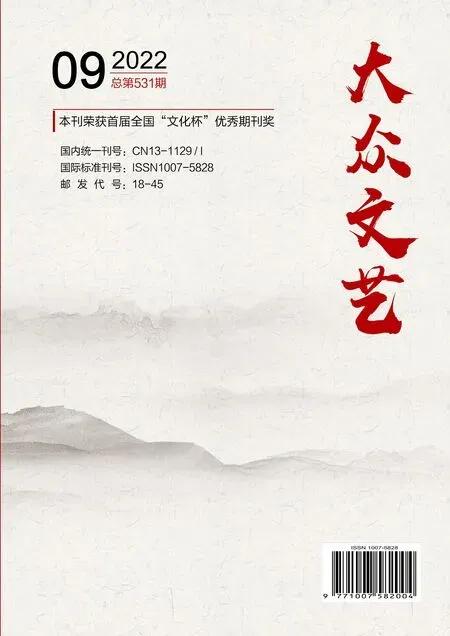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纵欲”对屠隆诗文创作转向性灵的影响
韩延波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550025)
“性灵说”是明代十分重要的一种文学理论主张,经过公安派大力提倡之后取得了广泛影响。而之前的复古占据文坛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字摹句拟的不良影响,僵化了文学的创作。屠隆是首先意识到复古弊端的人物之一,也是性灵论的首倡者之一,在他身上体现出复古与性灵的双重性,复古与革新的矛盾双方集于一身并得到了完美体现。
屠隆是一个情欲极其强烈的人,自然要通过一定的方式释放出来。而诗文创作自然而然地便将屠隆狂放的生活记录进去,这使得屠隆的诗文之中具有了一种特质,而这种特质就是“性灵”。这种创作是先于理论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状态。他认为情欲是人的天性,而“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写性情者也”,既然文艺应该写真性情,那像《叨叨令》这样的情色描写自是不必忌讳的。而这种“情真”恰恰是性灵所必需的。如其对私生活的描写:“朝从博徒饮,暮向娼家眠。行乐度年光,诗书不足观”。这不仅反映出屠隆的“纵欲”,而且也反映出屠隆的创作是“真”的,他不避讳自己的不检,反而大胆地表现出来,这就是“真”。正是因为在屠隆对“欲”的表达之中表现出了“真”,而这种“真”恰是性灵的因子,这些因子最终促成了性灵说。
屠隆的“纵欲”是贯穿始终的。通过对罢官前后屠隆“纵欲”的对比,可知罢官后他对“欲”的放纵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加速了性灵论的产生。我们可以这样说,屠隆对欲的表达越强烈,他对性灵的呼唤就越迫切。而屠隆所言“性灵”主要便是“真”:“即表达真性情、真情感,表现真生活,反对虚伪矫饰。”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肯定人欲的客观要求,形成了个性解放的潮流。但这种潮流却极易走向极端,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走向纵欲。屠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追求个性的展现,推重“真我”,最终由复古的推崇者走向性灵论的先导。由于受到整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屠隆的“纵欲”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种对欲望的放纵正是个性的解放和对礼教的轻蔑,是与时代潮流相应的。屠隆认为:“凡人情感于外而动于中,一有所贪恋,一有所住着,即细微丝发,皆欲也。”他一一列举了各种“欲”:“富贵荣名、酒色货财、歌舞声伎、滑神荡志、耗精伤身,故名之曰欲。”而男女之欲也自然地包括其中,并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屠隆的“性灵”论是以“真”为核心的,而欲又是人本身所固有的真实存在,那么受晚明个性解放的时代性影响下的“性灵”便具有了一种意味,即真实地表达“欲”,而不必对其遮遮掩掩。
虽然屠隆平日纵欲,但他对“欲”也是怀有惧意的。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及纵欲的危害性。《欲怒》篇说“欲火一然,至伤败伦理,破灭家身”。而且他还经常作警语,劝告世人不要沉迷于欲望。他把红颜比作白骨:“二八佳人,翠眉蝉鬓,销魂也,白骨生涯”;将淫色作为破家亡身之事:“如此则楚馆秦楼非乐地,陷阱之渊蔽乎!歌姬舞女非乐人,破家之鬼魅乎!颠莺倒凤非乐事,妖媚之狐狸乎!”这些言论往往使人误以为屠隆并非纵欲派,而是禁欲主义者了。但联系到屠隆生平的狂放不羁,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屠隆对于“欲”的担心害怕,乃是出于对自身的忧虑。正是由于自己纵欲一发不可收拾,久而久之便产生了焦虑。而他对世人的劝诫之语何尝不是对自己的警告呢。
屠隆受三教影响,也希望修心去欲。如其在《与王辰玉》中所说:“政恐儿女情深,道心退堕,须从爱河急猛回头。”正因为对“纵欲”的焦虑和想要修心静持的愿望,使得屠隆想要去克制欲望,“独无如名障欲根之难去矣……解脱如此不已,倘微有进处,以不负长者诚灰灭无恨”。然而“名障欲根,苦不肯断。世上万缘,独此二物为难除……乃知病根尚在,特潜隐不发尔”,“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般不破,若以巨石压草,石去草生,若以冷泉沃渴吻,暂时清凉,过而复热”,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屠隆在信件中说到自己“三年治欲”,而其服膺二氏的原因除了排解罢官后的失意之外,恐怕也想要借助佛老作为自己“治欲”的手段之一。罗宗强先生在概括明代纵欲风尚发展过程时便说:“极度纵欲而得病,于是信净土,求仙道。”虽说屠隆未必得病,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试图借助佛道来治欲的现象。郑闰便言:“屠隆的闲繙二氏,蒲团入道、静心顿悟乃是他强行克制自我欲念的方式。”正如屠隆所言,“读二氏书,志在清虚恬澹,解缚荡累”,目的是使心灵清明,解除精神上的负担。他在《与赵汝师司成》中说,“仆年来万念俱空,一丝不挂,闲中无以自娱,稍取三教理参订和合”。既然他说自己“万念俱空”,又说自己“独苦名欲根不断”,这难道不是互相矛盾吗?这也只是其自我安慰之语罢了。黄霖评价说:“他本来就‘行类滑稽’,好作‘游戏之语’,殊不类释道之徒。”吕天成《曲品》也说:“屠仪部逸才慢世……偃恣于娈姬之队,骄酣于仙佛之宗。”屠隆崇仙学佛,却又不忘“娈姬”,两相对举,殊为滑稽。更为可笑的是,屠隆本来是希望借三教以去欲,但最终却在佛道之中为自己纵欲找到了借口:“隔壁闻钗钏声,比丘名为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室与妇人处,罗什不碍成真。罗什之心不入故也。固知染净在心,何关形迹。”于是这一手段最终也失败了。禁欲的失败使屠隆意识到“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情欲是人的天性,“夫生者情也,有生则有情”,“其根固在”,是无法消除的。既然如此,那就按照自己的本心行事,放开对自我的压制,干脆走向它的反面——“纵欲”。
由此可见,屠隆经历了由对“欲”的克制到“纵欲”的过程。想要禁欲却没能做到,他也只能为此寻找借口,“贤达风流市人亦风流,贤达放荡市人亦放荡。贤达市人之所以异者在心之染不染也。”只要心不染,也就是保持“真心”,放荡风流都是无所谓的。《鸿苞·艳歌》也同样说“本色不害道,去其情,终日艳歌,终日是道,不去其情,终日不艳歌,终日非道”。也就是说只要“去情”,做到“本色”,终日艳歌亦无妨。
“性灵”既然是自由地表达真情实感,而人的情欲也是情感之一种,这种“性灵”文学观必然要对“欲”进行书写。屠隆的“性灵”与“欲”是分不开的,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事实上他在创作中表现的却是强烈的含有情识欲念的性灵。他所追求的本然之性灵是真,他在创作中也便呈现充满欲望的性灵。”而屠隆也希图借“性灵”的论调来达到宣泄情欲的目的,那么必然会在文学创作中留下痕迹。既然“性灵”的核心是“真”,我们就要看他的作品是不是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心境,是否如实地表现“欲”。他一生所创作的几部戏曲,如《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等大都是随意抒发情感的狂放之作,如其在《昙花记自叙》中所说的那样要“顺其欲而潜导之”,这也未免带来他人的指责。如管志道便斥其欲以声色化民:“近来淫曲滥觞,此作真是绝唱……《昙花》之绮终在声色之于化民,末也。声色而入剧戏,所化几何。亦犹或紾其兄之臂而谓之姑徐徐云尔。”这种指责当然是相当严厉的。
我们既已得知屠隆是一个欲望十分强烈的人,他怀有满腔情欲,自然想要释放出来。他的狂放行径便是一种释放的方式。但是,这种借狂放以抒发欲望的方式毕竟十分有限,而借助写作来抒发欲望便成为了日常的方式。
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说:“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来减弱他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并且在表达他的幻想时提供我们以纯粹形式的、也就是美的享受或乐趣……向我们提供这种乐趣,是为了有可能得到那种来自更深的精神源泉的更大乐趣。”这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就像一种幻想和白日梦,它可以将在潜意识里压抑的欲望通过写作宣泄出来。因此,写作无疑是一种宣泄欲望的方式,而屠隆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采取了诗文创作的方式来达到发泄欲望的目的。
屠隆在《欢赋》的序中说,“余处冗贱,百忧煎人,侧身天地,长苦局蹐,思欲挥闷散心,寄兴褚墨……友人冯梦祯谓仆曰:子何不为欢赋,悦心畅意,破彼我之烦闷,宣万物之郁塞,则此道贵矣。”由此看出屠隆认为文学创作可以达到“挥闷散心”“悦心畅意”“破烦闷”“宣郁塞”的作用。
此外,他在《鸿苞·诗选》中也说得十分明白,“夫诗者宣郁导滞,畅性发灵”,他认为诗歌的作用就在于“宣郁导滞”,而这里的“郁滞”虽难以确切指明,但从前面屠隆对欲望的苦闷可以看出,人的欲望在这里恐怕是占重要部分的。郑闰也直言:“‘有情则有结’——情欲郁结,也就是屠隆在《娑罗园题评》中指出的‘凡情自缚’的观点……屠隆提出‘有情则有结’的情欲郁结,人的情欲受到压抑,遭到郁结,是痛苦的。”屠隆既然承认诗具有“宣郁导滞”的功效。借助诗文来发泄,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将真情实感吐露于笔端,这与他的性灵论也就相符合了,因此他提出“性灵”来抒发欲望。
屠隆的性灵论讲的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情欲也是自然情感之一种,自然也就有写作的正当理由了。为了使自己所写的内容理所应当而不必受到别人的指责,这种肯定书写人的真情实感的“性灵”之论也就自然被屠隆所提倡。他在《与友人论诗文》中就为自己辩护说“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子所向,博综猥琐亦可”。这也就是说,只要是合乎真情,无论是高雅还是鄙俗,都可以写入诗文之中。而且他还用儒家的例子来使自己的观点合理化,“仲尼删诗,善恶并采,淫雅杂陈,所以示劝惩,备观省”。这里便利用孔子删诗之后保留桑间濮上之诗的典实,来明确地表示淫恶之辞亦可入诗。另外他在《太上感应篇序》中也说,“妙悟性灵,善恶俱融”,也就是只要是表达真我,无论善恶都要写进去,这才是真的。这无非就为屠隆借创作来发泄情欲提供了理论支撑。
另外,他在《昙花记自叙》里面也说道:“世人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投其所好,则众所必往也。”他提出对于人的“欲”,不能一味堵塞,而应该“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即予以自然疏导。在《章台柳玉合记叙》中他也提到:“每至情语,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绝,则至矣无遗憾矣。”这是一种“纵情”的文学观。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用“至情”,也可以说是“真情”,来放纵人们的情欲,以达到宣泄情感的目的。而对于屠隆自身,这种宣泄和疏导的方式还是需要借助可以“宣郁导滞”的诗歌。实际上,无论是屠隆借助性灵来抒发他人的情欲还是发泄一己之欲望或是兼而有之,性灵论都是一种为自己辩护的手段,其作用便是使欲的表达合法化。
综上所述,屠隆之所以由复古、格调转入“性灵”,“纵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催化剂。它在理论上促使屠隆的文学观念发生转变,也反映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综上所述,屠隆自身的欲望是最本质的动因,纵欲是其发泄的方式,写作是发泄的一种具体手段,而“性灵”则使这种手段获得合法性。其中“性灵”之所以能够为抒写欲望提供合法性,就是因为“性灵”是“求真”的。人的欲望是天性,是人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所以诗歌在表现“真我”的时候就不应忽视这一点。因此,纵欲是“性灵”的动因,是促使屠隆文学观念转变的重要因素。
——杨朱学说的异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