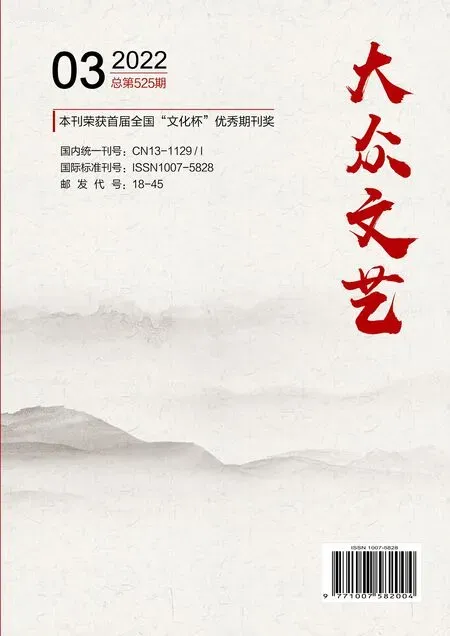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管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710055)
嵇康生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此时的司马氏篡权夺位,假借儒家“名教”之名,大肆压迫异己,以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此时的政坛及文坛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这时的文人们隐居山野,希望通过大自然的乐趣,修复心灵的创伤,寻求人生的真谛。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魏晋原本玄学当道,一众士人秉持着与自然为伍的心态畅谈人生,享受风光,嵇康这一提法,不仅对当时的玄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丰富的内涵和人生态度也对后世带来了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嵇康以诗词来表情达意,我们需要通过他的文字直达一颗火热赤城的心,了解他真正深深印刻在灵魂中的思想。“名教”一称,看似是简单的纲常人伦,道德规则,实则是对人性及本心的约束,冠冕堂皇称“以名为教”。正是这种看似合理的条条框框使嵇康看到了道德法规背后是对人性的束缚,是对人个性发展的封印,所以他提出“任自然”的思想观念,呼吁每一个个体以顺从本心的方式生存。
一
“越名教而任自然”出自嵇康的《释私论》:“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这里的“名教”指的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自然”指的是人或事物的本性或天性。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求人们摆脱传统儒家对纲常伦理苛刻的约束,遵从自己的本心,率性而为。嵇康笔下的孔子不是士大夫崇尚的神人形象,而是一个只为功名、因势利导的小人。嵇康眼中的“圣人”孔子尚且不同于寻常儒家士人眼中的形象,更休说他的“越名教”思想,更是不落窠臼、直斥其非。
(一)“去伪显性”,尚自然之美
所谓“去伪显性”,即“去伪存真显性灵”,这也是贯穿嵇康一生思想的重中之重,在自然之美方面,他崇尚天然无雕饰,这也是道家黄老之学的核心要义。嵇康的诗作中不常有纯粹绘景的作品,但对自然景致的热爱之情,无形之中渗透其中。
以嵇康《酒会诗》为例,全诗读来口齿生香,诗人借描写酒会中众人齐乐与自然之美景表达自己对自然的热爱与对功名利禄的不屑。全诗多处描写自然景观之美,“百卉”“崇台”“鲂鲤”“翔禽”“鳣鲔”皆是活灵活现的美景,仿佛使人身临其境与诗人一同感受着酒会的轻快愉悦,随之而来的是众人觥筹交错间的余兴节目,而最后一句“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可以说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将作者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这种寄情自然山水的生活态度正是他思想重心的真实写照,他不痴缠于功名利禄,将自己真实的本心放在第一位,任由自己的情感宣泄不受束缚,这才是他心中向往的所在。
嵇康《诗》中运用比兴的修辞手法,用群鸟嬉戏引起作者想要表达的人生感悟。人生在世,要如群鸟一样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这里笔者将其引申为感叹人生短暂,不必为礼法所束缚,而应该解放天性,顺应自然万物原始的生存发展规律。这恰恰也体现了老庄思想对嵇康的影响,顺应天时,无为而治。
(二)“浩然之气”,崇刚正不阿
孟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提及人要有浩然之气,即“正”与“义”之气,嵇康真是因为这样的思想储备与境界,在世俗之气摇漾的社会中,仍不改其志,砥砺前行。
高平陵政变使“竹林玄风”成为文人士子间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曹氏集团与司马氏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发生在魏晋玄学兴起的初期,两股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一方面拉通士人,另一方面也荼毒士人,许多文人志士在此情形下不得不选择保持中立或疏远朝政。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安定又充满白色恐怖的高压统治下,一些名士藏锋不露,避世独行,在世外桃源之处展开了一场旷世之风,竹林玄风。嵇康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嵇康个性孤傲,特立独行,绝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嵇康坚守志向不愿为官,即使当时司马昭想聘他为掾吏,他也无动于衷。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带领众人前往。等候很久也没有见嵇康回应,便打算离开。此时嵇康开口问:你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了什么?又是想见了谁再离开,钟会答:为听到听闻过的而来,为见到想见的人而去。二人因此生仇。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吏部侍郎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明自己的志向,绝不屈服于自己所不齿的思想毒瘤。
嵇康秉承这种刚正不阿的态度,特立独行,正如《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写,山涛投靠司马氏后希望他也同自己一起入仕,但是非但没有将嵇康拉拢为己用,反而招致嵇康的嫌恶,以一封绝交书斩断了二人之间的关系。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嵇康虽然语气不甚严厉,但却坚定不移,这也表现出嵇康不与当时的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高洁傲岸的品质。所谓“越名教”正是这种不与这种束缚人性的礼法相迎合,顺从自己内心的轨迹,渴望自然的天性得到解放。
二
(一)对儒家思想的“破”与“继”
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政治因素的催化中不断趋于繁杂,这一时期,儒学在不断地冲击中本应变得羸弱,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在道、佛、玄的冲击下反而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许多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思想。当此时,依然有许多士人坚定不移的支持儒家思想,并在不断的改革与提升中丰富和完善儒家文化,从而使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得到巩固。他们认为将儒家学说同神相提并论并没有什么用,所以提出了有无、本末、体用等哲学范畴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他们表面上推崇玄学,内里依旧无法破除儒学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尊崇孔孟之学大于黄老之学,认为儒家名教依旧具有社会价值。
司马氏“以名为教”的统治理念使文人志士生活在思想高度受限的氛围中,然而所谓“名教”不过是当权者巩固统治的工具,嵇康所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并非一味地否定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礼教礼法。正所谓“不破而不立”,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看似是对儒家腐朽文化的鞭笞,实则正是以循序渐进,先破后立的方式对儒家刻板的教条进行改革。“越名教”着重从“破”入手,从现实出发,揭示礼法的漏洞,使人民的本性得到解放。“任自然”从“立”入手,重新建构一个适合人民生存的舒适愉悦的生活环境。
与其说是彻底否定重新建构,不如说是取其精华,重新利用。嵇康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依然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并且重构仁义礼智的框架,在《释私论》中,他认为心中无是无非,行为不违背大道才是君子的本色,只有心胸宽广,无私坦荡的人,才能保持高洁傲岸的本性,因为 “无措之所以有是,以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则无道以至非也。抱一而无措,则无私。”虚以待人,无是无非,心无私欲,才能达到与礼教合一的状态,嵇康这一观点与儒家思想的礼教观相一致,由此观之,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起源于儒家思想,不同的是,其思想不断向道家思想靠拢并取其精华,择优继承。嵇康思想及当时的玄学之风看似与儒家经典相背离,事实上却是用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来调和,使儒学在创新与改革后重新适应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
(二)对道家及黄老之学的“变”与“通”
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源于当时的政治独裁,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援天道以论人事,最终取代黄老之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然而以“天”为道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治人的认知,王充就提出“自然元气说”对这种思想进行批驳这种批判也是承袭自黄老之学,而嵇康的思想与王充可谓不谋而合,嵇康“任自然”的玄学理论来源也初见端倪。
魏晋之际,儒道两家的结合逐渐分裂,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玄学思潮开始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进行扬弃,转而质疑儒法之士。道德实践的经验集合造就了儒家思想中的合理人格,其根本还是人的欲念所致,是有目的的世俗实践,而道家则更注重由内而外的造化,不为改变表象而努力为提升内在人格素养来实现外在表现出的高尚,站在“道”的高度审视人性与人格。因此,初期的玄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中“任自然”的说法正是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熏陶而产生的。
《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法可得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指出,精神对人体的影响是巨大的,只有人的精神康健,人格健全,才能够形成好的“形”,内在的“神”作为外化的“行”的根本,具有决定性作用。嵇康就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以神为主,兼而养形。
二、嵇康强调,如果不注重养生,肆意妄为,纵欲张狂,不尊重身体应该具有的调和环境,那么,便无法做到“养身”,没有养身的基础,更不必谈养心的达成。如果长久如此,人的身体并非草木与石,怎能经受长期内外消磨,必不能长命快活。
三、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养生须长期坚持方能有所成效,若三心二意,不持之以恒,也难有所成,不仅如此,须得又一人作为榜样,才好时时效仿,也是自我监督一种方式,如此便可“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道家思想崇尚“无为而治”,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就是让万事万物依照自然的顺序发展,不对其进行人为的干涉,“任自然”与之相同,任由事物自行发展,尊重自然的本质与力量,简而言之即是“顺其自然”,不做过多的染指与改变。
嵇康也认为“道”是人生存的本源,认为人应该顺应天性,即所谓的“道”,同时他也认为“无为而无不为”作为治国之道并无不可,反而因为顺应了自然,使国家发展得更加合乎天、地、人三者的共同发展趋势,所以在纠正儒家“名教”思想的同时也提出顺应自然的“任自然”说法,而“任自然”的出现则是要以“越名教”为基础的。
(三)对庄子“养生”思想的“传”与“承”
黄老之学经历了东汉末年的大动乱,社会形态在急速变化之后,人们仿佛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之处,道家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这得益于老庄思想简约自然的特点。经历了两汉经学浩浩激荡后,此时的魏晋士人已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急需在精神上寻找慰藉,而老庄哲学应运而生,成为魏晋士人疲惫精神的的休憩港湾。
当此时,以老庄哲学为内在核心的魏晋玄学因势而起。在玄学众多流派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重自然派具有较大影响力,嵇康以庄子为思想向导,在汲取庄子无为思想的同时也领略他飘逸旷达的精神境界,从而培养自己的文学思想及艺术气质。
老庄哲学虽将战乱、病祸、生命的短暂看得十分旷达,但从他们都极注重养生来看,对“生”的眷恋与渴望依旧是永恒不变的命题。嵇康《养生论》中认为“理”就是“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他的养生理论加入了庄子许多重要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庄子阐述了养生重在“缘督以为经”,即顺其自然,不受心灵的桎梏与羁绊。庄子认为,私欲是与人的自然发展相悖的,人只有抛弃私欲,或者较少私欲,才能达到心灵的纯净。
嵇康对于庄子的思想继承了其对本心的放纵,他所提倡的并未同老子一样是完全的“道”与“无为”,还有学者认为嵇康思想看似与黄老之学顺承,实则是披着“自然”外衣的礼法制约,更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弘扬。针对“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虽然有相当部分内容源自儒家学说,但究其根本,是对当时儒家思想禁锢与束缚的割裂,更多的保留了道家及老庄思想中对于尚真尚简、返璞归真的向往,以及对礼教束缚人性的反对与斥咄。单纯说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未免有片面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