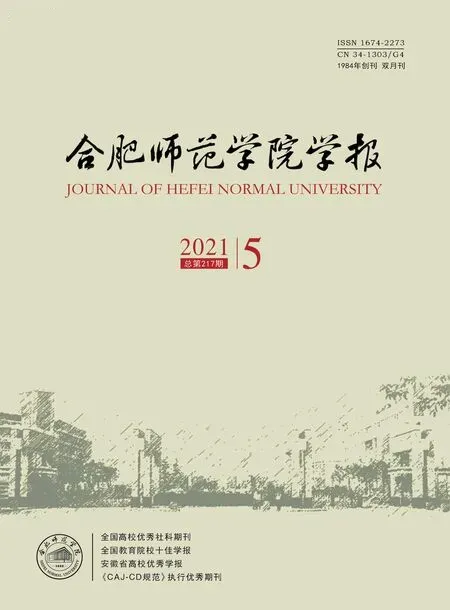王茂荫廉政砥品家训对领导干部家风培育的启示
张珍珍
(合肥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要求党员做到“克己奉公”“崇廉拒腐”“勤俭节约”等,要求领导干部做到“廉洁从政”“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等。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重申无论党员和干部都“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1]。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2],要求把艰苦朴素、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和对党忠诚纳入到家庭建设中来。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徽州歙县人,首倡清廷发行钞币,作为清朝货币理论家和财政学家,是唯一一个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中国人。目前对王茂荫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其生平追溯以及文献整理、注疏和辨析,另一方面是对其纸币思想、货币改革论以及人才观等方面的研究,集中对其经济金融领域的思想进行研究,对王茂荫家训研究甚少。王茂荫名垂青史亦非只有其卓越的经济才华,更以廉政、謇谔、孝悌流传后世。本文通过其遗留的千字家训深入分析王茂荫廉政砥品之理路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领导干部家风培育提供借鉴。
一、王茂荫廉政砥品家训之理路
晚清以降,外临西方强敌的军事侵略,内有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举步维艰。面对时局,王茂荫仁孝治家、尽忠报国、廉政奉公,以其身教重过言教,留给子孙千字家训。
(一)以孝悌为圭臬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孝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赡养老人是对孝的表面认知,还要敬重父母、继承父母遗志,再深层次理解就是对君尽忠视为大孝,忠孝一体,使孝完成了维系家族与政治的伦理纽带的功能,所以,孝悌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家训的半壁江山。
王茂荫认为孝悌为家庭根本,守之则昌,失之则亡,遗训王氏子弟代他在方太夫人身前尽孝,要求子弟遵孝悌守纲常,提出:“孝弟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字,其家断不能昌。”[3]168王茂荫在京为官将家眷留在老家代为尽孝,且每次家书都会问候家中的长辈尤其是方太夫人的身体状况等,多次叮嘱子女要代父行孝,孝顺祖母恭敬叔伯。王茂荫认为孝不仅仅是赡养敬重,更重要的是遵从先人之志,为官清廉謇谔尽诚。方太夫人对王茂荫等人读书以识义理、达孝贤为期望,不以及第登科为目的。故而,当王茂荫农部得官乞假归省,方太夫人教诲他做官要尽忠职守,守清白家风,千万不能被高爵厚禄所迷惑,叮嘱王茂荫:“汝宜恪恭,尽乃职,毋躁进,毋营财贿。吾食贫有素,与家人守吾家风,当不致冻馁,愿汝无忝先人,不愿汝跻显位、致多金也。”[3]282王茂荫以此为志,终身不敢忘。
(二)以廉政奉公为轨范
自古文人志士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孝悌文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忠报国的忧国恤民情怀有机融合在一起[4],在家尽孝,在堂尽忠,忠孝和家国是一脉相承的价值体系。
首先,以公而忘私、謇谔尽诚之圭表训诫子弟。王茂荫恤君荣辱、恤国臧否,以此教导子孙勿忘尊君安国。王茂荫丁忧期间本想告归,无奈外临强敌、内有匪乱,他不愿在清廷艰难危急时刻隐退,认为此举非君子所为,立意为君分忧解国之危机。“通籍食禄已廿余年,而敢於军书旁午之时,作抽身而退之计乎!义无可逃,非忘初愿也。”[3]168对于王茂荫而言,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是其本分,却因为时代局限有着忠君的迂腐与糟粕。
王茂荫以公而忘私为本分,做事以謇谔尽诚为圭表。王茂荫为官尽职尽责尽心,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前程。他曾经多次提出《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亦或《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皆“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3]171,甚至在咸丰流露出要去圆明园度假时,上奏《请暂缓临幸御园折》以“六个不可”劝阻其勿在时势艰危之时松懈享乐。王茂荫如此的立朝敢言、謇谔尽诚使之宦途坎坷,但他本人却胸怀坦荡,毫不在意,垂示子孙做官不能做尸居之人,更不能阿谀奉承,既居谏垣“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惟止可传家,不可传世”[3]171。
其次,以廉政奉公、廉介自持之表率训诫子孙。严守义利之辨、廉介自持为君子行为,坚守“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而不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5]。王茂荫“居官数十年来,未尝挈妻子侍奉,家未尝增一瓦一陇,粗衣粝食宴如也”[3]299,这就是其写照,对不义之财不敢苟取丝毫,可谓“京官无宅,钱官无财”。王茂荫对富贵功名等看得很淡泊,并不主张留给子孙银山金穴,认为子孙日后敦品力行福祸自求、各自努力勤俭治家必能发展。故而,王茂荫有言:“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吾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6]13
王茂荫率先垂范,教导子孙锱铢积累必重义轻利,不争钱财多寡。其一,见利思义。一个家族的兴衰要看子孙贤愚积德与否,并非是留给子孙银山金穴,而且正是对金钱的沉迷,后代往往自甘暴弃,游堕骄奢,品行败坏,反而容易招惹天灾人祸。故而,王茂荫告诫子孙品行败坏皆由财利起,处利害关头以义为准。“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3]169其二,家庭财产勿争多寡。世间杀父殴兄、家庭诉讼、争夺家产屡见不鲜,甚至还被百姓视为当然。如此这样,家无宁日、国无安好、社会风气败坏,究其原因,可能与家风不良有关。王茂荫平生廉介自持,没有给后代留下更多金钱上的财富,担心后人因生活贫困而罔顾伦理道德,因此谆谆教诲后代,家产上“勿因争多论寡,致失子侄之礼”[3]168,与人交往切记“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用不尽”[3]168。
最后,用以身报国之精神训诫子弟。王茂荫感恩清廷恩赐王氏一族的宠荣,食君俸禄为君分忧,在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清廷愈加举步维艰的时刻,萌生了“临危一死报君王”意念,愈发地想尽办法尽己之责,妄图一己之力来挽救清廷。“自揣不能出力杀贼,万一或有他虞,惟有以身报国。”[3]169尽忠报国在古代表现为某一王朝尽忠,尤其是在朝代更替之时,表现尤其明显,这种迂腐的封建教条和理念钳制了众多传统知识分子,却也铸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以身报国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
(三)以砥品植学为家法
立德为上。历朝历代修德齐家都是家训重要内容,重在对家庭成员的“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造就子弟“‘忠、孝、仁、信、勤、廉、耻’等道德品质,形成忠君报国、父慈子孝、兄弟和睦、邻里团结、勤廉节俭的家庭氛围和气候”[7]。王茂荫以身有道德、胸有诗书、家有正业来教子,以“才、学、识、存心”[8]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其中“才、学、识”是对才的要求,“存心”是对德方面的要求,四者最终以“存心”为正,以德为最高和最终要求。正所谓有德者正人近小人远,王茂荫教育子弟“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3]169。此外,王茂荫认为万恶淫为首,要后代谨记“戒色”。
行善先务。乐善好施、积善成德是徽州家训历来所强调的,加之王氏家族家风慈善,王茂荫守家风行善事,以身教为言,教育子孙“听好话,行好事,交好友”[3]171。王茂荫幼年入私塾,受塾师王子香厚爱,后王子香家道零落,王茂荫招其子来“所以慰劳勉励之甚挚,岁暮必邮金资助之”[3]251。资助亲族、捐助乡党更是常事,“戚党中之孤苦者亦按时资给,岁以为常。亲友称贷,必竭力以副”[3]251。凡是利乡利民的好事,王茂荫都欣然乐为,如修葺祠宇、修路修堤、造桥利民等事,无一不慷慨解囊,靡不量力佽助。
四业谋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儒家的耕读传家深入人心。王茂荫受“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影响,认为世家子弟要以读书为恒业为本分,于经术之中尽求人伦之道、尽得天下之理。若有治国才学可登科出仕,若无才识只求读书修身,王茂荫立下家训“日后子孙非有安邦定国之才,不必出仕,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3]170。长子王铭诏曾入邑庠,后捐贡生,“同治元年加捐中书科中书衔”;次子王铭慎“捐南北监”;三子王铭镇“授职员”[9]。另外,王茂荫支持子弟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这可能与其祖上及亲戚中均有人从事商业有关。所以,王茂荫曾提出:“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10]规定王氏子弟走正道、求正业、立正德、行正事。
二、王茂荫廉政砥品家训之基理
王茂荫廉政砥品的家训是和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伦理社会文化价值一脉相承。古徽州以“程朱阙里”名誉天下,程朱理学曾长时间占据徽州文化阵地,与徽州宗族制度融合衍生出诸多族规、家范、家训等,以族规惩恶、家范治家、家训教子,逐渐形成了徽州家训文化与传承。儒家思想是王茂荫家训的文化支柱和筋脉,古徽州家训底蕴是王茂荫家训的根基,再加上王氏家族良好的门风更直接影响了王茂荫家训的理路。
(一)徽州重文崇朱的文风
徽州人对读书明理、出仕做官给予期望,鼓励子弟读圣贤书识天下理。歙县名门望族许氏家训提出如果家族之中有聪明俊伟、家境贫寒的子弟,可以给予资助,帮助“有志于科第者也”[11]147。歙县谢氏宗族家规亦重视读书明理、敦品出仕的功用,提出“人家子弟,性资凶犷,礼貌粗俗,皆因不读书之故。宜延明师以教,端其性习,训其礼节。有志者,讲通义理,作诗、作文以取功名。不及者,亦要稍知文末,不失为士人”[11]124。基于此,徽州人重视蒙养教育,敬拜“养正于蒙”的圣功,家族设馆,聘请塾师教导本族童蒙,要求尊师重道,严加管教以望成人。歙县泽富王氏宗族立有“读书尚礼,交财尚义”[11]243的家规。明清时期的徽州“书塾数不胜数,座谈讲学蔚然成风,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历史”[12],重教育重读书氛围蔚然成风。
儒家伦理文化是徽州家训精髓,尤其是程朱学说对徽州家训影响更为深刻和久远,这与历史上朱熹三次返回徽州省墓或者讲学活动有关。在这三次活动中,朱熹培育出一大批徽州弟子,“歙县的吴昶、祝穆;休宁的程先、程永奇、金朋说……绩溪的汪晫等十七人。从此,朱学在徽州代代相传,相沿不绝”(1)周兆茂.论朱熹思想在徽州的流传和影响[J].朱子学刊,1994(00):93-113.。程朱理学成为徽州家训的思想指引,人伦有常讲孝悌诚信、治家有方讲勤俭和睦、居官有道讲廉政奉公、教子有法讲读书明理等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被徽州人视为读书圣典,是徽州家训文化和精髓的源泉。
(二)徽州重家训的家风
古徽州家训源远流长,尤其是明清时期各个世家大族所制定族规、家训、庭训等,涉及面极广,既有明人伦的孝悌教育,也有读书明理的治家教育,亦有廉政奉公的官德教育、童叟无欺的商德教育等等。这些观念在徽州广为流传,成为徽州人骨子里流淌的血液,成为徽州人的脊梁。重人伦敦品行是家训中的基石,“重伦理以教家。……然父子亲、夫妇顺、长幼序、朋友信,此等人而出事君,必为忠臣,为良臣”[11]127。重人伦讲孝悌是徽州必有的家训族规。而居官贫乏、做官清廉是徽州家训中所强调的官德教育。读书出仕以廉洁奉公为准,以两袖清风为绳,不能中饱私囊为患一方百姓。明朝嘉靖绩溪县葛氏宗族家训有言:“泛观世态,方穷居诵读时,不知学做好人。及得一第而居官也,则欺上剥下,无所不至,惟务足其囊箧,以为遗荫子孙之计……居官贫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如闻其丰裕,此是不好消息。”[11]2
清初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可谓一篇家训名著,流传甚广,王茂荫对《朱子家训》推崇备至,曾手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朱子家训》中的“经书不可不读”“自奉必须俭约”“为官心存君国”等思想对王茂荫家训影响甚深,不仅身教为范,严格自律,并亦从廉政奉公、勤俭持家、读书明理等方面制定家训,规范子弟言行举止。
(三)王氏讲忠孝的门风
王氏家族乃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历代家长都以孝行天下,以正直立于世。王氏家族原为唐代山西太原王仲舒的后人,后迁至徽州,到王茂荫时已是徽州王氏第十五世。王仲舒以“少孤贫,事母以孝闻,嗜学工文,不就乡举……贞元十年,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13]。王茂荫的曾祖、祖父、父亲皆敦行孝悌,曾祖王静远以孝义行于时,“事其父舜五公,不一日,离左右,父殁。事季父凤歧公如父焉”[3]279。在歙县的王氏宗族宗规中规定“为子者,必孝顺奉亲”[11]241。
抚育王茂荫长大的方太夫人对他品性影响很大。方太夫人是一个守孝之人。王茂荫的祖父王槐康去世较早,留下夫人方氏赡养两代婆母以及年幼的子女,方太夫人坚守孝道“先后善事祖姑及姑,皆年登九十”[3]281。而且,方太夫人还是一个品格坚毅、勤俭持家的人。在王槐康客死他乡之后,方太夫人拒绝了亲朋好友的二百金券馈赠,以一己之力赡养老人和抚育幼儿。在王茂荫及第做官之后,方太夫人教诲他及第登科要守家风、勤政廉政为上,以发财晋爵为耻。
三、王茂荫廉政砥品家训对培育领导干部家风的启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提出文明家庭的建设对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对全国家庭提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4]的希望,更是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寄予厚望,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树好廉洁自律的‘风向标’,推动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15]。王茂荫廉政奉公、敬亲尊老、砥品植学的家训为新时代领导干部家庭家风的培育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一)孕育时代新家风
构建时代新家风“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16]。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父母扮演家长形象,将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身份要求通过家庭共同生活、血缘联系的情感纽带等方式传递给下一代,进而完成社会身份认同。王茂荫家训中敬老尊亲等价值追求、砥品为上的人才观,“端家范”的教育方式等内容对孕育时代新家风都有积极意义。
传承敬老尊亲、勤俭行善等价值追求。领导干部对中华传统文化理解要有高度,对于敬老尊亲的理解,不仅指尊亲养亲,亦指继承先人志向,衍生出廉政、爱国等情怀。在家庭教育中传承孝文化,不流于尊亲养亲,要拓展到对先辈遗志的继承,要扩大到对整个民族先辈理想的发扬。“勤俭节约是我国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7]社会发展无非开源、节流两种途径,二者皆不可少。在促进经济发展、国力昌盛的同时,也要注重勤俭节约的倡导。勤俭不仅与个体修身的道德追求相随,也与干部廉政建设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态文明的持续发展。勤俭是对个人物质需求的道德约束,而慈善则是个人反馈社会的道德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沉溺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是将勤俭视为个体修身之法,强调施善于社会和他人,对行善布施的事情往往不遗余力去做,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
践行“砥品”的人才认同和“端家范”的教育方式。唯德选才养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成为一种主流的用人价值取向,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和名士大家所推崇”[18]。培养“光明正直之士,端方清介之儒”[11]134,既是利家兴乡之事,也是渐达于国的大事,与今日国家倡导的“立德树人”以及培养“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时代新人目标是一致的。领导干部要重视子女政治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坚决听党话、跟党走”[19],在家庭中要传达主流文化、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四个认同”的启蒙。效法“端家范”的家庭教育方式。身教重于言教,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能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首先就要己身正。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端家范”要求家长谨守礼法,做子弟表率,言行符合礼法,垂范子弟走正路、行正事。若己身不正,如何能示家责子呢?家长正己才能正家,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言行举动是下一代的模范榜样,行垂范之教。
(二)打造廉政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提出以“勤奋工作、廉洁奉公”作为衡量党员和干部的标准,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20],因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14]。
首先,以史鉴今,研究我国廉政历史、了解廉政文化。个体砥砺品性修身、勤俭行善与廉政相关,俭衍生廉、奢滋生腐,崇德树官声、奢靡败人品。我国一直有着廉政德治的官德文化传统,在历史长河中,我国既不缺乏关于廉政的理论论述,廉政奉公名留千古的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就安徽来讲,有“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的包拯家训,亦有将德名留给后世子孙的王茂荫。作为领导干部,既要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汲取智慧,也要继承百年红色家风,向杨善洲、焦裕禄等党的好干部学习,修己身正家声。领导干部家风培育,一方面“聚焦开展家风家训教育,促进社风民风向善向好”[21],营造勤俭、孝悌、行善的社会风气,培养立德为先、敦品力行的新时代个体,另一方面注重对在岗领导干部进行政治思想培训,从中华传统优秀家训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效仿优秀党员的良好家风做法,提升思想认识,提高家风培育能力。
其次,古为今用,“倡导净化家风政风社风,营造清正廉洁的文化生态”[22]。党员干部要带头重视廉洁操守的工作作风、勤政为民的政治作风以及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党员干部自身政治要过硬,要有“留书留德名”胜过留“银山金穴”的意识。明朝万历年间歙县黄山谢氏一门官宦世家,留书子孙出仕为官当遵“廉以律己,公以处事,仁以爱民,恕以待人”[11]125家风。
最后,普通家庭也要营造起廉政家风。在我国古代普通家族和家庭对子弟读书莫不有着登朝显亲扬名的期待,但登朝显亲扬名并不为食禄天家也不为策名仕版,只为惓惓之忠爱。忠诚二字,不仅指捐躯报国,更是“分猷宣力,靖献不遑,恪恭厥职,不二不欺总皆公而忘私,国而忘家”[11]106。淡化家庭教育中功利主义意识,营造成才先成人的氛围,建立整个社会的廉政生态文化,根植传统廉政家训文化,融合时代新需求,促成廉政社风的大好环境。
(三)铸牢家国大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容割裂的精神命脉……是以‘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为突出表征。”[23]“国之本在家”,家国一体的特质,使得家国情怀既表现在对个人道德的至高要求,也表现在对国家的绝对忠诚。新时代背景下“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24],已经成为家庭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辩证看待家国情怀的历史性和统一性。王茂荫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家训是有着忠君的迂腐,这是其所处历史和阶级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其廉洁奉公、以身报国的爱国情怀是不容置疑的,“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容置疑”[25]。党员和领导干部是国家机器的执行者,是执政者中坚力量,更体现管理者的意志和精神,是国之体现和民风所向。故而,新时代更加呼唤提升领导干部和党员浓厚的家国情怀、为民族振兴的使命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所以,领导干部和党员更要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汲取廉政之节、强国之怀、报国之情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与实现“两个一百年”新时代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合在一起。家国情怀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历史上家国情怀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公而忘私的政治情怀、有以身报国的爱国精神、有廉政奉公的人格追求以及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形成的红色精神。“当前,爱国主义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25]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仅要继承和弘扬传统家国情怀,还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王茂荫廉政砥品家训既有我国传统家训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也有其个体砥砺践行的精神品质,亦有社会背景所烙印的忠君封建色彩。对传统家训甄别传承,赋予传统家训新的时代内涵和意蕴,延伸至当代的尊老孝亲、廉政奉公、家国情怀、砥品植学等主流价值观,优秀家训和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传统家训孕育新时代家风,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家风、培育领导干部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