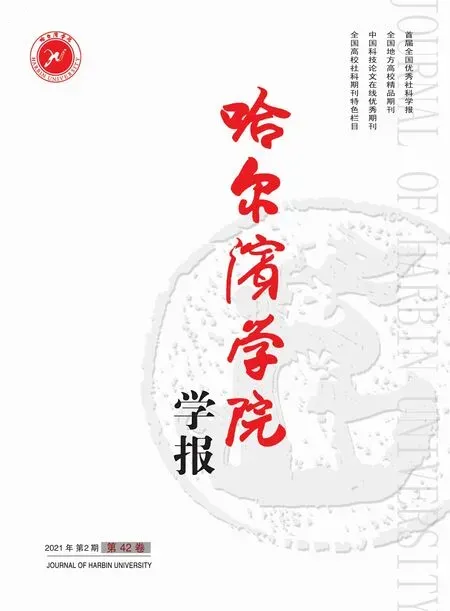论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悲剧意识
苏 曼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教学部,安徽 阜阳 236015)
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陆犯焉识》称得上是她的巅峰之作。作者以一个小女孩即主人公陆焉识孙女的视角,讲述了祖父经历社会运动、牢狱之灾,死里逃生,沉淀内心重新爱上他的发妻的故事。小说是在一种悲情的长河中缓缓流淌出文字来讲述发生在陆焉识身上的一切。文章充斥着悲凉、苦难、煎熬却不得不将生活继续下去,来完成自己内心对自由、对爱的坚守。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P297)《陆犯焉识》以缓慢的、平静的、不张扬的方式将社会、时代和个体等创伤面一点点展示于人。“悲剧意识是对人类生命在世生存的悲壮性的意识,生命悲壮性是由人类既有生存发展的强烈欲望又没有达到目的的可靠能力,只能依凭追求生存发展的意志和有局限性的能力冒险在世这一生存处境决定的。”[2](P1)在悲剧作品中,书中的主人公遭受磨难,放弃尊严,以求获得生的权利。在生存成为厚重愿望的同时,理智和情感伴随着焦虑、恐惧、不舍。严歌苓在小说《陆犯焉识》中,直面当时大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遭遇,用现在和过去两条时间线穿插叙述,展示出她对生命存在价值、爱情、亲情、友情的思考,透露出一种悲凉之美。
一、悲剧意识的根源
作者严歌苓,1959年出生在上海,12岁进成都军区文工团。少年时期的严歌苓家境衰败,父亲成为“反动作家”。在她的回忆中,父亲被下放到农场,与家里失去联系长达一年。这段经历为作者创作提供了历史背景素材。后来父母离异,成为她成长中最大的心灵创伤之一。她觉得在那个年代,父母的离异使她倍感耻辱,变得更加敏感,更加依靠自己的直觉去判断人的善意和恶意,读人的神色近乎出神入化。在《陆犯焉识》小说中,作者多次将自己的经历感受用到对人物想象的描写中:
“‘我必须请假去、去、去、去、去……场部礼堂。’五个‘去’字为他赢得了时间——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需要的时间,容他根据‘邓指’的反应及时编辑修正下的时间。陆焉识看见‘邓指’的眼睛里没有坏脾气,无非有一点儿恶心,正派人物对于反派的正常生理反应。”[3]作者在写作中借助主人公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去判断对面人物的内心,倘若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是无法完成想象和揣摩的。童年的遭遇是严歌苓形成悲剧意识的主要原因,作者将自己的经历过往一点点渗透到人物的性格中去,将谨慎胆小刻画的细致入微。在这种遭遇下,作者又赋予了人物内心的追求——活下去的动力,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处境,正视生命中的悲剧,在意志的驱动下,完成冒险。悲剧意识自身就包含着对自由的向往。
严歌苓在访谈中曾经讲到,她在再婚的父亲和再婚的母亲家里住过,有种异乡人的感觉,那种加缪小说中的陌生人的感觉。作者在小说中讲述陆焉识被平反后归家的状态,本是给予温暖、给予爱的地方,却生出了寄居者的心态。无论是自己内心的自觉,还是家人表现出的那般“施舍”,无不在敲打着“归者”的心。客观的身份改变不了,主观上的心境已从“家人”的角色转变为“客人”。没有身份过渡,敏感的心及时的提醒自己瞬间完成角色的转换,内心的爱与渴望顿时冷却,反而更加平静。作者的早期经历成为她在小说创作中宝贵的素材,赋予作者对人物、对生活独特的理解。严歌苓在采访中也说道:“我人生的悲剧感,喜剧感,荒谬感都来自这种不够真实的伦常关系。现在我到了这岁数,可以勇敢地诚实地来反省这样的感情,并诚实而勇敢地把它们表现出来。虚构帮助了我面对这些感觉,正因为我的虚构本领越来越大,我才能在虚构的人物和故事里保持自我真实。虚构给了我形而上的自我真实。”
《陆犯焉识》故事原型为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先生。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严歌苓曾经透露“她的祖父是一个神童,十六岁上大学,二十五岁读博士,之后有着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后来严先生在对时局的失望中自尽。尽管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严歌苓认为这本书一定要写,是她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是祖父的一生。同时她的父亲在“文革”劳教回来后,一直处在一种逍遥或者是消极的状态,总是在看书,这与小说中陆焉识在婉喻去世后的生活不谋而合。“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4](P384)严歌苓的生活中存在着这种悲剧性,作者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悲剧意识是顺手拈来,水到渠成的。“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5](P3)
二、悲剧意识的体现
在整部小说中,悲剧意识贯穿前后,在每个人物形象上都有体现。有面对生死的考验,有人性和道德的泯灭,有内心渴望自由的挣扎,有无力和无情的懦弱。唯有对人物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小说蕴含的悲剧意识。
(一)社会悲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P135)人的生活受社会制约,社会的发展由人促成,人与社会互相影响。大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人的行为必然会受社会的影响。小说主人公陆焉识,1907年出生于上海的富贵人家,青少年时期家境富裕,生活优渥。1928年去美国留学,在美留学的五年里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且没有耽于学业,“二十四岁的陆焉识披上了博士袍、戴上了方帽子。”[3]回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了颠沛流离风雨漂泊的坎坷半生。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军阀混战,战争烟云笼罩着整个上海滩,学术圈也掀起了“左右”的争论,作为某大学的教授,一名知识分子本无意加入任何阵营,但还是被裹挟其中,这也为日后埋下了隐患。战争的来临,他不得已跟随学校搬迁,前往重庆。满腹经纶的陆教授坚持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无教科书的情况下,用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陆焉识的这些做法没有错,错的是处在一个敏感的政治环境中,违背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错在政治恐怖时期,本应谨慎言语、小心行事的他却发文讽刺当时官员的做法,这为他招来了第一次牢狱之灾。1945年返回上海后,此时的上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掠夺”。陆焉识因被捕过丢失了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家里的房子又被政府腐败官员勾结的青红帮给霸占。战争把他“变成了这么个肯服软、不吃眼前亏、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的人了”,[3]让一个精通四国语言的留美博士变成了一个没用场的人。社会悲剧造成个人悲剧,此时的陆焉识无力挣扎,满腹失望。他清醒的认识到当前的形势不可改变,唯一可以调动的是手中的笔杆,企图掩耳盗铃式的一吐为快,却一次次栽在笔杆下。
50年代初,陆焉识以“反革命”的名头被关进监狱,判了死刑,在妻子婉喻用尽尊严的帮助下改判为无期。在漫长的二十多年的劳改中,将一个知识分子磨去了棱角,不敢妄谈一切,连尊严一并丢弃在西北的劳改场中。活着成了生命的动力,自由早已离去。陆焉识变得胆小甚微,生怕一点点的过失为自己招来臭骂、戴纸镣铐、罚跪或者罚饭(在1961年的西北荒漠中,不惜去吃冒领的死人口粮,饥饿让罚饭仅次于死刑),无论哪种惩罚对一个心高气傲的知识分子来讲都代表着屈辱,然而他却变得麻木。
因为自己“反革命”的罪行,除了妻子,孩子都在尽量远离他,与他划清界限,陆焉识甚至成了孩子们口中给他们带来一身麻烦的“老头子”。政治环境的压迫让陆焉识的子女心惊胆战,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有父亲。因为父亲,小女儿一直未嫁成为大家嘲笑的“老姑娘”,儿子失去了心中的挚爱。陆焉识被释放后,他已经不敢冒然回家。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剥夺了陆焉识身上的一切,他的坎坷不幸成为悲剧冲突的表现。特殊的时期和政治环境造成了陆焉识不可避免的磨难,所以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不能独善其身。作者对这些悲剧冲突的处理和环境的铺垫,使小说读起来更增一分悲凉意蕴。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历史、自然环境等原因,小说人物经历的磨难,也是当时社会的反映。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食物成为最匮乏的物质,很多人为了填饱肚子活下去,不惜丢掉自己的尊严,内心丑陋的一面在活着面前不值一提。在西北荒漠的草原上,文中的梁葫芦、徐大亨、张现行等人不论是吃树皮、冒领死人口粮还是扒老鼠洞的粮食吃,都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为了活着对生命做出的努力。
(二)爱情悲剧
陆焉识和婉喻的爱情是小说的主线。继母恩娘想用娘家侄女婉喻在陆焉识身上打一个“如意结”,软硬兼施的让陆焉识娶了婉喻。这段婚姻没有感情基础,陆焉识对婉喻生不出任何好感,他借助出国留学来暂时逃避婚姻带来的桎梏。在国外他自由的和意大利姑娘望达拥抱接吻,他心中有爱,但不属于婉喻,属于婉喻的是名份、是卑微。陆焉识回国归来面对前来迎接的亲人,他甚至忽略掉这位“期盼干了眼睛”的妻子,他对婉喻是怜悯,和爱情没有关系。但婉喻对他充满了敬仰,她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听从命运的安排,一边是婆婆兼姑母对陆焉识的扭曲占有,一边是丈夫对自己的无爱婚姻。她顺从的接受,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传统妻子的优良美德在婉喻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有了女儿后的陆焉识,即便有着照相机般记忆的人,有时竟然记不得婉喻的模样。父母之命的无爱婚姻戕害着男女双方,本应生出的温暖、甜蜜却被凄凉、冷落替代。
在重庆期间,陆焉识认识了重庆女子韩念痕。陆焉识对韩念痕生出激情之爱,韩念痕也爱上了这位才子。韩念痕的爱热烈、勇敢,两个人在精神上契合,这种自主的恋爱让陆焉识欲罢不能,但是又做不到抛妻弃子。敢爱敢恨的韩念痕最后退出了这份爱情。她是聪明的,为爱情心甘情愿的付出,在这无望的爱情中挣扎过后去寻求自己的生活,但也从侧面说明这是爱而不得的悲剧。
在陆焉识以“反革命”为由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婉喻对陆焉识的爱始终没变,她敬仰、爱慕丈夫,按时去看望,不管多远的路程,并且倾其所有带上给他的补品。“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螃蟹蛰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嗤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3]婉喻的爱细致、体贴、勇敢、平静,她努力地做好一个妻子,付出自己的爱。然而,陆焉识对这个以传统的方式得来的妻子仍然没有爱。此时的陆焉识尚且不知他的“死刑”改判为“无期”,是因为妻子对自己爱得太深沉、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和身子换来的。婉喻的爱是在个人悲剧的铺垫下步步迸发。
在西北荒漠,陆焉识回忆往事,想起婉喻的种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妻子,只是爱而不知。他在自己的脑海中为婉喻写了一封封倾诉感情的信,爱情此时成为他的信念。在没有尽头的改造中,陆焉识策划了出逃。他逃跑的目的是为了去婉喻的面前,告诉她,自己是爱她的。然而终究还是没有站到婉喻的面前说出,只是远远的观望。自首后的陆焉识,为了婉喻和孩子的前途,结束了和婉喻的婚姻关系。社会悲剧造成的爱情悲剧,让陆焉识明白此时他所能给予婉喻的爱是离婚。婉喻多年的爱等到了回应,悲剧的结局却包含着温暖。
当释放后的陆焉识回到婉喻身边时,婉喻却失忆了,她已经认不清眼前的男人就是曾经自己深爱的丈夫,但内心还在一直等待陆焉识的归来,即使在婉喻临终时刻她还在固执的守着记忆等待。陆焉识归来后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一场爱的徒劳,任何表象已经失去了意义,陆焉识已成为婉喻内心刻骨铭心的爱。这种两人大团圆式爱情结局,散发出一股悲凉和无奈。悲剧冲突的处理凸显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意识,也包含了另外一种意义,肯定了爱情的存在。
因为父亲陆焉识的“反革命”罪行,儿子冯子烨的爱情被扼杀,女儿丹珏的婚姻也被耽搁。小说对这对子女的爱情没有过多的渲染,但是依然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正视。
(三)性格悲剧
陆焉识的悲剧从其个人角度分析,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首先他心里清楚婉喻是继母“从娘家搬来的一把大锁,来锁紧不安分不老实”[3]的他,他痛恨这种传统方式对他爱情的终结,但是他接受了。他采取冷暴力、逃避的方式来驱散内心的不快。这种讨好式的委曲求全恰好说明了他的内心缺乏果敢、拒绝的勇气。“外部嘻嘻哈哈、迁就一切而内部猛烈挣扎”,[3]当不学无术、投机取巧的大卫来找他借论文时,内心明明是鄙视这种行为,但是看到“老朋友这样潦倒、因为拖欠牛奶公司的费用,孩子断了奶。他真觉得对不起大卫……”[3]他内心善良,他不允许自己的人品和学品有任何瑕疵,看到朋友的下场又让他极度不安。善良用错了地方就是一把刀,是扎向自己的刀。
不识时务、不通世故的陆焉识,被裹挟到政治斗争中。对学术、对文字他驾轻就熟,然而对人际、对社会关系,他一塌糊涂。自小生活优越的他,缺乏忧患意识,不善生计,知识带来的自信、清高最终败给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身上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耿直和坚持正义,在错误的时局下带来的是牢狱之灾。中青年时期的陆焉识似乎看不透,最终成为恩娘口中“没用场的人”。“有一身本事,误以为本事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让人们有求于他的本事……但是他们从来不懂,他们的本事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本事被榨干也没人会绕过他们,不知如何自身陷入一堆卑琐、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自由。”[3]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西北荒漠改造的二十年,陆焉识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有更多的时间去剖析认识自己,自我意识觉醒。他假装哑巴,让自己的脑子快于嘴,他学会了察言观色,保持沉默。曾经因为去送礼请客窘到发虚的陆焉识学会了贿赂、巴结、撒谎,更学会了小心翼翼的为人处世。但善良本性却始终未变,宁愿冒着被“邓指”枪毙的危险,都未曾说出颖花儿妈的事儿。
三、悲剧意识中的自由意识
“悲剧意识蕴含自由意识。人在既没有达到目的的绝对可靠能力,又没有上帝、他人可以依傍,但又不愿意放弃生存发展权利的情况下,只能冒险地、独立自主地承担生存发展的责任……只有自由,才能使人超越生存恐惧,发掘生命潜能,张扬生命力量,为生存发展创造可能。”[2]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倾注巨大的激情去写自由,文章的首句就写道:“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也没有剥夺他们的自由。”作者借助陆焉识的形象表述着知识分子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陆焉识逃离婚姻实则是为了逃避那个传统的方式,逃避别人强加给来的爱情,他追求的是自由的爱情。在陆焉识的眼中,没有自由,不配享受恋爱,他追求婚姻自由。在国外与意大利姑娘的恋爱是自我意识下自由迸发的爱恋,不受约束和羁绊。在重庆与韩念痕的爱情,是精神上的契合,他“想的多半不是她的身子”,超越肉体上的性爱,是精神上的迷恋。
在留学归来的游轮上,他哭泣自己即将逝去的自由。工作后,他常常流连于咖啡馆和图书馆来完成自己的学术文章,他受不住夹在恩娘和婉喻之间的被动局面,此时的他追求着身体上的自由。当纯粹的学术文章也会引来一派又一派的纷争时,他发现自己竟然丧失了学术自由。失去自由的陆焉识倍感恐惧,这对他意味着自己最重要一切的失去。在重庆教学时,他向学生宣传自由,他的内心对自由极度的渴望。陆焉识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游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内心坚定的独立自由意识,在现实中一次次遭受到碰撞。自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和追求,是追求平等、追求爱情、追求人生的自由。
在西北荒漠改造的二十年,精神文化的匮乏,政治的严苛,部分恶毒犯人为了获取丁点的利益不惜倾轧揭发,丧失的不仅仅是陆焉识行动的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的体面、尊严一并被践踏在泥里。第一次的出逃,看着眼前的妻子和孩子,只能偷偷地观望,“反革命”的罪行剥夺了他的亲情自由,这是他在荒漠中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和信仰。被释放后的陆焉识面对婉喻的失忆,重获爱情自由的他失去了机会。在亲情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儿子的嫌弃和利用,女儿的埋怨,亲情的自由似乎在形势的逼迫下已经丧失,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性人生。
婉喻的失忆是她重返自由的形态,婉喻的一生悲悯又卑微,她用自己的爱来坚守爱人,坚守整个家庭,失忆在某种程度上对她是解脱,是自由的释放。一生规矩、独立又隐忍的女人在患病后,去除了任何他人或自己对内心的束缚,如同孩童一般。然而,无论记忆怎样的丢失,唯一留下的是对爱人的期盼,在美好的幻想中离开。在悲剧意识形态下,为婉喻的执着和她的命运更留悲感。
自由和不自由始终是相对的,陆焉识的内心是自由的。晚年的他在没有自己位置的家里,带着自己的爱情一起奔向了曾经禁锢他自由、给予他心灵自由的广阔草原。压抑的情感让人唏嘘,小说充斥着荒诞悲剧的美学意义。
四、结语
严歌苓以陆焉识和婉喻的爱情为主线,以对自由的向往追求作为内涵,小说从孙女的角度来讲述,平静而悲凉的记录着属于他们的生活痛楚。然而,这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面,而是利用细腻的笔触,将上一代人的生活、环境、人性的变化,层层深入,挖掘每个人物的灵魂,直击人的内心,较强的画面感展示了那个时代生活的片断。苦难时代下人们的悲惨遭遇,无论是社会时代,还是投射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苦难,都是经过咀嚼含泪前行来追逐内心自我意识肯定的形态,这也是小说苦难凝聚而成的悲剧意识的价值所在,散发着悲剧艺术美。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