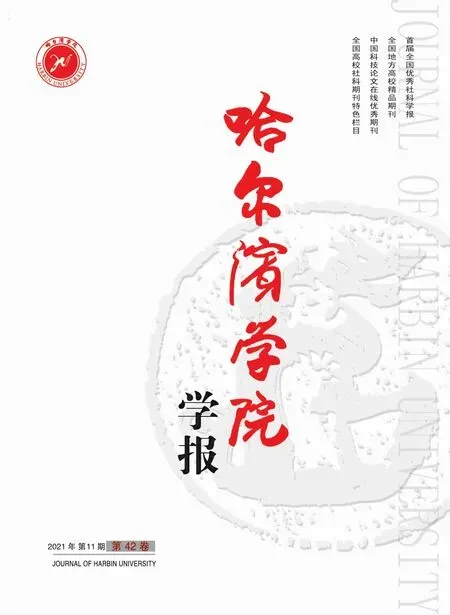《达洛卫夫人》中的“医疗乌托邦”书写
徐 晗,夏忠玉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享誉英国文坛的女作家,《达洛卫夫人》是其1925年创作的长篇意识流小说。对于《达洛卫夫人》的研究,学者们多从文本中意识流手法、女性主义、两性共存意识、心理叙述等方面入手,而对于通过分析作品中人物经历分析现代人对乌托邦的渴求却鲜有提及。本文以《达洛卫夫人》中的塞普蒂默斯为研究对象,从塞普蒂默斯的医疗经历入手,挖掘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医疗乌托邦”的向往,以及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渊源。
一、乌托邦与“医疗乌托邦”
乌托邦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早期出现的神话,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戏剧作品中也有呈现,我国东晋诗人陶渊明也曾描述过一个乌托邦社会,但具体提及“乌托邦”这一概念的是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作家玛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莫尔在其作品《乌托邦》中,借一个叙述者之口描写了一个充满暴力和阴谋的社会和一个宁静、和谐的社会,以此形成对比,用现实中的丑恶现象来凸显出乌托邦社会的美好和纯洁。
“广义的乌托邦理解一般把‘乌托邦’等同于一切人类理想社会……从功能或实际功效出发,分析乌托邦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和意义。”[1](P3)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从乌托邦的实现路径出发,强调了乌托邦的功能性,他认为乌托邦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向往,是一个发挥积极意义的概念。
布洛赫和蒂里西都将乌托邦视为人的可能性或者是期望的范畴。名词“医疗乌托邦”出自布洛赫,他认为,在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社会,梦想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表达形式中,包括非文本的表现形式,比如“医疗乌托邦”“建筑乌托邦”等。但早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当他描绘理想社会时,他特别指出,乌托邦人的健康状况是良好的,医药需要的不多,但他们十分重视医药知识,重视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对于身体的快乐的说法,乌托邦人认为是在于身体的安静以及和谐,即每个人享有免于疾病侵扰的健康。同样,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航海家描绘的太阳城:“他们那里没有痛风、手痛病、加答尔、坐骨神经痛等,因为这些疾病是由于湿气和分泌不良造成的……”[2]在太阳城里,每种疾病都有治疗秘方,城里的人通过锻炼、饮食、草药、祈祷来治疗疾病,无一不灵。可见,在早期的乌托邦社会的描述中,就表现出人们对高超医疗技术的向往和诉求。德国学者诺尔曼认为:“医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德国病理学家维尔萧认为:“政治从广义上来讲就是医学。”可见,人类社会离不开医疗,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其经历和时代背景有可能在作品中呈现这一诉求。
伍尔夫生活的20世纪,各领域都呈现出多元、开放和复杂的特点,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乌托邦态度也趋于复杂。或许是因为19世纪的人们对于乌托邦实践的失败,使20世纪的人们不再热衷乌托邦,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写作中都呈现出对乌托邦的批判,反乌托邦写作的趋势蔓延开来与反乌托邦思想相互映衬。但在将乌托邦视为政治之恶的20世纪,布洛赫、保罗·蒂利希等思想家在反乌托邦的逆流中重新诠释了乌托邦的内涵,赋予乌托邦以积极的意义,力图把乌托邦从骂名中拯救出来。
在布洛赫的强调乌托邦功能性的观点中,乌托邦具有冲破现实的需要,表达了对美好世界和生活的希望,能有效排除虚无主义,发挥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对于一生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的伍尔夫来说,她的病历和塞普蒂默斯有相似之处,在《达洛卫夫人》中,塞普蒂默斯的医疗悲剧遭遇或许是伍尔夫通过对“医疗乌托邦”书写来寻求对医疗的期望。
二、作品中“医疗乌托邦”书写的建构
“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对乌托邦冲动持一种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讶异、所有打破黑暗瞬间的希望都指向了救赎和自由王国。”[3](P158)但布洛赫在法西斯兴起后意识到,乌托邦也有可能带来毁灭。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对于塞普蒂默斯医疗的过程,展现的正是这种对于乌托邦思想态度的矛盾性,霍姆斯大夫的误诊甚至利用病人的弱点,对其进行语言攻击,使塞普蒂默斯痛苦不堪。但似乎伍尔夫更倾向于积极的一面,因为威廉爵士的出现,给患者带来了一丝光明,尽管塞普蒂默斯最终还是走向了死亡,但至少威廉爵士在给他治疗过程中,正确诊断了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还给予他关怀。
(一)霍姆斯大夫的误诊和伪善
在伍尔夫构建的“医疗乌托邦”中,霍姆斯大夫是作为反面乌托邦存在的。在他正式出场前,文中曾做过几次铺垫,每次他对塞普蒂默斯的诊断都是“他没有病”,并建议塞普蒂默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者在睡觉前服用溴化剂,他认为塞普蒂默斯的头痛、失眠和乱梦是神经质。塞普蒂默斯体重只要减轻,仅仅只是半磅,他也要让塞普蒂默斯的妻子雷西娅在早餐中多加一份燕麦片……这些诊断和治疗,在之后威廉爵士的再诊时表明,都是错误的治疗方式。而塞普蒂默斯不仅要承受精神和身体上的不适,还要面对霍姆斯大夫的冷嘲热讽。“总之,人性——这个鼻孔血红、面目可憎、残暴透顶的畜生抓住他了。霍姆斯抓住他了。……塞普蒂默斯在一张明信片背面写道:一旦你失足走入歧途,人性便会缠住你不放。”霍姆斯大夫并没有按照塞普蒂默斯的实际病情进行治疗,而是抓住他的弱点,对他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霍姆斯大夫长期混迹于贵族阶层,他的名声并不是由他的医术得来,而是靠在上流社会层层介绍和推荐。正如威廉爵士提到的,这些普通开业的医生!他一半时间都是花在纠正他们错误上,而且有一些根本无法弥补。霍姆斯大夫是典型的小市民形象,他贪图钱财,爱慕虚荣,在给塞普蒂默斯治病时拿他家的墙壁和什么爵士的墙壁做比较;在治疗病人时总是把精力转到搜罗古董式的家具上来……他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冷冰冰的话,当人们质疑他的医道时,他冷嘲道,如果他们很有钱的话,可以上哈利街去求医。对塞普蒂默斯病情的误诊以及对他心灵的摧残,使塞普蒂默斯的身体和神经全面衰竭,成为一个医疗悲剧。
(二)威廉爵士的再诊和人文主义关怀
威廉爵士是伍尔夫建构的“医疗乌托邦”中最理想的医生,他和霍姆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威廉爵士一看到塞普蒂默斯就断定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病例,每个症状都表明病情严重。他在和病人的交谈中注意到病人赋予“战争”象征性的含义,就建议病人离开亲人去乡下疗养院休养;他不会称病人为“疯狂”,而是用丧失平衡感来代替。威廉爵士有着专业的知识,其地位是因为他的能力得来的,他热爱这一行,并努力工作:“当病人走进你的诊所……那医生就得运用平稳的手段:命令病人卧床休息,独自静养,安静和休息;休息期间不会见朋友,不看书,不看通信……”威廉爵士医治时的专业和霍姆斯大夫的拙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此之外,威廉爵士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精神。他曾驾车六十英里,去乡间给穷人出诊,只恰如其分的收取病人能支付得起的诊费。威廉爵士不仅医术高明而富有同情心,善于洞察人心。“平稳,神圣的平稳,乃是威廉爵士的女神。”威廉爵士在诊断过程中,把平稳作为他的宗旨。他曾说平稳的姐妹就是感化,对于病人应去感化,而不是让他屈服。在这值得一提的一个人物雷西娅,她也是造成塞普蒂默斯医疗悲剧的重要人物,她一直逃避问题,自我麻痹,当霍姆斯说她丈夫没病时,她感到宽慰,“多么善良、多么好心的人啊!”当威廉爵士诊断了病情并给出医疗方案时,她选择逃避,觉得他们被医生抛弃。正如在威廉爵士心中的雷西娅形象一样,她不过是披着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爱情、职责和自我牺牲的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在很多时候,她不会露出真面目。她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顾丈夫的健康,体现了病人家属的自私和愚昧。
塞普蒂默斯的医疗悲剧,不仅涉及到医疗本身的误诊,还有作为大夫本身的霍姆斯的伪善,再者就是雷西娅的自私。威廉爵士用他精湛的医术和善于洞察人心的能力,还有他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把霍姆斯和雷西娅照得无处遁形。这个在人性的黑暗面下造成的悲剧,带来的是塞普蒂默斯的自杀和毁灭,但威廉爵士的出现也表明了在作者建构的“医疗乌托邦”中,还是寄予了希望和积极的意义。
三、“医疗乌托邦”书写建构的渊源
(一)社会根源
牛红英在《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第七章中提到:“20世纪被普遍解读为乌托邦已死的时代。”乌托邦文学在19世纪中叶达到高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盛转衰。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日益恶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19世纪建构的乌托邦世界已经幻灭,而此时的英国已经走向了衰败。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面临国内的自由民主即将解体的危险,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紧张的局面。在达成参战的共识后,接下来的年岁里,从心理和道德上给英国人的记忆和人生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影响了一代文学作品,塑造了此后20年英国人对于外来战争威胁的反应。尽管当时反战宣传者统计了触目惊心的数据,在帕森达勒的战争中,共有75万人牺牲,250万人受伤,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战争给英国的工业和社会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它使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集中控制权高度膨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造成大规模生命损失的战争,促使国内对生命更加重视,主要表现为改善医疗环境、关注儿童和老人、重视哺乳期母亲,以及像建立医学研究学会那样的医疗创新。到了20世纪20年代,似乎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一切恢复了平静,之前的集中主义机制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英国政府甚至为了表明其人道主义面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人们很快注意到,这一切不过是假象,根本无法回到战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只是一个躯壳,他没有自己的政党,其私人生活奢侈、浪费,无法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其后的暴力血腥执政和欺骗煤矿工人,引发了大罢工,这一系列活动对英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这一切追根溯源都源自于战争带来的后遗症。
伍尔夫塑造塞普蒂默斯的医疗事故时,是与克拉丽莎的宴会一起进行的,当宴会达到高潮时,塞普蒂默斯走向了死亡。塞普蒂默斯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战争这部绞肉机中的小小缩影,当英国上层社会的贵族享受着五光十色的宴会时,那些被战争残害的人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尽管战后的英国开始重视人的生命,改善医疗环境,但霍姆斯大夫这样的医生仍然存在,他正如当时的英国政府一样,外表披着人道主义面具,其实他伪善、自私,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伍尔夫塑造了威廉爵士的形象以讽刺那些弄虚作假的医生,同时从另一方面表现出其对于医疗方面的理想化构想。
(二)个人经历
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幼年时,就失去了母亲。伍尔夫说“她的死”“是可能发生的灾难中最沉重的”。[4](P44)在她的传记中,她认为母亲的去世,只不过是一次摧毁性的丧亲,根本没有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是,幼小的伍尔夫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才使得同父异母的哥哥乔治有机可乘。姐姐瓦奈萨和伍尔夫对于乔治的暴行选择了长期沉默,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保持一种无知的纯洁,而不是用行动去反抗暴行。这是伍尔夫体内毒瘤的源头,她深知,毒瘤会再次复发,甚至比以往都可怕。这心智毒瘤以一种精神上的腐坏在她13岁时袭击了她,在她的余生里,它一直就在某个地方不停活动着,永远悬而未决。这让她的心智结出一种伤疤,在一定程度上愈合并掩饰她持久的伤口。在后来的岁月中,伍尔夫一直被所谓的“躁狂”所折磨。
在《达洛卫夫人》中,威廉爵士给塞普蒂默斯诊断时,曾建议他到乡下疗养院休养,并远离和他亲近的人。在《伍尔夫传》中有提到,1910年伍尔夫在特威肯哈姆住到8月份,然后去了康尔沃的乡间,这是她最喜欢的,对她的健康很有益处。另外,威廉爵士对于“疯病”用“失衡感”来替换,在传记中也有提及,瓦奈萨清楚伍尔夫的糟糕处境,她在对生病的伍尔夫进行描述时是用了“病人”而避免用“发疯”这个令人恐惧的词。在创作《达洛卫夫人》期间,伍尔夫遭受了一次短暂但猛烈的精神震颤,但这件事对她没有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那时她正在写塞普蒂默斯的疯癫。13岁种下的精神毒瘤,使伍尔夫一生都在焦灼不安中度过,因为她不知道这个魔鬼什么时候会跳出来抓住她。正如塞普蒂默斯被霍姆斯大夫折磨时所说的那样:一旦你失足走入歧途,人性便会抓住你不放。威廉爵士被赋予了伍尔夫身边美好人的品质。在写完塞普蒂默斯的疯癫之后,伍尔夫再也没有提到过《达洛卫夫人》的进展。而后,伍尔夫决定搬家,从里士满搬到伦敦,她又恢复了,对丈夫充满愧疚,觉得欠了他很多。到此,我们能感受到伍尔夫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作品中她塑造了威廉爵士精湛的医疗者形象,也是她的希冀,她觉得自己也会和塞普蒂默斯一样幸运,或者更幸运。
伍尔夫从13岁起就和她的精神疾病作斗争,或者说更早,因为其父有躁郁症,有遗传的可能性。从开始发现有声音在和自己说话时的“死亡疗法”,到后来的伤口结痂又复发,她这一生都在和精神疾病做斗争,尽管有丈夫和瓦奈萨的照顾和陪伴,但最终还是被毒瘤吞噬。在这个过程中,伍尔夫对生活抱有希望,对文学异常热爱,在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时坚持创作,到后来和丈夫的相濡以沫以及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家人和医生等,都是她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的希望,这也表现出伍尔夫顽强的生命力。对《达洛卫夫人》中医疗乌托邦的建构,也是来自于伍尔夫自己的经历,尽管在她那个时代,英国社会充满了政党之争、战争的骚乱等,医疗设施的完善也只是战后的附属品,但伍尔夫仍构建了一个医疗的乌托邦,对未来寄予了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