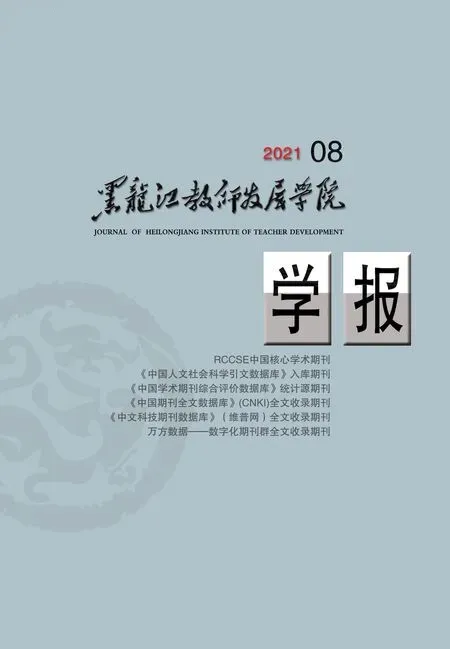冯梦龙《情史类略》底层妇女形象群浅析
吴玲玲
(四川开放大学 文法学院,成都 610061)
冯梦龙的《情史类略》以“情”为线索,汇集自周至明代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情感模式的情爱故事,共计902条。其中的底层妇女形象,以人物形象群及编者点评的方式,突破宏大叙事的史学传统及正统文学叙事中的才子佳人与神仙鬼怪自荐模式,自成叙事体系。通过对《情史类略》中底层妇女形象群的分类梳理、特征分析及形成原因探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晚明时期妇女的生活情形及晚明思潮在妇女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与影响。
一、《情史类略》中底层妇女的身份及类型
《情史类略》中的女性形象包括上至后妃、宫女、名缓,下至士农工商之妻妾婢女、尼姑、娼妓,旁及神仙鬼怪、自然动植物等非人类女性形象。本文的底层妇女指在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社会阶层均处于底层的人类女性。依此,通过对文本所涉妇女形象的梳理,能明确为底层妇女的形象为63个,其社会身份包括:卒人妻,如天台郭氏郭;农人妻,如从二姑、狄阿毛妻高氏;底层知识分子妻,如秀长董昌之妻申屠氏;寡妇,如章纶母、海昌董氏;穷家女,如朱葵本、周六之女;小商贩之女,如扇肆女;底层从业者,包括小商贩、卖身婢女、歌女等,如卖缒媪、刘奇、王善聪、歌者妇中的歌女、张住住等,以及一些未明及身份,但从其故事可推其身份当为类似于“邑人”之妻的底层女性形象,如资中盛道妻赵援姜、邑人王仁之妻罗敷等。此外,因妾在婚姻家庭中处于较为低层的地位,亦可归于此类,如张宁妾、戚大将军妾等。
底层妇女形象群体的叙事主要围绕着“家庭空间”与“家庭伦理”建构,可细分为三类:一是节烈型。全书以“情贞类”开篇,“情贞类”类多是死节、殉夫、妻代夫死等具有高度道德意涵的贞女形象。资中盛道赵援姜、德兴祝琼妻程氏、天台人郭氏、秀才董昌之妻申屠氏、赵璁妻从二姑、狄阿毛妻高氏等都是“节妇”型的典型代表。冯梦龙在点评中,给予了这一类女子极高的评价:“从二姑与高氏,皆田舍市井家儿耳。乃其捐生殉节,盖世胄读书知礼义者之所不能为也。”[1]14二是情感美满家庭幸福的贤妻型。这一类女性形象,散见“情贞类”“情缘类”。家庭美满,不只在于夫妻的相互忠诚,更在于夫妻的相爱之情。“情贞类”罗敷篇中罗敷丈夫王仁为赵王家令,罗敷能抵挡赵王的爱慕,是因“夫妇相爱之情”[1]6。“情缘类”中的张二姐“虽无恶疾,而形体枯悴,肌肤皴散,绝可憎恶”[1]45,张二姐温良的品质和与刘逸民相互扶持的经历,是夫妇和谐的基础。三是勇敢追求情爱型。冯梦龙主张“男女相悦而婚”[1]704。渔家女、扇肆女、刘奇、王善聪、张住住等均属于这一类,或勇于接受钟爱之人,或竭力追求心仪之人,或在日久情深之后勇于表白情感,卖缒媪、周六女、张二姐等则因其离奇的经历而获得了跨越自身阶层的美满婚姻。
二、《情史类略》中底层妇女形象群的特征
底层妇女自《诗经》起便是我国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重要构成,其形象往往是“勤劳”“奉献”“母性”等美德的化身。在《情史类略》中,底层妇女以人物形象群置身于“情感”话语体系中,呈现为“情感 ”“自主”“才智”等多层次的、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
(一)因情而贞
明代时贞节观念开始在大众日常中普遍流行,至晚明时期,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和各姓宗族都建立起了精细的贞节奖励机制,贞节成为衡量女性道德水平最重要的标准。在这样的主流文化影响下,大量的烈女节妇走上了历史舞台。据《明史》载,贞节女性记载于《实录》及《郡邑志》的,不下万余人。“万余”的绝对数字很大,但相对于当时的人口总量来看,贞烈只是小众行为;节妇烈女需要被表彰本身便说明贞烈并非日常生活实践。在民间的底层民众,更多的是按照客观现实需要与日常生活逻辑来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贞节与否是一种生活能否持续的选择,而不是必须的道德牺牲。
“情贞篇”中对单个形象贞烈行为简单的梗概式的叙述中,底层妇女对贞烈宗教般的自觉奉献,似乎有悖于人性常理、生活逻辑。如章纶母为一见之情而终身守节的叙述,与各类史书、地方志、节烈妇传中无血肉个性的道德符号与概念的叙述模式无太大差异,但与作者所标的“情教”相违背,更像是道德精英对无话语权与话语能力的底层妇女实施的语言暴力与思想囚禁,其底层妇女的贞烈行为叙述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与人性的多维性。但把全书底层妇女形象群视为一个叙事整体,其“贞烈”行为便有了合理的基础。“情缘类”中黄善聪和刘方两个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很值得注意。在这两则故事中的婚姻,基于相互对品行的认可,更基于共同生活经历中建立的情感。因此,当我们把《情史类略》中底层女性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时,其贞烈行为除了符合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价值观之外,还有其因情而贞的情感基础。此外,情贞是双向的,有节妇亦有义夫。《情史》收录的范围极广,除了夫死不改嫁之贞妇烈妇外,还有夫感妻之情义、妻死不另嫁之男子。情痴类中记载的源自《庄子》“尾生”,“尾生与女子期于梁,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冯梦龙评价他为“万世情痴之祖”[1]197。
(二)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对于个体的发展与生命选择具有至关重要性。一个具有高度主体性的个人可以在现有条件的制约下通过自己的选择来支配自己的生活,使自身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为情而“贞”的认识前提是女性的主体意识,既是编者对妇女主体性地位的认可,也是文本中女性人物对主体性身份的认知。封建礼教之下,相比较于上层妇女,底层妇女要更多地参与家庭之外的活动,有更多与陌生男人相遇相识的机会。双方情投意合,不圆满者私合后再遭生离或死别之苦,圆满者先私合再婚娶,无论是哪一类型,《情史》中的底层妇女都表现出了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与接爱,如扇肆女;对婚姻的自主选择,如淮安民家女子张翠翠、底层妓女张住住。
《情史》叙述中,对溢出封建规范的男女之情和合理情欲亦持宽容肯定的态度。情私类中的扇肆女与林生互生爱意,私定终身,两人深夜相会时林生体弱受寒猝死。对这种违背主流价值标准的行为,编者不但没有进行批判谴责,还在情节与结局的设定上对扇肆女的爱情选择给予了丰厚的回报。扇肆女因私情怀孕的行为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原谅,将孩子生下后因“惧人知”而“移居他所”。后来两家互认亲家,“二姓合居,共教其子,登科甲,为显宦。”[1]100扇肆女在编者的叙述中是一位敢爱敢为、生死不渝、忠于爱情的值得敬佩的女性。底层歌妓张住住则在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中,运用自己的生活智慧,摆脱了富家弟子陈小风的婚聘,嫁给了私订终身的穷家子佛奴。编者同样以佛奴“应试高中”的结局表彰张住住在婚姻上的自主选择,称赞其“不但有志气,亦有眼力”[1]94。
(三)才智、侠义
才智、侠义在正统文学的叙述中,是才女、侠女的专属特征。《情史》中,作者把这专属性的特征赋予了底层妇女,使得人物形象群更立体、更丰富。不仅有如张二姐一样吃苦耐劳的劳动女性,也有如申屠氏一般才智与侠义并具的女性。申屠氏年仅十岁的时候就能吟诗作词,在凶恶的杀夫仇人面前,她没有丝毫怯懦,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智慧,经过周密的安排,终于手刃了仇家。与申屠氏一样情商智商俱高的,还有罗敷女和李妙惠等众多女子。她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与阻碍自己幸福的恶势力作斗争。编者对“情贞类”中娼门女性的侠义、英烈之举同样予以高度赞扬。称赞南京妓张小三:“幼而知贞,长而守志,老而不逾节,卒以清白从杨生地 下。观其推财恤患,有古侠士之风。”[1]27赞叹长安杨娼“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贿,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1]29娄江妓屡次劝说其丈夫孙益以功名仕途为重,切不可游手好闲,并在十年中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在孙官运亨通之时,又劝说其“乞休”,切勿贪图名利,最后两人得以“小康终其身”[1]119。这种女子的见识和社会经验,丝毫不逊色于豪杰男子。
冯梦龙主张男女平等,对女子的才能与侠义的赞美,在《情史》中占相当比例。他认为女子的才华、智慧和胆识都不比男子差,肯定广大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起到的进步作用。《情史·情侠类》总评中,他列出在“豪杰憔悴风尘之中”“窘迫急难之时”和“名节关系之际”,被道学家所贬之为“难养也”的女子却能“识之”“急之”“周全之”。而“富贵有力者”“须眉男子”以及“以圣贤自命者”却是“不能识”“不能急”和“不能周全”,与小女子形成鲜明的对比[1]145。
三、《情史类略》中平民女性群像产生的原因
(一)晚明社会思潮的影响
晚明时期是一个社会思潮与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时代。在同一历史时空中,一方面程朱理学虽已走向末梢,趋于崩溃,但依旧在主流结构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在知识阶层传播迅速、影响深广,产生了诸多的王学流派。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在王学流派的影响下,产生了以李贽、公安三袁、 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尚“情”派。冯梦龙认为,天地万物皆由情生,大力提倡“情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倡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1]1。冯梦龙编撰创造的作品中,“情”是叙述的线索,更是叙述的焦点。
明代后期,在社会思潮与繁荣城市生活的双重影响下,妇女们开始大胆追求相对自由的婚恋模式。在择偶方面,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开始主张自我的择偶标准。在《三言》《二拍》中有很多类似的叙述,《警世通言》《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王娇鸾对周廷章“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爱相怜。”底层妇女也同样开始有着自主的婚恋标准,明代李开先在《村女谣》中描绘了一村女择偶观的变化。“东庄有个红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一心嫁在市城里,早起梳头烧好香。”《情史类略》中的卖缒媪、周六女、张二姐的婚姻都是对门第观念的突破。情仇类中的刘翠翠,其父母打破封建观念,让自己的女儿和一群男孩一起入学堂,而且在女儿的婚姻之事上也尊重女儿的决定,将她嫁与同窗刘金定。
(二)晚明文人浪漫主义思潮的折射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晚明社会的流动性,尊与卑、雅与俗、士与商等各种边界日益模糊,竟至于僭逆无涯之境”[2]。违越礼制、反叛传统、向往个性、追求真情的浪漫主义兴起于晚明文人之中。《情史》作为一本编辑类的书,在材料的收集选择、故事的叙述改写和编者评点上,必然带有当下文人的浪漫思潮。一方面表现为对礼制的僭越与挑战,另一方面把“情”当成僭越与挑战礼制的合理逻辑的同时,“情”亦是对“僭逆无涯之境”的中和和抑制。“情女”并非只是作为对抗礼教的标志,更是文人籍浪漫爱情故事,表达情理交融追求的叙述因素,“情女”终究会由“情真”转至“情贞”。《情史类略》中底层妇女的叙述,虽采集于历朝历代,但编者对文本的选择、改写、编排、点评都必受其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得整个人物形象群更丰富立体。其所叙“情贞”女子,不能止于对女子节烈这样一个既成事实表示的敬仰和感叹,更应是有情有智有义的血肉人物的真情叙述。
(三)晚明出版业发展使然
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城市市民文化繁荣,市民阶级的出现,为书籍出版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除官刻外,商业性民间书坊开始成为面对市场的主要出版主体。在出版利润的驱使下,出版商与文人阶层形成了出版流通与内容生产的合作关系。冯梦龙《今古小说》叙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今古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性,由期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3]出版面向市场,出版物要符合市民口味,大量满足市民需求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由书肆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冯梦龙作为当时出版业的积极参与者,其编辑的作品,在追求“情教”的同时,必然会考虑受众的审美接受。在人物的选择与点评叙述话语中,必然要打破简单的道德说教与示范模式,保有作为民间叙事代言的民间性,站在民间立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符合民间日常生活逻辑与审美逻辑,其人物叙述也就必然要符合底层民众的生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