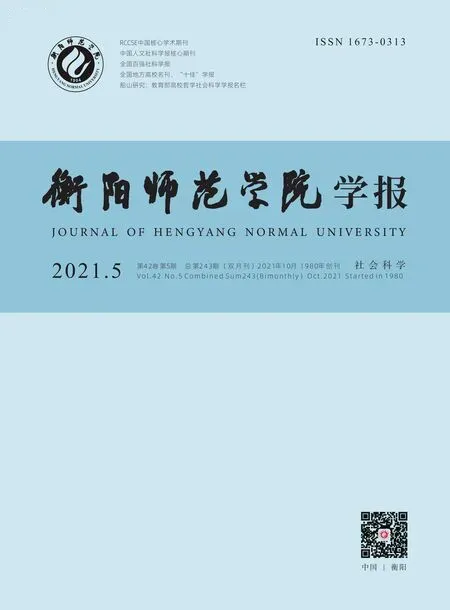中国“东方学”的萌芽与确立
黎跃进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中国古代就有大量考察和记录周边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的文献,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天朝”“中心”意识,中国只有方位意义上的“东方”“西方”概念,而没有世界整体中的“东方”概念。近代以来,由于东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天朝”理念的崩溃,20世纪初期,中国开始形成世界整体中的“东方”概念;而后在西方的“东方学”的促动和启发下,中国才形成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不过,中国的“东方学”并不是对产生于西方的“东方学”的理论承续,而是从自身面临的现实危机出发,试图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在20世纪初期风云际会的时代风潮中得以萌芽和确立的。
一、近现代佛学复兴运动与“东方学”的萌芽
佛教在汉代时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时已完成其中国化过程而达于鼎盛。宋代理学兴起后,佛学开始衰退,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进入近代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古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原有的价值体系开始崩塌。因此,一方面,社会动乱,厌世思想逐渐兴起;另一方面,部分有识之士试图挽颓败于狂澜,从传统中寻求资源,确立新的价值体系。于是,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儒学已经成为反思、批判的对象,而相对处于边缘的佛学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则成了人们重新发掘的资源宝库,一批新学人士、僧人、居士在“振兴佛教佛学”的旗帜下,开始从宗教层面发挥佛教整合社会思想文化的功能。
1920年,太虚大师创办刊物《海潮音》,刊物扉页有“海潮音十大特色”的广告语,其中有“二、东西文化之总汇”“四、顺应时代之潮流”“五、能扩张眼界开拓胸襟”等,由此可见,当时复兴的“佛学佛教”,不是消极出世的个人解脱和内心的融圆,而是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1930年,上海佛学书局将《海潮音》的文章分成专题,出版了“海潮音文库”。《海潮音文库编发大意》中说得非常明确:
世界大战以还,经世者见于战地各国苦痛,以及物质科学之危险,思有以挽救之,复以竞争进化之学,风靡一时,弱势者为功利物欲所诱惑,而唾弃精神之文化。窃谓人类生存之道,精神生活之需要实重于物质的文明,西哲培根有言,先求心灵上的满足,其余的不求自至,就不至也不感到缺乏了。通常哲学家亦云,真理不教吾人富贵,而教吾人自由,虽然,精神文化之部,东贤西哲所说,偏而不圆,都非了意,不惟无补于此,五浊炽盛之今日,且亦难以御锐利之科学家的攻击。海潮音社深觉佛法能救济物质文明之偏枯,可挽回狂澜于既倒,乃勾提法要,作为篇章,用以为社会潮流不可逾越之最大轨持,与不可超上之最高标准,根本解世界之纠纷,以谋人类永久之幸福。[1]4-5
近现代佛学复兴运动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主要包括四类人:1.在家修行习佛的居士。如杨文会(1837—1911)、欧阳渐(1871—1944)、韩德清(1884-1949)、蒋维乔(1873—1958)、刘洙源(1875—1950)、吕 澂 (1896—1989)、梅 光 曦(1878—1947)、唐大圆(1885—1941)、王恩洋(1897—1964年)等人;2.寺院僧侣。如太虚(1889—1947)、敬安(1852—1912)、圆瑛(1878—1953)、曼殊(1884-1918)、印光(1861—1940)、月霞(1858—1917)、谛闲(1858)—1932)、弘一(1880—1942)等人;3.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革者。如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唐才常(1867—1900)、章太炎(1869—1936)等人;4.文人学者。如沈曾植(1850—1922)、陈三立(1853—1937)、夏曾佑(1863—1924)、宋 恕(1862—1910)、汪 康 年(1860—1911)、谢 无 量(1884—1964)、陈 垣(1880—1971)、熊 十 力(1884—1968)、汤 用 彤(1893—1964)、梁漱溟(1893-1988)等人。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推动佛学复兴:编校、翻刻佛教经典,创设各类佛教学院,创办各种佛学刊物,展开佛学义理研究,组建各级佛教组织,开展中外佛学交流。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到,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学界精英大都名列其中,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人间佛教”则成为近代佛教文化思潮的主流。
近现代佛教的复兴,既与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之秋,力图从佛教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和政治变法或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密切相关,也与佛教强调“无我”“无畏”、重视“度人”和主体精神的作用等特点相关。作为东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佛教,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中首先作出了“东方”的回应。佛学复兴运动的推动者们在弘扬佛法、研究佛理、传播佛教的过程中,自然将东方、西方的文化互为参照后加以理解,并表现出振兴东方文化的使命感。如1926年唐大圆组织“东方文化集思社”,创办题为《东方文化》的刊物时,在发刊启事中写道:“今之世西化之弊亦极矣,代以东化,理势应尔,文化主持,国人有责。深愿海内硕学,群策群力,共成盛举。”[2]2释太虚也在文中写道:“西洋文化,乃造作工具之文化也;东洋文化,乃近善人性之文化也。造作工具之文化,而于能用工具之主人,则丝毫不能有所增进于善,惟盖发挥其动物欲,使人类可进于善之几全为压伏而已。”[3]29
二、“东西文化论争”与自觉的“东方意识”形成
我国文化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因而,在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的十余年间(1915-1927),我国学界围绕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有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偏向西方文化价值的“新文化派”和偏向东方文化传统的“东方文化派”。“新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胡适(1891—1962)、吴虞(1872—1949)、瞿秋白(1899—1935)、恽代英(1895—1931)、鲁迅(188—1936)、刘大白(1880—1932)等;“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杜亚泉(1873—1933)、钱智修(1883--1947)、梁启超(1873—1929)、章士钊(1881—1973)、梁漱溟(1893—1988)、吴 宓(1894—1978)、梅 光 迪(1890—1945)、胡先啸(1894—1968)、柳诒徵(1880—1956)、张 东 荪(1886—1973)、张 君 劢(1887—1969)等。他们分别以《新青年》《新潮》和《甲寅周刊》《东方杂志》为各自的主要阵地,围绕东西文化问题、东西文化的不同特点、东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势展开论争,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努力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方案。关于这场论争,学界已不乏研究成果①,这里不再赘述。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场论争中所说的“东方文化”,大都指的是中国文化,是以“中国”代替“东方”。在这场论争中影响甚大的《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对“东方文化”的含义做出过解释:“余所谓‘东方文化’一语,其内涵之意义,绝非仅如所谓‘国故’之陈腐干枯。精密言之,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和‘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之意蕴。……所谓东方文化者,无异指吾民族精神所表现之结晶,是东方文化所涵之内容,极为丰富而深厚。”[4]18-19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东方文化”就是“中国民族之精神”“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吾民族精神所表现之结晶”。这种对“东方文化”内涵的理解,在当时比较普遍,但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华,使这一状况得以改变。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世界著名诗人。之后,他经常到欧美各国游历、考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的危机有着深刻的感知和体认,认为西方文化过于功利,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欲望膨胀,缺乏精神的指引和内在灵魂的和谐,而东方文化追求精神价值,注重和谐,对西方文化具有弥补和拯救的意义。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也是以弘扬东方精神、促进人类文化转型为使命。这样,这位印度诗人便无意之中卷入了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他在中国的演讲遭到“新文化派”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也得到了“东方文化派”的肯定和支持。当时,《东方杂志》的主编钱智修对泰戈尔比较了解,他在泰戈尔还没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预测到了论争的必然性,且在《欢迎太戈尔》一文中写道:“泰戈尔到了中国了,不消说,东方文化与精神生活……等等问题,必又成为论坛的争端,而且这位倡导普遍的爱的老年诗人,其立身行事,说不定会因我们戴着有色的眼镜而发生主观的误解。”[5]1
泰戈尔的访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东西文化论争”的深入,也使学界拓展了“东方”的空间范围。首先,泰戈尔是来自中国之外的诗人、思想家,他的诗作和思想受到西方的热捧,被称为“来自东方的一阵清风”;其次,在泰戈尔的认知中,“东方”是指亚洲。他曾说:“我们亚洲文明,可分两派:东亚洲中国、印度、日本为一派,西亚洲波斯、亚拉伯等为一派,今但说东亚洲。中国印度的哲学,虽不无小异,而大同之处很多。……我们东方诸国,却如一盘散沙,不互相研究,不互相团结,所以东方文明,一天衰败一天了。”[6]138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中所说的“东方”,就是指整个亚洲,一再强调的“东方联合”,就是倡导建立“亚洲文化联盟”。
总之,“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争”带来了学术研究中自觉的“东方意识”,标志着中国学界自觉的“东方意识”已形成,中国的“东方学”也初步显示端倪。在这场论争中,无论是“新文化派”还是“东方文化派”,都是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展开论述,论争中出现了一批关于东西文化比较的研究成果,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伧父(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伧父的《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1917)、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林语堂的《机器与精神》(1919)、陈嘉异的《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1921)、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明》(1922)、瞿秋白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吴献书的《中西文化之比较》(1924)、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等。这些论述在比较中阐明东西文化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世界整体观念中的“东方意识”的形成。
三、《东方杂志》的出版发行对“东方学”的促进
《东方杂志》是我国近现代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直到1948年结束(中间因社会动荡,有过短时期的停刊),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上半期,“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②,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7]1。
《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几十年里有些调整。创刊号说明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8]1。17卷1号载《本志之希望》,“……今后之言论亦将以促社会之自觉者居大部分。……以记述世界大事为一大宗。……于世界之学术思想、社会运动均将以公平之眼观,忠实之手段介绍于读者。……今后拟以能传达真恉之白话文,迻译名家之代表作,且叙述文学之派别,纂辑各家之批评,使国人知文学之果为何物”[9]1-3。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炮火炸毁,停刊几个月后出版“复刊号”。胡愈之在《本刊的新生》中写道:“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做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10]12此外还有“编辑室杂话”“编辑后记”之类的文字,对杂志栏目的调整有些说明。但不管怎么“改良”,刊物的主题内容是报道世界大事件,评述时事政治,介绍各类新现象、新思潮和新知识,目的是促使国人在世界大势中的自我觉醒。为达到目的,《东方杂志》往往有意识地将东方与西方社会、文化进行比较,为“东方意识”的自觉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
首先,《东方杂志》以“东方”作刊名,在东西文化剧烈碰撞的背景下,这样的刊名无疑显示了一种文化立场,而且刊物发行量大,无形中对时代氛围有一种孕育和濡化作用。
其次,在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东方杂志》是“东方文化派”的主阵地,提出了关于现代文化的十个问题:“一、如何认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二、如何‘保守’中国传统文化并在走向现代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三、如何认识‘现代社会病’——由工业文明导致的现代战争等问题?四、如何认识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五、如何进一步引进和学习现代社会学科知识,并以之认识、引导和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六、如何引导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七、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关系?八、精英文化如何促进民众的文化普及与提高——‘促进社会自觉’?九、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个性与社会使命?其中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理念与人格现代化的方向。十、如何形成健康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应是社会真正尊重文化、文化界达成合理分工并能不断与社会发生互动的良性文化生成环境,等等。讨论留下了丰富的近代社会文化资料,后人自然可以加以深入研究,并且有益于现代社会的进步。”[11]这些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疑对东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具有积极作用。
再次,在西化、苏俄化的时代风潮中,《东方杂志》平等地看待东方,有大量关于东方国家、地区的报道,尤其是关于东方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报道,甚为引人注目。《东方杂志》报道和评述土耳其、印度、菲律宾、阿拉伯等国家、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及独立后的建设和发展,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一批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学者,在《东方杂志》看到了“东方学”的研究成果,如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③,陈垣的《元也可里温教考》④,谭云山、糜文开的印度文化研究,岑仲勉的东方民族关系研究,向达的中西交通研究,贺昌群的西域宗教研究,陈炎的东南亚文化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均对中国“东方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东方学”的确立:梁漱溟的《东西文化与哲学》
一门学科的确立,既是时代和社会需求所促成,也必须有扛大旗的学术大家和具有学术分量、体现学科体系特点、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做标识。考察中国现代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梁漱溟被称为“国学大师”“20世纪新儒学的开创者”等,他是第一个提出“东方学”概念的学者,他的著作《东西文化与哲学》便是中国“东方学”学科确立的标志。
梁漱溟(1893—1988),祖籍桂林,出生于北京的世宦之家、书香门第。他在小学、中学上的是新式学校,学习英文、数学等新学。在清末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梁漱溟关心社会和人生问题,他在中学时期便大量阅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风报》《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报刊,系统地了解时局大势。中学毕业后,梁漱溟“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12]32,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目睹了一些负面现象,因而精神上转向佛学。后来,他回忆道:
大约十六七岁时,从利害之分析迫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十七岁曾拒绝母亲为我议婚,二十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阅读,怀抱出家为僧之念,直至廿九岁乃始放弃。[12]43
我二十岁至二十四岁期间,即不欲升学,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12]74
研究佛学,是梁漱溟结合现实人生、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他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论著《究元决疑论》,并于1916年刊发于《东方杂志》。该论著引起了有心网罗各类人才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1917年10月,梁漱溟受聘于北京大学,时年24岁。1918年,梁漱溟担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的讲席教授。
梁漱溟在研究古代印度哲学的同时,还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而有意识地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他还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道和他一起交流、切磋,推动印度、中国的古代文化研究。在1918年10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梁漱溟刊出了《征求研究东方学者》的公告,全文如下:
此所谓东方学特指佛陀与孔子之学。由其发源地名之东方之学不止此,然自余诸家之思致亦西方所恒有,独是二者不见萌于彼土。其一二毗近佛陀者原受之于此,孔子则殆无其类。且至今皆为西方人所朱能领略。又东方文化之铸成要不外是,故不妨径以东方学为名也。是二者孔子出于中国,佛虽出印度,然其学亦在中国。而吾校则此中国仅有之国立大学。世之求东方学不于中国而谁求?不于吾校而谁求?是吾校对于世界思想界之要求负有供给东方学之责任。顾吾校自蔡先生并主讲诸先生皆深味乎欧化而无味于东方之化,由是倡为东方学者尚未有闻。漱溟切志出世,不欲为学间之研究,今愿留一二年为研究东方学者发其端,凡校内外好学君子有同心者极愿领教。又谨于成美学会中常年月捐其薪资二十元为立意研究东方学者之补助,余容续闻。梁漱溟谨肩。[13]548
在公告中,梁漱溟首次在中国学界提出了“东方学”的概念,并把它解释为“特指佛陀与孔子之学”,同时说明了“东方学”不仅只有这两家,但佛学和儒学最具有东方特色;而且,他还强调它们或源于中国,或在中国得以弘扬,因而发出了“世之求东方学不于中国而谁求”的责问。当时的梁漱溟,应该没有对产生于西方的“东方学”进行过系统了解,完全是从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出发而发出的感叹,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敏感性和追求真知的使命感,实属难能可贵。
正是由于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东方文化研究的使命感、责任感,加上梁漱溟身处“五四”时期各种思想学说非常活跃的北京大学,在这里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纠缠在一起,进而促使梁漱溟由佛学转向儒学,将佛学与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体,与西方文化加以体系化的比较研究。他自觉扛起“东方学”的旗帜,为弘扬东方文化积极思考、理性论辩、课堂讲演、著书立说,完成了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后来,梁漱溟回忆那时的情形说:“当时的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潮(赛恩斯与德莫克拉西),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我自己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我讲东方古哲学的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就是在这压力下产生出来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书内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国、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各予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适当的位置,解决了东西文化何题。”[12]51
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演讲,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该演讲稿经学生陈政记录、整理,刊发于《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7日—1921年2月8日)。1921年,梁漱溟又应山东教育厅邀请,在暑期演讲会就同一题目作了更为系统的系列演讲,由学生罗常培记录、整理。1921年10月,梁漱溟把两次讲演的记录和刊发于《少年中国》杂志的论文《宗教问题》整理成书稿,同年1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成书。1922年1月,该书稿以《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命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著作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学界震动,引起人们争相阅读、评论,并不断再版,成为当时“东西文化论争”的重磅成果,进而推动这场论争达到新的高潮。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奠定了梁漱溟中国“东方学”领头学者的地位,其著作也成为中国“东方学”确立的标志。
第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在反思“东西文化论争”的基础上,对东西文化做出系统比较的时代前沿著作。西方列强带着坚船利炮和自身的价值观念来到东方,东方面临着传统和西化的选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学界一直在探讨东方(中国)的出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讨论蔚然成风。在该书第一章“绪论”中,梁漱溟对当时讨论的情形和主要观点作出了分析和梳理。在梁漱溟看来,社会上流行的有关“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种种观点,虽然有一些可供参考之处,但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他甚至认为,“虽然人人说得很滥,而大家究竟有没有实在的观念呢?据我们看来,大家实在不晓得东西文化是何物,仅仅顺口去说罢了。”[14]11尤其对当时流行的“东西文化调和论”,梁漱溟进行了深入反思:“大家意思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像这样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既然没有晓得东方文化是什么价值,如何能希望两文化调和融通呢?如要调和融通总须说出可以调和融通之道,若说不出道理来,那么,何所据而知道可以调和融通呢?”[14]21
在后面的章节中,梁漱溟从“生命欲求”出发,提出了人生的三大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生命意欲由这三个方面的追求,引发出三种文化路向:
(1)人与物的关系,是意欲向前追求,也就是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得到外在的物质享受和满足;(2)人与人的关系,不能以征服的态度向外追求,只能反求诸己,修身养性,获得内心的满足与和谐;(3)人与自身的关系,关注的是身与心、灵与肉、生与死的问题,既不能向外追求,也不能寻求内心满足,只能放弃现世追求本身,去追求永生。
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路向,正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精神的体现。西方走的是“向前要求”的第一种文化路向,中国走的是“调和持中”的第二种文化路向,印度走的是“反身向后”的第三种文化路向。他还强调:这三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特点。但以当时的世界大势和三大文化的本质看,梁漱溟断定:“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4]202他在论述中运用了哲学、宗教、伦理、心理、社会习俗等多方面的材料,从现实问题出发,层层深入,富于逻辑论辩力。虽然现在看来,该书的观点和思路不能说无懈可击,但在当时,它确实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论著。
第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和人类文化的整体角度来论述东方文化,探讨东方文化的本质之类的问题,并考察其发展趋势的。梁漱溟在著作中不无自负地写道:“从已往到未来,人类全体的文化是一个整东西,现在一家民族的文化,便是这全文化中占一个位置的。所以我的说法在一句很简单的答案中已经把一家文化在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了。”[14]33确实,梁漱溟从人生意欲的角度分析东西文化,首次提出了人类有三大文化系统,它们虽然不能囊括人类文化的全部,但显示了人类文化是多元发展的,并没有好坏、新旧之分。贺麟评价道:“在当时大家热烈批评中西文化的大潮流中,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要推梁漱溟先生在1921年所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5]15
第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它在4年内被印刷8版。张君劢认为,“此三种文化的特点,说的很透辟,吾极佩服的”[16]120。严既澄评述:“梁君观察之精密,阐发之明晰,很足以增加我许多勇气,我很感谢他。”[17]475恶石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继绝学、开太平’的大发明”[18]485。即使不太赞成其观点的张东荪也认为,该著作的出版“好像在黑暗中点了一盏明灯”[19]50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成为了中西文化论争的经典,引发的争论持续了30年。
综上所述,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对东方文化论述的系统性、学术性和现实性,以及它在学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考察,我们将它视为中国“东方学”确立的标志,应该是恰当的。
结语
学科形态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随着近代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西方需要了解东方,从而研究东方。中国“东方学”的产生虽然晚于西方“东方学”,但它不是对西方“东方学”理论的直接继承,而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具有不同于西方“东方学”的特点:
第一,早期的中国“东方学”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不是纯学术的理论建构,而是关乎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近现代佛学的复兴、“东西方文化论争”以及《东方杂志》的出版发行,都内含这样的现实召唤。梁漱溟曾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对于西洋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的不行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过西洋文化之处。我原来并不曾想到著书立说、谈学问,只是心目中有问题,在各个问题中都有用过心思,无妨将用过的心思说给大家听;因为我的问题,实即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实实在在,无心著书立说,谈学问也。”[12]68
第二,早期的中国“东方学”是从现实出发对传统价值的发掘与认同。它不同于西方“东方学”以“他者”的东方为研究对象,服务于自身的海外拓殖。中国“东方学”是研究包括自身在内的东方文化,而且面对西方文化的侵袭,传统文化转型必然选择的建构自然是从东方传统资源中发掘可供现代转型发挥作用的元素,在现代世界大势中弘扬传统,甚至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势下,寄望用东方文化去拯救西方。“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认为:“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20]338
第三,早期的中国“东方学”与“国学”关系密切。所谓“国学”,指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包括经、史、子、集等内容。中国是东方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国际视野看,研究中国之学,自然是“东方学”的内容。只是现在的学科分类精细化,中国学者研究“国学”才从“东方学”中独立出来。但在20世纪上半期,很多“国学”学者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国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外来渊源或域外传播,在更大空间中拓展资源,从比较研究的层面来探讨中国文化,自然又属于“东方学”的范畴。王向远教授认为:“中国的东方学近百年来早已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体现了中国学者独到研究的中国‘东方学’,既是‘国学’研究的自然延伸,也自然具有了国学的品格,成为广义上的、开放性的‘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1]
20世纪20年代初,“东方学”确立后,中国便出现了陈垣(1880—1971)、岑仲勉(1886—1961)、冯承均(1887—1946)、张星烺(1889—1951)、陈寅恪(1890—1969)、朱谦之(1899—1972)、向达(1900—1966)等一批“东方学”家,他们开拓了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1)中西交通史;(2)宗教传播学;(3)西域学;(4)敦煌学;(5)西夏学;(6)南洋研究;(7)西域南海史地学。这些都显示了中国“东方学”的研究实力。
注释:
①这次大论战的资料汇编和研究著作可参看: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蚃和发展道路论证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大华的《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年版;马克锋的《文化思潮与近代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焦润明的《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袁立莉的《“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八位主编指的是:徐坷(I869-1928)、孟森(1868-1938)、杜亚泉(1873-1933)、钱智修(1883-1948)、胡愈之(1896-1986)、李圣五(1900--1985)、苏继靡(1894-1973)、王云五(1888—1979)。
③梁漱溟:《究元决疑论》,《东方杂志》第13卷(1916年)第5、6、7号。
④陈垣:《元也可里温教考》,《东方杂志》第15卷(1918年)第1、2、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