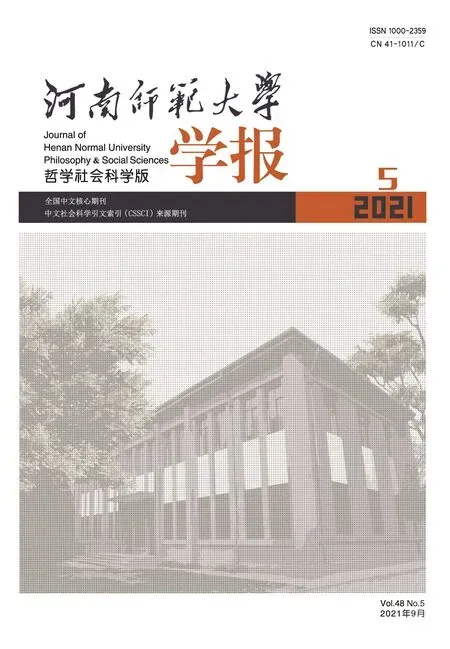义利之间:朱熹经营书肆述论
陈 广 胜
(河南大学 出版社,河南 开封 450008)
宋代是我国图书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勃兴和黄金时代,刻印书籍活动遍布各地,形成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南宋时期还形成了浙江杭州、福建建宁府、四川成都三大图书出版中心。其中朱熹长期生活的建宁府建阳县(治今福建南平市建阳区)被称为“图书之府”,刊刻的书籍种类包罗万象,发行流通遍及各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营销中心。受此浓厚的出版文化氛围浸染,朱熹在建阳县也开设过刻书作坊,从事书籍的编校、刻印与营销活动。关于朱熹编辑、校勘、刻印书籍的重要成就与影响,前人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有关朱熹经营书肆一事,因为史籍记载不详,研究编辑出版史者虽有提及却缺乏专门论述。本文以现存朱熹与师友门人的往来书信为主要文献依据,梳理朱熹开设书肆的始末原委,揭示朱熹编辑出版与经营活动的相关问题,以丰富我们对这位宋代思想家的认识。
一、缘起:朱熹经营书肆的治生之道
身为理学大师,朱熹深知书籍出版对传播文化知识和构建学术体系的重要性。他曾说:“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故自伏羲以降,列圣继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备。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34页。因此,他毕生从事儒家典籍的著述、整理、编刻等工作。
朱熹与书籍刊刻、印制业直接发生联系,是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他校订完成《谢上蔡语录》之时。谢良佐,字显道,河南上蔡人,史称上蔡先生,是程颢、程颐的弟子,在二程门人中见识最为超卓,被誉为“洛学之魁”,他的理学思想对朱熹早年有很大影响,其讲学内容被门人编为《上蔡先生语录》,或称《逍遥先生语录》《谢子雅言》等,有多种版本流行。但各本或重复、或遗漏、或掺杂他书,有失原来本旨。朱熹参考诸本,重加删改编订成《谢上蔡语录》,尚未完稿,就被人外传并刻版于江西(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谢上蔡语录后序》,《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09页。。这是朱熹编订的第一部理学家著作,也是有明确记载的、他自己编订的书籍首次被刊刻。
在淳熙五年(1178)赴任知南康军之前,朱熹有二十年的时间没有担任实际要职,以从事教育和著述为生。他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来论学授徒、研读和编修、著述儒家典籍,通过诠释经典来建构其理学思想体系。继《谢上蔡语录》后,朱熹又相继整理、注解、编订出版了与《孟子》《论语》《毛诗》《太极通书》等相关的儒家典籍,以及宋朝二程、张载等理学开创者的遗著、讲稿、文集等(3)关于朱熹编校、刻印图书的年代和书目,可参阅戴从喜《朱子与文献整理》之《附录·朱子文献整理活动纪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方彦寿《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其中有些书籍由好友张栻、吕祖谦及门人等在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和泉州等地先后刻版印行。
建宁府境内沿着建溪是一条通行方便的河谷走廊,从这里北上翻越仙霞岭、分水关两个古道关口可以通达今天的浙江、江西地区,从而连通其他各地;沿着河谷下行,从上游的崇安县经建阳县到建瓯县,可以通达闽江,最终到达福州、泉州,连通海路。这里盛产造纸用的优质竹子及其他刻印书籍的材料,又是北方士人南下福建的要道和集散地,因此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销售中心。其中建阳县麻沙镇书肆林立,被誉为“图书之府”,有“书林”之称,大量书籍汇集于此,在这里刻印,再由书商贩卖到全国各地,甚至流通到海外,呈现出“书籍高丽日本通”(4)熊禾:《勿轩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的盛况。致力于传播传统儒家道统学说的朱熹长期寓居于此,深受感染,他叹服于“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45页。的巨大文化传播及影响力,于是在建阳县崇化坊开办了刻书作坊,朱熹称之为“书肆”,后世在这里继续建设文化教育机构,称其为“同文书院”(6)参阅陈国代《文献家朱熹:朱熹著述活动及其著作版本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朱熹开设书坊从事图书刻印销售的商业活动,客观上受到了闽北地区刻书业繁盛的影响,但从其个人方面来讲,除了构建学术思想体系外,则是为生活困窘所迫,是出于生计需要的考虑。南宋国土面积比北宋大为减少,但是,选拔官员的数量没有缩减,官员人数与岗位缺额严重不符,“官多阙少”的矛盾突出,造成大量中下级官员待阙或担任无职事的祠禄官。在待阙期间,基层官员没有俸禄收入,祠禄官的俸禄也很少,官员们需要养家并建立广泛的亲友门人交游网。像朱熹这样的学者经常会接待从各地前来求学访问的学者,开支量大,因此不得不考虑生活费用,这一点在朱熹与张栻、林用中等友人往来的信函中都有体现。如乾道八年(1172),张栻在给朱熹的回信中曾说:“比闻刊小书版以自助,得来谕乃敢信。想是用度大段逼迫。某初闻之,觉亦不妨,已而思之,则恐有未安者,来问之及,不敢以隐。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鲜,若刊此等文字,取其赢以自助,切恐见闻者别作思惟,愈无灵验矣。虽是自家心安,不恤它说,要是于事理终有未顺耳。为贫之故,宁别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某心殊未稳,不识如何。见子飞,说宅上应接费用亦多,更深加撙节为佳耳,又未知然否?”(7)张栻:《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21《书》,中华书局,2015年,第1088页。对朱熹因为生活拮据而刻书卖书“自助”,张栻表示并不认同。宋代刻书有小字本和大字本之分,大字本疏朗悦目,方便阅读,但印制成本大、定价高,读书人购买能力有限,难于销售;与大字本相比,小字本版面字数容量大,能节约成本,费用少、定价低、方便携带,更贴合读书人的需求,易于销售,能获取更多利润。根据张栻这封回信可知,朱熹刻小字书版的事应是传得比较广泛,且在朋友圈中引起过议论。张栻担心刻印书籍的市场化行为不利于道学思想的传播,因此写信加以劝阻,建议朱熹改做其他小买卖以贴补家用。朱熹给远在湖南的张栻写信对此事进行了解释,现存朱熹文集并没有收录这封给张栻的信,其内容不得而知。但在朱熹看来,出版图书盈利以自给,相比用其他手段营生要好些。他在给林用中的信中说道:“数时艰窘不可言,向来府中之馈自正月以来辞之矣。百事节省,尚无以给旦暮……此事只得如此,而贫病殊迫,亦只得万事减节,看如何。钦夫(张栻的字)颇以刊书为不然,却云别为小小生计却无害,此殊不可晓。别营生计,顾恐益猥下耳。”(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6《林择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945-4946页。一般认为朱熹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及时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以及整理上至孔孟下迄北宋周、张、二程等人的著作,以便继承和弘扬”(9)方彦寿《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文献》,2000年第1期。,但从上述书信来看,朱熹开设书肆,从事图书印制与销售的商业活动,直接动因则是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出版图书,盈利以自给”(10)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被朱熹称为“书肆”的刻书作坊开办于何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张栻给朱熹的书信及朱熹给林用中的书信,均写于乾道八年(1172),这表明朱熹开始开办书肆应该在此之前。束景南认为,张栻批评朱熹印刻小字本图书是对乾道六年福建提举郑伯熊刻版的小字本程氏《遗书》《文集》《经说》而言的(11)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1页。。若此,则乾道六年,朱熹就已开办书肆从事书籍的商业经营了。
二、践行:朱熹经营书肆的精品意识
朱熹开办的书肆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经营,而是合伙经营的。其门人蔡季通、蔡渊、林用中等都参与了书稿的编校活动,其好友吕祖谦等人也从旁协助。朱熹本人对编辑出版业务相当精通,对书籍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从策划选题到编校书稿,从版面设计到雕刻字体的选择,从采购印刷纸张到计算成本、支付刊刻工费,直至市场销售、阻断盗版等,他都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参与其中,躬亲指导。
朱熹非常重视图书的编校质量。他认为,编刻书籍是要公之于世的“四海九州千年万岁文字,非一己之私也”(1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9《答许顺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48页。,要经得起时间检验,要对读者对后人负责,不能随意刻印。因此,从选题开始,他就严把质量关,对自己不满意的书“谨之重之而不敢轻出”。朱熹对当时社会上随便刊刻未定书稿的现象极为反感,“平日每见朋友轻出其未成之书,使人摹印流传而不之禁者,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远也”(1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6《与杨教授书》,《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45页。。他强调编辑加工书稿要精编精校,微观上要逐字逐句仔细校对,宏观上要全书从头到尾,全篇都要反复贯通,“逐字逐句,一一推穷,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莫论遍数”,使书稿文字内容达到“通贯浃洽,颠倒烂熟”才好(1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2《答吴伯丰》,《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21页。。在校对环节,朱熹强调以“精校为佳”,反对一人独校,主张两人相互雠校,“两人一诵一听看,如此一过,又易置之”,避免一人包校而导致校勘不精。在刻印程颐《易传》时,他写信叮嘱吕祖谦,“须更得一言喻书肆,令子细依此誊写,勘覆数四为佳”(1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47、1424页。。在刊刻《程氏遗书》时,他特地吩咐负责刊刻的程舶,要求把书样送给许升、王力行、林汝器、徐元聘、柯翰五个人分头校对,当得知程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只让叶学古一个人独校时,他十分生气:“如此成何文字?”坚持要求把书稿再送给以上五人复校,并殷殷叮咛:“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9《答许顺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48页。
朱熹十分重视书籍的装帧设计,非常关注刻书所用的书体字号。他认为,如果刻印书籍字间距疏密不均,就会让读者的观感不美,因此强调书籍开本大小、字体字号的排列组合应和谐一致。在刻印《女戒》时,朱熹明确指出“字数疏密,须令作一样写乃佳”(1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5《与建宁傅守劄子》,《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21页。。在补刻《古易音训》时,他要求按照原版开本的大小和行字的疏密写定(1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与建宁傅守劄子》,《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81页。。当时浙中地区刻书盛行取法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诸家字体,非常美观。而建阳的刻书作坊主多数追求产量大,不讲究字体的写刻效果,朱熹因此痛斥建阳刻印的书籍,“书白字画不方正,努胸垤肚,甚刺人眼”,感叹“不知乡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识好字?岂不见浙中书册,只如时文省榜,虽极草草,然其字体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1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3《答蔡伯静》,《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715页。。他很赞赏浙江版的写刻字样,在委托蔡渊刻书时,要求找出家里收藏的浙版书籍,比照“浙中字样”书写刻印。
朱熹密切关注图书市场行情,维护书肆的版权利益。如乾道八年,他指导书肆刊刻的《论语精义》因为印制精美,很受市场欢迎,身在婺州的吕祖谦写信告诉朱熹,说当地很多学者想买此书但很难买到,希望朱熹“告谕贩书者,令多发百余本至此为佳”(20)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第8《尺牍二·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市场销售情形看好,不良书商便欲盗印牟利,朱熹很快得知消息,写信给吕祖谦请求他出面及时制止(2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47页。。根据吕祖谦的回信,这次不法书商的盗印行为在他的干预下被及时阻止了,从中可见朱熹为捍卫书肆的市场利益所付出的努力。
朱熹对开办书肆兢兢业业,既重视书籍的编刻质量,也密切关注销售经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出版人。但是,其书肆经营得并不顺利,而是相当艰难。乾道八年,朱熹在给林用中的信中写道:“文字钱除前日发来者外,更有几何在彼?择之为带得几□(千)过古田?千万早示一数于建宁城下,转托晋叔寄来为幸。或已去手,能为收拾,专雇一稳当人送来尤便。此中束手以俟此物之来,然后可以接续印造。不然,便成间断费力也。千万早留意为妙。须知昨已修定,送伯谏处未取。大率事体亦只如所示,但条目差分明耳。”(2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6《林择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945-4946页。由此可以看出,朱熹书肆的运营资金很紧张。此后的情形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最后到淳熙四、五年间(1177-1178)经营陷入绝境,加上他淳熙五年受命到南康军去任长官,不得不终止了书肆的经营。
同开设的时间一样,朱熹书肆倒闭的时间,现存文献也缺乏记载。朱熹在给李宗思的书信中曾说:“书肆之败,始谋不臧,理必至此,无可言者。既败之后,纷纷口语,互相排击,更不可理会。幸已自脱去,不能复问。晦伯必自报去,某于此却似放得下,但马谡未易根究耳。一笑。”(2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8《答李伯谏》,《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787页。据顾宏义考证,该信写于淳熙四、五年间(24)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85页。,朱熹上述的无奈言语也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书肆是与人合伙开设的,经营失败后,朱熹主动脱身,不再过问其后的事情。朱熹把刻书作为产业来经营牟利算是失败了,但作为文化传播事业,朱熹从未间断编辑刻印书籍的活动,而是终身为之。
三、义利之困:朱熹经营书肆失败的原因
朱熹经营书肆持续了七八年,终因“始谋不臧,理必至此”,不得不退出。现代学者认为朱熹书肆的倒闭是由于“资金困难、经营不善”(25)方彦寿:《朱熹刻书事迹考》,《福建学刊》,1995第1期。,但对如何经营不善却缺乏深入论述。通过考析,其失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出版经营观念片面,未能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重视图书出版的社会效益而忽视了经济效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书导向的局限。为了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朱熹把宣传儒家道统作为出版主流,其书肆刻印的书籍主要是正统的儒家典籍及当世名儒的著述,相对排斥对其他书籍的出版,可供给读者选择的图书品种少,势必影响销售规模。朱熹对书籍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他说:“盖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讬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2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34页。他深知书籍对弘扬道统、传承学术的重要性,“圣人因其所见道体之实,发之言语文字之间,以开悟天下与来世”(2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9《答汪叔耕》,《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14页。。他把“明道”和“有补世教”“传之来裔”作为编刻书籍活动的价值追求(28)林振礼:《朱熹:作为编辑出版家的评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编刊书籍,目的在于向社会普及儒学,以儒家思想教化世人。朱熹编纂刻印的书籍虽经、史、子、集都有,但主要集中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和以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为代表的理学家的著作以及他个人对上述典籍的阐释注解之作。朱熹轻视甚或排斥出版其他书籍。如他认为“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29)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一册,岳麓书社,1997年,第170页。,故在他编刊的书籍中,除以道德史观从《资治通鉴》改编而来的《资治通鉴纲目》外,绝少有其他史书。对其他学者书籍的出版,他只要觉得有悖于儒家的纲常学说,就极为憎恶,甚或主张毁版。洪适在绍兴刊刻了二程的再传弟子、杨时的门生张九成的《经解》,因其中有些观点融合佛家学说,朱熹竟说:“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3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答石子重》,《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24页。庆元党禁时期,朱熹的作品与浙东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叶适和陈傅良都是儒学名家,因在一些学术观点上与朱熹存在分歧,朱熹就认为他们的书籍早就应该禁毁,“进卷之毁,不可谓无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毁者抑其外耳”(3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63《答孙敬甫》,《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065页。,由此可见朱熹对出版其他学术书籍的态度。二是不重视市场需求。朱熹开设书肆虽然是为纾解生活困难,但出于理学家“君子言义不牟利”的观念,对靠出版书籍赚取钱财,从内心还是反感的。只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他才不得已为之。他曾说:“今人得书不读,只要卖钱,是何见识?苦恼杀人,奈何奈何!”(3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5《答廖子晦》,《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87页。宋代出版业的繁荣与科举考试的发达有很大关系。两宋改革科举制度,取士规模扩大,选人追求公平公正,士农工商杂类皆可应举,读书应考的人数猛增。仅就福建地区而言,南宋进士数量不仅在全国排名第一,而且占到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33)戴显群:《试论福建科举的历史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由此,当地读书应试人的数量非常庞大,科举应试类图书的市场需求很广,不仅本地有需求,外地也有很大市场。岳珂曾说,应试科举书籍在市场的占有量“百倍经史”,“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34)岳珂:《愧郯录》卷第9《场屋编类之书》,中华书局,2016年,第123页。。当时,一般书坊都出版销量很大的科举类图书,朱熹对这类图书的市场并不重视。朱熹对科举考试持有异议,他认为读书求道应是士人的第一追求,不应该把应举做官放在首位,故而无视巨大的科举考试用书市场需求,自己既不编刻科举考试方面的书籍,也反对他人编刻此类图书。朱熹的好友吕祖谦开设有丽泽书院,从学者多时达二三百人,为招徕学者,吕祖谦曾编写科举考试的用书,如《历代制度详说》《古文关键》等。朱熹对吕祖谦编刊举业书籍很有意见,多次写信表达不满。他屡屡在信中对吕氏刊行“时文、杂文之类”深感忧虑,并说:“近年文字奸巧之弊熟矣,正当以浑厚朴素矫之,不当崇长此等,推波以助澜也。明者以为如何?”(3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52-1453页。又说:“但为举子辈抄录文字流传太多,稽其所敝,似亦有可议者。自此恐亦当少讱其出也。如何如何?”(3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37页。搞得吕祖谦很是尴尬,不得不回信反复解释,表示以后不再编刻此类书籍,“非特讱其出而已”(37)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8《尺牍二·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虽然朱熹后来对科举书籍的看法有所改变,认识到“科举文字固不可废”,并萌生出“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以此来改变劣质科考书籍充斥图书市场的想法,以达到“正人心、作士气”(3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答陈膚仲》,《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69页。的目的,但最终也没有开发出这方面的优秀选题,在庞大的科举用书市场中分一杯羹。朱熹去世后,他的学生们摘取他和其他道学领袖的作品,以类书的形式编辑科考书籍并在各地出版,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扩大了在举业用书中所占据的市场份额(39)魏希德:《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8页。,同时也扩大了朱熹思想的社会影响。
(二)资金不足,书肆经营难以为继。刻印书籍要有成本投入,尽管朱熹身边有一帮学者和弟子义务帮助做书籍的校对、刊刻等工作,但是,写刻文字需要雇用笔工和刻工,刻版需要版材,印刷需要纸墨,这都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要想维系正常书肆的运营,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作保障。朱熹开设书肆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节减或挤占刻书经费就成为无奈的选择。正如朱熹自己所说:“此事只得如此,而贫病殊迫,亦只得万事减节。”(4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6《林择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946页。作为学术大师,登门访问朱熹的士人学者络绎不绝,迎来送往的费用成为一大笔开销,反对朱熹开设书肆的张栻就说过,朱熹的“宅上应接费用亦多”。而朱熹又是重情好义之人,虽自己生活困难,还不忘周济他人。囊中羞涩,或不得不借贷度日,有时甚至挪用刻书资金。如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讲友程深的父亲客死异乡,此时的朱熹,生活艰窘得无以言状,“百事节省,尚无以给旦暮,欲致薄礼,比亦出手不得”。即便如此,朱熹还写信给林用中,要他用文字钱“兑钱一千官省。并已有状及香茶……烦为于其灵前焚香点茶,致此微意”(4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6《林择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945页。。碍于情面,朱熹有时甚至把刻书钱借与他人,造成刻书资金不能按时收回,影响到书肆的运营。对此,朱熹也深表愧疚,他在给李伯谏的信中说:“子礼兄金,渠已认还七月以后息钱矣。但书肆狼狈日甚,深用负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所当为,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满耳。”(4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8《答李伯谏》,《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786页。可见,挤占和挪用刻书资金对书肆经营有较大影响。
(三)书籍市场盗版行为的困扰。宋代书坊虽然已经有了版权保护意识,但是当时版权观念还较薄弱,盗版之风仍然盛行。朱熹编刻的书籍屡遭盗版,对其书肆的经营造成了很大冲击。宋孝宗乾道、淳熙之际,学术思想活跃,朱熹与张栻、吕祖谦在学界被称为“东南三贤”,深获世人拥趸,他们编刻的书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因此,也往往被一些不守规矩的书坊主盗印。如前所述,朱熹编刻书籍追求高质量,他刻印的书籍销路更好。如《论孟精义》,在婺州就难买到此书,婺州的书商认为有利可图,竟要私自盗印。朱熹为此不得不致信吕祖谦,求他从中干预并阻止(4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47-1448页。。盗印者的盗版行为使朱熹深感头疼,但在吕祖谦看来,婺州纸张价格高,图书定价也高,穷苦书生买不起,即使被盗印,也不会影响朱熹书肆对该书的销售,反而劝说朱熹不必过虑,还进一步对朱熹反对盗版的做法提出疑问,认为朱熹的反盗版有与人争利之嫌,有悖于平日的说教(44)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7《尺牍一·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1页。。此番盗印刚平息,朱熹编辑的《伊洛渊源录》在还没完全成稿的情况下又被提前盗印了,而此时朱熹经营的书肆正处于艰难时期。多年之后想起此事,他还愤恨不已。绍熙二年(1191),他在给门人吴仁杰的信中说:“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集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4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9《答吴斗南》,《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36页。淳熙四年(1177),朱熹在建阳编写成《周易本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或问》,但诸书还未修改妥当,也相继被书坊盗刊。对无良书商连续、集中、多品种的盗印行为,虽然朱熹也曾采取维权行为,对“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46)王懋竑:《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76-77页。,但对朱熹经营的书肆造成的冲击还是巨大的,此后不久,朱熹便宣告退出书肆经营。
书坊的盗印行为给朱熹留下的伤痛是深刻的,以至于退出书肆经营多年后,他在给朋友和门人的书信中还多次提到当年书稿未成而被盗印的苦恼:“《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47)黎靖德:《朱子语类》,岳麓书社,1997年,第393页。庆元三年(1197)他在一封信里说:“《本义》未能成书,而为人窃出,再行模印,有误观览。”(4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0《答刘君房》,《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86页。此时,朱熹已垂垂老矣,提起自己书稿被盗印的往事,已没有了往日的愤恨之情,更多的是忧虑盗版书中留存的错误得不到改正,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此外,朱熹经营书肆的失败或许与他的仕途也有关系。在建阳度过二十年的闲居生活后,在朝中大臣的推荐下,淳熙三年(1176)孝宗开始召用他知南康军,经过多次辞让,他在淳熙六年年初到任,开始了他有限的几年担任实职地方长官的生涯(49)胡迎建:《朱熹在南康军》,《朱子学刊》,1995年第1辑。,因此无暇顾及书肆的经营。以上种种因素最终导致朱熹经营书坊的倒闭。
四、余论
李致忠在论及宋代的出版史时说:“出版是文化事业,同时也是商品经营活动。从事业上讲,它有弘扬圣道、传承学术、传播知识的职责义务;从商品经营上讲,它又有降低成本、速成易售、行销盈利、可持续发展的正当权益。两者叠加,便构成了出版家的永恒的理念。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永远是出版者追求的目标。”(50)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11页。从事业上讲,作为编辑家和出版家的朱熹可以说是成功的。他把“有补世教”“传之来裔”作为图书出版事业的价值追求,穷其毕生致力于理学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弘扬儒学道统,促进了南宋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建构起庞大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使之成为其后数百年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但从市场经营上讲,朱熹是失败的。他的出版观是片面的,没能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最佳效果。朱熹经营书肆的成败,值得出版经营者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