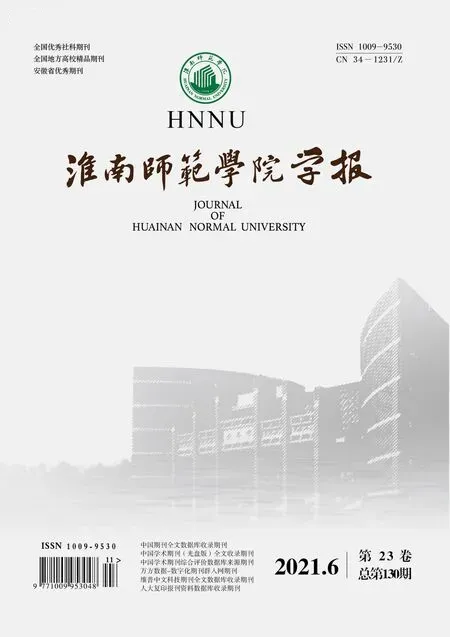“喜福会”:乌托邦式华裔女性共同体
许庆红,蒋云云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华裔作家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开始走出沉寂的状态,走向为华裔群体发声、赋权的文学实践。40年来,美国华裔文学的重要主题与同时期美国文学的主题比较吻合,大多集中在对种族、性别和身份等问题的探讨。谭恩美(Amy Tan,1952-)是著名的华裔美国女作家,其作品关注异质文化中的代际、性别和种族冲突等问题。在《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中,她基于个人的记忆,站在特定的视角观察中美历史和文化,聚焦华裔女性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历史和现实生存境遇以及不同代际的女性试图突破社会意识形态禁锢而寻求自我救赎的曲折经历。大体而言,中外评论界对《喜福会》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大多集中于对中国文化元素、母女关系的演变及其背后暗含的文化隔阂与和解、族裔身份建构以及女性自我赋权等问题的探讨,对小说建构的女性共同体内涵与缺陷却鲜有阐释。
根据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共同体”(Community)一词从14世纪便开始使用,该词在14到17世纪意味着“有别于上层人士的普通民众”,16世纪以后开始指代“一种共同的身份感和特征”[1](P39)。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城邦视为一种典型的共同体,“城邦是一种共同体,并且每一个共同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利益——每一个成员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追求在他们看来有益的事物”[2](P95)。他认为,共同体成员需要在精神上达成共识,每个成员为追求集体目标而奋斗。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则通过区分“社会”与“共同体”来明确“共同体”的概念。滕尼斯强调,“共同体意味着人类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共同体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P19)。共同体应该具有生命力、持久性与天然性,其内部各个成员间因为天然的情感纽带彼此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根据社会契约被人工聚合在一起。因此,基于亚里士多德、滕尼斯以及威廉斯等人的经典论述,不难发现共同体具有三个核心要素,即共同目标、情感纽带和共存空间。本文从这三个共同体要素切入,分析《喜福会》中华裔女性共同体的建构,并结合中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与现实,讨论这一共同体的缺陷,力图挖掘女性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缺陷。
一、华裔女性共同体的建构:自我与文化身份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裔在美国被忽视的状况开始改善,而华裔女性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性别和种族的双重他者身份。作为华裔女性的文学代言人之一,谭恩美与众多的第二代移民女性有着相似的经历。一方面,她是传统父权社会男性眼中的性别他者,父权社会的认知暴力通过家庭教育来灌输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她的母亲曾声称如果女儿不懂矜持,就会“怀孕并且生病,最后像一个肿胀的烂瓜一样死去”[4](P128)。另一方面,谭恩美是美国主流白人眼中的种族他者。尽管她生长在美国,但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她一度是无法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圈外人。在西方价值观的规训下,她对白人有着一些盲目崇拜的心理,不仅渴望成为白人太太,还幻想能拥有白人的长相,“圣诞节许愿的时候,我祈祷我能够得到金发男孩罗伯特的爱并且拥有一个高挺的美国鼻子”[4](P125)。因此,为了解决自我与华裔女性群体的文化身份危机,寻找归属感,谭恩美在小说中想象性地建构了一个温情、充满安全感的华裔女性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他们有着追求性别和种族平等的共同政治目标,有着母女亲情和姐妹情谊作为情感纽带,有着“喜福会”这一共存空间,她们既嬉笑怒骂又其乐融融,既冲突又妥协,努力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共同体,实现自我和群体文化身份。
(一)共同目标:性别与种族身份的诉求
共同目标指共同体成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而确立的努力方向,继承于同一祖先或在长期生活中获得的共同信仰或共同经历。“共同目标的定义形成于中世纪,它基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指的是一种切合共同体集体利益且只有通过集体努力才能被实现的利益”[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共同体的城邦,其追求的是一种“至善”,每个成员因这一目标而团结协作,以获得“幸福而满足的生活”[2](P95)。滕尼斯也认为,“共同体生活意味着共有与共享共同的利益”[3](P8)。只有确立了共同目标,才能调动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喜福会》中的华裔女性同根同源,在移民到新的国家后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性别与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相似的母国文化背景与人生境遇使她们达成共识,即要在异国建立一个共同体,致力于摆脱性别与种族双重话语的规训,实现真正的政治平等。
首先是要揭露种族主义的假面。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主要问题之一,从19世纪中叶美国华人移民现象出现后,华人的作品主题之一便是揭示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自然,种族主义更是压迫华裔女性的一根身体和精神枷锁。在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中,黑人女性被比作“世界的骡子”[6](P29),因为她们不仅遭受父权主义的压迫,还受到白人种族主义的“歧视”。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同为有色人种的华裔女性也面临着与黑人女性相似的境遇。身处美国的她们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而自我和文化身份的模糊又使其陷入精神危机之中。在美国梦的吸引下,《喜福会》中所描写的第一代华裔女性在20世纪40年代逃离了旧中国的苦难,移民美国,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在美国收获成功,幻想着“在那里,她会过得丰衣足食,无暇烦恼”[7]。但事实上,她们的生存境遇愈发艰难。在中国,顾莺莺出身高贵,住在体面的大户人家,有仆人伺候。但到了美国后,在丈夫圣克莱尔的管控下,她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和生肖,也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变成了家庭主妇,穿着不修边幅的“宽大的美国服饰”,做着“下人的活儿”[8](P305)。林多在到达美国前就已经被“美国化”了,她想象着在美国生个女儿,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可以使其规避华裔身份,从而免遭歧视,顺利在美国安家乐业。然而,当她抵达美国之时,为了能够顺利地通过移民局的审查,编造了许多谎言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最终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同样,对于第二代华裔女性来说,尽管她们身处美国,并竭力模仿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她们也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被精英阶层拒之门外。故事中的四个女儿们都是工薪阶层,吴菁妹甚至游走在失业的边缘。
其次是要推翻父权社会的压迫。性别歧视是造成女性生活不幸的原因之一,是对社会现实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主义的批评对象。女性作为“第二性”、附属品的地位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认为,“对男性至上这一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可保障了男性的优越地位却贬低了女性的价值”[9](P26)。父权社会将女性他者化,通过婚姻、经济和情感等方式制约女性认知。在旧中国,女性遭受数千年的封建压迫,受尽了屈辱,或卖身为奴,或嫁做小妾,或摊上一个风流成性的丈夫,成为丈夫的私人财产,没有自我人格。而男性则具有不容置疑的特权,可以妻妾成群,也可以随便休掉发妻。《喜福会》中的林多豆蔻之年就被许配给黄家做童养媳,父母规约她的行为,“顺从于你的夫家,不要给娘家丢脸”[8](P52),而婆婆更要求她将丈夫视为“天”,对丈夫言听计从。莺莺的第一任丈夫林萧将婚姻视为彰显男性权威的途径,得到了莺莺的青春、纯洁与爱情后,就开始在外面寻花问柳。安美的母亲原本是封建大家庭里的太太,丈夫早逝,她被吴清强暴,“被吴清一把揪住头发,猛地摔在地上”[8](P285)。她走投无路,只好做了这个男人的四太太,最终自杀。同样,小说中的第二代华裔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父权价值观,错将父权社会中的性别二元对立当成了认识自我的尺度,在情感和经济上成为丈夫的附庸。丽娜有一份独立的工作与收入,在公司里是辅佐丈夫哈罗德的一把好手,可是她的表现不仅得不到丈夫的认可,哈罗德甚至认为她的表现都仰赖于自己对她的提拔。而对于此,丽娜出于情感,有苦难言,心中郁闷纠结,不自觉间丧失了自我人格尊严。罗丝虽然拥有优雅的外表和清高的性格,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柔弱的受难之人,而身为风云人物的丈夫泰德则是上天派来拯救她的勇敢骑士。所以,当她的婚姻亮起红灯时,她心甘情愿地将生活的重心转向家庭,成为伍尔夫所言的“屋子里的天使”。
(二)情感纽带:母女亲情及姐妹情谊
情感纽带是维系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和伙伴情感,它能将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3](P33)。情感纽带具有多种形式,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真正的友谊”以及滕尼斯描述的“亲情”和“邻里之情”。“在共同体中,人们的相互联系是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的基础上。”[7]在《喜福会》中,维系着华裔女性共同体命脉的两条情感纽带分别是家庭里的母女亲情和姐妹情谊。
首先是母女亲情。滕尼斯认为,“人类意志的完全统一……以最强有力的方式,通过三种关系表现为直接的、互相的肯定,而第一种就是母亲与她的孩子之间的关系”[3](P22)。在《喜福会》中,母女间的关系尽管因为年龄代沟、成长背景的差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而存在芥蒂,但母女亲情作为情感纽带,在精神沟通与文化兼容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母亲用自己的丰富人生阅历为女儿化解心结,帮助她们认识自己,建立自信。莺莺很不理解丽娜和哈罗德之间倾斜的婚姻,敏感地洞察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她想着自己晦暗不堪的过去,更加为女儿的要爱情不要过度依赖的所谓平等婚姻忧心忡忡。她将自己比做一只潜伏在河对岸的老虎,随时准备为保护女儿而战斗。“丽娜从来都不吃冰淇淋”,莺莺指责女婿,“她变得如此之瘦,以至于你会忽视她。她像是一个鬼魂一样消失了”[8](P190)。她的发声不仅挑战了女婿的男性权威,而且唤醒了女儿内心深处对真正感情的渴望。在母亲的启发与鼓励下,丽娜意识到自己的隐忍和牺牲并没有给她带来婚姻的幸福、尊重与爱。她对哈罗德说,“我觉得我们必须改变”[8](P193)。 最终,她勇敢地告别过去,追求自己的内心,找到了新男友。同样,安美和女儿罗丝也是精神相连。当罗丝与泰德之间的婚姻出现裂痕时,罗丝对曾经坚定的爱情心生恐惧,丧失了自我主见。安美鼓励她勇敢抗争婚姻的阴影,追求自己所希望的幸福与个人价值,“为什么不为你自己说句话呢”[8](P231)?受到母亲故事的震撼,那股流淌在罗丝体内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血液唤醒了她的自我意识。面对丈夫的胁迫,她不卑不亢,怒吼着“我说我要留在这里”[11](P234)。罗丝不允许泰德夺走房子与女儿,最终重获丈夫的爱情和尊敬。林多对女儿薇芙丽的美国男友有着诸多不满,可是在她心里,女儿的幸福就是母亲最大的快乐,她最终宽容和接受了薇芙丽的第二次婚姻。另一方面,女儿也是母亲的精神支柱。母亲帮助女儿们寻“根”,女儿也改变母亲对自我的认知。如同萨斯托(Chantharothai Sasitorn)所言,通过“几代女性的连续性奋斗”[10](P33),华裔女性才可能实现自我救赎。林多不懂得“美国时尚”,她总是自己剪头发。但为了参加女儿薇芙丽的婚礼,她任由女儿带她去找美国发型师,剪一个适合婚礼的发型。她相信女儿的眼光,当她从镜子中看到自己,惊喜地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柔软的,每一缕头发都是乌黑的”[8](P323)。同时,薇芙丽在国际象棋上展现出的天赋和成就也塑造了林多的身份,她逢人必夸女儿,增添了自己身为人母的自豪感。
因此,正如作家南希·维拉德(Nancy Willard)所称赞的,“谭恩美在这本小说中的杰出贡献不是揭露母女之间是如何彼此伤害的,而是她们如何彼此相亲相爱,并最终宽容对方的”[11]。在母女亲情的纽带作用下,她们在冲突之中达成和解,成为伙伴,这是摆脱“他者”地位的一剂良方。
其次是姐妹情谊。友谊是共同体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纽带,亚里士多德认为:“友谊意味着共同体。”[2](P270)殷企平也认为,“任何共同体的建构,都不能忘记生活在‘漏洞’和‘边角’里的共同朋友”[12]。《喜福会》中有两种友谊:第一种是母亲之间的友谊。安美鼓励林多摒弃旧中国父权思想的禁锢,克服婚姻要“门当户对”和女性矜持的旧观念,勇敢地追求自己心仪的伴侣,还教林多写求爱信。素媛死后,她的几个姐妹在其女儿菁妹面前细数她的各种优点,代笔为素媛写信给她遗失在中国的女儿,并自愿资助菁妹去中国与自己同母异父的姐姐团聚,齐心协力帮助素媛实现心愿。第二种是女儿们之间的友谊。女儿们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受到美国文化的浸染,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受到排挤的“他者”,时常困囿于强大的美国主流文化。但是,她们得到母亲们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耳濡目染,当面对用美国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便转向植根意识深处的中国文化价值,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调和,在彼此之间寻找共融。丽娜对自我文化身份产生了错误的认知,罗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启发她,与罗丝谈话后,丽娜觉得“我的自我感觉好了些”,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我很聪明,我很理智而且我的直觉力很强”[8](P183)。菁妹带着“喜福会”众人的期盼回到了从未踏上的中国土地,与两位姐姐团聚,从而体会到血浓于水的亲情。
(三)共存空间:“喜福会”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74)中谈到空间的社会特征时指出,“任何空间都暗示、包含和掩饰着社会关系”[13](P83),因此,建构共同生存空间的过程也是建构共同体话语权、维护情感纽带的过程。共同体的共存空间是一个“人们生活并且进行日常活动的场所”[3](P79),这个场所十分重要作用,能够带给成员安全感与归属感。通过建构“喜福会”这一特殊的空间,华裔女性在很大层面上找到了情感的归宿和对抗异化的武器,重构了自我文化身份。在这一空间中女性由被动的命运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自己生命意义的行动者。在旧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素媛与其他几位女性拒绝坐以待毙的生活,组成“喜福会”,在危难与伤痕面前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到美国后,她将“喜福会”发扬光大,跟几个第一代华裔女性在这里聚会、打麻将,聊叙家长里短,彼此倾诉心声,发挥着庇护女性的作用。她们为每次的聚餐准备寓意美好的食物,如寓意财富的饺子、长寿的面条等,通过传承饮食文化传统来建构自我身份[14](PIV),这些琐碎的工作是共同体的基石。莺莺在旧中国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她担心丈夫对离异女性有偏见,无法对他倾诉。但在“喜福会”中,她能够找到和她有着类似遭遇的其他女性倾听者。素媛在战火中无奈抛弃了两个女儿,这种行为是要遭受唾骂的,而她也只能在“喜福会”中讲给自己的姐妹听。
同时,喜福会也是一个更广意义上的华裔共同体空间。美国韩裔学者金伊莲(Elaine Kim)认为,“许多移民者起初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来到唐人街,但后来他们一直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能得到积极的身份认同,以对抗西方世界的压迫”[15](P162)。“喜福会”作为唐人街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华裔心中传统文化的栖息之地以及重获种族身份与话语权的场域,让这群身处异国他乡、徘徊在美国主流文化边缘的异乡人可以穿中国服装,用母语闲聊、讲故事,在强烈的母国文化氛围中找到情感慰藉。大部分第一代华裔英语水平都不高,受到英语霸权的影响,他们是被销声的,无法自由地表达自我想法。“母亲能感觉到,这几家女人们各自都有她们遗留在中国的隐痛,也都对新生活有所憧憬。但是,蹩脚的英语使她们无法将这种憧憬一吐为快”[8](P9)。但是在“喜福会”内部,她们通过创造自己的“官方语言”——中英混杂的语言来表达自我,用一些不受英语语言限制的句子。例如:“You watch us,do the same.”(“你看着我们,也跟着做。”)[8](P24)打麻将时,她们还会使用行话,例如“碰”和“和”。在“喜福会”中,她们不再是被言说的少数族裔,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故事的发言人。
二、华裔女性共同体的缺陷:“母性谱系”和“东方主义”
在当代美国社会话语环境与作家本人际遇的影响下,谭恩美笔下的华裔女性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想象性建构:她将女性理想化而将男性他者化,形成“母性谱系”;她依循白人意识形态而实行族裔异化,具有西方认知结构下的“东方主义”色彩。两者的叠加,使共同体重新陷入性别与种族二元对立的窠臼,只不过这是一种女性优越与男性低劣的二元对立,其依旧是本质主义的话语实践,最终呈现乌托邦的愿景。
首先,《喜福会》共同体中的女性大多被理想化成勇敢、坚韧与聪慧的化身。安美的母亲用死亡洗刷自己的懦弱,换来女儿的坚强;林多从小靠自己的聪明成功挣脱不幸的包办婚姻并逃往美国;莺莺离婚后移居美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靠卖衣服自给自足;薇芙丽作风干练,能力超群,在国际象棋上打败了比她大的白人男孩,被尊崇为美国最大的希望;罗丝乐观自信,有着独特的性格魅力;菁妹如那片天鹅的羽毛般白净纯洁。她们均展现出近乎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打破了华裔女性的刻板形象。与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相反,华裔男性的形象几乎都是消极负面的,他们残忍、无情和霸道,被排除在华裔女性共同体之外。黄天裕出生尊贵,第一次见面时就将林多当作仆人对待,企图将其压制在男性力量之下;林萧花心残暴,将小刀插入西瓜中再缓缓拔出的行为暗示着对莺莺的性暴力;吴清的五次婚姻无一不建立在生儿子的基础之上,传宗接代的封建传统思想在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见,为了强调女性的自立和美德,谭恩美对于男性人物的塑造陷入单一模式,男性成为边缘化群体,如同蒲若茜所言,包括谭恩美在内的华裔女作家“似乎要重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西苏和乔多诺所描述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性谱系’,给处于弱势的华裔女性寻找力量的源泉”[16]。
其次,华裔女性共同体或多或少是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霸权文化背景之下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同化,按照西方的想象来建构共同体,强化了华裔男性的刻板印象,抹杀了华裔男性的声音,甚至有些歪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文内容均体现出西方认知结构下的自我/他者、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正如萨义德(Edward W.Said)在 《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中所说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复杂的霸权关系”[17](P5)。小说中的华裔男性可以说是劣迹斑斑,相反,白人男性金发碧眼,英俊潇洒,是华裔女孩们追求的对象。比如,同为帅气的富家少爷,林萧花心残暴,而泰德虽然也出过轨,但彬彬有礼。同样,在这一共同体中,在四个母亲和四个女儿的背后,是父亲角色的集体缺席,华裔父亲始终生活在女性的故事之外,处于“失语”状态,在房子的角落里读着报纸,像观众一般旁听着母女之间的争吵与和解。
此外,在捍卫民族文化尊严方面,华裔父亲的身影同样被抹去了。虽然在中国近代的社会环境中,移民人格卑微、经济落后,使得华裔男性在异质文化中也被边缘化,但作者把中国的过去和美国的现在做对比是存在偏差的,这种错位对比的背后透露出西方认知结构下的“东方主义”倾向。事实上,在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淘金热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铁路修建工程中,华裔男性都付出了努力。然而,小说中罗丝的父亲甚至无法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终日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伤之中。在他身上,罗丝看不到身为一名父亲所应有的勇敢与坚韧。与此同时,菁妹的父亲也游走在家庭的边缘,经常读着报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在小说中的唯一任务就是讲述妻子的故事,并带着菁妹与姐姐重聚。在完成任务之后,这一人物便从文本中消失了,叙事空间再次留给姐妹三人,他被完全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另外,小说中有一幕将华裔父亲的尴尬地位刻画得最为直接:薇芙丽的父亲试图在家庭聚会上讲一个笑话来营造气氛,然而当他说出排练多次的笑话之后,却遭到了其他人的漠视,只有他自己大笑起来。在这场聚会上,他仿若一个隐形人,一个被无视和“被阉割”的对象。
诚然,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思想背后涉及特定的话语语境。从历史层面上看,这是源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了华裔男性低下的地位。在上文提到的美国铁路建设工程中,华人男性并未得到政府许诺的荣誉与财富,反而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征用。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排华法案”,1924年又通过法案禁止华裔男性与白人女性通婚,种种政策造成华裔男性在美国的艰难处境;从文化意义上看,相比于东亚文化中父亲的严厉形象,母亲反而成为更加容易沟通的对象;从现实意义上看,作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边缘化的华裔作家群体成员,谭恩美采取异化策略,构建出有些“东方主义”的画面,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主流话语的认可。有研究者评论切中肯綮:“谭恩美笔下母女关系的演变是多种权力话语角逐的结果,包括政治权力与白人主导性话语等。 ”[18](Pv)
三、结 语
谭恩美以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华裔女性的中美经历、观念流变与身份蜕变。在《喜福会》中,她聚焦华裔女性过往与现在所遭受的性别与种族双重他者身份危机,建构了一个华裔女性共同体来寻求归属感。华裔女性以追求性别和种族平等为共同政治目标、以母女亲情和姐妹情谊为情感纽带,通过建构“喜福会”这一女性共存空间,完成了女性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在各种冲突背后,实现了一定层面上的文化融合。然而,这一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母性谱系”和西方认知结构下的“东方主义”特色。谭恩美或多或少受到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她利用异化策略,将华裔女性理想化、华裔男性他者化,这一共同体想象重新陷入了性别和种族二元对立的窠臼,使其最终呈现为一个“乌托邦”。在当下的世界语境中,华裔群体应当团结整个群体的力量对抗一切文化身份歧视,建构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真正提升华裔的整体社会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