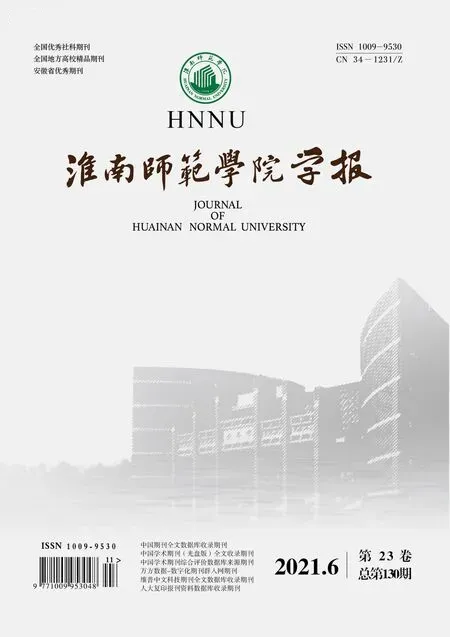对《淮南子》因势思想的探讨
霍 效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230039)
从战国到汉,道家哲学由对形而上的道的探讨开始向形而下的社会现实探究转变,道由无逐步落实到有,指导着现实人生的方方面面,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道”形而上与“物”形而下贯通的理论跨度成为汉代道家哲学思想家所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淮南子》一书正是这一问题最直接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尝试解答者。
《淮南子》一书对于道物贯通的解决方法是多方面的,既有对“道”的突破性阐释,也有对宇宙起源论的创新性构建,而因势思想同样也具有着这样的思维逻辑。李秀华认为:“老庄派在吸取老子、庄子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无为就是不在条件不成熟之前贸然行动,而是顺势因循或推动事物基于天性的自主行为,突出了无为由道化成术的一面。”[1]而《淮南子》之所谓“无为”即是因循事物自然之性与势的“为”,在这因势的“为”中完成由道到术的贯通,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物得到无滞的流通。但学界对《淮南子》因势思想的研究却相对稀缺,关于其间的人间之学的价值也仍有待深入挖掘。
一、以天地万物自然之性为内容的自然之势
在《淮南子》中从道到物是道的一种自然的展开,同时也是道向物的一种实然的贯彻,道物的过程呈现一种整体性、系统性。关于“道”,陈广忠认为:“《淮南子》中的‘道’,指的是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2](P1)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一书则针对《淮南子》之“道”指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道无所不能,宇宙间万事万物,无论多么巨大和微小,不管是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的,都是由道化生的;道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它是由自身内部阴阳二气矛盾作用而推动的;道是构成宇宙的物质实体,却又没有形象,但又主导万物。”[3](P91-92)道既作为万物的本原也作为万物本体而存在。在宇宙生存论上,万物由道而生,同时道也作为万物的规定性而存在,表现为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郭象注解《庄子》指出:“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4](P1)道生万物而赋予了万物各自之性,万物的自身之性既是其本身之所以然的原因,同时也是道的一种物的表现。
在这种宇宙生存论的基础上,《淮南子》继承了《庄子》的道物关系论,提出因势的思想。《庄子·齐物论》云:“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4](P38)“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比之谓物化。”[4](P61)《庄子》既看到物作为道的展开所具有的一种道性上的同,同时也看到万物虽然秉持了道不为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性而统归于道的最高规则之下,但在具体的展开上却也具有各自不可混淆的独特性与独立性。正是这种同中的不同,给纷繁的世间以可能,也为万种不同间的和谐提供了依据。与《庄子》更多的停留于对道物关系本身的探讨而提出“道通为一”的理论不同,《淮南子》则将这种关系更多的运用到对实物操作层面的指导之上,亦即《淮南子》的因势思想。
《原道训》云:“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2](P12)作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道的至高性显然是不变的,这也就意味着秉承道而来的物的自然之性同样也具有着不为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性。物的属性既然是客观实在的,那么违背物的自然之性的行为,也就无疑的导向错误,因此《淮南子》认为人作为物,生活在万物之间,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把握万物的自然之性,顺从万物的自然之势而行为,如此方能做到物我不伤。亦即《本经训》所云:“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辵然无欲而民自朴,无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谁何。”[2](P291)只有体察万物自然之属性,遵循万物独特的自然之势,在万物的道性下,做到不违背道的规定,在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逆反物的必然性,才能“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
《淮南子》中的自然之势有两种不同的区分:一是作为道生物与道成物指导性原则的道势;二是万物本身源于道所秉持的自身之属性与必然性之物势。
首先是道势。在作为规定性、主导性存在的道层面上,道下贯到物,不代表道就完全归于物,万物而万殊,是道赋予了物这样的独特性,故每一物性都可称作是道性的一种,但所有的物性相加却并不等于完整的道。道虽“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2](P4),并不实际具体地规定物的发展过程,却并不代表万物之外就是无道的,万物的发展就是肆意的。《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5](P7)长短相济,有无相生,物与物间的相縻与物自身的发展一样贯彻着不移的道性,受着道指导性的约束,在物性与物性的相互作用下达到“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2](P1),这也是《淮南子》所追求的至高道境。
其次是物势。物势同样分作两种:物个体本身所具有的较稳定之物势与物交縻所形成的随物态不断变化的较短暂之势。《原道训》云:“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2](P1)山以势高,渊以势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若以山为之低,渊以之高,则鸟至山前而头破,兽临渊而碎骨,此不知他物之性;若兽以走为飞,鸟以飞为走,则兽临渊而不知避,鸟至山前而无路,此不知自性。故得道柄者,知它性以避,知自性以顺。所谓自性,因在《淮南子》中“人”作为人所关注的一切活动之主体,故自性更多称之为人性。所谓它性则有个体之性与物态之性的分别。个性即单个物源于道的自身独特之规定性与本性(包括人性);物态之性则是个体之物相交縻,在道至高的指导原则下,物性与物性相合和所产生的一种随物态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虽短暂却客观不移之性。
在《淮南子》看来,天地有势,势相转运,万物成化,道的变化在天地的范围内表现为万物相互间的运转变化,阴阳二气的相縻以万物分和的运化周转作为形式而呈现。因循自然之势,也就是遵循天地之道。因而在道的实体层面,物的分和就是道运化的过程,道的客观必然性也就同时呈现在物不断的分和变化之中。只有清晰分辨这源自道的万物之性,才能在万物的不断变化之中顺万物而达道体,体道而识物性,达因势的第一层。
二、作为世界运转内容的物态之情势
万物在道赋予的各自“天地之性”下,“相縻”“相守”演化出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而人作为集认知与能动性于一体的独特存在参与其中经受着考验。《原道训》云:“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2](P12)作为本原的道虽然不能为人直接的感知,但由道而生的物的属性却是可以被人所发掘的,能否把握到这物性的本真就是人是否在这世间找寻到自身位置的判断标准。《人间训》作为《淮南子》一书中集中阐述如何处理人世间种种关系的思想之作,诚如陈广忠学者所说,它兼具了“心”、“术”、“道”[2](P788),是三者的融合贯通,是《淮南子》对“道”之形而上与“物”之形而下相贯通,这一问题给出的最直接的答卷。从“道”体“术”,以“术”归“道”,一“心”之间,“八极”而“一筦”,“无竟”而“一端”,《人间训》为我们呈现了《淮南子》因势思想解决人生问题的总原则。
通过《人间训》我们看到,回归物的本真对应着物性的两个方面同样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回归自身之本性,二是探寻物态之中不断变化的必然之势。回归自身之本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首先是对认识主体人的本性的回归。《人间训》开篇云:“清净恬愉,人之性也”[2](P788),作为一切事物的参与者,人只有保持自己的一颗清净之心才能更好的接纳接受外界的一切可能,加以分析辨明本末,予以应对。其次物性在物与物交织的过程中往往也容易在彼此的物性中呈现一种扭曲状态,同样需要还本归元,认清源头,如此方能在道的最终原则指导下,随着物态的不断变化而能清晰的把握其本身所蕴含的必然之势,亦即事物当下之性。关于探寻物态之中不断变化的必然之势,《人间训》云:“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2](P847)。因为这种新的自然之势交织在交縻的物性之中,且随着交縻之物的数量与程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故此加剧了人们认知辨识的难度。《淮南子》指出要辨识它就必须“得数”,《人间训》云:“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2](P846)审其所由而“得数”,“得数”亦即得道。《道应训》云:“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2](P475)万殊的物性随着物与物间不断的交縻,时刻的变化着,但不论其如何变化都是道之下物性的一种,溯本追源找寻到其原初物性之起点,遵循道最简单也是最高的衍化原则,结合以参与之物的独特之性,必能“得数”而明当下之物。
把握了物态的必然之势是不是就意味着逃离呢?《人间训》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秦牛缺径于山中,而遇盗。夺之车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盗还反顾之,无惧色忧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盗遂问之曰:‘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志不动,何也?’秦牛缺曰:‘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盗相视而笑曰:‘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圣人也。以此而见王者,必且以我为事也。’还反杀之。”[2](P830)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遇盗而不畏,失资财而志不动,可谓明道,然知道而未至道,世不以为贵,因为“凡有道者,应卒而不乏,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为人行也。其所论未之究者也。”[2](P830)能知之,不若能以知不知也,执本知要不是为了跳出事物之外,而是为了能更好的存活于事物之间。世界就是世间万物不断的分和聚化,人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一切事物的参与者,也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承载者。道生万物,道也就在万物之中,自绝于物,实则也就是自绝于道。《人间训》强调:“昭昭于冥冥,则几于道矣。”[2](P830)“昭昭”即明天地之性,万物之势,不被纷繁复杂的物之表象所蒙蔽,看清事物发生发展的原与末,把握事物的本真。“冥冥”则意味着虽然看清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看到表象与根本的不一致,但也同时认识到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样也是道演化的一部分,是自身不可抗拒的必然,因而做到不被表象所蒙蔽,却也不随意干扰事物的自然运行。所谓知事所当然而行其所必然,不以其知而逞其智,明其理而避其锐,知若无知以情度势,故而行以保真,知近真知。
知物顺势并不意味着人在一切事物面前都是毫无能动性的。《人间训》云:“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而莫能加务焉,则未可与言术也。”[2](P826)发展的物态的必然之势是在物与物的交縻之中不断生成变化的,明物性而防范于势之未生,此因势之最高境界。“晋公子重耳过曹,曹君欲见其鈘肋,使之袒而捕鱼。厘负羁止之曰:‘公子非常也。从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无礼,必为国忧。’君弗听。重耳反国,起师而伐曹,遂灭之。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祸生于袒而捕鱼,齐、楚欲救曹,不能存也。听厘负羁之言,则无亡患矣。”[2](P826)明白物与物相交所形成的必然之势,预见其将带来的不幸后果,则使物不交而势不成,祸不伤矣。曹君未见己国之势弱,晋公子重耳之非常,欺而妄之,故国灭。假曹君明己而知人,祸何至乎?此不明己、不明人,未知天地之势所祸于天。因此人在一切自然之下并不是毫无能动性的,只不过人之“动”必须是在因循万物必然之势的情况下“为”,如此才能不伤己、不伤物而身存。明己,明物,并在道的指导原则下时刻关注物态必然之势的变化而顺之。《淮南子》通过因势之思,调和了人之“人为”与自然之“无为”间的矛盾,使得人与自然的沟通在逻辑上与事实层面上都得到进一步的落实,道无与道法自然间的鸿沟也在悄无声息中获得弥合。
三、承接万物秉势之人心
因势的理论得到阐明,但却并不代表因势的行为就能得到贯彻。人作为一切活动的主体,是否能够明晰并把握天地之性,是否能够不被万物之表象所迷而坚定的因循万物之势前行,都是《淮南子》之“因势”所考虑的内容,亦属于因势之一部分。《人间训》开篇即言:“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2](P790)福祸自人而来,并不意味着人的意志决定着福祸本身。人对福祸的作用是“生之”、“成之”,是推动性的而不是决定性,顺着万物之势而事则自能避祸就福,反之则祸之自来。
能否察天地之性、顺万物之势对人来说就是福祸转换的关键,而心则是人作为主体能否明道顺势的决定者。《人间训》言:“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2](P788)在《淮南子》看来称誉与诽谤实则都是失道的表现,是一心之发动,心动则道失。
“人心”性“清净”,人之因势就必须把握物的本然之性,而要明了物的本然之性就必须先保持自身的“清净之性”。《精神训》云:“夫静漠者,神明之定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不随也。”[2](P250)心作为人与外界互通的门户,掌握着人性向外发散的尺度,反过来人心向内反馈的外界信息又同时影响着人性自身的洁净度,在这本与末之间人的这种清净之性往往受到人心变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故所谓“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2](P250),人之因势也就同样打上问号。
关于心的修炼,《淮南子》之因势要求“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2](P19)志者,《说文解字》云:“意也,从心之声。”[6](P421)“弱志”实即要求人临事时能够排除心之执念,而能“心虚”以广纳客观之势,进而能顺势做出最正确的行为。《淮南子》这里有迹可循的继承发展了《庄子》“心斋”之思想。《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4](P80-81)外界发生之事靠心的接受而转化为人内在的感知,进而决定人外在的行为,万物而万殊,万物相縻事端无穷,不论是物还是由物相縻而产生的时变时新的物态都秉承着道的不为人意志所转移的实然性,客观作用于主观,如果心有锢、有执、有念,亦即主观有选择的接受客观所反映的一切可能,那么由主观所反映的客观必然就是背离道的实然的,而由此所激发的行为也就必定是不和于事态、不因循于物势的。因此不论是《淮南子》还是《庄子》都强调“心虚”以待物。不过不同于《庄子》着重在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心斋”“坐忘”之思,《淮南子》在这里更多的从其在现实人生的具体运用上对其进行阐述。
对现实人心的修持,《淮南子》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曰修己心;二曰察他心。所谓修己心,罗毓平指出:“人心显现人性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人心通过自我修养与接受圣人教化相结合的两条途径实现的”[7](P102)。人心只有经过修持才能真实的体现人清净之性,这一点几乎是《人间训》最着重所要探讨的。《人间训》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2](P791)何谓损之而益?孙叔敖功于楚而其子请于有寝之丘、沙石之地,以其大功而请其贫瘠不详,此所谓损,然“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2](P791)。此所谓益。之所以如此,因知其子无大功而不受厚禄,未被眼前之利蒙蔽知性顺势之心。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厉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谀。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2](P791)取胜占地此天下之愿,然何则国倾而身死?以其“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之故。当其胜,才必胜其任。至胜累则意气骄横,忘其所恃,以胜心而据常心,德薄而得厚,心塞而身败,此利欲之败心。高阳魋为室而匠人辞穷,“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后果败”[2](P805)。摒弃专业人士之知,而以一己之见涉猎自己不曾熟悉的领域,此自以为智之败。“鲁人有为父报仇于齐者,刳其腹而见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2](P821)徐之为疾,迟之为速,追者曰:“此有节行之人,不可杀也。”[2](P821)此不虑而得,不谋而当,不以求生之心而乱义之活。
人生的福祸当然不止利欲、情、智等,《人间训》中颇多论及,不过也多未逃出《庄子》所归纳之二十四种。《庄子·庚桑楚》云:“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4](P428)所谓勃志、谬心、累德、塞道,皆不过是人一心之取舍,是人内外交织的动态过程。就如罗毓平所说:“《淮南子》中,道的根本意义是道的人性意义,即道性表现为人性。”[7](P98)只有修己心,明己性,方能见大道,因世势,达到《淮南子》所追求的圣人境:“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 ”[2](P15)
修持了自心,拂拭了自性,最终要达到的是“与造化者为人”。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人所要面对的就不止是自性所带来的物态之变化,同时也是他人之性所引起的物势的突变。《人间训》云:“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2](P847)虞氏富,登高楼,设乐陈酒,积博其上,适游侠相与其下,飞鸢至而腐鼠堕,遂有“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2](P847)之谚出。虞氏亡而游侠相得安否?虞氏祸于意满,得意而忘形;游侠祸于卑与妒,自卑而鼠堕以为辱,因妒而恶向胆边生。虞氏未明己性又未知它性,恣肆于人间,故祸从天降,身死而家亡。《人间训》慨叹道:“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2](P850)正是因为人之心对人之性的巨大影响,作为道性之表现的人性,给世间带来了无尽的不确定性,因此,不仅要修己性,同时也要关注他性,在己性与他性的交织之中达到真正的“常静”,最终因势而物我不伤。即所谓“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2](P840)此《淮南子》所追求的在人间界人生修养之最高境界,也是因势得以可能的人间修行的最高目标。
四、结 语
章晓丹在《〈淮南子〉的自然整体主义世界观》一文中指出:“《淮南子》思想中,无论是人还是自然万物都统称为‘物’,……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于大地共同体。”“在这种广阔的整体的眼光中,人类才能够做到合理地对待整体中的成员。……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它超越了以人类的主观需要为中心的偏见。”[8]《淮南子》之因势正是在这种思维进路下,明己、明物,修心、修性、修道,由宇宙界贯彻到人生界,使得“道无”与“道法自然”问题得到恰当的解决,在先秦道家及黄老道家的基础上,为新时期的汉朝开拓了一种更可取的、现实的人的行为准则、规范与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