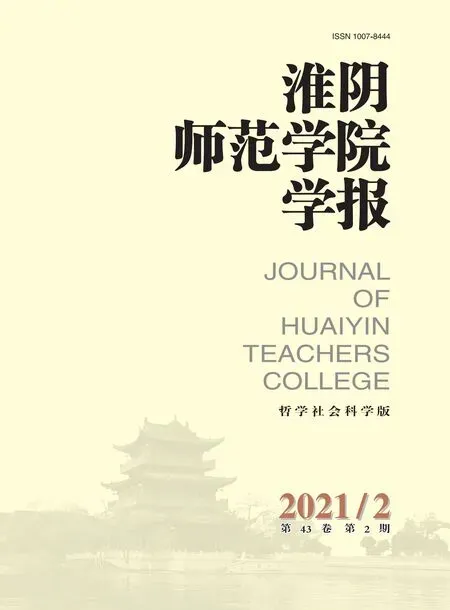周恩来旅日实证研究的力作
——《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岚山的周恩来:难忘日本!》评介
孙艳华
(淮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日本学者运用实证性研究方法研究周恩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矢吹晋编、铃木博译的《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与王敏著的《岚山的周恩来:难忘日本!》堪称典范。这两部书也是对周恩来旅日经历的深入探讨之作。
一、《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
《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是在考察周恩来旅日生活及其背景时不容错过的材料。该书全文翻译了《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日记部分为主体,共分9章:一、踏上留学日本之路;二、参观帝都;三、忧国;四、落第;五、艰难的抉择:是学习,还是革命;六、再次落第;七、短期回国;八、烦闷——沉默不语;九、再见!日本。每章附有“解说专栏”,共有10个专栏,依次为:神保町一带与留学生状况、三越和服店、当时的中国、毕业于美院绘画专业的保田、周恩来与读书、政治觉醒、当时的浅草与和食、大正民主、短期回国时的路线、空白的7个月。“解说专栏”从饮食、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描述了周恩来在日本的生活实景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周恩来的活动区域、交友、所读书籍和短期回国时的路线等进行了考证。其中,“政治觉醒”的解说还对周恩来思想的变化进行了考察。如果说专栏部分是对日记内容的深入解读,那么卷末的“解说:成为日中友好原点的《周恩来旅日日记》”则是对周恩来一生的总括,成为该书的画龙点睛之笔。该书通过丰富的一手资料——详细的年表、图表、照片、地图、《露西亚评论》上登载的论文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试题等参考资料和言简意赅的解说,鲜活地再现了周恩来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行。周恩来虽未实现进入高等学府的梦想而最终回国,但近一年半的东京体验对于其后的中日友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专栏和解说部分的文字虽非长篇大论,但在对事实的描述和背景的考辨中时常表现出论者的识见。例如:周恩来是“时代之子”;师爷是解读周恩来一生的关键词之一;周恩来调解人际关系的能力自幼得到锻炼,后来成长为具有非凡调解能力的伟大政治家;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才华出众与其个性相关;周恩来的魅力体现在兼具外交家的微笑与革命家的坚韧;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周恩来调和、妥协、自省,具有大局意识与灵活性,因而他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多采取调和或中庸的态度。
论者客观分析了周恩来的行为方式,评价中肯。例如:针对《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协定》秘密谈判的抗议活动成为周恩来日本留学生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周恩来与其说是行动派,不如说是冷静的观察者;1920年被捕入狱,使周恩来经过约半年的历练,从关心国家命运、热心于社会改造的进步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但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该书认为青年周恩来带着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国民性的感性认识回国,这成为他日后准确理解日本人的基础。老一辈日本人中有许多热爱周恩来的人士。周恩来与日本人交往方式的原点在于留学日本时期,即“在‘军国主义日本的形象’之前接触到了‘大正民主思潮中的日本国民的真实形象’”。这对于中日友好事业意义非凡,“周恩来熟知日本人的国民性和风俗习惯,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其见地发挥了很大作用”。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其学术价值体现于通过考证有许多新发现。书中披露了如下史实:(1)汉阳楼首任店主是绍兴籍。论者认为周恩来频繁光顾汉阳楼是为重温故乡的味道;“中华第一楼”位于面对神保町的铃兰街,现搬至银座。第一代店主林文昭是社会活动家,明治时代末期与孙文一起来到日本。当时的“中华第一楼”极其兴盛,成为鲁迅、犬养毅等名人及政府要人的社交场所;维新号是神田一带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料理店。(2)日记中唯一实名登场的日本人是保田。保田与周恩来的关系被电视制片人郡进刚于1999年挖掘出来。保田本名保田重右卫门,即后来的保田龙门,生于和歌山,时年27岁,年长周恩来7岁。周恩来日记中说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其实,保田早在周恩来到达日本的半年前业已毕业。周恩来寄宿在保田租住的灵梅院是因为严智开的关系。后因房子被收回,周恩来仅住了3周。保田龙门长子保田春彦发现了两份珍贵的史料:一份是找房子时的笔谈记录,记录中日本人是保田,中国人是严智开或周恩来;另一份是保田所绘周恩来画像,肖像画中的周恩来身着和服,正视前方,目光炯炯有神。保田与周恩来后在巴黎重逢。据龙门自书年谱(1921年)记载:剃光头的周恩来来到研究室,嘲讽我们的雕像似意大利通心粉,大概是说没有中心思想的意思吧。(3)论者根据日记和当时的时刻表详细再现了周恩来短期回国时的路线:从下关乘船到釜山,从釜山乘火车到天津。但关于回程,日记未记载。论者认为出于日程的考虑,从天津乘船的可能性不大。(4)演员高峰秀子的随笔集《人的肚脐》收录的《梅原龙三郎与周恩来》一文写道,“我想画的男性,全世界唯有一人,那就是周恩来”。该文将周恩来评价为“男人中的男人”。
同时,该书匡正了日记及周恩来研究文献中的如下错讹:(1)1月20日日记中的“王越美服店”应为“三越吴服店”,系出版时编辑辨认失误。(2)在日记中,周恩来将《露西亚评论》误记为《露西亚研究》。(3)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加深了对十月革命的理解,通过阅读河上肇的《贫穷物语》(1917)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汉语版1906)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但是,日记中并没有直接触及上述情况。(4)另一个误传系日本捏造的报道。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掀起周恩来热潮,搭便车的报道屡见不鲜。载于《女性自身》杂志(1972年1月15日号和22日号)的《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神近市子采访周恩来的报道便是其中之一。
再者,该书史料极为丰富。家谱、主要人物关系图、标注着周恩来活动范围的地图及数据、收支记录、年表、参考资料、地图、照片等种类繁多,为读者了解周恩来当年的生活和经历提供了直观的材料。
该书首次将《周恩来旅日日记》翻译成日文,不仅为日本学者研究周恩来提供了研究基础,也使普通日本民众通过该书更直接地感受到青年周恩来的生活细节。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通俗流畅、解说简洁精到,既具有研究著述的学术性,又避免了学术著作的晦涩。在周恩来逝世20余年后的1999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人们久远记忆之际,该书的面世为肩负中日友好未来使命的日本年轻人了解周恩来,以及日本民众重温周恩来与日本建立的友谊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岚山的周恩来:难忘日本!》
日本关于周恩来思想和政治理念的探讨多散见于论文或专著中,系统性论述周恩来思想、政治理念的专著非常之少。王敏在《岚山的周恩来:难忘日本!》中的尝试无疑具有开创性。该书以宏富的文献资料和翔实的实地考证,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源头探赜索隐,体现出作者扎实、细密的研究风格。作者为探寻周恩来两度访岚山的缘由,实地考察了岚山的人文地理环境,发掘出中日文化交汇的点与线。这里的“点”即是大禹和被称为日本大禹的角仓了以、日本黄檗宗开山鼻祖隐元及推广者高泉;“线”则指共同的文化背景将四者联系在一起。进而,该书点明周恩来两度访岚山时的发现与感悟,及其对中日民间外交的启迪意义,指出“疏通”是周恩来以民间为主体的外交思想的源头。
全书共分6章,第一章“雨中岚山”之邀、第二章“雨中岚山”逍遥考、第三章“疏通”促进对日民间外交、第四章周恩来与法政大学、第五章近代中国人的日本留学、第六章关于日本大禹信仰的考察。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的是前四章。
在第一章中明确了以下事实:周恩来纪念碑位于岚山龟山公园南门附近。角仓了以的铜像与周恩来纪念碑近在咫尺。角仓的铜像于周恩来游京都的6年前,即1912年建成。角仓系日本水运之父,传承了大禹精神,被视为日本的大禹。角仓创建的大悲阁千光寺位于岚山入山口,原属天台宗,1808年改宗黄檗宗。
作者实地考察了《雨中岚山》诗词中所描写的景致,推测出周恩来1919年4月5日的行程:从吴瀚涛位于左京区的住所,即现在的左京区区役所出发,乘坐于1910年3月25日开通的京福电车。从始发站四条大宫上车,在终点站岚山下车。下车后,一边欣赏沿途风光,一边来到渡月桥。过桥,步行40分钟后,作者被眼前的景观震慑住了:山水环绕的道路尽头是大悲阁千光寺山道的入口,与《雨中岚山》中描写的“突见一山高”的景观完全吻合。山道入口右侧景色正如诗中所描绘的,“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山道两侧立着石碑,上面刻着黄檗宗高僧高泉性潡所作的七言绝句《登千光寺》。
第二章从治水之家的历史、绍兴的祭祖习俗、自中学时代便已深入周恩来内心的大禹精神、中日文化的交融等方面考证了周恩来岚山之行的目的及在岚山之新发现,指出此行的意义在于,“说得极端一些,通过游岚山提升了替对方着想的独特感性,磨炼了灵活多元看世界的眼光。这在其一生中形成一种惯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中不自觉地加以发扬。这种惯性有效促成了对外外交的潜在效果,在面临无数国际关系难关时发挥了作用”。替对方着想成为周恩来人格魅力极为突出的因素。
关于治水之家的历史,该书指出周恩来生母的娘家——万家三代人与治水有关,培养了周恩来对大禹的感性认识与关注。史传记载的以大禹为主题的历史遗迹40余处,绍兴大禹陵为其发祥地。绍兴与大禹历史渊源很深,绍兴人的大禹情结浓厚,周恩来自幼也明显受到大禹文化的熏陶。
作者推测周恩来选在清明节游岚山是为了祭祖和祭祀大禹。第一次游岚山时偶然发现被称为日本大禹的角仓了以铜像,知道了大悲阁千光寺的存在,因而对于大禹的虔敬之情陡增,自然会产生再访岚山的念头。1919年4月5日的岚山飘着小雨。对于中国人来说,清明时节雨纷纷正符合祭祖的心情。1919年的清明节是4月6日,周恩来为什么特意选在5号去岚山呢?这是因为4月6号要与新中学会的八位成员会面。书中附有周恩来与新中学会成员的合影,照片上赫然写着“中华民国八年四月六日摄于日本京都”。
在探讨隐元和高泉对周恩来的影响时,该作指出,隐元于明末清初来到日本普及推广黄檗宗。追随隐元的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黄檗宗影响了后世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成为在日华人的精神寄托。鲜明的中日文化融合的烙印在岚山大悲阁千光寺集中体现出来。这必然诱发了周恩来强烈地追溯历史文化根源的欲望。可以想象,“何人治水功如禹,古碣高镌了以翁”,高泉的这一题词也势必勾起对大禹抱有特殊情感的周恩来对故乡和祖国的情感。同时,也一定再次全面加深了对日本的亲近感和认识。作者认为,相同的历史文化在与岚山相关的人物——角仓、大禹、隐元和高泉身上重叠,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将原本分散的点连接成线,而多条线交错在“治水”这一点上。进而,通过“疏通”这一治水手段与周恩来的民间外交联系起来。
此外,作者还考证了周恩来在京都的住所。关于周恩来在京都的落脚地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吴瀚涛家。作者依据《周恩来旅日日记》记载的地址进行了实地考察,该住所现已变为左京区区役所。另一住处被认为是大德寺芳春院,位于京都市北区紫野大德寺町。经作者确认,没有资料记载周恩来曾经居住在大德寺芳春院,也未发现相关传言。
在第三章中,作者推断,周恩来两度游岚山的动机是为寻找治国的参考素材,断言“一点光明”指的是角仓给予的启迪。周恩来注意到角仓的成功范例可为中国提供借鉴。角仓模仿大禹以“疏通”为本的治水法在日本获得成功。或许青年周恩来从中悟到了“疏通”方法的可行性。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将从“疏通”中得到的启示活用于对日外交也是可能的。要想改变敌对关系必须“疏通”,“疏通”的主体姑且交给民间。因此,要想“疏通”中日关系,至少初期阶段的外交需要以民间为主体。
作者指出,周恩来提倡对日民间外交与1919年考察岚山不无关系。在岚山遇到的人物群像和岚山的历史人文环境可以视为对日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难以想象在对日外交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周恩来对日本风土人情的观察。留学日本使其构筑和积累了建立良好国际关系的经验和知识,对日本社会的实际考察巩固了其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外交框架的信念。他从日本体验中把握了将中日两国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的历史文化脉络,重新系起断绝的纽带。这些都是通过岚山的雨中樱花而得以升华的。
作者在第四章中援引原法政大学总长中村哲和大内兵卫、原法政大学社会学部教授柘植秀臣、法政大学教职工等关于周恩来曾在法政大学附属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学习的观点,通过查阅载于法政大学编纂的《法学志林》上的法政大学附属高等预备学校招生广告,考察《周恩来旅日日记》,以印证上述观点。作者指出,日记中虽未明确记载曾在法政大学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但是从中可发现一些间接线索:(1)《周恩来旅日日记》内容不完整,没有记载抵达日本的最初三个月及回国前约半年间的经历,这期间存在去法政大学附属高等预备学校或是其他学校听课或临时入学学习的可能性。(2)日记中记载了与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的范源廉见面交谈一事。范源廉与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创建与发展渊源极深。周恩来有可能受到范源廉的影响对法政大学产生兴趣。作者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周恩来在法政大学附属高等预备学校学习的可能性。
作者认为周恩来留学日本是“符合时代的个人选择”,“具有学习实用专业的倾向”,体现了“以日本为媒介的留学观”。周恩来旅日期间积极理解日本社会和民情。对于周恩来而言,日本即是学校,也是检验历史的试验场;既是把握世界时代潮流的媒介,亦是掌握变革中国所需知识的场所。作者高度评价周恩来的留学经历,指出周恩来广博的人民外交思想的根源在于留学体验。共产主义思想连接起旅日和旅法,积累了构筑良好国际关系战略的经验和智慧。周恩来以日本体验为基础,依据法国留学时对欧洲的观察,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必须共同承担艰难,中国人也应该适当分担”。彼时,周恩来刚刚20出头,中国共产党尚处孕育期,苏俄革命尚未明确前进方向,能够提出如此具有思想高度的观点,其意义不容忽视。周恩来旅日期间获得的认知,在旅法期间有了长足进步与提升,并逐渐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主导的一系列外交战略中。
综览21世纪的日本周恩来研究界,在日华人学者的研究十分活跃。王敏的《岚山的周恩来:难忘日本!》正是这种现象的缩影。该书系在日中国学者首部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学术专著。该著的日文版和中文版相继在日本面世,影响不容小觑,其突出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视点新颖独特。该书并不试图展现周恩来旅日的全部图景,而是以周恩来的岚山之行为切入点,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开掘。中国的学者经常以“革命生涯”为出发点探讨周恩来的各个阶段的经历与其成为革命家的关联性,将周恩来留学日本时期归纳为其革命生涯初期的探索阶段。该书则另辟蹊径,从中日文化交融的视角对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进行追根溯源。
第二,实证研究与理论深度的完美结合。为撰写该著,作者沿着周恩来的足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如周恩来从吴瀚涛家出发至岚山及到达大悲阁千光寺入口的路线,甚至亲赴万隆和法国进行考察。日本研究界所重视的实证性研究在该书中得到集中体现。同时,该书不满足于仅仅在实证性研究基础上对事实进行客观描述,还通过思辨与论证,开掘诸多事实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关系,实现了实证研究与理论深度的完美结合。其研究价值正如作者所言,对周恩来旅日期间的活动进行现场调查和时代考证,不仅可以科学地展示先贤们探索外国知识与智慧的模式,解析留学文化与中国革命的表层与潜在的联系,更有利于论证周恩来为中国与世界融合共存所发挥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第三,背景知识考证翔实。作者十分重视原典性材料和科学实证。一是援用了大量历史照片、图片和绘图。例如,1936年京福电车的路线图,1919年4月6日周恩来与新中学会八位成员在京都的合影,1939年3月30日周恩来回绍兴呼吁抗战顺便与亲朋祭祖参拜大禹陵时的照片,1911年早春鲁迅与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及同学参拜大禹陵时的照片,不一而足。其中,不乏第一手资料,如周恩来两次在岚山的活动路线手绘图、大悲阁千光寺山道入口处照片、高泉诗碑照片、角仓了以铜像照片等。二是对相关背景进行了广泛、细致而深入的考察。例如,关于日本大禹信仰和黄檗宗的形态及流传脉络的探讨,关于对日民间外交定义及人民外交思想研究资料的引用等,从而增加了研究的厚度。
周恩来旅日研究是日本周恩来研究的优势领域。但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事实没有被描述出来。《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的意义在于首次将《周恩来旅日日记》翻译成日文,依据史料对日记及周恩来旅日研究进行甄别与考据,纠正了许多错误认识,并以大量第一手材料还原了周恩来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为深入解读《周恩来旅日日记》提供了帮助。《岚山的周恩来:难忘日本!》的价值在于通过实证性研究考证了周恩来岚山之行的路线、目的、感悟及其意义。而且作者知微见著,将岚山之游提升为周恩来的精神之旅,将其视为周恩来以民间为主体的外交思想的原点。《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和《岚山的周恩来:难忘日本!》在准确还原周恩来旅日经历,深入开掘旅日体验的意义方面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