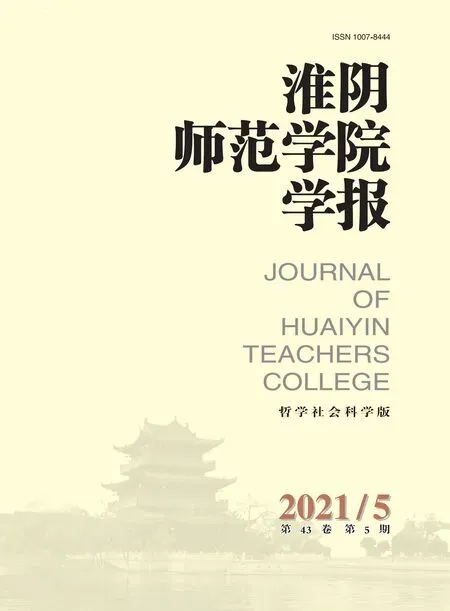商鞅变法后秦统治理念的变迁
冯国亮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秦自商鞅变法后,修法理政,崛起于西陲而终并天下。在此过程中,秦国确立了君主直接控制、支配百姓的政治格局。(1)刘泽华将这种格局称为王权支配社会,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5页;雷戈则将这种格局描述为“皇帝—民众关系的二元对应性”,见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探讨秦国国家体制确立的过程,不能忽略其统治理念的变化及其对于秦国政治的影响。
有关商鞅变法后秦国统治理念的研究成果丰富。(2)如蒙文通:《秦之社会》,《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齐思和:《商鞅变法考》,《燕京学报》1947年第33期;杨宽:《商鞅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林剑鸣:《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李存山:《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章;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章第5节;刘泽华:《中国政治通史(秦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章;邢义田:《秦汉基层吏员的精神素养与教育——从居延牍506、7(〈吏〉篇)说起》,载《今尘集——秦汉时代的简牍、画像与文化流播》,中西书局2019年版;等等。早期研究多认为秦国统治理念以法家思想为主,摒弃德政。例如徐复观先生认为,秦国“离开了法家思想的线索,便无法理解(秦国)专制政治出现的根源及其基本性格”[1]76。随着出土材料增加和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关注到秦统治理念中的德政因素。例如张梦晗认为,在(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等文本中,秦官吏呈现“君子与良吏兼而有之的形象”,“不能轻率认为秦对‘以吏为师’政策下,官吏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暴政、急政的危害性没有认识”[2]。肖永明认为,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等文本肯定了慈下爱民、谦恭有礼的儒家思想在秦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3]学界认识到秦统治理念至少杂糅了任法重刑和德政的思想,但关于秦国统治理念的变化过程及其未取得实际行政成功的原因,尚有待探讨。
本文以秦统治者对待“任法”与“德政”的态度为核心,分析秦孝公、商鞅及其之后数代秦国执政者的为政思想,阐述商鞅变法后百余年间秦国统治理念的变迁,为秦统一及其短祚而亡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以冀增进对于秦中央集权式政治诞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解。
一、商鞅变法时期:任法重刑理念的确立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实行的第一条举措即“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4]2230。这表明,秦国变法首先致力于立法与司法体系建设。商鞅通过设立严刑峻法,并利用司法实践中的连坐及基层什伍组织内部自我监管的功能,规范百姓行为,通过简单易行的奖惩机制,迅速实现君主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建立“君—民”社会联系。变法条文中对于“告奸者”“匿奸者”与“斩敌首”“降敌”赏罚相当,“显系以军法控御”百姓。[5]变法伊始,秦国统治理念即体现了强烈的任法重刑倾向。
记载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集中反映了秦统治者已摒弃善政理念。《去强》:“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6]27商鞅认为,实行为善、怀柔的政策必然导致“奸民”增多,民强则国起内乱,民弱则众皆依上,唯以权力压制民众,才能使秦国“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4]2231。所谓“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6]80。可见,重刑轻德是商鞅重构秦国社会秩序的坚定主张。
在秦国统治者摒弃善政理念的背景下,任善的理念也遭到否定。所谓“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6]125。商鞅认为,善治与法治是一对相悖的概念,若任用行使德政的官员,则会导致社会意见纷繁,法治难以推行。秦国统治者的任官方针落实为两点:一曰任功。“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6]77二曰明法。“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6]22商鞅主张以“任功”“明法”作为任官重点,目的是使秦国社会维持一种高压态势,集权于统治上层。
值得注意的是,商鞅所反对的“任善”仅是官员的“私善”。“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6]130,意即官员私自对百姓实行善政会阻碍法治的推广。由此,他否定怀柔手段在行政上的意义。《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6]80可见,行政上的“修善”及礼乐、诗书的教化均被商鞅视为建立君主集权的障碍。因此,商鞅要求秦国官吏将对百姓的“私善”转变为对君主的“奉公”。《商君书·定分》说:“法令明确后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6]144商鞅将官员的为善行为限定于“自治奉公”,即对君主效忠。商鞅变法使传统政治道德让位于“公德”,即法治集权,任法重刑理念开始流布于秦国。
有学者认为,“与法家思想结合后的秦文化,是一种‘作壹’(或曰‘用一之道’)式的文化,实际即一种以‘战’为核心的结构失衡、畸形发展的文化”[7]。秦孝公时期,秦国统治者选取重刑轻德的理念,既出于与诸国争衡的需要,更导向构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目标,“君—臣—民”三体关系中的利害诱导和法令约束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突显出来。
二、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时期:任法重刑理念的深化巩固
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前期,秦国政治局势发生显著变化,商鞅变法期间被压制的政治势力有所抬头。秦昭襄王统治前期,甚至出现了“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4]2329的现象。
这一时期,秦统治者继续以任法重刑为行政理念,以巩固自身统治。秦昭襄王后期,任法重刑的理念达到高峰。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昭襄王晚年生病时,“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昭襄王得知后,不仅不感念百姓对自己的爱戴,反将其称为“擅祷”,依秦律处以罚金。秦昭襄王认为,若因百姓爱己而允许其擅自祭祷,将导致法律不行,而“法不立,乱亡之道也”[8]336。这体现了当时秦统治者轻视道德教化和善政善治,以及对秦法有效执行的重视。
这一时期,秦统治者还着力于压制权臣势力,加强君主集权,在任法重刑的基础上,又以重术的理念来驾驭群臣。秦昭襄王中期,秦君已能随意任免官员、主宰官员生死。例如,秦昭襄王听信范雎之言,驱逐权臣魏冉,魏冉只能出关往其封邑陶地,死后陶地亦被昭襄王收为秦郡。尽管魏冉身为国舅,“贵极富溢”,秦昭襄王仍可使其“身折势夺而以忧死”[4]2330。又如,邯郸之战时,秦昭襄王“强起”武安君白起,白起不听令,则免为士伍,并赐剑自尽。[4]2337白起一生战功赫赫,是“秦地半天下”局面的直接缔造者,却因忤逆国君之意而不能善终,秦君独断之威势可见一斑。可见,从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时期,尽管秦国集权进程出现了些许波折,但从结果来看,君主权力得以加强。
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期间的驭臣之道,以加强人主威势和统御之术为核心内容,主要手段是控制、压服和利用官吏。秦君对待臣僚的态度亦为诸国士人所知。当齐国孟尝君欲入秦为相时,苏代前往劝阻,指出孟尝君若轻率前往秦国,会有“不得还”之危险。后孟尝君入秦为相,秦昭襄王果因他人谗毁而对其起疑心,“囚孟尝君,谋欲杀之”[4]2354。
荀子曰:“秦人其生民郏厄,其使民也酷烈。”[9]从秦孝公商鞅变法至秦昭襄王逝世的百余年间,任法重刑的行政理念和任功重罚的任官理念在行政实践中不断强化,最终奠定了秦国的行政模式。
三、秦孝文王至吕不韦时期:“德政”“任善”理念的推行
秦昭襄王统治后期,因君权过度集中而削弱了中央的纠错能力和国力。长平之战后,秦昭襄王因忌惮白起战功,拒绝其立即进围邯郸的建议,错失占领赵国首都的时机。之后数月,秦昭襄王又固执己见,在赵国已有准备的情况下让王陵进攻邯郸,导致“陵兵亡五校”[4]2336的军事失败。同时,酷烈的驭臣之道也使官吏产生叛离之心。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8),“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4]2417。昭襄王后期,秦国陷入“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4]2337,“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4]2418的境地。
有鉴于此,秦昭襄王死后,继位的秦孝文王与秦庄襄王对秦孝公以来的统治政策进行了改良。《史记·秦本纪》载,秦孝文王即位时曾“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秦庄襄王即位时亦“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4]219。两位秦君在即位后迅速实施爱民惠民的政策,并表明厚待功臣宗室的政治态度,说明任法重刑理念有所松弛,以控制、压迫为主要手段的驭臣之术得到调整。秦孝文王与秦庄襄王之政策转变,可能部分出于个人的原因(3)如秦庄襄王早年在赵国为质子,与秦交通悬绝,在秦廷内政治势力单薄,其即位完全依赖吕不韦和以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势力的支持、故其即位之初放弃任法重刑,结好宗室和重臣,并怀柔百姓,有争取各阶层支持,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但主要是为了纠正秦昭襄王统治后期的政策失误,这也为“德政”“任善”理念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秦庄襄王去世后,吕不韦在赵太后支持下迅速把持朝政,以至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4]2509,秦国君强臣弱的局面一度改变。为进一步树立个人声望,吕不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4]2510。秦国政治局面的改变,促使统治理念进一步发生变更。
吕不韦出于保持权势的目的,宣扬怀柔臣下、善待百姓,摒弃法家专任刑法的统治理念。这从《吕氏春秋》的内容可知。《吕氏春秋》杂糅了当时各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吕不韦在组织宾客编撰此书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对诸子百家思想皆有所吸收。[4]2510《汉书·艺文志》认为《吕氏春秋》具有“兼儒墨,合名法”[10]1742的特点。更有部分学者认为《吕氏春秋》中缺少法家理念。徐复观即称,《吕氏春秋》“因含有反对秦国当时所行法家之治的深刻意味,故一字不提法家”[1]117。可见,一向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理念的秦国统治者,竟允许这种包含各种学派主张的书籍出现,显示任法重刑政策有所松动。
同时,《吕氏春秋》将德政摆在首要位置。此即所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11]517,明确提出了行政应非赏罚、重德义的观点。而德政的核心,在于君主本人的“为善”。《吕氏春秋·骄恣》称:“以理督责于其臣,则人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非;可与为直,而不可与为枉。”[11]576而君主为善的目的在于使民爱上。“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11]191为约束君主而使之为善,则务须求取善士,所谓“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11]311。此处的“善士”,并非商鞅所要求的明法令、“自治奉公”式的官僚,而是“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11]270的诤士。由此可知,吕不韦并不提倡士人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总体来说,德政、任善主张的提出,除了反映吕不韦试图扩大权力、把控秦廷政治外,也反映了其反对法家单纯依靠刑法、赏罚治国的理念,主张以道德教化手段怀柔民众的政治理想。这体现了以吕不韦为首的官僚缓解秦国社会矛盾以维持局面稳定的努力。
德政理念的宣扬对秦国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吕不韦执政期间,除秦王政二年(公元前245)麃公攻卷一役外,其余战争均无斩首记录。杨宽先生认为,秦此时放弃“尚首功”之传统,当与吕氏鼓吹“义兵”“诛暴君”有关。[12]
德政理念的推行,使秦国缓和了国内外的矛盾。经历邯郸之战后,秦国国力得到一定恢复,稳固了在争霸中的优势地位,为秦王政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秦国的统治理念亦因此开启了对任法与德政思想的杂糅,并深刻影响之后的政治活动。
四、秦始皇时期:“法治”与“德治”理念的矛盾杂糅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并天下,任法重刑、任功重罚的统治理念重新得到强化。始皇的统治特点被司马迁评价为:“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4]238秦始皇在泰山刻石亦记其统治手段云:“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4]243在琅琊刻石载其功绩曰:“端平法度,万物之纪。”[4]245这说明秦始皇执政后,首先实行秦孝公至秦昭襄王时期的行政理念。其任法重刑之举,符合当时秦国一统天下、加强君权的政治需要。其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远征四夷、徙民戍边、营建长城宫室陵寝、巡游天下、广发徭役兵役、钳制社会思想,均基于任法重刑的政策之上,即所谓“上乐以刑杀为威”[4]258。吕不韦主张的君主为善理念事实上被摒弃。
然而,秦始皇虽然在具体行政上逐渐回归任法重刑,却并没有像商鞅那样赤裸裸地鼓吹法治与君主集权,而是以德治作为补充手段。在琅琊刻石中,秦始皇夸耀自己在德治上的成就:“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4]245其在任法重刑的大前提下对推行德政的宣扬,表明他认为道德元素是一种有效的治理补充,官员和百姓对道德和礼仪的遵守,能够缓解苛政造成的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4]262,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
秦始皇也通过任用有道德和为善理念的官员,树立秦廷的“德治”形象。从作成于秦统一天下前后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为吏之道》和《岳麓秦简》之《为吏治官及黔首》等官吏教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阶段“任善”方针的推行。在《为吏之道》中,秦政府对官吏提出了“审智(知)民能,善度民力”和“喜为善行”[13]167-168的道德要求,并要求官吏做到“宽俗(容)忠信”“慈下勿陵”[13]167。秦政府不仅要求官吏自身具有德治理念,更将褒扬行善风尚作为官吏的治政职责。《岳麓秦简》中有一条指令:“黔首或事父母孝,事兄姊忠敬,亲弟(悌)兹(慈)爱,居邑里长老(率)黔首为善,有如此者,牒书。”[14]此时秦始皇大概已经认识到一味地任法重刑会对国家治理带来伤害,力图减弱苛政的影响,通过要求官员率先道德垂范和行使怀柔手段来缓解社会矛盾。可以说,外表严苛的秦始皇在行政中事实上秉承了吕不韦时期的某些“任善”措施。
此一阶段的秦简中屡见地方官员推行德政的记录。《里耶秦简》9—2283是一份洞庭郡征发徭役的文书,其中提到征发徭役时“必先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急事不可留,乃兴(民)徭”,这是因为“田时也,不欲兴黔首”[15]85。从这封文书可见洞庭郡守对民力的爱惜。《里耶秦简》8—1796载“都乡黔首毋不平苦者”[16],简9—1305载“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15]49,均展示了迁陵县官员对百姓冤情疾苦、医药用度的关心。《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二十二,有一份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推举卒史的文书,其中肯定了该官员具有“廉洁敦悫”“平端”[17]111的道德品质。
秦始皇在统治中一方面主张“任善”,另一方面又强调“任法”,两种相悖的理念同时应用于政治实践中,本身会造成一种抵牾。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要求地方官员在行政时慈爱百姓、宽容忠信。而同样在睡虎地秦简《语书》中,南郡守腾却以严厉的措辞,指示南郡各县、道啬夫要敢于使用法令。“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殹(也)。”[13]12-15郡守腾所秉行的,是用强力行政手段改变原楚地民俗,消除南郡地区百姓对秦的抵抗,稳定统治秩序。工藤元男指出,睡虎地秦简有着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容忍基层习俗的倾向,另一种是批评和禁止地方习俗,使秦国走向一元化统治体制的倾向。[18]这一观察可谓精当。
睡虎地秦简所体现的这种矛盾是遍布于整个秦国社会的。秦上层统治者试图弥缝二者,一方面要求秦国官吏实行任法重刑的苛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为善爱民。在实际行政中,官吏们往往不知所依,最后变成按个人的理解裁量。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案例十八记载:秦攸县县令广隼在判案时为击盗时败北逃亡的大批百姓减罪,并将这一决定上书秦始皇。但复核案情的南郡卒史攸却认为县令是“绎(释)纵罪人”,维持对百姓的死刑原判,并将县令广隼免官判刑。[17]104县令广隼为百姓减罪的行为,体现了其对百姓遭遇的同情;将判决上书始皇,也反映县令广隼相信秦始皇是具有德政理念的君主。卒史攸的判决则反映了一部分秦国官员任法重刑的倾向。张家山汉简的这一案例说明秦国地方官吏在对任法与德政进行选择时存在分歧,而分歧本身又会削弱官僚集团的团结与凝聚力。
任法与德政的矛盾,甚至反映在皇帝自己身上。根据湖南益阳兔子山所出秦二世即位文告,秦二世曾宣称要实行德政,“尽为解除流罪”,“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19]。而事实上的秦二世时期,“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赋敛愈重,戍徭无已”[4]2553。迫于眼前的统治压力,秦国统治集团无法调和任法和德政的矛盾,最终德政思想让位于任法重刑的实践。大部分秦国官吏也只能服从于任法的方针,如秦范阳令徐公,“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4]2574,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10]2327,引发反秦的浪潮。
综上,秦自商鞅变法开始,经历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吕不韦执政时期以迄秦始皇、秦二世,其统治理念和政治路线是不断变化的,“法治”和“德治”交错杂糅。如邢义田先生所言,“秦王朝的统治者至少在理论或理想上,或许不像汉人描绘的那样残苛失德,暴虐无度。他们其实和汉儒一样,也要求官吏都该具有忠孝仁爱节义公正一类基本道德”[20]。只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无法克服,秦自始皇以后又以任法重刑为主要施政方针,将“德政”“任善”等理念与严刑峻法相融合的期望最终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