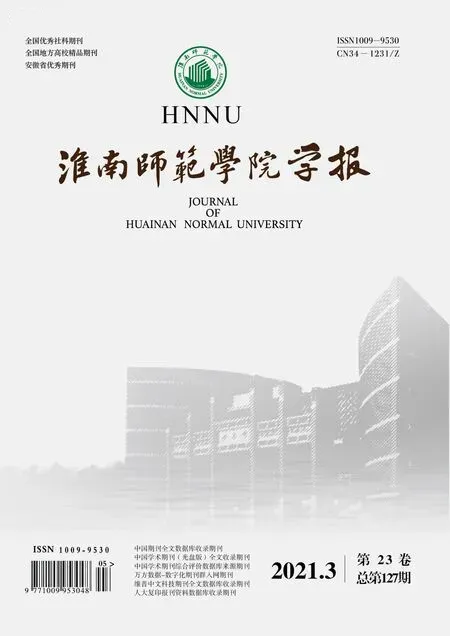牛汉早期诗歌的草原书写
乔军豫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牛汉在青年时代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有着自觉的命运选择与责任担当意识。其在1942年创作了长诗《鄂尔多斯草原》(以下简称《草原》)《草原牧歌》,精心营建独一无二的草原世界,铸就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关于草原书写的壮丽诗篇。草原是牛汉诗歌生成的文学地理空间和诗歌想象生发的起点,不仅代表他的精神家园,而且也是当时苦难中国的写照,寄予着诗人的审美理想、现实关怀和革命愿景。因此,《草原》既是诗人送给时代的一份圣礼,又是献给祖国的一首衷曲。令人惊奇的是,诗人并没有亲历过草原,却创建了散发深沉魅力的草原世界,委实值得一番探求。目前诗学界对牛汉早期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七月诗派的关系上,而关于他的草原书写涉及极少。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牛汉早期诗歌中的草原世界出发,厘清他草原书写的脉络,重点探讨草原书写的“启蒙者”、草原的具体呈现形态以及草原书写背后蕴含的情怀。
一、草原书写的“启蒙者”
牛汉深受民族文化和故乡的影响,基于草原进行创作。在诗人看来,草原这片热土,让他探索到诗歌创作上的异质性。草原书写呈现出诗人立足故乡、深情凝望历史、放眼革命前景的创作态度或写作方式。诗人视草原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他的祖先曾生活在草原,若不是家族南迁,他会一直生活在那里。因此,他对草原牧民怀有极深的感情,对民族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他诗歌描写的对象有鲜明的民族基调,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表现出蒙古族人民特有的生活和斗争。草原特有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信仰、社会背景、文化气息等,影响了诗人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和审美价值取向,将诗人带向一条别致的诗歌创作之路。诗歌中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种不可置换的特质,是牛汉创作的一种标志,从而使他在众多的诗人中脱颖而出,他的诗歌具有了显而易见的辨识度。草原书写使诗歌从内容、形式、意义上进行开拓和延展,从视觉和听觉上尽情展示草原独特的风光和愿景。与众不同的地域风情和民族风格不仅激起牛汉创作的想象力,以一种诗意感悟、寄予生命情怀的方式表现外在世界,在拓宽诗歌审美意蕴的同时,还能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价值观念等方面提供文化基因。牛汉挚爱的这片地域以及地域上的人们,给了他心灵的慰藉和温暖,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和启迪。牛汉的诗歌是在民族文化土壤和家乡生活土地上萌生、成长、结果的。进一步而言,诗人所在的地域与地域上承载的民族文化让草原书写自带异质性。
牛汉系蒙古族人,出生于山西定襄下西关村。定襄地处晋北,地广人稀,距离内蒙古不算远,地理特征与内蒙古相似,适合放牧。外地人到了定襄下西关一带,他们一定很是惊讶,满目都是跑动的成群的牛羊,很难见到本地人。牛汉在这样的坏境中成长并自得其乐,曾庆幸地回忆道:“由于村里人一代一代都跟牛打交道,家家都有几把祖传的宰牛尖刀。”[1](P6)这里所说的“尖刀”特指蒙古尖刀,是蒙古族身份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惟力是恃,惟力是爱,勇力出众者,众人敬重之”[2]。“勇力出众”“众人敬重”,当然少不了有蒙古尖刀的功劳。作为蒙古族后裔,牛汉民族身份的认同感极强,以拥有粗犷豪迈的民族血统而自豪。诗人自小崇拜充满血性的力量,对孔武有力的英雄怀有十足的敬意。他五六岁就练习摔跤。定襄摔跤的历史悠久,当地人称之为“挠羊”“跌对”,上场交手采用搭、拉、掼、拧、绊等技艺,如龙虎争斗,场面激烈紧张、威武雄壮。诗人对此从小就耳濡目染,逐渐养成好强、自尊、难以驯服的个性。幼年的生活赐予牛汉丰厚的创作资源,对其后来的诗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牛汉整个的童年在家乡度过,像那里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帮助家里大人做农活、放牧。他家养着一群牛羊,出圈、归圈、照顾小羊羔、小牛犊等活计他都参与其中。放牧途中,诗人接受大自然的润泽和洗礼,开阔的草甸、塞外的烈风、山间的大树、谷底的野花、悦耳的牧羊曲,等等,这些都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赋予他诗意的种子,为他性格的塑造和诗歌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他后来谈及《草原》的创作经验时所言:“诗里出现的情景,都萌发于我的童年与少年生活。”[3](P92)牛汉一生眷恋故土,虽然随着他外出求学、革命渐行渐远,但他并没有真正走出故乡的怀抱,他视那里为生命的发源头和诗歌创作的摇篮。有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他的诗常常有着自己的故乡”[4](P9)。牛汉来自蒙古族家庭,高祖父“忙兀特尔”是蒙古人,曾祖父长期在蒙古人聚集地经商,祖父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民族自决”事业,父亲这支仍有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的亲人,母亲的外祖父家也属于蒙古族。家里陈设着黄牛角、毡子和刻着花纹和图案的铜佛等蒙古人特有的物件,一直保留来自草原的印记。他的思想观念自小就受到整个蒙古族家庭的感染和熏陶,打下蒙古族深刻的烙印。家庭的生活习性和传统文化,对牛汉的一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P10-11)。牛汉的生命植下蒙古族桀骜不驯的反叛因子,从其坚韧不拔硬朗刚烈的性格中可见一斑。顽强不屈的生命意识伴随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在诗人看来,漫山遍野触目皆是不屈的生命:“一条河/一弯弓背的山岗/一道黄色的路/鼓起生命的弦”(《走向山野》)。牛汉的生命之根牢牢扎在蒙古族血统里,在此萌发丰沛的诗情诗意。
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国处于黑暗与光明、民族的苦难和民族的希望共存的时代。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牛汉此时已十八岁,投奔共产党的队伍上前线打仗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所在的学校把他管制起来连上街游行的机会都给剥夺了。诗人的情感异常压抑苦闷,他开始怀念家乡、英勇骁战的祖先以及历史上那些伟岸铮铮的生命。《草原》《草原牧歌》作为特种方式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可以这样说,牛汉诗歌的现实起点是时代,创作的逻辑起点是草原[6]。正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牛汉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对时代的关注则集中表现为强烈的责任心和拯救意识——拯救苦难、拯救现状、拯救整个民族”[7]。面对国破人亡的惨景,诗人不能等闲视之,他革命的激情在爆发,血脉在喷张,将目标聚焦草原。这与1940年代中国饱受外辱和内战的大环境密切相关。时代风云的裹挟与催逼促使牛汉反思自身和家国的命运,启发他开始寻求自身和民族自由解放的道路。牛汉将满腔的热血倾注草原,发出生命抗争的呐喊,找到了革命的另一种方式——一个进步的革命青年用笔倾诉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鄙视及对光明前景的探索。草原给了诗人精神的动力和革命的信心,正如牛汉所言:“在我稚弱而苦闷的心灵上,蒙古草原似乎冥冥之中能给我以雄浑的力量,成为诱惑力极强的梦境。”[8](P25)
牛汉对草原意蕴的发掘还有一部分来自间接的资源,除了童年时期家里人的口耳相传之外,另一个则是他个人的阅读经验了。俄罗斯文艺作品的阅读经验是“肥沃”、丰富“草原”的艺术养料。牛汉在甘肃天水国立五中高中部求学期间对俄罗斯的诗歌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后来大学读的是俄语专业,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艺作品,尤其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诗歌,在视觉层面产生的部分心理体验与这些经历过苦难折磨和悲剧人生历练的俄罗斯诗人的忧患感一脉相通。再者,俄罗斯的地貌和人文环境与北中国的草原类似,幅员辽阔而显荒凉,实行农奴制度。北中国草原的牧民和俄罗斯的农民一样饱受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悲怆凄惨的日子。对此,诗人印象深刻,同情、忧愤、抗争的心理潜滋暗长,并将这种心理“平移”到草原,追随俄罗斯文艺传统进行细致的情感释放。
二、草原书写呈现的形态
牛汉笔下的草原是现象中的世界。一直到1986年,之前牛汉都没有真正涉足过鄂尔多斯草原。因此,缺少实地考察的草原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并没有营造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地方,与纯粹的浪漫的想象有别,而是根据诗人的意愿,将黑暗的现实与革命的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虚构和现实并存。牛汉建构的审美空间是真实的,用自己宏阔的想象力将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场景联接,使之可感可信。草原书写基于诗人心理体验和感悟所发掘出来的细节,既符合历史或现实逻辑又符合情感逻辑,从而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诗人从自己祖国的草原找到美学意义上的书写对象和革命的寄托。换言之,草原不仅是诗人精神的故乡,而且也是灾难深重的中国的缩影。草原哺育了诗人的心灵,支撑着他人生的信念,指引着他革命的方向。惟其如此,牛汉有了对草原美好的遐想的空间。
牛汉将恢弘的想象定格于辽阔博大的草原,构建了他独特的诗歌审美长廊,呈现出草原的别致形态。在诗人的巧妙构思里,一开始,在为远祖们的草原文明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清醒的觉察到当下的危机和悲哀。广袤的草原像老牧人干枯杂乱的须发,痉挛地飘飞着,受旱情损害,“生命是干涸的沙窝”(《草原》)。牛汉描绘了一个荒凉的死气沉沉的世界,道出了心中的郁闷与愤激。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牧民们似乎觉醒了,奋起自卫投入了火热的战斗,“闪着血红的光芒”(《草原》),经受战火的冶炼。诗人把牧民比作沙土里滋长的红柳,顿时仿佛发现了生命之光和希望之路,情绪由低沉缓慢转向慷慨激扬。牛汉认为“远古的悲泣停止了”(《草原》),牧民的血液开始滚动了,鄂尔多斯草原成为了“绿色的生命的乳汁/绿色的生活的海/绿色的战斗的旗子”(《草原》)。整个草原在诗人的眼中复活了,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由悲歌到颂歌,从低缓变高昂,诗里的情感起伏显示出时代的变化。
牛汉创造了草原世界,没有斧凿的痕迹,显得那么自然。如同田野里蔓生的植物恣意舒展和生长的触须,直接触碰着我们心灵深处柔软微妙的部分。因为纯粹、自然,所以闪烁着诗意的光辉。牛汉的创作激情和才华在《草原》里尽显。《草原》虽然是诗人构筑的想象的世界,但是却源自他最初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因此,这首诗具有了自然原始的艺术风格,表现了牛汉真挚的生命情感以及对个人命运的升华与超越。诗人歌唱草原礼赞生命,不再是一个离开家园漂泊远方的游子,更像长期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人民之中的一员。悲哀着“被太阳摒弃在寒冷的北回归线上”的草原,感叹着被冻结“静静地躺在草原上”的黄河。牛汉把草原比作母亲,当母亲哀叹自责由于自身的贫乏给宠爱着的“孩子们”——牧民——造成的局限时,诗人理解草原母亲的无奈之处和良苦用心,并行动起来,“陪伴着”她“一起悲歌”(《草原》)。牛汉安慰她不要一味责备自己没有让现在的“孩子们”过上自由、富裕的生活,那最初的哺育也曾历尽千辛万苦,人们应当感恩和牢记,“草原的绿色/也曾哺育过/人类饥饿的生命”(《草原》)。鄂尔多斯草原哺育人类的历史不容置疑,成就马背上这个强悍的民族更令人骄傲。
草原呈现一部蒙古族及其人民的命运史。远古草原辉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牛汉笔端当下的草原呈现出一派灰暗的色彩,“没有草/没有花/没有一滴水/没有一个脚印”(《草原》)。40年代的草原如同一位昔日叱咤风云而如今却步入暮年的英雄,飒爽的英姿宏大壮观的气象已消失殆尽。绿草、野花、流水、脚印这些草原上标志性的生命哪里去了?荒凉的景象惨不忍睹,令人深思。诗人心情低落可能导致山河失色,极易让人联想到草原的荒凉意味:以人类为主体的草原文化日渐衰微、蒙古族精神的支柱即抗争意识日趋丧失。牛汉在写景状物上带有浓厚的悲情色调,“那困厄的扎在草原的蒙古包”诉说着寂寞,彰显蒙古族人民的困苦与危难,“他们世世代代/牧放着牛羊/而他们自己也是王爷们的牛羊/被剪去温暖的毛/被挤干甜蜜的奶”,“那些像沙漠上的百合花的女郎/那些像地鼠一样可怜的小孩子/那些像老骆驼一样瘦弱的女人”(《草原》),在悲哀的岁月里挣扎,承担着生活的沉重和痛苦,心灵被“刻满了深深的血痕”。
诗人谛听了草原上飘荡的悲歌,体会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同胞的苦难与困厄,指明了改变草原现状和牧民们命运的希望所在,塑造了“旅人”这一光辉形象。“旅人”给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牧民们带来了革命的火种和真理。只有起来反抗旧势力推翻旧制度,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活路。牧民们革命的热情高涨,“棕色的皮肤上/黑色的血脉/高高地滚起/反抗的浪”(《草原》)。整个草原沸腾起来,牧民们的热血“像解冻的热流”,化为巨大的力量,冲出冰冷的“皮肤表层”,突破“冰冷的生活的牢狱”,迎接血与火的战斗。诗人眼中的草原获得新生,“今天/牧民们在战斗/生活的河流/解冻了,澄清了/澄清得能照清鄂尔多斯草原/新的生命的图像/澄清得能照清他们自己”(《草原》)。牛汉深受鼓舞,作为一个草原之子,积极响应战斗的号召,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投身革命,就像“无数火星一样的旅人/在燃烧,在奔走”(《草原》)。牛汉面对草原令人欣喜的转机,英雄主义豪情万丈,一边战斗,一边高歌,期待“从我的歌声里/喷出草原复活的笑/扬起新的生命力/我要让这歌声/扬得更高,更响”(《草原》)。“旅人”是草原名副其实的救星,让陷入绝境的草原迎来了新生。牧民们迎接着快马奔来的旅人,心中升腾起希望,与旅人一起围靠在火堆旁。“旅人/在火堆旁/烤着冻紫的手/喝一杯奶茶”(《草原》)。 牧民们热情地招呼着旅人,旅人也道出暖心的话语,让牧民们感受到这份从远方而来的温情。“白发连着白须/静静地呷着奶茶”的老牧人喜笑颜开,心中的阴霾已散开。旅人勾留一会喝了杯奶茶,“又钻进那满天遍野的风沙中/默默地走了”,“就向路和不是路的路继续走去”,走向“浓重的夜雾里”“深邃的灌木丛里”“野狼的悲嗥声里”(《草原》)。旅人选择勇敢挺进的姿态,奋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代表着一种光明的前途。觉醒后的牧民们坚信,“明天/草原上会滚来一轮火红的太阳”(《草原》)。旅人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到来让死寂悲观的草原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难怪诗人将旅人尊称为“赶着太阳的车夫”。
《草原》是一曲深情的生命进行曲、也是一首希望进行曲。诗人立于民族之根,发挥联想和想象之力,抒发对草原的神往和眷恋。他仿佛亲吻着生命之土,在精神圣地上引吭高歌。绿色的鄂尔多斯草原是一片生命的海洋,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原野。那夺目的翠绿,那悠长响彻寰宇的一阵阵的音浪,令诗人赞叹不已,“我歌唱着/唱出了/从远古便沉淀在草原里的生命的绿色”(《草原》)。牛汉似乎置身远古的草原,遥望远方的翠绿滚滚奔流,不经分辨就能听出“牧笛吹出的原始的粗犷的歌音”,还有马蹄卷来的牧歌,羊、骆驼、牧狗的铃音。这些都是鄂尔多斯大草原的杰作。更使人振奋的是,“赶着太阳的车夫”唤醒鄂尔多斯大草原的命运的主宰者——沉睡的牧民,他们开始为幸福的未来而奋起斗争。草原迎来了光明和希望,承载着憧憬与理想。
三、草原书写蕴含的情怀
牛汉致力于草原书写,倾注了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爱。他认为:“人与大自然本来有着许多相似的命运与习性。”[8](P68)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存在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诗歌在二者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牛汉全身心融入大自然,将自己的爱贯注其中,与其建立深情厚谊。大自然被赋予诗人生命的体温和真实的感受,诗意便从中源源不断迸发出来,营造了牛汉早期诗歌的草原世界。对大自然的密切关注,对草原及草原上生命的热爱是蒙古族的一种优秀的品质。草原上有迷人的景色,蒙古族人民置身其中,与草原上的生命和谐相处,长期以来就养成了珍爱生命的习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任何幼小的生命都是被关注被爱护的对象,诸如他们对小羊羔、小马驹、小牛犊怜爱有加;在他们的生命哲学里,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珍爱,甚至对凶残的草原狼——他们的敌人——也有一种天然的仁爱之心;蒙古族有世代相传的狩猎规矩,适度捕杀,从不滥捕滥杀,还经常为保持生物链的长期存在而放生,忌捕猎杀带仔、怀胎、睡眠的动物;牧人手中的皮鞭也不是用来征服牲畜的,而只是虚晃一下用来惩罚或者震慑的。蒙古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上,按自然规律做事,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从而做到与自然平等友爱、共生同存。这一民族格外珍视草原这个生命的家园,当牧场和牲畜的供求出现矛盾时,牧草和水源地满足不了牲畜的需求时,就会自觉迁徙至水草丰厚的地方,形成了保护草原的游牧制度,有效地维持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平衡。崇尚大自然,珍惜大自然,爱护生态环境;敬畏生命,热爱生命,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民族思维方式和心理追求。元朝统一后,蒙古族大量的人口向内地迁徙,即使他们离开了草原,离开了蒙古族聚焦的中心,如同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但他们根深蒂固的民族信仰与民族性格依然深深影响着后代,依然教化着诗人牛汉。
草原书写表达了诗人不惧战斗、追求革命的英雄主义豪情。蒙古族以勇敢、武威、强悍著称,北方冰冻天寒、狂风暴雪的恶劣天气和严酷贫乏的现实生活以及居无定所的游牧制度,使这个民族养成了勇毅无畏的性格和“金戈铁马”的精神气质,形成了崇拜英雄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力、勇、义”的社会风尚。在蒙古族的生命信念里,氤氲着这样一种勇气和胆识,大丈夫应战死于疆场,一腔热血沃大地,而耻于病床终老。这一民族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毫无疑问会反映到牛汉身上,他崇拜蒙古族历史上的英雄,诸如成吉思汗等。这些英雄为了既定的目标一往无前浴血奋战,将生死置之度外,最终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牛汉为他们伟岸的人格、超人的力量、崇高的英雄主义气概所折服,将英雄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来进一步追求。诗人为祖国和人民而勇敢歌唱,唱响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为自由与正义而不屈斗争,体现出民族的风骨和精神特质。牛汉热爱阅读草原文学的书籍,那些歌颂反抗邪恶、征服敌人、以赞美勇敢和力量为传统主题的读物更是让诗人爱不释手,从中深受感染和教育。大学时期参加革命的经历深化了草原书的内容,入狱遭受的打击非但没有阻止诗人对革命的追求,相反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生存与精神上双重的紧迫感与反抗意识,激励他抗战救国、谋求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信心,启发他在诗歌中构建草原世界,绘制草原上革命的画卷和蓝图。
草原书写呈现了牛汉自由独自阳刚的精神之美。诗人以蒙古族身份为荣,借此强调他的民族血统和性格特征:“我的老祖先能征善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的生涯,他们总骑在马上向远方奔跑……我的这种不愿意被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或小圈子里的难以驯服的性格,可能有民族传统的基因。”[8](P3-4)蒙古族人酷爱自由,性格中蕴含着顽强不屈奋力抗争的成分,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作代价来换取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自由、独立。牛汉的精神底色里保持着这种民族性格,不断为民族也包括个人在内的自由独立而战。这更深一步影响到他的诗歌审美观,“我的诗总在躁动,总在奔跑,总想游牧到水草丰美的地方”[8](P4)诗人不愿将自己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境地,那样视野就会被蒙蔽,思想就会受到约束,身心得不到舒展和自由,陷入困顿之中无法发挥诗思。他需要以“游牧”和“梦游”的状态去寻找诗意,不断开拓诗的新境界。诗思驻足在鄂尔多斯草原达成了诗意书写。
蒙古族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赋予其骁勇善战自由奔放的性格。牛汉属于蒙古族中的一员,喜欢自由独立。迫切希望自己能像草原一样拥有宽阔博大的情怀,不被现实的窘况所羁绊。从牛汉的草原书写中可以看出,牧民们怀念祖先自由的生活,他们曾为这片土地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过。诗人缅怀历史,激励自己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继续战斗。牛汉从草原汲取革命的勇气和力量,诗歌中的情景在他的生命里孕育了许多年,从生命内部和灵魂深处点燃出艺术火光,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化为书写的动力,全身心投入这次寻根之旅和革命之旅,让草原“发着被开垦的芳香的气息”(《草原》)。同时,牛汉也在此呈现出自由独立积极进取的精神之美。
四、结语
牛汉的草原书写既是一场寻根之旅,又是一场革命之旅,融合了诗人青春的梦幻和革命的豪情壮志。在诗人的笔下,鄂尔多斯草原最终以熠熠的绿色展现在诗坛,成为哺育北中国“绿色的生命的乳汁”,成为牧民们“绿色的生活的海”,成为一面“绿色的战斗的旗子”(《草原》)。绿色含有激情、自由、希望、生机,昭示牛汉的精神历程和革命历程。牛汉作为“草原之子”,草原书写是其应有命题,他在远祖生活过的草原那里创造了自己艺术生命、诗歌写作、革命起源的“神话”,确定了自己历史传承、民族传承、精神皈依的原点。诗人以激荡昂扬的姿态通过草原书写深切关怀家国的前途命运,展望民族的未来新生,发动别种形式的革命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