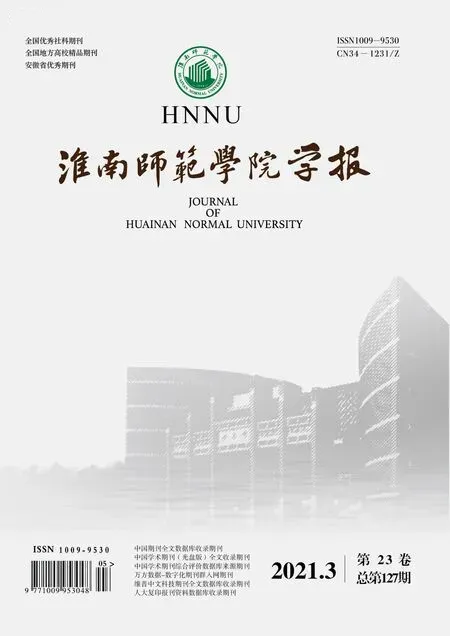肉体乌托邦语境下庄子身体哲学的现代价值
金 洁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柏拉图主义开创了西方哲学抑身扬心的传统。柏拉图不仅将人分割成身体(欲望、冲动、感性)和精神(意识、灵魂、理性)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还在《佩德罗篇》中用著名的“灵魂马车”之喻阐释了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灵魂优于也高于身体。从柏拉图至黑格尔,这一身心二元、扬心抑身的哲学传统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精神谱系。精神(心)不仅登上了主体之位,还在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的推动下登峰造极,制造了现代社会的主体神话。思维(认知)主体成了万事万物的奠基者,现代社会中的逻各斯和上帝的替代物,以及一切知识、道德和价值的立法者和终审者。身体则始终处于被忽视、贬损和压抑的状态。
尼采的身体革命引发了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身体转向和持续的身体研究热潮,长期以来被遮蔽的身体从精神、道德伦理和理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得到全新的肯定和阐释。然而,随着消费主义的全球蔓延,身体革命逐渐走向一场以身体为名义的肉体狂欢,刚刚解放了的身体面临着新一轮“肉体乌托邦”的践踏和宰制,“在理论宽容之下的肉体乌托邦,任由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实际上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这和政治与革命的专制一样可怕。 ”[1](P5)
身体的解放任重而道远。作为一个兼具物质性和文化建构性的存在,身体的巨大可能性空间仍然有待后来者发掘,身体主体的建构需要更多的研究视角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参与。
一、身体的回归与狂欢
后现代主义以解构柏拉图主义的相同的逻辑拆解了笛卡尔式的精神主体。随着精神主体的“退隐”和“死亡”,西方哲学中沉默了两千多年的身体踏上了回归之旅。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置于显著位置的哲学家。“一切从身体出发”“我全是肉体,其他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指肉体方面的某物而言罢了。”[2](P31)尼采以其革命性的言论引发了20世纪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身体转向。在尼采依“身体”而筑起的哲学图景中,世界是具有身体性的价值世界,身体是解释世界的终极之因,万事万物遭受身体的检测。在尼采这里,身体的主体身份被初步确立,长期被贬低、压抑、侮辱的身体开始展示主体的尊严,身体及其内部的力可以对世界作出起源性的解释和评估,精神则成为身体的产物。
尼采之后,以梅洛-庞蒂、福柯和德勒兹等为代表的西方哲人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身体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对身体主体的建构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20世纪80年代,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1983)、唐·约翰逊(Don Johnson)的《身体》(1983)、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的《身体与社会》(1984)、约翰·奥尼尔(John O’ Neill)的《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1985)和《交流的身体》(1989)等一批直接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力作集中问世,标志着身体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无不将身体纳入自身的研究范围,形成了身体现象学、身体美学、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人类学和身体文化学等一系列学科形态。至此,身体不仅完成了其全面的回归之旅,还迎来了20世纪末一场盛大的身体狂欢。
随着消费主义在全球蔓延,“我消费故我在”取代了“我思故我在”,身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身体,尤其是其外在显现成为自我的象征。由于“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表征与身体感觉,而不是出身门第、政治立场、信仰归属、职业特征等,来确立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3]消费社会中的广告、杂志、网络、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无不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年轻、美丽、悦人心意而又充满欲望的身体形象。消费文化将各种身体产业对身体的包装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画上等号,因为“在消费文化中,人们宣称身体是快乐的载体:它悦人心意而又充满欲望,真真切切的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美丽、结实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换价值。 ”[4](P331-332)
两千多年来一直被遮蔽和压抑的身体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身体的能动性与丰富性不见了,身体窄化成肉体,发端于尼采的身体革命正导向一场肉体的盛大狂欢。身体看似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以及前所未有的呵护与标举,然而,身体无限尊荣背后的代价是身体如同其他商品一样也被纳入到消费文化的掌控中,物化成符号性消费品。这场肉体的狂欢以人的“以身为殉”为代价,在消费社会滋生出的对身体的霸权与控制下,人往往不由己地做出“为身体而身体”的事情。当身体从存在的手段变成了存在的目的,身体革命的解放意义恐怕已难再寻,肉体的无限尊荣不过是一场乌托邦的幻象。
二、庄子哲学的身体主体之思
现代性解放话语中的身体似乎又包含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力量。从思维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的身体面临着新一轮的践踏。身体何时才能真正属于我们?无论是思维主体对身体的禁锢还是消费文化对身体的物化与宰化,究其根本原因,西方身体哲学的身体始终没有完全脱离西方意识哲学的窠臼,受“身心二元论”的影响,身体始终是作为物理对象的一种“异己”的存在。
面对身体带给我们的新的困惑与迷思,回到原初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回到“前身体”时代,探讨一种亲身性的“本己性”身体作为时代需要呼之欲出。庄子身体哲学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话语体系都与西方身体哲学迥然异趣,就身体主体的建构展开中西方哲学的交流与对话有助于拓展身体的场域,促进身体的真正解放。
(一)以气构身的身体观
中国传统语境中同样存在类似柏拉图身心二分的前设。当屈原在《招魂》中呼唤“魂兮归来”时,身体已经与灵魂分离,成了灵魂的寓所和可以抛弃的存在。《周易》开创的“天人合一”象数思维模式虽然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身体观念,但是先秦诸子时代,无论是儒家的德性身体和礼仪身体,还是法家的刑罚身体,身体本身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身体或者是某种内在规定性的外在形态,或者是权力规训的对象。
真正对身体给予本体论关注,使身体脱离了纯粹物理性存在上升到道的高度的是庄子哲学。“以气构身”的气化身体观是庄子身体哲学“即身即道”的根本前提。
“今已为物矣,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 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也。”(《庄子·知北游》)
庄子的身体概念打破了二元论学说树立起来的身与心、人与物、外在与内在、主观与客观等等对立二项。在庄子看来,气弥漫于天地间,天和人同质,都由基本的原质气组成。万物置身在天地一气相通、流注无穷的变化状态中,由于变化而通于一体,通而与他人他物相感,从而达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境。心、气、形实际是一体三相的统一整体,身与心这一对立的二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哲学融为一体,取消彼此的对立。当身与心不再对峙时,“我”与万物融化为一,本真的身体/主体于焉呈现,此时“通天下流行于一气,故我身自可与物化,我神自可与天地宇宙和合不二,甚而,我所谓我与物,物我皆融通于一派活泼泼的自然生机自在显发之中。”[5]
当本真的身体呈现时,“形”与“心”均统摄在“身体”之下,身体作为真正的主体介入世界之中,既是存在和实践的主体,也是世界意义开显的场所。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形上道论”,认为世界由无目的性、无意识性的“道”所产生。相比于老子的“道”,庄子的“道”虽然很深远,却又是实在性的、存在性的。人处在无所不包的“道”中,与大化同流,身体就是世界意义生成的本源,身体与道同一,人与身体的关系也就是人与道的关系。身体主体与身体客体整合成了一现象学整体,身体就是一种最亲切体己的存在。
(二)身体介入世界的方式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对思维主体进行拆解与破除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两千多年前庄子早已经觉察到思维主体的可疑,提出了思维主体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庄子与蝴蝶”身份混同背后反映的正是庄子对“思维主体”的怀疑——思维主体真的可以对世界作客观认识并且把握世界的真相吗?
庄、惠著名的“濠梁之辩”进一步反映了庄子对思维主体的勘破。“濠梁之辩”很难从论辩的角度判定高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庄惠之争就是古与今之争,是两种主体以及两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之间的争论。惠子的“知”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以逻辑概念、命题与判断的方式对世界进行主体化整理,是现代认知主体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般思维方式。庄子的“知”则是一种“前理论”的“体知”。作为“本己”性存在的身体是人最直接的把握对象,也是人介入世界的方式。由于身与道合一的体证关系,人对世界的认识——“以道观之”实际就是“以身体观之”。
庄子对世俗知识和思维主体持怀疑和漠视的态度,推崇没有“认知意”的“真知”或“体知”。“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思维主体总是“拘于虚”“笃于时”“受于教”,有限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和僵化的文化环境决定了思维主体的有限性。又由于受“成心”所左右,思维主体表现出自我中心与排他性,所以一般的认知活动往往仅是主观是非的争论,很难对外在事物作客观的认识。唯有“真知”才能透过时空的拘囚,照见事物的本真。“真知”重主体内在的感受,是一种内观之知,“有其内在的独特性、特殊性和超言说性。它不靠实验或证明去获取,而透过自觉与自证去把握。”[6](P232)因为只有体道的人才会有“真知”,所以“真知”又是一种对道的“体知”,是身体主体“以身体观之”而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体知”不以逻辑和对象化的方式对世界进行分割,而是将身体直接介入世界,形成特定的情境,产生一种超越概念知识的智慧。与“认知”相比,“体知”不是建立在分离的基础上,它强调“通”,身与心贯通,物与我贯通。
“濠梁之辩”中,庄子以“以身体观之”的方式打破了人与鱼主客对立的格局,还原了人与世界的始源关系,展现了一种和惠子的“认知”并不一样“体知”,“因为无认知意,所以它呈现的模态是气的感通,是内在于存在界的讯息的流通,它是超越认知主体与情欲主体的一种全体之敞开。”[7]从“认知”到“体知”是一种回溯到前知识状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主体需要超越一般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思辨,需要不被概念体系化的思路禁锢,因此,庄子的“以身体观之”实际内蕴了“吾丧我”的修身工夫。
(三)身体主体的正成
在世的有形之躯由于受到心的主宰,总是被各种功利、成见和知识所翳蔽,虽然成了知识主体,却成为攫取知识的工具,越来越脱离精神自由,丧失了生存者的诗性情怀。因此,认知的一般过程恰恰也是对浑然一体的道的破坏过程。庄子哲学中身体主体的正成与经验知识无关,而是反身向内,通过内在生命的修养,使自然身体重返气机流行之境,层层剥落自然身体之上的羁绊与束缚。这一过程即“吾丧我”。
(颜成子游)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庄子·齐物论》)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
《齐物论》的开篇庄子就假借南郭子綦和颜成子游的对话,说出了“吾丧我”的境界。郭象《庄子注》解释道:“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8](P45)按陈鼓应先生的理解,“‘丧我’ 的‘我’ ,指偏执的小我。‘吾’ ,指真我。由‘丧我’ 而达到忘我、臻于万物一体的境界。”[9](P45)小我沉溺在功利世界、实用知识中,束缚在物我对立、身心纠缠中,因此丧小我,忘小我,才能成就大我。
“吾丧我”在《大宗师》中对应的修身方法就是“坐忘”。“忘”在庄子哲学里是一个主动性的行为,也是一种超越的方法。主体可以“忘年”,“忘形”,“忘利”,“忘我”,“两忘而化其道”,通过“忘”而融合在“道”中,从而不再拘泥于“小我”的形躯与情感。
按照劳思光先生的说法,“坐忘”意味着忘掉两种“我”,一个是“躯体我”,另一个是“认知我”[10](P214)。
“认知我”是以惠子为代表的思维主体。“认知我”以追逐那个最终的客观性为中心,用理性的判断、推理和逻辑代替了浑然一气的感通。鱼究竟乐不乐,其实从“认知我”的角度永远找不到答案,即使今天先进的生物学也无法彻底弄清鱼的情感和心理世界。而当我们舍弃“认知我”,忘掉“知”,进入前知识状态时,气化流行成为世界的本相。世界的整全、人与世界的感通从遮蔽走向澄明,在这种“以天合天”的境界中,另一种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使得万物如其所是地涌现。此时,主体反倒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躯体我”和“认知我”一样,都属于“吾丧我”中的“小我”。忘掉“躯体我”关键在于“支离”。“保身”是庄子追求的人生目标,一定条件下,只有通过对“形”和“德”的“支离”才能达到“保身”的目的。“夫支离者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乎!”(《庄子·人间世》)“支离其形”意在“忘形”,“支离其德”意在忘德,不为统治者宣扬的虚伪的道德所束缚。除去自然之身体上一切的外在价值,超越统治者所厘定的道德罗网,保证主体的自适与自由。庄子在《德充符》这一篇中描写了以申屠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为代表的很多身体存在残缺或长相怪异的人物。这些人尽管身体形式异于常人,但是,庄子认为他们形体的丑陋甚至扭曲并不能影响生命的本真意义。他们不废不弃,追求形体之外更高价值的东西,重视整体的人格生命,“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反而在崇高的自然生命中流露出一种吸引人的精神力量。
庄子的“以身体观之”将身体的修持和对世界的认识结合在一起,以“坐忘”的方式还原人与世界的始源关系,以掏空主体性而实现了主体性的完全敞开。
三、重释庄子身体主体——传统对时代问题的回应
“我们有身体,但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我们也是身体。”[11](P61)“身体”不仅既是一切人生问题产生的终极之因,也是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终极之方。在造成人生困境的众多因素中,“身患”是根本大患,认识身体就是认识世界。
相较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有关“身体”的论述极其丰富、深刻,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身体性”哲学。“这种‘身体性’ 表现为中国古人一切哲学意味的思考无不与身体相关,无不围绕着身体来进行,还表现为从身体出发而非从意识出发,中国古人才为自己构建了一种自成一体,有别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不无自觉的哲学理论系统。”[12](P3-4)中国哲人一开始就把世界的问题反躬和聚焦于身体,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意识”并非源自对世界本质的“惊奇”,而是源自对人自身处境的“忧患”。正因如此,以“身体”为元话题的西方身体哲学一进入中国哲学家的视野,便激起中国哲学家的兴趣,“正是在对这些‘身体’ 资源给予现代解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身体转向’ 。 ”[13](P13)
中西文化,因社会生活条件不同,各自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又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尤其是在哲学思想方面,因为大家都在想那最基础、最本质的问题,道理上就更有相通之处,有些地方,其类似的程度,竟可令人惊叹不已。”[14](P28)庄子哲学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在“身体”问题上都体现出一种极具前瞻性和现实批判性的时代精神,对促进身体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一种“前现代”思想,庄子“即身即道”的“身体”溢出了“身心二元”思想的局限,而是一种生命原型意义上的身体。相较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身体”,庄子直接将身体介入世界,用“以身体观之”的方式去认识和把握世界,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更具有始源性和确定性,展现了一种同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一样的消解现代思维主体的逻辑与路径。同时,在消解了思维主体后,庄子的身体的主体性依然傲然挺立,庄子身体哲学内蕴的修身途径将对世界的认识和身体的修持结合在了一起,以“吾丧我”消解物与我、身与心、内在与外在的对峙,使身体始终作为一种本己的存在,避免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身体”问题上的矫枉过正。
以“身体”为考察对象,探究庄子身体哲学的现代价值,既是摆脱西方意识哲学的研究范式,切入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全新视野,也是在传统中拨开迷思寻找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传统既属于历史,又开放而生动地处在一个常新的语境中。在当下我们所置身的文化语境中激活我们的传统,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境遇中思考我们共同遭遇的问题,让今人和古人“视域交融”,让文明传而承之,统而续之,这正是所谓“传统”的意义。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各种观念纷繁杂呈,面对有关身体的种种困惑与迷思,选择回到传统中去追问那根本性的问题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四、结语
消费社会对肉体的高扬不仅没有实现对身体的解放,还将身体置于肉体乌托邦的宰制之下。身体被展示、观看和崇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主体性。在消费逻辑的控制下,人反而越来越失去对身体的支配。当下,身体的积极性和丰富性仍然未得到全面的开发与挖掘,身体主体的重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庄子身体哲学视域下的身体作为一种最亲切体己的存在直接介入世界,这种亲身性的身体根本上克服了身体的异己存在,对于化解消费文化对身体的宰制具有重要意义。重新解读庄子的身体哲学有助于推动人的自我认识,促进人在主体性上的新觉醒和自我理解层次的跃迁。同时,展开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也有助于拓展身体讨论的场域,为重构当代身体主体提供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宝贵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