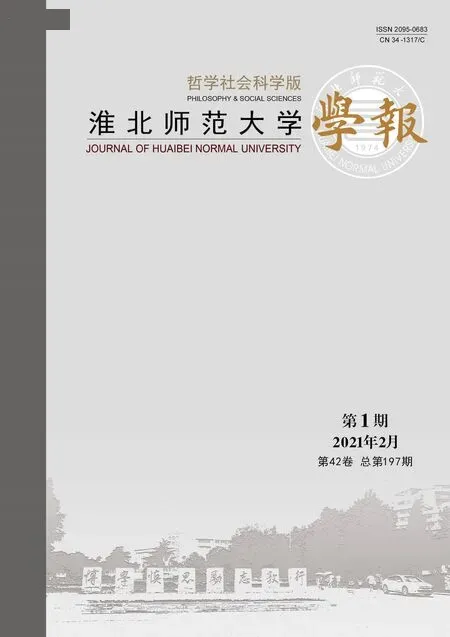潘之恒文学交游与诗学思想的互动生成
陈昌云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223300)
受心学思想影响,晚明人文复兴思潮高涨,诗坛风云激荡,声势浩大的七子派复古运动日趋式微,复古派诗人经历着时代文化思潮转型的阵痛决择,于是乎王世贞、汪道昆晚年思想新变,“末五子”“广五子”在坚守中微调。在努力寻求复古派诗学突破转向的征途中,徽州著名文人潘之恒表现突出,在与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心学代表人物、戏曲名家们的长期广泛交游中,他与时俱进、兼融众家,较好完成复古派诗学的历史转型任务,值得关注。但因其诗集《鸾啸集》《涉江诗草》主体部分留存于日本和中国台湾①郑志良:“潘之恒的《鸾啸集》和《戊己新集》均不传”(《潘之恒著述考》,《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黄仁生:“《涉江诗选》七卷,万历刻本,日本内阁文库;《鸾啸集》十八卷,万历刻本,日本尊经阁文库。”(《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岳麓书社2004年版)。张秋蝉:“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鸾啸集》十六卷,万历刻本。大陆:《涉江集选》清顺治陈允衡刻本,存北京图书馆、《漪游草》万历刻本三卷,存国家图书馆、《金昌诗草》残本,万历二十六年刻本,上海图书馆。”(博士论文《潘之恒研究》,苏州大学,2008年),学界目前对潘之恒研究多关注其戏曲、小说与散文方面成就,严重影响国人对其诗歌的认识和评价。目前仅有张秋婵博士论文《潘之恒研究》略为谈及,相对其“新安诗派”殿军的地位远远不够。少数明清文人的评价也互有抵牾,钱谦益认为“景升既倾心公安,其诗故服习汪、王,终不能有所解驳”[1]丁集下631;四库馆臣评其“始终随人作计者也”[2]2473。两者都批评他不能坚守复古诗学,过于追随时尚,没能发扬光大“新安诗派”。时人谭元春却赞其能“变”:“而景升六十有余之年,好学深思不倦,皇皇终日,若有所营者,能变故也”[3]616。认为正是“变”成就潘之恒与时俱进的诗学品质:“而予皆归其功于变。夫不变不化,则又安有景升矣”[3]616。时贤后学的褒贬不一,让人莫衷一是。事实上,通过深入考察潘之恒文学交游与诗学思想的互动生成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其诗学思想的形成过程鲜明折射七子派复古诗学转向的历史轨迹,更具备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品质,值得大力肯定。
一、广交七子派名家,深得复古诗学精髓
汪道昆、王世贞是“后七子”派主将,也是嘉万时期的文坛领袖,“海内之山人词客,望走噉名者,不东之娄东,则西之谼中”[1]丁集上441。青少年时期的潘之恒便得二人的赏识和真传,“景升少而称诗,才敏而词赡,从其乡汪司马结白榆社,又师事王弇州,其称诗弇州、太函也”[1]630-631,“自君髫时,辄以古文词受知汪伯玉、王元美、李本宁诸公,赫赫名起”[4]326。汪道昆与潘之恒祖父为至交,“潘汀州为余肺腑”[5]1436,潘之恒“总角即侍左司马伯玉先生”,“稍知埮藻,则奉司马为指南。”[6]卷七汪道昆对潘之恒“时时规以绳尺”[6]卷七,招潘之恒入丰干社和白榆社,并亲自为他保媒,统筹规划人生发展。万历三年,汪道昆正式归休,给予潘之恒精心指导和扶持,“同里汪司马道昆举白榆社,之恒以少隽与焉,由是知名”[7]卷十二。潘之恒首部诗集就被汪道昆推荐给王世贞,“当景升之荐始,其稿曰蒹葭馆”[8]卷五十一。万历十一年秋,汪道昆又携潘之恒到太仓拜访王世贞。万历十六年,潘之恒客王世贞南京官邸,多次得到王世贞面授。王世贞非常赞赏潘之恒的勤奋好学,“每见必出其所业,余因得以窥其进”[9]卷五十四,认为他是众多追随者中的“最褎然者”[8]卷五十一。
汪、王二人是后七子派复古浪潮中的擎天巨擘,受王阳明心学思想影响,他们晚年时期能够辩证看待拟古与创新之间关系。汪道昆早年“惟道古为洋洋,不乐近体”[5]518,晚年则言“夫诗,心声也。无古今,一也”[5]548、“古人先得我心,师古即师心也”[5]1737。王世贞“虽以坚持复古论的文艺思想为主,却并不摒弃其他各种有价值的理论,甚至兼收并蓄,融会贯通”[10]2003。他早年倡“性情”以正“剽窃模拟”[11]66诗病,晚年则倡导“有真我而后有真诗”[8]卷五十一。钱锺书赞之:“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12]4汪、王的热情教诲与后期融通思想,直接影响到潘之恒勇于“求新善变”品格形成,其“诗也者,心之声”[13]卷一观念更得益于早期二位老师的“师心论”和“性情观”滋润。
潘之恒通过白榆社、青溪社、南屏社等社团与李维桢、屠隆、胡应麟等同属七子派后劲的“末五子”进行交流,接触到更为开放的复古派诗学思想。李维桢是继汪、王之后的晚明文坛盟主,他于万历十二年应邀入白榆社,潘之恒由此开启与之近四十年的友谊,“潘景升才名垂五十年,与余交垂四十年”[14]卷二十三。李维桢思想开明,早在万历十三年,就提出“缘机触变,各适其宜”[14]卷九的诗歌创作论,运用辩证思维看待师古与师心问题,其变通的诗学思想必然影响潘之恒。屠隆是晚明著名诗人和戏曲家,为人豪爽,行为狂放,是明末最早提出“性灵”诗学主张的人物之一。万历十三年,屠隆应邀入徽州参加白榆社集会,潘之恒与之相识,此后二人交往不断。在屠隆影响下,潘之恒接受其“纵欲”思想,行为更加狂放,也较早领会其“性灵”诗学观。屠隆对潘之恒也十分赞赏,夸他“其为诗文也,仰而慕其古法,返而运其心灵”[4]327。
潘之恒青少年时期的交游以复古圈子为主,交往的多为复古大家和青年后劲,“其所与俱则司马长公与其二仲,其所取材则司寇元美先生,其所主则戚大将军、豫郡伯吕中秘、朱光禄、吴水部。所与往来则沈嘉则、莫廷韩、李本宁、胡元瑞、曹子念、吴翁晋之属”[15]卷十。因此他早期诗学取向以“复古”为主,“于古人而不越畔,吾之守此有年矣”[16]287,年未二十已深得复古诗学精髓,“以其余力为诗,即一言出而倾其坐人。其先有名文章家者咸心折景升,不敢与齿。景升益自翔异,进而求之古人,自风雅汉魏乐府以至盛唐,无不疑神而夺像也者,有《蒹葭馆诗》”[16]283-284。三十而立,诗坛地位已经确立,“盖司马、司寇而下,莫不衷好景升,而以为畏友矣”[15]卷十,成为“新安诗派”殿军。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与李维桢、屠隆等人的交往,潘之恒已意识到机械复古的局限:“我犹未尽我之材,未造物之境,未达变之情”[15]卷十,为他后期诗学思想的转变奠定基础。
二、与戏曲名家交流,领悟诗歌缘情属性
家道殷实、生性浪漫的潘之恒不仅喜欢结社交游,还好听歌赏曲、追欢买笑。多次漫游吴越途中,他和汤显祖、梁辰鱼、张凤翼、梅鼎祚、汤宾尹、屠隆、臧懋循等戏曲家兼诗人们斗酒赋诗、听歌选伎、狎妓品剧,在风花雪月和醉生梦死中,越发领悟“诗本性情”属性。初次游吴,他结识青年英才张凤翼。张凤翼性情洒脱,风流自任,既好诗歌,又“好度曲,为新声”[1]丁集中483,可惜其诗名却被曲名遮掩。他论诗重情意,介于复古派与性灵派诗学之间,认为“吾发于吾情而止于性,发于意而止于调。反之,我而快质之古,而合以为如是足耳”[17]卷四十五。受其影响,潘之恒亦有相近论调:“心之声犹焕于文,而况心之文,其绪于音,为流水,为行云,其何所不振耶。”[13]卷十一只是张诗更重格调,潘诗更为俗化。
潘之恒与汤显祖初识南京,“时余官留都,获与定交”[18]1193。潘之恒是《牡丹亭》最热情观众,“余十年前见此记,辄口传之”[13]卷三,“不慧抱恙一冬,五观《牡丹亭记》,觉有起色”[13]卷三,亲自排演《牡丹亭》,甚至专门撰写《情痴》一文阐释其主题和内涵。汤显祖论文持“至情观”,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18]1050。潘之恒对其“至情论”作过最贴切诠释:“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之无足怪也。”[13]卷三作为汤显祖的崇拜者和知音,潘之恒自然受其“情生诗歌”思想影响。在与戏曲家们的交游吟唱中,潘之恒为诗愈加“重情”,“景升东游有所媒而姬焉,是以多情至之语”[15]卷十,“中多情语”[16]286。忘年交汤宾尹称赞他是“因情之需而属对”的真诗人:“使吾不见景升,谓景升当是诗人,海内士定名相附耳。孰知其深情能中人,一至于此”[19]卷一,“感事而发,触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语。世人好景升与其诗,无不一见倾倒,则景升意气有以盖之矣”[19]卷一。潘之恒此时诗作中的景语、事语皆为情语,充分彰显诗歌的抒情特质。
东游吴越期间的广泛交游和声色之娱使潘之恒对诗歌“言情”本质有过深切体认,加速他对复古派泥古不化、真情难抒弊端的警醒,因而主张诗学多家,不拘于盛唐一体,汉魏、宋诗均可拟之,“夫生也,取骨于汉魏,其旨远;取态于宋齐,其词艳”[16]287,因而作诗能得建安、晋宋、齐梁、贞观、开元、大历等神韵,“古之人得其一犹足以棋于世,景升会而同通之,神而明之,不徒沿其体格,而其风有独存者”[16]284。此时期潘之恒论诗虽主情,却仍未摆脱复古诗学束缚,“变出于心矣,体合于古矣”[16]287。好在他已经萌生不惧世人诟病、彻底摆脱拟古羁绊的决心:“毋违性情,毋叛风雅,毋貌取汉魏六朝初盛唐内自欺,而时好是狗。毋要誉,毋避訾,毋中离间之言。”[20]卷七随时准备学习时尚新诗体,抒发真性情。
三、西游楚地,倾心公安派独抒性灵诗学观
万历十三年起,心学大家李贽开始在湖北麻城龙潭湖讲学、著述,时间长达十年,楚地由此成为晚明人文思潮中心。其“童心说”将纯任自然的真情、本性作为人性最高范畴,主张顺应自然,尊重人性本真,发展自主个性,形成“重情”“求真”“尚俗”的人文主义思潮,在晚明士人中引起广泛响应。如袁宏道、汤显祖、梅国祯、丘长孺等文坛名家,或当面请教,或以文字神交,形成文坛“尊情轻理”风尚。万历二十二年冬,潘之恒终于弥补“三岁向往,日逐梗泛,无由问道龙湖,开我聋瞽”[13]卷十二之遗憾,于龙潭寺拜谒李贽,接受心学思想熏陶。二十一年入楚,与袁中道结社于五咏楼,进而交接袁宏道,“余既盟小修,以神交中郎,及为吴令,始通书定盟”[13]卷一。之后二人又分别于万历二十四年于真州会晤谈诗,二十五年于歙县潘之恒家相会。与李贽、三袁交往,引起潘之恒思想很大震动,李贽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袁氏兄弟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主张成为潘之恒彻底跳出拟古制约的催化剂,让其追求自由的思想完全放开,不羁的天性彻底释放。
游楚期间,潘之恒不仅积极接受新思想新理论,还在诗歌创作中努力践行之,“所为诗顾独清新超脱,不入近代蹊径”[16]290。游楚所作《涉江诗》虽遵古体,“取骨汉魏,取藻六朝,取韵三唐”[4]328,“大都君古体,能禀于法,而未始不极其才。近体能抒其才,而未始不闲于法。要以苍健为骨,秀美为泽”[4]326,又不失自我风格,多朴直新奇、豪宕放任之作。由此可见,他终于走出“体合于古”[16]287的思想局限,突破诗歌体制束缚,努力尝试书写“源心”之诗,有些新诗多源自亲身体验,情感真实自然,感人肺腑,程仲权赞之:“取必会心,往必当物。不造伪以率合,不引妄以相诡。与其滥于藻绩,无宁契于神情;于其讬古之肖,无宁贵我之真。”[21]卷七袁宏道亦夸奖:“倘有刻意为诗,无湔旧习者,请从《涉江》为篙橹焉。”[16]291江盈科更给以高评:“方之古人,鲜有不合;求之近代,罕见其侣。”[4]326游楚之后,潘之恒诗学思想与诗风的改进使其诗歌创作更具生命力和艺术魅力,于是名声大振,“是时景升诗名传播海内,其才十倍余,而游道之广百焉,以故诗益富而名益彰”[16]285。
四、晚游金陵,接受竟陵派深幽孤峭诗境论
潘之恒晚年出游地主要是南京,“晚而倦游,家益落,侨寓金陵”[1]丁集下630。除和故交来往之外,还与钟惺、谭元春等竟陵派为主的新友交往频繁。陈广宏《钟惺年谱》和《谭元春年谱》中都有潘与钟、谭二人交往的大量材料,如: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钟惺、潘之恒等人结冶城大社;四十七年,潘之恒与钟、谭等倡秦淮大社;同年,钟惺作《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为他募刻;天启元年前后,潘之恒“与竟陵谭友夏游甚乐”[4]300。谭元春文集中有《潘景升戊己新集序》《赠李校书同潘景升》《逢潘景升》等诗文。在与钟惺、谭元春等人交游过程中,潘之恒主动学习他们重寻诗歌古典审美风格,追求“深幽孤峭”诗境的主张,近而改进自己诗歌的低俗、随意之失,对审美意境的追求更为主动,“时秦淮一勺,固耳目常玩,一落髯翁笔底,物无故者”[21]卷首。由此邹迪光评曰:“夫景升所为诗,出于曲房之下,酒垆之畔,男女嬲而杂坐之顷,击筑鼓缶,呼卢博塞传筹之隙耳,而类能吐肝哕胆,刳心剔肠,句啄字磨,穷致极变。”[22]卷三十二潘景升晚年诗歌虽多取材通俗,但出于真情,精心打磨,达到“穷致之变”的艺术效果。
竟陵派是活跃于晚明的最后一个诗学流派,标志着明代诗学复古拟古与求新求变不同派别间无休之争的落幕。潘之恒通过与他们交游,最终更好解决复古与师心关系,形成自己特有的诗歌风貌,其晚年诗集《戊己新集》堪称代表。该集是戊午春应汤宾尹邀游宣城所结《漪游草》与己未春僦居青溪所结《青溪社草》的合集,诗作多以声色浇心中块垒:“或以其多蔓草之遇,芍药之赠,恋景光而媚窈窕,颇见尤于礼法。不知《国风》好色,靖节《闲情》,皆意有所至,而借以舒其幽懑,发其藻丽。”[21]卷首谭元春为之作《潘景升戊己新集序》云:“其虚衷而从事于变移之途者,非尽虚衷也。才足以变,不必止于其所也”[3]616,称赞他完全能够正确处理“师古”与“师心”、“复古”与“求变”之间的关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
五、文学交游中形成的主要诗学观念
潘之恒一生活跃于徽州、吴中、越地、郢中等文坛中心,先后青睐七子派复古诗学、汤显祖等戏曲家“至情论”主张、公安派“独抒性灵”主张、竟陵派“深幽孤峭”审美追求。在转益多师和长期漫游中,潘之恒几乎接纳晚明诗坛所有流行观念,最后转化为自己的诗学思想。虽然观点不多,但亦可谓一家之言。
关于诗歌本源,潘之恒认为“诗也者,心之声”[13]卷一。在长期探索实现复古、性灵与自我个性完全融合的最佳路径中,他提出“诗也者,心之声”的“文心”诗学观。他认为“文心”为诗文本源:“昔人谓文生于情,此为有情言耳。若具文心者,固无待于情生,嬉笑怒骂,微哂单词,莫非文也。晋陵李纫之,多警语而善谑,因物曲应,无不合节,短咏尺牍,各极于情,其义得之曲,其情出于音,义浅而充之以识,音变而调之以律,故为文日新而不诎,言入化而不穷之角者屡矣。”[13]卷十一认为只有发自内心之“情”的文字才自然真实动人,“心之声犹焕于文,而况心之文,其绪于音,为流水,为行云。”[13]卷十一而诗歌是纯文学代表,更具“言情”特质,更能体现“文心”,因此“诗心观”是其诗论的核心思想。
在诗歌发生论和创作论方面,潘之恒主张“诗何其径,情按而求之”。他认为写诗贵在“有情有生”[6]卷七,诗人要表意通畅,绘景生动,须有自然真实情感:“诗何其径,情按而求之,志无不畅,而景无或匿矣”[13]卷一,诗文只有“极于情”“情出于音”,方能“为文日新而不诎,言入化而不穷之角者”[13]卷十一。有文心者必超然物外,心中只有一个自我,“予恶乎质哉!水鉴不若人鉴,人鉴不若予鉴。物以予为不祥,且然乎哉?众人以予为不肖,且然乎哉?祥则不祥矣,肖则不肖矣,于诗亦然。游以诗,观于道几矣”[13]卷五。因此培养诗情、书写诗情是诗人必备的品质与能力。
在诗歌艺术追求上,他强调“诗之为道,工意为上”[13]卷五。潘之恒在《评许恭甫诗代引》一文中提出作诗要正确处理意、调、辞三者关系,强调“诗之为道,工意为上,工调次之,工辞为下”[13]卷五。他认为作诗以“意”为主,“意宣,而调与辞随而并至者也”[13]卷五。其“意”就要体现真性情,即使与传统伦理道德相违背,只要发自内心真诚就算好诗,“自徐文长、汤义仍、黄平倩、袁中郎辈出,而稍以意相乘,或纤或峭,或捷或彻,劣于调而俚于辞,虽暂诎正雅,而己意常伸,俗嚣一洗”[13]卷五。他强调“己意”正与晚明人文觉醒思潮相吻合。他还认为“调”“辞”为宾,也要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上的审美追求,“调”“辞”当则“乌得而废诸?尚意者自能参而衡之”[13]卷五,不当则“意以辞害、以调掩者”[13]卷五。
在诗歌鉴赏方面,潘之恒提出“境合”“情合”“神合”三重标准。“境合”指借助有限、孤立的物象显现大自然混沌一体的整体美,“故其为诗也,如水空而镜彻,其泌神也,无所不融多;如烟蜚而象玄,其幻游也,无所不适”[13]卷一。“情合”即情与景的无痕互融,“情与景每互涉而迟出,则会心之效尔”[13]卷五。“神合”指作者通过人、景、事的描绘彰显以“情”为基础又超越于“情”的精神和气质。诗人应该拥有独立风格,“人各自媚尔,谁相为言哉”[13]卷五,“卿子之于中郎,犹林宗之于卿子,皆媚乎诗者也。中郎以境合,卿子以情合,林宗以神合,情融乎境,神超于情”[13]卷五,故三者无别高下,“所感不同,而冥情离幻,意无不之,而情无不极也”[13]卷五。潘之恒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努力践行“三合”标准,助推其诗歌创作水平的提升。
结语
潘之恒一生好游好学,漫游开拓眼界,交友丰富诗论,好学求新是其人生常态和不懈追求。少年时期,“每见必出其所业,余因得以窥其进”[9]卷五十四;年逾六十“好学深思不倦”[3]616。谭元春概括其文学交游历程:“景升六十年中,初与琅琊、云杜游,欢然同志也。已而与公安交,复欢然同其志。弇州诸先生力追乎古以为古,石公游千古之外以追乎古。今二三有志之士,以为无所为古内古外,而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即古人之用意,下笔俱在是,而景升复欢然同志于其间。”[3]616。谭元春十分赞赏其思想开放、融通多家,用“变”“化”二字归结潘之恒成功秘诀:“其年能待,其才能不衰,景升得乎天。前后之交,如一时一士,景升得乎人。夫不变不化,则安有景升焉。”[3]616潘之恒亦自言一生都在“变”“化”:“余十年守一字,曰:离;近更进一字,曰:舍。幻可离,法应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离矣!舍矣!进乎忘矣。”[21]卷首可见求新善变、化为己用正是潘之恒诗学思想的显著特征。
由此来看,钱谦益、四库馆臣等人对其评论有失公允,没有联系中晚明文人风尚与诗学思潮演变的具体历史语境。潘之恒主要生活在社会思潮激进的万历朝,彼时文坛呈现人文思潮高涨态势,诗坛主流思想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先后为诗坛主流,师古与师心主张在长期对抗中逐渐融合,文人的门户派别意识日渐消融,诗人个体诗学观念在交流唱和中互相影响、启迪,共同与时俱进、整合贯通。如吴国伦入“后七子”后推举复古思想,后自省转向关注性情,“以情志为本”[23]卷四十一。再如复古领袖王世贞重于新变,“余则以日新之与变化,皆所以融其富有拟议者也”[24]第1284 册,824。他早年倡“格调”领文坛风尚,晚年标举“淬砺南北菁华,格调与性灵并重、藻彩与气骨相剂”[25]75新文风。由此可见,潘之恒的诗学思想嬗变历程是晚明整体时代诗人的具体缩影,反映复古派后期诗学转向的主要路径,并非“始终随人作计者也”[2]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