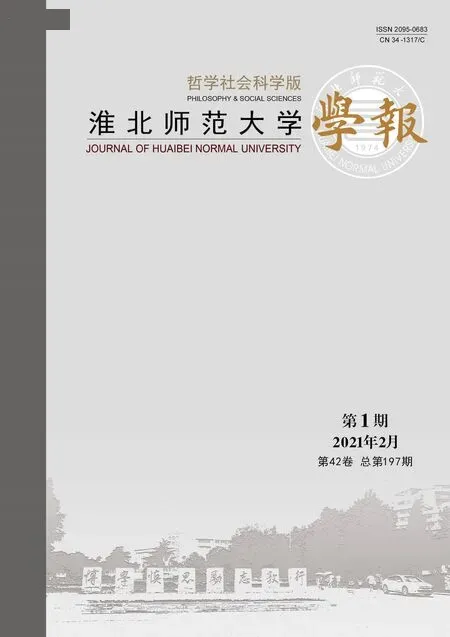张载礼学思想的实践理路
冒婉莹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241)
张载的学术在北宋儒学中自成一脉,学界对其义理研究的成果颇多。礼学是其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倡导礼学的研习应当兼重义理与实践两个方面。在礼学问题上,到宋儒这里明显出现了以义理为先的研究趋势,但兼重二者的学派亦有所坚持,他们青睐探索改造世界的方法[1],张载的关学正是如此。张载云:“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工商之辈,尤能晏寐夙兴,亦有为焉。”又云:“在古气节之士冒死以有为,于义未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况吾于义理已明,何为不为?……盖君子欲身行之,为事业以教天下。”[2]130这里的以身行之、教化天下的处世态度,即可见其兼重二者的礼学特色。吕大临记张载之讲学:“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2]383也反映了他贯通义理与实践的教学风格。当前学界对于张载礼学思想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义理之论,然若其礼学思想本身就呈现了兼重义理与实践的特色,那么如果能够直接展现二者在其礼学思想中互为致用的特点,或能更准确地豁显张载礼学在现实生活层面的实践活力。以下,本文将述清张载礼学如何从义理阐释走向实践致用的理路。
一、见礼于理的认识实践
宋代儒者论礼之特色在于贯通心、礼、天,张载亦将礼视为人对宇宙万物产生规律性的体认后,做出的回应或顺应之言行。但同时张载又主张礼豁见于理,认识礼就是开显理的实践。为此,他提出对礼的认识实践第一要义不是对六经的研读,而是对理的体认。
张载对礼的思考,遵循从天道贯彻至心性的逻辑。礼包含具体之礼与抽象之礼两个内涵,它是天人相交的媒介形式、人伦社会结构中的道德科目以及政治统治的载体,又同时有超越这些具体形式的引申意义:
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五常出于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为,但不知耳。[2]264
引文意在将“无体之礼”与“礼之原在心”相贯。“太虚”是张载哲学体系里的核心概念,与朱熹的“天理”更为接近[3],它既代表气作为本体性存在,同时又具有运化之道的动态含义,其兼具体用双重性质。张载如此诠释“无方无体”:
神,天德;化,天德。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神无方”,“易无体”,大且一而已尔。[2]15
“太虚”是“大且一”的存在,而“神”“易”则是对其运行作用状态的描述,又云:
体不偏滞,乃可谓无方无体。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合一闭”,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2]66
在这里,张载为“无体之礼”赋予了“太虚”的特质。礼同样存在于恒久不变又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中:
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地之性叙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须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2]264
此即是说,天地之礼依据天地间本有的秩序,这种秩序在没有人的时候就已经如此运作,由此可确定礼不是由人制定出来的,而是本就依循天道存在的,万物的礼法就是天地本有的秩序表现。宋儒对天人关系的论述,落脚点皆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4],张载除了从形式上类比了天道与礼法的相似,还对二者的内在关联加以分析:
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2]264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2]9
这里,张载引入“性”作为帮助其诠解礼自天道出的佐证。他认为人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天地之性”,另一是“气质之性”,两性在太虚运化中都会发挥作用,相对之概念由此融于一体,如显隐、有无、性命皆通贯于气化生成之中。由此天道与人性相通,“知虚空即气,则有无、显隐、性命通一无二”,人的身与心、性与命达到所谓“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状态。张载的“天人合一”形成了一种新突破,他肯定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的开始。[5]当然,天地之性表现为至善,而人性却气质万千,但经典所载、圣人所制之礼乃是依据天道、本于天地之性。人之所以能通过礼的形式内容把握天道,实现“礼所以持性”,就是因为三者先天存在“礼-性-天”的一贯性联系,即所谓“能守礼,己不畔道矣”。
除“性”之外,张载还引入心的概念对此一贯性加以分析。张载道:
《复》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壮》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时,则有形见;情则见于事也,故可得而名状。[2]113
心在张载这里亦是一个体用兼具的概念,“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心统性情”,换言之,人心即是天地之心,那么它朝向客体生发的情亦是天地之情。张载此处对咸卦之解更进一步表明,人的“心”与“情”皆生发于天心之心、天地之情。“咸”即天道与人道一贯,天显现出“日月、寒暑往来、屈伸、动静”的变化规律,而人则据此“精义入神以致用”,此又表明天道与人道不仅是内容之一贯,更见诸于实践之一贯:
人道之交贵乎中礼,且久渐而成也。[2]127
这里又指出人世情况中的特殊性。如果天道与人道无论内容还是实践都是一贯的,似乎人道就不是“久渐而成”的。这是因为礼是“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而人世间之事无法脱开“情”之影响,有“情”则有私欲。礼正是用于化人之“情”,所谓“克己复礼”义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载这里礼的“久渐而成”并不意味着礼与人心是对立的两端,礼于人并非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性存在。张载认为人“心无由尽,正大之情无从可见,而道于是乎晦矣”,他的“心”是能够“体天下之物”“尽合天心”的心,这使它也具有天道“生生”运化之特点,所以“情”生于此亦可为之所把握,而以心持情就具体表现为人在事上的言行。朱熹就言:“性、情、心,唯孟子、横渠说得好。仁是性,恻隐是情。须是从心上发出来。心统性情也。”[6]礼是“尽心”之学,张载说:“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以心体证自在的天道,就是化情入理的身体力行之功。
经典所传、圣人之制的礼,根源于圣人内在的诚心,而这种诚心以与天地之心相合为一,所以圣人是在已经通达了礼乃“合内外之道”的前提下书写了礼的内容与形式,即“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道”。礼即体现为“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礼行。”这样的“秩序”就是“天地之德”,它可以通过人的勤勉之功而与人相合。对“秩序”的勤勉功用皆出发于诚心,这样人所认识到的“秩序”才是天道,才可表现为正人间之理而发用的礼。
可见,张载对礼的认识实践方式的分析上,充分发挥了人心与天地之心的至善性相通的特点,以及人心具“生生”之功用的特性。基于人心特性所建制的礼自然应该落实在人间大道上,这一点也是实现天道与人道贯通的关键。因此,张载主张人认识礼的途径应以天道之理为先,圣人之道次之,而礼经文本最末。
对礼的认识实践,即如何从理中见礼,对人而言这一过程似乎十分依赖于礼经文本的研习。但张载在此有不同看法,他对礼经文本之于礼的认识重要性有新的解读。首先,张载是认同读经的,经典本身就是圣人与天道相合所作,时常习之、诵之就会自然践行之:
孔子谓学《诗》学礼,以言而立,不止谓学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须要此不可阙。不学《诗》直是无可道,除是穿凿任己知。《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2]278
张载指出经书的要义应当具有付诸人伦日用的可能,所以他肯定六经的重要性,认为这类经典是立足于日常之道所作,而除此以外的则并非必须习诵。六经经典本身以现实之道为落脚点,那么反复的记诵就会使其中的义理彰明:
故唯六经则须著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个则又见得别。[2]278
如此看待六经之于礼的作用,恰好符合张载将经典文本置于认识礼的实践方式最末尾的主张。一方面,六经之道落实于人事之道,书写于圣人对天道之领会,所以它自然次于天道义理与圣人之道;另一方面,人对六经经典的研习必须经由内化才能彰显,换言之其中义理本身与人心性相合才能完成这种内化,人的心性本源于天道,那么诵读经典自然次于心性对天道的直接领受。况且天道义理无穷尽,而经书所能容纳的是十分有限的,反复研习经典是为使“心”成为具有体知义理能力的心,而不是使心局限于经典之中。张载云:
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故虽有不识字者,何害为善!《易》曰:“一致而百虑。”既得一致之理,虽不百虑亦何妨![2]277
其所举为极端之例,即使不识文字亦不妨碍人心与天道相合,反而是将心拘泥于文本之中,倒有可能“迷经”:
人之迷经者,盖己所守未明,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己守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须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2]277
所以无论是经典文本,还是圣人之道都并不是绝对的天道大义:
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2]275
“心解”即是对圣人之道、经典之说的深入拓展,如孟子对孔子之继承与拓展。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2]275
认识礼的过程亦是如此,“明则经义自见”表明理本是优先于经典,礼从理而非从礼经文典。它既可以先于经典与心性相合,也可以通过经典培养专注大道之心再持续求索。经典文本的作用始终在于对心性的培养使其无限发展,而不是使其受制文字。
二、鉴礼于性的生成实践
经典对“常道”的关注与书写,决定了张载如何定位它在认识礼的实践活动中的地位。但因其内容特点,在礼向人的生成实践中,张载又十分看重其价值。他主张“统贯诸经”,即是坚持礼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以正经行事,以“知礼成性”的方式作为礼的生成实践。
何为正经行事呢?张载道:“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依照秩序行事就是人间伦理常道的方式,以此落实就是礼的生成。上文已提及,张载认为“秩序”就是天地之道,他谓之:“志学然后可与适道,强礼然后可与立,不惑然后可与权。博文以集义,集义以正经,正经然后一以贯天下之道。”[2]34则以礼安治天下乃是以天地之道来行事,而不可以经文为标准。他说:
易简理得则知几,知几然后经可正。天下达道五,其生民之大经乎!经正则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2]34
精义入神,豫而已。学者求圣人之学以备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来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则自一月前栽培安排,则至是时有备。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在于此积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经,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2]215
引文正印证其说法,“正经”是经过了“知几”的工夫达成的,“知几”之意是指对极细微之处的把握,它出自《周易·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张载将人间伦理的恒常性与天道的恒常性相贯通,《易传》所说的“知几”就是达到对这种具有超越性理则的认识方法,可看作是个人实现穷理尽性的准备。精小细微之处自然不能离开日常之道,所以“知几”“精义”的工夫就在人事之中,“正经”之目的亦是在此,在人伦生活中落实天道,具体之礼如五常、九经等在人道施行,就可以实现礼治。引文中强调五常为“生民大经”,而九经则是求圣人之学必备,皆可见张载将礼的生成实践重点落实在人事伦常之中。张载强调“知几”作为“知礼成性”的前提,正是因为现实事务气象复杂,唯有做到知其精义,才有可能在面对具体之事时实现正经而行事大道,他说:
知几其神,精义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见事于未萌,豫即神也。[2]217
但仅有“知几”尽精微仍有可能无法应对人事的繁杂,张载此处又提出“时中”,即展开对现实情势的有效判断,如此“正经”才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张载云:
然非穷变化之神以时措之宜,则或陷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2]51
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始得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此方是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2]264
他又具体举例说: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2]24
天人不须强分,《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若分别则只是薄乎云尔。自然、人谋合,盖一体也,人谋之所经画,亦莫非天理耳。[2]232
显然,张载的“时中”之概念,是为礼的生成提供可践行的保证,他主张理是体用兼备,那么当程朱那类纯粹的形上之理下贯到具体人事上时就会僵化难行。因此可以说,张载为“理”新增了实践属性,而礼源于理,是理的形式表现,其云:“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那不妨说个人的“穷理尽性”之完成就是礼向人伦社会的展开。二程将这一过程表述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了”“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可见其将“至”和“知”两个践行动作等同起来,知即是至,有过程即结果之意。但张载对此过程则有不同阐述:
知与至为道殊远,尽性然后至于命,不可谓一;不穷理尽性即是戕贼,不可至于命。然至于命止能保全天之所禀赋,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不容有不知。[2]232
“知”与“至”是此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所指的内容并不一致。首先要明确的是,穷理、尽性与至命是不同的阶段,“知”是由“穷理”到“尽性”的实践方式,张载云:
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如人矣。知天知人,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同意。[2]234
这其中就展现了张载的创新与重点,即其将“知”的实践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知天”层次,这一层以“穷理尽性”为目标,二是“知人”层次,这一层则需要以伦理常道为实践场域,以此实现“至命”的目标。张载对“知”进行这种分法的原因: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知之,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徳性所知,不萌于见闻。[2]24
由引文可知,主要是由于知的来源有二分。见闻之知有限而德性之知无穷,见闻应以德性为准则,以避免陷入耳目感官的限制中。从知天到知人事就是由天道贯通人道的过程,人心由内向外扩张的过程。基于此,张载继而提出“大其心”作为尽性的方法。人心之所以能与天道相合为一,是因为天赋的德性之知与至善道体是一致的,而感官所带来的闻见之知往往会遮蔽德性之知,“大其心”的核心就是摆脱闻见的桎梏,彰显德性与天地之性的贯通性。由此,“知人”即对伦理常道的理解就成为实现“穷理尽性”不可或缺的一环。前文已提及,张载将“知人”作为达成“至命”境界的手段。张载道:
既穷物理,又尽人性,然后能至于命,命则又就己而言之也。[2]235
“尽其性”能尽人物之性,“至于命”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诸道,命诸天。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至于命”,然后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2]22
由此看来,张载将“穷理尽性”作为实现个体生命意义(以天道合一)就必须遵循的宗旨,但如同他提出“时中”这样一个符合人伦社会的务实理念一样,他亦警觉地为个体生命意义找到了群体归宿,以避免“至命”之结果落入虚无。也就是说,个人之命是无法脱离群体而存在,那么“至命”的命题亦要回归于人群,进而“至命”的问题就得以落实到对“秩序”的实践上来了。张载说:
进德修业,欲成性也,成性则从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则谓之圣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节而成性,若圣人则于大以成性。[2]76
“成性”是圣人境界,张载的“至命”与“从心皆天”是同样的状态。这里可以把“成性”境界看作“至命”的结果,那么“知礼成性”的知礼亦是“至命”的重要内容。《周易·系辞上》中载:“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异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张载将其阐释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昼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礼性也,非己有也,故知、礼成性而道义出,如天地设位而易行。[2]191
“知”是“穷理尽性”之学,以知天道运行、天人相通的大道为目标。而“礼”则代表世间的伦理秩序。“行礼”必先“知礼”,而“知礼”和“行礼”都指向个体的成性目标。[7]“穷理尽性”的过程就是使知与礼相统一、明确礼自天道出的过程。“知”是人德性精神层面的,礼则是合于德性的实践层面,张载谓之:
知极其高,故效天;礼著实处,故法地。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2]192
张载的天人贯通之理论,使人在“知”与“礼”两个层面都具有实践生成的可能。“知”可效天,而“礼”则著于实处,有实践的方向即能促成“成性”,也就能推进“真义理”的生成。在张载这里,效天之知可以通过著于实处之礼而精进,而“知”本身于人又是一种德性引导。张载说:
何以致不息?成性则不息。诚,成也,诚为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于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为圣人也。然清和尤是性之一端,不得全正,不若知、礼以成性,成性即道义从此出。[2]192
显然,张载并不认同仅依靠心性对天道德性的直觉体认就能获得“真义理”这种绝对单一途径之说,他主张同时需要人去发挥智用以鉴“诚”心。“成性”的过程是动态的不断实践天道的过程,“诚心”以“知”的动作不断显现,所以亦不能是悄然无息、寂然不动的:
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诚谓诚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则当有所尊敬之心,有养爱之者则当有所抚字之意,此心苟息,则礼不备,文不当,故成就其身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2]266
以礼的实践行为鉴“诚心”以至“成性”,张载将此完全落实在人伦常道中。“至于成性,则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矣”,实现心性上的感通,必“知”人之以日常人道的实践环节的参与,该环节的核心则是以礼处之。
但一贯的天道之理、至善德性在下沉人世的时候会混杂其它气质,礼是天理大道的外在形式、规范准则,所以礼的教化就显得尤为必要。程颐、程颢就将天理看作万事万物各存一理[2]129,再回到圣人制礼、经典载礼的初衷来看,本就是他们凭借天地之理、至善德性通过人间教化的方式使人通达“成性”的境界,无论是“大其心”或是“穷理尽性”都必须落于实处才有效用。张载说圣人能到达“成性”的境界,就是因为他们做到知天理而行人礼的,如他所说:
圣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后道义从此处,譬之天地设位则造化行乎其中。知则务崇,礼则惟欲乎卑。成性须是知、礼,存存则是长存。知、礼亦知天地设位。[2]191
之前张载所阐释,旨在说明天道与人道相贯通,礼见于理,所以需要践行礼于人世方可使人至性至命,这里更多的是在讲落实“礼”的必要性。而在此处,张载所论则在于突出人的价值性,所谓“知礼亦如天地设位”,在于突出人不会因天生资质之差异而失去“成性”的资格这个观点。对于个人来说,心性贯通于天道是生来被平等赋予的特性,因此对能否“成性”的更有挑战的考验则在于,是否能够坚持在世上笃行礼义。鉴别个人于世间的礼义执行程度,即是鉴别个人“成性”之境界。
三、践礼于群的发展实践
如上文所述,张载认为于世上实践礼,可以通达“成性”的境界,这一点与他所说的“变化气质”的个人修养论相辅相成。太虚运化,天地有生生之性,它赋予人至善德性的同时,也混融进其他气质,比如恶的气质。礼是本源于天地之理,是“穷理尽性”的学问,所以变换气质以恢复至善本性,学礼、行礼是最有效的方法。张载提出“躬行礼教”之说,这是对“理”之外的、自我欲念滋生的恶的克服,是使纯然本性显露的自我修养工夫。人在社会化与伦理化的过程中,先天本有的道德才会壮大发展[8]。如果个人的礼生成,那么就会发展、推行于整个社会,所谓“天下有道,道随身出”就是指个人之礼向社会之道的发展的积极结果。
张载所提倡的在礼上需“躬行实践”对人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是从内部确证人心性与礼的一贯相通。学是躬行的第一阶段,在无法通过自我体认这种比较高阶的“成性”方式肯定自我的时候,以学为手段就可以克服吉凶、真假、大小等外在之象的干扰,获得内在印证的目标。第二重是从外部也就是社会伦理生活中确立个体的价值与意义。礼之结果是有秩序、道德的公共社会生活的落成,个人心性的理需要外化成礼所建构的社会形态,个人的气质变化是从这种礼的外化中表现出来的。张载说:
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习者自胎胞中以至于婴孩时皆是习也。其及长而有所立,自所学者方谓之学。性则分明在外,故曰气其一物而。气者在性、学之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之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则当世习熟缠绕。……苟能除去了一幅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2]427
这里张载肯定了人的身体对道体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讲,体道与行道都无法离开身体感官,无需将身体作为体道的阻碍,反而因为心性与天道相合,那么由心性支配的身体官能发挥同样与天道相合,这种功能发挥就是礼的表现:
立本既正,然后修持。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2]270
张载言“知礼成性”,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治身的方法。由于气质之性的复杂,人身难免被欲望所限制,“成性”的过程也是克服“身体”的过程,但人的身体就是太虚运化的生生表现,所以身体感官依照天道秩序来发挥作用就是在克服“身体”的限制。换言之,身体本来就作为礼的承担者而存在:
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2]25
那么,对礼的实践就是个人修养提升的方式。但张载并不满足于礼止于治身,他进而由礼于个人之用推展到礼于社会之用。
他最为重视的是礼对于维护宗族群体秩序的重要性。礼的内容与形式中,表现出了差序分别的情况,这是因为礼在最初制定时,首先运行于具有血缘联系的群体之中,社群维系以及正常运转的基础就是各个个体各司其职、各尽其分,这也符合天道生生不息之德性。张载云:
礼别异,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礼天生自有分别,人须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2]261
这里所阐述的礼的三个特点,与礼和血缘族群之间的深刻联系有直接关系。首先是“别异”的特点,因为族群个体有长幼尊卑之分;其次是具“不忘本”的特点,因为族群是由血缘紧密相连接的群体;最后是以“节文”的形式出现的特点,这是因为族群有延续性上的优势与传承性上的强烈诉求。因此,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族之礼值得推行。张载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地方分权主张在北宋现实社会中的灵活运用[9],尤其是在宋代科举取士的方式使得庶民获得晋升士大夫的可能的情况下,这使得阶层的流动性更为频繁,以宗族群体为主的礼法有利于将流动性的庶人阶层也纳入到道德规范中来。张载说: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于礼,庶人之礼至略,直是不责之,难则也,盖财不足用,智不能及。[2]317
显然,张载对宗法礼制的重视,与其作为士大夫阶层而特有的教化理想是一致的。在张载看来,礼教的推行和宗族建设是一体的。[10]“民胞物与”是张载所建构的礼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他所提倡的宗族礼法就是在这个宏大价值下的具体落实项目。主张推行宗法与井田制,既是张载的社会理想,更是他作为士人良心的体现[11],“知礼成性”者就是能够体悟“民胞物与”的精神气质,张载云: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2]62
“民胞物与”的价值观与理想之下,宗族群体的礼法系统不仅具有维系族群的向心力的作用,同时会朝向国家一体发展,张载对此颇有信心,云: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士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血统,虽至亲,恩亦薄。[2]258
宗族礼法中“不忘本”的特色尤为突出,其中具体的构成,如宗子制度、家族谱系书写等执行方式,可以有效地用来规范个人言行从而稳定社会的秩序: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2]259
而对于家族礼法的执行,他亦以“正经”之用直接述之:
某自今日欲正经为事,不奈何须著从此去,自古圣贤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远者大者又难及得,惟于家庭间行之,庶可见也。今左右前后无尊长可事,欲经之正,故不免须则于家人辈,家人辈须不喜亦不奈何,或以为自尊大亦不奈何。盖不如此经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为其子孙之益者也。[2]290
引文中,张载言及吾辈虽暂无为国家大礼有所贡献的能力,但可身体力行于家庭宗族之间。仅从当下来看,奉行于宗族群体之间的礼似乎只是对个人精神气质的提升,但长远来看,宗族群体里的道德化、秩序化是于国家有益的,它并不逊色于大礼大用。显然张载对普及宗族礼法的这项工作还寄寓着其能发挥治世之效的厚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张载对宗族礼法的看重,并不是刻板的以礼的形式为重,他所积极宣扬的仍然是礼仪背后的礼义根源,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述的礼是“正经”的外在表现。比如在丧葬之礼的规仪解读上,张载就说:
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朝以下,未始有哀麻之变;祭先之礼,异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2]283
祭所以有尸也,盖以示教;若接鬼神,则室中之事足矣。至于事尸,分明以孙行,反以子道事之,则事亲之道可以喻矣。[2]294
丧礼中的礼仪形式固然重要,但其祭法背后的礼义更值得思考,它是礼序的根源。张载对礼义的解读常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如《礼记》中讲对尸体的处理应当按照:“为人子者,……祭祀不为尸”,“《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来执行。张载对此解读为:
“抱孙不抱子”,父与子主尊严,故不抱,孙自有其父,故在祖则可抱,非谓尸而抱也。[2]294
接鬼神的仪式无需在堂前举行,而祭祀尸体则需要在堂前完成。这样的礼法安排表明礼的“亲亲”之用较之鬼神信仰是有极大的优先性的。而以孙辈抱祖辈,父辈不可,则是因为一个宗族中,父辈主尊严,祖辈主慈爱,这种礼序是维护礼法的根基,不可被随意破坏。
张载论祭祀中对鬼神的态度时,亦是将礼对于宗族群体的现实意义放在首要位置。祭祀典礼中,中心应当是祭祀人群,而非被祭祀者:
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知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2]64
张载对佛教所主张的生死轮回之说极为反对,批评为妄说: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圣者,至诚得天之谓;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2]9
大率知昼夜阴阳则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则能知圣人,知鬼神。……舍真际而谈鬼神,妄也。[2]65
而人无论是心性还是身体才是与天地之道一贯相通的,乃太虚运化所生,死后就是归于太虚,即“形溃反原”。行礼是在知晓天德、圣人、鬼神的真知之下开展的,换言之就是对礼义的通晓。圣人的“成性”境界就是体认到“阴阳”“鬼神”不二于体,所以祭祀中的主体应当在祭祀群体而不是鬼神之类。当“真际”不明时,鬼神自然大行其道,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以学通达礼才能转变。既然鬼神之事并不是“真际”,那礼中为何有“接鬼神”之举呢。张载对此论道:
祭祀之礼,所总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数尤不足,又安能达圣人致祭之义![2]294
张载此处的阐释,实际上借助丧礼祭祀的问题,来说明礼需要在社会族群中践行从而得到发展的观点。一方面,就礼的形式而言,圣人制礼之对象具有范围性以及意向性,或是亲族血脉之祭,或是地域山河之祀,其中的礼体现的“别异”可使此礼范围内的对象形成有序的关联,被祭祀者同样是这种关联中的一环,或主尊严,或主慈爱,祭祀“鬼神”的行为使这种关联始终保持完整性,这亦是“天地之礼”的本然模样。另一方面,就礼的意义而言,由形式带来的礼序运行的完整性,能引起对礼义的深思,所以祭祀中祭鬼神之礼并没有偶像崇拜或异化自身的含义,更多的是教化与敦促的含义。
结语
综上所述,张载的礼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实践礼教特点,“知礼成性”所通达的境界,其实正是个人以礼作为修身指导而展开的不离人伦常道的生活态度。儒家以通过提升个人修养而成圣人为一贯宗旨,而仅仅体悟内在心性的天道相通,是不可能实现士人构造理想社会的愿景的。很显然,这种宗旨表明儒家所强调的“礼”的实践,侧重在公共生活的层面,特别强调他律的功效[12],这与释道宗教所引导的信仰层面的规范有着明显差异。张载所述礼的实践之独特,就在于他将人的道德能力置于极高的位置,这种能力是与太虚相贯通,而世俗所流行的公礼秩序本身就应当由人的内在之性来开显。因此,张载将身体同样纳入这个与天地相通的体系中,这样的身体力行使礼能够“著实处”而现“真义理”。张载明显意识到,无论是从心性论谈礼的内在本然性,还是从天道论说礼的贯通一致性,如果不能为其开辟“著实处”的实践场域,礼义就会淹没于礼仪之中,内在性与贯通性将极易变成封闭自我、精神胜利的口号与安慰剂,他如此注重凸显其礼学的实践面向,正是为克服世俗礼学之积弊做出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