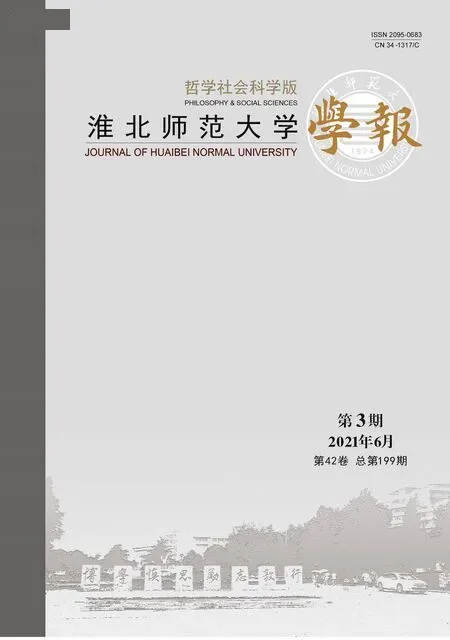周汉郊祀观念及郊祀诗书写比较
文晓华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军事战争诉诸于外,用以巩固疆土,抵御外侮;祭祀则是诉诸于内,祭奠祖先和神灵,祈求保佑,凝聚人心。郊祀活动,古已有之,《尚书·舜典》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1]54-55,记载舜曾祭祀上帝。郊祀时用乐用诗。《礼记·郊特牲》载有一首《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2]804,相传为伊耆氏举行腊祭时的祝咒之语,可看作最早的郊祀用辞。《文心雕龙·祝盟》载有舜的《祠田辞》:“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3]358可见,郊祀仪式用诗由来已久。
周之郊祀诗由太祝掌管,《文心雕龙·祝盟》曰:“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3]363。这些郊祀诗主要保存在《诗经》雅颂诗中①本文中的《诗经》文本均引自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汉代的郊祀之礼进一步完善,郊祀诗由大批文人统一创作,较为完整地保存在《汉书·礼乐志》中,共十九章,《乐府诗集》有专门记录②本文中的汉郊祀诗文本均引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作为早期的郊祀诗,二者在郊祀观念上有何异同,在写作上又有何发展演变?它们对后世郊祀诗的写作有哪些影响?本文拟从周汉郊祀诗文本出发,讨论相关问题。
一、从以祖配天到以帝配天
郊祀观念首先体现在祭祀对象上。祭祀者满怀敬意,祭祀心中无比重要的天神地诸位神灵,但周与汉郊祀诗均显示出人们增添了其他的祭祀对象。
(一)周代郊祀以先祖配天
周代郊祀往往以祖配天,即在祭天时以某位周人先祖作为配附一同来祭祀。《周颂·思文》《周颂·我将》二篇可为代表,歌辞如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周颂·思文》)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我将》)
《思文》言以后稷配天,既言天帝之功,又陈后稷之德,后稷是周人的始祖,“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4]145;《我将》言祀周文王于明堂,即祭天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祀,祈望上天与文王保佑天下,文王是周王朝的开创者。二诗均把本族祖先中有大功者与天同祀。
以天为主以祖为配的祭祀方式,并非自周始。《荀子·礼论》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5]375可见,祭祀天帝以先祖为配的做法是上古的传统作法,周人也只是在继承这一传统。以祖配天,是对本部族先祖和伟大人物的敬颂。先祖或伟大人物开创功业,对本部族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以祖配天时,配合仪式的郊祀诗往往要回顾先祖创业的不易,感念恩德,从而表示更好地珍惜当今,继续发展。《礼记·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孔颖达疏曰:“此一经释所以郊祭天之义。天为物本,祖为王本,祭天以祖配,此所以报谢其本。”[2]801-802报本反始,指不忘根本,天为物本,祖为王本,故而并祭。这一作法,明显带有致敬先祖提高祖先地位威望的意识。祭祀时以祖配天,最大程度彰显了孝道。《孝经·圣治》:“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6]63-78,将以祖配天推入孝道大义,意义深远。
祭祀时以祖配天,实为树立孝悌榜样,标榜于天下,其目的是巩固统治。国家郊祀仪式中歌颂先祖,述说功德,表达敬意,即是公开宣扬孝道。这一作法,从根本上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论语》首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5-7。国家郊祀礼仪尊亲尊祖,实为在民众面前树立孝悌榜样,这样做,可以聚拢人心,防止犯上作乱,并帮助建立一套齐整有序的孝悌秩序,为统治的稳定服务。周人奉行“亲亲尊尊”的统治理念,“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2]1001。亲亲与尊尊,是周不可变革的统治原则与礼法基础。“亲亲父为首”,必然强化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推崇对亲者的孝;“尊尊君为首”,必然强化等级秩序,推崇对尊者的忠。以祖配天的祭祀礼仪正是周代孝、忠观念最高层面的结合,是宗法等级社会用孝与忠编织成的一张礼仪大网,是一种统治策略。
(二)汉代郊祀诗将古代帝王与神同时歌颂
汲黯曾对汉代的郊庙诗歌表示不满:“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8]1178班固也批评说:“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9]1071,不满之一点是祭祀诗未能“承祖宗”“未有祖宗之事”。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代郊祀诗十九章及庙祀诗《安世房中歌》均“未有祖宗之事”,二人的说法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汉代郊祀诗的特点,这也是与周郊祀诗的明显不同之处。虽然不曾歌咏祖宗之事,但汉郊祀诗中却有一组诗较为特别,即《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五首。这五首作品表现内容为祭祀五时五方神灵,并同祭五位上古帝王。如《帝临》一诗: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匽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
《帝临》诗歌颂季夏中央后土神,并同祀黄帝。黄帝可称华夏民族的始祖,是人间帝王。《青阳》诗颂神句芒、帝大皞,《朱明》诗颂神祝融、帝炎帝,《西颢》诗颂神蓐收、帝少皞,《玄冥》诗颂神玄冥、帝颛顼。这五首诗,虽不是对刘氏祖先功绩的歌颂,却歌颂了整个华夏民族的五位始祖:黄帝、大皞、炎帝、少皞、颛顼。
四季五时祭祀五神、五帝的作法,周时便已存在,《礼记·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2]458,立春、立夏、年中、立秋、立冬皆要举行类似的祭祀。祭祀时,既要祭神,也要祭人帝,“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2]442-541。祭祀虽有,周人却并未作诗于仪式上演唱,汉郊祀继承了这一祭法,并用诗歌传写了出来。这种写作包含的便是帝、神同祭的理念,同时表达出虔诚的尊奉天道之意:
又王者必五时迎气者,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昊,冬以颛顼。[10]242
汉代郊祀诗,并未书写刘氏祖先功业,个中原因颇为微妙,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汉代刘氏先祖无功业可述,这恐怕未能说到根本。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汉代的祭祀制度造成的。周朝祭祀,往往融郊祀与庙祀为一体,汉代祭祀则不然。汉初,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用为宗庙乐歌,分担了祭祀的部分功能,郊祀歌诗便成为了纯粹的祭神乐歌,自然,歌颂祖先的功能便应由宗庙乐歌而不是郊祀乐歌来承担,因此,郊祀歌诗中不见歌颂祖先功德也是必然。汉代郊祀歌诗将古代帝、神同祭,应是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由五经家共同写作的结果。《史记·乐书》云:“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8]1177,这些由五经家共同创作的郊祀诗歌,融入《礼记》思想,形成了帝、神同祭的创作现象。
二、从单一的农业祈祷到多样化的个性诉求
祭祀观念也直接地体现在祭祀目的上,为何而祭,祭有何求,其背后凝聚的是祭祀人心底最大的欲望,也必定包含一些深层观念。周、汉郊祀诗,祭祀神祇,恭敬虔诚,其大旨皆为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统治长久,但从细处分析,周、汉二朝的祈愿目的各有偏重。
(一)周郊祀诗往往祈求农业丰收,体现出周人贵民贵生的观念
首先,人们往往祭祀天、帝、田祖,祈求风调雨顺,保佑丰年。大旱时,人们往往举行祭祀活动,请求天降雨露缓解旱灾: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大雅·云汉》)
这里,祭祀者极力表达对神灵上帝的虔诚,上下奠瘗,礼敬诸神,他们用祈求甚至绝望、埋怨的语气,呼告神灵降下甘雨。
除去祈雨,周人也往往向上帝、帝、后稷、田祖等直接祈求农业丰收。周天子每年春天都要祈谷于上帝,《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2]461,即是祈求上天保佑有个好的收成。《周颂·噫嘻》《载芟》均为春天祈谷之歌,《毛序》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11]1317,戴震《毛郑诗考正》卷四云:“‘噫嘻’,犹‘噫歆’,祝神之声。……此诗春夏祈谷于上帝之所歌,故噫嘻于神。”[12]96
这里,周人尊奉的有无所不能的帝,还有周民族的祖先后稷、司农之神田祖。后稷,作为周之先祖,带领着百姓发展农业,种植五谷,《大雅·生民》就歌咏了其出色的稼穑本领: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后稷懂得种植之艺,挑选良种,拔除杂草,荏菽、禾麦、瓜瓞无不生长有力,获得丰收。舜帝曾命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1]74,以利天下。弃便是后稷,因此周人尊其为神,祈求后稷能够赐予丰收,并在祭祀上天时以后稷配祀,“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周颂·思文》)
田祖即是农神。《小雅·甫田》云:“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周礼·春官》记“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13]631。田祖,即先啬、神农氏,朱熹《诗集传》谓:“田祖,先啬也,谓始耕田者即神农也”[14]631。“神农氏”,《周易·系辞下第八》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15]298《风俗通义》卷一云:“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16]第274册352页神农氏教给百姓制作农具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实为农耕时代的开创性人物,故而民众以之为农神祭祀之。
人们又往往于获得丰收后向神祭祀禀告,时间通常为秋天,是为报谢天帝之意。《周颂·良耜》毛序曰:“良耜,秋报社稷也。”[11]1361《丰年》亦为秋报之辞,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歌极力描绘丰收的图景,并献上丰厚的祭品以答谢上天。
先秦时期,生产力低下,在农业生产中,旱涝丰欠,人们往往不能自主,只能将一年的收成寄托在大自然及各类神祇的庇佑上,因而农业祭祀活动非常发达。无论是固定时间举行的春祈秋报之礼,还是特殊天气状况时的特别祭祀,亦或是申戒田官劝导百姓,均围绕着农业丰收的主题,体现出对农业的重视。“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4]15。
重视农业实际上是对民生的重视。民生最基本的含义当指民众的生计与生活。统治者认识到只有保障百姓的生活,才可能施行教化、民富国安、统治长久。《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177,《泰誓》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27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277,便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先秦郊祀诗正体现了鲜明的贵民贵生思想。《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写丰收给百姓带来的欢乐,又云:“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小雅·大田》),将重心放在无依无靠的寡妇群体上,希望她们能拾到田里的遗秉、滞穗,以维持生活。《周颂·良耜》云:“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写出农业丰收所带来的妇宁室盈的和乐景象。《大雅·云汉》一诗为民祈雨,更可作为为民请命诗歌的代表:“王曰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使天下百姓受灾,周王不停哀告上天祖先,为何不能庇佑这些“周余黎民”,接着指责昊天上帝、群公先正,不能体恤下情早降甘霖:“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最后,仍然不弃百姓,显示了强烈的统治责任心:“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反复剖白自己的一腔爱民之情。
(二)汉代郊祀诗的祭祀目的则要丰富得多,祭祀观念也较为复杂
首先,汉郊祀诗通过大力描写诸神带来的嘉风喜雨,来表达祈求国家强大、庄稼丰收、吉祥长寿之意: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海内安宁,兴文匽武。(《帝临》)
西颢沆砀,秋气肃杀,……奸伪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西颢》)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惟泰元》)
神之来,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华烨烨》)
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赤蛟》)
神灵带来的有甘露庆云,那么自然有一个丰收的年景在等待;神灵保佑国家海内安宁、四夷宾服,那么国家自然没有内忧外患;神灵还会赐予人长寿,那么自然人人都可摆脱生命短暂的苦恼。这些美好的愿景,已经比周郊祀诗的内容要丰富多了,更有意味的是,汉郊祀诗并不像周诗那样祈求神灵赐予雨露丰收,而是用一种肯定的语气描写神灵自然会带来幸福与美好,这表明,汉人已经逐渐地看重了自身,或者说,是神在为人服务。这里,既充盈着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昭示着人神关系的拉近。
其次,汉郊祀诗中的祥瑞描写歌颂了汉朝统治的符合天意,这使得汉郊祀诗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汉代郊祀歌诗中有一组特殊的作品,它们是《天马》(二首)、《景星》《齐房》《朝陇首》《象载瑜》。这六首作品皆描写汉代祥瑞,天马来归、地出宝鼎、灵芝连叶、狩获白麟、巡得赤雁,随后有文人依事作辞,于郊祀时歌唱。以祥瑞入郊祀诗,并非先秦传统,因此汲黯曾经予以批评:“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8]1178《宋书·乐志》也曾批评曰:“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17]550但武帝丝毫不为所动,个中关键便在于歌咏祥瑞便是歌颂政治。
所谓祥瑞者,是罕见而美好的事物,它连接的是天意与人间。在人们的意识中,天帝、诸神以其无所不能掌管着人间的一切,天意成为人们行事的最高原则。一些具有先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则借天意行己意,把尊天、顺天变成政治统治的借口与工具,天意遂为人所用,具有无上威严的“帝”命、“天”命化身为人间革命与统治具有合理性、神圣性的权威通行证。在如何体现天意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那些难得一见的事物。有些罕见的事物美好而祥和,有些事物却让人心生恐惧,人们赋予前者以美好的寓意,如凤凰、庆云等;而让后者成为灾难、恐惧的象征,比如日食、月食等。人们认为,美好事物即祥瑞的出现是上天对帝王统治的赞成,而灾异现象则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警示。汉代,此说更为盛行,董仲舒将之发展成天人感应之说,汉武帝格外重视天降祥瑞,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支持下,文人们大胆采用祥瑞入诗,并获得了武帝的强力支持。
综合来看,周郊祀诗在贵民观念的影响下更祈求农业丰收统治长久,汉代郊祀诗的“野心”则很大,他们不仅希望上天降下雨露,赐下和平幸福、长生长寿,还要借上天之手,向天下宣告统治的合理与正确,让百姓永远保持敬畏与臣服心理。这其中,既有社会发展状况变化的因素,更是古老的祥瑞观念、天人感应思想在发挥作用。
三、文学书写方式的丰富
虽是祭祀用诗,但周、汉郊祀诗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大雅·云汉》中声嘶力竭式的呼喊,让人动容,《小雅·甫田》描写田妇送饭的场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充满温馨与欢乐;汉诗《天马》描绘天马的飞驰,气势雄壮;元陈绎曾在《诗谱》中评价汉郊祀歌“锻意刻酷,炼字神奇”[18]627,指出其炼字锻意之奇。文学书写虽然是外在形式,但采用何种写作方式、运用何种语言形式,也一定包含了作者的用意,体现出一定的时代写作观念。
(一)从自然书写到丰富意象的使用
周郊祀诗具有自然素朴的特点,其所叙述、描写不过是田间地头、自然风雨、满仓米粮,与农业祈求的祈愿目的相关。作品中的自然事物往往集中于农业主题: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旱既大甚,涤涤山川;……瞻卬昊天,有嚖其星。(《大雅·云汉》)
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各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大雅·生民》)
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周颂·载芟》)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周颂·良耜》)
这里有旱灾时的暑气蒸腾、寸草不生、河流断绝的景象;也有田间劳作、不辞辛劳的耕种情形;还有丰收的场景、百姓的喜悦之情。这一切,都是最为真实自然的场景。
在进行描写时,周郊祀诗往往采用一定的修辞手法来加强表达效果。比如,比喻和夸张等手法,丰富而巧妙。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它可以使所喻之物更加生动可感,具体形象。如《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如茨如梁”比喻曾孙之稼多,“如坻如京”比喻曾孙之庾高,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云:“如梁之梁本应作荆。……茨即蒺藜,系蔓生密集之草,……诗人咏‘曾孙之稼’,以茨之密集与荆之丛生为比,系形容禾稼之多。其言‘曾孙之庾,如坻如京’,系形容庾囤之高。”[19]132-133《大雅·云汉》诗中,“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句,以雷霆比喻旱灾的猛烈可怕,“旱魃为虐,如惔如焚”句,云干旱如火烧,直言旱灾之烈。《周颂·良耜》言其收获之丰,云:“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收获后的粮堆不仅高如城墙,且密如梳齿,后世遂有“栉比”之语。夸张者,指特地言过其实,以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如《周颂·噫嘻》:“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对此,孔颖达疏曰:“各极其望,谓人目之望所见,极于三十。每各极望,则遍及天下矣。三十以极望为言,则‘十千维耦’者,以万为盈数,故举之以言,非谓三十里内有十千人也。”[11]1320方玉润亦云:“窃意,诗言‘三十里’者,一望之地也。言‘十千维耦’者,万众齐心合作也。一以见其人之众,一以见其地之宽,非有成数在其胸中。”[20]599则“三十”与“十千”均为夸张之词。《周颂·丰年》一诗中“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的“万亿”亦为夸张之数。
汉代郊祀诗则化自然景物为特定意象,将丰富的情感包蕴在一定的意象之中。意象,是表意之象,创作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思想包蕴在一定的客观物象之中,客观物象也就凝定成了意象。汉郊祀诗出于歌颂王朝的目的,集中运用了大量的祥瑞意象。这些祥瑞意象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虚写的意象,即在写作的当下并未出现,它们往往是具有固定意义指向的传统意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庆云”“甘雨”“甘露”:
灵之车,结玄云……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练时日》)
神之来,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华烨烨》)
云风雨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惟泰元》)
庆云,又作“景云”“卿云”,是一种预示吉祥、喜气的祥云,《史记·天官书》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喜气也。”[8]1339《列子·汤问》中即有“命宫而总四弦,则景风翔,庆云浮,甘露降,澧泉涌”[21]177之语,用以比喻音乐的超强感染力,渲染喜庆气氛。甘雨即好雨,哺育万物,带来无限生机。
《诗经·小雅·甫田》也曾写到“甘雨”:“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这里的“甘雨”更多地指向自然意义的及时雨,浇灌庄稼,带来丰收。汉代郊祀诗中多次出现的庆云甘雨,则带有了某种象征性意义,即由纯自然物象发展成了意象,象征着神灵到来时的喜庆吉祥。
第二类意象是一组特殊的实物意象—祥瑞之物。这些意象均在汉朝出现,有天马、汗血马、灵芝、赤雁、白麟、宝鼎等。如上文言,人们以天的名义赋予了一些稀见之物特殊的象征含义,在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天马,重在“天马子也”,地位特殊、来源神异;宝鼎则是皇权的象征,黄帝铸三鼎,夏禹铸九鼎,鼎遂成为政权的象征;灵芝、白麟、赤雁皆世所罕见、难得一睹,代表着祥和、仁善、吉祥。众多祥瑞的集中出现,预示着君王拥有仁德、天下大治、顺应天意。这些祥瑞,均摆脱了其自然物种性质而具有象征意义,反观周代郊祀诗,则没有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
意象的运用,代表着抒情的更高阶段。意象往往具有超出表象的深层含义,运用意象往往能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启人深思。就汉代郊祀诗而言,运用意象表达对朝代的赞美,是一种深沉的政治策略和写作策略,在众多“五经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汉代郊祀诗确实含义深刻,艺术效果大增。其郊祀观念非常明确地表现为利用天意、借助意象表达政治观念。周时代的郊祀诗往往更多地描绘自然物象,直接抒发情感,尚处在较为自由的抒情阶段,其背后的郊祀观念表现为朴素生活理想之下的贵生观念。
(二)从四言到三言的诗体范式意义
周、汉郊祀诗为后世郊祀诗确立了诗体范式,其中,汉诗对周诗有继承,又有发展。
周郊祀诗确立了四言体的郊祀诗体例。周郊祀诗以四言为主体,又兼有杂言体。四言诗的节奏是比较稳固的“二、二”组合式,较为单调,缺少变化,但特别宜于配合曲调舒缓、风格庄严典雅的祭祀音乐。韩高年在《诗经四言体成因蠡测》一文中指出:“《诗经》四言诗体的形成,一方面与先秦审美文化崇尚对偶的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早期诗歌,尤其是《诗经》诗篇多为仪式而作或多在仪式场合由打击乐器伴奏而歌的事实相关”,是“周代基于行礼奏乐的现实需要”[22]作出的有意识选择。郊祀诗作为仪式用诗,其风格正如《诗薮》所云:“雅颂宏奥淳深,庄严典则”[23]3,四言体正是郊祀仪式场合用诗的最佳选择。汉郊祀诗继承了由《诗经》开辟的郊祀四言体式,祭五帝的《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等诗采用四言体形式,与之相应的,语言也颇显古雅,情感表达虔诚庄重,是《诗经》以来的雅颂风格。后代郊祀诗也沿续着这一诗体体例,以四言体进行创作,严肃庄重,表现出对祭祀对象的敬重之情。
汉代又增加了三言体的郊祀诗体例。汉代郊祀诗中有八首三言诗,它们是《练时日》《天马》(二首)、《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诗经》中已有三言句,但纯粹的三言诗却是汉朝出现的。诸位学者多认为三言句与“楚辞体”密切相关①对此,清人王先谦认为“兮”字是“班氏例删之文”“班氏删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第487、488页)。后代学者亦多同意此说。萧涤非曾深入研究此现象,他以郊祀《天马》诗与相和歌“楚辞钞”《今有人》为例,认为其系“由于省去楚词《九歌》中《山鬼》、《国殇》等篇句中之‘兮’字而成三言体者”,并且,“据此,则知汉人原有此一种省去‘兮’字以创为三言之办法,且似惯用此办法者。”(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38、39页)张永鑫、郑文等亦认为汉郊祀中三言诗系由骚体例删“兮”字而成。,因而带有楚辞善于抒情的特点。我们看到,凡汉郊祀诗中的三言诗,风格往往较为轻松活泼,这是对楚辞抒情性的继承。细加分析,汉郊祀三言诗具有三个特点:(一)描写祥瑞多用三言体诗,如《天马》:“天马来,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来,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三言诗的节奏较为轻快,突出了天马的英武矫健、充满活力。(二)三言诗往往描写神灵饮酒作乐与民同欢的场面,如《华烨烨》云:“神之揄,临坛宇,九疑宾,夔龙舞。神安坐,翔吉时,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贰觞,福滂洋,迈延长”,把神灵接受祭祀时的安闲、快乐情态呈现于眼前。(三)仪式的起、止两支曲子迎神曲、送神曲均用三言体。《练时日》是迎神曲,《赤蛟》是送神曲,两只曲子一为描写神灵来到人间受祭,一写神灵受祭完心满意足地离开,诗句带有强烈的画面感,神灵形象生动具体。汉代郊祀诗中的三言诗,充满灵动、活泼的描写,与四言体诗迥然不同,更成为后世郊祀诗的创作体式,同样具有典范意义。谢庄在造作宋明堂歌时,特地说明“右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17]569。
我们以隋朝《圜丘歌》为例来看其对四言、三言体郊祀诗的继承:
肃祭典,协良辰。具嘉荐,俟皇臻。礼方成,乐已变。感灵心,回天睠。闢华阙,下乾宫。乘精气,御祥风。望爟火,通田烛。膺介圭,受瑄玉。神之临,庆阴阴。烟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辅。流鸿祚,遍区宇。(《昭夏》)
于穆我君,昭明有融。道济区域,功格玄穹。百神警卫,万国承风。仁深德厚,信洽义丰。明发思政,勤忧在躬。鸿基惟永,福祚长隆。(《皇夏》)
享序洽,祀礼施。神之驾,严将驰。奔精驱,长离耀。牲烟达,洁诚照。腾日驭,鼓电鞭。辞下土,升上玄。瞻寥廓,杳无际。淡群心,留余惠。(《昭夏》)
这三首诗,前后两首《昭夏》分别为迎神诗、送神诗。迎神诗写人间具礼,神灵下降,乘着精气,御着祥风,终于来到人间。送神诗写礼毕后,神将离开,辞下土,升上玄。这两首诗便继承汉郊祀诗,采用三言体写作。神灵的形象较为活泼,写作内容也较为轻松。而歌颂国君的《皇夏》则采用四言形式,语气肯定,稳重平和,是对周郊祀诗四言诗体的继承。对此,胡应麟曾称《诗》《离骚》及汉之《安世》《郊祀》“皆文义蔚然,为万世法”[23]3。
周郊祀诗被视为雅颂文学的源头,被赋予了某种正统意义,引起后世的继承与模仿,其所表现出的以祖配天观念和祈求农业丰收的祭祀目的,体现出周时代的重孝精神与贵生意识。相对于周而言,汉郊祀诗凸显的是政治话语权。神灵被汉人拉平到亲密共处的地位上,祥瑞的吟咏代表着天意的嘉许,这些写作,都深深地刻上了时代观念的烙印。魏晋以后的郊祀诗,在二者的基础上,或承袭、或抛弃,表现出对周汉郊祀诗的强烈接受。从祭祀对象看,后代往往兼取周汉,在诗中兼祭祖、帝。如刘宋的明堂歌辞,既有祭五帝诗,又同时作《歌太祖文皇帝》诗,对本朝的先祖进行歌颂。这是对二者的兼收并蓄。汉郊祀诗中独立而直接描写祥瑞的做法则被后世抛弃。对于此种做法,汲黯、沈约都曾直言不讳加以批评,刘勰更严厉批评祥瑞诗歌:“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3]235,直指祥瑞诗歌非典不经,不合传统,不够典正。正因为如此,后代的郊祀歌诗中极少有专门歌咏祥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