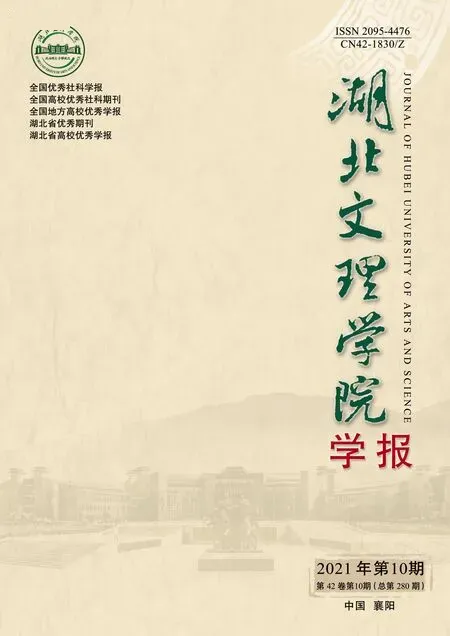楚歌与早期临终诗起源
陈毅超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早期临终诗,是指先秦、秦汉时期出现的临终诗。在文献记载中,先秦时期的临终诗有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孔子的《曳杖歌》、屈原的《怀沙》与荆轲的《易水歌》。然而,先秦时期的临终诗除了屈原的《怀沙》,其他诗歌创作年代的真实性大抵存疑。屈原之《怀沙》,或乃最早之临终诗。考察楚汉时期的临终诗作,其文体形式多为楚歌。因此,不妨假定早期临终诗与楚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早期临终诗创作年代质疑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的临终诗有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孔子的《曳杖歌》、屈原的《怀沙》与荆轲的《易水歌》。然而,《采薇歌》《曳杖歌》《易水歌》皆见于两汉文献而无先秦文献佐证,因而其创作之年代实则相当可疑。
《采薇歌》必然为伪作,《采薇歌》一诗载于《史记·伯夷列传》,然今《史记·伯夷列传》[1]2121-2129实则乃改编自《庄子·让王》或《吕氏春秋·诚廉》。[2-3]该诗“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显是改编自“是推乱以易暴也”的记言文字,因而该诗实际的产生年代应当是汉朝。
荆轲的《易水歌》也殊为可疑,首先《史记·刺客列传》于此处的记载文法颇不通顺: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伉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1]2534
何以“为变徵之声”,又“前而为歌”,最后又“复为羽声伉慨”?若删去中间“又前而为歌曰”部分,则行文将流畅许多,“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与“复为羽声伉慨,士皆瞋目”形成对句,显然更符合作文之法。其次,应劭《风俗通义》引文和《太平御览》引《春秋后语》都未著录此诗,晚唐人陈盖注胡曾《咏史诗·易水》所引《春秋后语》亦无此诗(《春秋后语》乃兼采《战国策》与《史记》而成),而将此诗之出处归于《文选》。[4-6]根据张海明先生的考据,认为《易水歌》一诗乃出自《燕丹子》,只是后人在补佚《史记》之时,将此诗抄入其中,随后又补佚至《战国策》中。因此,《易水歌》也很可能并非先秦时期的诗作。[7]
《曳杖歌》诗载于《史记·孔子世家》[1]1944与《礼记·檀弓上》[8],然其源应出自一处。此段文献显是后学儒生托伪所作,其破绽在其“宗予”二字上。“宗予”二字,似与孔子的自我定位不同——他并不向后世那般将自己视作学派领袖,而是将自己视为卿大夫的一员。因而他在感慨自己的不遇时,大多用的是“用我”而非“宗予”,如《论语·阳货》篇“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9]234又如《论语·子路》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9]174此外,“泰山其颓乎”一句也绝非出自孔丘之口,《论语·八佾》篇便记载孔子不满季氏祭泰山之事[9]31,如何临终时又以“泰山”自比?因此笔者推测,《曳杖歌》及其相关的诗歌背景显是后世儒生为了鼓吹孔子而编造的故事,此诗不大可信。
当然,有关《怀沙》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的认为“怀沙”之义并非朱子所云“怀抱沙石以自沉”之义[10]89,而是怀念长沙的意思[11],有的认为《怀沙》并非绝笔之作[12]。但不管题义如何,是否为绝笔,《怀沙》之中自绝之义显而易见,所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10]89比之其他诗作中的徘徊、疑犹,屈原于《怀沙》中的死志显得极为决绝,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因此《怀沙》应当是屈原的临终之作。换言之,《怀沙》很可能是先秦时期唯一可靠的临终诗,也应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临终诗。以此推之,在先秦时期,唯有楚地出现了临终诗这一特殊的诗歌题材。如此便不得不猜测楚文化与临终诗之间的特殊关系。
二、早期临终诗多为楚歌
如果说先秦时期临终诗的案例太少,不足以说明早期临终诗与楚文化关系的话,屈原之后的临终诗,或能进一步说明早期临终诗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屈原之后的临终诗作,有项羽的《垓下歌》[13]1817、戚夫人的《舂歌》[13]3937、刘友的《幽歌》[13]1989、刘旦之《歌》[13]2757、刘胥之《歌》[13]2762、息夫躬的《绝命辞》[13]2188和刘辩的《悲歌》[14]。其中,项羽的《垓下歌》必然是楚歌,刘旦的《歌》与刘辩的《悲歌》极可能是楚歌——这两首歌完全符合项羽的《垓下歌》及刘邦的《鸿鹄歌》所表现出来的楚歌演唱模式,即独特的“和”歌形式。楚歌的“和”歌与一般的声歌应乐形式不同,乃是先有歌辞,再以舞蹈或诗歌和之,如《项羽本纪》“歌数阕,美人和之”即是此义。[1]333刘辩乃汉末人物,离汉初楚声鼎盛之际时代遥远,然汉宫一向流传着楚乐歌曲,如《房中乐》即是一例(1)《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固至其时,宫廷贵族尚能作楚歌。而戚夫人之《舂歌》,虽难以确证为楚歌,但或许沿用了楚歌声调的形式,《史记》记载戚夫人能以楚舞和楚歌[1]2047,想必对楚文化有相当的了解。而息夫躬所作之《绝命辞》为骚体诗,虽非楚歌,但和楚辞有密切的关系,乃是楚辞在汉代的变种文体。换言之,早期之临终诗,大多与楚地诗歌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是汉代的临终赋,亦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如贾谊自以为将死而作的《鹏鸟赋》[1]2492-2495,其文体形式也继承自楚赋。
除了形式上的继承,汉宫中的临终诗在情感内容方面也颇类楚歌。早期临终诗与魏晋、南朝时期的临终诗有着完全不同的抒情逻辑。魏晋时期的临终诗有着鲜明的“自反”意识——如嵇康自叹“曰余不敏,好善闇人”[15],欧阳建自悔“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16];而南朝的临终诗则往往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通过佛道诸如“轮回”“尸解”等观念以宽慰自身的死亡恐惧。(2)如谢灵运《临终诗》:“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又如顾欢《临终诗》:“五途无恒宅。三清有常舍。”陶弘景《告游篇》:“冠剑空衣影。镳辔乃仙身。”等等。换言之,深沉的思考是魏晋南朝临终诗的一大特质。早期临终诗则不然,其情感吐露方式表现出直截朴素的特点:“哀”与“怨”乃是临终诗最为主要的情感要素。这种抒情方式实与屈原《离骚》《九章》作品的抒情方式不谋而合,这也揭示了早期临终诗和楚歌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西汉中前期宫廷临终诗的大量涌现极可能是楚歌在汉宫中继续发展的自然结果。初期的西汉王朝与楚文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首先刘邦本人即是楚人,且对于楚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爱好,《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乐楚声。”[13]1043刘邦能楚歌,亦能楚舞,史书记载他过沛时“上乃起舞,忼慨伤怀”[13]74其次,从政治上讲,在秦末的“反秦”斗争中,“张楚”是一个重要的旗帜,陈胜举事之时,便“号为张楚”[1]1950-1952,此后反秦义军更是尊楚怀王为义帝;此外,楚歌是一种更具民俗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因而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接纳和喜爱。因此,自楚歌被刘邦带入深宫之后,便受到诸多统治者的青睐,如汉武帝便令刘安作《离骚传》,章帝时九江被公也因“能为楚辞”而被“召见诵读”[13]2821。而自汉中期以后,宫廷之中文风渐变,宣帝之子元帝酷爱儒风。考虑到经学家对辞赋文学的负面态度(3)《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武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楚文化的遗产自然难以受到同等的重视,固自宣帝以后,汉宫临终诗的数量骤减,这无疑也从反面论证了楚歌与早期临终诗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楚招魂巫辞与临终自悼传统
若要洞察诗歌的文化背景,则需对其所蕴含的思想观念进行追溯。考察早期临终诗的产生,则可通过历史上士人生死观的变迁进行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大抵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主体的毁灭而感到的恐惧;一方面是对超验的不可知而感到的恐惧。为了平息这两方面的恐惧,原始宗教往往奉行灵魂不灭的观念,并对死后世界进行一系列具体的想象。自礼乐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系统的主流文化后,人们的生死观念就转向理性化,因而鬼神话题实际上也成为士人阐释现实人事的一环,如《左传·昭公七年》所记之子产说鬼一事,将鬼的产生解释为人灵魂的强大,而判断灵魂强大的依据乃是“其族又大,所凭厚矣。”[17]680-681显是以鬼事说人事。在这种生死观念的环境下,比之生死,中原士大夫无疑更注重政治声名的存毁,或者说,他们看重政治生命远超生理生命,即平子所谓“生死而肉骨”。[17]771所以,中原士大夫往往将死后世界看作是尘世的一种延续或翻版,在那里,那些士人可以依靠子孙后代的祭祀享受生前的地位,如《哀成叔鼎铭》所说:“死于下土,以事康公。”[18]即是此义。在这种生死观的引导下,极少士人会有“临终自悼”之举——在他们的临终仪式中,嘱托与训诫方是他们更为重要的活动。
然楚地则不同。楚文化更多得保留了殷商时期的重巫传统,从而导致当地的文化风俗与中原地区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比之中原模糊的死后世界,楚歌辞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更加具体,也显得更加阴森恐怖:
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恐自遗灾些。[10]129-140
从《楚辞·招魂》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楚地文化的死亡观包含相当强烈的“地狱”意识。所谓“地狱”意识,就是认为人在死后,其灵魂将会受到折磨。因此,生者需要通过一系列巫术手段以救济灵魂,这便是“招魂”。中原地区亦有招魂之习俗,然与楚地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原招魂之辞简练朴实,一般只唤“皋某复”则罢,而如《招魂》《大招》所记之辞则显得繁复神秘;其次,中原“招魂”之仪式乃是确定死者已死,如招魂之后“复而不苏”,就正式启动下葬仪式;而《招魂》中所反映出来的招魂仪式,乃是在死者已死后召唤亡灵,希望通过巫术仪式以救济死者的灵魂。[19]换言之,比之中原文化对于鬼神的尊敬和远离,楚地文化对于鬼神表现出一种同情的态度。此外,在《招魂》《大招》之中,明显表现出对招魂仪式的夸耀:如通过宫室、酒肉、美女、音乐等等事物以引诱死者“反故居”[10]129-140,突出地反映了楚文化鲜明的“娱鬼”特点。这种通过招魂仪式完成对亡灵救济的风俗,实质上构成了楚文化临终自悼行为的文化、心理原型。
这种心理在汉代的临终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汉代的宫廷临终诗表现出对死后世界的恐惧,如刘胥临终歌所说的“黄泉下兮幽深”[13]2762,又如刘辩所说之“逝将去汝兮适幽玄”[14],显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地狱”意识;此外,汉代临终诗包含着直白而又沉痛的自哀色彩,如刘友,为自己“为王饿死”[1]403-404的结局愤愤不平,向上天大声诅咒吕氏,刘辩则直呼“天道易兮我何艰”[14]——这是楚地招魂诗对死者同情的一种另类表现,原本对亡者的同情转向了自身,从而使得“哀悼”转变为“自哀”;最后,临终诗本身的文体形式便反映了楚地文化对临终自悼这一行为产生的塑造作用。以诗自哀,实是楚人以歌娱鬼的一种变体形式——在《楚辞·九歌》中,有相当多通过表现鬼神之哀戚以娱神的作品,而临终者将其同情的对象由神转向我,将其娱神的诗辞用以自宽,这便形成了临终诗的文体形式。换言之,临终诗的创作本身,或者说临终自悼行为的施行,便是临终者通过情绪宣泄,以完成自我宽解的一种形式——它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脱落了巫术色彩的自我救济。
总而言之,楚文化的“地狱意识”构成了临终诗写作的重要动力——死亡恐惧;而楚文化的招魂巫辞则为临终自悼行为提供了原始模板——通过一定的言辞以实现对某灵魂的救济。
四、楚歌与早期临终诗的出现
如《诗大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本是一种抒情文体,然而当特定的诗歌固定为一种言辞范本后,它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在《诗经》中,不乏充满抒情色彩的诗歌,然而在它被乐官所采,进入官方的礼乐系统后,它的抒情特点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孔子所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173《诗经》中的诗辞,在春秋战国时期常被用于外交场合,这在推广诗歌传播的同时,却也损害了诗歌的文学性——实用功能的过度膨胀,往往使诗歌的抒情功能受到削弱。到了西汉,对《诗经》的曲解更甚,经学家们往往抛弃诗歌自身的诗意和情感,转而去寻求其可被附会的历史典故和道德范畴。这不仅使得《诗经》中的诗歌失去艺术生命力,也使得四言诗这种文体逐渐僵化——如韦孟、韦玄成之诗,通篇劝诫,了无新意,完全背离了诗这种文体原初的审美要求。
然而人们抒发自我情感的心理需求依然存在,因此各地的谣曲成为了人们表达自我情感的一种文体形式。谣曲的优势在于,它没有“交接邻国”,“称《诗》以谕其志”[13]1755-1756的职能,此外,它们的创作极其自由。早期诗歌多为声诗,如《诗经》中的“雅”“颂”,皆配乐而作,甚至来说,早期儒生的观念中,“乐”的意义是高于词的,《论语·子罕》篇记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18-119又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9]210-212配乐的需求固然保证了诗歌创作的音乐性和艺术水准,但也限制了人们表达自我情感的自由度。谣曲则不然,《释乐》云:“徒歌谓之谣。”[20]这些谣曲往往即兴而作、随声而发。如《侏儒诵》:“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朱使我败于邾。”[17]502然而应当指出,这些各地的谣曲由于缺乏文人的关注和参与,整体来看创作水平不高,思想内容较为平庸。若要真正将一种地方性的歌曲艺术升华为一种足以替代传统四言诗的抒情工具,还有赖文学家的参与和改造。
在屈原之前,楚歌仍然保持在一种较为原始状态,从《楚辞·九歌》中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楚歌在战国中后期仍未完全脱去其巫歌的色彩。大抵是在屈原开始,楚歌才开始突破其固有形态,成为一种更贴近人事的诗歌形式:首先,屈原改造了楚歌原有的巫术色彩,将其衍化为一种对文学性的隐喻和象征,如《九歌·少司命》中“荷衣兮蕙带”[10]41之语,本是指神人的服饰,而在《离骚》中,其“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10]14,则将“荷衣”转化为一种道德修养的象征;其次,屈原改变了楚歌固有的人神结构,而缔造出全新的主体与客体——君臣。如《山鬼》,通过爱情的象征手法表现唤神仪式,而到了《离骚》中,屈原则将这种妇女之心疾用于表现贬臣之失意;最后,屈原改变了楚辞创作的目的,将其与祭祀仪式解绑,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抒情文体。在《九歌》中,其诗皆表现的是祭祀仪式的场景,其题名即为祭祀的对象或是祭祀的仪式;而在《离骚》与《九章》中,诗歌的意旨皆在表达诗人自我内心之情感,并不涉及鬼事。此外,这种解绑进一步改变了楚歌的演唱方式,使其成为一种无需配乐配舞的徒歌,乃至不遵乐律的徒诗、徒赋。《九歌》中的篇章,大多是配乐演唱,如《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10]32,《东君》“縆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10]42,而至《离骚》则不然:从其文章篇幅来看,很难想象这是一篇足以配乐的诗章,且其各节之间用韵极为松散灵活,字格不一,无法看出所遵循的统一韵律,似不大可能配乐演唱。在屈原改造楚歌之后,楚歌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抒情文体——从淮北到川蜀,楚歌遍布。然而,这只能说明普遍意义上楚歌与早期抒情诗歌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具体地说明楚歌与早期临终诗之间的关系。
更能反映楚歌与早期临终诗之间关系的,乃是二者情感基调的高度一致。与“雅”“颂”端庄的诗风不同,楚歌的基本情调是哀。虽然《楚辞》作品的哀伤特征与屈原的诗风有很大的关系,但应当指出,“哀”乃是楚歌创作固有之传统,它们在唤神时,往往以恋人之间的离愁代指。又如宋玉,他其实是一位颇具诙谐特色的作家,可他的《九辨》[10]126-127,亦包含有浓郁的哀情成分,乃至到了秦末汉初,楚歌中的悲歌色彩依然存在——如项羽之《垓下歌》、刘邦之《鸿鹄歌》,都显得壮丽凄美——就是如《大风歌》这般激昂壮阔的诗歌,其末尾也难免“安得猛将兮守四方”[1]389的感慨。到了汉代,人们在继承楚歌传统时,也认识到了其“悲歌”的文体特征,因此在拟作之时,往往叙怨抒哀、一顾九叹,甚至本无哀思,却强作悲辞。而两汉宫廷之人亦深受此影响,以致于他们在内心郁积之时,难免以楚歌吐露心中悲凄。最为直接的证据乃是刘旦之歌,据《汉书》记载,其谋反事发后,自歌曰:
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13]2757
其文辞与一般的临终诗颇不类,似未明说诗人将死之意。但根据其妃华容夫人之“和”,我们便可以明白这首诗的意思:
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13]2757
这几句显然并不指临终之事,而意在勾勒一幅因战争或疫病造成“国人”大规模死亡的画面。可见,这首诗乃是“悼亡诗”或“国殇诗”,并非刘旦自作之临终诗。刘旦此处引用此诗,乃是借用此诗中的悲伤情绪。这种“引用”很能说明早期临终诗的起源与楚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总而言之,不管是楚歌的悲歌传统,还是其较为自由的文体形式,都为早期临终诗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合适的诗体。
“人为何会临终赋诗”是临终诗研究的一个根本话题,然而从传统中原文化的礼乐思想中,我们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从早期礼乐文化所塑造的生死观念来看,死亡恐惧在士人心中并没有多少分量,因而很少为自我死亡作出艺术性的描写和注解;其次,春秋战国时期《诗经》所载之“诗”表现出实用功能膨胀、抒情功能弱化的倾向,因而这一时地的诗歌难以孕育出临终自悼的题材。然而,汉代宫廷突然涌现的大量临终诗必然有其可追溯的文化根源,因此不妨从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楚文化中去寻找其得以孕育的土壤。事实上,楚文化重巫风俗所孕育出的“地狱意识”及其一贯的悲歌传统,确实为早期临终诗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文化原型。首先,死亡恐惧使得“临终赋诗”这一行为具备了心理动力;其次,楚歌又为临终诗提供了合适的文体形式。因此到了汉代,随着宫廷动乱的频繁发生,一大批宫廷临终诗孕育而生,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颇为特殊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