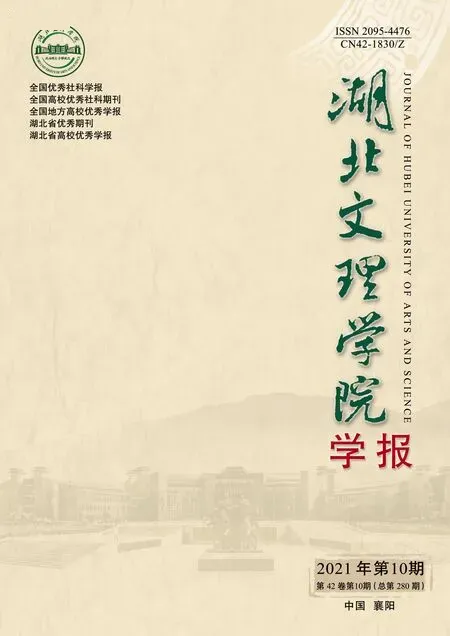襄阳三国地名文化的复杂性及其独特价值(下)
王前程,谭 颖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三
地名伴随着人类活动而产生,是人类足迹和思维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战争频发、群雄纷争的乱世,三国地名与遗迹是汉末三国乱世历史的一种特殊记忆,从中能分明感受到三国英雄的豪情壮志和普通百姓的爱憎情感。复杂多样的襄阳三国地名与遗迹正是这一特殊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反映了襄阳地区在汉末三国时期的特殊地位
襄阳原本为楚国北津戍,乃一处军事城堡,汉初始设县,故改称北津戍城为襄阳城,但两汉时期襄阳只不过是荆州南郡一个边鄙小县。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豪强各自为政,肆意杀伐。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长沙太守孙坚杀死荆州刺史王叡,多地郡守、县令拥兵作乱。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两年后为荆州牧),联合蔡瑁、蒯良、蒯越等襄阳豪族势力,文武兼用,恩威并举,很快便平定了荆州地区的乱局,并以其过人睿智将荆州州治迁至襄阳,襄阳始以一个边鄙军事小镇一举成为富裕大州州治之城。毫无疑问,作为名震天下的鄂北重镇,襄阳的发展始于刘表时期,从襄阳古城、荆州街、荆州古治、呼鹰台等荆襄英雄地名与遗迹中不难看到刘表等人在襄阳发展史上的开创性作用。
更重要的是,刘表坐镇襄阳经营荆州近二十年,形成了一个“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趾,年谷独登,兵人差全”[12]1435的一方乐土,与中原地区频繁战乱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的悲惨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清平安宁、沃野千里的荆州便吸引了大批逸士俊才云集襄阳,隆中、鱼梁洲、司马德操宅、徐庶宅、崔州平宅、庞士元宅、仲宣楼等三国地名与遗迹集中表现了汉末名士俊逸寓居襄阳的盛况。这些名士俊逸寓居襄阳不仅仅是为了逃避战乱或放浪形骸,他们都是极富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战略家,静观时势变化、审慎思考问题是他们隐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故而当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便为蜀汉集团呈献了思考成熟的三分天下的宏伟蓝图:“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接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4]678后来庞统也向刘备提出了“权借益州”的鼎足之计。由此可见,诸葛亮《隆中对策》既是他个人思虑已久的立国之策,也是云集襄阳的英才们共同研讨认为切实可行的战略方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国争霸历史的起点实质上始于襄阳。
事实上,不仅诸葛亮等蜀汉英雄将襄阳选定为日后北伐中原的前沿基地,魏、晋、吴各方军事家们也无不将襄阳视为北伐或南征的战略支点与战略要塞。曹操南下荆州首先重兵威逼攻占的便是樊城、襄阳城,攻占襄阳地区后立刻分南郡北部别立襄阳郡。赤壁之战受挫后,曹操命令曹仁、乐进、徐晃等名将驻守荆襄地区,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宁可放弃江陵,也决不放弃襄阳,曹魏名将们也充分认识到襄阳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三国志·满宠传》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蜀将关羽借助洪水向襄阳城、樊城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樊城危在旦夕,部属多建议主将曹仁弃城全身,副将满宠则坚决反对:“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4]538曹仁在满宠的支持下死守樊城、襄阳城不退,直至徐晃援军到来,最终成功地挫败了关羽占领襄阳、建立北伐基地的战略企图。从曹仁擂鼓台、东冈、庞德墓等地名与遗迹中不难感受到当年曹魏名将们死战到底、决不后退的战斗风采。吴国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后,亦多次发起襄阳袭击战,试图将襄阳城变成北伐前沿,陈邵、陆逊、诸葛瑾等吴国名将均涉足襄阳,但都遭到魏军强力反击而失败。司马氏代魏之后,依旧高度重视经营襄阳郡,始终将荆州都督府设在襄阳城,羊祜、杜预等晋初名将均长期坐镇襄阳,并缜密制定和实施了规模宏大的灭吴之战的战略方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晋南征灭吴、统一天下的步伐亦始于襄阳。
襄阳地处汉水之滨,是中原地区与南方荆州重要的交接点,汉末三国时期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天下俊士文豪云集之地,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大量的复杂多样的三国地名故事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襄阳的辉煌历史和特殊地位。
(二)反映了中国传统忠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建安六年(201年),刘备集团在汝南之战中遭到曹操重创,被迫南下荆州依附刘表,奉命镇守襄阳北大门新野县(今河南新野县)。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降曹,刘备集团被迫撤至江夏郡。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据荆州大部郡县,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伺机北取襄阳郡,但襄阳郡始终控制在曹魏集团手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率部进攻樊城,水淹七军,围困曹仁,声震华夏,但数月之后在吕蒙偷袭江陵和徐晃救援樊城之下土崩瓦解,从此蜀汉集团再也没有涉足襄阳。也就是说,蜀汉英雄们在襄阳地界有过八年左右的活动经历,而从未真正控制过襄阳,远远比不上刘表集团统治襄阳二十年、魏晋英雄经营襄阳七十年的深厚根基。
然而,与大多数地区三国地名文化的情形相似,襄阳境内亦以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占比最大,民间百姓最津津乐道的依然是蜀汉英雄们的行踪和故事。这并非因为蜀汉英雄们给予了襄阳百姓巨大的恩惠,而是因为中国传统忠义思想长期浸润尤其是宋元以来忠义思潮盛行的深刻影响所致。六朝隋唐时期,三国故事开始传诵于民间,而蜀汉君臣形象最符合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的标准,民间日渐形成推重蜀汉君臣的倾向。到了两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频繁侵扰,终致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在宋元外敌侵凌、民族式微的背景下,社会普遍涌动着一股人心思汉、救亡图存的忠义思潮。于是,在三国故事流传和三国文学创作过程中,人们将忠义著称的刘备君臣视为汉民族的象征,而将曹操等人影射为北方强权统治者,将孙权等人视为背弃盟友的卑劣小人,形成了一种“拥刘反曹贬孙”的思想倾向。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北宋说书艺人说三国故事时融入了十分明显的主观情感倾向,令少年儿童们“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13]7关汉卿《单刀会》杂剧再三强调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渲染蜀汉英雄们坚守忠孝节义思想的自豪感,叙述关羽训斥鲁肃道:“俺哥哥合承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着:百忙里称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种强调汉家正统、大张忠义精神的文化思潮一直延续至元末明初,无疑对小说《三国演义》的成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作家罗贯中笔下,吴魏英雄在品德上多有缺失或不突出,蜀汉英雄们则是传统仁义道德和民族气节的象征,尤以诸葛亮、关羽为最杰出的代表。
而《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功,又反过来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明清时期的审美风尚,广大民众和士人阶层以传扬蜀汉英雄功业、歌颂蜀汉英雄品德为美,地名故事中多附会蜀汉英雄正是这种审美风尚的反映。如前文所述,襄阳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数量最多,但虚构性强,附会成分明显。如关羽的帽子不会化成山丘,张飞的丈八蛇矛不会将山腰捅个无底洞,白云也不会因赵子龙插旗而涌出等等,这只是后世襄阳百姓为了纪念心目中道德高尚的英雄们而杜撰附会出来的故事而已,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社会民众对于传统忠义精神的充分肯定和赞美。
(三)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德治的充分肯定
襄阳三国地名与遗迹中,并非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一家独大,荆襄英雄地名与遗迹、魏晋英雄地名与遗迹亦颇引人注意。无论是史学家陈寿,还是小说家罗贯中,对于刘表的评价都不高。《三国志·刘表传》认为刘表缺乏远大志向和博大胸襟:“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4]160又说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4]163将刘表视为同袁绍一样的无能者。然而,刘表自幼尚儒,遵守中庸之道,积极推行仁政。初至襄阳征询治理荆州之策,襄阳名士蒯良主张行“仁义之道”,刘表欣然接受。在坐镇襄阳统治荆州近二十年中,刘表打击豪强,安定地方,广招儒士,开办学校,惠及荆州百姓。《后汉书·刘表传》载曰:“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安民养士,从容自保。”[12]1637又载:“在荆几二十年,家无余积。”[12]1639刘表在争霸天下的乱世中固然缺乏英雄才略,但广行仁政德治,善待百姓,蓄养士人,使荆州成为乱世中的“王道乐土”,而自己则为人清廉,不敛资财,无论是个人品德,还是政风政绩,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以刘表为核心的荆襄英雄地名故事流传至今,正是千百年来襄阳人民对于刘表的肯定和赞许。
作为蜀汉集团的对立面,曹魏人物在《三国演义》中屡遭谴责,但曹操亦广行德政,在中原百姓中颇有声誉,而且曹操善于笼络人心,善于使用英才,具有非凡的政治胸襟和人格魅力,对此罗贯中又给予了充分肯定。曹仁以忠勇著称,庞德以气节闻名,小说同样给予了赞美。故而,襄阳三国地名文化中亦不乏曹魏英雄的身影。
对于通过强权和杀戮建立起来的司马氏政权,后世士人和广大民众普遍无好感。然而,襄阳百姓对于羊祜、杜预两位坐镇襄阳的西晋官员却敬爱有加。《晋书·羊祜传》记载了“堕泪碑”的来历:“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宇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8]667襄阳百姓何以对羊祜有如此深厚情感为其病逝而落泪呢?原因很简单,就是羊祜是广行善德仁政的楷模:“(羊祜)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8]662-663“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8]666如此有德量有政绩的仁者,死后连敌方将士为之哭泣,更何况他治下的百姓呢!作为羊祜的继任者,杜预同样推行德政,关注民生疾苦,在忙于战争筹划中亦不忘发展经济,惠及民众。《晋书·杜预传》载:“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8]673正是由于羊祜、杜预重视百姓生存问题,广行仁政,故而襄阳百姓自发为他们建造祠堂,岁岁奉祀其英灵。尽管襄阳境内有关羊祜、杜预的地名故事占比不大,但都充满着浓烈的敬爱之情,充分表现了古代襄阳人民对于仁政德治的渴望和肯定。
总之,三国地名故事是三国历史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记录,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价值。大量的襄阳三国地名与遗迹故事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汉末三国英雄的足迹行踪,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襄阳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真实地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人心所向,对于中国传统忠义精神的歌颂和对于仁政理想的肯定,正是襄阳三国地名文化的独特价值所在。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