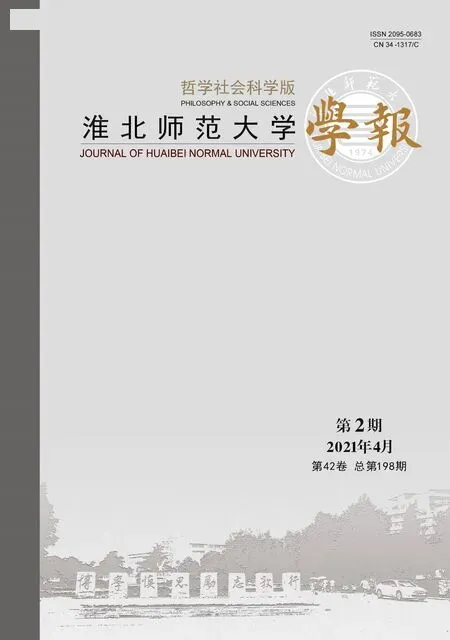拉什迪的家园书写与文化身份
刘苏周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是饮誉英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先后创作了《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羞耻》(Shame,1983)、《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愤怒》(Fury,2001)、《弗洛伦萨的女巫》(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2008)等长篇小说十余部、短篇小说集2 部、随笔集3 部。1981 年获得“布克奖”后,又相继斩获“卡佛文学奖”“安徒生文学奖”等国际文学奖项,引起世界瞩目。迄今为止,其作品被翻译为多种文字,不仅赢得世界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成为新时期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论及拉什迪作品中的家(园)和身份主题。管笑笑(2010)分析了《午夜之子》中的人物流散经历和碎片化叙事技巧,认为拉什迪通过书写试图实现完整自身历史、回归家园的愿望。苏忱(2014)则认为,《午夜之子》的叙事手法和描摹中所蕴含的“异域情调”不可避免地使印度(家园)书写成了西方读者的消费对象。郑婕(2017)则聚焦拉什迪在短篇故事集《东方,西方》中对东/西二分法的质疑,从地点流动性、语言模糊性和叙事混杂性三个层面探讨了作家对“无家”状态的拥抱。本文侧重从拉什迪的身份追寻、混杂家园叙事和流动家园观的维度审视拉什迪的家园和文化身份主题,以期更好理解作家对新时期移民个体文化身份的重新思考和再定位。
家园历来是文学作品的母题。它不仅可以指代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如一间房子、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也是指代一个情感意义上的存在,如愉快或悲伤的记忆、亲密的家庭关系,更是让人有安慰、舒适感、归属感以及伙伴的共同体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家园总是与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现实中的家园会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二战”后,随着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各种原因漂泊在世界各地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家园概念被彻底解构,并在新的时空中得以重构,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一方面,移民在内心里会排斥家园的改变,并借助各种方式努力弥合业已出现裂痕的家园;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书写的方式在心中重构一个完整的“想象的家园”,并以此应对因身份迷失所导致的心理焦虑以及文化认同危机。因此,移民的家园书写与流散个体的身份重新定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作为一位大半生混迹于西方社会的印度裔英国移民作家,拉什迪的流散经历和去国状态让他不仅时刻回望业已逝去的老家印度,而且无数次地审视着自己所置身的新家——英国和美国,并试图在比较中重新建构理想的“想象家园”。换言之,拉什迪通过家园书写不仅思考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移民和发展等问题,还试图努力追寻着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身份归属问题:我是谁?
一、寻求身份的家园回归
从拉什迪的迁徙路径和创作实践来看,跨国界、跨文化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错位和文化认同危机,共同推动了拉什迪寻求身份的家园回归之旅。
拉什迪出生于印度孟买,并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然而,从14 岁前往英国伦敦求学之日起,他便过着一种“候鸟般”的生活:先是在毕业后随家人搬迁到巴基斯坦,后孤身返回伦敦并加入英国国籍,新千年后又移居美国。这种身体上的不断移位,不仅开启了拉什迪的流散旅程,也同时也开启了他“几分普鲁斯特式”(Somewhat Proustian)的追忆之旅。于是,拉什迪凭借着对故乡支离破碎的记忆,通过文字的方式述说着自己的想象家园。
从1970 年代起,拉什迪曾先后多次携妻儿重游印度孟买。在《想象的家园》中,拉什迪曾详细记录了自己的一次归家之旅:
几年前,我曾回到孟买——它曾占去了我生命的一半,而我却失去了它。刚到不久,我信手翻开电话簿,居然在上面找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多令人惊讶,那上面竟然还有他的名字,有我们家的老地址,甚至电话号码,仿佛我们从来没有搬往边界那边那个无名之国(巴基斯坦)去似的。这是一个奇异的发现,它仿佛是在告诉我,我远方的生活不过是幻象,而这种延续才是唯一的真实……[1]10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什迪的归家算得上一次重新发现之旅,不仅试图重新找回自己失落的时光,寻求对过去和记忆的所有权,更意在重新获得身份上的认同。只不过,拉什迪知道,尽管故乡一切如旧,但这种真实的存在只不过是幻象罢了。因为自从他踏上异国求学之旅起,尤其是父亲举家迁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那个心爱的家园了。同时,拉什迪也清楚地意识到,“像我一样流亡在外,异地漂流,没有国家的作家,都会被一种失落感纠缠……远离印度造成的最深层的不确定感,意味着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丧失了那些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再也没有完璧归赵的可能性了。”[1]10很明显,拉什迪归家之旅后的内心是失落的。对他来说,造成这种“失落感”和“不确定感”的原因不仅仅有时光的流逝,更有地理、文化空间的阻隔和错位(dislocation)。换言之,拉什迪所经历的跨国界、跨文化的生活不断地加深他的身份错位意识和文化认同危机,让他在东西方之间、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无所适从,不知所归。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身份往往与其出生地、语言、家庭和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它不会突然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基本上是单一的、固定的。但在后殖民时代,当移民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异质文化时,他们的传统身份和文化的连贯性开始被打破,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定位(relocation):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米兰·昆德拉曾将移民作家划分为三类:一是无法融入移居地主流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隔离感和孤独感;二是融入移居地主流文化,却有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三是彻底融入移居地主流文化,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之根。不过,拉什迪似乎很难被归入任何一种。他是一位双重移民作家:一方面,他虽出生于印度,却并不属于印度主流社会的印度教教徒,而是一个穆斯林;虽然他后来随家人搬迁到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巴基斯坦,却又因难以忍受那里压抑的政治氛围,很快便离开那里,加入英国国籍,后又移居美国。另一方面,拉什迪虽然接受了南亚次大陆传统文化的熏陶,却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留学后更是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可以说,拉什迪就像一个无根的浮萍一样,始终漂浮在两种文化、四个地理空间之上。然而,不论是以印巴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还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都无法单独获得拉什迪的完全认同。换言之,拉什迪注定只能置身于这样一个由不同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的中间地带,这同样也注定他只能拥有一个“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暧昧身份。一般说来,这种含混不清的身份定位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和焦虑,很容易让移民(作家)产生一种去国离家的怀旧和乡愁、异国他乡的孤独和异化、文化认同的焦虑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拉什迪对于故乡的记忆开始变得扭曲。他既不能像普鲁斯特那样追忆“流逝的年华”,又不得不面对去国离家带来的这种空间错位(displacement)。这就难怪他不无慨叹地说:“过去方是我的家园,即便那是一个已经失落在时间迷雾和失落城市之中的失落的家园”[1]9。从拉什迪连用的三个“失落”(lost)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流散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强烈错位感,也容易理解拉什迪为何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虚构一块可供立足的土地,以便可以展开自己精神上的家园回归了。
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拉什迪不论身处何地,始终在作品中不时回望故乡印度,并将其作为他刻画的所在地的参照系。可以说,印度不仅仅是拉什迪地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苦心经营的文化家园。问题是,拉什迪是如何通过小说来描写那个失去的家园和逝去的岁月呢?
二、立足“边界”的家园书写
尽管拉什迪与大多数流散作家一样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但不同的是,他并未过多地纠结于由此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反而认为,移民所经历的时间、空间和语言的多重错位让他摆脱了传统民族主义等力量的控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让他们可以同时看到“里面”和“外面”。在《想象的家园》一文中,拉什迪这样写道:
我们现在部分属于西方,我们的身份是多重而不完整的。有时我们会觉得横跨两种文化,有时,我们又坐在两个凳子之间。尽管这地方暧昧而游离不定,但对占据此地的作家来说,倒是一块肥沃之地。假如文学部分的存在是要寻找穿透现实的新视角,那么又一次,我们的背井离乡和由此而得的远大地理视野,应当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角度和视界。[1]15
基于上述认识,拉什迪创造性地提出了“边界书写”(border writing)概念。所谓“边界写作”,顾名思义就是指作家立足于多元文化的边缘,以一种单一民族文化作家所不具有的、更为宽广的移民文化视角,来观察并书写宗主国或母国的一切。在拉什迪看来,与基于单一的文化视角下的写作不同的是,“边界写作”推崇的是“混杂性、非纯洁性、杂糅性,是源自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之间新的、意想不到的混合所产生的变形”[1]394。换言之,混杂性是拉什迪边界书写的最大的新颖之处。基于此,拉什迪开启了一系列独特的混杂式家园书写。
首先,拉什迪笔下的家园是一个时空混杂的场域。一方面,拉什迪的小说多以印度为故事背景,却时常游走于东西方世界之间。受萨义德的影响,他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不是独立单纯的,而是杂交的、混合的,继而他力图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基本范式,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构建出一个界限模糊的中间地带——“间质空间”(liminal space)。因此,拉什迪笔下的故乡印度(孟买)则完全成了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城市,一个“此人会‘渗透’进彼人,此文化会‘渗透’进彼文化”[2]14的现代化城市。同样,在短篇小说集《东方,西方》中,广场上的印度男孩唱着美国流行歌曲哄着小女孩,而印度的外交官则沉迷在“星际迷航”的白日梦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拉什迪的小说虽说建立在印度历史的基础上,却又远超历史小说的范畴,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小说《午夜之子》的主人公萨利姆是印度独立时午夜出生的孩子之一。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他不仅目睹了印度独立后的社会动荡,更通过追忆的方式讲述了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同时,他还故意偏离线性时间轨道,频繁穿梭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小说《弗洛伦萨的女巫》先从充满神秘色彩的印度首府斯格里(Sikri)开篇,旋即又将读者引向欧洲开往印度的海盗船。其间,故事更是频繁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印度的阿巴克王朝宫廷和意大利的弗洛伦萨,游弋于过去和现在之中。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印度家园在拉什迪的故事中被解构了,不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地点,而成了一个东西方文化混杂的中间地带。
其次,拉什迪笔下的家园人物大都是东西方文化的“杂种”。鉴于拉什迪的流散经历和双重文化身份,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大都或多或少带有他本人的“自白”色彩,如《午夜之子》中的混血儿萨利姆、《撒旦诗篇》中发生变形的吉百列和萨拉丁、《弗洛伦萨的女巫》中寄居异乡的印度公主卡拉·阔兹等等。这些人都是东西方文化杂交的产物,其经历、身份和心理的混杂性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拉什迪家园书写的混杂性。
《午夜之子》中的萨利姆是印度低种姓流浪艺人的妻子和英国殖民者私通的杂种。萨利姆长着东方人的耳朵、西方人的头发,从小生活在养父母的穆斯林家庭,却又深受信奉基督教的印度奶妈的熏陶,这让他的文化身份变得异常混杂。小说一开始,萨利姆就通过对外公阿齐兹生存困境的描写,展开了对身份问题的思考。阿齐兹从小生活在克什米尔,经常着迷于老艄公泰讲述的印度神话和魔幻故事。在他的记忆中,故乡克什米尔曾经是人间天堂。那里风景秀丽,一派平和的景象:“万物气象一新。经过一冬的孕育,山谷已自寒冰破壳而出,变得开放、湿润、鹅黄。嫩草在地底下静候时机;山峦撤向温暖季节的避暑地……”[3]4而从德国留学归来后,经历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他明显嗅到了故乡克什米尔“改变的气息”[3]6:那里不仅失去了原初的宁静和秀美,反倒是显得有几分狭仄和压抑,就连他自己也成了乡亲们眼中的公敌。更为糟糕的是,阿齐兹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体内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无法填补的“大洞”。为了弥补这个因丧失信仰之后宗教文化身份的缺失所造成的黑洞,他娶了一位传统印度的年轻姑娘娜芯·甘尼(Naseem Ghani),却发现此后的家庭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换言之,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和西方文明的入侵,阿齐兹心目中传统的印度家园不可避免地变得支离破碎了。
相类似的是,《撒旦诗篇》开篇以魔幻的手法讲述了印度移民吉百列·法瑞希塔和萨拉丁·查姆恰空难后在当代英国的蜕变、重生的经历。他们都尽力想修复各自过去的生活,试图寻求新的文化认同和混杂状态下宜居的想象家园,却在经历孤独、异化、疏离等痛苦之后,彻底迷失了自我。为了去除自身的“印度性”(Indianess),建构自己的“英国性”(Britaness),萨拉丁砍倒父亲为他栽种的胡桃树——一株代表着孩子的童年和印度传统生活方式,更是“保存孩子灵魂”[2]56的生命之树,并将自己具有印度特色的名字萨拉胡丁·查姆恰瓦拉(Salahuddin Chamchawala)改成更符合英语发音习惯的名字萨拉丁·查姆恰(Saladin Chamcha)。砍树和更名之举不但意味着他斩断了自己与印度历史、文化的联系,也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家园。因此,当萨拉丁再次回到故乡时,不自觉地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审视、抱怨印度故乡的一切:“吊扇没有牢牢固定在屋顶上……食物太油腻……顶楼阳台不安全,油漆也剥落了……花园中植物也长得太过茂盛……看看我们的电影是多么没水平……疾病那么多,水龙头出来的水也不能喝……”[2]37-38在这个过程中,萨拉丁放弃了自我,否定了自身,主体性被蒙蔽,也必然会落入“若即若离的困境”之中。
再次,拉什迪还编织了家园的混杂叙事空间。如果说时空混杂的家园及家园中的文化“杂种”为拉什迪的“想象的家园”建构提供了便利的话,那么混杂叙事空间则让他得以自如地游走于东西方文化的“间质空间”。作为一个叙事大师,拉什迪并未照搬殖民文学的范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通过“重写和反写”的方式,将东西方的文学经典——《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项狄传》等——“互文性地编织进自己的文本中,使作品在重写羊皮纸(palimpsest)上呈现流动的叙事空间”[4]83。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印度史诗的挪用。一方面,拉什迪延续了史诗的口头叙事传统,让萨利姆充当一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一家三代人的经历。另一方面,他充分利用史诗的容纳空间,将萨利姆的“个人历史”与印度独立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官方历史”杂糅在一起,成就了一部“滑稽体史诗”(comic epic)。这里的“滑稽体”指的是拉什迪所采用的碎片化、脱离中心的叙述方式,它“符合了西方后现代所谓的开放的、不确定文本的说法,表现的是支离破碎的历史”[5]28。拉什迪认为,历史正如一面映射已逝岁月的镜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镜子中的一切变得不再清晰,因此,对家园的书写也只能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而萨利姆对自己“在场”和“不在场”的历史书写,也只能依靠他个人的记忆和想象展现出来。于是,萨利姆的主观感受和碎片化回忆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混杂在一起,展现了一个虚实难辨的叙事空间。
此外,拉什迪还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将想象与事实、魔幻与现实杂糅在一起,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譬如,《午夜之子》中的1001 个孩子个个天赋异禀——变身、飞行、预言、使魔法等,似乎象征了独立后印度家园建设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撒旦诗篇》中的移民吉百列和萨拉丁在经历空难后,前者成了头带光环的天使,后者则变形成了头上长角、脚趾分成两半羊蹄的魔鬼;而《羞耻》中的苏菲亚更是变形为“人面狮身”的复仇怪兽……凡此种种,不仅让拉什迪巧妙地为读者呈现了印度次大陆家园光怪陆离的历史和社会,也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拉什迪的“边界书写”策略成功地为其塑造了混杂的印度家园,也让他在借助传统口语叙事传统的同时,兼容并蓄了魔幻现实主义、蒙太奇等叙事手法,彻底跨越了二元模式之间的界限,实现了他解构并重新书写印度家国历史,构建一个种族混杂、文化多元的理想家园的夙愿。
三、超越家园的文化身份
在小说《羞耻》中,拉什迪曾这样写道:移民最大的劣势是“空荡的行李箱”。这里的“行李箱”显然并非那种“装几件意义被抽干的纪念品”的“有形的、也许是纸板的”行李箱,而是移民随身携带的那只“看不见的文化行李箱”[6]71。与所有的移民知识分子一样,拉什迪对故乡印度充满了爱恋,并以一个游子的身份对印度家园展开深情书写。不同的是,拉什迪的家园情结显然并非早期移民作家笔下浓浓的“乡愁”,而是一种对印度瑰丽文化的热爱和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罪行的憎恶相交织、混杂的复杂情感。更为重要的是,拉什迪认为家园绝非某个固定的场所,而应该是一个动态建构的空间,是考察“所居之地”文化、政治、宗教以及流散个体的身份定位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场域。换言之,拉什迪秉持一种流动的家园观,其“行李箱”中所装纳的文化内容已不是区域性,而是多元化、全球性的了。
很明显,拉什迪的流动家园观超越了民族主义对家园(包括民族与国家)的狭隘理解,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诠释20世纪中后期乃至新千年的移民“新”家园。在他看来,如果国籍或者护照并不足以定义一个人身份的话,那么,出生地或者居住地同样也不能简单地用来确定一个人的家园。一方面,“传统的家园/故国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抽象符号,而是充满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与‘世界性’密切粘连着、互动着、协商着、碰撞着”[7]30。当移民的文化和地理等空间发生多重错位时,他们需要不断根据这一新的语境,对家园进行持续的、重新的定义。另一方面,拉什迪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对家园的理解始终持续保持一种开放的、不确定性(unstuckness)的状态。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早期移民所经历的跨国度、跨语言、跨文化的体验已然变得司空见惯。新时期的流散者可以自由频繁出入家园,并逐渐摆脱“处处是家,无处是家园”的窘境。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凄凉无助已渐渐淡化,更多地是以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视野审视故园、批判故园、反思人性、表达人性”[7]30。相比奈保尔笔下“家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移民个体悲观的异化而言,拉什迪则是以一个更加积极的精神对待后殖民语境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即家可以是任何地方。换言之,在拉什迪对家园的思考中,或许“哪里不是我的家”比“哪里是我的家”更具有现实和形而上的意义。
在散文集《想象的家园》和小说《羞耻》等作品中,拉什迪还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被翻译过的人”(a translated man)。他这样写道:“从词源上讲,‘翻译’一词来自拉丁语translatio,意思是导向彼方。出身跨界(being borne across)的我们因而是被翻译过的人。一般说来,在翻译过程中,总会失去一些东西;不过,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能获得一些东西。”[1]17
在桑加(Jaina Sanga)看来,拉什迪所说的“翻译”其实是“一个使用语言对已经形成的文化、社会、政治意识模式进行再创造和重新建构的过程”[8]48。它已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字、文本间的跨语转换,而是更多地指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它除了带来语言的变化、地域的变化和文学样式的变化之外,还带来了文化和人的变化。它让移民作家在跨文化的同时,也让他们把“被殖民主义扯碎的世界再次拼拢起来,把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连接起来”。同时,这种文化翻译的经验“不仅能刺激发明的灵感,而且也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去观察作家‘老家’所在国的情况。再说,‘出身跨界’能为那些‘出了国的作家提供素材’,这种素材‘能赋予他们那个完全脱节的世界以想象的形式’”[9]276。更重要的是,拉什迪强调的并不是失去的东西——印度文化,而是获得的东西——通过西方文化而使印度文化得以重生……拉什迪变成了两种文化的翻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移民个体的文化身份已经“不属于任何已有的存在,而是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10]203-204于是,这位“被翻译过的”拉什迪开始通过自己的小说来寻找“如何衔接他抵达的不同世界”,探索“如何将这些世界连接起来——不仅仅是东方如何流入西方,以及西方如何流入东方;而且是过去如何塑造现在,现在如何改变对过去的理解;以及想象的世界……是如何渗透过将其分离的边界的”[11]68-69。换言之,拉什迪决定立足于自己混杂的移民体验和双重边缘“他者”的混杂身份定位,利用边界书写的优势,在作品中宣扬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构建“既在内又在外”的差异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拉什迪流动家园观的形成除了与其一生不断迁徙的经历密切相关外,还源自他对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和本土世界主义理念的推崇。巴巴将流散者置身其中的那个由不同文化冲突、交融的和抵抗的空间称作“第三空间”,认为身处其中的文化主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自我”文化的束缚困境,抵制“他者”文化的压制。同时,在自我和他者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主体最终形成了混杂的文化身份。此外,巴巴还据此提出了他的本土世界主义思想,认为如果两种异质文化能够抛弃各自不平等的权利地位的影响,就能够化解矛盾冲突,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在《愤怒》《弗洛伦萨的女巫》等后期作品中,拉什迪不再只是将目光聚焦于印度次大陆,而是将视野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对“无家性(homelessness)”理念和世界主义理想的关注。《愤怒》中的主人公索兰卡虽然远离了故乡孟买,却不再纠结于对旧家园的追忆,不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世界公民,探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和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如种族歧视、恐怖主义等。而《弗洛伦萨的女巫》中的主人公摩格与卡拉虽处于异域文化中,却试图跨越文化和种族的藩篱。同时,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宗教文化宽容的莫卧儿王朝阿克巴时代,在一定意义上蕴含了拉什迪为本土世界主义寻找的历史参照。或许,在拉什迪看来,唯有基于“第三空间”建立的想象家园方是移民(作家)“安全的身体栖居之地和心灵皈依之所”[12]86。
面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大趋势,如何有效解决因不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观念、身份认同等原因所导致的各种冲突和碰撞,促进各层面的融合与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通过立足“双重边界”的家园书写和流动家园观的建构,拉什迪在作品中不仅成功地超越了以“乡愁”为主题的传统家园书写模式,而且将落脚点放在新时期移民群体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的重构上,并凭借他丰富的想象、混杂的叙事技巧及对本土世界主义哲理性思考,在东西方的中间地带打造了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家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