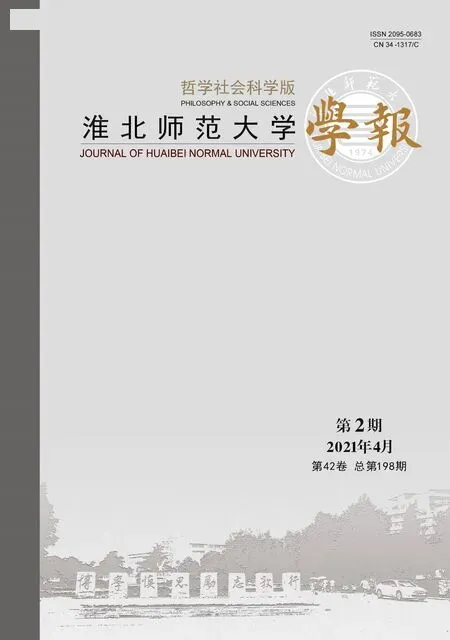文以传意:范晔“类传”思想论析
——以《后汉书·皇后纪》为中心
郭海涛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127)
《后汉书》是记录中国东汉时期史事的一部断代纪传体史书。范晔不仅在宏观结构上对《史记》《汉书》中“书”“志”等撰史体例进行继承与借鉴,且在具体的微观细节里,以“纪”“传”的论赞等形式,承沿和发挥着司马迁、班固著史的“正统”①关于班固儒家正统思想,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以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被削去为例进行说明,后杜维运在《中国史学史》中沿加肯定。笔者这里援引前人论断,将它引入到整个“纪”设定中。(详见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7页。)立场与史观。正因为范氏对马班开创的中国传统史学的良好承续,后世认为“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1]28。故而,它在成书后的流传中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并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自《后汉书》成书之后,不乏前辈学者对它展开过研究,除侧重文本的辑佚校注研究外(如惠栋《后汉书补注》、王先谦《后汉书集释》等),对《后汉书》内容的考察和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历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如刘知幾描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而已”[2]343,由此可见范书流传之广和影响之大。然而刘氏本人对范晔及《后汉书》评价并不高,其在“二体”“六家”分析中并未将《后汉书》与同体例的《史记》《汉书》对等看待,反而认为“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2]87。刘氏以为,范晔以文采代替史才的做法不仅和“自谓无惭良直”的说法不符,其本质实是“朱紫不别,秽莫大焉”[2]116。后来宋代学者基本沿袭了刘氏的说法,对范书多有批评。特别是对范晔自视甚高的赞语,反而认为那是“赞辞佻巧,失史之体云”[3]180。亦如陈振孙甚至评价说“自今观之,几于赘矣”[4]98。无论如何,范书自唐以后便成为记录东汉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而后人的评价也从整体议论转向具体的文本分析。如清人赵翼总结范书的体例组织思想是“各以类相从”[5]80。但这种议论侧重的是对文本内容的归纳,而对分类背后的思想原则缺乏足够的思考。近现代以来学者更侧重从史学史的角度考量范书的历史价值,如瞿林东先生总结范书类传设置时便强调范晔在“揭示东汉政治得失方面,在称颂历史人物的才行方面,在关注世风治道方面,都反映了著者的积极的思想旨趣”[6]70。现代学者也有专门对《后汉书》某一类传进行总结概括的学术成果,但是于史学史宏观考察时疏于分析类传演变前因后果,而单传的解读也割裂了类传设置中作者的总体思路和学术倾向。例如《皇后纪》在多种史学史的专著中都有提及,且一般都将它归纳到范氏反对“外戚”干政的史学思想中,但文本具体如何体现这种思想并不明确。至于专文类传研究则对《皇后纪》多有忽略。本文试以《皇后纪》为考察中心,辅以范书其他“纪”“传”,总结类传名目增删变化背后的原因,以窥范晔的历史撰述旨趣。
一、类传“旧”例中的范晔“新”意
通过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书的宏观体例对比分析可知,范著中明显存在着对前人经验成果的继承。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继承性将范书与马班史学相比较,不仅仅是因为三人所撰作品在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承接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纪传体例在马班开创和完善后,“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3。即后来中国传统史家的撰述,基本没有脱离马班所设定的基本框架,以范氏与司马迁、班固比较是对前者史学撰述体例溯源性的考察,并非以此忽略二家外的史学著作对范氏的影响。范晔虽然以东汉一代为限,撰述断代史以接续班固《汉书》,而他本人生活的南朝宋时,在他之前已有官方机构和学者私人撰述过东汉历史。据瞿林东先生以王仲荦先生考据资料所制“诸家东汉史撰述表”[7]74来看,在范晔之前已有东汉史书11种共946卷(含2种编年体60 卷)。范晔写作时可借鉴的既有成果可谓十分丰富(但如今这些书籍大多已佚),而这与前文所说“皇后纪”问题的关联十分密切。
清代史学名家赵翼对范晔创设“皇后纪”的做法颇有微词,“《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5]3。赵氏一方面认为范氏的做法是仿效马班而来,另一方面对此“冗余”做法颇不以为然,而赵氏的说法正是传统史家批评范氏史学的一个代表性意见。回顾《史记》《汉书》中所设“高后纪”,司马迁与班固同为女主设“本纪”的做法,其背后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史记》言“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8]1,故所谓“天子称本纪”[8]1。结合司马迁在帝王“本纪”中的具体做法和刘知幾“系日月以成岁时”的总结来看,“纪”是以君主事迹与纪年相融合的写作形式。但司马氏《吕太后本纪》却并非纪年性作品,其内容只是对吕后主要生平事迹的梳理和总结。这与其他帝纪中严格的以帝事纪年的撰述形式相比,《吕太后本纪》只能算作传了,因为“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5]4。而《汉书》中《高后纪》的撰述形式,已经完全与诸帝本纪相同。如果说司马迁在纪传体史书的草创中对类传的设立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那么班固的《汉书》则正式使纪传体的形式得以完善和确立。但是,在较为完善并可供借鉴的前例情况下,《后汉书》不仅为皇后全体设“纪”,在内容上更是以列传的形式进行撰述,最后自然招致“纪名传体,所以成嗤”①《史通·卷二·列传》,第47页。刘氏此句本是针对《史记》中项羽被撰入“本纪”的批评,原文是:“《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笔者认为这与将皇后传设为纪体所招致的批评相类似,因为刘氏认为“案范晔《汉书》纪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纪名传体”这种针对名实不符情况批评同样可以应用于此,所以笔者将它加以沿用。的批评。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批评并不赞同。“世讥范蔚宗创《皇后纪》,非也。《晋书》称华峤作《后汉书》九十七卷,有《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改《皇后纪》,次《帝纪》之下。然则皇后之纪,乃峤自出新意,蔚宗特因之不改尔”[9]195。华氏《后汉书》今已亡佚不存,无法比较两书。但钱大昕通过考证《后汉书》中的《皇后纪》并非是范晔的创造,侧面说明了是范氏借鉴华峤同名著作的结果。这样虽然为范晔洗脱了首创名实不副类传的罪名,反映出范晔史学中的继承因素,但范氏“特因之不改”的态度和做法,更是显著地表明范氏要借此新传表达特殊的意涵。
二、文以传意的范晔史观
前文已提及《后汉书》对马班史学纪传体例的继承,但是范晔本人并不是将纪传类目视为不可逾越的规定性模式。范晔自称“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精思,未有此也。”[10]1831在范晔看来,纪传本身只是记录或叙述历史大事的一种方式而已,将大概情况记录清楚即可。但包含在大略记录中的“诸细意”更值得注意,即内容撰述背后的思想才最具重视价值。与司马迁和班固的纪传编排相比,“《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5]7。而班固在对《史记》体制进行改进后,“确立起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11]222。所谓“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12]50。《汉书》体制整齐且叙事详明,范晔也承认自己“博赡不可及”。但在自谦之后,他更加强调文辞背后所表达的主旨的重要性。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讬,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10]1830在范氏看来,撰述不能仅是文辞优美和详实便可称善,特别是撰述的主旨常常被文辞自身所束缚,因辞害义,所以在文与意的关系当中要以“意”即所要表达的思想为主。这里所指的文已不只是文章,它包含了史书的撰述。由此便可理解范书《皇后纪》没有因循《汉书》纪传体例的做法,实是作者出于对“意”的重视和追求。因而“皇后纪”设立的“诸多细意”,不只是窥见范晔史学思想的重要线索,也是范氏史学新见的突出表现。
(一)“正统”观下的贯古通今思想
前文已言,自司马迁至班固对帝后单独设纪的做法,以及“后纪”形式与内容的演变,不仅突显了史家对“直书”原则的追求,也反映了汉代以后史学中“正统”思想的兴起。从范书将“皇后纪”厕列帝后的做法与“名纪体传”的实际内容来看,范晔史学思想中的“正统”观念非常浓厚,这与是书所设其它列传可以相互印证。但是,蕴含在《皇后纪》中的“细意”并不仅是一点“正统”观而已。仅如此便没有将“皇后”这个群体设纪的必要,这样反而更符合班固所确立起的严格整齐的纪传体例。对于这种在既有史书体例中的创新①虽然范晔“皇后纪”的设立是借鉴华峤《后汉书》而来,但华书早佚,华、范二书之间有多少重合部分已经不可知。且自范书以后,后世史著再没有“皇后纪”的设立。而历代学者在史学评论涉及纪传体例问题时多以范书为援比对象,因而笔者在此将范晔此举认为是一种在纪传体内的创新。,范晔表达出的历史认识和史学思想非常明显。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诸侯僭纵,轨制无章。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冢嗣遘屯。爰逮战国,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弛防,先色后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前史载之详矣。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向使国设外戚之禁,编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贻厥方来,岂不休哉!虽御己有度,而防闲未笃,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13]397-400
在《皇后纪》序论中,时间跨度上自三代,下及前朝。范晔的叙述不只关注作为帝王正位配偶职权的演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叙述中将王朝的兴衰和女主联系起来。对比《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高后纪》,以及《汉书·元后传》可知,司马氏与班固二书都只是个人的列传或编年大事记,对于“皇后”这个群体本身并没有关注。但是范晔不仅将此群体设为一“纪”,更是从古今历史沿革的视角中,考察和审视这一群体的由来和变化,体现了范晔贯通古今的史学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和历史认识并非是范晔作此纪的根本目的,即范氏“纪”中的“细意”并非止于此。根据引文所见,范氏在强调君王身边女性地位变化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她们职权的扩大趋势和对政治的影响力度。序言所举多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政治产生重大消极影响的女性,而通过对女性地位升降的变化和干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描述,表明范氏蕴含在《皇后纪》的“细意”是对东汉政治从清明走向混乱、直至灭亡的系统、整体性反思。
(二)明辨是非的“自得”史见
东汉冲帝继位时,“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冲帝寻崩,复立质帝,犹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劳,推心杖贤,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务崇节俭。其贪叨罪慝,多见诛废。分兵讨伐,群寇消夷。故海内肃然,宗庙以宁。而兄大将军冀鸩杀质帝,专权暴滥,忌害忠良,数以邪说疑误太后,遂立桓帝而诛李固。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宠,以此天下失望。”[13]439-440这里,范晔明确肯定了梁皇后主持朝政时对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安宁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范晔也指出梁氏用人的缺陷,以及外戚梁冀残暴的行径对东汉政治运行的巨大破坏,这种对历史人物功过区分对待的撰述,是范晔辩证史学思想的表现。桓帝时期,“后借姊兄荫势,恣极奢靡,……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13]444结果后宫之内的倾轧争权,直接导致了帝王的子嗣“倾宫虽积,皇身靡续”[13]321,朝局自然向着“主少母壮”的外戚掌权局面演进。范晔以敏锐的眼光和细腻的笔法,在东汉帝王“本纪”与《皇后纪》这两种不同的纪传之间,构建起了一条明晰的朝政兴衰因果关系线,并藉此对东汉一代政治发展情形,作了既全而微的梳理。此后“太后临朝定策,立解犊亭侯宏,是为灵帝。……及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何太后临朝,重与太后兄大将军进权势相害,后每欲参干政事,太后辄相禁塞。……太后临朝。后兄大将军进欲诛宦官,反为所害……并州牧董卓被征,将兵入洛阳,陵虐朝庭,遂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13]445-450范晔通过对后宫女主的纪传勾勒出东汉后期政治兴衰更迭的整个过程。他不仅从侧面补充了帝王本纪中所无的东汉后期君主册立的细节,同时也指出了在君主、外戚、宦官、朝臣等多方势力斗争下,东汉政治日趋没落的原因和演进路线。
“坤惟厚载,阴正乎内,……身当隆极,族渐河润。乘刚多阻,行地必顺。咎集骄满,福协贞信。庆延自己,祸成谁衅。”[13]456范晔在总结帝后职权时,特别强调女主作为帝王辅助身份的重要性。他反复劝喻帝后在自身因德行或姿色获得尊位,并延及家族恩荣时,更应警戒慎重。而屡见于后宫的刚强、骄纵是祸乱的开端,这一切都是源于自身而不要归咎别人。至于外戚,“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13]2253,如果能“中于道则易以兴政,乖于务则难乎御物。……况乃倾侧孽臣,传宠凶嗣,以致破家伤国,而岂徒然哉!”[13]1187外戚本具备强大的政治优势,如果能秉持公正、节励自身,则能兴助政治。如若不然,则是夷族灭家,甚至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破坏。范晔在整个“皇后纪”中始终将外戚势力的兴衰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起来,以此说明东汉一代政治中“外戚”地位是何等重要,同时也在警觉后世要以此为鉴。在这整个论述过程中,范晔并没有片面强调外戚对政事的破坏作用,即未将东汉后期政事的颓败完全归结于外戚一身。同时,他纵观整个东汉历史,甚至上溯三代以来的过往旧事,明确认为对外戚的合理支持与外戚的襄赞之功,是王朝保持清明稳定的重要助力。这既是范晔纪传所要表达的“诸多细意”之一,也是范晔“以文传意”,即“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10]1831的“自得”史见。
三、以史为鉴的著作意旨
(一)整体、系统的治乱反思视野
东汉自光武帝建国,经明、章二帝主政,政治较为清明。范晔在明帝纪中特别强调说:“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13]124所谓“建武制度”,即是光武帝所定的治国政策,这当中包括对后宫女性德行的高度要求和对其权力的严格限制。而后“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13]400。根据前文所言,明帝所矫弊端正是“外姻乱邦之迹”[13]399,而记录馆陶公主的例子正是来说明君主对此严加防范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但自章帝之后,政局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自和帝幼年继位,太后临朝至其弟窦宪被杀,皇帝本人是在外戚失势之后始得以亲政。后来殇帝夭折,“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13]203,而“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13]243。范晔总结安帝时期的政治认为,安帝虽然享有天子名号,但是君权实际掌握在邓太后手中。并且进一步强调,这种后宫即女主掌权的局面是导致东汉政治衰败的开始。他引用《尚书·牧誓》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典故,评论女主政治对东汉清明政治的巨大破坏。“论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懑,悬书于象魏。借之仪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衰斁之来,兹焉有征。”[13]430在范晔看来,邓太后以女主身份把持朝政,帝王空有名分,而失权势诱发君主心生怨愤。这种怨愤情绪,在帝王亲政后演化成滥杀贤臣、亲近小人的局面,政事也因此从清明向混乱转变,进而引发王朝走向衰败、崩溃。在这整个王朝兴衰的因果关系分析中,范晔认为“皇后”临朝称制是这种衰亡的初因和标志。但需要注意的是,范晔对于东汉政治兴衰的把握不只是将女主即“皇后”视作唯一的因素。《后汉书》中范晔是将它与“外戚”“宦官”联系起来同时作为重点加以考察,反映了范氏整体、系统审视历史的史学思想和广袤的历史视野。
所谓“外戚”,一般是特指中国传统帝制中君主母系亲属的统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8]2387据此可知,司马迁曾在《史记》中特设《外戚世家》以记录吕后以来多位皇后事迹,并以君主专制下特殊的内宫职位皇后、太后,概论“外戚”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针对女主与外戚对王朝政治不利影响的分析,司马迁以汉武帝故事作出了自己的评论:“‘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8]2408据《谥法》,“武”字虽然有多重含义,但司马氏这里强调的是汉武帝在临终前为昭帝解决了“主少母壮”的不利局面,是对武帝这一做法所示“远见”的高度肯定。而这一“远见”所代表的“为后世计虑”,便是避免了昭帝年幼继位后,主母所代表的外戚对朝局的控制及引发的动荡。司马迁亦因此认为武帝配得起“克定祸乱曰武”的赞誉。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女主、外戚的政治破坏力十分警觉。但由于他本人生活年代的限制,武帝之后的政治发展情形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史记》除了通过独列“吕太后本纪”来强调女主和外戚对政治的影响外,“外戚世家”更多是从福祸由来的角度强调安守本分的作用。①司马迁在《自序》中明言外戚特别是女主的安分与否和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因此作《外戚世家》的动因。即所谓“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適代,厥崇诸窦。栗姬偩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详见《史记》,第4017页。)但在《汉书》中,过往一代历史已经可以被整体地思考与总结。因而班固在延续设置“外戚传”的基础上,“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呜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14]4011班固总结西汉一代帝后及其家族兴衰的历史,强调了外戚招致祸乱过程中的自身因素,对于前者与王朝兴衰的关系虽有涉及但不够重视。“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5]67但正是在此残酷的历史事实面前,《后汉书》却并没有延续前史设立“外戚传”的做法,而是直接删削了这一传目。详考《后汉书》所设类传体例,范氏这种做法不仅不是他对东汉社会及政治考察的缺失,反而可以认为这是在避免传目设置程式化的一种创新,以及在此背后追求“正一代得失”的“自得”的史学思想与撰述旨趣。
(二)“正一代得失”的撰述旨趣
前言马班设立“外戚传”以记录一代女主及其家族兴衰,并以此间接表达对“外戚”扰乱政治和祸及自身的思考,提示后来者对“外戚”保持重视和警觉。但是,相比较只有“吕后”单独设纪的特例,司马迁与班固对“外戚”重要性的认识并未和历史发展的实情相一致。因而虽然整个西汉历史受外戚影响巨大,但二者仍然将外戚视作帝王的补充,进而将其设在“纪”下之“传”。这一方面是受正统思想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马班史学对王朝兴亡认识存在不足的反映。与此二家不同的是,范晔将“皇后”设纪,并以这个职位背后的整个东汉帝后群体作为“纪”主进行叙评。因而“外戚传”已经被“皇后纪”所代替,所以没有重复设置的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范晔将“外戚”对历史的影响上升到了与同朝帝王相近的地位。结合范晔撰述中“诸多细意”,可知“皇后纪”的设立,是他以史论“正一代得失”[10]1831旨趣的突出表现。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辀继路。而赴蹈不息,燋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13]401
据范氏自叙可知,《皇后纪》写作的目的是“以缵西京《外戚》”,即继续《汉书》设立“外戚传”的写作传统。但在《皇后纪》序论中,范晔更为明确地指出“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这一深刻的历史认识,并且以四帝六主的实例强调东汉王朝遭遇这种危机的严重性。在此之外,范晔更进一步强调女主临朝背后实际是政权“委事父兄”的局面,并进而引发外戚通过册立幼主以达到长久执政和罢黜贤明来扩张自身威势的目的。国事因此糜烂不堪,而外戚自身同样在权势更迭后遭受灭亡之祸,最终是“陵夷大运,沧亡神宝”,整个国家政权由此衰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范晔并不是笼统、含混地将“外戚”视作东汉政权兴衰变化的一种缘由。他是从东汉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与整体性两个方面,“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例如光武帝管戒后宫甚严,所以“郭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13]402,后弟“(郭)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13]402。“后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13]406。明帝“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13]400,而马皇后“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毘补,而未尝以家私干”[13]410。后来马氏成为太后,以“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的理由,“削去兄防参医药事”[13]410,其后“(章)帝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13]411这里范氏所列举的东汉初的数位皇后、太后,都以其自身的政治修养,极力避免自己背后外戚与朝政的牵连,并多以慈俭率领群伦,裨益政事。此外,在范氏的记录中,东汉初的数位后宫之主,亦自以前朝外戚擅权酿祸为戒,极力将自己与娘家亲属防避在朝政核心之外。正如明帝皇后马氏所言,“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13]411,而后宫亦常念“倾覆之祸”。如此帝、后合力对外戚的压制,东汉初才未延续前朝外戚乱政之弊,而此一时期也是范氏所认为的东汉最兴盛、清明的时期。但自东汉章帝以后,君主对后宫的控防松弛。后主也在政局中逐渐握权,不断加大自身对朝局的影响,但结果却是政事逐渐走向浊乱和崩溃。
所谓“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13]400,因而“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13]415,“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兄宪,弟笃、景,并显贵,擅威权,后遂密谋不轨,永元四年,发觉被诛。”[13]416“自窦宪诛后,帝躬亲万机。……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更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13]194-195东汉社会自光武至和帝时期的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安定。但至“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衰斁之来,兹焉有征。”[13]430东汉和帝之后,国家的发展势头开始由进而退,而后宫邓太后长期把持朝政被范晔视作这一衰退趋势的表征和直接原因。此后“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13]243即自东汉第五位君主孝安帝以后,帝后及其亲属把持朝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如宫内“后专房妒忌,……遂鸩杀李氏”[13]435,即后宫内的争权邀宠已经不惜代价和手段。安帝暴崩,阎后为了控权更是秘不发丧。其后“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兄弟权要,威福自由。”[13]436-437从后宫宠爱之争,延及帝王的生死和外朝最高权力的全面更迭。外戚的这种强势导致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反倒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即如顺帝在帝后争斗中,曾一度成功击败阎太后一系的外戚集团。但顺帝亲政后的数年不但未能一改前朝弊政,反而多有承袭,以至于范晔嗟叹“何其效僻之多与”[13]274。可见外戚对政局影响的程度之深,亦见范晔欲借史事表达的“正一代得失”的旨趣之重。
四、余论
综合上文所述,从《后汉书》对纪传体例的承袭情况可知,范晔的历史撰述曾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除形式上的撰述体例外,内在思想上范氏同样延续着马班史学以来的“正统观”。但作为一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杰作,《后汉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在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其作为“正史”流传至今的重要依据。从《皇后纪》的设置即可看出,范氏一方面在形式体例上,依据现实的历史情况,对现有史著的体例作出变更与创新。另一方面,范氏的这种创新做法,蕴含了其本人独特的史学思想,即《后汉书》的“类传”设置背后是范氏对历史发展的自我认识,以及对著史与史著二者关系的重新思考。正如范氏自己对《后汉书》价值的高度自信,其信心来源于书中“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10]1831质言之,即相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草创与完善贡献,范晔并不满足于史学的“博赡”特征与“整理”性质,他所追求的是在纪传“举其大略”之外,“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即通过形式变化与论赞评述表达文字之外的撰述旨趣。故而他自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10]1830,最终回归于“正一代得失”。范晔打破常规将东汉一代“皇后”这个特殊群体与帝王并列设“纪”,并以此代替以往的“外戚传”,一方面是范氏以外在体例的迥异凸显对东汉“皇后”群体实际政治影响力的重视,另一方面显示出他对“外戚”集团膨胀与东汉政治兴衰关联极其密切的深刻历史认识。因而在帝后纪论赞中,范晔几次将“女主临朝”视作东汉历史发展的转折。范晔从“皇后”这一特殊职位和群体出发,将女性以及外戚个人的内在品德修养与权力集团的利弊影响,同国家的兴衰更迭联系起来,辩证地看待多种因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展现出他作为史学家对历史问题的辩证分析能力,同时也反映出对历史发展的深刻认识能力与著史的客观精神。“通观其帝纪后论,则清晰地揭示了东汉皇朝从中兴走向衰亡的几个转折,堪称卓识。”[15]
当然,《后汉书》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远远不是纪传体例变革与“皇后纪”一传的分析所能尽览。以《后汉书》类传设置为例,范晔便在班固与司马迁的基础上新设七种类传,特别是在以《皇后纪》替代《外戚传》之外,范晔新设《宦者列传》《党锢列传》以补充对东汉政治发展的考察。“东汉政权腐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外戚、宦官擅权使政治更加昏暗。……而和帝以后,朝廷上和宫闱内演出的一幕接一幕的外戚、宦官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则直接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16]883-884,这也是范晔总结东汉衰亡时所言“东都缘阉尹倾国”[13]2537的佐证。此外,对与“外戚”“宦官”正面直接对抗的朝野政治势力,范晔新设《党锢列传》予以褒奖。这不仅是与另一新设《独行列传》同样表彰气节,同时也是对展现东汉中期以后政治斗争激烈的全面补充。范晔通过“皇后”“宦者”“独行”等新类传的设置以及传文中的“诸多细意”,对东汉一代兴亡的历史作出了深刻的思考,表现了范氏本人整体、全面的历史认识。而他“‘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既是史家作史的目的,更是史家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17]后世学者批评马班之后,史著失去著述本义,撰述“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薄书”[12]52。但从范晔著述《后汉书》的情况来看,他能在史学已有体例中“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据,而后能起迄自如”[12]52,甚至将“诸多细意”蕴含到撰述当中,突显出范书以“资考证”与“得其是非”[18]397的重要史学价值。以此观之,范晔有意通过“称情狂言”,以匡正世人在史著中“贵古贱今”的偏颇倾向,其做法确实称得上苦心孤诣。而通过探析其新设《皇后纪》中所蕴藏的诸多“细意”,则更能体会到范氏史学的“体大而思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