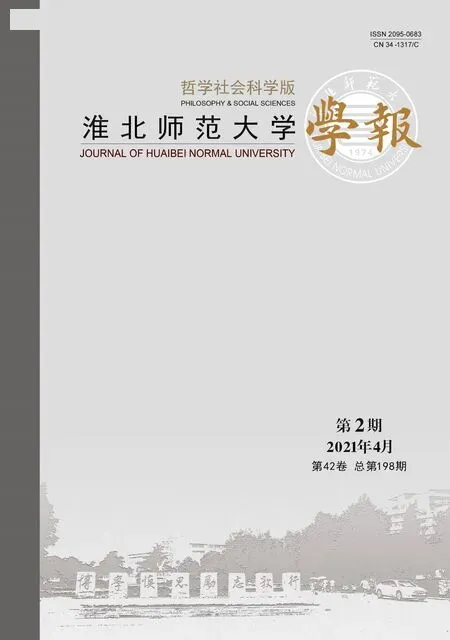贾而任侠:明清徽商精神气质的另面
张浩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安徽 合肥231131)
中国传统社会“贱商”“抑商”,在“士农工商”社会排序中,商人被排在“四民”之末,被视为鄙陋猥琐、唯利是图的“市井小人”。明朝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型,商业的重要性与商人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写道,“……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1]。在贾与儒的频繁互动与融合中,“贾为厚利,儒为名高”[2]卷五十二,“士商异术而同志”[3]的观念深入人心,士商阶层不再壁垒森严,逐渐走向合流,商人阶层也逐步跻身于社会的主流阶层。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的著名商帮,他们人数众多、经营广泛,资财雄厚,创造了称雄商界三百年而不衰的商业神话。在社会生活与商业活动中,徽商一直以“贾而好儒”著称于世,除此之外,他们身上还有“豪侠不羁”“尚气任侠”的另面。他们虽为商贾,身上却兼具“儒”和“侠”的双重品格,呈现出不同于先辈的商人儒侠形象。目前,就徽商人文内涵方面,学界讨论最多的是其“贾而好儒”的特征,对其“任侠”的气质特征所论相对较少,一些学者也有涉及①详见杨瑾.儒侠互济的徽人精神——浅论汪道昆《太函集》中的士商形象[J].鸡西大学学报,2011(2):113-115;连启元.儒商之外:从汪道昆《儒侠传》看徽商“侠”的精神[C].中国明史学会编.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349-356.,如杨瑾关注到汪道昆在《太函集》中为徽人作传时,对“儒侠”精神的突出,认为“儒侠”是徽州士商的一种重要品质,是促进徽州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连启元从儒、侠的角度,去理解《太函集》的徽州人物描写,认为这些人物传记在塑造徽州士商时,除了进行“儒化”,还可能掺杂着“侠客化”,而“侠客化”的思想背后,仍是遵照儒家思想的脉络而来。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汪道昆的《太函集》特别是其中的名篇《儒侠传》为讨论核心,集中关注的是徽州士商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对书中提出的“儒侠”概念及其背景也进行了初步探讨,但这些研究相对于徽商丰富的“任侠”文化内涵来说,还不够全面,依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笔者认为,“任侠”之风赋予徽商“侠”的气质,客观上会影响徽商的行为方式与商业活动,把握徽商“任侠”精神的另面,探究其“任侠”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走进徽商的精神世界。
一、贾而任侠:徽商易被忽视的另一种特征
侠的起源,前辈时彦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①见汪聚应.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3-48.。历史上,人们对侠的认识存在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批判到匡正的过程。法家韩非子在《五蠹》篇中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将侠与儒者、商工之民等列为扰乱国家的“五蠹”;班固在《汉书·游侠传》前序中视侠“罪已不容于诛”[5]1202,对其加以严厉的批判。最早为侠正名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既指出了古代以侠自命的暴豪之徒的种种劣迹,又较为公允地肯定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6],但具有一诺千金、杀身不悔、扶危济困、不图报答等他人难以企及的品行。司马迁的定位使侠一扫先前“原侠”轻薄狂放的沉疴积习,成为卓然特立、匡扶正义的英雄人物,触动了大众对于正义与公道的内在需求,而侠也成为世人仰慕和竞相效仿的对象,如我国秦汉与隋唐时期,慕侠尚气之风弥漫于整个社会,在任侠风尚的带动下,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多以“任侠自喜”。任侠,俨然成为一种“时尚”。任侠,在史书与典籍中一般也称作“使气任侠”“好气任侠”等,有附带意气,以侠义自任的意思。“任”代表一种精神观念和行为方式,《墨子·经说上》篇云“: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7],突出了侠的利他属性。《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5]卷三十七。任侠之士不仅急人所急,还要以自己的能力,如权势、勇力或财力等手段去辅助他人,从而将“任侠”这一行为从理论层面付诸实践,也正因为“侠”和“任侠”字面意义相近,学界常将这二个词混同,皆用来指那些具有好交游、轻生死、重诺守信等品质的人。
在我国古代,商人和侠虽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作为民间力量的存在,他们在以“诚信”“仁义”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涵上却有很多共通之处。郭沫若则直接认为侠出于商贾,他在《十批判书》中指出,“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若唯利是图便沦为市侩奸滑之徒,而商贾中有侠义心肠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8]。事实上,古徽州人也把“行商”看成是一种“侠行”。新安江氏族谱中记载了他们对行商的理解,“以故徽之贾于四方者,多磊落节侠之行,无市心”[9]。徽商虽身从贾业,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以儒学伦理和价值观来规范自身的言行;另一方面徽商作为市井之民,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热心公益,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以种种“义行”“善举”为民解难,为国分忧,具有“富而好行其德”的侠义精神,濡染了流传于民间的侠义精神。明清文人的文集中,有大量商人传记、墓志铭和跋序之类的作品②详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G].合肥:黄山书社,1985.,如出身徽商世家、历任朝廷和地方官的徽州籍学者汪道昆,不遗余力为商人作传,其《太函集》有商人传记112 篇,有70 余篇专为徽商而作,其中有相当的篇幅记述了徽商“好修任侠”“为气任侠”“任侠不羁”的事迹。《太函集》中多次将商人以“节侠”称之,称徽商为侠,不仅在于徽商转毂四方,弄潮商海“,挟一缗而起巨万”[2]卷十八的传奇经历,更在于他们对自由、自主生活和人生乐趣的追求都近于侠。“任侠”不但丰富了徽商的人文内涵,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
二、徽商“任侠”精神的内涵及表现
(一)豁达坦荡,豪侠不羁的个性
徽商在社会交往中,不但要组织和团结好自己的伙伴,还要交结与商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各方势力,由此锻炼出了慷慨待人、轻财重义的品质。休宁旧俗,“挟赀豪侠者,多往来达官贵人”[10]。徽商性好交游,倾心接纳官府权贵,结交士人,积极组织各种士人交游活动。明末休宁人陈太学,“为人意气自豪,善交游,海内名流恒欲得而交之,故座客堂满,樽酒不空,有北海之遗风焉”[11];盐商钟九皋“节侠名东海,至则诸贾更引以为重”[12]382,晚年厌倦商海,每日里结交侠少英豪,纵情声色之乐。扬州徽州籍盐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2]卷二。在侠游中,徽商一掷千金,自负狂傲、浪荡不羁,不拘礼法,展现出侠的豪荡之气。徽商的侠气还表现在为人的豪迈坦荡以及遇事的处变不惊上,休宁商人程兰谷,在大宴宾客时,有人告诉他“倭奴焚质库且尽”[13],他从容自若,询问人员伤亡情况,对财产的损失毫不在意,满座皆为其气量折服;婺源商人李贤“平生胸次脱略宏伟,不能为局促鄙琐之态,一日而得千金无喜色,一日而挥千金无吝容”[14]。休宁商人汪起凤,经商南陵,“辄以意气自命,持杯看剑外,绝口不道奇赢,同列甚重之”[15]。徽商的豁达坦荡集中表现其金钱观上,他们从事商业经营,不排斥追名逐利,却不屑于“设智巧、仰机利”“卑卑而取富”,认为大贾“当种德也”[16]。休宁商人汪寰,“生平阔达乐施,振人之厄”,晚年事业不幸破产,在大家为之惋惜时,他笑道,“财,身外长物也,丈夫负躯天地间,宁以此介介耶”,“萧然而归,曾不见有芥蒂意”[15]。
(二)见义勇为,兼济天下的襟怀
侠的作风有时放纵不羁,却不妨碍他们强烈的道德意识,历史上侠具有自由与兼爱的道义属性,具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精神品格。徽商侠贾尚气谊,好施予,常“救人于厄,振人不赡”[7]。婺源瓷商洪宗旷,泊舟鄱阳湖,有客商资本被盗,情急之下欲投水自尽,洪宗旷慷慨解囊,以百金相赠,助其度过难关[17];祁门药商倪前松,行医景德镇,“每视人疾,询其困乏孤寡不受酬”[18]。徽商守信重义,践行侠“损己利他”的行为准则,虽力不能逮,亦必全力以赴。光绪《婺源县志》载,婺源人王廷柏,性格豪迈不羁,经商致富,慷慨助人,“偶有一诺必践,凡属知交无不沾其余润者”,晚年千金散尽,身无长物,“而伉爽之概不减曩时”,在淮扬间有“王救贫”[19]卷三十一之誉;歙县商人江兆炯,为人“沉厚宽博,然诺不欺”,那些穷乏无以为生之人,纷纷来投靠,他无不设法相助。有人得罪权贵无赖,他主动为其排忧解纷,“自奉节约,而勇于信,坐是致困”,故闻君名,“咸以古义侠者流”[2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明清之际,天灾不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许多徽商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尽一己之力,拯济一方,把扶危济困、帮助弱小的侠义精神推向了极至。明崇祯庚辰年间,上海松江府发生大饥荒,青黄不接,饥民朝不保夕,歙县粮商吴午庆将船上几千石粮食全部捐出,赈济灾民,活人无数。顺治庚寅,常州遭水灾,他“治粥糜以蒿饥者,里之富人感公高义,相率出粟治粥,民赖以生”[21]。明清鼎革之际,扬州城破危在旦夕,为拯救城中百姓,阻止清军滥杀,祁门商人汪文德冒险去军营面见清豫亲王,献金三十万,换得“愿王下令勿杀”[22]的承诺。徽商兼济天下的侠义精神还体现在保卫乡里,赴国急难上,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一些徽商或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干脆弃贾从戎,杀敌疆场,如休宁商人程良锡,倭寇猖獗时,毅然弃贾从军,被任命为宣州指挥佥事,率军多次大败倭寇,成为平倭战场上的一员名将[13]。
(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魄力
徽州俗多负气,“男尚气节,女慕端贞”[23],每遇不平之事,“宁甘斗讼,好义故争”[24]。商人虽地位低下,但慷慨尚义,“独耻苟容,不受挫于强有力者”[2]卷四十七,不乏有强烈秉持公义,不惧强权的社会责任感[25],面对强暴,敢于挺身抗争。歙县盐商黄鉴,“矜怪好气任侠”,见商人们卑微渺小,常被那些刁悍无赖之徒欺辱,义愤填膺,上前直面怒斥,力挫其锋,令其“缩茳而退,不敢复作悍态”[16]。徽商自幼大多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强,当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敢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明末社会腐败,关津丛弊,一些官吏对境内过往的商人巧立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如九江关蠹李光宇等把持业务,“盐舟纳料多方勒索”,导致许多商船被迫停泊羁留在关外,翻船溺水之祸频发,商贾们敢怒而不敢言。歙县盐商江南能,毅然“叩关陈其积弊,奸蠹伏诛,而舟行者始无淹滞之患”[20]。万历年间,明神宗在全国各地派驻矿监税使,横征暴敛,导致多地百姓暴动。休宁商人金文耀,经商楚地,恰遇矿监税使搜刮钱财,激起民变,多人被牵连入狱,而首事者又已逃亡,他挺身而出,赴官府替他们申辩,其人方得释[26]卷六。康熙《休宁县志》载,休宁商人汪汝蕃,为人“倜傥有奇略”,举家定居扬州,总兵高杰为争驻扬州,大肆屠掠,汪汝蕃情绪激昂,冒死抵营劝说,终于使高杰怒气消解,扬州百姓赖以得安[26]卷六。
(四)不矜其能,谦逊低调的作风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古代侠客于名利最为淡薄,他们“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徽商行侠厚施而薄望,不张扬、不自喜,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在明清徽商的传记中,在记述徽商义行善举时,尤其会注意记录徽商事后的表现,于是“略无德色”“无德色”等记载屡见笔端,如明朝徽商王子承带领族人子弟入蜀经商,“分授刀布,左提右挈”,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各致千万有差,无德色”[2]卷十七,从不居功自傲。休宁西门商人汪洪,“乐善而亲贤,疏财而仗义,造福乡梓,有佐城筑、修桥道、构路亭、恤孤寡之功,虽以是迭蒙旌扁,无德色焉”[10];婺源人程开纯,经商稍有余裕,遇善举则倾囊资助,生平济人急,无德色[19]卷三十四。今天看来,虽有自我标榜的嫌疑,但也侧面反映了徽商对谦逊低调、淡泊名利的侠义精神的认同。事实上,徽商在侠方面的表现,不在于外在的武勇表现,更多是内在的精神与涵养,而不矜其能,温良谦恭的态度越是能博得侠名,赢得世人的敬重与赞赏。
三、徽商“任侠”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一)任侠是徽州尚武、负气风俗的传承
徽商任侠之风与徽州历史上“尚气好胜”“武劲之风”有着天然的传承关系。历史上徽州是山越生活的地方,山越人尚武好战,崇尚气力。此外,东晋南朝时期,南迁徽州的北方世家大族初来乍到,为站稳脚跟,用武力进行征服与开拓,并浴血捍卫,中原迁徙之民也逐渐养成了崇尚武力的风气。无论是山越人还是中原迁徙之民,这一尚武之风,一直被沿袭并传承下来,成为徽州突出的社会风俗之一,也成为宋代以后徽州人“武健自负”和“性刚喜斗”的性格基因[27]。
徽州在地理环境上,山环水激,俗多负气,这种尚气与武劲之风深深浸润在徽州人的血脉深处,激发了徽商务高奇节、负气不受非礼之辱的侠气。如明歙县人凌世明,边务农边经商,欲租东溪街古渡旁的房屋做生意。屋主嘲笑他,“田舍翁居委巷,力田亩足矣,何用此为,且余屋僦金,尔果有此大力乎”,公怒,遂止。且曰:“吾异日居街上,当先买此屋”[28],后家业丰盈,买宅果从此屋起,积至数十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徽商长途贩运,跋涉山川,奔走四方,“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26]卷一,江湖赋予徽商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冒险精神,沿途所见的不平之事,多少会让他们有种打抱不平的冲动。
(二)任侠以徽商雄厚物质文化基础为支撑
行侠不仅需要强烈的正义感,还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慷慨好施、仗义疏财,捐资兴教、修桥铺路、赈灾济贫无不需要雄厚的财力为支撑。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文化素质为行侠提供了物质和文化基础。徽商自幼大都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他们习律令、性喜讼,每遇不平之事,不惜斥巨资用以争讼。此外,徽州宗法制度强大,出于血缘、地缘的关系,为了维护本宗利益,“遇乡争讼,不啻身常之,醵金出死力”,且“不胜不止”[29],大有打不赢官司决不罢休的气势。休宁商人朱承甫,在淮楚间经营盐业,见朝廷派来的太监税使额外增加盐税,承甫倡义执言,揭发税使门下作奸犯科的行径,义正辞严,令税使哑口无言,无奈取消增加的盐税。众骇曰:“是何文弱儒生而撩虎头捋虎须,几不免虎口哉!”[30]朱承甫是一位出儒为商并具有侠气的人物,他义气凛然,据理力争,以“儒”的方式,维护了商人的合法利益,这也是商人儒侠不同于普通游侠的区别所在。
(三)任侠是徽商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自我表现
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造,任侠指向的已不仅仅是具有舍己为人、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等道德观念与英勇行为的特定人群,实际上它已积淀成为一种深层的文化观念和心理意识,其更多的扩展意义在于个人的一种精神追求、行为指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尚、民间风气。任侠在士人那里既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理想人生的追求,成为一部分文人性情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趣。历史上,士商身份地位存在等级的差异,在徽商的内心深处,经商致富并不是他们最高人生追求,读书取仕才是他们内心的终极关怀,于是包括任侠在内的士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徽商竞相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歙县《郑氏宗谱》载,郑方山弃儒为商后,“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完全是一派“儒侠”的打扮,世人认为其“虽商也,而实非商也”[31]。事实上,徽州人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丰南志》中,官员罗应鹤曰:“余观里父善富者,率以捃拾起家,其言义侠好施与者,徒豪举为名耳”[12]册五,由此可见,徽商建立在雄厚经济基础之上的侠游,不过是“交四方英杰,谒诸缙绅大夫”[12]册五的处世方式,这种交游或为攀附权贵,或为抬高自身以取信于人的公关目的,也是商人融入主流社会,赢得尊重与人望的必要手段[32]。
(四)任侠是徽商儒家人格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彼此之间既互相冲撞又互相融合,儒与侠之间存在着“侠出于儒”“儒侠同源”的先天渊源,如果对儒、侠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厘定的话,会发现它们之间在以“仁、义、勇、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准则上有其明显的契合之处,它们共有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某种程度上“儒侠互通”,儒就是侠,侠就是儒[33]。
徽商贾而好儒、贾而任侠,作为儒家文化和侠文化的实践者,他们身上兼具儒和侠的双重品格。徽商的侠义精神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许多徽州人弃儒从商,除了“治生”目的,还将经商提升到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度,以此寄托自己本想用于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歙县商人许太明,携赀商游西湖,击楫而言曰:“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34]正因如此,徽州商人虽置身于名利场上,但他们自觉地以儒家伦理来规范自己,甘为良贾、廉贾,在经营中“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在致富后,仗义疏财,解人之困、救人之难,积极从事当地事务,参与地方建设,以任侠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价值,达到儒家所要求的“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可以说,徽商任侠实质是其儒的思想的行为外化。
结论
综上所述,明清徽商除了显著的“贾而好儒”的特点外,还有“贾而任侠”的另面,在徽商的观念中,“行商”看作是一种“侠行”。“任侠”赋予了徽商豁达坦荡,豪侠不羁的个性;见义勇为、兼济天下的襟怀;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精神;不矜其能,谦逊低调的风度。徽商“任侠”之风的兴盛有着多元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在徽州尚气与武劲之风的熏染下,在雄厚物质文化基础的支撑下,任侠成为徽商显示人格,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自我表现,是徽商践行儒家思想,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徽商的任侠从表面看有侠的形式,但从思想意识、精神实质看仍以儒家为主,这种“内儒外侠”的形式,其实正是徽商身上儒与侠精神的复合与互济,这不仅揭示了徽商异于前辈的精神内涵,而且揭示了优秀徽商的可贵品质,提高了整个徽商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观照历史,徽商的任侠精神对新时代的商业经营者完善人格修养、践行社会责任、促进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侠义精神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