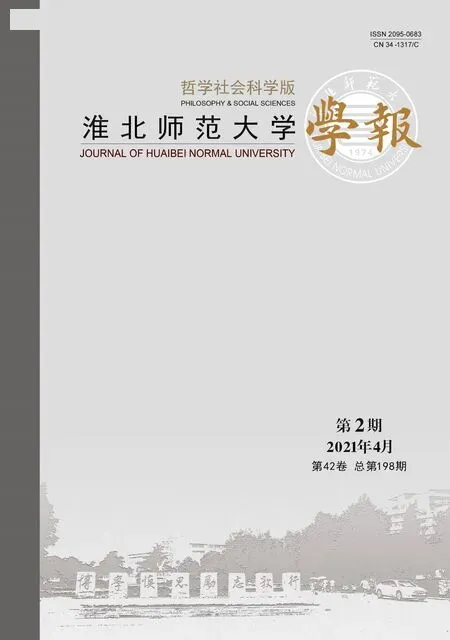《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儒家式生态伦理思想
金怀梅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088)
《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Life&Times of Michael K,1983)是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J.M.Coetzee,1940—)的布克奖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孤独的园丁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南非挣扎求生的故事”[1]。由于作品以种族隔离制度盛行下的南非内战作为故事背景,故批评家们的解读多聚焦其政治意蕴,将其视作对“南非畸形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寓言式表征”[2]。然而,主人公K 的园丁身份和其充斥全篇的园艺梦想似乎亦提醒读者:作品在政治议题之外有其生态关注。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该作品的生态内涵,但往往将其纳入西方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阐释框架内,认为“这部小说的生态内容是对政治状况的注解”[3],“具有明显的后殖民生态书写特色”[4]。这些研究论点鲜明,分析深刻,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欣赏该作品提供了崭新的维度,但亦不难看出,其仍然在政治框架下阐释生态内容,未能脱离“英语后殖民文学批评的狭窄范围”[5],未将生态书写视作库切独立的创作思想,忽视了其一贯的生态关注。毕竟,自创作伊始,库切就始终“把一颗担忧他类生命乃至地球生态环境的拳拳之心呈现于读者眼前,形成其独有的生态言说”[6]。
此外,文学文本往往是多种文化现象的结合体,尤其像库切这样横跨南非、英美和澳洲,同时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比较熟稔的跨文化流散作家,对其文本的解读可能需要超越西方文化和理论话语的单一视角和既定框架,方能展现其文本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并有望开掘出新发现和新价值。同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理应凸显中国视角和中国话语,“外国文学研究必然也必须有研究者的本土视角。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中国视角”[7]。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运用中国哲学文化研究外国文学,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因此,本研究尝试将儒家生态哲学建构为外国文学批评话语,用以观照《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对其生态书写作出中国化阐释,在展现文本超越国族和文化阈限的普适性生态价值的同时,彰显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儒家生态哲学在人与自然万物的价值关系上强调人的德性价值,“认为人的价值在于承继天地生生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8]。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加剧,学者开始转向中国智慧,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与观念资源,儒家生态哲学自此成为中外学界热衷探讨的课题,现已在哲学、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伦理学、文化与美学等诸领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但其与文学尤其是国外文学批评实践的整合研究则相对鲜见。本文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恩至禽兽”:动物纳入道德共同体成员
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将动物视为绝对客体,在人与动物之间构建起排斥性的二分法,儒家生态哲学视动物为道德共同体成员,要求“恩至禽兽”[9],主张人类承认动物的内在价值,爱护其生命,并与其建立情感联系。在儒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天地万物皆是禀气而生,因而有着内在的生命联系,构成自然界的生命共同体。这种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伦理导向作用,引导人类以“德性主体”身份规范自身的行为,并积极地对动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很好地体现了儒家式的动物伦理思想。
作为一名热忱的动物权利保护者以及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库切惯于在创作中揭橥人类对动物的暴行,将自己对人与动物之伦理关系的探讨内置于作品中,其动物伦理思想已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与赞誉。麦凯认为,“库切对人与动物之伦理关系的关注是持续和严格的”[10];奥尔森指出,“库切小说长久以来一直关注对非人类动物尤其是狗的地位的描述”[11];国内学者亦坚称,“库切是一位具有坚定、浓厚的动物伦理情怀的作家”[12]。尽管《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绝非一部动物伦理小说,然而,如同其他几部早期小说一样,库切在社会历史与政治议题之外不乏对动物伦理命题的涉猎。所不同的是,库切并非仅止步于对动物所受残酷遭遇的揭露,而是更进一步,将人与动物同构,旨在消弭人与动物的界限,从根本上质疑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并重构动物价值认知。
主人公迈克尔·K 是库切所有作品中最具颠覆性的人物,原因在于他的“动物人”形象。K 逃离战乱频仍的开普敦城,途中又不断逃离政府设置的营地,一心奔向人迹罕至的荒野,选择过动物般的生活。他自筑洞穴,像蠕虫那样爬进爬出,吃昆虫和植物的根,“好像他曾是一个动物”[13]126,“他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于在晨昏和黑夜中活动的动物”[13]141-142。同时,他逐渐变得依靠触觉和嗅觉而非视觉生活,靠触觉判断面前是否有障碍物,凭嗅觉知晓是否有雨天以及分辨各种灌木的不同。库切让K 成为德勒兹(Gilles Deleuze)哲学意义上的“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目的是还原宇宙中生命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在人和动物两种生物之间实现解域化,破除其固有的物种疆界,赋予人以动物的习性和感知,让其体会动物的感受和存在状况,并使二者的关系走向多种可能性。“生成动物在传统的‘人’和‘动物’的二元对立之间创造出一条逃逸路线,从而将人类的文化编码解域化,让人逃离‘(大写的)人’所规定的恰当的人类行为、感情”[14]。K 蜕变为动物他者,并非是消极意义的异化,而是承载了文本厚重的隐喻性符码和强烈的批判功能,在与信奉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哲学文化保持疏离和抗争的同时,暗合了儒家生态哲学所倡导的人与动物为一体的生命观,从形式上解构了人主宰动物的必然,为人类道德地对待动物提供生物学层面的注解和观念上的疏通。
K“生成动物”不仅表现在生活习性和生存状态方面,更是呈现在其内在的精神和情感认同上。动物类比充溢于小说全篇,K 视动物为亲密伙伴,积极地构筑起自己与动物之间的同伴物种关系。当在山峰中寻找地洞时,他认为自己“是一只在岩石中挖出自己前进之路的白蚁”[13]82;当从营地逃离出来,睡在一片灰色沙地上时,他感觉自己“好像一只不知道自己的洞在哪里的蚂蚁”[13]103;当感觉住所要被人发现时,“他觉得自己好像一只突然赤条条暴露在阳光下的鼹鼠”[13]130;当洞穴被洪水冲垮,身体淋湿透时,他觉得自己像“一只没有壳的蜗牛”[13]138-139;对于生活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他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在香肠中打瞌睡的寄生虫;好像一只伏在石头下的蜥蜴”[13]143;当被期待解释自己是谁时,他觉得自己“更像一只蚯蚓”或“一只鼹鼠”[13]218。已有个别学者对如此多的动物类比产生了兴趣,然而却未能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范式,认为“动物被隐喻性地用来描绘卑微/非人化状态”[3],将动物意象的使用完全视作库切为突出K卑微生存状态所运用的艺术手法。这样的解读不免片面,忽视了动物在作品中的主体地位,仅将其降格为人类的参照物。事实上,动物占据着文本的独立空间,远非K 生存场景的幕布。那些挥动翅膀发出沙沙声的“夜鸟”[13]56、急匆匆爬过地面的“甲虫”[13]72、发出嘤嘤嗡嗡声的“苍蝇”[13]83等微不足道的生命形式都悉数登场,成为文本伦理关切的聚焦点,有着和K 一样重要的存在。此外,K 逃离有床睡、有饭吃、有工作做的营地,执意奔向荒野,是其追寻自由、挣脱黑暗政治和动荡乱世的自发行为,荒野生活是其乐享其中的“桃花源”,远非卑微的生存之地。故而,K的动物类比更多的是出于对动物的怜悯以及对于动物的亲密感。库切不仅希望唤起读者对动物生存境遇的感知和关注,更是通过主人公人兽同体的居间状态引发人们对生命共同体的思考,继而道德地对待动物的生命权利和生存权益。
不可否认,在儒家哲学中,人可以使用动物。但儒家将人对于动物的使用置于天道之下,人不可滥用动物,这在著名的圣王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以及“禽兽以时杀焉”[15]、“钓而不钢,弋不射宿”[16]等狩猎限制中可窥一斑。小说中,K为饱腹猎杀一头羊,事后却懊悔不已,加上一个人消耗有限,导致吃不完的羊的尸体开始腐烂,这更加剧了他的自责,誓言以后“不要杀害这么大的动物”[13]71。他埋葬了羊的尸体,并自制弹弓,改为打树上的鸟吃。K 的做法彰显了与儒家一致的动物观:爱惜动物,对动物取之有度。正如泰格勒所言,K不杀大动物是因他“学会抵制人类统治动物的道德败坏的立场”,这样做才不“违背他的本性”[17]。
小说中,库切不仅设计人兽同体的主人公形象,模糊人与动物的界限,让主人公身处动物的境地感动物所感,想动物所想,与动物建立亲密联系,展示人与动物实为生命共同体的本质,而且主张儒家式的动物观:人可以为了生存的目的使用动物,但必须道德地、有节制地使用。
二、“恩及草木”:植物纳入道德共同体成员
在儒家哲学中,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同源,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员,因而,人与植物同样是生命共同体,植物亦应该是人的道德关怀对象。“和对待动物一样,儒家对待植物的态度也是尊重其生命,让植物完成自己的生命”[18]。尽管为了生存,人可以利用植物,开垦荒地,但是儒家主张对植物需节用、慎用,要求保护、珍爱植物。《诗经·大雅》中的“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19]、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0]以及阳明“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21]92等均能体现儒家将植物纳入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要求人类因着植物自身生命的完整性,而用道德的眼光和态度对待它们。为此,董仲舒强调:“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22]372。
小说中,K 表现出了与儒家生态哲学高度契合的行为。他热爱大自然、怜惜植物。他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中怡然自得,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自由,“达到了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状态”[17]。他醉心于耕种,对自己亲手种植的西瓜和南瓜无比呵护。他称呼南瓜为“我的孩子们”[13]79,把它们看成“亲兄弟”,把西瓜看成是“两姐妹”,甚至给刚长出来的两个西瓜铺上草垫,“这样它们的皮就不会受伤”[13]139。他无比感恩于大地的馈赠,在吃着那些“大地生产出来的食物”时,流下了“快乐的泪水”[13]140,显然,这种“吃南瓜的快乐不仅仅是一种生理行为,还包括一种与食物相关的情感方式”[17]。在K看来,人与大地上的植物同是大自然的孩子,所谓“物,吾与也”[23]。如此,读者便不难理解K对植物的亲密情感。
K 对母亲的埋葬方式同样呈现出他所具有的儒家式生态观。为了让“母亲重归(return)大地”[13]72,他把母亲的骨灰一点一点撒在土地上,然后一锹一锹铲土盖好骨灰。K采用这种播种种子的埋葬方式,一方面,恰如雷德尔所言,“‘return’一词的使用表明迈克尔视大地为一切生命的来源,包括他母亲的生命”[24],同时,这也说明,对于K而言,人与植物一样同为大自然的产物,故植物与人具有同样的生命价值,理应被道德地对待。K认为母亲在过完了地球上的生命周期后,“被吸收到 野 草 的 叶子 里去 了”[13]153,“她在 促 进植 物生长”[13]158。如此,库切激进地拆解了西方传统中“人是万物尺度”的大写“人”字观,将宇宙间生命的流动性范围扩展至草木,构建起人与植物之生命共同体。此举并非降低人的地位,而是提升同样拥有生命的植物之价值,将人的重要性从“人类中心”挪移到“人类主体”,倡导人类运用“德性主体”的身份去关爱伴随其生存的植物。
何止植物,K 甚至对无生命的大地亦珍爱有加。小说中,大地同样被纳入人类道德共同体。作为园丁的K将自己视为“土地的照看者”[13]140,尽管逃亡之路荆棘艰险,但他始终怀揣一包南瓜种子,随时伺机播种。其对种子和耕种的信仰源于其对大地的道德关怀,对大地生命力的执着追求,因为在他看来,如若耕种“这根绳索断裂了,大地就会变得坚硬”[13]135。小说中有个场景感人至深。当K看到士兵要在土地上挖坑时,顿觉心痛不已,他恳求士兵让自己挖掘,从而避免大地承受粗暴行为的蹂躏。K 对大地的同情共感让其无法忍受大地的痛苦,正如泰格勒所言,K 与大地“相互归属的神秘事实使他很难目睹暴力施加在大地上。他觉得大地的痛苦是他自己的”,而由他自己挖掘,“行动会温柔得多,不会造成伤害”[17]。
儒家倡导人类的关爱对象延括至鸟兽草木瓦石,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有情互感。《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展现了同样的生命情怀。库切赋予主人公K与草木及土地产生情感和心灵相通的跨种际道德联系,传达出人与草木及土地之生命具有相同本源的儒家式生态观,由此号召人类担负起对自然万物的道德关注和伦理责任。
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小说中,人和物均是库切的聚焦对象,动植物的存在形式和生命价值涵括在其伦理书写范围内,恰如有论者所言,“库切的政治伦理视野并不局限于人类,像动植物这样的微小生命形式与人类生命一样重要”[3]。库切以主人公K 为行为表率,不仅倡导人类应关爱和保护自然万物,更是为人类如何实现这一伦理目标提供了路径启示。
在儒家的生态论中,个体道德与生态道德是合一的,人的道德水准是实现生态道德的必要前提。儒家将其最高道德准则“仁”作用于自然万物,即所谓“仁民而爱物”。无论是董仲舒所言“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22],还是程灏、程颐主张“仁者,浑然与物同体”[25],抑或是王阳明号召“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20]91,均赋予“仁”以生态伦理之要义,将“仁”作为“爱物”的必备。如此,儒家构建起“仁”与“爱物”的直线联系。《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库切阐明了同样的关联,其试图揭示:人类的仁爱之心是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根本和关键。
K 背离西方“唯我”传统中人与万物主客二分的执念和生活法则,其在荒野中的生存方式是背离欧洲传统的,是反克鲁索的。他与“非我”融为一体,而非以占有为目的,恰如有论者指出,“这部小说以多种方式展现了迈克尔抛弃欧洲生活的特征,走向一种更具本土性的存在方式”[26]。亦因此,K被认为是库切所有作品中“与自然交流最为亲密的一个人物”[27]。而究其根本,K的行为源自其内在的仁爱之心。无论是其怜悯动物、埋葬羊的尸体、决意不杀大动物,还是爱护草木大地、与其建立情感联系,都出于对万物生命的尊重,是他“仁”心的外显和表现。对比农场逃兵垂涎羊群、欲将其变成盘中餐,以及士兵暴力炸毁土地、肆意破坏庄稼,K的行为令人瞩目,而有无仁爱之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和方式亦甚为清晰。如此,库切的伦理主张呼之欲出。如同爱德华·威尔逊针对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现象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拯救全球动植物的新策略,需从道德开始”[28],库切通过创作为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万物的紧张敌对关系提供解决思路,那就是身为“德性主体”的人理应修养心性,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界中的生命共同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伦理旨归,毕竟人与自然万物休戚与共,“因为使我们生长发育的‘气’,也是容纳木石禽兽于宇宙大化的生命活力”[29]。
除却仁爱之心,库切同样强调同情心在尊重并关爱一切生命形式方面的重要性,这与儒家提倡的“恻隐”之心如出一辙。如同仁爱之心,儒家的“恻隐”之心亦扩展至万物,人与万物皆是其作用对象。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30]218,他认为齐宣王不忍杀牛便是出于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30]14。王阳明进一步将恻隐之心的对象由人和鸟兽扩展至草木瓦石,将其视作是跨越人与天地万物之鸿沟的桥梁,是建立人与万物情感联系的纽带。库切传记作者坎尼米耶认为库切所有作品都弥漫着同情心[31]418,《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自然亦不例外,且这种同情心不仅笼罩社会最底层的人,也作用于被人类摧残的非人类他者。在K的旅途中,读者不仅跟随他的听觉“听”到了“绵羊的可怜的咩咩叫声”,也紧跟其视角“看”到了“车上的绵羊挤在一起,有些羊靠后腿立着”[13]43。一向惜墨如金的库切并未大肆描写卡车上待屠宰的羊群的悲惨境况,亦未发表任何议论和感想。然而,寥寥两句客观冷静的“闲笔”,看似不经意,却意蕴悠远。专注K境遇的读者被迫猝不及防地转移注意力,停下来留心思考运载车甚至其背后关联的养殖厂和屠宰间里动物的悲惨生存状况,并有可能在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动物的处境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有所反思和行动。
作为一名动物权利保护者和素食主义者,库切视动物养殖产业化为动物受苦的重要源头,认为人类“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停止以宰杀为目的的蓄养动物的行为”[31]601。因而在创作中,他毫不避讳展现养殖业的冷酷行径。譬如,《铁器时代》中,库切呈现了养鸡厂的暴力情境:工人们“扒出内脏清洗尸体,再把成千上万的尸体冷冻起来,成千上万的鸡头和鸡爪,几英里长的鸡肠子,堆积如山的鸡毛”[32]。这里,尽管叙述者话语客观冷静,然而,数量词的连续使用和鸡的碎片化展示揭示的是不计其数的鸡所遭遇的悲惨境况,唤起读者的怜悯之心,迫使读者将其与自己的餐桌饮食建立关联。主人公卡伦太太正是因为目睹了养鸡厂的状况,才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平日里制作美味佳肴的那些“鸡的胴体”竟然和鸡厂流水线上的“大屠杀”作业有勾连。同样,《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中,库切希望向读者揭露“动物—肉”之间的中间暴力场,让其明晰食肉行为的暴力本质,感同身受动物的苦痛,从而将自己对动物的同情转化为恰当的饮食选择。
小说中的另一场景描写具有同样的警示效果。库切细致描述K最初为果腹而猎杀一头羊的过程,羊的“惊恐”“抽搐”以及死亡的惨状让K 和读者尽收眼底,乃致K原先的“那种紧迫强烈的饥饿感消失了”[13]68,而“目睹”了被暴力残杀的羊的读者也不免经历了震惊、恶心、联想、同情和反思的心境。在库切看来,动物所受暴力的呈现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让其设身处地感受动物他者的痛苦,从而有所行动。在一次受访中,库切说道:“人类不可能洞悉动物意识。然而,通过同情,人有可能真切感受到动物的感受”[33]。在其另一部著作《动物的生命》中,库切借笔下人物科斯特洛传达出同情具有无限力量的观点,认为同情能让人“把自己想成蝙蝠、黑猩猩或牡蛎并能与它们共享生命之源”[34]。可见,库切认为,同情是人类消弭自身与非人类他者之物种界限以及心理疆域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构建人与动物乃至自然万物之伦理关系的重要基础。
库切通过创作为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提供了两大儒家式的伦理解决方案:仁爱与同情。这不仅是对环境科学、哲学、动物伦理学等学科所持的纯理性立场之局限性的补充,更是为人类在实践层面的伦理行动提供了有效指导和更大可能。毕竟,伦理道德的力量不可小觑,在处理人类重大难题方面,它具有理性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结语
库切的伦理书写不仅关涉人际关系、族群关系和国别关系,亦不乏对人类与非人类他者之关系的描摹。库切期望通过创作唤起读者对自身生存困境的反思、对自身与非人类他者之关系的伦理关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库切生态伦理书写的典范,恰如有论者所言,“《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特别强调文学的伦理潜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写作过程中建立起的与他异性关系的伦理潜力”[35]。小说展现了儒家式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同源,动物、植物、土地等一切“他异性”理应纳入人类道德共同体,成为人类关爱和保护的对象。同时,小说为人类的关爱行动提供了两大伦理方案,坚信仁爱和同情有助于人类跨越物种界限的藩篱,走向人与万物良性互动发展的美好彼岸。小说的生态书写与伦理主张丰富了其思想内涵,彰显了库切人文知识分子的伦理情怀,在当下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尤显珍贵。从儒家生态哲学视角重新审视该小说,既体现出其超越国族界限的普适性生态价值,亦为库切伦理思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内涵。小说的生态伦理思想跨越时空阈限,与儒家生态哲学相暗合,体现了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互为相通的精神旨趣,彰显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库切作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