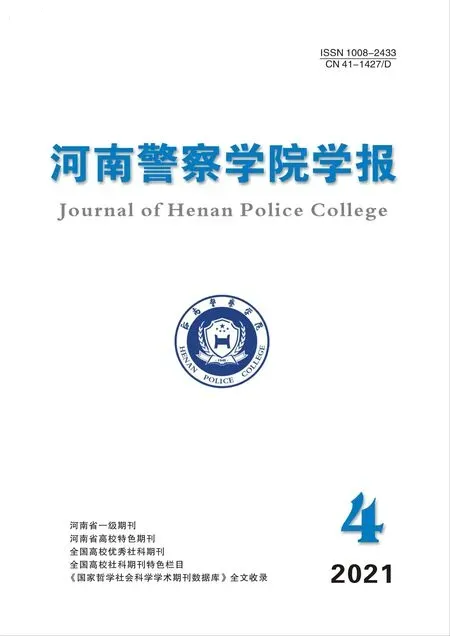黑恶势力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以文化冲突理论为视角
翟艺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黑恶势力的性质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黑恶势力都可被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换言之,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恶势力发展的最终阶段。这就意味着,两者在文化、组织构架、犯罪成因等方面具有共通性与相似性。由于“黑恶势力”这一概念并未在规范性文件中得到明确,所以,若要对“黑恶势力”的概念进行界定,还需对“黑”“恶”“势力”三个词采用解构的方式进行深入剖析。
(一)“黑”与“恶”的概念界定
黑恶势力之所以被冠以“黑恶”之名,其原因有三点。一是,黑恶势力通常都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式呈现,而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可以被定义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以暴力和贿赂为主要手段,具有组织机构的层次性、组织功能的分解协调性、组织指令的规范性和组织成员的稳定性、组织形态由低到高的有序性的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系统。”[1]在此基础上,黑恶势力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基本上可以做同质化理解。另外,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恶势力团伙发展的高级阶段,二者前后相继,生长轨迹呈线性形式[2]。
二是,在黑恶势力中,对“恶”字可以进行双层递进式理解。其一,“恶”是“善”的相反概念。在社会一般人的认知中,“恶”会触及每个具有同情心与正常道德素养的社会人的道德临界点。在“恶”的理念指导下采取的行为,大多会触犯社会的统一道德规范,并且会对人的权益造成各种侵害。其二,“恶”并非局限于道德层面上的判断,还可以将其上升为刑法的高度。在刑法层面上,“恶”主要侵害人身、财产等专属性法益,也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政治稳定等造成侵害。
(二)“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征
“黑恶势力”一词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恶势力犯罪。1995年后,“黑恶势力”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于市场经济监督管理领域与社会治理领域[3]。在2009年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中,国家首次将“黑恶势力”这一概念纳入法律规范文件中,并且明确“黑恶势力”即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随着扫黑除恶的逐步深入,“黑恶势力”一词被理论界、实务界广泛接受。笔者认为,可将“黑恶势力”的特性类型化为内在关联性、外在逐利性、行为共生性、共同危害性四部分。
其一,内在关联性。“黑恶势力”内部均具备一定的组织性,并且通过发展组织内部的底层人员,不断向外部延伸。“势力”便是根据上述发展路径,在一定的区域内逐步形成的。“黑恶势力”可在共犯体系之内解决,其组织规模较大并极具稳定性。其组织内部具有较为严密的层级划分与分工,组织内部各个层级之间呈金字塔型。实务界认为,“黑恶势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犯罪,其涉案人员至少为三人或三人以上。在犯罪组织中,参加人员承担的角色并不相同。如果案件由多人参加,并且形成较为固定的组织,也可将之称为犯罪集团[4]。
其二,外在逐利性。对于非法经济利益的追求,是黑恶势力犯罪的最终目标。其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主要通过以下几种行为手段:一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经济利益,如收取保护费、敲诈勒索、绑架等;二是通过非法经营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如高利放贷、开设赌场,或搞套路贷等。
其三,行为共生性。“黑恶势力”犯罪大多通过暴力手段或以暴力相威胁等方式进行犯罪活动。“黑恶势力”的成员在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时,具有一定的暴力性。换言之,黑恶势力组织的罪犯通常在犯罪动机、主观目的、实行行为等方面具有共同性。在多数黑恶势力犯罪中,上级对下级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明示或默许,其犯罪行为具有共生性。
其四,共同危害性。“黑恶势力”的活动范围限定在一定的区域或地域内。在合法社会控制力量弱化的地方,非法社会控制力量就会滋生[5]。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自然区域或行政区域内,非法社会控制力量会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黑恶势力的社会危害行为一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固定的区域及一定的行业内采取暴力等手段侵害公民的权益,或者垄断某一行业;二是对一定区域内的行业采用非法手段进行控制;三是黑恶势力对一般的民众实施一定的心理强制或非法的威慑控制。
二、对黑恶势力“文化”的解读
(一)黑恶势力“文化”的产生
“文化”一词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从其广泛的人种史的意义上说,是将知识、信仰、艺术、伦理、法律、风俗囊括在内的,是包括一个人掌握的任何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6]基于此,可以用文化的抽象性特征解读社会中发生的各类现象,并且对其根源从特有的文化视角进行解读。文化是社会的特有存在,从社会存在可以反推出个体在文化中的位置。即,个体的文化形成于其社区历代相传的生活模式与准则。从个体独立之时,其所处的风俗就在打磨与塑造个体的经验与行为。到个体具有辨别能力时,其便能成就自身文化且参与其中。而这种被参与的团体,便是具有同质性的个体的集合。因此,从个体出发可将文化总结为历史与当下全部信息的沉淀与累积。在群体与组织内,文化的共同指向性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生活在社区中的个体大多处于同等阶级,其教育、经济水平、生活模式更为一致。在社区之外的社会中,则存在着不同等级的阶级,根据默顿的失范理论,社会中的每个阶级的文化目标与规范化方式不尽相同。
在以群体为单位的黑恶势力组织当中,也会构建出特有的“文化”。黑恶势力组织的形成绝大部分具有自发性。这种自发性通常伴随着黑恶势力组织成员之间人格及行为的相互影响,这种互动对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黑恶势力组织成员并非被动,或被强行灌输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而是自发、主动地接受黑恶势力组织特有的“文化”观念。
在黑恶势力组织中,由于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一致性,所以个体会存在一种默认此行为标准的心理倾向。换言之,个体通过群体对外采取相同的行为方式,他们会逐渐产生趋于一致的判断与认知。这种一致性,在每一次群体活动中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从而导致个体自觉接受群体行为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个体往往将群体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等作为自己的参照标准和榜样,加以认同和模仿[7]。个体与个体之间也会在心理方面、行为顺从方面产生相互作用。这样一来,黑恶势力组织通过个体的互动,确立了一定的标准,继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规范。
(二)黑恶势力“文化”的规范作用
作为个体,人生来便处于文化当中,并且天生具有接受与选择关于自身及与他人关系的知识的禀赋。从其接触社会初始之时,便开始了漫长的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由来自环境、他人的训诫或者教导,加之自身的领悟与学习,人们便会汲取及接受各种正式或非正式途径传播的观念。若将这些观念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要素,便是文化要素。个体都对这些文化要素存在着正常(顺应)或异常(反抗)的回馈与反应,并且经由这些方式制定出自己认同的文化规范。因此,社会中只要存在人的集合体,就必然有行为规范的存在。换言之,行为规范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不是哪一个规范集团的创造物,它们也不附从于任何政治界别,它们的表现形式也不局限于法律规范的形式[8]。
个体需要通过黑恶势力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满足自身的安全。同时,长期的团体生活与共同行为成为维系组织成员之间契约关系的纽带。这一纽带不仅使成员的认知、意识、行为判断的差距缩小,更使得组织成员产生了对团体利益的认同。黑恶势力组织的特有文化规范不仅能够填补个体成员在主流社会文化中的满足感与存在感的缺失,更能够在获得组织高层的赞赏后,进一步增长对组织的认同。犯罪组织成员无一例外地在犯罪组织中得到赞赏、满足、安定的正面感觉[9]。
三、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文化分析
(一)文化规范冲突的根源
规范是为个体行为提供的范式与参照构架。文化规范,意指在一定状态下某一类型的群体遵从的特定的行为方式与共同承认的行为规则。也可以说,文化规范意指生存于某一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在特定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何种标准采取行动的规则。规范冲突即为,生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群体产生的行为与认知上的差异。
塞林提出的“文化冲突”概念,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文化分析具有重大意义。塞林认为,文化冲突产生于社会变迁之中,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但是变迁中衍生出的犯罪定义与法律分类不足以应对极具动态性的犯罪现状,所以,二者皆不足以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基准。因此,应当重新确定一个更具普适性的基准,从而可以将行为规范的任何变化囊括其中。塞林认识到,在犯罪定义中反映出的法律标准,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人为与专断的标准;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忽视了与“一般社会利益”相冲突的其他重要社会行为[10]。塞林提出的文化冲突这一概念,即为社会范畴中相悖于主流文化的其他文化。文化冲突与犯罪的关键区别在于,文化冲突下产生的行为是否踏入刑法设定的中线之内。这一判定标准的根据在于,刑法是社会的主流文化规范,并且将社会的主流文化整体呈现于法律规范之中;犯罪行为则是与此类社会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现象。
黑恶势力组织成员不遵循社会主流文化,将黑恶势力的文化观念及内在固有的规范显现于外在行为之中。多数黑恶势力组织的文化规范与社会主流文化规范的产生与构成方式存在差别,黑恶势力组织的文化规范基本上建构于社会主流文化规范的对立面。换言之,黑恶势力组织以消极态度对待社会主流文化规范,且不承认社会主流文化规范的正确性。
黑恶势力组织的犯罪文化存在两类相悖于社会主流文化规范的需求,一是与传统合法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相反的行为方式,即,黑恶势力组织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二是黑恶势力组织需要在社会主流文化之中实现,并且黑恶势力组织实施犯罪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当犯罪人把“挣大钱”作为自己价值体系的核心时,他们是在遵守而不是僭越社会规则[11]。获取财富这一要素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中的关键要素。黑恶势力组织以获取财富为首要目的,实际上便是对主流文化目标的认同。只是其获取财富并非依靠制度性手段,而是采用了与社会常规性制度手段全然不同的方式。
(二)黑恶势力对主流文化规范的否定评价
犯罪以一种非法的形式存在着,或者说,犯罪这一现象在人类的特定历史时期总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犯罪现象集中表现着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是社会矛盾在各类生活场所中的凸显。犯罪是犯罪人基于其感情的行为判断和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囊括了犯罪人从事犯罪的原因与欲望。需要指出的是,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种种要素,则与犯罪人所处群体的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可以借用犯罪人所处群体的文化背景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解读。其一,犯罪行为是孕育于文化之中的社会现象,若要对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深入探究的话,必然离不开对犯罪文化背景的分析。其二,如果仅仅对文化及背景进行浅层了解的话,也不会读懂犯罪原因的深层含义,换言之,犯罪问题必须要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深层解读[12]。不论哪一类社会群体,其文化目标的确立都是以这个社会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念为基准,同时以规范性的制度(法律规范)设定来作为达到文化目标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则将能够最为有效达到文化目标的方法排除在外(如犯罪)。当社会中的成员都能够接受社会统一价值观念所形成的文化目标,并能够采用合理且合法的制度性手段将文化目标予以实现时,便不会产生紧张情绪从而避免引发社会越轨行为。反之,当个体无法应用合理且合法的制度性手段达成文化目标时,就会出现目标与手段失衡的情况,进而引发个人的紧张情绪,并使行为处于失范状态。大多数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成员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初期,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此类紧张情绪,并且其实施的行为多会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反复跳跃。但由于黑恶势力组织具有集团性,这一特性便会将成员因实施越轨行为而产生的自我怀疑与愧疚等情绪进一步消解,导致其向黑恶势力的文化观念逐步靠拢。
塞林认为,可以将刑法视为行为规范体系中的一种,且其为禁止的行为规范。同时,刑法也列明了违反禁令的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惩罚方式。刑法规范的特征以及其所规定的禁止行为的类型或种类、惩罚的措施与方式,都取决于社会中对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的集团的特点[13]。人类作为个体,生来便处于文化当中。同时,人类天生具有选择和他人建立何种关系的禀赋,从其在接触社会初始之时,便开始了漫长的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由环境、他人的训诫或者教导、自身的领悟与学习,人们便可以汲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观念。对个体而言,大多存在着正常与异常的反应方式,这类反应的判断标准就是群体制定的规范。只要有社会集团的存在,便肯定伴随着行为规范的存在。极端地说,行为规范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不是哪一个社会集团的创造物,它们也不附从于任何政治界限,它们的表现形式也不局限于法律规范的形式[14]。上述规范为个体的反常行为提供范式与参照构架,文化冲突便是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之间的冲突。它们是文化生长与文明生长过程中的副产品,有时被认为是行为规范从一个文化复合体或区域迁移到另一个文化复合体或区域的结果[15]。而上文中所提及的刑法规范与行为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其会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其中,刑法中有关犯罪的定义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地域中更是存在定性层面的差异,这事实上是不同的社会阶段中社会规范与行为规范相异的体现。
亚文化都是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换言之,亚文化根植于主流文化之中,其产生却代表着主流文化的反向延伸。黑恶势力组织成员不仅普遍认同社会主流的文化目标,并且其在进行犯罪活动以外的日常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仍然遵循着主流文化的目标与规范性的制度。这是因为黑恶势力组织成员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具有趋向性。规范性制度如果能够对黑恶势力组织成员实现文化目标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组织成员便会遵循这一规范性制度手段;倘若制度性手段不能使其实现文化目标,那么组织成员就会否定规范性制度从而采取其他能实现文化目标的手段。
黑恶势力组织成员将自身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内在合理化,并且将自身认同的价值观念进行中和。而后,组织成员对于法律规范的认同与否,是决定其在主流文化与组织文化冲突时进行选择的关键要素。因为法律代表着主流文化规范,如果组织成员积极地对法律规范进行否定,抑或是对法律产生消极认同的态度,都会导致组织成员与主流文化相背而行。与此同时,此类成员便会以黑恶势力文化为主导,继而实施犯罪行为。其中,也有组织文化认为,作为主流文化规范的法律是“非法”的,这里的“非法”意指组织成员对文化规范的全面否定。换言之,黑恶势力组织成员对于组织文化的认同度远远高于主流文化,并且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便是将此类组织文化的思想外化于具体的行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