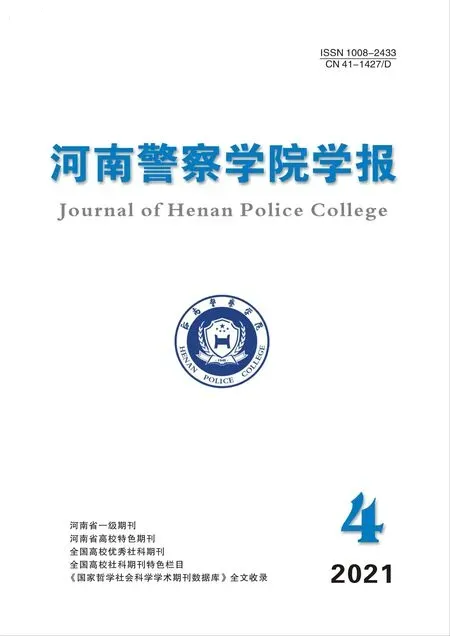警察酌情决定权和中国的恢复性司法
——基层警察的故事
张 彦(著),万 立(译)
引言
恢复性司法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运动,改变了世界各地人们对犯罪和冲突的理解和应对方式(1)Johnstone, G., & Van Ness, D. W. (2007). The meaning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G. Johnstone & D. W. Van Ness (Eds.),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pp. 5-23). Willan.。恢复性司法在基础理论上有别于其他司法模式(“报应”模式和“改造”模式),它将犯罪视为对人和关系的侵犯,而不仅仅是对法律的侵犯(2)Bazemore, G. (1998).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earned redemption communities, victims, and offender reintegr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1(6), 768-813.。在理想的恢复性司法中,罪犯和受害人之间有权通过沟通确定如何进行补偿(3)Johnstone, G. (2002). Restorative justice: Ideas, values, debates. Willan Publishing. Zehr, H. (1990). Changing lenses: A new focus for crime and justice. Herald Press.。有人认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多样化和规模最大的恢复性司法计划(4)Braithwaite, J. (2002).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sponsive reg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oke, K. (1987). Politics and values of medi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Mediation Quarterly, 17, 69-82.。但是,对比西方同行现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有关中国的恢复性司法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有所不足。中国各地公安机关每天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调解,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我们试图通过研究这些基层警察的调解故事来改变这种寂静状态。派出所是(中国的)一线警务机构,每天处理中国社会中的大量纠纷和冲突。它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同时容纳人民调解、治安调解、刑事和解三种调解模式的机构。因此,调解程序在中国地方派出所的实施是一个缩影,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中国恢复性司法的“庞大”与“多样”。
为了解恢复性司法在中国公安机关的实施情况,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警察在三种调解制度中就调解案件的选择和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协议这两个问题如何使用酌情决定权。本文采用了利普斯基的基层行政机构理论(SLB)和威尔森的警务组织形式理论的概念框架,运用基层行政机构理论对中国一线警察日常调解工作进行概念分析,描述了一线警察在面对庞大的调解工作量和其他复杂的调解工作时,如何运用酌情决定权作出决策。本研究还参考威尔森的警务形式,分析了“群众路线”原则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并认为这是理解中国警务的关键,也是影响中国警察决策的组织因素。基于2016年在中国某地方公安机关搜集的访谈和观察数据,本文认为,一方面,中央政府正在地方警察系统中推行恢复性司法制度,这符合威尔森警务组织形式的混杂性。从基层来看,中国警方在选择调解案件时,坚持以“社会安定和谐”作为至关重要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一线警察在主持调解会议和促进利益相关方之间达成协议时,培养了应对复杂情况(如案件数量和绩效评估)的战略判断力。因此,基层行政机构理论推进了中国的恢复性司法改革,并支配着参与恢复性司法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在中国警察自由裁量权与恢复性司法的相关文献。
一、基层行政机构和警察酌情决定权
利普斯基的观点极大地改变了公共机构的传统概念,对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该观点认为,法律的实施取决于服务提供者和目标人群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和权威决策的目的相吻合(5)Sees 5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5(4).。这种自上而下的观点被批判为将实施过程视为一个完全的行政过程,忽视甚至无视环境和关系因素(6)Berman, P. (1978). The study of macro and micro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olicy. Public Policy, 26(2), 157-184. https://doi.org/10.1177/009539979102200404 Van Meter, D. S., & Van Horn, C. E. (1975).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6(4), 445-488.,并专门强调政策制定者是关键实施者(Matland, 1995)。相反,利普斯基强调自下而上的权力,并将基层行政人员的酌情决定权和判断作为政策执行的核心要素。
基层行政人员是指警察、社会工作者、教师和其他直接接触群众的一线公职人员(7)Lipsky, M.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3.,他们工作条件具有挑战性。在日常工作中,基层行政人员必须对服务需求做出反应,而服务需求往往会超过供给。同时,他们只有有限的资源或时间来做决定(8)Maynard-Moody, S., & Portillo, S. (201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theory. In R. Durant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bureaucracy (pp. 252-27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和复杂的情况,基层行政人员在工作中运用了一定程度的酌情决定权,发明了一套应对手段(9)Lipsky, M.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14.。 利普斯基认为,酌情决定权是政策分析和执行的核心,因为“……他们(基层行政人员)建立的常规路径,以及他们发明的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和工作压力的手段,也成了他们所执行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10)Lipsky, M.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 xiii。因此,法律的正式表述和愿景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书本上的法律”和“实践中的法律”的概念中(11)Goldstein, H. (1963). Police discretion: The ideal versus the re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3(3), 140-148. https://doi.org/10.2307/973838。
警察作为一种典型的基层行政人员,其酌情决定权被大量研究过。然而,关于警察如何决策,特别是在恢复性司法制度中如何决策的研究并不多见。韦斯特兰(Westmarland)等人发现,在处理家暴案件时,警察对男性罪犯的惩罚更为严厉,并且容易将女性罪犯转介到恢复性司法程序。在对恢复性司法相关案件的研究中,大家更多地关注警察酌情决定权的组织决定因素。斯图尔特(Stewart)和史密斯(Smith)的研究表明,服务式的警官比法治式或看守式的警官更有可能将少年犯转介到恢复性司法程序。根据斯托克代尔(Stockdale)的研究,如果一个警察局的绩效文化很强,尽管上级批准使用恢复性司法程序,但一线警察还是会倾向于侦查。为有助于系统地解释警察酌情决定权如何影响恢复性司法的实施,我们的研究还将利用威尔森的警务组织形式的优势。
组织的决定因素是管理形式,更普遍地说,它们是约束和指导官员行为的基本原则。威尔森(1968)提出了三种警务组织形式,即存在于地方警察局的看守式、法治式和服务式。根据威尔森的类型学,如果警察认为维持治安的目的是维持秩序而不是执法,那么警察组织往往是一种看守式的组织,同时他们强调“判断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不是根据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描述,而是根据其直接的和个人的后果”。坚持法治式的警察则认为,严格执法是重中之重。对于这种警务类型,逮捕是处理所有犯罪的首选方法。警察的表现是根据与执法有关的活动来评价的,例如成功逮捕的人数。服务式的警察机构则注重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务,强调以居民满意度为中心的组织目标。服务式的警务在解决不严重的问题时优先考虑非正式的、非逮捕的替代方案。因此,这类(服务式的)警官坚持社区警务的原则。下一节将对当代中国警务的组织维度进行背景分析,这一分析建立在对不同调解程序的研究上,旨在解释警察在调解工作中的酌情决定权。
二、深入理解当代中国警务
(一)从“群众路线”到社区警务
社区警务的概念是在2002年从西方“传入”中国的(12)Zhong, L. (2009).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na: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Police Practice and Research, 10(2), 157-169. https://doi.org/10.1080/15614260802264594。中国社区警务被认为是扩大警察基础设施以覆盖最底层民众的政策。中国社区警务可以定义为以“群众路线”为主导原则,以预防犯罪为重点,以非正式邻里网络为依托的地方化控制价值观(13)Sun, I. Y., & Wu, Y. (2010). Chinese Policing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1978-200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6(1), 20-35.。 “群众路线”原则要求警察与人民保持亲密关系;警方应优先考虑社区服务,并与居委会和其他非正式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动员他们参与犯罪控制(14)Chen, X. (2002). Community and policing strategies: A Chinese approach to crime control. Policing and Society, 12(1), 1-13. https://doi.org/10.1080/10439460290006646。另外,非官方的宣传为满足市民的需求,实行了“四有四应”。在机构上,街道一级民警被派往当地派出所,协助居委会调解家庭矛盾、社区内违法违规等纠纷(15)Chen, X. (2002). Community and policing strategies: A Chinese approach to crime control. Policing and Society, 12(1), 1-13. https://doi.org/10.1080/10439460290006646。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在提高警务系统的法律地位和执法能力(16)Fu, H. (2005). Zhou Yongkang and the recent police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8(2), 241-253.。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犯罪率不断攀升,中国警方不得不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这一趋势。犯罪控制乃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预防性巡逻和快速部署警力应对犯罪事件机制在中国得到推广和加强(17)Cuvelier, S. J., Jia, D., & Jin, C. (2015). Chinese police cadets’ attitudes toward police roles revisited. Policing, 38(2), 250-264. https://doi.org/10.1108/PIJPSM-09-2014-0101。另一方面,以责任制的方式对中国警方打击犯罪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保障(18)Wong, K. C. (2002). Polic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oad to reform in the 1990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2(2), 281-316.。简言之,警察的绩效评估是根据诸如逮捕率、结案率和被起诉罪犯人数等统计指标进行的。这些指标在决定警察晋升、绩效工资和嘉奖等方面至关重要。财政激励和责任制是激发警察提升绩效、服务和动员群众的关键机制。
总的来说,中国警察系统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服务式社区警务和以“打击犯罪”为重点的法治式社区警务,很可能是并行不悖的,当代中国警务制度中的基本原理是共生的,这些基本原理对警察调解的实施应该具有共同作用。
(二)维护社会稳定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动荡(19)Trevaskes, S. (2009). Restorative justice or mcjus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 Farquhar (Ed.), 21st century China: Views from Australia (pp. 77-96).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Tanner, M. S. (2004).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7(3), 137-156. https://doi.org/10.1162/016366004323090304Pei, W. (2014).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n China: Consequentialism in history,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China-EU Law Journal, 3(3), 191-221.。群体性事件被视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威胁。因此,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2006年,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方针、目标和原则。
在基层,绩效评估体系变得极为关键,根据“一票否决”规则,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会影响对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等各方面的表现的评价,影响其在奖金、晋升(机会)和单位竞争组织荣誉等方面的资格。来自维护稳定、解决社会问题的行政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的警务人员承担的(20)Fu, D. (2017). Disguise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4), 499-527.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15626437。
三、书本上的恢复性司法:警察局的三种调解程序
由于基层官员的酌情决定权可以用“书本上的法律”和“实践中的法律”来描述,本节将简要介绍法律所规定的三种调解方案,然后详述基层警察的实际执行情况。
人民调解机制是化解群众矛盾、第一时间防止轻微矛盾升级为严重犯罪的根本机制(21)Deng, Y., & Xu, K. (2014). Strategy to motivate and facilitate compromise in Chinese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5(1), 4-20. https://doi.org/10.1108/IJCMA-11-2011-0076。然而,直到2010年《人民调解法》颁布,第一个规范人民调解机制的国家法律制度才得以建立。2018年,人民调解案件总数达到953万件(国家统计局,2019年)。《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对话、协商等方式,为民事纠纷利害关系人自愿达成协议提供便利的一种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农村的村委会或者城市的居委会建立起来,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并没有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警察介入民事调解工作的唯一法律依据是1995年的《警察法》,该法规定,当人们寻求纠纷解决时,警察应当提供帮助。此外,“四有四应”方针是警察日常执勤的原则。民事纠纷中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报警,也可以直接找派出所进行调解或通过其他办法解决,警方有责任作出回应。
治安调解立法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时。《条例》规定,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违反治安管理而不触犯刑法的案件,情节轻微的,警方可以主持调解。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替代了《条例》,正式确认了治安调解的法律地位。2007年的《公安机关治安调解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治安调解是由公安机关主持,通过劝导教育,促使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自愿达成协议的机制。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作为一项特别程序纳入其中(第五部分),共有三条。这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颁布刑事案件调解法,这是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开创性时刻(22)Braithwaite, J., & Zhang, Y. (2017). Persia to China: The silk road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2(1), 23-38.。新《刑事诉讼法》严格界定了刑事和解的范围:因民事纠纷引发的犯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或者过失犯罪,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渎职罪除外。公安机关(警察)、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人民法院(法官)负责主持和解会议,审查最终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当利益相关者达成协议后,警方可以向检察官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检察官可以建议法官从轻处罚,如果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决定不起诉嫌疑人。法官可以对罪犯从轻处罚。
四、方法和数据
这项研究是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中有关中国恢复性司法的一部分。作者于2016年在重庆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查,在此过程中,采用了自然建构主义方法,因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重要但未预料到的问题,如样本量的变化、新的研究问题和数据收集过程的调整,等等。 “关系”(个人网络)作为获得中国访问数据和参与者信息的重要渠道(23)Xu, J. (2016). Criminologizing everyday life and doing policing ethnography in China. In M. Adorjan & R. Ricciardelli (Eds.), Engaging with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pp. 154-172). Routledge.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支持。作者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的政法大学,这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并保证了数据收集过程的顺利进行。
该博士研究项目始于2012年全国开始广泛实施刑事和解制度之际。那时作者开始采访一些关键的线人,问他们一些“广撒网(net-widening)”的问题,如“你是否认识促成了刑事和解的人?”或“我是否有机会观察和解会议?”然而,他们的回答令人失望。基本上,刑事和解的执行率远远低于新法规定的执行率,因此,2012年的恢复性改革被认为存在阻力。笔者便以“抵制”为核心主题,通过滚雪球的采访方式,采访了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这使笔者越来越沉浸在研究课题中。总的来说,研究进展相当缓慢,直到笔者遇到了某区派出所的副所长。他告诉我,他们没有多少刑事和解案件,但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民调解和治安调解案件。然后我被安排到基层公安机关,收集了三个指定调解方案的人种志数据。
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系”来获取数据。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会改变研究趋向,并引发一些额外的问题(24)Liang, B., & Lu, H. (2006). Conducting fieldwork in China: Observations on collecting primary data regarding crime, law,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2(2), 157-172. https://doi.org/10.1177/1043986206286918。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受访者告诉我,他们在实施调解时严格遵守了法律。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可能在追求社会理想(25)Callegaro, M. (2008). Social desirability. In P. J. Lavrakas (Ed.), Encyclopedia of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他们喜欢将自己想象成忠于法治的形象,并拒绝接受我的负面评价。为了验证这些发现,我们使用了多种数据资源来保证交叉检验。我在派出所调解室呆了2个月,观察调解案件的过程。在调解前后,我还与警方调解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在食堂与警察的随意交谈也是我的数据来源。这种三方测量方法(26)Mertens, D. M., & Hesse-Biber, S. (2012). Triangulation and mixed methods research: Provocative position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6(2), 75-79.生成和比较不同类型的数据,调查不同受访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对研究主题的深入了解,提高了研究的有效性。
在整个博士研究阶段,我采访了15名警察、6名检察官、5名法官和4名律师。此外,还收集了40起调解案件。我的编码策略是从一个开放编码模型开始的,通过将访谈记录和现场笔记(来自访谈和观察)输入NVivo。编码遵循三个基本程序:(a)注意相关现象,(b)收集这些现象的例子,(c)分析这些现象,以发现共性、差异、模式和结构。最初的代码是根据诸如一个术语、一个句子或一个案例之类的信息创建的,这些信息可以捕捉到警察对执行调解方案的抵制的想法和理由。然后,我的重点转移到特定的问题和概念,这些问题和概念包含了警察在选择案件和促成协议时应对复杂性和巨大工作量的核心思想。为了完善这些想法,我也通过这两个镜头选择性地重新读取和重新编码数据。
五、实践中的恢复性司法——调解还是不调解
a) 案件量视角。“有困难, 找警察” 在中国人中是一个流行的口号。中国社区警务的这种服务取向,深深植根于“群众路线”原则,其宗旨是建立密切健全的警民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需要,任何人都可以拨打“110”寻求警方协助,这已成为一种常识。警方必须对大多数电话作出回应,其中许多是非警务问题和恶作剧电话。自1986年中国在广州建立第一个“110”系统以来,“110”电话逐年增多。1996年,这个数字是522万。据公安部统计,2016年(1月至11月)“110”平台共接到1.29亿个电话,其中公民救助案件2670万起,交通肇事案件8248万起,刑事案件1990万起,治安案件148万起。与此同时,中国的警察公民比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每万名公民中有12名警察,这还不到全球平均值30/10000的一半(Xu, 2018)。因此,越来越多的案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某派出所是中国大规模基层警察系统的一个缩影。一份内部报告显示,2016年7月至12月,该所调解室共立案203起,其中民事纠纷调解71起,治安调解107起,协助调解125起。但这些数字不能充分反映实际工作量,因为许多民事纠纷都是在现场处理的,许多治安案件甚至未经登记就进行调解。一位警官解释说:
我们派出所每天能接到60-70个紧急电话。其中只有3-4起是潜在的刑事案件,3-4起可能是公共秩序案件,大多数是非警务电话或恶作剧电话。尤其是“四有四应”政策出台后,这些日常琐事确实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占用了我们的时间。
面对大量的民事案件,中国警方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最常见的是将决策责任转移给其他人员或机构,以节省时间和资源(27)Lipsky, M.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147。在大多数观察到的民事案件中,警方对利益相关者的开场白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你们相互间可以自由协商,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可以自己直接去法院起诉,然后让法官来做决定。民事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责任范围。
中国警方可以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执行从罚款到拘留的行政处罚,这赋予了他们比西方国家警方更大的酌情决定权(28)Lai, Y. L., Cao, L., & Zhao, J. S. (2010).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entity on confidence in legal authorit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5), 934-941.https://doi.org/10.1016/j.jcrimjus.2010.06.010; Ma, Y. (1997). The police law 1995: Organization, functions, powers, and accountability of the Chinese police.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 Management, 20(1), 113-135.。这也成为警方避免民事纠纷案件过量的一种手段。
与民事案件调解一样,治安纠纷调解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周末晚上,某区派出所的警察一般要处理7到8起涉及醉酒男性的打架事件。然而,与民事纠纷不同的是,警察确实依靠治安调解来减轻工作量,特别是打架斗殴的小案件,构不成犯罪。正如一位官员强调的那样:
如果所有的治安纠纷都是通过刑罚方式处理,我们就要调查现场,收集证据,采访证人,写一页又一页的文书。即使我们不吃饭,也很难全部都结案。太累了!即使我们把案件都搞清楚了,结果也只是拘留5天或罚款500元。
“群众路线”原则确定了中国社区警务的服务式组织方式,并转化为基层警务人员的巨大调解工作量。随之而来的工作压力培养了中国警察的常规(工作能力)和策略,使他们优先考虑减少他们在选择调解案件时的工作量。然而,调解工作本身既是要避免的工作量(人民调解),又是警察管理额外工作的策略(治安调解)。
b) 绩效评估很重要。以服务为导向的“群众路线”原则在中国社区警务时代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方式得以复兴。从理论上讲,中国警察在提供服务和作出决定时,不需要通过定量服务来获得公民的服从。然而,观察和访谈数据显示,绩效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警察是否调解的决定,财政激励和责任制是激发警察绩效、服务和动员群众的关键机制。简单地说,中国警方(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每年都要成功地起诉一定数量的犯罪嫌疑人,以证明他们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根据斯托克代尔的研究,如果警察局的绩效文化具有影响力,尽管上级批准使用恢复性司法,但一线警察仍会诉诸侦查,这也是中国地方警察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绩效评估对中国警察决策的影响是微妙的,这取决于不同调解方案的性质。
如果一个案件被确认为轻微刑事案件,并且符合新的刑事和解法规定的刑事和解条件,那么它可能会与警察绩效评估产生冲突。
与检察官的补充面谈也反映了警方的理由。正如一位检察官所说:
我承认我们的不起诉决定会对警察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他们的工作评估可能会打折扣。
调解轻微刑事案件与组织目标相矛盾,但不一定会引起警察对和解的抵制。一方面,如果利益相关者选择和解,在警方充分准备起诉后最终达成协议,警方也会有所考虑。正如一位警官所说,警方在文件工作、证据收集和证人面谈方面的许多努力的效果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检察官也可以调解轻伤案件。因此,这位警官还提出了以下顾虑:
如果我们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直接起诉一个轻伤案件,那么检察官就有可能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调解此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就是浪费时间,我们也得不到绩效。
激励机制、价值冲突、检察机关的决定等因素对警察的决定起着相反的推动作用,最终使警察对轻伤案件的处理程序化。通常,警方会主动要求利益相关者在一开始就愿意和解。如果他们拒绝或未能达成协议,那么警察的动机就会改变。警方希望从那时起对此案提起公诉。
绩效评估对警察以不同方式处理其他两种调解方案的合理性有影响。对于民事调解和治安调解,警察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调解工作不会带给他们任何功劳。在民事纠纷中,警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顺其自然,因为他们既可以将决策责任移交民事法院,也可以在前面提到的某些案件中通过行政制裁来避免增加案件。对于治安案件,警察既不能通过调解也不能通过制裁来得到好处,而是依靠治安调解来减轻工作量,节省时间。正如一名警官抱怨的那样:
治安案件不存绩效评估,所以我们倾向于调解这些案件“群众路线”原则强调中国警察作为向公民提供调解服务的传递者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警务系统的职业化,以“打击犯罪”为核心的法治警务作风盛行,警察工作受到绩效指标的激励。然而,根据不同的调解方案,法治式警务对中国警方调解案件选择的影响是复杂的,可以是积极的(治安案件)、中立的(民事纠纷)或消极的(刑事案件)。
c) 维护社会稳定势在必行。“和谐社会”重构了相关法律和司法的内涵,如2006年的决议所述:“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2010意见》),重申了这一议程的重要性,刑事司法系统以此对“和谐社会”的要求作出了回应。
简单地说,《2010意见》的核心思想是“对一些重罪酌情从重处罚,对轻微罪酌情从轻处罚”(29)Li, E. (2015). Towards the lenient justice? A rise of ‘harmonious’ pen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0(4), 307-323.。在新的“平衡”思维的“严厉”一端,对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严重犯罪仍然实行“严打”。在“宽大”一端,包括调解和刑事和解在内的宽大手段适用于社会影响较小的案件或不可能危害社会的罪犯(30)Liebman, B. (2014). Leniency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Everyday justice in Henan.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3(1), 153-222.。
各种调解法的立法依据可以用“民事纠纷”和“轻微影响”两个术语来阐述。首先,“民事纠纷”和“轻微影响”是三部调解法立法的基本标准。人民调解是民事纠纷的调解;治安调解是指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违反治安管理的、影响轻微的案件,不适用刑法;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影响轻微的犯罪,规定刑事和解。“自上而下”立法的理由也深深植根于基层官员对调解方法的看法。当被问到“你认为什么样的案件适合调解”这样的开放式问题时,所有举报人都强调“民事纠纷”和“轻微”,并或多或少地解释如下:
对于凶杀、纵火等严重故意犯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犯罪人进行严厉打击,而对于因邻里或熟人之间日常纠纷而造成的轻伤(有伤口或骨折)案件,我们更倾向于调解。
挑拨离间、寻衅滋事等事项,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故不设调解。而人与人之间因民事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主观恶意较小,可以为其主持调解。之后,利益相关者可以再次成为朋友。
“民事纠纷”和“轻微”也是警察在决策时的基本工作范畴。“民事”和“未成年人”案件的基本考虑是“社会稳定”。我采访了一名派出所教导员,他解释说:
最近,我们接获至少四宗扰乱城管执法的案件,如果我们不严厉打击这种现象,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干预行政人员执法,攻击他们,而事后只需要支付经济补偿。这将是对政府权威和社会稳定的挑战,远远不是一场小小的民事纠纷。
以下案件涉及警方对法律的类似解释:
西瓦(SYW)海鲜市场的两家餐馆在争夺生意,一家餐馆的工作人员偷偷地把碎玻璃和钉子扔在另一家餐馆的人行道和停车场,刺穿顾客的汽车轮胎。恶性竞争最终升级为群殴,造成两人轻伤。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他参与人未经调解就立即被拘留。随后,警官向我解释说:
“这个案子不像是一场简单的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对市场有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应该严厉打击这一现象,以遏制任何进一步的不健康竞争和负面后果。所以不允许调解。”
在中国,不同调解法中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影响”都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标,它定义了调解的范围并指导警方做决定。这个范围之外的问题被视为对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威胁,因此可能引起警察更多注意。在这种形势下,即使调解法规定了调解,调解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六、协议的便利化
如果案件走上调解之路,利益相关者的最终协议便成为警察工作的头等大事,效率和秩序的维护是警察工作的主要考量因素。否则,对于民事案件,纠纷双方会一次又一次地到派出所去,如果他们的纠纷得不到解决,甚至会引起一些麻烦。对于治安案件和轻伤案件,如果不能迅速解决,警方可能不得不诉诸行政处罚或起诉,如前所述,这将耗费大量时间,但不会给警方的绩效考核带来多少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拥有很大的酌情决定权来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协议。
在一些有难度的案件中,警察会利用一些手段,快速、有序地让利益相关者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特别是在一开始,当利益相关者激动、愤怒之时,警方会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定量提供服务,并控制调解对象,以最低成本(31)Lipsky, M.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促成他们的和解。
控制调解对象以使他们遵守程序是最典型的选择。在调解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总是复述事件并就细节进行辩论,这很容易让当事人感到不安,有时会导致进一步的言语和身体暴力。为了加快进程,避免情况变复杂,警方通常会打断讲故事的过程,并强调,“不要再提那些问题了,我看过你的笔录,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重复这些话对解决问题没好处”。然后,利益相关者通常会停止复述故事,并迅速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警察还会对利益相关者做工作,以使他们更加配合。一位警官介绍说:
当利益相关者不理智或不愿意达成协议时,我团队的同事会跟我合作。一个看起来很凶的人会对利益相关者说:“你们要么达成协议要么上法庭,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家!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其他同事会耐心而温和地解释为什么调解能带来好处。有时,我的同事们会一个接一个地用不同的音调和术语来强调同一点,然后利益相关者会认为这一点必然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警察都这么说了。
如上所述,警方确实会通过控制调解对象(利益相关者)应对调解过程中的复杂性,以达成协议。然而,过度使用就变成了愚蠢的应对策略。布雷思韦特(Braithwaite)强调,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警官不至于愚蠢到想要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支配调解过程,否则,他们将面临增加额外工作的风险。不难想象,在某些情况下,警察的控制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不信任、担忧和进一步的不合作,然后,警察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促成一项协议。因此,有经验的警察会运用他们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操纵,来促成协议。
第一条准则就是不要引起利益相关者的担忧,以为警察可能对他们有偏见。大多数警察告诉我,他们不想在调解中表现得太热情。否则,争论的一方会怀疑警方是否从另一方拿好处。那案子就很难继续了。
基层行政机构表示,在一个社区长期稳定地指派同一名警察可能会助长警察的偏见行为,然后可能会导致客户投诉、不合作和不信任,这将进一步恶化工作状况。这也是目前中国警务的一个现实(Sun et al., 2018)。一位律师分析说:
警察长期在一个社区居住和工作,他们可能对一方比另一方更熟悉,这会引起利益相关者对警察工作的担忧和不信任。
警察调解员对这个问题也很敏感。一名警官描述说:
在调解前或调解期间,我不会接受任何被调解一方提供的香烟,否则,另一方会怀疑我们是否有私人关系或交易,这将使调解更加困难。
动员作为“群众路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警察促进调解会议的另一个策略。警方有时会邀请有关第三方协助沟通或劝说争议双方。一位警官提到:
在两个学生打架的案例中,我们邀请了他们认识的老师,随后调解顺利进行。
在另一个案例中,主人打了她的保姆,因为她认为保姆偷了她的钱。受害者被鉴定为轻伤。警官发现房东在感情上非常依赖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一位大学教授,警方认为他应该更加理性。随后,警官动员丈夫安慰并劝说妻子解决问题。
有时候,警察的个人经验和个性比他们的专业精神在调解中更能发挥作用。我采访的警官们的专业背景从生物学到商业管理等各种各样,只有少数人以前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或调解培训。警察们通常不使用法律,而是使用语言、幽默和个人生活经验来促进沟通,鼓励和教育利益相关者达成协议,无论是民事、公共秩序还是刑事案件都是如此。
在一起公共秩序案件中,警方调解员说:
即使是非常大的冲突也都可以通过谈判和对话来解决,为什么你们这点日常琐事就不行呢?你们的冲突不要再升级了,否则,唯一的赢家就是收取医疗费的医院。
在主人伤害保姆的案件中,警官发现主人习惯性地不耐烦,因此,这位警官一再提到她是个好主人,因为她通常在保姆做完家务活后一起分享蛋糕和水果。警官的表扬慢慢地软化了她的态度,让她承担起责任。
结论与讨论
斯图尔特和史密斯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式或看守式的警察相比,服务式的警察更倾向于选择恢复性司法机制。这一结论在中国也相当有效。然而,中国的地方警务系统同时容纳了威尔森的三种警务组织形式,且这三种形式正以明显微妙的方式指导中国警察对不同类型调解做决定。“群众路线”原则在中国社区警务中得到了哲学上的强调和战略上的贯彻,应该有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然而,现实中,理想化的“为群众服务”给中国基层警察带来了很大的调解工作量。此外,中国警务的“打击犯罪”理念将绩效考核和责任制放在首位(32)Dutton, M. (2005). Toward a government of the contract: Policing in the era of reform. In B. Bakken (Ed.), Crime, punishment, and policing in China (pp. 189-233). Rowman and Littlefiel Publishers.,对民事和公共秩序案件,并没有规定绩效评估。刑事和解更为复杂,因为起诉对象、案件性质和检察官的“风险”共同造就了警察在选择案件时的酌情决定权。
“看守”理论是警察决策中的重要决定因素。中国警察依靠法律规定的类别(主要是“民事纠纷”和“轻微影响”)来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相当实际的基层酌情决定权,最重要的就是“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对于这一类的案件,警方的酌情决定权用于对付案件的海量和案件的复杂性。然而,对于可能升级为进一步威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案件,警方将更加重视,并使用更多的强制干预措施。
阅读中国当地警察的实地报道可以发现,其与利普斯基的基层行政机构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由于民事诉讼案件量大,警方已通过移交人民调解决策责任的方式制定了策略。对于公共秩序案件,警方的决定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作出的。一方面,中国警方可以利用其对行政处罚的高度酌情决定权,将民事案件转为治安案件,然后迅速拘留罪犯,而不是主持人民调解。这可以减少工作量。另一方面,治安调解本身就是一种避免治安案件的惩罚过程耗时费日的策略。当案件进入调解程序时,警方总是希望利益相关者能够迅速达成最终协议,因此,他们制定了定量提供调解服务和控制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对于那些激动和愤怒的利益相关者,警方会施加心理压力,促使他们配合,以迅速达成最终协议。同时,警方也会避免过多参与和操纵,因为这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不信任和不合作,从而愚蠢地带来额外的工作。相反,警察利用他们的语言、幽默和个人生活经验来促进沟通,鼓励和教育利益相关者,或动员必要的第三方参与,以软化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促进协议达成。
总之,当今中国的恢复性司法是由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普遍的国家法律改革所形成的,这些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路径依赖(33)Zhuo, Y., & Cao, L. (2016). Intended and actual use of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66(5), 507-523.,这为恢复性司法运动创造了一个比西方对标国家更大的制度空间。中国恢复性司法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